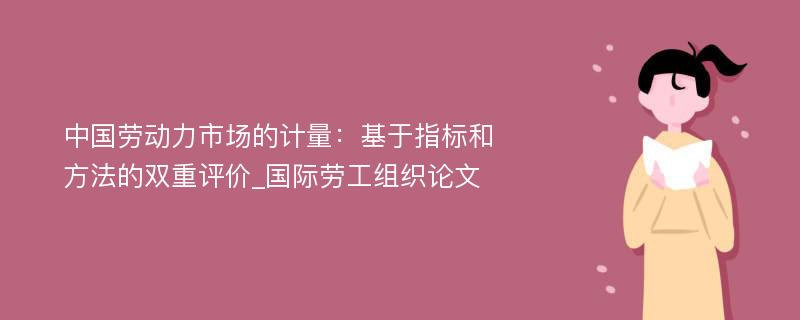
中国劳动力市场测量:基于指标与方法的双重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测量论文,指标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有赖于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测量,而对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测量依赖于科学的指标结构与恰当的方法选择。对劳动力市场测量有效性的评估可从测量指标与测量方法两个方面进行。国际劳工组织早在1985年的劳动统计大会上通过的第160号劳动统计公约中提出了劳动统计应覆盖到的主要内容①,并在随后的国际劳动统计大会决议中分别制定了针对不同统计内容的标准和原则以及具体的指标设计等更为完整详尽的信息。这是衡量我国劳动力市场测量指标体系完备性的重要标准。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共性还使得发达经济体成熟的劳动力市场测量的“最佳实践”可作为评价我国劳动力市场测量的参考依据;另外,我国特殊的国情使得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我国独有的问题,劳动统计指标也应当能够客观而准确地反映出我国特殊的劳动力市场现象,这是评估我国劳动力市场测量体系的另一原则。特别重要的是,国际劳工组织对不同国家统计发展水平的划分使我国能够在更广泛的国际比较中明确中国劳动统计发展的现状,明确应采取的完善措施。在国内的劳动力市场测量研究中,这些方面并没有得到系统的关注,特别是在测量指标结构的评估领域。
一、劳动力市场测量的价值定位
劳动力市场测量体系的构建取决于其价值定位。劳动力市场信息在衡量宏观经济状况,监测劳动力市场正常运行,有效规划人力资本及制定劳动政策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②。随着国家工业化程度加深,工作结构的复杂化及生产技术的多元化,发展一个正规的劳动统计体系也变得日益重要起来③。从最一般意义上看,劳动力市场测量不仅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状况,而且反映了整个宏观经济状况;并且,由于劳动力市场直接涉及劳动者的利益,因而对个人选择、家庭福利与社会稳定也至关重要。劳动力市场测量的主要目标便是通过辨别出经济中有没有为国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的部门来判定既定的国民经济状况,为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的预测提供最重要的定量基础,从而有效地制定并评估经济政策④。更进一步,劳动力市场测量不只是起到“衡量”的功能,它还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组成部分,这一点可以从欧盟委员会为配合“里斯本战略”的实现而选择制定的结构性指标中得到清晰体现。欧盟确定2000-201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为:“成为世界上最富竞争力的和最有活力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出更多和更好的工作并实现更强的社会整合。”⑤欧盟委员会制定了一组结构性指标作为实现此战略目标必需的基础。这一组指标从就业、创新与研究、经济改革和社会整合等方面全面刻画了欧盟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并深刻地反映出欧洲经济发展中的特点与瓶颈,构成其区域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背景下,从全球视角来了解和把握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力市场也变得日益重要。因此,劳动力市场测量还为各个国家在有效的国际比较中判断与衡量本国劳动力市场状况以制定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在劳动力市场测量体系中,测量指标与测量方法是实现其价值定位的两大支柱:合适的方法确保“正确地测量”,而合适的指标则保证“正确的测量”,因此,基于指标与方法的双重评估是劳动力市场测量评估的基本前提。测量指标结构始终是劳动力市场测量的核心。国际劳工组织在1985年的第160号劳动统计公约以及第170号建议书中均提出了劳动统计应覆盖到的主要内容⑥,包括经济活动人口、就业、失业、显性的就业不足;工资和工时;消费价格指数;家庭收入与支出;职业伤害和职业病;劳动生产率。针对不同统计内容的标准和原则以及具体的指标设计等内容也不断被国际劳工组织所完善。在此“一般性”的基础上,反映一国劳动力市场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的“特殊性”信息均应有适用的指标来测量。就劳动统计的数据来源而言,劳动力市场测量的方法有多种,最主要的方法包括人口普查与家户抽样调查、企业调查、行政记录。每一种测量方法均有其独特的优势与局限性。家户调查往往能够覆盖到更广范围的人口群体,所得到的劳动力数据也较为准确;然而,由于家户调查的样本往往不是足够大,以至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估计上的偏差。企业调查最主要的优势是被调查者能够提供可靠的工资和有酬雇佣的数据,也能够提供较准确的未填补的职位空缺的数据;但是同样,抽样方法的使用使得对群体的估计往往存在偏差,而且被调查企业的样本往往只能够很好地覆盖大型企业,而对小型企业和未注册的企业则不具有代表性。最后,行政记录在理论上是很好的劳动统计数据来源;然而,在实际中往往存在着行政登记的覆盖面小(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行政记录中的数据所依据的概念、定义和分类与国际统计标准不一致等问题⑦。因此,没有哪一种单一的测量方法能够满足所有的劳动力市场测量需求,测量方法的选择应取决于具体指标的特点,二者的恰当结合是构建全面与完备的劳动力市场测量体系的基础。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测量的指标结构
一个完备的劳动力市场测量指标体系是全面勾画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前提。我国现行的劳动力市场测量指标体系涵盖了国际劳动组织第160号劳动统计公约中提出的劳动统计内容的绝大部分。在就业统计方面,我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包括有经济活动人口指标,就业人员数目及其地区、行业、职业、企业类型的分布,就业人员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就业身份、户籍性质的结构性指标;在失业统计方面,除了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登记失业率以外,我国1999年及以后年份的《劳动统计年鉴》中均增加了关于城镇失业人员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失业前所属行业和从事的职业、失业原因及寻找工作方式的结构性指标。从2004年开始,我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增加了对城镇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统计。在工资方面,我国历年均对各种类型的单位进行详细的就业人员劳动报酬统计。此外,我国的劳动统计中还覆盖到了消费价格指数、家庭收入与支出、职业培训与技能鉴定、劳动争议、劳动保障监察、社会保障和工会工作等方面的指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状况。⑧
然而,基于一个劳动力市场测量的价值定位以及国际相对成熟的测量标准与测量实践,我国劳动力市场测量指标的结构体系还相当不完善。这个指标结构的重大缺漏之一是劳动力参与率指标。作为测量劳动力市场供给行为的一个最基本的指标,劳动力参与率反映了劳动力市场活动的水平,以性别和年龄组分类还反映出一个国家经济活动人口的分布情况⑨。劳动力参与率是影响就业和失业周期变化规律的重要因素,因此,把就业、失业和劳动参与率三者同时研究,不仅对理解劳动力市场规律大有帮助,也对宏观经济反周期的政策制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⑩。然而,在我国的劳动统计中,劳动力参与率却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我国虽然早在1994年的《劳动统计年鉴》中发布经济活动人口的资料,但至今没有精确的劳动参与率的资料。因为我国的经济活动人口不仅包括16岁(法定年龄)以上的就业与失业人口,还包括16岁以下实际从事工作的就业者,这样就无法准确计算出16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11),进而也无法依据性别和年龄等指标分类统计劳动参与率,而这恰恰是准确理解一国劳动供给状况不可或缺的信息。
另一个重大缺漏是我国劳动力市场测量体系中尚未有对城镇非正规部门就业的统计。非正规部门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就业和收入创造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早在1993年,第15届国际劳工统计大会通过了《关于非正规部门就业统计的决议》,确定了非正规部门的国际统计定义、操作定义、数据收集、指标设定等方面的内容(12)。对非正规部门就业的统计不仅可以更真实地反映就业状况,还有助于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核算的完整性(13)。在我国,非正规部门就业自1978年来一直在增长,并且仅在1996-2001年间,非正规部门就业与单位就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之比从大约1:4提高到超过1:2的水平。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主要方面(14)。值得注意的是,非正规部门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大量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与“城市贫困”现象。199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表明,下岗人员中有80%以上属非正规部门就业和非正规就业(15)。目前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虽然已掌握了关于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的统计资料,然而,对城镇非正规部门就业的统计在我国仍然是一项空白,使得劳动力市场的真实状况无法得到准确把握,曾经一度出现了统计上的“分总不合”现象——即分单位类型统计的就业人员之和与城镇全部就业人数之间存在较大差额,这个差额部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扩大,到2002年达到9642万人,超过了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就业之和,占全部城镇就业的39%(16)。非正规部门就业测量指标的缺失造成了劳动就业统计数据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反映严重失真。
“显性不充分就业”指标是我国的劳动统计中的第三项缺漏,这一指标早在1985年国际劳工组织第160号劳动统计公约中即已提出。不充分就业的数据对于就业和失业状况的统计是一种有益的补充。该数据可以提高对与就业质量相关问题的解释,也可以评估为促进充分就业而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现有人力资源的程度,还有助于更好地对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规划问题进行设计和评估(17)。已经有学者指出,对于低收入国家,对不充分就业的测量甚至比对失业的测量更为重要(18)。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尽管存在着较低的失业率,但这往往是由于这些国家缺少缓解失业的项目所致,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未必真的有效率。在我国,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产生了大量的企业富余人员和下岗职工;另外,我国的农村地区还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不充分就业”在我国相当普遍,约占到全部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此高的比例在国际上也属罕见(19)。这就使得在我国劳动统计中增加不充分就业的统计项目成为必需。第16届国际劳工统计大会通过的《关于不充分就业和不恰当就业状况测度的决议》中指出,对不充分就业的测量是劳动力测量框架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0)。我国在1995年确定了不充分就业的统计定义,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对“不充分就业人员”的判断标准仍存在较多的分歧(21)。在历年的《劳动统计年鉴》和《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中都从未出现过关于不充分就业的统计。我国《劳动统计年鉴》从2004年起增加了对城镇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及工作时间构成的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有限的与工作时间相关的不充分就业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劳工组织为促进各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比较并促进区域劳动力市场发展而制定的“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体系”中,劳动力参与率、城镇非正规部门就业以及与工作时间相关的不充分就业均是重要的指标(22),对不同国家劳动参与率的比较对于深入探究劳动供给行为,有效制定有利于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政策都富有重要的意义。而城镇非正规部门就业与不充分就业状况的测量都为了解劳动力市场中的“不正常”状况而设定,这些状况往往是就业和失业指标所无法涵盖的(23)。在我国,由于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不成熟,恰是这些“不正常”的现象相当普遍,因此是准确了解劳动力市场状况不可缺少的方面。而这些指标在我国劳动统计中的缺失不仅给了解劳动力市场的真实状况带来了困难,还阻碍了我国对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国际比较的参与,对探究解决问题的原因和借鉴相关的国际经验等都带来了困难。
上述三项指标均是从劳动供给角度提供相关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但是,作为反映劳动力需求的主要指标,“职位空缺”也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高质量的职位空缺数据是描述劳动力市场动态机制的不可或缺的指标,能够反映特定地区或特定职业的劳动力需求水平,并为劳动力短缺状况提供了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指标。西方国家对职位空缺数据的收集自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24)。美国劳工部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时期就开始进行实验性的项目来检验收集职位空缺数据的可行性。1961年,美国总统经济委员会在评价就业和失业统计时,高度强调了收集职位空缺数据的重要性,强烈建议系统性地收集职位空缺数据使之服务于实际操作、政策管理和经济分析(25)。国际劳工组织也将“未被填补的职位空缺的数目与特征”作为劳动统计的基本内容之一(26)。当前,美国劳工统计局开展多年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Job Openings and Labor Turnover Survey,JOLTS)便很好地提供了全国范围内的职位空缺的月度统计数据。英国国家技能专门组(Skill Task Force,STF)自1999年开始的“雇主技能调查”(Employers Skill Survey,ESS)提供了全国范围内的职位空缺(包括难以填补的职位空缺和与技能相关的职位空缺)的水平和影响因素的全面而详细的信息(27)。在我国,加强对职位空缺的测量与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在今后的若干年内,扩大就业一直是我国政府的战略重点,这就要求从劳动力需求角度来把握就业岗位的数目及其变化趋势和特点。另一方面,在我国当前各层次的技术人员短缺,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短缺的背景下(28),作为测量这种短缺范围与程度的标示性指标,职位空缺数据的收集能够很好地服务于制定缓解当前的短缺问题的政策的需要。当前,我国的职位空缺调查的研究工作刚刚起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信息中心以及中国就业培训指导技术中心从2001年开始每季度公布全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但是这些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鲜有有关测量的信度和效度的研究分析报告(29)。
在根据国际标准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测量体系以满足劳动统计指标一般性标准的同时,一国的劳动统计指标还应当准确反映出特定国情下的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是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党的十五大前后,我国大规模实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方针,带来了“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给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压力。我国的劳动统计中针对这一现象有着较为全面的反映,自1995年起,原劳动部建立起季度的下岗职工统计,国家统计局在1996年的劳动统计年报中也增加了“下岗职工”统计指标。在同年的城镇住户劳动力抽样调查中有更详细的“下岗”统计指标(30)。《劳动统计年鉴》自从2003年开始逐年统计下岗再就业中的困难群体“4050”人员,即40岁以上女性和50岁以上男性下岗职工人数,体现了政府再就业扶持政策的重点。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下岗问题的出现也给我国原本就不完备的就业失业统计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外学者广泛质疑我国官方公布的城镇失业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认为其没能够反映出大量城镇下岗职工存在的事实(31)。我国对下岗职工的统计曾一度与失业的统计分离开来,影响了失业统计的客观性。同时,由于对下岗人员的就业状态的认定存在种种分歧,也曾出现了社会上不同部门对全国职工下岗形势判断差距甚远的现象(32)。因此,对当时的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情况缺乏客观的数据描述。在1996年劳动力调查制度建立之初,下岗人员仅被分成两类:对符合失业定义的下岗人员作为失业人口统计,对不符合失业定义的下岗人员则全部按就业进行统计,这种统计口径的划分显然过于粗略。从1997年起,对下岗人员的统计开始完全依照其实际的就业状态——就业、失业和非经济活动人口——进行划分,统计口径较以往趋于规范与合理了(33)。
继我国城镇出现大量下岗职工的问题之后,青年失业问题构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又一严峻挑战,而其中又以“大学生就业难”最为突出(34)。目前,我国关于大学生就业状况的主要统计指标是就业率,由教育部每年对外公布。但该指标并不能客观地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反映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如将主动不就业者也统计为失业,并且没有包括未签约就业的毕业生,因此需要按照事实就业状态来建立对高校毕业生的统计指标(35)。同时,就业率这一指标仅能反映出大学生就业的数量情况,没能够涵盖大学生就业的质量问题。在美国,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统计指标除了总的就业率以外,还包括工作稳定性、劳动报酬、工作满意度、工作与专业相关度等指标,是对毕业生的就业数量和质量的综合评估。相比之下,我国现行的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的指标则显单一(36)。由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校的教学质量和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状况的适应性,因此,全面地掌握大学生就业状况成为指导高校教学水平调整、专业设置以及及时满足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的重要依据。遗憾的是,在我国的劳动统计中则缺乏对这一重要的劳动供给群体就业状况的客观反映,是我国劳动统计对具体国情状况反映的缺失。
更进一步,如前所述,劳动力市场测量不只是起到客观真实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功能,其本质作用是服务于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欧盟委员会选择制定的结构性指标便是一个典范。我国的劳动统计体系一直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完善,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宏观政策的需求。例如,在当前“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下,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政策中的着力点(37)。在我国目前的《劳动统计年鉴》与《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中均有专门的职业培训与技能鉴定、劳动关系、劳动保障监察和社会保障的指标,服务于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加强就业权利保护和促进劳动力市场法制化的目标;并且,从1990年开始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指标》与《中国科学技术统计年鉴》系统性地提供了我国科技活动发展的情况,包括具有国际可比性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数据(38),为建设“创新型国家”(39)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最基本的信息,这些均是值得肯定的地方。然而遗憾的是,在我国急剧的结构性调整背景下,针对就业岗位的创造和消失,及其按照地区、行业、职业等的细分指标却一直不存在,使得“千方百计扩大就业”的目标失去了基本的数据支持;而且,前述各个关键性指标均是分散在《劳动统计年鉴》及其他的统计当中,没有进行体系化的构建以形成一个核心的战略性指标体系,因而无法集中地反映我国当前的战略重点,也没能够突出地体现劳动力市场测量指标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所应具有的本质意义。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测量的方法选择
科学的指标体系是劳动力市场测量的核心,而合适的测量方法则是准确进行信息收集的保证。我国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收集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已开始,信息收集的方法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变迁而不断地调整。概括而言,我国劳动统计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五种:失业登记,“三合一”就业统计,人口普查,城镇劳动力调查,以及其他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不定期进行的零星专项调查。
我国城镇劳动力的失业登记统计制度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及其失业率是迄今为止我国官方正式公布并予以采信的唯一用来反映我国失业规模和失业水平的统计指标。然而,由于对失业定义的局限性以及实际操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一指标所标示出的中国城镇失业率水平受到广泛质疑,普遍认为其不能反映出我国城镇的真实失业状况(40)。
“三合一”劳动统计是我国就业情况的重要信息来源。“三合一”统计取名于三种不同统计合并产生每年分行业就业人员数的事实。它们分别是:由国家统计局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的城镇单位劳动统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员、个体劳动者的行政登记以及由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负责的乡村就业人员统计。三种统计合并形成了每年公布的分行业就业人员数。该序列作为我国唯一每年可以利用的分行业数据,通常被用来反映就业人员行业结构变化,或者被用于分行业劳动生产力的比较研究。但是,由于“三合一”统计遗漏了城镇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以及其他行业的大量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按该种方法统计的就业数据与实际就业情况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难以全面反映我国的就业情况(41)。
我国就业情况统计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人口普查。目前我国大约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至今已经进行了五次;其中间年份的1%人口抽样调查是昂贵的普查成本和两次人口普查间隔过长的折中,内容、组织实施形式和数据发布的时间与方法等都与大普查相似。在公开出版的普查或者抽样调查资料上,可以找到经济活动人口数、就业人员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行业、职业等特征,以及失业人口的类似特征,而且这些信息通常详细到分城乡、分省的程度(42)。我国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每年进行一次。在三种人口调查中,人口普查提供最详细的人口和劳动力信息,其结果通常被作为基期资料使用。其他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则是以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并根据每年的小样本调查结果调整编辑而成的。例如,目前每年公布的就业人员总数就是以人口普查的就业人员总数为基础,并依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结果估计得到的(43)。然而,我国的人口普查未能准确地确定就业人员的行业所属(44),高估了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数目。另外,人口普查中的劳动统计毕竟只是在收集人口信息的同时,对人的劳动力属性进行的附带调查。从劳动统计的需求来看,仍然缺乏针对性与全面性。
鉴于以往我国就业与失业测量方法存在的种种缺陷与局限性,我国于1996年建立了城镇劳动力调查制度,这也是国际劳工组织向世界各国推荐的获取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方法。从1996年10月我国进行的第一次劳动力调查开始,以后每半年组织一次(45)。在劳动力调查中主要指标采用了国际标准,在调查方法上采用了住户调查的方式;同时也根据中国特殊的国情制定了具体的实施细则。在劳动力调查实施的近十年中,针对样本设计、指标口径、组织实施、数据处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不断的改进与完善。2005年,国务院决定正式建立全国的劳动力调查制度,这在我国劳动统计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分散进行劳动力统计的历史,建立了完整统一的劳动力统计制度,使我国的就业统计工作实现了与国际标准的接轨,相关统计数据具有了完全的可比性;最重要的是,它使我国的劳动力统计数据可以全面、准确地反映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基本特征,为宏观管理和经济分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46)。
然而,与发达经济体劳动力调查的实施技术与操作方法进行对比,我国的劳动力调查制度还存在相当多的有待改进之处。如在调查样本的设计方面,其他国家劳动力调查的终极样本一般是住户,而在我国则是整群抽样的设计,终极样本是调查小区,并且没有采用样本轮换技术;在数据的汇总方面,我国缺乏按照总体的真实构成对调查数据进行加权,从而对失业率存在高估或者低估的问题;同时,调查员的专业素养也有待提高(47)。最后,最应引起关注的是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发布问题。与美国劳动统计局每月在其网站上公布失业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虽然于1996年即开始开展劳动力调查,但调查失业率从未向社会公开过(48)。曾有多位学者撰文估计中国的失业率,但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甚至相差甚远(49)。中国的调查失业率数字,在劳动力调查开展了10年之后,仍然是一个未知的谜,这无法不引起各方的猜疑与深思。
另外,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对各国劳动统计发展划分的三个阶段,我国目前处于统计发展的中级阶段(50)。国际劳工组织对处于该阶段国家的建议一般包括引入月度或者季度的劳动力调查;将对特殊劳动问题(一般与工伤、培训、劳动力流动等相关)的调查作为常规的劳动力调查项目中的一部分;增加常规的专项家户调查(与童工、非正规部门、家庭收支等相关);对企业调查进行改进,包括扩展调查的覆盖范围,并增加劳动力流动和未填补的职位空缺数据的统计;提高行政记录的覆盖范围、频率和汇报准确度以提高数据质量,并提高数据的利用程度(51)。
四、结论
劳动力市场作为一国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门,在不断加强经济发展的当今世界,对其有效的测量显得愈发重要。而一个科学完备的劳动力市场测量体系则是获得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基础。对劳动力市场测量有效性可从其两个组成部分——测量指标和测量方法——来进行评估。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测量指标体系在满足一般性的国际标准方面,尚存在四项重要统计指标的缺失;在反映我国特殊性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下岗”与“大学生就业”方面,也有失客观与准确;并且,由于缺少结构化指标体系的构建,还无法集中地反映我国当前的战略重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测量方法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国际劳工组织和发达经济体成熟的测量标准与测量实践相比,改进与完善的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ILO,C160 Labour Statistics Convention,1985,Geneva.http://www-ilo-mirror.cornell,edu/public/english/employment/skills/recomm/instr/c_160.html.
②Louis J.Ducoff and Margaret Jarman Hagood,Objectives,Uses and Types of Labor Force Data in Relation to Economic Polic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vol.41,no.235 (Sep.1946),pp.293-302.
③Robert S.Goldfarb and Arvil V.Adams,Designing a System of Labor Market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no.205,Washington,D.C.,1993.
④Louis J.Ducoff and Margaret Jarman Hagood,Objectives,Uses and Types of Labor Force Data in Relation to Economic Policy.
⑤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Structural Indicators,Brussels,27.9.2000,COM (2000) 594 final,2000.
⑥ILO,C160 Labour Statistics Convention,1985,Geneva.http://www-ilo-mirror.cornell,edu/public/ english/employment/skills/recomm/instr/c- 160.htm.ILO,R170 Labour Statistics Recommendation,1985,Geneva.http://www.ilo.org/ilolex/english/recdispl.html.
⑦Robert J.Pember and Honoré Djerma,Development of Labour Statistics Systems,Bulletin of Labour Statistics 2005-1.ILO,Geneva,2005.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bureau/stat/download/articles/2005-1.pdf.
⑧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89-2005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⑨ILO,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Geneva,1999.
⑩Lawrence H.Summers,Understanding Unemployment.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90.
(11)李丽林:《中国转型时期劳动力参与率的测量、变化及其意义》,载曾湘泉等著《中国就业战略报告2005-2006:面向市场的中国就业与失业测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ILO,Resolution Concerning Statistics of Employment in the Informal Sector,adopted by the Fif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Labour Statisticians.Geneva,1993.
(13)叶世芳:《我国失业统计的改革》,《统计研究》1998年第3期。
(14)蔡昉、王美艳:《非正规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发育——解读中国城镇就业增长》,《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期。
(15)徐丽梅:《浅谈我国非正规部门的发展与统计》,《上海统计》2002年第3期。
(16)蔡昉、王美艳:《非正规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发育——解读中国城镇就业增长》,《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期。
(17)ILO,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Geneva,1999.
(18)Robert S.Gotdfarb and Arvil V.Adams,Designing a System of Labor Market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19)宋长青:《就业统计新概念》,《中国统计》2003年第6期。
(20)ILO,Resolution Concerning the Measurement of Underemployment and Inadequate Employment Situations,adopted by the Six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Labour Statisticians.Geneva,1998.
(21)宋长青:《特殊时期、特殊现象、特殊方法——对下岗及下岗人员统计的理论思考》,《中国统计》1998年第3期。
(22)ILO,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Geneva,1999.
(23)ILO,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KILM).Geneva,1999.
(24)Charles C.Holt and Martin H.David,The Concept of Job Vacancies in a Dynamic Theory of the Labor Market.In NBER (ed.),The Measur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of Job Vacanc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6.
(25)唐纩:《发达国家职位空缺数据收集和调查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对我国的借鉴》,曾湘泉等著《中国就业战略报告2005-2006:面向市场的中国就业与失业测量研究》。
(26)Robert J.Pember and Honoré Djerma,Development of Labour Statistics Systems.
(27)参见2000-2002年期间的《雇主技能调查报告》:Derek Bosworth,Rhys Davies,Terence Hogarth,Rob Wilson,Jan Shury,Employers Skill Survey:Statistical Report,DfEE,Nottingham,2000.Terence Hogarth,Jan Shury,David Vivian,Rob Wilson,Employers Skill Survey 2001:Statistical Report,DfES,Nottingham,2001.Jim Hillage,Jo Regan,Jenny Dickson,Kirsten Mcloughlin,Employers Skill Survey 2002,Research Report no.372,DfES,Nottingham,2002。
(28)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分析表明,技工短缺已成为我国的普遍性问题,在对各类劳动力的需求中,高技能人才需求增长的幅度最大(参见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关于技术工人短缺的调研报告》,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网站,2004-9-8)。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有相当多的企业存在着严重的技术工人岗位空缺,致使企业无法及时满足市场需求,产品质量受到影响,制约着对外创汇,并不得不高价竞聘技工,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持续正常增长(参见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课题组《民工、技工“荒”在哪,为何“荒”?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结论》,《职业技术教育》2004年第24期)。
(29)曾湘泉:《建立面向市场的我国就业与失业测量体系——2005-2006年中国就业战略总报告》,曾湘泉等著《中国就业战略报告2005-2006:面向市场的中国就业与失业测量研究》。
(30)宋长青:《下岗及下岗统计研究》,《统计研究》1999年第3期。
(31)Dorothy J.Solinger,Why We Cannot Count the Unemployed? The China Quarterly,no.167(Sept.2001),pp.671-688.
(32)宋长青:《特殊时期、特殊现象、特殊方法——对下岗及下岗人员统计的理论思考》,《中国统计》1998年第3期。
(33)张志斌:《中国开展劳动力调查的回顾与评价》,曾湘泉等著《中国就业战略报告2005-2006:面向市场的中国就业与失业测量研究》。
(34)游钧主编《2005年:中国就业报告——统筹城乡就业》,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年。
(35)曾湘泉:《变革中的就业环境与中国大学生就业》,载曾湘泉等著《中国就业战略报告2004:变革中的就业环境与中国大学生就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36)张爱民、李春亭:《中外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体系比较研究》,《生产力研究》2005年第4期。
(37)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4932440.html.
(38)刘树梅:《我国科技统计发展概况》,中国科技统计网站,2006-5-10。原文见http://www.sts.org.cn/fxyj/other/documents/fzgk20060510.html.
(39)参见国务院于2006年2月9日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全文见http://www.gov.cn/jrzg/2006-02/09/content_183787.html.
(40)Dorothy J.Solinger,Why We Cannot Count the Unemployed?
(41)岳希明:《我国现行劳动统计的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张志斌:《中国开展劳动力调查的回顾与评价》,曾湘泉等著《中国就业战略报告2005-2006:面向市场的中国就业与失业测量研究》。
(42)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搜集到的劳动力信息仅仅用于每年就业人员总数的估计上,而有关就业人员的性别、年龄、教育以及行业等信息目前没有公开发表。(参见岳希明《我国现行劳动统计的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43)岳希明:《我国现行劳动统计的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44)参见岳希明《我国现行劳动统计的问题》,《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岳希明在其文章中指出,人口普查的工作人员最早发现了人口普查在确定就业人员行业属性时存在的问题(李树海:《从甘肃第四次人口普查就业结构的数据偏差看农村行职业划分中存在的问题》,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编《中国人口普查方法科学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其后,Alwyn Young对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参见Alwyn Young,Gold into Base Metals: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Journalo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1,no.6,2003,pp.1220-1261)。
(45)(46)张志斌:《中国开展劳动力调查的回顾与评价》,曾湘泉等著《中国就业战略报告2005-2006:面向市场的中国就业与失业测量研究》。
(47)耿林:《美国的就业与失业测量》,曾湘泉等著《中国就业战略报告2005-2006:面向市场的中国就业与失业测量研究》。
(48)《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仅在1997和1998两年公布过城镇调查失业人数,此后就再未公布过。
(49)冯兰瑞在《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情况及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一文中估计,到“九五”末期,我国的失业率可能达到21.4%;胡鞍钢在《中国城镇失业状况分析》(《管理世界》1998年第4期)一文中估计,我国1997年的失业率为6.9%;周天勇在《中国城镇的失业率究竟是多少》(《财贸经济》2003年第11期)一文中估计,中国2002年的城镇劳动力失业率为12.44%,达3437万人;张车伟在《失业率定义的国际比较及中国城镇失业率》(《世界经济》2003年第1期)一文中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推算,目前中国的城镇实际失业率大约为8.27%;蔡昉在《论就业在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中的优先地位》(《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3期)一文中,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2年下半年进行的一次五城市的调查,推算自1996年9月以来,这五个城市16-60岁人口的失业率一直在8%以上,并持续上升,从2002年2月开始,失业率超过了14%。李实、邓曲恒在《中国城镇失业率的重新估计》(《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4期)一文中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于2002年组织的城镇住户调查所得数据,根据失业率定义是否把非正式工作认定为就业和劳动力供给量是否考虑农民工,估计出四种不同情况下的失业率。其中将非正式工作认定为就业并且劳动力供给量中也考虑农民工的失业率定义下(这个定义与国际标准最为接近)估计出的城镇失业率为8.59%。
(50)处于统计的中级发展阶段的国家的主要特点是:a.具有来源于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和年度的家户劳动力调查的定期的劳动统计(包括对受过训练的劳动供给的统计)。b.具有就某些特殊的劳动问题(童工、非正规部门、家庭收支等)进行专项家户调查。c.具有来源于正规部门企业的常规的调查项目所提供的关于有酬雇佣和工资的年度统计数据,但是覆盖到的行业范围有限。d.具有来自于行政记录的足够的数据,但是质量参差不齐(例如,记录可能没有包含重要的数据,或者没有覆盖到所有值得关注的事件)。覆盖到的内容一般包括:登记求职者,职业伤害,培训与教育机构的产出。e.具有足够高的技术能力,但是没有维持一个常规的且覆盖广泛的企业样本框,或者计算能力和分析撰写报告能力不足。(参见Robert J.Pemberand Honoré Dierma,Development of Labour Statistics Systems)
(51)Robert J.Pemberand Honoré Djerma,Development of Labour Statistics Systems.
标签:国际劳工组织论文; 充分就业论文; 中国统计年鉴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统计调查论文; 城镇人口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失业率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