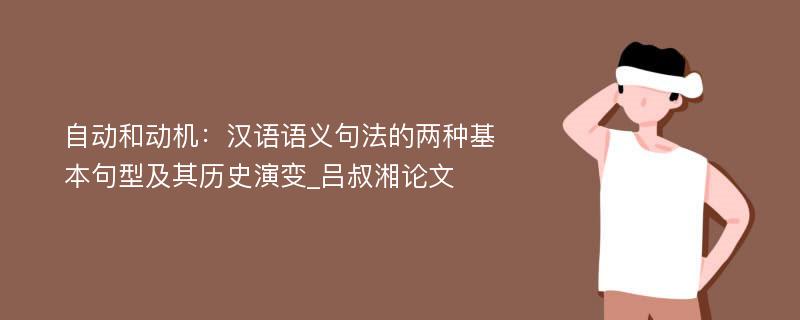
自动和使动——汉语语义句法的两种基本句式及其历史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句法论文,两种论文,句式论文,语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一种语言有定性范畴的特点,我们认为汉语语义句法的基本句式是自动和使动(徐通锵,1997)。但是,如果要用这两种句式来直接解释现代汉语的句法结构,那是困难的。因为语言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不通过历史的分析就无法弄清楚现代的语法结构规则和这两种基本句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的重点不是挖掘新的语言事实,而是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揭示各重要语法规则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出一条理解复杂语法现象的简单线索,对补充式、连谓式、受事主语句之类被公认为汉语语法结构特点的成因作出理论解释。
一 现代汉语句法结构的两种格局
现代汉语的语法理论和分析方法基本上来自西方。 吕叔湘(1986a)曾根据《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经验进行过这方面的总结,认为:“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也就没有系统的语法理论,所有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这里的“‘结合’二字谈何容易”八个字,字字千钧,值得仔细琢磨。我想,“结合”中最根本、最困难的问题可能是“结合”基点的选择,即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立脚点去实现和西方语言理论的结合。自《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基本上是用印欧语的语法理论来分析汉语,总结出一套语法规律,并且把那些不同于印欧语的结构名之为动补式、连动式、兼语式、受事主语句、主谓谓语句,等等,认为这些都是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这些规律基本上是在现在称之为“及物性理论”(Hoppe-r&Thompson,1980)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就是说,它的基点不是汉语,因而不完全适合汉语语法结构的分析,有很多现象还难以解释,而且这些称之为“特点”的规律相互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人们也说不清楚。近几十年来,西方语言学家根据某些印第安语的研究提出一种颇有影响的ergative(作格,唯被动格)理论,并被用于印欧语及其它语言的研究。国外的一些汉学家,特别是那些华裔汉学家,想用这种理论来分析汉语,认为印欧语是一种及物性语言,而汉语是一种作格(ergative)语言,开始了一种新的“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的研究途径。
作格的最大特点是不及物句的主语和及物句的宾语有相同的格位变化(详细情况可参看Lyons,1977,341—343),和及物性语言的形态变化有原则的区别。及物性和作格(或唯被动性)是两种不同的语法结构格局, 即使如此, 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也乐于用作格去分析如英语J-ohn moved the stone和The stone moved这两种句式之间的关系,进行作格结构的研究(Lyons,1977,350—371;Halliday,1985,144—154)。及物性和作格,如果以典型的单句结构“名物[,1]—过程—名物[,2]”和“名物[,2]—过程”(John moved the stone和The stone mo-ved)的语义结构为参照点,那么“名物[,2]”在及物性结构格局中是受事,在宾语位置上取宾格形式,在主语位置上取主格形式,而在作格的结构格局中名物[,2]在语义上虽为受事,但不管处于主语或宾语的哪一个位置,其结构形式一样,是句法结构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中介。这一事实说明,“主语”这一概念用于及物句时部分地取决于希腊语、拉丁语等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结构,其中包含两个条件:第一,及物句的施事名词与不及物句的主语有相同的格位屈折;第二,动词的数、人称等决定于不及物句的主语名词和及物句的施事名词,英语如用代词去分析,这两个条件都很清楚(Lyons,1977,342)。我们这里强调这一点,是想再一次说明“主语”是诞生于印欧语基础上的一种语法理论,不一定适合于其他语言的分析,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它看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因而汉语的语法研究也没有必要受“主语—谓语”框架的束缚(徐通锵,1991)。
汉语中类似英语The stone moved这样的句子特别丰富, 一般称为受事主语句。可能是由于这种原因,有些研究汉语的学者认为汉语是一种作格语言。吕叔湘(1987)曾以“胜”“败”两字为例讨论过这两种结构格局。1987年,中韩女篮进行比赛,结果是中国女篮以大比分取得了胜利。《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在报道这同一事件时使用了不同的标题,前者是“中国女篮大败南朝鲜队”,而后者是“中国女篮大胜南朝鲜队”,反义字“胜”“败”在这里竟然使这两个句子具有相同的意义。吕先生据此讨论了汉语的两种句法结构格局:
第一格局第二格局
X——动词——YX——动词——Y
X——动词 Y——动词
中国队 胜南朝鲜队 中国队败南朝鲜队
中国队 胜
南朝鲜队败
这第二格局就是一般所说的作格结构。吕叔湘针对“汉语是一种作格语言”这一论断说:“我不知道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什么,是不是跟前面所说的动词第二格局有关。”吕先生在分析了有关的语言现象之后进一步得出结论:“很重要的一点区别作格语言和受格语言(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作格和及物性)必须有形态或类似形态的手段做依据。汉语没有这种形态手段,要说它是这种类型或那种类型的语言都只能是一种比况的说法。如果汉语的动词全都只能,或者大多数只能进入前面提出来的第二格局,不能进入第一格局,那么说它是作格语言还有点理由。可是事实上汉语的及物动词绝大多数都能进入第一格局的二成分句,而进入第二格局的二成分句却很受限制。这就很难把汉语推向作格语言一边了。”看来“依葫芦画瓢”地套用作格理论来分析汉语的结构,是很难取得预期的结果的。吕叔湘以“胜”“败”两字为例而进行的分析,一方面否定了“汉语是作格语言”的结论,但另一方面也肯定了汉语语法有两种不同结构格局的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汉语语义句法的基本句式的构造。
把ergative翻译为作格或唯被动格,似乎都不是很确切,而且人们也不容易理解。仔细推敲作格的意思,似与我们传统所说的“使动”没有什么原则的差异,只是观察的角度有别。ergative(作格、唯被动格)着眼于形式,强调不及物句的主语与及物句的宾语同形式;“使动”着眼于语义,强调某种力量使名物[,2]发生变化。汉语没有形态变化,谈不上什么作格还是受格。从语义上说,使动是汉语语义句法的一种重要句式,它和自动句的语义差异主要是:自动句对受事产生影响的力量是“明”的,处于动字前的位置,如“中国队大败南朝鲜队”的“中国队”,John moved the stone 的John;使动句的力量是“暗”的,句中没有出现相关的结构成分,如。“南朝鲜队(大)败了”,不是南朝鲜队自己愿意“败”,而是有一种力量使它“败”,只是这种力量没有“明”说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有定性的受事移至句首,形成所谓受事主语句。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把汉语说成是作格(ergative)语言,那是表述有误,如改成“汉语是一种使动性结构的语言”,就较为确切。否!使动只是汉语中和“自动”相对的一种句式,不能片面地强调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结构格式。吕先生说它是汉语语法的一种结构格局,完全正确,我们与吕先生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强调使动是与“自动”相对的一种基本结构格局,或者说,是汉语的一种基本句式,虽然在现代汉语中它的使用范围很狭窄,但有很多语法规则在历史上却是从这种使动结构中脱胎出来的,因而可以用来解释一系列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
二 使动式的变异和“动补”式的发展
一种语言的基本句式决定于它的有定性范畴。印欧语的有定性范畴是谓语动词,因而它的基本句式是主动和被动;汉语的有定性范畴是句首位置的话题,它与行为动作的语义关系决定了汉语的基本句式是“自动—使动”。自动相当于印欧语的主动,其主要的语义特点是:句首的话题必须是有生性的名物或相当于有生性名物的辞语,充当施事,对行为动作能发生一种支配的力量;话题与说明之间可以嵌入“能、会、应该……”之类的一般称之为“助动词”的辞语,虽然在肯定句中它们可以不出现,但在否定句中必须有“不能、不会、不应该……”之类的成分。自动虽然相当于主动,但由于主动是和被动相对立的结构,因而我们不用“主动”这个概念,而用“使动”。“自动—使动”和“主动—被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结构,难以进行简单的类比。自动和使动在结构上可以同型,例如前引的“中国女篮大胜南朝鲜队”和“中国女篮大败南朝鲜队”的语义等价,结构形式一样,主动和被动不可能有这种同型的结构。“使动”中尽管可以包含一些被动的因素,但比重不大,和“被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主动和被动,相互之间可以进行自由的转换,像传统语法就非常强调主动句和被动句的相互转换关系。乔姆斯基出版于1957年的《句法结构》基本上也是以主、被动句的转换为基础研究它的转换—生成语法。汉语的所谓被动句在句法中没有像印欧语被动句那样的地位,“被”(包括“给、叫、让”等)基本上只是一种使有定性的施事后置的语法形式,和相应的自动句的转换很不自由。以往以及物性为基础的语法理论为什么不大适合汉语语法的研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语的基本句式不同于印欧语。“自动—使动”是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实现和西方语法理论的“结合”的最合适的基点。
“自动”是汉语的一种基本句式,人们容易接受,而且现在的研究也已取得一些重要的进展,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篇论文就是马庆株1989年发表于《中国语言学报》上的《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说“使动”也是汉语的一种基本句式,人们恐怕难以理解,因为它很难直接用来解释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从表层的语法结构来看,情况确实是那样,但从深层的结构来看,我们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需要涉及“自动—使动”的基本结构格局和它们的历史演变。我们在研究音系的结构时曾经说过:语音很容易发生变化,但语音系统的结构格局很稳固,制约着语音变异的方向和目标,使语音的演变很难超越结构格局所许可的范围。这就是说,语音现象的易变性和音系结构格局的稳固性是自发地驾驭音系演变的杠杆,任何变化都是围绕着这一杠杆而运转的,因而今与古的语音结构虽然可以有很大的差异,但音变机理不会有大的区别,我们完全可以用现实的音变机理去解释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规律。我们曾用这一原则对汉语声母系统的演变和韵尾的阴阳对转进行过一些探索,并作出了一种新的、可以验证的解释(徐通锵,1990, 1994,1996)。这是语言史研究中的一条重要而有效的原则, 同样适用于语法的研究,即语法演变也无法摆脱语法现象的易变性和语法结构格局稳固性这一矛盾运动的杠杆的控制。我们可以在现实的语法结构和“自动—使动”的基本结构格局之间找出它们内在的联系。
“使动”和“自动”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失去了系统性对立的痕迹,但在古代汉语的一些表动作的字还明显地存在着自动和使动的系统对立。王力(1965,442)曾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认为:“在古代汉语构词法上有一种特殊现象,就是自动词和使动词的配对。这种现象在现代汉语里也还存在着,不过有些词的古义已经死去或仅仅残存在合成词里,自动词和使动词的关系就不如古代汉语那么明显了。 ”吕叔湘(1987,2)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也指出:“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的使动用法是古汉语里常用的用法手段。现代汉语里,动词的使动用法已经不能广泛应用了,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如‘端正态度、严格纪律’等等,是最近三四十年里才出现的。”语言现象虽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它的结构原理不会轻易变动,人们一定可以在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语言现象中找到它的变异形式。一向被中外语言学家看成为汉语语法结构特点之一的动补式就是这种使动式的演化。其实,王力早在四十年代的《中国语法理论》中就已涉及到这个问题,称之为使成式,后来在《汉语语法史》中又进一步对此作了明确的论述,认为“由使动用法发展为使成式,是汉语语法的一大进步。因为使动用法只能表示使某物得到某种结果,而不能表示用哪一种行为以达到这一结果”(王力,1986,367)。可能是结构语言学方法论的影响,在语言的共时分析中不管历时的因素,因而人们只根据共时的特点来分析这种结构,类比动宾式的名称而称它为动补式,并对“补”进行结果、程度、趋向等等的分类。脱离历史眼光的共时分析不容易抓住结构的特点,这种分类的方法就“补”析“补”,离开句法结构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的分析,很难说清楚“补”的是什么。最近,吕叔湘(1986b,5—9)独辟蹊径,把补语和主、谓、 宾的语法关系、和施、受事的语义关系等一起结合起来去考察补语的语义和语法功能,提出了一条独特的研究思路。比方说,“句子的语义关系是:动作发自主语,及于宾语,结果表现为补语,宾语和补语构成一个表述,也不妨说是有一种主谓关系。例如:“小刘爬上车身,拉紧帆布蓬,拴牢绳子。”这里的宾、补的关系是:帆布蓬紧,绳子牢,在语法上是一种主谓关系。吕叔湘的分析很细致,除“把”“被”字句外,一共分出八种类型,并图解示意。上引的例子是其中的一种类型,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补语和句中其它结构成分的语义关系的大致状况。这一研究使述补结构的研究水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摆脱了人们难以得其要领的、单纯考察“补”与“动”的关系的静态描写。北大的《现代汉语》(1993)说补语有些“是直接说明充当述语的动词的”,“有的是说明述语动词的施事的”,“有的是说明述语动词的受事的”,显然是受到吕叔湘的研究的影响。这些研究虽然比以往有进展,但我们仍旧感到不足,因为还没有清理出一种驾驭“动补结构”的简单线索;找不到这种线索,说明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弄清楚“补语”的性质和功能。那么,驾驭“动[,1]+动[,2]+名[,2]”(动[,2]也包括一般所说的形容词)的“动补结构”的线索是什么?就是古汉语的“自动—使动”的结构,主要是看“动[,2]”的语义指向:指向受事,“动[,1]+动[,2]+名[,2]”就是一种使动结构的变异;指向施事,继续保持自动结构的格局,所谓“动补结构”就是这两种句式的遗留和变异。循着这种思路,或许可以比较容易地把握住所谓“动补”结构或“述补”结构的基本脉络。
先讨论“动[,2]”的语义指向受事的结构。这种结构的意义可以概括为:“名[,1]用动[,1]使名[,2]发生动[,2]的变化”。吕叔湘所举的八类述补结构,前三类显然属于这种使动结构的类型。由于我们的研究重点不是补充新的语言事实,而是对现行的事实作出理论的解释,因而下面的用例都选自吕先生的文章。每类各选一个例子,分成A、B两组,其中A组为现在一般所说的动补式,B组根据我们的假设还原为使动式的语义结构:
A
B
1、……拉紧帆布蓬,拴牢绳子
“拉”使“帆布蓬紧”,“
拴”使“绳子牢”
2、(你)说破了嘴唇皮(也不中用)“说”使“嘴唇皮破”
3、(你真是吃浆糊)吃迷了心
“吃”使“心迷”
“使名[,2]发生动[,2]的变化”是这三类例子的共同特点。意义的核心在“动[,2]”,“动[,1]”实际上只表示“动[,2]”的一种原因、方式之类的意义。如例1是因“拉”而“紧”,因“拴”而“牢”。 这种结构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句中既要出现名[,1]和名[,2],又要出现动[,1]和动[,2];动[,1]的语义指向名[,1]的施事,动[,2]的语义指向受事的名[,2]。如例2的动[,1]“说”指向名[,1]“你”,而动[,2]“破”指向名[,2]“嘴唇皮”,它们相互间具有吕叔湘所说的特定语义关系。至于“说”和“破”,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语义关系,现在人们把它看成为“结果补语”,实际上是印欧语“词”的概念模糊或掩盖了句中结构成分之间的实质性的语义关系。第二,名[,1]可以省略,而名[,2]如具有有定性的语义特点,它就可以移至句首充当话题。这样,句中就会只出现一个“名”。上述的三个例子就可以改说成:1’、帆布蓬拉紧了,绳子拴牢了。2’、嘴唇皮说破了。3’、心吃迷了。受事的位置变了,但使动的语义没有变,因“帆布蓬”不“拉”是不会“紧”的。吕叔湘所说的第7种类型,即:“这个字写错了。 ”也属于这种使动式的类型,因为“这个字”是动字“写”的受事,“错”的语义指向这个受事,而且它可以移位至“动[,1]+动[,2]”的“写错”之后而不改变语义。现在所说的所谓“受事主语句”实际上是使动式的一种历史变异。
这种使动性的结构性质弄清楚了,剩下的几种类型也就不难解释了,因为这些例子的“动[,2]”的语义都指向施事,因而它没有使动的性质,而是和使动式相对立的自动式的变异和遗留。我们先从4、5、6、7四种类型中各引一例,然后再考察它们的语义特点:
4、别理他,他是喝醉了酒发酒疯。
5、……咱们吃老了,儿子吃大了,还有了孙子。
6、地已经下饱和了,雨不再渗进去。
7、这种酒喝不醉的。
这里,“动[,2]”的语义都是指向施事性“名[,1]”的:例4 的“醉”指向“他”,是“他”醉了,而不是“酒”醉了;例5 的“老”指向“咱们”,“大”指向“儿子”,是“咱们老了,大了”,而不是“吃”的“老了,大了”,把“吃老”“吃大”等看成为“动补结构”,这种实质性的语义关系就看不出来了。例6、例7的情况与此类似,只是施事性的结构成分在“动[,2]”的前面没有出现:例6 相当于施事性的“雨”出现在后续小句;例7是陈述一种事情,施事应该是有生性的名物,因为“喝”的语义隐含有这种语义。它不属于使动式,因为“这种酒”不能移到“喝不醉”的后面去。总之,这些类型的结构不是使动式,适合从自动式的角度去解释。“动补”式的语义关系的解释的主要根据是动[,2]的语义指向。
吕叔湘的研究已经接触到“动补式”的原型,为后辈的研究铺垫了一层坚实的台阶。这里的“动补式”我们打上了引号,这是由于我们对这一术语有保留,因为它是仿效印欧系语言的“动宾式”类比出来的,不能反映这种结构的实际性质。使动的说法比它更合适。
前面曾一再强调,语言现象是容易发生变化的,而支配和控制这种变化的结构原理是很稳固的,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这里讨论的“动补式”和古时自动式、使动式的联系和区别,可以再一次说明“语言现象的易变性和结构格局的稳固性”这一对立统一的矛盾与语言演变的辩证关系。
三 使动式的变异与“连谓”式的发展
使动式的“动补”性变异的关键是动[,2]的语义指向,没有涉及动字后的有定性结构成分;如果这个有定性结构成分的位置因语言的发展而发生变动,移至动字之前,那么语言中就会产生日常称之为“兼语式”之类的“连谓”结构。我们不妨先看看古汉语使动式的一些例句:
1.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庄子·外物》)
2.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孟子·梁惠王下》)
3.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
4.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己: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孟子·梁惠王上》)
这些例子都引自王力(1965,442;1986,367)。带横线动字的后面都是有定性的结构成分,为行文的方便,我们下面把这种结构成分的语义称为使事。使事既不同于施事,也不同于受事,而是兼有施事和受事的一些特点。施事的语义功能是支配动作,受事的功能是受动作支配,而使事一方面接受施事所支配的行为过程的影响而成为受事,但另一方面又有可能去支配某种行为过程,有它自己的受事。这种句式的语义特点,简单地说就是:施事支配使事去影响行为过程的进行。随着语言的发展,这种使事性成分的结构位置如因适应结构调整的需要而挪至表行为过程的动字之前,它就变为现在有“使”类动字标记的使动句,现在的一般语法书称之为“连谓结构”。
有“使”类动字标记的使动句是汉语句法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使事成分如挪至动字之前而不加“使”类字,一是句法不通,二是失去了使动意义。如例1仅仅把“我”挪至“活”字之前,语句不通, 如说“君岂有斗升之水而使我活哉?”那就可以保持原来的使动意义。使事位置的挪动给句法结构带来的影响与[±有生]的语义特征有密切的关系:如为有生性的使事成分,它挪至动字之前,而且在其前面再加上“使”字类的动字,它就会向兼语式的方向转化,如“朝秦楚”只能说成“(王)使秦楚来朝”,这就与上古时期已经出现但还不发达的递系结构,如“王命众悉至于庭”(《书·盘庚上》)、“令彭氏之子御”(《墨子·贵义》)等,合流成为现在一般所说的兼语式。时间顺序原则(戴浩一,1985)使汉语的一个句子可以出现若干个表示行为过程的动字,因而这种使动句在汉语中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根据吴竞存、梁伯枢(1992,238 )的研究, 《红楼梦》前八十回有3000来条递系结构,其中使动句有2000来条,占三分之二。这种比例数不是偶然的,是“自动—使动”体系中的使动式的转化,这里最“值得研究和注意的是那些在句中表使动的动词。这些动词只有少数几个纯粹表使动义(使、叫、让、要、令),多数都还另有各自的词汇意义。但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词汇意义外本身带有使动义,如派、求、劝、托、逼、准许、催、号召、发动、打发、分付、组织、动员、怂恿、允许、阻止、命令,等等;一种是词汇意义外,本身不带有使动义,只是进入‘V[,1]NV[,2]’后,句式赋予它使动义”。这一发现很有价值, 说明“V[,1]NV[,2]”这种句式就是一种使动式, 是古汉语的使动用法在现代汉语中找到了它的栖身之所。
前面讨论的使动式的变异(有“使”类字标记的“连谓句”),影响使事的施事大都是一些有生性语义成分。这是主流。但是,这种句式一旦形成,在以时间顺序为基础的汉语语义句法里,它就具有一种强大的生成力量,人们可以仿效这种句式生成新的句子。如果能对使事产生影响的力量是无生性的,那就需要在“使”类动字之前加上这种无生性的结构成分,形成一种使动的因果句:“使”字之前为因,之后为果,也就是说,由于在使事成分之前加上了一个“使”类动字,原来那种含而不露的原因,即对使事产生影响的力量,就从“幕后”跑到“前台”,成为使动句的一个结构成分。请比较:
5、个个雪白的衬衣,鲜红的领巾, 使我想到大海上空白色羽毛的海鸥群。(报)
6、……由于各种原因使生态环境恶化, 昔日的沃野良田变成了不毛之地,终于形成了今日的65平方公里沙漠。(报)
7、在旧的落后观念支配下,各种势力联合起来, 逼得枣花的母亲走上了绝路,最后悲惨地死去。(报)
这些例句中“使”类动字前的成分都是表使事的原因的。如例5,如果删除“使”和“使”之前的成分,句子照样成立,至于是什么原因使“我想”,那就含而不露,可作多种解释。这一类句子只要加上“使”类字标记,其前面就必须有明确的原因,使其成为话题,突出“使”的前后的因果性。
语言的演变是在结构格局控制下的自我调整,虽然可以改变某些结构,但不能脱离原来的结构基础。“连动式”和“兼语式”(或简称为“连谓式”)的语义特征都是有生性的话题对行为进行控制和支配,区别只在于“连动”的控制性和支配性的动力是同一个有生性的施事,而“兼语”则是不同的有生性施事,是一个有生性施事使另一个有生性使事发出一种能对他事物产生影响的力量。这一类语言现象的挖掘和分析始于本世纪的四十年代,是王力首先在《中国语法理论》和《中国现代语法》两部著作中提出来的。比较印欧系语言的句法结构, 王力(1943,23)发现汉语的句子可以没有主语,谓语可以不止一个动词,因而为了“表彰中国语法的特征,汉语和西洋语法相同之点固不强求其异,相异之点更不强求其同。甚至违反西洋语法书中之学说也在所不计”,“从语言事实出发才是研究语法的正确的道路”,因而他根据汉语的特点提出递系式这一类汉语特有的句型。由于“印欧语的眼光”对中国语言学家的影响太深,无法摆脱“主语—谓语”框架的束缚,因而对这一类句式的解释始终难以取得圆满的结果。王力(1944,134)认为“凡句中包含着两次连系,其初系谓语的一部分或全部分即为次系的主语者,我们把它叫做递系式,取‘递相连系’之意”。“递系”的概念由此而来。五十年代之后,这类结构格式不断改变名称,反映学术界对这类语言现象的性质还缺乏统一的认识。丁声树等(1953,112)把它称为“兼语式”,其特点“是两个主谓结构套在一起”。陈建民(1960)反对这种分析,认为兼语式不是主谓套主谓,而是述宾套主谓。朱德熙(1982,160—167)反对连动和兼语的划分,统称为连谓式,认为“连谓结构也跟主谓、述宾、述补、偏正等句法结构一样,是由前后两个直接成分组成的”,不能因N指施事就把这种连谓结构看成为兼语式, 不指施事的看成为连动式,因为“如果当N指施事时,说N是V[,2]的主语, 那么当N是受事时,是不是说N是V[,2]的宾语呢?其实不管N与V[,2] 之间意义上有什么样的联系,从结构上说,N只是V[,1]的宾语。有的方言里,某些人称代词有格的变化,作主语是一种形式,作宾语时是另一种形式,而在所谓递系式里,用的正是宾语形式。这个事实说明即使在N指施事的时候,N也只能看成V[,1]的宾语,不能看成V[,2]的主语”。 朱先生在这里忽视了一个事实,这个“N”是有定的,在句中是使事, 兼有施事和受事的特点,与宾语的一般表无定性受事的语义特点不一样。有定而兼有施、受的语义特征,这才是所谓“兼语式”中“兼语”的实质。正由于这种类型的结构难以用现行的语法理论来分析,因而有人干脆主张取消“连动”“兼语”这些名称(肖璋,1956;张静,1977)。这些争论的背后隐含着汉语的语言事实和印欧语的语法理论的矛盾;我们如果摆脱不了“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自然也就只能在“连动”“兼语”或“主谓套主谓”“述宾套主谓”之类的概念中兜圈子。这些意见,观点尽管不同,但方法论的原则是一致的,都是就谓语论谓语,没有一家能联系N与其它结构成分的关系进行语义结构的考察。 根据我们的假设,这类递系性的现象看起来很复杂,实际上是由一条简单的语义规则支配的,这就是:两个有生自动句的套合和组配,一个有定性的施事指令另一个有定性的使事去实现它想实现的行为过程,其结构公式是:有定性施事+“使”类动字+有定性使事+行为过程。
比方说“我请你叫他找人寄这封信”这个句子,若沿用“主语”“述宾”“兼语”之类的概念,那分析起来就相当复杂,而且难以掌握它的要领;如果我们用语义结构规则来分析,那就要简单得多,只要掌握“有定”“有生”和“时间顺序原则”(包括施事在受事之前、施事在使事之前、原因在结果之前等等)原则,大体上就可以对这一类现象和它的变体进行有效的解释。这个句子是几个使动句的套合,变换有定性使事成分的位置,句子的语义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语法现象是复杂的,但任何复杂的现象中都隐含有一种驾驭它们的简单线索。抓住自动句和使动句这两种基本句式以及它们的变衍,人们就有可能以简驭繁,把现在分别研究的一些重要的汉语语法规则系统化,指明它们的内在联系。自动和使动可能是理解和把握汉语语法结构规则的一种最简单的线索,值得进一步去探索。
四 结构单位的复音节化和句式结构格局的调整
使动式的结构为什么会发生变异?这自然需要从语言的演变中去寻找原因。根据王力(1986,359,368,410)的研究,跟我们前面的讨论有关的几种句式,如连动式、使成式(动补式)、兼语式等,虽然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和使用,但是广泛的使用和发展却是在汉、魏、晋时期。这是汉语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是上古汉语迈向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汉语的一级重要的阶梯,很多特点都是在这一时期定型的,跟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关的主要是结构单位的复音节化问题。
先秦时期虽然已经有复音字,但数量毕竟有限。有些学者想证明汉语从来就不是一种单音节语,就到先秦的典籍中去寻固定性字组,称为复音辞(马真,1980;程湘清,1982),但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字组能不能称为最小结构单位的“辞”,还需要推敲。到了汉代,复音辞大量产生,其中最有力的一个证明就是利用重言AA的格式,填入实义字,产生不会引起任何歧义的、有足够资格称为辞(固定字组)的重叠。丁声树(1940)关于《诗经》“采采”的解释可以为此作出有说服力的注释。“采采”一辞以往有两种不同的注释,或释为外动词,训为“采而不已”,或释为形容词,训为“众盛之貌”。丁声树针对这两种不同的解释,统观全局,从语言发展的观点深入分析有关的现象,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以全《诗》之例求之,单言‘采’者其义虽为‘采取’,重言‘采采’必不得训为‘采取’”“遍考全《诗》,外动词绝未有用叠字者,此可证‘采采’之必非外动词矣”“夫外动词之用叠字,此今语所恒有(如言‘采采花’‘锄锄地’‘读读书’‘作作诗’之类),而稽之三百篇乃无其例;且以声树之寡学,仰屋而思,三百篇外先秦群经诸子中似亦乏叠字外动词之确例,是诚至可骇怪之事。窃疑周秦以上叠字之在语言中者,其用虽广,而犹未及于外动词;外动词祗有单言,尚无重言之习惯,故不见于载籍,降及汉代,语例渐变,叠字之用浸以扩张,向之未施于外动词者今亦延及于外动词。习之于唇吻者,不觉即形之于简编,毛氏诗传训‘采采’为‘事采之’,韩诗章句亦言‘采采而不已’,此皆狃于当日语言之常例以释《诗》而不自知其乖违”。我们可以由此推想,利用双声、叠韵联绵字AB的格式而填入实义字,产生双音辞,大概也盛行于两汉。可以作为参考比较的是程湘清(1984,335—336)的两组统计数字:
总字数
总词数总字数
总词数
《论语》: 15,883183 《孟子》:35,402
336
《论衡》等五篇:15,553562《论衡》等14篇:35,221
764
尽管这里所说的“词”不一定是我们所说的固定性字组(辞),但不同时期的“词”数的差异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双音字在两汉时期的盛行情况。最小结构单位从单音节发展为双音节,这对语法结构规则的调整和改进是有重大的影响的,大体呈现如下的情况:结构单位单音节化的比重越大,“因字而生句”(《文心雕龙》)的字的组配限制就越小,规则就越灵活,相互呈反比的关系,每一个字都有多种组配的可能;相反,语言中的双音字或多音字的比重越大,结构单位之间的组配就会受到比较多的限制,因而对语法规则的调整、改进的推动力也就越大,相互处于一种正比的关系中。两汉时期多音字的大量产生,就不能不使汉语的语法结构规则出现局部的调整。抓住这一点,或许对理解使动式结构格局的调整有一些帮助。先请看下面一组例子(转引自王力1986,368):
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汉书·高帝纪》)
汉氏减轻田租。(《汉书·王莽传》)
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史记·项羽本纪》)
标着重号的字组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动补式”,是两汉时期产生并广泛运用的一种结构格式。它们都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结构单位,是由于结构调整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形式,目的是改进汉语的编码方式,扩大动字的组配功能,既能表达说话人想要表达的复杂意思,又能使结构达到尽可能的简练。如果结构单位仍是单音节,那么带着重号的部分应是“推寡人,使寡人(处于)高(位)”“减田租,使田租轻”“推孝惠、鲁元,使之堕车下”,显得累赘;而且“推寡人”的意义与“推高寡人”的意思还正好相反。动字后再加上一个动字(包括一般所说的形容词),进行补充,既可以把两个组成部分合一,经济简练,又可以扩大动字的组配功能,准确地表达人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当然,这里有条件的限制,就是补充成分(动[,2])的语义或指向施事,或指向受事,而就上述的例子来说,都指向受事。这无疑是汉语语法结构规则的一种重要发展。结构单位的音节的“单”与“双”会影响句法结构规则的调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在“斫而小之”这种结构的“之”的位置上是很难容纳像上引例子中的“寡人”“田租”“孝惠、鲁元”等多音节的结构单位的。
人们可能会提出问题:自动和使动既然是汉语的两种基本句式,那句式格局的调整为什么都集中在使动式上?根据和汉语有亲属关系的藏缅系语言的研究,自动和使动的对立有形态变化的依据,“古藏语动词的使动式有两种构成方式:形态手段和句法手段。前者主要是在动词词根前附加前缀s—或b—/—,使非使动词变为使动词。有时也用声母交替的方式”“使动词的第二种构成方式是在动词后头加—par bjed或—ladu”(马学良,1991,165—166)。我们猜想, 汉语的使动式早期 也应该有一定的形式标志,主要通过声母复辅音中的前置辅音表示。根据谐声原则,音首有复辅音,这基本上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不清楚的是这些处于音首位置的前置辅音的功能。我们想,这些前置辅音可能承担着使动的功能,藏缅系语言的结构对汉语研究来说,应该有启示意义,值得参考。随着复辅音的简化,表使动的形式标记消失,促使结构单位的复音节化,并推动结构格式进行必要的调整。语言是一种自组织系统,会根据交际的需要和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自发地进行适当的、合理的调整。“合理”的“理”是什么?是时间顺序原则,根据现实事件的先后发生顺序安排结构单位的排列(戴浩一,1985),其中包括有定性的施事在行为动作之前,原因在结果之前,等等。自动式的结构规则与这种原则没有矛盾,因而自古至今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使动式与此不同,对行为动作能起支配作用的使事如继续在动字之后,这就与时间顺序的原则相矛盾,因而在使动式缺乏形式标记的情况下就必须对结构单位的排列顺序进行必要的调整,不然就无法准确地表达语义。调整的方向,一是把有定性的使事成分挪至动字之前,在其前面再加上一个“使”类动字,产生“连动”“兼语”之类的“连谓式”;一是使事性成分仍旧处于动字之后,但在动[,1]之后再加上一个动[,2],产生所谓“动补式”,使使事受到某种行为动作的限制。这两种调整的方向语义上各有特点,一般说来,前一种方向的使事在语义上多为有生和有定,后一种方向不受这种语义条件的限制。这两种方向的调整一旦完成以后,在语言中就形成一种固定的结构格式,人们就可以根据这种格式造出交际所需要的结构单位。
自动和使动是汉语语义句法的两种基本句式,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点吸收西方语言学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把握汉语语法的基本结构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