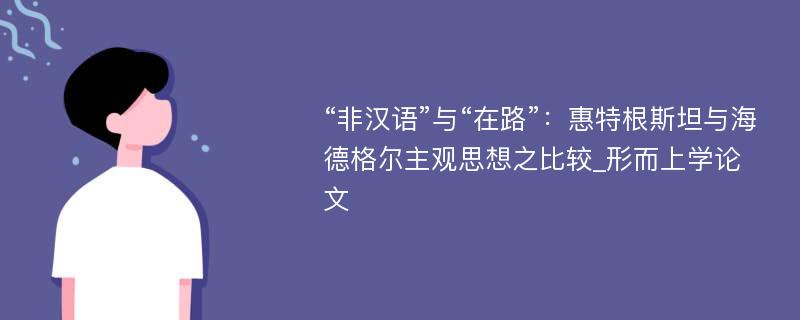
“非之中”与“在之中”——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主体思想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特根斯坦论文,海德格尔论文,主体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中图分类号]B5116.5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3-0093-07
“在之中”是海德格尔哲学中此在的先天机制,它的基本内涵就是此在“在世界之中”,它表明了此在与世界先天的寓居关系。而“非之中”则是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中界限主体(主体的界限化)的存在机制或存在方式,其基本内涵为界限主体“不在世界之中”,它表明了主体和世界的特殊共界关系。从主体和世界的关系来看,“在之中”与“非之中”是两种明显互相对立的主体存在机制,具有互不相容性,但是,从实质上来说,它们都关涉世界之为整体,都是关于世界整体的一种超越机制,都与否定性相关。作为同时代的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为我们描述了这两种看似对立实则具有一定同源性的主体存在机制,这是非常有意味的,而且,对这两种主体存在机制的进一步揭示和比较,对于更好地理解主体本身及主体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非之中”的逻辑特性:无“外”的否定机制
“非之中”是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中主体的存在方式或机制。关于主体,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主体不属于世界,乃是世界的一个界限”[1] 72。换句话说,“哲学的自我并不是人,不是人的身体或心理学所论的人的灵魂,而是玄学的主体,它是世界的界限而非世界的一部分”[1] 72。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中对主体作了界限化的处理,即把主体作为世界的界限,而不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不是世界中的某种存在物,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主体形式——界限主体,界限主体的存在方式或形式就是“不在世界之中”。因此,它具有一种形式的逻辑结构,即“非(在……之中)”,将其名词化以后就是“非之中”。从逻辑的角度来看,“非(在世界之中)”的逻辑形态是“非P”,而“在世界之中”就是P,如此,我们可以通过非P以及非P与P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进一步理解界限主体“非世界之中”的逻辑特性。
在逻辑哲学中,P表示肯定命题,而非P表示相应的否定命题。P与非P之间具有如下逻辑空间关系:(1)~P(非P)在P之外。“任何一个命题只有一个否定……只有一个命题完全处于P之外”[2] 56e,而且是处于P的整体之外,因此,否定命题~P具有一种“在……之外”(outside)的存在结构;(2)~P依赖P,~P的outside结构意味着它不能独立构成,必须依赖P;(3)~P与P共界(P and~P have a common boundary)[2] 57e,即P与~P有着共同的界线。从这种逻辑空间关系可以看出,非P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在之外”特性,它在P的逻辑空间之外。从P和非P这种逻辑空间关系出发,结合“非(在世界之中)”和“在世界之中”的关系,我们来看看“非世界之中”以及“非之中”的一些逻辑特性。
“非之中”并不具有“在之外”的特性,它不表示“在世界之外”,它是无“外”的。按照一般的看法,“非世界之中”就意味着“在世界之外”,而且,非P的逻辑结构也显示出它具有“在之外”的特性,即“在P的逻辑空间之外”。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认为“非世界之中”就是“在世界之外”,“非之中”与“在之外”不是同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不在世界之中”并不意味着就“在世界之外”。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令人较为困惑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非P表示“在P之外”,而“非世界之中”却不表示“在世界之外”呢?这主要是因为世界整体的不可否定性。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是逻辑的世界,我们可以否定的东西只是那些在世界(逻辑世界)之中发生的东西。P作为一个事态(对应于命题P),是逻辑世界中的东西,因此,它是可以否定的,对P否定以后所形成的非P“在P的逻辑空间之外”,但这个“在之外”还是处于逻辑总体空间之中,而不是在逻辑(世界)的总体空间之外。也就是说,逻辑空间包括“在之外”这部分空间。相比之下,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外”,世界无“外”,这类似于“至大无外”,这样的整体不可能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因而是不可否定的。如果世界整体可以否定,那么,必然存在某个空间,它在“世界整体之外”,也在逻辑空间整体之外,如此一来,作为至大的世界整体和逻辑空间整体就不完全了,它就不是一个整体。维特根斯坦用具有无“外”性的“非之中”来表示界限主体与世界整体的关系,就是为了表明与“在之外”的区别,以防人们把界限主体看作“在世界之外”。因此,“非之中”仅仅表示“不在(世界)之中”,绝不表示“在(世界)之外”,它具有无“外”性。
就主体而言,“非之中”既“不在世界之中”,但同时又“不在世界之外”,那么它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实际上,它只是作为世界的界限而存在。由于没有“外面”,这样的界限只是一种内在的单面关系,也就是说,世界的界限只有“内面”,但没有“外面”。如此则界限不是由界限的“内面”和“外面”两个部分来共同划定的,不是像P和非P之间的界限那样是由P的逻辑空间和在它外面的非P的逻辑空间共同决定的。因此,对于世界界限的划定并不像在某个空间的中间画一条线,然后区分出界限的一边和另一边,或者区分出界限的“内面”和“外面”,而是仅仅从内面来划定的。这样的界限不存在共界性。至于划定界限的方法,它依赖于逻辑的肯定和否定,它是由逻辑中真的肯定命题和否定一起从内部来划定的。这样,“否定就作为某种属于逻辑形式(‘怎样’)的东西,和作为某种属于事实性(‘这样’)的性质……‘真’一起,可以指明世界的界限”[3] 55,即否定命题与其相应的肯定命题一起从逻辑的内面规定了某个逻辑空间,而当逻辑中所有的肯定命题和否定命题的逻辑空间都给出以后,整个逻辑空间及其界限就给出了,整个世界和世界的界限也就给出了(因为世界的界限和逻辑的界限是一致的)。因此,维特根斯坦强调哲学应当自内部通过可思者(逻辑的东西)为不可思者(非逻辑的东西)划界限[1] 39。
在“非之中”的问题上,维特根斯坦显然遇到了某种困难:一方面,“非之中”具有否定性的特性;但是另一方面,世界之为整体又是不可否定的,“非之中”具有无“外”性。怎样解决这种困境呢?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是把否定作为“非之中”的影子(否定在世界上投下了影子)[3] 55和原型来参照的。界限主体的“非之中”特性表明,它本质上具有一种否定性存在机制,而不是一种肯定性机制,它具有类似于否定形式非P的某些特性,但不具有非P的“之外”性。在“之外”的意义上,界限主体可以说不是一种否定形式。
二、“非之中”的形而上学特性:外在的超越性
作为界限主体的存在方式和机制,“非之中”是一种逻辑的形式和结构,但是它还具有形而上学的一面,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这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主要表现为对世界整体的超越性和对价值世界等“不可说者”的积极建构作用,而这种超越性是借助“非之中”的否定性形式通过界限主体来实现的,这是一种外在的超越性。
在此,让我们先来看看具有“非之中”结构的界限主体的一般特性。从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来讲,界限主体作为世界的界限而存在,它是一个极点(限),一个“广延的点”,属于主体系统中的一种“极限情形”。界限主体犹如重言式,又如算术中的零,它“正如‘0’之属于算术的符号系统”[1] 49,零和其他的数(如1、2等)相比同样是数,在数的质上,零不比1、2、3等数少些什么。界限主体的这种特性使其成为一种“零位主体”,这种“零位主体”是形式上的,不具有任何实在性的内容,但不是一种“无”,不是主体的消亡,它只是一种变换了形式的主体。为了更好地说明界限主体的特性,维特根斯坦用眼睛作比喻。他说:“一个玄学的主体……正如眼睛和视野的情形。但是你实际上看不见眼。而且在视野中,也没有什么使你推出:它被一只眼所看到。”[1] 72眼睛是实在的,它与其视野虽然密切联系在一起,但不可能成为视野的一部分。“零位”主体表明:“能思维能表象的主体是没有的”[1] 71,同时也表明主体不受制于世界的逻辑必然性。
这样一种形式的主体具有外在的超越性。界限主体“非之中”的否定性存在特性和“零位”特性表明,界限主体对于逻辑世界并不发生肯定性的建构作用,最多只是一种零性的符号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界限主体是没有意义的,界限主体的意义在于:界限主体所具有的“非之中”结构实际上是一种主体的超越性结构,是对“在世界之中”的一种超越。因为,“非”本身具有超越的意义,非P就是通过“非”以“在之外”的形式实现对P的超越的,“非世界之中”也是对于在世界中的一种超越性机制,只不过这种超越的形式不是否定词“非”所具有的“在之外”,而仅仅是“非之中”形式。维特根斯坦主体超越性机制的特点是:超越是关于世界整体的,是对于世界整体的超越,因此,界限主体的超越性与世界整体相关;超越是一种否定性的超越,即它是以否定命题非P为逻辑原型构建的,超越是通过“否定”来实现的,通过“不”、“非”等逻辑常项,以类似“非P”的形式,或者说以“否定的影子”来实现的;超越的方式或形式是“非之中”,而不是“在之外”,它是一种对于世界的离心的超越,因而是一种“外在”形式的超越。
界限主体的“非之中”式超越不是单纯的为超越世界而超越,它还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它通过超越世界整体以把握那些“非世界之中”的不可说者,如意义、价值等,起到建构价值世界的积极作用。界限主体对不可说者的把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价值世界的建构,二是从生存论意义上来把握世界的存在。就价值世界而言,价值世界是“非(逻辑)世界之中”的世界,但它依赖于逻辑世界,“关于上帝和生活的意义,我知道什么?我知道这个世界存在”[2] 72e;但是,仅仅依靠逻辑世界是不能够产生价值的,价值必须以主体的存在为前提,界限主体对于世界而言虽然是一种“零主体”,但它对于价值世界而言具有意志的一面,表现为“意志主体”,它是价值世界产生的逻辑前提之一,它是从逻辑世界到价值世界的纽带。
至于对世界存在和存在本身的把握,则具有神秘的一面。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价值世界和逻辑世界都依赖世界的存在。“为了理解逻辑所需的‘经验’并不是某物如何如何,乃是某物存在(something is)。”[1] 69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某物”存在是指“世界的存在”。世界的存在有其特殊的含义,它指的是如下的情形:一是指世界的整体,即世界的整体性存在,而不是世界中的个体或某个部分的存在;二是世界的存在不是指世界“如何”发生,而是指“世界已在这里”这一事实性;三是对于这种存在,我们不能说出它的理由,因为它是不可否定的,我们“不能想像它的不同情形,我们不能想像一个世界在某个时刻存在,而在另一个时刻不存在”[4] 77,因而也不能说它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形。因此,对世界的存在我们不能用语言去描述它,一旦去说就会陷入荒谬;同时也不能感到惊讶,“说我对世界的存在惊讶不已则是荒谬的,因为我不能想像它不存在”[5] 26。我们具有的只是一种神秘感,“神秘的不是世界如何,而是其存在”,对于神秘的东西,我们只能去体验它,而“对世界这样生存着的把握,就是对存在的把握,就是对根植于时间中的存在的把握”[6]。
界限主体通过“非之中”实现对世界整体(逻辑世界)的超越以把握“不可说者”的主体模式,这只能说是一种特殊的主体模式,是一种特殊的超越模式,虽然它具有独特的意义。但它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界限主体的“零”性特征和否定式机制所具有的依附性和符号性不仅消解了主体对于世界的建构作用,而且造成了实际上的二元性,即世界和世界的界限之间的二元性和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又造成了主体和世界的不可通约性,它把主体和世界分离并对立起来了。因此,这种主体的存在模式和超越方式是非辩证的。此外,界限主体是一种“大我”,明显具有原子特性和唯一性,这种原子性和唯一性扼杀了“他人”的存在,造成了一种无间性主体,使主体失去了与他人“共在”的层面。
三、“在之中”的形而上学特性:内在的超越性
与维特根斯坦“非之中”的存在方式不同,海德格尔建立了以“在之中”为存在方式的主体——此在,并以此确立了一种不同的超越模式。这里的“在之中”是此在的先天存在机制,它意味着此在“在世界之中”,“在之中”的先天结构是一种“向心的”内在超越模式。
海德格尔的此在理论是在对笛卡儿和康德主体思想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海德格尔在肯定笛卡儿“我思”主体意义的同时,着重指出了“我思”主体存在的缺陷,即主体对于“我在”的忽视,对于主体与世界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关系的忽视。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儿没有在“我在”的意义上,没有从世界和“在世”的角度来进一步阐述主体,这造成了主体和客体(世界)之间的对立以及对存在的遗忘。维特根斯坦界限主体的主要缺陷也在此。为克服这种缺陷,海德格尔用此在代替了“我思”主体,使此在与世界具有一种先天的“在之中”关系,“此在本质上就是:存在在世界之中”[7] 17,以此来建立“在世界之中”的主体超越机制。
当把此在的机制理解为“在之中”,并且使此在成为一种能理解存在的超越机制时,需要面临一个巨大困难:即此在一方面“在世界之中”,但同时又“超越世界”。因为一般认为超越的结构和特性就是把握整体,应该具有“在之外”或“非之中”这样的结构,而不是“在之中”结构,而“在之中”与“非之中”结构刚好相反,因此,要建立“在之中”意义上的超越性,就必须克服这种困境。海德格尔在建立“在之中”的结构的同时,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困境,并把这种困境描述成人的“在之中”的有限性和超越性的困境。海德格尔认为:“首先,每个形而上学问题总是包括形而上学问题的整体。它总是这个整体自身。其次,每个形而上学的问题都只能这样被追问,即:发问者本身包含在问题里面,也就是说,已被摆到问题中去了。由此,我们得到下列启发:形而上学的追问,是必须就整体来进行,并且必须从发问者此在的本质的处境中来进行的。”[8] 136简单说来,就是有限的人总是在整体之内,即以“在之中”的方式存在,而对整体的把握又必须处于整体之外。面对这种困境,海德格尔并没有放弃主体的“在之中”机制,反而运用“在之中”机制来实现超越。
为建立对于世界的超越机制,海德格尔首先对世界概念进行了重新解释。他认为,“在世界之中”的世界不是一种现成的世界,而是一种筹划的世界、可能的世界,是此在的“何所往”。他说:“我们把此在本身进行超越的何所往称为世界,现在并且把超越规定为‘在世界之中存在’。世界乃是超越的统一结构……”[8] 171这实际上意味着世界并不是一种超越的对象,它本身是一种超越的结果。世界本身就意味着超越,它是主体性的此在的一种筹划,具有“我属性”。
世界作为一种超越的结果,不是单个的和部分的存在,而是整体的存在。世界的形而上学本质在于:“它指的是关于与存在者整体相关联的人之此在的解释。”[8] 190存在者整体就是世界整体。在此基础上,此在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一种逻辑空间关系,因为逻辑空间关系不与世界整体相关,它们是一种先天的寓居关系。“之中”并不意味着空间关系,它不是一种处所,也不是一个在另一个之中。“‘在之中’有别于一现成东西在另一现成东西‘之中’的那种现成的‘之内’;‘在之中’不是现成主体的一种性质,仿佛这种性质可以通过‘世界’的现成存在受到影响或哪怕只是开动起来,引法出来;‘在之中’毋宁是这种存在者本身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7] 162“在之中”源于“居住”、“逗留”,它表明了此在“依寓世界而存在”、“融身在世界之中”的状态,这种寓居关系与世界的整体密切相关。
世界的整体性是通过“无”得以显现的,也就是说,此在与世界整体遭遇,是通过“无”来实现的,此在是通过“无”来超越的。海德格尔认为,“无”的基本作用就是使此在显现,使其自身成为此在,“这个原始的能不的‘无’的本质就在于:它首先把此在带到这样的存在者之前”[8] 145。“无”在把此在带到存在者面前的同时,也以有限的方式遭遇和把握了存在者整体。“此在将自身嵌入‘无’中时,就总是已经超出了存在者整体之外了。”[8] 146“存在者整体在此在之‘无’中才按其最特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才以有限的方式达到自己本身。”[8] 151因此,形而上学问题的本质就是追问“无”,或者说对“无”的追问启示着形而上学,这里的“无”比逻辑的“不”、“非”更原始。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还对“无”的根源作了进一步的揭示,认为与整体相关的“无”又是通过畏来显现的,“畏启示着‘无’”,“‘无’在畏中是与存在者整体浑为一体而露面的”[8] 144。
四、从“非之中”到“在之中”:从逻辑世界到生活世界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非之中”与“在之中”这两种机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表现为简单的逻辑对立,更主要的表现在形而上学方面:“非之中”表现为一种对于世界的“离心的”外在存在机制,而“在之中”表现为一种向心的“世界介入”[9] 58。如果把这两者作一纵向的考察则会发现,“非之中”和“在之中”具有某种承继关系,从“非之中”到“在之中”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当代哲学从笛卡儿经康德和维特根斯坦到海德格尔、胡塞尔等人的哲学历程,体现了从孤立的意识世界到逻辑世界再到生活世界的转变。阿佩尔认为:“笛卡儿的主体—客体关系不足以为一种认知人类学提供基础。一种纯粹的对象意识不可能独自从世界那里获得任何意义。为了获得一种意义构造,本质上‘离心的’意识必须向心地介入,也就是,它必须体现此时此地。”[9] 56这种“此时此地”就是对生活世界的介入,它具有“在之中”的形式和机制。
从维特根斯坦本人前后思想转变的过程来看,他从逻辑哲学到日常语言哲学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从“非之中”到“在之中”的轨迹。界限主体及其“非之中”结构是逻辑哲学的产物,是世界逻辑化以及语言分析代替知识论的一个较合理的结果:一方面,从逻辑哲学本身的发展及其特性来看,由于世界的逻辑语言化,逻辑和逻辑必然性主宰了世界,具有建构作用和自由性的主体逐渐从世界中被排斥了出去,因此,对于逻辑世界而言,“主体及其意向、灵魂等等之类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变得多余了”[9] 14,“能思维能表象的主体是没有的”;另一方面,主体又必须存在,因为没有主体的世界或思想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谓主体的消亡只不过是主体存在形式的变换而已,有鉴于此,维特根斯坦使主体界限化,形成了具有“零位”特性和否定性存在机制的界限主体,以此来克服逻辑必然性和主体的自由性、必需性所带来的问题,这不失为一种恰当的选择。但是,“零位”主体作为一种主体的“极限情形”,表明逻辑哲学已经走到了它的顶点,那种脱离世界的纯粹逻辑化的超越模式再也没有发展的余地和可能了,因而,“非之中”的逻辑主体模式逐渐为“生活世界化”的“在之中”主体模式所代替。于是,维特根斯坦在界限主体的基础上又向前走了一大步,放弃了界限主体,建立了语言游戏形态的主体模式,这也是一种“在之中”的主体模式,这种主体显然仍然具有先验性,但他是“生活世界”中的人,是语言的理解者,“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先验的主体就是理解精确语言的人”[10] 548—549。这种主体及其对世界的介入构成了“语言性的世界理解”。
但是,即使是同属“在之中”形式的主体,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主体和海德格尔的此在主体也是不尽相同的。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主体首先是一种语言意义上的主体,它主要依赖生活中的“我们”建立起来,其主体性表现在“我们的用法”这一语法特性上;而海德格尔的此在是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主体形式,表现为对存在的先天把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海德格尔思想的发展,其主体形式演变为一种整体性的“语言”主体,即“语言”“说”的形式[11] 2,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又回到维特根斯坦的界限主体上去了,因为维特根斯坦的界限既是世界的界限,又是语言的和逻辑的,而界限主体实际上就是一种整体性主体。
标签:形而上学论文; 命题的否定论文; 逻辑结构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主体思想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