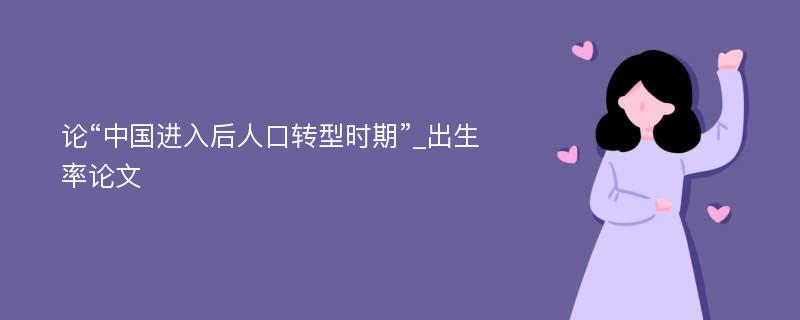
再论“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人口论文,时期论文,再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1999年下半年,笔者和李建民教授一同参加了国家计生委“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分别对中国人口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了回顾、评估和展望。在综合大量不同来源信息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可以做出中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期的大势判断。而后在如何描述中国人口低生育水平的措词上,颇费了一番脑筋。在一次由郭志刚教授、李建民教授和笔者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我们在如下说法上达成了共识:“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在未来几十年,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些观点或提法被随后的2000年中共中央8号文件和《中国21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所采纳。
那么,如何描述“新的发展时期”?在有关会议的讨论过程中,我们曾经提到“后人口转变”的概念,因考虑到可能会有争议,就没有写入有关文件中。但是,我们没有停止对“后人口转变”概念的探讨。在课题结束后,我们分别对“后人口转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发表了各自的观点。需要说明的是,对“后人口转变”的探讨不是文字游戏,也非哗众取宠。正如笔者在“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一文中所言:用“后人口转变时期”一词描述中国今后的人口发展,特别是生育态势或许词不达意,甚至是谬论。之所以使用“后人口转变”为题,旨在提示人们尽快跳出人口数量多少和生育水平高低的狭隘视野,更多地关注今后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质量、结构、分布和开发问题。同时,利用中国人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时机,探讨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未尽的内容,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理论。
最近,笔者高兴地看到了几位学者对“后人口转变”论点的质疑。学无止境,观点越争才能越明,这也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宗旨所在。以下是笔者对有人口转变和“后人口转变”的进一步思考,仅是个人的观点,欢迎批评指正。
二、如何理解“人口转变”和“后人口转变”
20世纪初期,西方国家的人口变动促成了人口转变理论的产生,而人口转变理论经过众多学者的修正、补充和完善,已经不仅仅是对人口发展历史的描述,作为一种理论,它同样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变动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当人口转变理论提出之时,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出现过稳定的零增长或负增长,但是,在几乎所有版本的人口转变理论都预见到了这一天的到来,而且这一预见正在某些国家或地区成为现实。法国人兰德里和美国人汤普森分别于1909年和1929年提出了人口转变的现象,而将这一现象概括和上升为一种理论的第一人是美国人诺特斯坦(Notestein,1945),其后的人口转变论都是对诺氏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当今社会许多人口问题并没有在人口转变理论中得到阐述。同所有理论一样,人口转变理论自诞生以来一直有争议。人口转变开始于西方国家,人口转变理论产生于西方社会,但是即使在西方国家,人口变动的原因和结果也是千差万别,何况将其应用到发展中国家中。1973年,美国著名人口学家AnsleyCoale(1973)对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发起挑战,并赢得了一批人口学家的喝彩。1976年,澳大利亚人口学家John Caldwell(1976)也撰文猛烈批评人口转变理论。对于人口转变理论的争论至今还没有结束,也不可能结束,但是,这并不影响人口转变理论在人口科学中的地位。在所有的人口学教材中,无不把人口转变理论作为非常重要的章节。
我们如何理解人口转变的概念呢?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将其复杂化,也没有必要去设定一个严格的标准去衡量人口转变是否完成的指标。只要我们能了解和掌握人口现象的数量关系及其规律性,并能正确运用于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就达到目的了。要在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找到一个已经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问题的答案是不可能的。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人口学理论通常将人口再生产划分为三种类型,即:“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简称“高高低”类型)的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简称“高低高”类型)的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简称“低低低”类型)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对人口再生产三种类型的划分,相信没什么疑义。按照联合国2000年的最新估计,世界人口在2050年前后将达到93亿左右,总和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降低到13‰和10‰,最终实现“低低低”类型。“高高低”类型已经是历史,“高低高”类型还能持续多长时间是可以遇见的,而“低低低”类型能走多远我们还不得而知。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人口转变”,就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过渡。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将几个过渡阶段描述为:第一阶段:死亡率首先开始下降,但出生率基本不变,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第二阶段:死亡率稳步下降,出生率也开始下降,但死亡率的下降速度快于出生率的下降速度,人口自然增长率居高不下,但势头放缓;第三阶段:死亡率逐步下降到了一个稳定的水平,变化不大,出生率也继续下降到了一个较低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相应地下降到了较低水平,最终实现了“低低低”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刘铮、李竞能,1985:109;张纯元等,1983:342;王胜今,1988:158;李竞能、吴国存,1992)。
在笔者看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只要实现了“低低低”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即可视为完成了传统意义的人口转变。至于“低低低”到底有多低,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高高低”人口再生产状态下,波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同样,在“低低低”人口再生产状态下,波动也将继续,但趋势是逐渐降低的,直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笔者认为,零增长和负增长是“低低低”人口再生产状态下的一种延伸,而不应该将其与“低低低”类型割裂开。如果一定要出现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状态,人口转变才算完成的话,那么,当70年代人口学家讨论西方国家的“后人口转变”时,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真正完成人口转变的过程。直到今天,法国的人口也没有出现负增长。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估计是20~25年后,法国才会出现人口零增长。谁能说法国还没完成人口转变?
那么,实现了“低低低”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后,还往哪里“转变”?是否还有第四种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到第四种再生产类型要经过几个转变阶段?其实,人们并不清楚未来人口将“转变”到哪里,但是,不清楚不等于不存在。正如在实现了工业化社会后,人们不知道会出现新经济时代和信息化社会一样。由于各国各地区人口问题的多样化难于一言以蔽之,于是人们简而言之,将完成了传统意义上转变的人口叫“转变后的人口”,而为了与有些现有词汇对应,如“后工业化社会”,人们套用了“后人口转变”的概念。当然,也有一些人口学家使用其他的词语来描述转变后的人口变动状态。1986年,荷兰人口学家莱萨赫和冯德卡首次使用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来描述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欧人口变化的模式(Lesthaeghe and Van de Kaa,1987)。在他们的文章中,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基本特征概括为:(1)协议同居家庭数量上升。(2)非婚出生大幅度增加。(3)从一而终的男女减少。(4)初婚初育年龄大幅度提高,年龄别生育率高峰后移。所有这些特征都是因为生活方式的巨变,价值观念从利他主义向利己主义转变的结果,辅之以性道德观念和避孕技术的发展。当然,如同人口转变的讨论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
综上所述,“后人口转变”不过是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完成了一个转变阶段,开始进入了“低低低”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时期而已。至于“后人口转变”的阶段、内容和长短,人们并不清楚,这要经过若干年后由未来的人口历史学家来总结。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不是进入了“三低”是一回事,而“三低”状态是如何实现的,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则是另外一回事。“三低”人口再生产类型条件下的人口问题可以说是千差万别的,因为每个地区进入“三低”的手段、时间、条件各有不同,决定了“三低”下的人口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些人口现象在一个地区或许是问题,而在另外一些地区或许不是什么问题。
无论用何种指标来衡量,今天的中国人口都进入了“三低”状态。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是不争的事实。1998年,联合国开发署和人口基金在一份文件中称“泰国已经完成了其人口转变的历程”;大量文献称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完成了人口转变(如John Bongaarts,1998);2000年,美国兰德公司劳动力和人口部的出版物,明确使用了“中国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词语(RAND,2000)。
尽管中国的人口转变还不成熟,还有人为的因素,但至少从不同来源的统计数据和估算上看,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低生育和低死亡时期。用“后人口转变时期”一词描述中国今后的人口状态,无可非议,关键是要正确理解其内涵。长期以来,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是控制人口增长的势头。人口研究工作也是紧紧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探索,并对实际工作进行了指导。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人口增长的势头已经得到了控制,今后中国人口增长的力量来自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而不是由于生育水平高。因此,今后的主要任务是稳定低生育水平。
没有人否定人口数量问题是目前中国的首要问题,更没有人说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头等大事。问题在于,在人口数量问题、质量问题、结构问题、分布问题和开发问题等诸多矛盾中,控制人口数量是相对简单的工作。我们都承认,进入新世纪后,中国人口问题更复杂化和多元化了。问题复杂在哪里?除了人口状态发生了变化外,国际国内形势变了,经济体制变了,人们的观念变了。相应地,在确保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内容和方式要转变,人口理论研究要前瞻、要创新、要深化、要发展。一味地在一些陈旧的话题上翻来复去,无助于判断复杂的形势,也没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在众多复杂的问题中,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宏观发展趋势,才能使我们拨开重重迷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国外学者的评论
为了深入理解人口转变和“后人口转变”的概念及其在中国的应用,笔者与国际上部分知名学者进行了网上对话,以期得到他们对中国是否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的评论。
在联合国人口基金技术与评估处工作的人口学家Richard Leete博士认为,无论用谁的人口转变论来衡量,中国人口再生产都已经完成了传统的转变过程,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早在1987年,Leete博士就指出,一个地区的人口只要生育率降低到了一定水平,并持续一定的时间,在正常情况下(除非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或中国1960年前后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生育率不会有持续的反弹,就可视为处在“后人口转变”时期(leete,1987)。传统的人口转变论从来没有对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做出明确的界定。
美国密执安大学人口研究所的John Knodel教授对人口转变和“后人口转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出现转折性变化时,人口学家总是会在一些问题的判断上发生争议。他说,千万别太在意“后人口转变”这一措词,其实它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定义。过去人们的生育行为是没有约束的,也没有条件控制,是原始和自然的,而现在的家庭规模可以由夫妇按合理的计划,进行有效的控制,这就是人口转变。请相信,群众是真正的决策人,只有他们最清楚自己应该生几个孩子。中国政府采取与众不同的强硬措施,要求每个家庭生育固定数量的孩子,但是具体的目标从来没有真正实现。直到最近几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才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逐渐与政策要求接近,为什么?因为中国变了,中国人变了,生育观念变了,而不是生育政策变了。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适度人口状态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中国的方式就是其中之一。无论如何,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们在过去几十年中,没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育。如果政策放松,生育水平会回升。自然的,中国的人口学家对使用“后人口转变”论提出批评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中国的生育政策会放松吗?如果你用我的定义,中国毫无疑问完成了传统的人口转变过程。至于能否使用“后人口转变”的概念,要看你是如何解释其中的内容。
Knodel教授最后提示说,假如中国公布的数据是真实的话,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8,那么,中国的人口学家应该小心地应对将来的人口发展问题,仔细研究低生育水平下可能出现的人口问题,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美国人口理事会人口学家John Bongaarts先生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是指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的一个过程。人们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比较清楚,但是,全世界的人口学家在如何界定人口转变结束的定义上从来没有形成过一致的意见。1970~1975年间,欧洲国家许多人口指标与中国90年代的情况非常类似,如总和生育率为2.3,出生预期寿命为70岁,出生率为17‰,死亡率为10‰,婴儿死亡率为32‰。唯一不同的是,欧洲当时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达到了10%。与人口老龄化相伴的现象是死亡率也比较高。但是,中国80年代开始讨论人口老龄化现象,90年代已经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70年代,人口学家开始讨论西方国家的“后人口转变”问题,那么在相似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不能讨论?问题在于,如何认识人口转变和“后人口转变”的概念。John Bongaarts说:“我对于是否完成人口转变的要求比较苛刻,那就是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死亡率必须在低水平上等于或高于出生率才能称为完成了人口转变,按照我的标准,目前只有欧洲个别国家进入了所谓的‘后人口转变’时期”。
美国加州大学Irvine分校的Susan Greenhalgh教授回答说,按照我的理解,提出“后人口转变”是为了告诉人们中国人口状态出现了新的局面。从理论上看,人口转变的概念没有解决完成状态一端的问题,因为世界人口总是在不断变化。任何宣称某种状态成为历史的概念总会引发争论。看看今天的俄罗斯,你说那里的人口转变是什么状态?传统的人口转变论假设人口变化的方向是单一的,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人口转变实践证明,这一假设不成立。为此,她提出若干可以选择的说法:(1)区分第一次人口转变与荷兰人口学家莱萨赫和冯德卡提出的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然后检验中国的情况。(2)区分生育转变和人口转变的概念。我们可以说,中国已经完成了生育转变,但是还没有完成人口转变。John Bongaarts和Susan Greenhalgh都认为,将人口出现负增长作为人口转变的标志更有把握。(3)区分人口转变完成的形式和内容。人们可以不在乎措词是否恰当,只要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都比较低,就可以广而言之人口转变已经完成。但是,人们要注意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和稳定要依靠行政力量,要确保不反弹。(4)区分中国整体人口转变、中国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人口转变的状态。(5)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而不把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
她最后说,事实上,只要你能自圆其说,用什么词汇并不重要。她提醒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或许会修正我们讨论的结果。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的Charles Westoff教授认为,低生育水平是每个国家都要经过的一个阶段。一旦生育水平降到一定程度后,再回头不容易。中国政府即使不干预人们的生育行为,生育水平也会下降,只不过速度会慢一些。目前欧洲国家的生育水平确实很低,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东亚的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日本和韩国,生育水平也很低。但是,他对用“后人口转变”一词持异议,因为他对“人口转变”理论本身就不敢苟同。
美国东西方中心的Griffith Feeney教授的观点较为委婉。他指出,从历史上看,人口学家对于生育水平的预测没有什么成功的记录。谁会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了生育水平的巨大反弹?谁会想到中国的生育水平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如此大幅度的下降?中国的人口形势与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同,但生育水平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后再反弹的可能性不大。在他的评论中,没有提及人口转变和“后人口转变”问题。
以上人口学家的评论各有独到之处。在与他们的对话中,笔者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应该加强人口理论的基础性研究,应该根据中国特殊的人口转变之路,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理论。中国的经验要靠自己总结,人口问题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解决。任何西方的理论和模式必须经过批和判才能应用到中国的实际。
四、尚未结束的讨论
同所有国家一样,传统意义上人口转变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也不等于人口压力的减轻,更不能说人口与计划生育使命的结束。应该说,高生育水平下有人口问题,低生育水平下也有人口问题,而且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口问题更为复杂。作为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口问题具有普遍性,但更具有中国的特殊性。
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只是标志着中国人口发展开始了一个新时期。这一时期到底有多长?没有人知道。这一时期会出现哪些人口问题?我们只知道一部分。中国特殊的人口转变之路决定了至少在2010年前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首要的任务是如何稳定地区分布不均衡的低生育水平。但是,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瞻前顾后,面对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不同,一个生产周期为一代人,预见到的问题,现在不谈不议,等到“人口的冬天”来临之际,不知要等多长时间才能迎来下一个“人口的春天”。
最后,笔者愿对如下问题阐明观点:
第一,我们对中国人口转变的认识,是基于对中国人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了解,是将中国人口转变放到了国际国内大形势下进行的判断,并没有脱离中国的国情。
第二,我们并非仅仅从人口统计指标的变动来判断中国人口状态,其实中国人口出生、死亡水平的变化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
第三,我们提出“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论点与稳定低生育水平不矛盾,更没有掩盖控制人口数量仍是中国目前的首要问题之意。就中国的特殊情况而言,人口转变完成之前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工作重心是降低生育率,而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稳定低生育水平。
第四,感谢其他学者的质疑。所有新的理论和概念都是在批评中成长和完善的。人口科学要发展,需要更多的批评家。在“后人口转变”的定义上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统一认识,这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
最后,笔者坚持认为,中国人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无论用“后人口转变时期”、“转变后的人口”,还是“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其实并无大碍,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