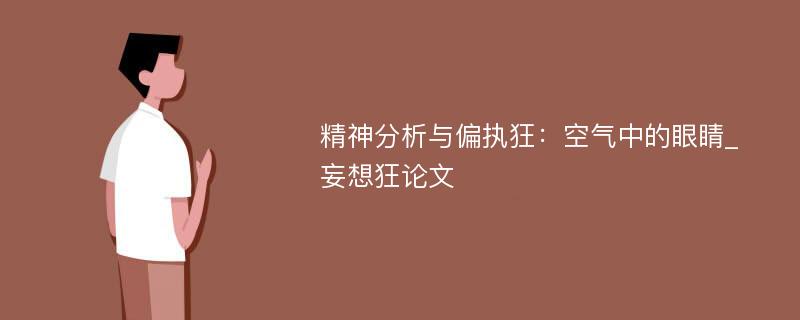
精神分析和妄想狂:空中的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妄想论文,精神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后现代主义和妄想狂
威廉·克里甘(William Kerrigan)和约瑟夫·史密斯( Joseph Smith)在他们合译的德里达的《我的机遇》(Mes Chances)一书的引文中,拟定了一条简单而又切实可行的描述后现代文本的准则:文学后现代主义是“话语的不确定性的回归”。在他们二人看来,后现代的叙述经验往往是与对事件的某种认识的专致与信奉相结合的,而这些事件却无法从外部得到证实,它们是对“话语的不确定性的赞美”。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在《后现代条件》(The Postmodern Condition)一书中对后现代主义持有更富哲学性的立场,尽管他的观点依然围绕着信仰问题展开:利奥塔德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失信于元叙述”。尽管上述两种论点侧重不同,但它们——对话语的不确定性的赞美和对有保证的权威性话语或元叙述的失信,都与某种“妄想狂”视角相一致,而这一视角则拒绝已被广泛接受的权威性或同一性的对现实的认识(正常人所公认的现实),即使是在维持一种“不确定”的话语(妄想狂的对事件的另一种认识)。这里我想提出,就其是一个从根本上讲属于投射性行为之结果这一点而言,后现代话语是“妄想狂”的。在这种投射性行为中,叙述被读作具有个人特有的和意外的视角的功能,而非任何可考证的甚或相一致的对现实的记录。
就上述论点作点发挥(在我早些时候的著作中),我已经就后现代文本提出了文学上和理论上的四点特征:(1)后现代文本是重复性的, 在想要重复的冲动的驱使下,它无法摆脱引用和循环式的叙述模式;(2)后现代文本充斥着后果、遗迹、过量、碎屑:的确, 它好象目击了一个全球性的灾难,生理的、历史的或美学的,包括笛卡尔式理性主体的破裂;(3)后写作反映了合法性所面临的深刻危机, 包括语言作为指涉的权威性,对于语言理解和说明它所创造和面临的世界的能力提出质疑。显而易见,它也怀疑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有机的观点;(4)后文本倾向于喜剧性模式,其油滑的语言小丑常常有助于贬低权威(例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他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1992)一书中,注意到了后现AI写作作的拼凑倾向)。
当我广泛地读了一些后现代小说后,我又补充了第五个特征:后现代文本往往反映一种自由流动的妄想狂。的确,我已经提到妄想狂的特性在文章开始所引用的那两个论点中看得很清楚——史密斯和克里甘的对一种无法验证的话语的“回归”:因为这种不可验证性最终代表了妄想狂本人特有的对世界及其事件的认识的“确定性”。这一观察问题的视角同样也适用于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个定义,即利奥塔德的“对元叙述的失信”。因为元叙述仅仅是,以文字表达出来的事件的一致性体系,对普通人所珍视的历史的目的论的阐释(例如人们对于进步和启蒙的深信不移)。
有趣的是,拉康认为妄想狂的代表特征是不相信(Das Unglauben),一种对于象征界的保证性的不信任(《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妄想狂对事件和原因的认识与有理性思维的正常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正如拉康所指出的,“正常”人通过与象征界达成协议,此界保证被体验的现实是有意义的,并且存在于他者(作为意义的保证者)的主体间性的网络中。然而,妄想狂则拒绝达成关于象征的协议,根据协议,“现实”得到作为“假定能够认知的主体”的他者的保证;妄想狂对于被他者(大O)保证为意义所在地的象征界失去信心。而且,作为权威所在地的这一充满变化的王国是杰出的元叙述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相信诸如进步和理想这类得到象征界的他者保证的固定概念。妄想狂不相信他者,而去建构另外的信念,即拉康所谓的“他者的他者”,一个建立瓦解显而易见的象征界的体系的疯狂的迫害者,使“现实”与其他人眼中的现实不相符合,而且提供对现实中任何事件的解释:人们联想到O[,z]国巫师的闻名于世的最后精彩时刻,“伟大的巫师”,在同一性的现实中备受推崇,被“披露”出真实的面目,也即一个他者的他者,一个在幕后操纵绳线的人。或者以另外一个儿童故事为例,妄想狂实际上认清了象征界的盲目的自动作用,认清了“皇帝什么也没穿”。(换句话说,妄想狂不相信皇帝的衣服是华丽的——这一在象征的契约层次上被确认的现实——他知道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他暗中参与了主导外表的密谋。)当然,正如弗洛依德提出的、经过拉康确认的,他者的他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妄想狂本人——他虐待的意识是他自己的无意识信息,然后又以颠倒的方式返回到他自身。妄想狂不相信,他知道,因为他自身就是他所证明具有的知识的无意识源泉。当他说话时,他便说出一个不受他者的象征性社会现实影响的真理。
假定妄想狂与象征的失真有联系,或与话语的不可验证性有关,那么妄想狂形式出人于许多后现AI写作作这一点就毫不奇怪了。我们在许多后现代作家的作品中发现,它们都存在着一个相似的主题关系——在巴恩斯(Barnes)、品钦(Pynchon)、奥斯特(Auster)、 罗伯—格利耶(Robbe Grillet)、埃米利·普拉格(Emily Prager)、 希利·哈斯特维特(Siri Hustvedt)、 巴塞尔姆(Barthelme)、 德利洛(Delillo)、 埃柯(Eco)、 卡尔维诺(Calvino)、 凯西·阿克(Kathy Acker)、昆诺(Queneau)、佩拉克(Perec)等作家笔下, 主人公感到被注视,被来自天空的眼睛审视着;陷入一只全方位的深讳莫测的密谋的手中;或者被来自无法看见的地方的“白色噪音”的饶舌声死死纠缠着。与他们的现代主义前辈不同,后现代作家不是简单地重现了自我指涉的兴衰。他们远非沉浸在自己内心世界的崇高与博大之中——尽管备受折磨——但这些后现代作家笔下的人物似乎都遭受着来自莫名之处的胁迫,被神秘的人物纠缠着,生活在一度遍布的、无从捉摸的、罪恶的阴影下,而主人公则是既无法思索出也无法触摸到这一阴影。这些主人公的脑海里翻动着生命之谜,深受其苦,没有形而上学的现代厌恶感,而有着某种类似侦探所特有的强迫性,受到要侦破事情真相这一动力的驱使。但是,这种对系统的着魔,对列表、发现和说明的迫切需要,往往引发误入歧途的调查,以及随之而来的类似小说或剧本的剧情说明——于连·巴恩斯(Julian Barnes)笔下的文学史家发现福楼拜的真正的鹦鹉有无数系列的“原本的”模本;尤奈斯库(Ionesco)笔下的阿夫迪在柜橱里放有一具巨大的尸体,象麦西(Macy)的游行气球那样,不断地膨胀,在突发的时刻从衣橱里冲出来。同样地,在《亡父》(The Dead Father)中,巴塞尔姆(Donald Barthleme)的小人国英雄,拖着一个巨型父亲的尸体横贯原野,一路上以尸体为食。
啊——一具父亲的尸体——精神分析的确为妄想狂的后现代场景设置了舞台。什么是妄想狂?又是谁想知道?(我们想一下为什么如此多的“后现代”作家是男性,而且, 和斯皮瓦克(Spivak)和斯各尔(Schor)这类女权主义理论家一起,思考这种极富性别特色的、 以男性为主的、妄想狂作为病态的表现,进行这样的思索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但这将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
我对后现代文本的阅读来自关于妄想狂的两种心理分析结果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弗洛依德关于施莱伯(Schreber)的论文——他关于女性妄想狂的短文和拉康在系列演讨会之三和《精神分析的四项基本概念》中阐述弗洛依德著作的文章。的确,所有这些理论思考均围绕着投射(projection)和内投射(introjection)这一概念,以及在一个共同的视野中的清晰可见的相关性概念。这样,这些理论便从不同的侧面合成一个基于象征、想象和现实相互间作用的复杂位置。这里我不仅想探讨投影或自居作为后现代主认公的一则后标志这一问题,而且要提出我的论点,即后现代文本的妄想狂语气给写作行为本身打上了烙印,不仅在主题上,而且在结构上影响了写作本身。因为正如精神分析学家很清楚地指出的,妄想狂与惧怕不同,甚至在它互为主体的自居性机制这点上,与焦虑也不同;妄想狂模糊了幻想与现实,正面英雄与反派人物之间的界线,甚至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界线。
二、弗洛依德的妄想狂式叙述:作为后英雄的施莱伯医生
在关于施莱伯医生的著述的著名分析(1911)中,弗洛依德告诉我们,妄想狂是执迷于自恋状态而导致的紊乱,它导致人的力比多转向内部,或者被固定在一个类似的物体上,从而引发同性恋趋势。在施莱伯医生的案例中,弗洛依德认为,妄想狂是一种防御措施和应变策略:心灵通过向外投射力比多冲动而趋赶同性吸引,从而使冲动得到转换和掩饰,以迫害和侵略的面目出现,而非爱情上的俘获。(这在弗洛依德著名的语法例子中得到显示,追溯“我爱他”和“他恨我”之间的转换,其信息作为威胁回敬给它的发出者。)施莱伯的迫害式幻想和对声音的倾听伴随着全知的幻想,制造出一个完整的宇宙系统的紧迫感以及世界末日的幻想。在施莱伯的叙述中,迫害者,他者的他者,是上帝本人,与他直接交流,上帝将他当成自己的情妇,后来又沦为上帝的牺牲品。弗洛依德告诉我们,这是投射式思维的一个主要例子——施莱伯的同性恋,向外部投射,把“被解释的”作为同性恋式的侵略归还给他,也即一种宇宙系统化的能量,体现在一个痛苦的、神经和射线组成的网络中,这一能量最终甚至威胁到上帝本人。
如此这般,投射性思考便成为幻想的动力,驱动着精神病式的幻觉。许多弗洛依德主义者的确强调投射性思考在妄想狂身上占有主导性,而非迫害性幻想,因为妄想狂不仅是一种病态,而且是一种感知和思维的模式,这二者的区别仅仅是程度的不同;诚然,许多正常行为也具有妄想狂的色彩,特别是我们想要事先预见他人的反应并与之协调一致所采用的反射性模式。(例如,这是侦探采用的策略——杜宾或福尔摩斯——在后现代意识和注释中如此鲜明——它同样也成为作家本人的策略。)
颇有意义的是,在施莱伯的案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后现代小说中出现的主题和先见的轮廓:宇宙论的幻觉,世界末日的幻想(如奥斯特的《在最后一点东西的国度》(In the Country of Last Things), 维安的《阳光泡沫》(L'Ecume des jours), 昆诺的《蓝色的花》(Les Fleurs bleues),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 贝克特的《晚会的收场》(Fin de partie)等作品)。 以曾经被爱过的满怀仇恨的迫害者为中心(品钦的《葡萄园地》(Vineland)中的未出场的母亲,巴塞尔姆的《亡父》(Dead Father); 希利·哈斯特维特的《障眼物》(The Blind fold)中的拒绝的情人等);百科全书式的详尽的宇宙或系统的建构(瓦尔特·阿比什的《依字母排列的非洲》(Alphabetical Africa);佩雷克的《生活:使用者的手册》(Life:a user's Manual等。);以及对细节和数据增殖的极度关注(如尤奈斯库、品钦、佩雷克、萨洛特;这种增殖的一个特别恰当的例子与侦探和侦探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有关,可在哈斯特维特的小说《障眼物》中觅见,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受雇于一位城市隐士,其职业是提供精神病患者对一位被谋杀的女人的财产的精确描述。)有时,这些数据看起来象一个背景噪音的增殖(如德利洛的《白色噪音》之主题)的确,正如弗洛依德笔下的女性妄想狂,错误地将自己在情欲高潮时的悸动当作一架隐蔽的相机的喀嗒声,许多后现代主人公也被难以解释的噪音缠扰着,实际上是内部噪音向外投射;因为谣言——贝克特所指的那种唠叨——可以当作一种妄想狂的建构,它不是背景噪音,而是后英雄自己心灵之轮转动的声音。
同样,关注细节的能力也成为后小说无法摆脱的顽固特性,它是困扰许多后主人公的祸患,诸如罗伯-格利耶笔下的侦探或奥斯特笔下受调查的记者,或佩雷克笔下的脱离躯体的叙述之眼(如《生活:使用者的手册》),一架漂浮着的相机,随着它描绘由楼梯联接起来的各个不同公寓内的场景,它进入到一个语言的谜宫,并且探究这些住户的生活故事彼此交缠错绕而成的谜团。所有这些作家的当代俄底浦斯们均构成了一个神秘离奇的发现,就写作中隐含的线索进行解码:最终,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发现,他们在嵌有代码的城市迷宫中追寻的那位神秘的罪犯,他们所怀疑的对象正是自己,而非任何他人。这里的秘密调查者实际上是一只秘密的眼睛,一个妄想狂式的迫害者,他的指控的凝视最终还是转向了自身。
俄底浦斯的另一种回声出现在后现代神话中:在许多这类作品中,一位死去的或沉默的父亲——戈多或诺特——凌驾于、盘旋于小说中描叙的事件之上,尽管他们并不出场,或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人物。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这一凌空盘旋的他者,看起来象超个人的残渣余烬、被杀害的父亲的残余躯体、或阴魂不散的父亲的尸体,即使在他的法则已被摧毁、驱散,或更糟糕的,被一个毫无价值观的后现代代码和全然表演性的控制论法则所替代。就好象这位死去的父亲、这位导航人、这位能指,在一个否认或抛弃的行为中被主体驱逐出来(弗洛依德的那种拒绝),仅仅以一个隐约呈现的威胁、一只盘旋天空的眼睛回归一样,这只漂浮的眼睛监视着荒凉的后现代世界。
有趣的是,在阿瑟·克罗克和大卫·库克的扰乱人心的书《后现代景观》(The Postmodern Scene)中,后现代的主导标志是脱离躯体的眼睛,一个间谍卫星,克罗克和库克在CBS 的团体象征中激发了它的具体化身,即富科《戒律与惩罚》的圆形监狱,马格利特(Magritte)的空洞的、有着反射性的眼睛,甚至在《液体天空》(Liquid Sky)这一迷信电影中飘浮可见的外国人。这一脱离躯体的眼睛也令人忆起克里斯蒂瓦的《黑色天空》(Soleil Noir), 乔治·巴塔耶的色情作品《眼睛的故事》(L'Histoire de L'oeil)中上下颠倒的眼睛。较为近期的,当然是CNN的摄像机成为最大限度漂浮着的眼睛, 将战争当作媒体新闻进行现场报导。的确,库克和克罗克的后现代世界只是一个全球性的信息网络,其中人这一主体,不仅沦为透明的,而且是无助的甚或返祖的东西。因为在这一荒凉的结局中——预示着俄底浦斯互主体的终结——实际上,现实和电话中的性(这两类都属“投射”)代替了真正的人与人的接触。同样,更具扰乱性的是让·鲍德里拉(Jean Baudrillard)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颇有影响的文章《交际的狂喜》(The Ecstasy ofCommunication),以及他最近的著作《罪恶的透明性》(TheTransparency of Evil)鼓吹“社会之死亡”,在那里漂浮的眼睛引发了互主体对话的内向爆发。鲍德里拉的幻觉散文编织出一个孤独的个体的未来主义世界,一个卫星人漂浮在类似宇宙飞船小舱的空间,受着实在现实以及一场终极的游戏机游戏,“交际的狂喜”的支配。在这一极乐线路中,主体成为某种屏幕,一个纯粹信息发布仪式的平面终点,它代替了痛苦的社会接触(即人们互相交谈,而非互相交流信息)。线路上的交流代替了面对面的接触。
现在,这一后现代的媒介的世界与施莱伯医生建构和投射的世界惊人地相似,正如弗洛依德所说,医生一连数小时全神贯注地静坐着,沉浸在“极度兴奋的状态”中,思考被他称之为上帝的巨大神经网络,经受着内部声音喧泄的折磨,此时他正预示着一个完整的宇宙系统(实际上他与网络在线路上交流)。在施莱伯的案例中,上帝自身是一个与沉浸在狂喜中的主体相连接的终点,一只罪恶的、满怀敌意的眼睛,它俯瞰着世人,而不是所谓法律和价值的施予者。的确,正如我的这些简单例子所表明的,我所引述的和在施莱伯案例中展现的妄想狂的所有倾向,都非常显著地表现在后现代小说和理论中:关于迫害的幻想,精密系统的建构,内部现实语言的或其它方面的向外投射,恢宏壮观的规划。被漂浮的眼睛监视着,后现代主人公在恶魔式的冲动驱使下,去阅读隐含在罪恶的自然景象中的线索,可能为了赎回这个世界,或至少拯救其自身。
因为投射思维是妄想狂状态的印记,而且,后叙述与梦幻有着某种共同之处——反映作者的愿望、在“景象”的掩饰下,执行某项意愿的实现的预示性投射。正如弗洛依德所指出的,梦想是还现实的愿,在梦中“假如”成为“已经”。在这些术语中,妄想狂成为恶梦式的梦想,在妄想狂臆想中“假如发生……怎么办”成为“噢,不,不是那样的”。在梦中,正如在妄想狂的幻想中,愿望被当成一个可塑性情景、一个揭示“退化性”的梦的技巧的剧情概要,这些梦的技巧诸如泛灵论、抽象之具体化、做梦者对其它人物和事物的影响的位移。
实际上,许多后现代文本似乎是以一种梦幻的、预示性的模式写作的,其中欲望的摇摆塑造了文本,有一条细微的界线区分愿望的实现泛灵论和妄想狂投射。在这些经常陷入妄想狂恶梦的文本中,读者通过被故事深深地吸引而分享了迫害的终极幻想。而且,人们通常认为,写作本身也有一种妄想狂的层次:读者充当某种“监视者”,“天空中的眼睛”,伏在作者的肩膀上鸟瞰世界,因为她能预示“读者想要的是什么”。
三、拉康的后理论:重访妄想狂
在这些问题上拉康的见解是很有帮助的。他曾在系列研讨会之三中断言,妄想狂是对知识、信仰和语言的质疑。他以“谁在说话?”这一问题开始分析妄想狂,这正是所有互主体的语言的中心。当然,对于拉康来说,语言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二元体,一个有待破译的含有代码的谜——主体通过它以颠倒的形式从他者那里获得信息。(著名的《失却的信件》作为“始终达此目的”之例子,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在拉康看来,语言有两种形式:既是忠实的语言(Fides), 语言的自身输出,将他者当作物体占有(“你是我的女人”);或者是虚假的语言(谎言),以隐蔽的形式输出信息(拉康著名的例子便来自弗洛依德的玩笑书,即广为人知的关于两位犹太老人在他们去克拉科(Kracow)的路上发生的趣闻,问话人将真情当作谎言来读,他报怨道:“你为什么对我扯谎,说你要去克拉科?而这样一来我却认为你是要去什么别的地方,而实际上你真的去了克拉科!”)我们很容易从听者对于真情充满了警惕的反应中看出,这一投射性自居带有妄想狂的一面。因为第二位老人并不把象征界当作可靠的信息加以信赖——他转而依赖妄想狂知识,将自己放在他者的位置上,以颠倒的形式接受信息。坡笔下的侦探杜宾(Dupin)(见关于《失却的信件》的讨论)象其他侦探一样, 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也依靠妄想狂式的推理来察获实情。
拉康强调所有交流行为中的妄想狂本质,他这样来进行描述:语言总是互主体性的,因此总存在一个未知的因素(“语言使他者说出如此这般的话——即令人无法知道实情的话。他者作为绝对的他者,构成谎言的因素正是令我们无法知道它是否是谎言的因素”。)
在系列研讨会之三第三章中,拉康继续探讨了他自己的一个案例,值得注意的是,那是一个女性妄想狂。当她在楼梯上遇见一个臭名昭著的追求女色的人,并告诉那人“我刚刚去过肉店”,她抱怨也听到了一种声音,可能是那屠夫的声音,骂她是“猪”,这骂名具有鲜明的性内涵。拉康坚持认为这个回答是个错觉,象征这位妇人对那位漂亮的猎艳能手的欲望,特别是她坚持此辱骂的性本质(她暗示,猪在屠夫那里被填满并且被肢解)。因此,拉康坚持认为这段妄想狂话语有投射和证明的本质:
在妄想狂话语中,当主体对你说起他自己时,他便成了一个客体,即他者的迫害对象。她自己的某部分谈论着他者(小他),那个她在楼梯上遇见的男人,而且能够嘲弄他[…]但是,还有另一层意思,她在谈论她自己,她在和我谈论某个有生命力的东西。简而言之,她目睹——目睹了她信以为真的迫害。
换句话说,妄想狂的语言是对他或她的信任的考证,这在正常人看来,出于他们淡漠的观点,是对事情的不信任。但是拉康告诫我们:“淡漠的交流是失败的证明,其中人人均认同,意见一致。这是知识传递的理想模式——语言给出了每个人都同意的证据”。与此相反,妄想狂的语言,交流的是全力以赴的证明,而不是淡漠的信息。
无论如何,拉康认为,某种妄想狂是我们获得主体间性知识的方式,这些知识是关于联系、关于现实的,而不是关于真实的。因为通过使用投射思维以及他自己的推理能力,将自己置身于他者的地位,妄想狂从有关这类对象的所有知识中寻求共同点,他制造联系,通过代替他者来创造情节——人们想起了《富科的钟摆》(埃柯)或《49号的叫喊》(品钦)的“情节”。(在他最早期的有关妄想狂知识的讨论中,拉康用比喻来阐释他的理论:三名罪犯被带去看两个黑补丁和三个白补丁;每个补丁被固定在一个人身上,然后将他们留在一间房子里。第一个判断出他背上补丁的颜色的人可获自由。每名犯人都认为他背上的补丁是白色的,沿着同样的思路:设想假如他的是黑色的而另外两位会有什么行动,等着他们去行动,而他们却无动于衷。)拉康认为,这种转换主体位置的能力是一种基本的人性,而非病态:“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源于妒嫉的辩证法,它是交流的基本现象。小孩的传递方法是,当他说他人打了我时,他没有说谎,他就是这个他者”。
投射自居的妄想狂结构是区分人类世界和动物世界的基础,动物世界里没有物体间的本能接合:“使人类世界成为充满众多客体的世界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兴趣的对象是他者欲望的对象(即某种主体的传递是必要的,允许主体转换到他者的位置)”。这种传递是镜台效果,其结果是无意识总是暗示着斗争,暗示着与以入侵者面目出现的他者不可共存:
[……]自我的初始综合基本上是他我(alter ago), 是被离间的(自我的自恋式构成)。想要的人口主体是围绕一个中心建构的,这一中心,就他赋予主体他的整体而言,是他者,第一个与对象相遇的是作为他者欲望对象的对象[…]一个原始的他性包含在这个对象中,就原始意义上它作为竞争的对象而言[…]
所谓的妄想狂知识是建立在妒嫉的竞争基础上的,通过主要的自居过程,我以镜台的方式试着定义这种主要的自居。语言征服竞争,达成一项协议——这是你的,这是我的——一项协约。因此知识具有想象的功能;语言依赖于一个象征契约。如果他者不同意,我必须废除他或他必须废除我——这一辩证的开始是在他者中的离间。
对于拉康来说,大写的他者(大O),即就其不被知道而言的他者, 与小写的他者(小o,即我,或我的他我,所有知识的源泉, 我的竞争者)的区别是基本的。他性的王国(小o)是契约的王国, 另一个他性的王国(大O)充满了欺骗的可能性。拉康断言,“整个错觉的辩证法置身于这两种关系之间的间隙和叉开的角度”。
妄想狂结构的基础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主体理解他所明确表达的东西,那个已经以语言的形式对他说话的东西。无人怀疑这是一个虚幻的人,甚至不是他,因为他总是处于一个这样的位置,即承认和他说话的原体的含糊不清的性质。对于你,妄想狂目睹了这个和主体说话的人的结构。
假如所有的知识,至少从一开始,都是妄想狂性的,是一种投射和自居的效果,那么正常人和妄想狂的精神病态表现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拉康坚持认为,作为幻想的一般形式的间离与精神病的间离在程度上是有区别的,不仅仅是自居问题,也不仅是小写的他者的景象。从主体开始说话的时刻起,他者就已经在那里(说话了)[……]确切地讲,那是分析者理解它的意义上的主体,是带有问号的主体。分析表明这个主体是无意识……主体之外的部分在说话,谈论的他比他自己认为的要多。
在拉康看来,理解说了些什么仅仅是开始,整个问题是它如何说以及妄想狂的话语结构。在讨论妄想狂的话语结构时,拉康重新引用了弗洛依德著名的关于主体位置的语法转换例子(在他的讨论中再次引用了受虐狂——一个被殴打的孩子)。其基础是一个根本性的趋势的话语,最终被人们在神经病中认识到,即——我爱他和你爱我。弗洛依德称主体有三种方式来避免这种认识,三种以语法转换或投射为基础的错觉类型:
第一种否定它的方式是说——爱他的不是我,而是她(投射),作为我的连体,我的复身。第二种是说——我爱的不是他,而是她。(使注意力转移的离间。)在这个层次上,对于妄想狂主体来说,辩护是不够的,掩饰也是不够的,他不安全,投射必须进入运行。第三种可能性是——我不爱他,我恨他。这里单单颠倒是不够的,至少弗洛依德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投射机制必须干涉,即——他恨我。这样一来,我们便拥有了迫害的错觉。
在精神病投射中,妄想狂自居作用着,正如在对他者的性妒嫉中一样:“通过一个颠倒的间离,那是你所认同的人,即你妻子,你使她成为你的感情的使者,你的感情不仅涉及到另一个男人,甚至波及——正如临床症状所证实的那样——一些或多或少在数量上无法确定的男人。一个恰当的有关妒嫉的妄想狂错觉是不确定地重复出现的,它在体验的每个转折点上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并且它们大多暗示着地平线上隐现和不隐现的主体。”在精神病中,投射被颠倒并且被概括化了。最后,在迫害性的妄想狂中(他不爱我,他恨我),“这是一个转换过的间离,爱转变成恨。[这表明]整个他者系统的深层变质……对世界的阐释的广泛性本质,这里表明,恰当的想象上的干扰正处于它的最大延展处”。
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拉康解释了神经官能症和心理变态在投射的起因上的区别:在神经官能症中,投射起因是受压抑的回归;
在心理变态中,是被遗弃的东西(不是受压抑,而是被遗弃)从没有出处的地方的回归。(一个例子是在拉康的一篇关于哈姆雷特的文章中,他认为王子与父亲鬼魂的相遇是一种回归,即人遭到阉割的受排斥的“现实”的回归。)这里拉康经常探讨的理论,即病态心理是现实的一个空洞:让我们以这样的想法作为开始,一个空洞、一个错位、一个外部世界结构的断裂点,被心理变态的幻想所填补。如何解释它才好呢?投射机制可供我们任意使用。
拉康在第四章里又详尽描述了拒绝(Verwerfung)——对诸如阉割这样的没有经过象征化的现象的摈弃——内部没有经过象征化的东西靠它回归,现实中外部的空洞也得到了填补,最终导致了妄想狂的错觉。不是受压抑者的回归,而是遭遗弃者的回归。心理病态的投射是“使陷入拒绝之中的——即被置于一般象征结构之外的主体——从没有出处的地方回归的机制”。而且,拉康坚持认为,对于心理病态,现实不是处于疑问状态,而是处于确定状态。“在错觉语言中,他者是真正被排斥的,[话语的]后面没有真理,或有极少的真理,以致于主体自己在那里什么都没有放置,面对这一现象,他的态度是困惑”[……]。妄想狂并不怀疑他的幻想没有现实性,但是他确信,这个他者被他者的他者控制着,虽不是现实的,却是真实的:“大写的他者被真正地排除在外,有关主体的话实际上被小写的他者、他者的阴影(在施莱伯的案例中)说出来,被虚构的、临时凑出的人说出来。小写的他者则有效地呈现出趋向于不实际的不实在性”。捍卫正常象征现实的大写的他者,则被从妄想狂的互主体相遇中排挤了出来。有趣的是,拉康的主要例子并不是沃夫曼或施莱伯,而是女性妄想狂——遭受性侮辱(“猪”)的色情狂:
说这个女人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妄想狂的理由是,对于她来说,这个循环包含着对一个大写的他者的排斥。这条线路在两个小写的他者中封闭了起来,他们是与她相对立的傀儡,傀儡说着话,她的信息便引起共鸣,而她自身,作为自我,则总是他者,通过暗示在说话。
这种暗示的、错觉的、投射的语言在后现代妄想狂的文本中是如何起作用的呢?这里我们指出,弗洛依德的理论可以(至少)在四个层次上阐释后现代文本:主题层次,妄想狂是文本内部的题目(主人公是妄想狂,到处看见的都是阴谋的“迹象”);文本或结构层次——故事反映了妄想狂的剧情说明,如世界末日之幻想,或暗杀者正是自己之类的恶梦。(在这些文本中,主人公不是妄想狂,他是正常人——人们出来接近他。故事本身是妄想狂式的。)在文本的开始和创作(文本外的)层次,妄想狂式的人物作为愿望得到满足的一种方式,正如弗洛依德在《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中认为的,这种方式在每个文学行为中都起作用。最后,在互文本这一层次上,我们能够引用文本之间大量的交互作用,使它们经常在一特定的游戏模式中操练(维安笔下那位名叫“让—索尔·帕特”的知识分子型主人公,向我们展示了吃饱饭引起的呕吐;昆诺以把各种风格拼凑一起的方式写作整个章节,包括侦探小说)。
后现代文本中呈现出的对妄想狂的强调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指涉对象的后现代式的丧失以及合法性所面临的危机是如何导致爆炸性的叙述神经机能病,而结尾却被立即引发并被拖延的?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构造问题,后现代文本的重复性叙述是否与精神分析对象的不由自主的“重复”相似?或者它与弗洛依德所谓的“回忆着并且工作着”相似?德里达的所谓“文本外什么都没有”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关于妄想狂的定论,还是从社会角度对文本的一个新定义?
四、后小说:妄想狂的一个范例
假如后现AI写作作记录了某一观察性的他者的出现,即空中的眼睛,那么它有时也记录了对一个完全透明和统一的视野的游戏性反叛。这里我特别联想到雷蒙德·昆诺的《蓝色的河流》,它在主题层次上,是梦想、写作和妄想狂投射性思维三者之间的游戏。文本的主人公分裂为两个主角,一个中世纪的公爵和一个现代巴黎人,每一个都可作为另一个的妄想狂式的投影来阅读。小说以一种后果的情景作为开始,带有明显的梦想特性,使读者沉浸在某种改变了的现实氛围中,也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末日式的“投射”。叙述本身产生于一则关于历史(histoire)一词的双关,这个词语可以解释成历史、小说、骚乱或事故。这一文字游戏首先被公爵这一身份引入,他栖息于他的塔楼,观察似乎是历史爆炸和语言爆炸引起的后果。 “Tant d' histoires
pour
quelquescalembours!”他大喊道(如此多的历史或骚乱,如此少的双关引起如此多的故事!)公爵在这里是一个窥探者,盘旋于各种各样的天空中的眼睛:观察着散落在视野中的支离破碎的东西。这是一个含有双关、历史、陈词滥调和具体化的谚语和说教的视野(一些旧法朗和新法朗散落在海滩上,几个铁匠在趁热打铁;罗马人在描绘希腊人;人们在鸡孵化前数小鸡,等等)。这是一些拒绝分解的文化残渣,扯谎的、乱七八槽的。这些语言文化的残片象“日常的残片”一样,被弗洛依德称为组成梦的场景的成分,“真理的颗粒”总是居于妄想狂的幻想中,并在其周围构成。
这部作品清楚地将梦的过程与写作游戏相联系,同时也与某种“妄想狂”的投射性思维方式相联系。小说表面上的二分制结构来自奥格和希德洛林两人相互交织的梦的经历;中世纪的公爵和现代的汽艇看守人相互做着梦,在交替的叙述中,每个人依据自己的“日常琐事”编造出另一个人的存在。换言之,两位主人公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另一个的妄想狂式的投射、他者的幻觉,以旁观的他我的身份作用着:直至有一天他们真的相遇了,幡然醒悟,把两个自我重新结合在一起,发现他们有着同样的姓(Joachim)。还有,在镜子般妄想狂的相互投射过程中, 每个主人公都纠缠、追踪着梦中的他者,这一过程与写作行为有关。因为当他睡觉,即“梦着”奥格时,希德洛林习惯性地在他自己的大门上乱涂瞎画;而奥格则在他走向巴黎、走向二十世纪的征途上,伪造史前人的“洞穴画”。
书中还有另一位重要人物,一位过路人,他观察到希德洛林在每晚大门被涂上“谋杀者”字样后,每天早晨都重新油漆大门。这位观察者最终揭发了希德洛林,正是他本人自我诽谤,观察者还强迫希德洛林坦白他阴影里的夜间活动,因为使希德洛林遇见了他做梦的对象,因此奥格这位万能的过路人对全文的妄想狂语调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角色具体化了读者作为一名旁观的“历史”见证人的位置。有意义的是,希德洛林在进行自我诽谤这一事实被挑明后,他和奥格被洪水分开了。最后,小说以洪水过后出现的蓝色的花朵作为重新开始。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与一成功的分析相平行,其中妄想狂将自己认作那个威胁他的“他者”,并且重新与自身相结合。然而,小说又有别于分析;昆诺的故事提示我们,小说需要一个根本上的错误认识或持久的幻觉:将希德洛林与其他我分隔开的洪水,冲刷干净了门板,为涂鸦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样一来,小说又可以重新开始了。但是,昆诺的作品,就其规定使系统完整化的努力必遭失败而言,最终是一个寓言,一个抛弃关于妄想狂的总体结论的寓言,即使当陷入投射式思维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是关于一个差异的后现代世界,一个持久的或重新被激发的欲望的后现代世界。如果昆诺的后现AI写作作记录了某种观察性他者的出现,即空中的眼睛,那它也是一个对于完全透明与一致的世界的反叛。当蓝色的花朵在洪水后种植起来,昆诺又为另一种“后现代主义”欢呼:不是使信息网络联成一体的,或关于平板的疯狂人物的后现代主义;而是差异的“不可决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在这种后现代主义中,无人持有终论,俄狄浦斯纠缠着我们,他确保我们作为社会性的人,时刻关注着他人。谁去了那里?妄想狂高声喊道。谁在说话?法国的弗洛依德主义者问道。但是,后现代副文本对于二十世纪晚期的自我崇拜主义的文化附有一则警告、一个教训和一则提示:一个非社会性的脱离,有可能导致一种作为若隐若现的威胁的回归,一场全球性的灾难,一场浩劫。正如弗洛依德在反思俄狄浦斯的故事——这个人最坏的恐惧也得以实现——时,提醒我们的那样,每个妄想狂的幻想都含有真理。
徐燕红译
标签:妄想狂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心理投射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学论文; 精神分析论文; 他者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