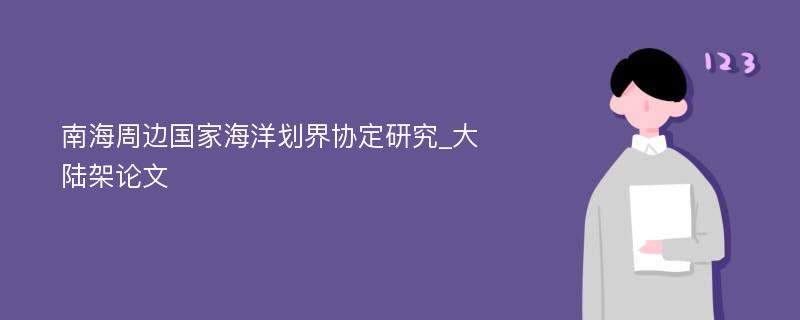
南海周边国家海洋划界协议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海论文,周边国家论文,海洋论文,协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制度的确立,使世界各沿海国在扩大其享有管辖权的海洋区域的同时,与周边邻国的海洋划界问题也日益突显。《公约》第15条、第74条和第83条分别为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设计了基本法律框架,并在第十五部分“争端的解决”中为沿海国解决海洋划界争端提供了第三方争端解决方式。几十年间,国际法院及仲裁庭通过海洋划界案例,发展出日益成熟的追求灵活性与确定性并存的海洋划界原则与规则;在国家实践层面,世界各沿海国也缔结了大量的划界条约或协议。 对南海周边各国来说,海洋划界问题格外复杂。南海被六个沿海国——中国(包括中国台湾)、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所环绕,形成一个由东北朝向西南走向的海域,属于《公约》第122条规定的半闭海。①多国环绕的事实,加之各国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包括200海里以外大陆架主张,使南海存在沿海国权利主张的重叠;同时,南海遍布着海洋地物(marine features),包括岛屿、暗滩、暗沙、暗礁、沙洲和浅滩,形成了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四大群岛。②而南海周边各国,除印度尼西亚外,均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些海洋地物主张主权,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约》规定岛屿享有和陆地一样产生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④捍卫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对保障中国在南海海洋划界中的利益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岛礁的主权归属涉及南海周边各国海洋权利重叠区域的格局。同时,因《公约》第121条对岛屿和岩礁的分类,岛礁因定性不同在海洋划界中的作用有所差异。因此,特定岛礁在南海海洋划界中的效力,将是南海周边国家在海洋划界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尽管问题复杂,南海周边国家在解决南海海洋划界争端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具体体现在:一方面,南海周边一些国家已经签订了涉及部分南海海域的划界协议,如1969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与马来西亚关于两国大陆架划界协议》(以下简称《1969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划界协议》)、2003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两国大陆架边界的划界协议》(以下简称《2003年越南—印度尼西亚划界协议》)以及2009年《马来西亚与文莱达鲁萨兰国2009年3月16日换文》(以下简称《2009年马来西亚—文莱换文》)中划定两国海洋边界的内容;另一方面,南海周边国家之间在非南海海域签订了海洋划界协议,如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以下简称《2000年中越北部湾划界协议》),虽然该协议并不涉及南海海域,但是由于缔结于南海周边国家之间,也有其参考意义。 对南海周边国家而言,上述协议除了对海洋划界争端在未来的解决具有潜在参考价值外,还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除《1969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划界协议》外,另外三份协议均签订于《公约》生效之后。这些实践,与其他《公约》通过之后的海洋划界实践一起,可能构成《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三款第二项的“嗣后实践”,从而对《公约》有关条款的解释有所影响,对未来的南海周边各国海洋划界亦有参考意义;第二,南海区域内这些率先签订划界协议的国家,是否充分尊重了第三国的利益,也值得重视。这些协议的签订,不能掩盖其对其他有关国家海洋权益的侵害。 因此,本文将重点研究南海周边国家海洋划界协议的内容,特别针对划界基线的选择、划界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以及岛屿在划界中的效力问题进行集中探讨,同时对南海海洋划界面临的挑战提出初步意见。 二 南海周边国家海洋划界协议的缔结与内容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政府于1969年10月27日签订了两国的大陆架划界协议。该协议共12个条款,确定了三条划界线,划分了两国马六甲海峡和南海的大陆架。位于南海部分的划界线有两段,分别是西段(西马来西亚东侧海岸近岸海域)和东段,即沙捞越(Sarawak)近岸海域,各自由9个折点和5个折点相连接,分别是折点11至折点19、折点20至折点25。⑤在该协议中,印度尼西亚的纳土纳(Natuna)群岛与马来西亚沙捞越北部达都角之间的界线,进入中国的南海“断续线”以内,损害了中国作为第三国的利益。因此,虽然该协议已完成当事国的批准程序,但根据国际法原则,未经第三国同意,条约不得对第三国创设义务,因此该协议中涉及侵害中国海洋权益的部分当属无效。涉及到中国海洋权益的部分可以留待未来与中国进行划界谈判时协商安排。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大陆架划界协议的缔结与生效均在1982年《公约》通过之前。因此,两国缔结该大陆架划界协议时所主张的权利依据并非来源于《公约》,而主要来自1958年《大陆架公约》对大陆架权利的规定。 中国与越南于2000年12月25日签订了北部湾划界协议,该协议于2004年6月30日生效。中越北部湾划界协议为单一划界,划分了越南与中国在北部湾的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该线段由北向南通过21个折点(折点1-折点21)相连接,划分了北部湾海域。⑥其中,折点1至折点9划分了两国在北部湾的领海界限,从折点9至折点21则通过一系列单一线段划分了两国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中国与越南都是《公约》的缔约国,依据《公约》的规定沿海国有权主张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并享有至少200海里的大陆架。但是,越南曾在1982年《越南政府关于领海基线的声明》中称:“中越在北部湾的海洋界线已经由1887年清政府与法国政府签订的《中法边界条约》确定,该界线靠越南一侧的海域为越南的历史性水域,从而享有内水地位。”⑦这一立场并不为中国政府所接受,有学者指出,越南在北部湾划界过程中已放弃了这一历史性水域主张,⑧而中国在两国划界之前在北部湾的权利主张范围则不甚明确。 印度尼西亚与越南政府于2003年6月26日缔结了两国位于南海海域的大陆架划界协议。该协议共6个条款,第1条规定了两国大陆架界线的折点。划界线首先由西南至东北共连接5个折点(P20,H,H1,A4,X1),随后从折点X1转为由西北向东南走向,连接到折点P25。需要指出,折点P20是《1969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划界协议》在南海西段划界线的终点——也就是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三国的等距离点;折点P25是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在南海东段划界线的终点。因此,通过这一划界协议,印度尼西亚完成了其在南海这一区域的岛屿与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大陆架划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协议所涉海域位于南海南端,且位于中国“断续线”内,因此这一协议的签订并未充分考虑中国作为第三国在南海的利益和立场。虽然该协议于2007年5月29日完成两国国内的条约批准程序,但与《1969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划界协议》的情况相同,该协议涉及到侵害中国海洋权益的部分当属无效。 2009年马来西亚与文莱签署了划界协议。这一协议采用换文的形式,其具体内容未向国际社会公开。⑨然而,从文莱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的有关确立文莱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初步信息来看,文莱确认这一换文划定了两国200海里以内的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⑩同时,从马来西亚和文莱政府于2009年3月16日发布的联合公告来看,划界协议涉及四大事项:第一,两国之间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界;第二,在婆罗洲岛近岸建立石油共同开发区和“商业安排区”(Commercial Arrangement Area);第三,确定马来西亚与文莱的陆地边界;最后,确保马来西亚国民往返沙捞越经过文莱海域的通行权,马来西亚同时确保文莱的法律和规则得到遵守。(11) 马来西亚与文莱均为《公约》的缔约国,且两国相邻。文莱曾在1983年颁布《渔区界限法案》(Fishery Limits Act)确立了以领海基线起算200海里为范围的渔区。尽管文莱主张200海里的渔区,但从其公布的地图来看这一渔区的界限实为与越南大陆的中间线,距文莱所称的领海基线距离约为265海里。(12)直到1993年,文莱才主张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这一主张的界限与《渔区界限法案》所规定的界限一致。虽然换文的内容尚未披露,但从协议涉及的内容来看,两国的划界区域应位于中国南海“断续线”以内,因而涉及到侵害中国作为第三国的利益而导致相关协议条款无效的问题。同年5月,文莱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上文已提及的初步信息。根据该初步信息,文莱主张的大陆架外部界限将不超过350海里。(13)这一主张的范围也与中国在南海海域内的权利有所重叠。 上述四份海洋划界协议除《2009年马来西亚—文莱换文》中的划界协议内容尚未向国际社会公开外,其余三份划界协议均已向联合国秘书处登记。需要注意,除《2000年中越北部湾划界协议》外,其他三份划界协议均涉及到侵害中国作为第三国的利益而导致协议条款无效的问题。 三 南海周边各国划界协议中的基线 在基线的运用上,上述四份海洋划界协议提出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方案。 在《1969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划界协议》中,两国各自认可了对方的领海基线,并以此来构筑划界线。这体现在马六甲海峡内的划界线和南海西段划界线分别是两国直线基线的等距离线。印度尼西亚于1960年2月18日公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第4号令》,宣布采用直线基线连接印度尼西亚各个处于外部的岛屿的最外各定点,这一法令是基于当时尚未获得国际法认可的群岛国理论。(14)《公约》通过后,确立了群岛国的群岛基线制度。依据《公约》规定,印度尼西亚享有群岛国地位,可划定群岛基线。马来西亚在1969年公布《紧急法令》,确认其领海基线的划定将依据1958年日内瓦《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的有关条款。(15)这一法令并未给出马来西亚领海基线的具体基点坐标,但从《1969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大陆架划界协议》附图上可看出,马来西亚采用的是直线基线。马来西亚采用直线基线这一做法被认为明显是“有意让马来西亚和采用直线基线的印度尼西亚在大陆架划界中处于更加平等的地位”。(16) 然而,马来西亚所划定的直线基线并不符合当时国际法的规定。因为,按照1958年《领海及毗连区公约》(马来西亚于1960年12月21日加入了该公约)第4条的规定,只有“在海岸线甚为曲折之地区,或沿岸岛屿罗列密迩海岸之处,得采用以直线连接酌定各点之方法划定测算领海宽度之基线”,而马来西亚海岸并不符合上述条件。有学者认为,如果在划界中采用的不是马来西亚的直线基线,而是正常基线,在仍然适用等距离划界方法的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将会得到大约1000平方海里的大陆架区域。(17)此外,印度尼西亚之所以认可马来西亚在划界中使用直线基线,是为了获取后者在之后的第三届海洋法会议上对群岛制度的支持。(18)可是,在这个划界协议后,马来西亚始终没有公布其领海基线的坐标和图示。马来西亚于2006年颁布了《海洋区域基线法案》,该法案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的内容分别是基点坐标和基线问题。但是,马来西亚仍然未依法案要求在政府公报上公布基点坐标和基线地图。从而,外界并不清楚马来西亚是否会切实采取直线基线以及其具体的范围。 与《1969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划界协议》不同,中国与越南在北部湾划界时并未以各自的领海基线作为划界的基线。越南于1982年11月12日发布《关于领海基线的声明》,确立采用直线基线法来划定领海基线,并公布了由11个基点(19)以及连接这些基点的10条线段划定的直线基线。诸多学者提出,越南的这一直线基线显著背离《公约》的要求。(20)中国于1996年5月15日公布了部分直线基线,包括中国大陆和海南岛以及西沙群岛的直线基线。但中国与越南均未公布两国相邻的北部湾内的领海基线。虽然可以明确北部湾划界并未以直线基线作为依据,但并不清楚直线基线或正常基线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划界。(21) 《2003年越南—印度尼西亚划界协议》的内容是有关越南大陆与印尼所属的纳土纳群岛之间的划界。《1969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划界协议》中,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在南海海域西段与东段的两段划界线划分了纳土纳群岛东西两侧的海域,而此次与越南大陆架的划界协议,则是以一条长约250海里的线段划分了纳土纳群岛北部的海域。在这一划界协议中,并未提及两国各自的领海基线,最终的划界线更偏向于印度尼西亚一侧的等距离线,也就是经调整后更有利于越南的等距离线。据学者研究,该等距离线的作出并未以两国各自的直线基线体系为基础,而是出于划界的目的另行指定基点。(22)当时,印度尼西亚已经通过1998年、2002年和2009年的国内法修订,使其群岛基线系统大致符合《公约》的规定,(23)但越南仍然保持其极富争议的直线基线体系。两国在2003年大陆架划界协议中也未提及以两国各自的领海基线为基础来构筑等距离线。(24) 可见,领海基线是否适用于海洋划界中,取决于国家的合意。前述截然不同的做法都符合《公约》这一法律框架,并与国际司法实践和国家实践相吻合。《公约》仅规定在领海划界中领海基线为划界基线。按照《公约》第15条的规定,在没有相反协议或历史性所有权等特殊情况下,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间的领海界线是两国领海基线的等距离线。(25)在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中,《公约》并没有规定应以领海基线作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的基线。 国际司法实践认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中的基线与领海基线在本质上是相互区别的。(26)对于领海基线,国家在符合《公约》规定的条件下,可以自行确定有关的基点和基线。但是,因为划界涉及到两个或者更多的国家,法庭不能将自己的决定仅仅建立在其中一方对基点的选择上。因此,法庭在划界时,必须依据海岸地理状况来选择基点。也就是说,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构有权自行选择基点,而不论该基点是否位于当事国的领海基线上。 此外,国家实践对领海基线是否适用于海洋划界则有多种方式,既存在以领海基线为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划界的实践,例如,1971年意大利与突尼斯缔结的大陆架划界协议中,双方在协议第一款约定“两国大陆架界限应当是中间线,中间线上的每一点距离两国各自的领海基线的最近各点都等距离”;(27)也存在不以领海基线作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的例子,如1974年意大利与西班牙就各自所属的岛屿撒丁岛和梅诺卡岛的大陆架划界协议中,虽然双方均采用直线基线划定撒丁岛和梅诺卡岛的领海基线,但是在这一划界协议中并没有使用两国的领海基线来构筑等距离线。(28)同样还存在这两种情况并存于同一划界协议的情形,这一情况发生的原因,可能是沿海国不承认对方的领海基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谈判中,双方各自有所妥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与古巴的海洋划界谈判。美国不承认古巴采用的直线基线体系,而美国当时并没有划定领海基线。(29)最终,两国的划界线分为三段:一段是以美国在佛罗里达州的临时基线与古巴的直线基线的等距离线,第二段是双方各自海岸低潮线的等距离线,第三段虽然不是等距离线,但是平分了这一区域。(30) 上述有关南海周边国家划界协议的介绍与论述,对中国南海海洋划界的启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在划界谈判中,当事国在划界中是否适用领海基线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合意;其次,当事国对各自领海基线的不同理解不应成为海洋划界的障碍;例如,虽然中国在与越南缔结北部湾划界协议时,双方均未公布两国各自北部湾内的基线,但是,在未来中国就西沙群岛与越南大陆之间进行划界时,并不一定限于各自的领海基线。最后,即使领海基线尚未公布或尚未确立,也不应影响海洋划界的展开。例如,中国尚未确立南沙群岛的领海基线,而南海周边国家如马来西亚也未公布其领海基线,这不应妨害海洋划界的展开。尤其对于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而言,考虑到划界所用基线与领海基线的性质不同,划界时可另行确定基线。 四 南海周边各国划界协议中的划界方法 划界方法的选择和适用是海洋划界问题的核心。当事国综合考虑各种情形后,选择何种或哪些方法并以何种方式呈现各自的海洋区域,决定着其管辖权范围。正如有学者所言,“划界方法的选择,以及通过划界方法把有关的地理和其他状况转化为一条准确的划界线,是海洋划界中最困难的问题”。(31) 《公约》第15条所规定的领海划界方法,被称为“等距离/特殊情况划界规则”(Equidistance/Special circumstances rule)。而第74条和第83条并未规定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可适用的具体的划界方法,只强调划界的公平解决。(32)正是由于《公约》缺乏对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具体方法的规定,才突显出国际司法实践在这一问题上的重要性。(33) 自1969年第一个大陆架划界案“北海大陆架案”以来,提交国际法院、国际常设仲裁法庭、临时仲裁庭以及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海洋划界案日益增多。经过40多年司法实践的发展,国际司法机构逐渐发展出一套三步划界方法,即首先划一条临时等距离线,(34)再通过对有关情况进行考察决定是否对临时等距离线进行调整,最后再通过对划界所得的海洋区域和有关海岸的比例进行比较决定划界结果是否实现了公平解决。这一划界方法被总结为“等距离/有关情况划界方法”(Equidistance/Relevant circumstances method)。(35)这一方法与领海划界中的“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的区别在于,后者的适用方式是,若无历史性所有权或特殊情况时应适用等距离线,也就是说等距离划界方法是规则、特殊情况是例外;(36)而前者并不强调等距离线是规则,等距离线受制于有关情况的衡量,换言之,划界线的最终形态应是综合等距离线与有关情况的结果。 在已有的南海周边国家的划界协议中,除《2009年马来西亚—文莱换文》所采用的划界方法尚不清楚外,其余三份划界协议均涉及到等距离划界方法的运用。在《1969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划界协议》中,除南海东段划界线偏离了等距离线外,两国位于马六甲海峡内的划界线和南海西段划界线均是采用等距离划界方法、平分两国的直线基线而得出的等距离线。南海西段划界线从折点11(新加坡海峡东部边缘点)开始,由西南至东北大致呈S形直到该段终点折点20,平分了马来西亚半岛和印度尼西亚所属的阿南巴斯群岛和南纳土纳群岛的直线基线。折点20是距离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的三边等距离点(tri-point)。(37)而南海东段则从位于达都角的折点21开始,由南至北直至位于183米等深线上的折点25。除了东段南侧靠近两国海岸的一小段线是等距离线外,该线段大体上偏离了两国直线基线的等距离线,使马来西亚获得了大约6250平方公里的大陆架——如果按照严格等距离线的做法,这一区域的大陆架应属印度尼西亚。(38) 在《2000年中越北部湾划界协议》中,双方并没有采用严格的等距离划界方法。依据北部湾划界线,越南获得了53.23%的区域,而中国获得了46.77%的区域,相差大约8000平方公里。按照越南的说法,其之所以享有更广大的区域是因为越南在北部湾的海岸线更长、在北部湾内的岛屿更多。这表明,划界结果并非严格适用等距离划界方法所得,而是综合双方其他因素对等距离线进行了调整。(39) 在《2003年越南—印度尼西亚划界协议》中,两国最终的划界线是等距离线和非等距离线的结合。划界线的西段是印度尼西亚的纳土纳群岛和越南的鸿快岛(Hon Khoai)的等距离线。而随着划界线东进,划界线向南侧偏离,使最终的划界线更有利于越南。(40) 可见,等距离方法对三份海洋划界协议均有一定影响,但三份协议的结果均是综合考虑其他有关情况得出的。南海周边国家划界协议对等距离方法的适用表明,等距离只是划界方法中的一环,划界过程还要综合考虑其他有关情况的影响。在南海周边国家已有的划界协议中,影响了划界过程的其他有关情况有:《1969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划界协议》中,南海东段偏离等距离线是出于政治考虑,即印尼为获得马来西亚对其群岛基线的支持而妥协;《2000年中越北部湾划界协议》中,则可能考虑了越南更长的海岸线与湾内越南岛屿的存在;《2003年越南—印度尼西亚划界协议》中,划界线更有利于越南可能是由于越南享有更长的海岸线,并且印度尼西亚所属岛屿更加远离印度尼西亚陆地。(41)而且,虽然越南获得更广大的管辖权范围,但印度尼西亚确保了其位于划界线西侧的岛屿获得“全效力”,并保全了印尼在纳土纳群岛周边海底资源开采的利益。(42) 南海周边国家划界协议中有关等距离方法的适用与国际司法和国家实践中的适用相类似。海洋划界线的最终形态并不取决于某种单一的几何式的划界方法,如等距离、角平分线等等,而是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在国家实践中,这是一种务实以尽力实现公平的划界方式。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哪些因素能作为有关情况来考量则有所限制,原因在于:《公约》通过后,沿海国主张专属经济区权利依据的是200海里距离标准;而大陆架权利则分为自然延伸和200海里距离标准(当沿海国的自然延伸不足200海里时)。两种权利主张依据均是以沿海国的海岸为基础来主张的。也就是说,“陆地支配海洋”这一海洋划界的基本原则是以沿海国的海岸作为中介来具体化的。(43)于是,司法实践中通常衡量的有关情况,主要是与海岸地理有关的情况,例如海岸的形状、(44)有关岛屿的存在,(45)以及沿海国海岸线长度的差异等。(46)相应的,与海岸地理,也就是与沿海国的权利基础无关的因素,通常就不予以考虑,包括:经济社会因素(47)和国家安全因素(48)等。但是,在国家实践中,社会经济因素和国家安全因素则可能会成为海洋划界谈判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总之,对等距离方法的适用并非强制性的,等距离方法既不是《公约》规定的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划界规则,也不是习惯国际法规则,其能否适用取决于在个案中能否实现公平解决。并且,等距离方法往往也只是划界过程中的一环,等距离方法的适用常常受制于有关情况的衡量。在南海问题中,中国所属的南海诸岛与其他国家的陆地海岸进行划界时,南海诸岛的海岸线长度、岛礁自然特征等地理因素可能成为有关情况的考量因素。值得一提的是,安全因素也可能成为影响南海海洋划界的重要因素。安全因素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尚未得到采纳,但包括国际法院在内的司法机构均认可,在特定条件下安全因素也可以成为有关情况的一种。(49) 五 岛屿在南海周边各国海洋划界中的效力问题 南海周边国家现有的几份划界协议中,针对不同的情况对岛屿的效力做出了不同的安排。 在《1969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划界协议》中,出于两国对岛屿效力的安排,南海东段划界线偏离了等距离线。虽然从地图上看,位于达都角西北方向的印度尼西亚群岛作为印度尼西亚直线基线的一部分是两国大陆架划界的基点,但是其并没有被赋予划界的“全效力”,从而使南海东段划界线偏离等距离线而靠近印度尼西亚一侧。这是在协商过程中马来西亚坚持的结果。印度尼西亚对马来西亚这一坚持的妥协仍然被认为是为获取后者对群岛国制度的支持。(50)同时,有必要指出,这一南海东段划界线的划定是建立在假定马来西亚对南威岛和安波沙洲享有主权的基础上的。南威岛和安波沙洲为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因此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这一安排是侵害中国主权的行为,以南威岛和安波沙洲为基点的划界线对中国不产生效力。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该段划界线最终应予以调整。 在《2000年中越北部湾划界协议》中,影响最终划界线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岛屿的效力。其中最重要的岛屿是越南所属的白龙尾岛。该岛位于北部湾中部,面积约为2.5平方公里,高出水面60米。如果该岛具有享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完全的效力,那么它的存在将对等距离线产生巨大的影响,会使得等距离线朝靠近中国的一侧偏离。最终,两国协商确定,白龙尾岛享有25%的效力,也就是其享有15海里的水域。(51)这15海里可以被认为是12海里的领海及3海里象征性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位于北部湾南部,距离越南8海里的昏果岛(Con Co)被赋予了“半效力”。越南所属的其他一些岛屿也未能获得“全效力”,而是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一定的效力。(52) 在《2003年越南—印度尼西亚划界协议》中,影响划界的因素除岛屿效力外,还源于两国岛屿所处的位置及两国海岸线长度的差异。首先,划界线的西段之所以是等距离线,是因为在此处印度尼西亚的岛屿被赋予了“全效力”,由此,印度尼西亚得以控制纳土纳岛周边的油气资源;其次,正如前文已提及的,越南大陆相对更长的海岸线也是影响划界的因素之一,因此,出于公平的考虑,两国政府可能因此调整了划界线的位置;最后,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岛屿位置问题,印度尼西亚的纳土纳岛的位置距离印度尼西亚大陆更远,而越南所属的岛屿则距离越南大陆更近。(53) 上述划界协议中,岛屿问题是影响最终划界线的重要因素。其中,岛屿所处的位置对岛屿能否被赋予“全效力”有重要影响,例如,岛屿是否处于等距离线附近(中越北部湾划界的情况)与岛屿是否远离大陆(印度尼西亚与越南划界的情况)等这些情况。实际上,无论是在国际司法实践中,还是在国家实践中,岛屿的效力问题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且并没有一个普遍的规则对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效力进行规范。(54) 未来南海周边国家海洋划界问题涉及到岛屿效力的两个层次:第一,中国所属的南海四大群岛与周边国家大陆海岸或岛屿的划界中,四大群岛作为产生海洋权利基础的效力问题。其中,东沙群岛与菲律宾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有重叠区域,西沙群岛与越南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相重叠,黄岩岛位于菲律宾主张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之内,而南沙群岛则与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纳土纳群岛)主张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有权利重叠;(55)第二,在南海诸岛与南海周边国家海岸划界过程中,南海诸岛中的某些岛屿或其他国家所属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效力问题。例如在南沙群岛与越南大陆海岸的划界中,会涉及越南所属的昆宋岛(PouloCondore)等岛屿的效力问题。上述第一个层次涉及到大陆国家的远洋群岛与其他国家的划界问题,而第二个层次则是海洋划界过程中岛屿的效力问题。下文将着重探讨第一个层次的问题。 中国南海诸岛在与其他国家进行海洋划界中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西沙、中沙、南沙群岛是作为整体与周边国家进行划界,还是其中仅有部分岛屿与其他国家进行划界的问题;若作为整体,其享有海洋权利的依据为何、海洋权利范围如何界定。 讨论南海诸岛的整体性问题,既涉及中国本身的立场和主张,也涉及南海周边国家的立场与主张。中国的立场和主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以下简称《领海及毗连区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法和大陆架法》(以下简称《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二是以南海“断续线”为核心的海洋权利主张。如何理解二者的关系也将影响中国在南海海域划界中的立场。《领海及毗连区法》第2条明确了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为中国领土,第3条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采用直线基线法划定,由各相邻基点之间的直线连线组成。虽然目前仅西沙群岛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的声明》划定了直线基线,东沙、中沙和南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尚未公布,但依据上述第3条的规定应划定直线基线。 2012年9月10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的声明》也以直线基线法划定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然而,以直线基线划定东沙、中沙和南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在国际法律依据及具体的基线划定技术上仍存在深入探讨的空间。(56)按照《公约》规定,沿海国大陆架权利范围自领海基线起算,包括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或者在不足200海里的情况下扩展到200海里。中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也采用了这一定义。虽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确立了大陆架权利范围并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但并未对中国所属的岛屿享有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范围进行明确规定。只要符合《公约》第121条的规定,岛屿和大陆一样享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权利。因此,若以直线基线法划定南海诸岛的领海基线,则岛屿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范围应从领海基线起算。南沙群岛包括群岛和岛屿14个,沙洲6个,暗礁113个,暗沙35个,暗滩21个,(57)分布于东经109度30分至117度50分,北纬3度40至11度55分之间,要将范围如此之广的群岛及其水域以直线基线包围起来,无论从法律依据上,还是具体的基线划定技术上都是极大的挑战。而如果不按群岛整体主张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而是仅就单个岛屿主张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则应考虑每个岛屿的具体情况,且涉及到《公约》第121条第三款的解释及适用问题。(58) 虽然第121条三个条款均被认为是习惯国际法,(59)但对于第三款的解释与适用,仍存在很大研究与讨论的空间。而中国对南海诸岛是以整体享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还是仅就某些岛屿享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尚未明确表态,仅在2011年4月14日针对菲律宾对越南—马来西亚联合划界案回应的照会中称,“中国南沙群岛拥有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60)从这一表述来看,中国似将南沙群岛作为一个整体享有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61) 南海“断续线”也可能对中国在南海海洋划界的立场有所影响。从中国对南海“断续线”权利的表述来看,“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对相关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但目前中国官方尚未公布南海“断续线”的性质。学界的讨论倾向于认为“断续线”为岛屿主权归属线和历史性权利线,也提出其具有作为海洋划界线的剩余功能。(62) 如果不以群岛整体主张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而仅以符合《公约》第121条第二款规定的岛屿主张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权利,“断续线”内有些海域将不是中国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这些海域的海床、底土和水体不能作为大陆架或者专属经济区与其他国家进行海洋划界,而应考虑以历史性权利为依据,在海洋划界中发挥有关情况的作用。 南海周边国家均对南海诸岛的性质有所表态。越南和马来西亚均认为西沙、南沙群岛不符合《公约》第121条第二款的规定,而仅享有12海里的领海。这两个国家于2009年5月6日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联合划界案,并未在划界案中使用西沙群岛或南沙群岛的岛屿作为基点,表明两国似乎认同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均不享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权利。(63) 文莱的态度和立场不甚清晰,在其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的初步信息中,文莱称其未来完整的外大陆架划界案将涵盖文莱领土的自然延伸,并未提及文莱主张主权的“南沙岛”。(64) 印度尼西亚在2010年7月8日针对中国就越南和马来西亚联合划界案的照会,援引了中国驻国际海底管理局第15届会议代表陈京华大使的声明,即“如果无人居住的、偏远的极小岛屿可以享有200海里的海洋界限,则会严重损害国际社会对国家管辖权以外海洋区域的有效管理”,(65)这似乎表明印度尼西亚认为南海诸岛中无人居住的、偏远的极小岛屿不应享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 菲律宾则认为黄岩岛为《公约》第121条第三款规定的岩礁,(66)并在其2009年通过的领海基线法案中将黄岩岛和所谓的“卡拉延群岛”(即中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置于《公约》第121条岛屿制度之下,(67)而菲律宾在依据公约附件七提起的强制仲裁中称,中国依据南海若干岩礁、低潮高地和水下地物提出的200海里甚至更多权利主张与《公约》不符,并称中国占领或控制的部分南海岛礁为公约第121条第三款所称岩礁。(68) 从上述国家的态度和立场来看,可以预见,若主权问题得以解决而进入到海洋划界阶段,这些国家可能提出南海诸岛中大部分岛礁都不能享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且对符合公约第121条第一款岛屿定义的岛礁,在划界中采用“包围法”(enclave)圈出12海里领海,而对其他海洋地物,例如低潮高地,则依据《公约》第13条的规定确定领海宽度。 因此,未来南海海洋划界的挑战有两个重要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涉及到《公约》第121条第三款的解释问题,二是涉及到南海诸岛在划界中的效力问题。判断南海诸岛在海洋划界中的效力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如下两个立场: 第一,不能在划界之前就认定南海诸岛中的一些岛屿或岩礁不享有任何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权利。有学者认为,南沙群岛整体都不应享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权利。(69)这一看法是否能得到支持,如前所述,需要通过对《公约》及习惯国际法进行解释,论证南沙群岛的整体性问题,且还涉及第121条第三款的解释与适用问题,并结合南沙群岛的实际情况作出判断。例如,南沙群岛最大的岛屿太平岛不仅本身具有水源,在事实上也供人类居住,很难认为太平岛是第121条第三款规定的岩礁。(70) 第二,也不能因为南海诸岛大部分由小岛构成,就在划界中只享有有限的效力。有学者认为,即使南沙群岛中的某些岛屿享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权利,当其面对的是一国的大陆海岸或者更大的岛屿海岸时,其效力应当受到限制。有学者认为,“虽然岛屿有权享有海洋权利,但当其面对大陆陆地时这些岛屿不能享有完全的效力……即使南沙群岛被允许享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权利,但当它们在与更大的岛屿或大陆国家之间划界时它们产生这种权利的能力是有限的。”(71)事实上,这一说法不符合国际法理论与实践。 国际司法实践早已确立起一项原则,岛屿享有与大陆一样产生海洋权利的能力。国际法院在2001年卡塔尔诉巴林案中就指出:“《公约》第121条第二款反映了习惯国际法,即岛屿,无论其大小,均享有和陆地一样产生海洋权利的地位。”(72)这说明,当认定某一海洋地物是属于第121条第二款规定的岛屿时,其享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能力是与大陆一样的,在划界时应享有“全效力”。在1993年扬马延案和2012年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国际法院的做法均支持了这一原则。至于最后对等距离线的调整,则是考虑到其他相关因素,如海岸线长度差异而做出的调整,在划界开始前是认可了岛屿享有完整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权利的。此外,大量的国家实践也证明,在远洋岛屿的划界中,大部分划界协议均给予了远洋岛屿以完全的效力。(73)因此,不能认为在岛屿与大陆之间的划界中,岛屿只能产生有限的效力。(74) 六 结语 已有的南海周边国家间划界协议的内容及形式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未来南海周边国家海洋划界不仅可以借鉴其中的有益内容,也应该避免其中的问题,尤其是对第三国利益的保障问题。无论是从《1969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划界协议》,还是《2003年越南—印度尼西亚划界协议》,或是《2009年马来西亚—文莱换文》透露的内容来看,它们均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中国作为第三国在南海海域的利益。 自2009年以来,南海周边国家未能就解决南海海洋划界争端实现突破。这些国家海洋划界谈判进展缓慢的最主要原因是南海诸岛的主权争议。根据“陆地支配海洋”原则,确定岛屿主权的归属是海洋划界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在岛屿主权归属确定的情况下,才能判断哪个国家可以就该岛屿主张海洋权利。(75) 2009年以来南海海洋划界面临的新挑战是南海周边国家对200海里以外大陆架权利的主张。截至目前,在南海海域,已有越南—马来西亚联合划界案和越南就其北部区域单独提交的划界案,这两份划界案皆因有关国家的反对而延迟审查。此外,文莱提交了初步信息,中国提交了就东海部分海域的外大陆架划界案,但在执行摘要中提出该划界案不妨害中国以后在东海或其他海域提交划界案。(76)这保留了中国在南海海域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的权利。 以上划界案和初步信息,包括有关国家针对划界案提交的照会,表明了南海争端的存在。除主权争议外,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海域的外大陆架主张使得南海海洋划界问题更加复杂:一方面,南海周边国家的外大陆架主张使南海海域的权利重叠情况更加复杂,即,除主权争端外,还有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包括外大陆架以及历史性权利主张的问题,涉及到海洋划界的多个层次;另一方面,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法律原则和规则尚未在司法实践或国家实践中得到清晰、一贯地适用。除了善意和公平等一般国际法原则外,对具体的远洋群岛和大陆国家的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应如何划界,仍是理论与实践上的前沿问题。 中国一贯坚持采取双边协商的方式解决岛屿领土主权归属、海洋划界等纠纷,(77)而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文莱等东盟国家则提议采取多边谈判的方式,如通过东盟组织与中国进行谈判。中国强调,南海问题并非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而是中国与小部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问题。双边纠纷应通过双边对话协商解决。(78)双边协商应是解决南海海洋划界问题更为可取的方式。原因有二:第一,国际法上所谓的“争端”,是指双方在法律、事实认识、观点或有关利益上的分歧与冲突。(79)也就是说,争端是存在具有相互冲突的法律观点或利益的当事方之间的。东盟10国中仅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菲律宾与我国存在南海划界争端,因而从争端解决角度来讲,引入整个东盟组织作为谈判的当事方是不恰当的;第二,这种通过东盟内部联合再与中国进行谈判的方式,并非一种平等的多边谈判方式。 面对以上南海周边国家的海洋划界问题,如何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维护区域内的安全与发展,无疑对各国的外交和政治智慧提出了挑战。应该承认,和平友好的协商谈判方式是解决国家间争端的主流,第三方争端解决方式只是补充。(80)考虑到各国共同发布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南海周边国家应坚持《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自我克制”的要求,坚持国际法上的善意原则,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南海争端。 注释: ①《公约》第122条:“闭海或半闭海”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所环绕并由一个狭窄的出口连接到另一个海或洋,或全部或主要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沿海国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构成的海湾、海盆或海域。 ②See Zou Keyuan,"South China Sea Studies in China:Achievements,Constraints and Prospects",(2007) 11 Singapore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85,p.85. ③See Nguyen Hong Thao and Ramses Amer,"Managing Vietnam's Maritime Boundary Disputes",(2007) 38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305,pp.306-308. ④《公约》第121条第二款规定:“除第三款另有规定外,岛屿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应按照本公约适用于其他陆地领土的规定加以确定。”这一规定意味着,除第121条第三款规定的“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之外,岛屿均享有和陆地一样的产生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 ⑤“折点”指两国划界线的转折点,下文有相同词汇的,不作另行标注。Se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Malays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Indonesia on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shelv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27 October 1969,available at:http://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TREATIES/MYS-IDN1969CS.PDF(last visited October 25,2015). ⑥需要注意的是,该协议中所指的北部湾与采用其他技术手段测量所指代的北部湾的意义有所区别。例如,有些资料所指的北部湾面积为44,238平方公里,而与此相比较,中越划界协议中指代的北部湾海域已经超过了126,000平方公里。See ZouKeyuan,"The Sino-Vietnamese Agreement on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in the Gulf of Tonkin",(2005) 36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13,p.14. ⑦Statement of 12 November 1982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 Nam on the Territorial Sea Baseline of Viet Nam,available at:http://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VNM_1982_Statement.pdf(last visited October 25,2015). ⑧See Nguyen Hong Thao and Ramses Amer,"Managing Vietnam's Maritime Boundary Disputes",p.313. ⑨Robert W.Smith,"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Potentiality and Challenges",(2010) 41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214,p.219. ⑩Brunei's preliminary information,para.10,available at: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lies/preliminary/brn2009preliminaryinformation.pdf(last visited October 25,2015). (11)See Joint Press Statement by Leader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Working Visit of YabDato' Seri Abdullah Haji Ahmad Badawi,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to Brunei Darussalam on 15-16 March 2009,available at:http://bn.chineseembassy.org/eng/wlxw/t542877.htm(last visited October 25,2015). (12)R.Haller-Trost,"The Brunei-Malaysian Dispute over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Claims in International Law",1(1994) Maritime Briefing 1,p.43. (13)Brunei's preliminary information,pars 24,available at: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preliminary/brn2009preliminaryinformation.pdf(last visited October 25,2015). (14)See 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1971,"Straight Baselines:Indonesia",Limits in the Seas,No.35,p.2,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e/oes/ocns/opa/c16065.htm(last visited October 25,2015). (15)See Article 3,Emergency(Essential Powers) Ordinance,No.7,1969,as amended in 1969. (16)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1970,"Continental Shelf Boundary:Indonesia and Malaysia",Limits in the Seas,No.1,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1975.pdf(last visited October 25,2015). (17)Victor Prescott,"Indonesia's Maritime Claims and Outstanding Delimitation Problems",(1996) 3 Boundary and Security Bulletin 91,pp.94-95. (18)Leo Bernard,"Whose side is it on?-The Boundaries Dispute in the North Malacca Strait",paper presented at the 2nd CIL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1,ASEAN's Rol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Faculty of Law,Gadjah Mada University,Indonesia,21-22 November 2011,p.6. (19)领海基线上所设定的点或者出于划界需要在海岸上确定的点为“基点”,应与划界线上的“折点”相区分。 (20)See W.Michael Reisman and Gayl S.Westerman,Straight Baselines i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92),p.133; See also 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1983,"Straight Baselines:Vietnam",Limits in the Seas,No.99,pp.8-13,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e/oes/ocns/opa/c16065.htm(last visited October 25,2015). (21)See Zou Keyuan,"The Sino-Vietnamese Agreement on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in the Gulf of Tonkin",(2005) 36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13,p.15. (22)David A.Colson and Robert W.Smith(eds.),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Volume VI(Leiden/Bost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11),pp.4308-4309. (23)Clive Schofield and I Made Andi Arsana,"Closing the Loop:Indonesia's Revised Archipelagic Baselines System",(2009) 1 Australian Journal of Maritime and Ocean Affairs 57. (24)David A.Colson and Robert W.Smith(eds.),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Volume VI(Leiden/Boston:MartinusNijhoff Publishers,2011),p.4308. (25)《公约》第15条:“如果两国海岸彼此相向或相邻,两国中任何一国在彼此没有相反协议的情形下,均无权将其领海伸延至一条其每一点都同测算两国中每一国领海宽度的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的中间线以外。但如因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而有必要按照与上述规定不同的方法划定两国领海的界限,则不适用上述规定。” (26)Maritime Delimitation in the Black Sea(Romania v.Ukraine),Judgment,I.C.J.Reports 2009,p.61(hereinafter "the Black Sea case"),at p.108,para.137. (27)See 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1980,"Continental Shelf Boundary:Italy and Tunisia",Limits in the Seas,No.89,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58822.pdf(last visited October 25,2015). (28)See 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1980,"Continental Shelf Boundary:Italy and Spain",Limits in the Seas,No.90,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58823.pdf(last visited October 25,2015). (29)后来美国对其所有的领土都采用低潮线划定领海基线,即使阿拉斯加的部分海岸非常曲折,符合《公约》第7条的适用条件。See Victor Prescott and Clive Schofield(eds.),The Maritime Political Boundaries of the World(Leiden/Bost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5),p.144. (30)Lewis M.Alexander,"Baseline Delimitations and Maritime Boundaries",in Donald R.Rothwell(ed.),The Law of the Sea(Cheltenham/Northampton:Edward Elgar Publishers,2013),p.93. (31)Legault,L and B.Hankey,"Method,Oppositeness and Adjacency,and Proportionality in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in Jonathan I.Charney and Lewis.M.Alexander(eds.),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 Volume I(Dordrecht/Boston/Lond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3),p.206. (32)《公约》未对具体的划界方法作出规定的原因是,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主张等距离划界方法与主张公平原则划界方法的集团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主张等距离划界方法的集团要求公约将等距离划界方法作为具有强制力的划界方法,这遭到了主张公平原则的集团的反对。该集团以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判决为依据,主张划界应以公平原则为依据,即否认任何划界方法具有法律强制力,而是要综合考虑一切有关情况来予以决定。为了调和两派的矛盾,最终的第74条和第83条的内容既没有规定等距离线的适用,也没有对公平原则作出规定,而这两个条款在有的学者看来是“没有太大意义的”。See R.R.Churchill and A.V.Lowe,The Law of the Sea(Oxford: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p.191. (33)Malcolm D.Evans,"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in David Freestone et al.(eds.),The Law of the Sea:Progress and Prospect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38. (34)2009年黑海案判决总结划界第一步为“通过几何学上客观并适合划界区域地理状况的方法,做出一条临时划界线”。尽管临时划界线并不等同于临时等距离划界线,但从法院紧随其后的补充来看,无论是海岸相邻情况下的等距离线,还是海岸相向情况下的中间线,都表明法院的意图是将临时划界线与临时等距离线等同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法院指出在海岸相邻的情况下临时等距离线的适用存在例外,即“除非具有极强的理由使等距离线段的构建不可能”,也就是类似2007年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案中由于河口的位置极不稳定而导致难以确定合适的基点以构建等距离线这样的情况;而在海岸相向的情况下,法院并未指出任何例外。因此可以认为,国际法院的意图是第一步应构建临时等距离线。See the Black Sea case,para.116. (35)自1985年利比亚诉马耳他案以来,国际法院在审理海洋划界案时会以临时等距离线作为起点,再考察有关情况决定是否对临时等距离线作出调整。这一划界步骤逐渐得到巩固和发展,不仅在国际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在国际常设仲裁法庭的案件中也得到了遵循。首次对这三步划界方法进行归纳总结的是2009年国际法院审理的罗马尼亚诉乌克兰的黑海划界案,而在2012年国际海洋法法庭审理的孟加拉国诉缅甸的孟加拉湾划界案中,海洋法庭将这三步划界方法明确称为“等距离/有关情况划界方法”。See Dispute concerning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Bangladesh and Myanmar in the Bay of Bengal,Judgment,14 March 2012,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available at:https://www.itlos.org/fileadmin/itlos/documents/cases/case_no_16/C16_Judgment_14_03_2012_rev.pdf,(hereinafter as "Bangladesh/Myanmar case"),p.73,para.229.这一划界方法在最新的国际司法案例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也得到了遵循。 (36)有关《公约》第15条的解释存在争议。该条来源于1958年《日内瓦领海公约》。在1977年英法划界案中,仲裁庭认为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是一个统一的规则,而不是规则与例外的关系。而国际法院在2007年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案中则推翻了这一解释,而采取了本文中这一解释方法,以特殊情况的存在为由排除了等距离方法的适用。本文认为,从《公约》第15条的文本来看,应采取2007年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案中的解释。See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 between Nicaragua and Honduras in the Caribbean Sea(Nicaragua v.Honduras),Judgment,I.C.J.Reports 2007,p.659,at p.743,para.280. (37)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1970,"Continental Shelf Boundary:Indonesia and Malaysia",Limits in the Seas,No.1,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1975.pdf(last visited October 25,2015). (38)Victor Prescott,"Indonesia's Maritime Claims and Outstanding Delimitation Problems",(1996) 3 Boundary and Security Bulletin 91,p.95. (39)Ted L.McDorman,"Central Pacific and East Asian Maritime Boundaries",in David A.Colson and Robert W.Smith(eds.),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Volume V(Leiden/Bost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5),p.3446. (40)Tara Davenport,Southeast Asian Approaches to Maritime Delimitation,Paper presented at the 3rd NUS-AsianSIL Young Scholars Workshop,NUS Law School,23 February-24 February 2012,p.28. (41)David A.Colson and Robert W.Smith(eds.),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Volume VI(Leiden/Boston:MartinusNijhoff Publishers,2011),p.4302. (42)Ibid.,p.4310. (43)Prosper Weil,The Law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Reflections(Cambridge:Grotius Publications Limited,1989),p.51. (44)例如是否存在海岸凹陷地形。在2012年孟加拉湾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考虑到孟加拉国海岸呈凹陷地形,若严格采用等距离线会对孟加拉国造成不公平的结果,因此调整了临时等距离线的位置。Bangladesh/Myanmar case,pp.90-92,paras.291-297. (45)岛屿的存在,包括其位置及其效力均可能会对划界的最终结果造成影响。例如,在2001年的卡塔尔诉巴林案中,国际法院完全忽略了巴林所属的无人居住的吉塔特杰拉达(Qit' at Jaradah)小岛的效力,认为如果赋予这样一个毫不重要的小岛海洋划界的效力会造成不合比例的效果。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ahrain,Merits,Judgment,1.C.J.Reports 2001,p.40(hereinafter as "Qatar v.Bahrain case"),at p.104,para.219. (46)基于陆地支配海洋这一基本原则,沿海国能够主张的权利范围与其海岸长度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划界应当反映沿海国海岸线长度的差异。在2012年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案中,国际法院就依据尼加拉瓜大陆与哥伦比亚所属岛屿之间海岸线长度的巨大差异,调整了临时等距离线的位置。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Dispute(Nicaragua v.Colombia),Judgment,I.C.J.Reports 2012,p.624(hereinafter as "Nicaragua v.Colombia case"),at pp.700-702,paras.208-211. (47)1982年利比亚诉突尼斯案中,国际法院否定了经济因素与大陆架划界的相关性,国际法院认为:划界是一项永久的国家行为,而经济因素则是变化多端的;一个国家可能今天贫穷,但明天可能因资源的开发而变得富有,因此,不能在划界过程中纳入这种多变因素的考察。Continental Shelf(Tunisia/Libyan Arab Jamahiriya),Judgment,I.C.J.Reports 1982,p.18,at p.77,para.107. (48)2009年黑海案中,国际法院否认了两国提出的国家安全因素与划界线位置的有关性,这一判断延续了国际法院在1985年利比亚诉马耳他案中的判断。The Black Sea case,p.128,para.204. (49)See the Black Sea case,p.128,para.204; see also Continental Shelf(Libyan Arab Jarnahiriya/Malta),Judgment,I.C.J.Reports 1985,p.13,at p.42,para.51. (50)Jonathan I.Charney and Lewis.M.Alexander(eds.),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 Volume I(Dordrecht/Boston/Londo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3),p.1022. (51)Tara Davenport,Southeast Asian Approaches to Maritime Delimitation,Paper presented at the 5rd NUS-AsianSIL Young Scholars Workshop,NUS Law School,23 February-24 February 2012,p.28. (52)Jonathan I.Charney and Robert W.Smith(eds.),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Volume IV(The Hague/London/New York :MartinusNijhoff Publishers,2002),pp.3749-3750. (53)See David A.Colson and Robert W.Smith(eds.),International Maritime Boundaries,Volume VI(Leiden/Boston:MartinusNijhoff Publishers,2011),pp.4308-4310. (54)Bangladesh/Myanmar case,p.50,para.147. (55)Alex G.Oude Elferink,"The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How Does Their Presence Limit the Extent of the High Seas and the Maritime Zones of the Mainland Coasts?",(2001) 32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169,p.171. (56)大陆国家的远洋群岛能否划定直线基线的问题存在一定的争议。参见贾楠:《论大陆国家远洋群岛的法律地位》,载《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12年第1期,第29-57页。 (5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3年第10期)。 (58)See Yann-huei Song,"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21(3) of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to the Five Selected Disputed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2009) 27 Chinese(Taiw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Affairs 43; Jon M.Van Dyke,"Disputes Over Islands and Maritime Boundaries in East Asia",in Seoung-Yong Hong and Jon M.Van Dyke(eds.),Maritime Boundary Disputes,Settlement Processes,and the Law of the Sea(The Hague:MartinusNijhoff Publishers,2009). (59)Nicaragua v.Colombia case,p.674,para.139. (60)Note Verbale of China,Communication dated 14 April 2011,available at: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mysvnm33_09/chn_2011_re_phl.pdf(last visited October 25,2015). (61)在英文翻译件中,表述为"China's Nansha Islands is fully entitled to Territorial Sea,Exclusive Economic Zone(EEZ) and Continental Shelf'(emphasis added),这似乎是将南沙群岛作为一个整体。 (62)参见贾宇:《南海问题的国际法理》,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6期。See also Zhiguo Gao and BingBing Jia,"The Ninedash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History,Status and Implications",(2013) 107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ernational Law 98. (63)Hong Thao Nguyen & Ramses Amer,"Coastal Sta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Submissions on the Outer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2012) 42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pp.245-263. (64)Brunei's preliminary information,para.20,available at: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preliminary/brn2009preliminaryinformation.pdf(last visited October 25,2015). (65)Note Verbale of Indonesia,Communication dated 8 July 2010,available at: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mysvnm33_09/idn_2010re_mys_vnm_e.pdf(last visited October 25,2015). (66)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Philippine position on Bajo de Masinloc(Scarborough Shoal) and the waters within its vicinity,April 18 2012,available at:http://www.gov.ph/2012/04/18/philippine-position-on-bajo-de-masinloc-and-the-waters--within-its-vicinity/(last visited October 25,2015). (67)An Act to Amend Certain Provisions of Republic Act No.3046,as Amended by Republic Act No.5446,to Define the Archipelagic Baseline of the Philippines and for other Purposes,Section 2. (68)参见中国政府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mfa.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217143.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0月25日。 (69)Jon M.Van Dyke,"Disputes Over Islands and Maritime Boundaries in East Asia",in Seoung-Yong Hong and Jan M.Van Dyke(eds.),Maritime Boundary Disputes,Settlement Processes,and the Law of the Sea(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9),p.69. (70)Yann-huei Song,"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21(3) of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to the Five Selected Disputed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p.61. (71)Yann-huei Song,"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21(3) of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to the Five Selected Disputed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p.73. (72)Qatar v.Bahrain case p.97,para.185. (73)Yoshifumi Tanaka,Predictability and Flexibility in the Law of Maritime Delimitation(Oxford:Hart Publishing,2006),pp.214-215. (74)事实上,在距离不足400海里的海岸相向国家之间的划界中,任何一个国家均不能享有200海里完整的海洋区域,这不意味着其200海里的海洋权利主张没有得到承认;而在岛屿与大陆国家之间的划界中,例如扬马延案中,临时等距离线向岛屿一侧调整也不意味着岛屿200海里的权利主张没有得到承认,而是综合考量了案件中的有关情形之后,为公平解决作出的安排。两者是不同的概念,应当予以区分。 (75)Robert Beckman,"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2013) 107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42,pp.149-150. (76)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划界案执行摘要,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Depts/los/clcs_new/submissions_files/chn63_12/executive%20summary_CH.pdf.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0月25日。 (77)2014年3月31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mfa.gov.cn/mfa_chn/fyrbt_602243/t1142645.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10月25日。See also Huy Duong,Negotiating the South China Sea,The Diplomat,available at:http://thediplomat.com/2011/07/negotiating-the-south-china-sea/(last Visited October 25,2015). (78)South China Sea issue should be resolved through negotiations by parties directly concerned:Chinese FM,Xinhuanet,available at: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3-07/02/c_124946440.htm(last visited October 25,2015). (79)See Mavrommatis Palestine Concessions(Greece v.Great Britain),Judgment of 30 August 1924,1924 P.C.I.J.(Ser.A) No.2,p.11. (80)Free Zones of Upper Savoy and District of Gex(Fr.v.Switz.),1929 P.C.I.J.(Ser.A) No.22(Order of Aug.19),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