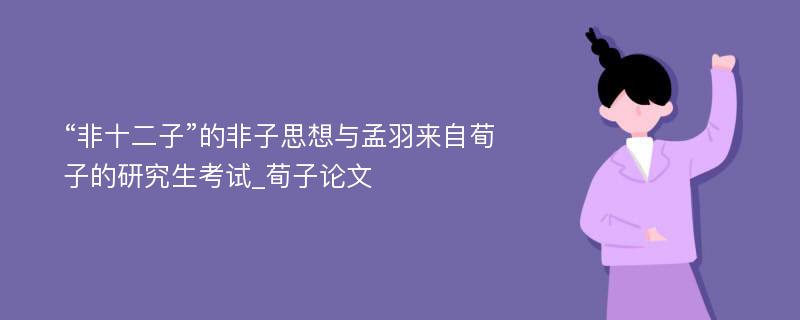
《非十二子》之非子思、孟軻出自荀子後學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荀子论文,子思论文,二子论文,後學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代學者王應麟根據韓嬰在《韓詩外傳》中引《非十二子》的內容時無最後一“非”(對子思、孟軻之非)而認爲,它是後加的,而不是原有的。雖然這種看法得到個別人的認可,但至今未被多數人所接受。本文試圖提出更多的證據以證明這一看法,並從一個新的視角考察孟荀關係。 爲了討論的方便,先把《荀子·非十二子》對十二人的批評完整地引用于後: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奸言,以梟亂天下,矞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在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雎,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嚣、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于上,下則取從于俗,終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弓爲茲厚于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這段有名的文字批評了六家,每家有兩個代表。最後一“非”很特別,它應該是後加的,而不是原有的,其理由有以下十項: (1)從結構上看,對前五家的批評都先指明其缺點,然後接著有一個固定的表述:“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XX、XX也。”但是,對第六家的批評則没有此表述。遺憾的是,這種結構上的不均衡,並没有引起論者們的重視。在我看來,它强烈地提示:非前五家的作者和非第六家的作者應該是不同的。假如是同一個人寫下上引全部文字,他應該在批評子思、孟軻的時候也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子思、孟軻也”。荀子用詞造句之講究,在先秦諸子中非常突出。如果他在前五個“非”中用同樣的結構,而在最後一個“非”中卻不用了,這確實很難理解。合理的推測是:荀子寫下了前“五非”,而荀子後學把最後“一非”加上去。 (2)最後一“非”與前五“非”還有其他結構上的不均衡。最後一“非”說到“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而前五“非”都没有“某某之罪”這種表述。在前五“非”中,被批評的兩個人是緊緊相連的:“它囂、魏牟”,“陳仲、史”,“墨翟、宋鈃”,“慎到、田駢”,“惠施、鄧析”,没有“某唱某和”的說法。類似“子思唱之,孟軻和之”這樣的說法只有在最後一“非”中纔有。 (3)在前五“非”中,前一“非”和後一“非”之間的關係與第五“非”和第六“非”之間的關係是不同的。在前“五非”中,前一“非”和後一“非”之間的關係是並列關係或相反關係(第一非的“縱情性”和第二非的“忍情性”處于相反關係,其他的則處于並列關係)。但是,第六“非”以“略法先王”來承接第五“非”的“不法先王”,使兩“非”之間形成遞進關係或遞退關係,于是便破壞了原有的並列關係或相反關係。把最後一“非”加上去的人非常聰明:在已有的批評惠施、鄧析“不法先王”之後,他(或他們)巧妙地以“略法先王”承接之。這樣使讀者形成文氣很順的印象。但事實上這是欲蓋彌彰的做法。 (4)從字數上看,最後一非共一百一十二字,遠遠超出前面的任何一非。第一非四十字;第二非四十五字;第三非55字;第四非七十字;第五非六十二字。前五非平均每非五十四字,而最後一非比這個數的兩倍還多。這表明最後一非實在太另類了。有人恐怕會認爲,後一非比前一非在字數上有不斷增加的趨勢。這樣的說法到第四非爲止是成立的,不過,增加的幅度不算大,遠遠没有最後一非(第六非)比第五非的增幅(一倍多)大。更要注意的是,第五非的字數没有比第四非的增加,反而減少了,這就證僞了不斷增加說。 (5)在先秦時無子思、孟子之相連,此一相連是漢代纔有的。韓非子有一段很有名的關于儒家各派的話:“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顔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①子思之儒與孟氏之儒爲兩個不同的學派,兩者之間隔著顔氏之儒。顯然,思與孟在這裏不相連。韓非子認爲這八個學派“取捨相反”。在他眼裏,子思之儒與孟氏之儒是不可能合爲一個學派的。既然如此,我們有理由認爲,韓非子的老師荀子也會把子思和孟子分開。這就意味著:他不太可能寫下“子思唱之,孟軻和之”這樣的話。在我的有限視野裏,我未看到在《荀子》以外的先秦的著作中有子思、孟軻之相連;只是到了漢代纔有這種相連,例如,揚雄的著作記載:“孫卿非數家之書,侻也;至于子思、孟軻,詭哉!”② (6)荀子批評俗儒已淪爲墨家而不自知,而孟子之反墨是衆所周知的。在《儒效》中,荀子把儒分爲三種:俗儒、雅儒、大儒。俗儒被他否定,而雅儒、大儒則被他肯定。他批評俗儒道:“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其言議談說已無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③“略法先王……繆學雜舉”與《非十二子》中批評子思、孟軻“略法先王……聞見雜博”很類似。那些堅持此批評是荀子作出的論者無疑會認爲他把孟子歸入俗儒一類。不過,以“辟楊墨”爲神聖使命的孟子對墨子的批評是很有名的,而《孟子》中也未顯示任何容納、吸收墨子的痕迹。比孟子後幾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荀子應該知道孟子對墨子的態度,因而不可能將他歸入俗儒一類。因此,合理的推測是:荀子後學挑選了《儒效》中的一些話(如“略法先王”)和改編了其中的一些話(如“繆學雜舉”)而用來批評孟子,但同時又故意抹煞了其中的一些話(如“其言議談說已無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 (7)在《非十二子》之外,荀子還在其他地方連續性地用排比句批評諸子,其中最有名者有兩處:“慎子有見于後無見于先,老子有見于詘無見于信,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④“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賢,申子蔽于勢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辭而不知實,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⑤在這兩處論述中,荀子都没有批評孟子,而這些被批評的“子”,其大部份又在《非十二子》中被再批評。假如你是荀子並且是孟子的批評者,你在第一處的最後寫下“孟子有見于善無見于惡”、在第二處的最後寫下“孟子蔽于X而不知X”這樣的話不是很自然的嗎?荀子没有這樣寫不是太意味深長了嗎? (8)西漢的韓嬰在《韓詩外傳》中大量引用《荀子》,但在引《非十二子》的內容時無最後一“非”。宋代學者王應麟指出:“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托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⑥清代學者汪中說:“《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⑦現代學者徐復觀說:“他(指韓嬰——引者)在《外傳》中共引用《荀子》凡五十四次。”⑧汪中和徐復觀所說的數字上的差异,可能是統計標準的不同而引起的。不管如何,從韓嬰大量引用《荀子》可見他深受荀子的影響。把他作爲荀子後學是說得過去的。王應麟認定是韓非子、李斯之流把非子思、孟子加到《非十二子》之中,不一定有過硬的根據(前面已經指出,韓非子把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分開。既然如此,說他把兩人合起來同屬一個學派而寫下“子思唱之,孟軻和之……是子思、孟軻之罪也”這樣的話是不可思議的)。但是,說荀子後學(不能確定具體的人)這樣做則是合理的。清代學者盧文弨在談到《非十二子》時說:“《韓詩外傳》止十子,無子思、孟子。此乃並非之,疑出韓非子、李斯所坿益。”⑨與王應麟相比,盧文弨加上一個“疑”字,語氣相對平實一些,但是,還是不應該點這兩個荀子弟子的名。在衆多荀子後學中,這兩個名人之外的其他人都有可能把對子思、孟子之非加上去。完整地看《韓詩外傳》中的那一段論述,對于我們考慮此非是什麼時候加的會很有幫助:“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奸言,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睢、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鈃、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自爲工,道無所遇,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衆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⑩這裏的文字顯然源自《非十二子》,但没有非子思、孟子。“聞見雜博”、“按往舊造說”、“之罪”在《韓詩外傳》中是泛說,用于批評十子,而在《非十二子》中是特說,專用于批評子思、孟子。非子思、孟子的荀子後學襲用韓嬰的說法,但將他的泛說改爲特說。在我看來,非子思、孟子的荀子後學應該晚于韓嬰。 (9)那些堅持《非十二子》中之非子思、孟軻的話是荀子說的人,至今爲止没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表明荀爲什麼這樣說。唐代學者楊倞指出:“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僻違無類,謂乖癖違戾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幽隱閉結而不能自解說,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興作方略也。荀卿常言法後王,治當世,而孟軻、子思以爲必行堯、舜、文、武之道,然後爲治,不知隨時設教,救當世之弊,故言僻違無類。”(11)楊倞認爲荀子法後王,而孟子法先王,但事實上,荀子說法先王遠多于說法後王。據我粗略的統計,《荀子》一書中提到法後王的一共只有五次,而提到法先王或肯定先王的起碼有二十五次。楊倞把“五行”解釋爲“五常”,但没有說爲何荀子反對五常。梁啓超傾向于楊倞的解釋,但又指出:“果屬五常,似不能謂爲‘僻違無類,幽隱無說,閉約無解’,故此數語終不甚可曉。今强申楊說,則:孔子只言仁,或言仁智,或言智仁勇,未有以仁義禮智信平列者。孟子好言仁義禮智,義禮本仁智所衍生,以之並舉,實爲不倫,故曰無類;其說不可通,則無說可解也。然孟子亦無以信並于仁義禮智爲五行之語,故此說亦卒未安。”(12)在20世紀70年代馬王堆帛書公諸于世之後,龐樸認爲,“五行”是指“仁義禮智聖”。(13)此說受到很多論者的贊成。但是,他對爲何以“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等來批評“五行說”的解釋則太簡單、太籠統。廖名春在接受了“五行”就是指“仁義禮智聖”的基礎上,將《非十二子》中之非子思、孟軻之語與《荀子·性惡》聯繫起來,以爲其關鍵是批評兩人的性善論:“子思、孟軻卻倡言仁義禮智聖出于人性。這在荀子眼中,是公然違背孔子遺教的行爲……他當然就要奮身而起,斥責思孟這種荒謬的五行之性說……子思、孟軻既稱人性爲善,仁義禮智聖出于人性之本有,又說要法先王,實際上連先王產生的必要性都否定了,連聖王禮義存在的邏輯根據都拋弃了,這種抽象肯定而具體否定的方法,無异于塞源而求流暢,伐木而求葉茂,所以說是‘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仁義禮智聖出于人性,始于子思,而爲孟子所系統化,故荀子以爲是‘造說’……所謂‘案往舊’,就是子思、孟子制造此說利用了前人的思想材料……仁義禮智聖出于人性的‘五行’說,也就是性善論。荀子認爲性善論不合乎孔子重視後天學習的思想,故云‘邪僻’;性惡是聖王之所以成立、禮義之所以產生的邏輯根據,而性善則否認了聖王、禮義存在的必要性,這就是‘不知其統’,故云‘無類’;性善說既不能‘節于今’,也不能‘徵于人’,没有辨合、符驗,‘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故云‘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14)這些說法非常有創意。以性惡論爲中心來解釋《非十二子》中之非子思、孟軻,確實很有意思。但是,廖名春之說起碼難以回答兩個問題:首先,既然這篇文章批判子思、孟軻實際上主要就是批判他們的“性善”或“性善說”,爲什麼通篇不出現這兩個字或這三個字或類似的字呢?如果我是此批判者,在“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後加上諸如“道性善”這樣的話是再自然不過的了。其次,如果說有確鑿無疑的證據表明孟子主張性善的話,那麼,從傳世文獻或出土文獻中能找到說得過去的證據表明子思也明確主張性善嗎?廖名春把《非十二子》與《性惡》聯繫起來研究,這個思路很好。不過,20世紀初的劉念親聯繫兩文來研究,卻得出了剛好相反的結論:荀子不主張性惡。對此,我們在本文最後一部份要詳細討論。如果荀子真的主張性惡,爲什麼他不在《非十二子》中明確批評孟子的性善說呢?如果真的像後世所接受的那樣,兩人對人性的分歧是他們最大的分歧,爲什麼荀子在這個關鍵的地方不明確顯示此分歧呢? (10)在《孟子》全書中,完全没有提到“五行”,而據說是子思作的《中庸》也同樣未提。既然如此,怎能批評兩人主張五行呢?顧頡剛解釋說:“《非十二子》中所駡的子思孟軻即是鄒衍的傳誤,五行說即是鄒衍所造。”(15)在顧看來,是荀子張冠李戴,把鄒衍之說挂到子思、孟軻名下了。頭腦清醒的荀子應該不會如此糊塗吧。顧頡剛之說肯定難以被人接受。不過,他認爲是鄒衍造五行說,這倒比較可信。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鄒衍在孟子之後。五行說大盛于漢代。《孟子外書》很可能提到五行,但它早已被趙岐判爲非孟子所作。它應該是出自漢人之手。在漢代流傳而今天失傳的挂著子思之名的著作也可能說到五行。看來,是漢代的人假托子思、孟軻說五行(正如時人假托黃帝之名而編《黃帝內經》一樣),思、孟本身並不說五行。 綜觀以上十條理由,我們不難看到:說荀子本人寫下《非十二子》中非子思、孟軻的部份,是很不可理解的。下一部份所說的荀子對孟子的肯定和吸收,會更有力地表明:他不可能用激烈的言辭批評孟子。 《荀子》一書中有兩處正面地肯定了孟子,它們顯然出自荀子本人之手,其中之一是: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辟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聲,閑居静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强矣,未及思也;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辟耳目之欲,遠蚊虻之聲,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忍!何强!何危!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强也。仁者之思也恭,聖者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16) 在上引論述中,荀子將觙、孟子、有子和至人(聖人)作了比較。有人認爲荀子在這裏温和地批評了孟子。但是,我認爲,完整地看這一段話,說他正面地肯定孟子更恰當。荀子當然認爲聖人是最高級的,但並不認爲低于他的那三個人不好。在荀子看來,好思的(危的)觙、自强的孟子、自忍的有子都是不錯的,只不過不如已達到最高境界的、“微”的聖人而已。聖人從心所欲不逾矩,故無思、無强、無忍。這裏的論述確實比較正面地說孟子,而與《非十二子》中對他的尖銳批評截然不同。實在難以理解一個承認孟子自强的人會以“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等嚴厲的措辭來批評他。 《荀子》中更明顯地肯定孟子的話是:“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17)在此話的前後,荀子没有對孟子的明確評論。但是,從他的客觀叙述中,我們不難發現他對孟子“攻其邪心”的肯定。雖然《大略》不是荀子所作,但它體現了荀子的思想。楊倞說:“此篇蓋弟子録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已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18)我們這裏所引的《大略》的話和上一段所引的話,被太多關注孟、荀關係的人所忽略。仔細琢磨這些話,我們必然會對這種關係產生新的看法。顯然,說這些話的人猛烈地攻擊孟子有“罪”是不可思議的。合理的解釋是:說這些話的人與猛烈地攻擊孟子的人不是同一個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說的很多話明顯來自孟子。試比較以下兩邊的文字,上荀下孟: A.聖也者,盡倫者也。(《解蔽》) B.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富國》) C.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富國》)。 D.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修身》) A1.聖人,人倫之至也。(《離婁上》) B1.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公孫丑上》) C1.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孫丑下》) D1.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唯士爲能。(《梁惠王上》) E.聖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鼋鼍魚鱉鰍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污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王制》) F.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七教,所以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大略》) G.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議兵》) E1.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 F1.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奪其時,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道之也。詩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也!(《梁惠王上》) G1.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盡心上》) 對照以上左邊荀子的話和下邊孟子的話,顯然可見兩者高度的相似性。A和A1幾乎一樣,都以倫或人倫來說聖人;荀子把孟子的“至”改爲“盡”,但兩個字是同義的。B和B1的意思也很接近,而“百技”和“百工”在表達形式上也相似。在C和C1中,天時、地利、人和的先後順序一樣,只不過孟子更重人和,而荀子未在意三者之輕重。D的道與D1的恒心,其具體所指大致上都是仁義禮智,荀子和孟子一樣都認爲士人即使在貧窮的狀態之下也要堅守之。對照E和E1、F與F1,可見荀子在語言表達上對孟子的接受或吸收更爲明顯。在《梁惠王上》中,F1緊接在E1之後,而E、F則分別見于《王制》和《大略》。從用詞到造句,E和E1、F與F1實在太相似了。對這種相似性的合理解釋是:荀子在說這些話之前,肯定看過孟子的話。從孟子的“王道之始”到荀子的“聖王之制”、從孟子的“魚鱉”到荀子的“鼋鼍魚鱉鰍鱣”、從孟子的“穀不可勝食”到荀子的“百姓有餘食”、從孟子的“材木不可勝用”到荀子的“百姓有餘材”、從孟子的“五畝之宅”到荀子的“五畝宅”、從孟子的“無失其時”、到荀子的“勿奪其時”、從孟子的“謹庠序”到荀子的“設庠序”,如此等等,都明確無疑地顯示了荀子的說法是來自孟子的。對照G與G1,也發現荀子在表述上吸收孟子的說法。孟子說的是“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荀子在同一篇文章中首先說“所存者神,所過者化”,然後又說“所存者神,所爲者化”。孟說和荀說如此接近,只能用後者來自前者來解釋。 從荀子方面看,《富國》一篇就有兩句話出自孟子或者受到孟子的啓發,《議兵》也同樣如此。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議兵》中,出自孟子的同樣的或很接近的話說了兩次。從孟子方面看,《梁惠王上》中被荀子引述的就有三處。作爲《孟子》的第一篇,《梁惠王上》最容易被讀者注意到。因此,荀子引用本篇之語最多,這是很容易理解的。面對這些荀子引用孟子的話,誰能想像他會寫下《非十二子》中那些猛烈地攻擊孟子的話? 事實上,荀孟之同大于异。後人不斷地添油加醋,誇大兩人之异,遂覆蓋了歷史的本真。上一部份所說的荀子對孟子的引用和吸收表明了兩人之同,以下再進一步說兩人思想之同。 以德服人。作爲儒家的代表,荀子和孟子都繼承了孔子的以德服人的思想。孔子的名言“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19)是這一思想的具體表述。孟子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20)荀子說:“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俞强。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埶,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衆,奉養必費。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饑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期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俞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21)顯然,荀子所說的與孔子、孟子所說的是一致的。荀子對三種兼人(以德兼人、以力兼人、以富兼人)作了比較,得出的結論是:以德兼人好,而以力兼人、以富兼人都不好。第一種兼是王,第二種兼是霸。荀子肯定知道前引孔子的名言,而且也應該知道前引孟子的說法。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争奪的越演越烈。王霸之辯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王者主德,霸者主力。在很多人看來,王者是理想主義者,而霸者是現實主義者。在王霸之辯中,儒家一律堅持王道。秦滅六國是表明了霸的威力,但王道的價值也經受了長久的歷史考驗。 以道固國。大家都很熟悉孟子的有名的話:“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22)荀子繼承了孟子的說法而指出:“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23)“禮者,治辨之極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24)荀子將孟子之道具體化爲禮義辭讓忠信或者禮(在前一段話中,道是禮義辭讓忠信;在後一段話中,道是禮)。假如孟子活到荀子之時,估計他會接受這樣的具體化。以道固國與前述以德服人的思想完全一致。這也表明,荀子的政治哲學與孟子的是一致的。 惠民政治。對照上一部份所引的E和E1、F與F1,可見荀孟兩人都贊成惠民政治。他們對民的態度確實是一致的。孟子要求儒君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就是仁政,其具體內容主要包括:(1)給民以“恒產”。民的“恒產”主要是指土地(“百畝之田”)和園宅(“五畝之宅”)。(2)輕賦稅薄徭役。(3)要民服役時不要違農時。(4)省刑罰,不株連。(5)救濟窮人鰥寡孤獨等弱勢群體。這些都是惠民的具體措施。荀子的以下之言表明他完全認可這些措施:“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徵,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25)他和孟子一樣不僅主張惠民,而且主張重民。孟子對儒家重民傳統的一種經典表述是:“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26)荀子對此傳統又有另一種經典表述:“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27)孟子的民貴君輕和荀子的立君爲民都顯示了民在儒家心目中的地位。 不與民争利。很多人都未能貼切地理解《孟子》開頭中“何必曰利”的話。孟子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28)顯然,孟子反對言利首先是針對國王說的,其次是針對大夫說的,再次是針對“士庶人”說的。如果把“士庶人”解釋爲一類人,那麼,他們就不包括百姓;如果把他們解釋爲兩類人(士、庶人),那麽,他們就包含了百姓。我個人傾向于把他們解釋爲一類人。當然,就算作兩類人的理解,庶民也不是孟子在這段話中關注的重點。在我看來,孟子在這裏表述的是上者(尤其是君王)不與民争利的思想。這與他的惠民主張是一致的。民求利天經地義,但君與民争利則遺害無窮。與孟子相比,荀子具有更明確的不與民争利思想:“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争業,樂分施而耻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29)荀子要求天子、諸侯、大夫、士不言利,不與民争業,這樣民就“不困財”。如果士以上的人個個逐利,那百姓的日子就很難過了。荀子還更嚴厲地說:“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30)既然富民那麼重要,自然就預設了民求利是正當的。關鍵在于上者不與民争利。與民争利的最嚴重後果是亡國。 大丈夫精神。《孟子·滕文公下》中對這種精神的表述衆所周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與之相比,荀子所說的德操非常相似:“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31)我們于此又可見荀子在用詞造句方面對孟子的模仿:從文字上看,兩個“移”完全一樣,“不能”的反復使用也完全一樣,而且,“傾”與“屈”接近,“蕩”與“淫”也接近;從句子上看,兩人都寫了三個類似的排比句。荀孟文與義的一致性昭昭然。孟子的大丈夫精神和荀子的德操,都顯示了儒者不屈服外界的精神和對堅定、頑强意志的追求。 天人之誠。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32)這是孟子對天人之誠的經典論述。荀子對天人之誠的經典論述是:“君子養心莫善于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33)雖然荀子的論述比孟子的詳細得多,但是,兩者的一致性是很明顯的。兩人都非常注重誠,都既重天之誠,也重人之誠(相對而言,也都更重人之誠)。順便指出,荀子的“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令我們想起孟子的話:“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34)兩者在文字上的類似又再次表明荀子對孟子的接受。 批評墨子。孟子對楊、墨的批評衆所周知:“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35)儒家主張愛有差等,而墨家主張兼愛。同爲儒家代表的荀子繼承孟子對墨子的兼愛的批評就是很自然的。《荀子》一書有多次對墨子的批評,其中包括:“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36)“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37)“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38)荀子指責墨子“僈差等”、“不足以容辨异、縣君臣”、“有見于齊無見于畸”,這些都是與孟子對他(和楊朱)的“無君無父”的指責一脉相承的。 以上所列的,並不是孟荀一致的全部內容。兩人對心的看法、對心身關係的看法、對養氣的看法、對聖人的看法等等,都還有一致之處。因篇幅所限,無法一一詳述。後人的說法往往會掩蓋前人的本真。荀子與孟子的一致,在後人越來越誇大兩人的對立中被逐漸掩蓋了起來。不過,只要細心研讀《荀子》和《孟子》,這些被掩蓋的東西不難被發現。宋代的唐仲友雖然跟其他人一樣以性善論、性惡論分梳孟荀,但已意識到兩人的一致:“卿獨守儒議,兵以仁義,富以儒術,强以道德之威,旨意與孟子同。”(39)面對這如此多的荀孟的一致,你還會堅持荀子寫下了《非十二子》中那些猛烈地攻擊孟子的話嗎? 《荀子》全書只有兩個地方明確地反對孟子:一是《性惡》,二是《非十二子》。前面已經反復辯明:《非十二子》之非子思、孟軻部份不出自荀子之手。論者們一定會問:難道《性惡》也不是他寫的嗎? 劉念親和日本學者金谷治、兒玉六郎以及美國學者孟旦(Donald J.Munro)等對這個問題作了很好的探索。1923年1月16、17、18日的《晨報副刊》連載了劉念親的文章:《荀子人性的見解》(以下引文,如無注明,全出自該文)。梁啓超加推薦語道:“友人劉君鴻岷,以其族弟著存君近作此篇見示,疑性惡篇非荀子所作。此讞若真,則學界翻一大公案矣。余方忙于他課,未暇重繹荀子全書,對于劉君之說,不敢遽下批評。惟覺此問題關係重大,亟介紹之以促治國學者之研討云爾。”(原文“國聞”顯然爲印刷錯誤,應爲“國學”) 劉念親的文章廣泛引用《荀子》一書中《性惡》之外的對性(包括生,先秦時生與性同)的十七條論述,它們完全没有性惡的意思: 1.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鱉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鱉致之,六驥不致,是無它故焉,或爲之,或不爲爾。(《修身》) 2.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夫不知其與已無以异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君子之所爲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异也。(《榮辱》) 3.好修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可謂篤厚君子矣。(《儒效》) 4.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隆性矣。師法者,所得乎積,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也。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積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並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儒效》)(40) 5.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人一之于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則兩喪之矣。(《禮論》) 6.性者,本始材樸也;僞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禮論》) 7.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者,謂之性。(《正名》) 8.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正名》) 9.性傷謂之病。(《正名》) 10.有欲,無欲,异類也,性之具也,非治亂也。欲之多寡,异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正名》) 11.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正名》) 12.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夫是之謂以己爲物役矣。(《正名》) 13.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賦》) 14.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大略》) 15.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勸學》) 16.凡人有所一同,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爲堯禹,可以爲桀紂,可以爲工匠,可以爲農賈,在注錯習俗之所積耳。(《榮辱》) 17.人倫並處,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富國》) 以上所列的十七條,都在《性惡》之外,都没有明述或暗示人性惡。劉念親還注意到,第2條中的部份內容又以類似的形式出現于《儒效》中:“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第16條中的部份內容更以完全一樣的形式出現于《非相》之中:“饑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如果把完全重複或接近重複的話也算進去,那麼,在《荀子》一書中,《性惡》之外對性或生的論述共有十九條。這些論述都完全没有人性惡的意思。劉念親指出:“若是性惡篇是他作的,不但與道家的‘任性命’儒家子思的‘率性’孟子的‘性善’爲極端的反對;就視孔子‘相近相遠’的說法,也带些异采。這正是他創獲的見解,豈有不于別篇說性各條揭櫫出來?”在《荀子》一書中,說人性惡的文章只有一篇。如果這一篇真的是荀子所作,那麼,他在其他多篇論及人性的文章中,爲什麼一律地不說人性惡呢?劉念親以新穎的思路、以充分的材料向我們表明: 說荀子是《性惡》的作者實在令人不可思議。作爲一個頭腦嚴謹的思想家,荀子怎麽可能在一篇文章中說人性惡,而在其他大量的文章中說性不惡呢? 與廖名春以《性惡》解釋《非十二子》之非子思、孟軻相反,劉念親看到: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未批評子思的率性說和孟子的性善說:“非十二子篇荀子向异己的學說,痛施攻擊,若是他曾斬截下了一個‘性惡’的斷案,那子思的率性說,孟子的性善說,便是與他根本上不能兩立的所在。他這篇非子思孟軻下,還肯將此層輕放過去麼?”假如荀子真的反對孟子的性善說,這是一個表明它的最好機會,爲什麼荀子放過了這個機會呢?廖名春將《性惡》與《非十二子》聯繫起來,以爲後者之非子思、孟軻,其關鍵點是批評兩人的性善論。並無令人信服的理由支持這種聯繫。相反,我們明顯看到的是:《非十二子》之最後一“非”不非性善論。 劉念親還看到:荀子有名的弟子中無人主張人性惡。劉念親考察了荀子弟子韓非子、李斯和再傳弟子賈誼以及傾向于荀學的董仲舒等人對人性的看法,都未發現他們主張人性惡。他引用了他們對人性的具體的論述,很有說服力。劉念親還發現,司馬遷在爲荀子作傳時没有說到他主張人性惡。他說:“揣量遷所見本,尚莫有性惡篇,故没有荀卿以爲‘人性惡’這類的話。” 在以充分的證據質疑荀子是《性惡》的作者的基礎上,劉念親認爲,荀子對人性的看法最典型地表述于《正名》之中。劉念親說:“總括起來:荀子人性的見解,性是生之所以然。好,惡,喜,怒,哀,樂,六情,是性中含的質……性得其養,欲雖多不傷欲于治;性失其養,欲雖寡,不止于亂。性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至于性的本體的斷案,只是‘本始才樸’四字。”劉念親充分地闡發了《正名》中的人性論。在他看來,這纔是荀子的人性論。荀子于《正名》中說的“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等,都表明了他對人性的基本主張。這些主張是與《性惡》的相反的。更難能可貴的是:劉念親將《正名》的人性論與《禮論》的人性論結合起來,把性論與禮論打通,得出了有理有據的結論。衆所周知,荀子重禮。如果囿于荀子是性惡論者的傳統看法,很難說得通他對性與禮的關係的看法。 上述劉念親的一系列看法,都是非常有新意的。他的《荀子人性的見解》是荀學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獻。但是,據我所知,雖然有梁啓超的推薦,劉文發表後似乎没有引起太大的反響。胡睿在《晨報副刊》1923年2月6日發表《〈荀子人性的見解〉的研究》,對劉文表示不同看法。不過,胡睿對《荀子》未有深入的研究,國學素養也不够好,甚至語言功夫也不好,故未構成對劉念親的看法的實質性挑戰。當然,另一方面,我也未讀到當時贊成劉念親的看法的文字。確實,以荀子爲性惡論的代表的觀念,有兩千多年的歷史。要推翻這種頑固的觀念,談何容易!而且,這裏還有一種心理因素值得注意:人們對于對稱的東西會特別有興趣,而孟子講性善、荀子講性惡的表述就非常地對稱。當有人說荀子不主張性惡的時候,這種心理因素就會起作用(經常是潜意識地起作用)。就算讀到劉念親文章的人在意識層面覺得它有根據,但是,這種潜意識的作用會淡化、消磨這些根據。隨著時間的過去,這些根據就可能逐漸被人忘記。不過,根據總歸是根據。 日本學者也向我們表明了一些有關根據。例如,金谷治在1951年看到,《韓詩外傳》未引《性惡》,而《非十二子》也没有批評孟子性善之主張,因此,《性惡》也許是荀子後學的作品。(41)再如,兒玉六郎在1974年則進一步指出,荀子人性論的核心是性樸,而不是性惡。(42)另外,美國學者孟旦看到,在《性惡》以外的《荀子》各篇,都未以人性爲惡,而以之爲某種不成熟的東西(something undeveloped)。(43)這些外國學者的看法,也很值得我們注意。本人在前賢看法的基礎上,反復申說荀子不是性惡論者,而是性樸論者。(44) 前面在考證《非十二子》中之非子思、孟軻部份不出自荀子之手的過程中展示了孟荀的一致性,這並不意味著兩人没有差异,更不意味著荀子思想没有獨立的價值。事實上,他們對人性的看法是不同的,這種不同並非如大家接受的那樣一個主性善,另一個主性惡,而是一個主性善,另一個主性樸。上述劉念親所引《荀子》中《性惡》以外的對人性的論述,都支持性樸論,其中,尤其以出自《禮論》的第6條“性者,本始材樸也……”最爲明顯。性樸論既不同于性善論,又不同于性惡論,也不同于性無善無惡論。性樸論隱含著:性中有善的潜質,但没有完備的、現成的善。從荀子思想的整體來看,它無法容納性惡論。荀子與孟子的不同還包括:荀子特別重禮,而孟子不怎麼重禮;孟子主張寡欲,而荀子不贊成寡欲;孟子談大人與小人之分,而荀子則談君子與小人之分;積、積靡、群分、師法等,都是荀子常用的概念,而孟子則幾乎不用之;從寫作方式上看,孟子擅長對話體,而荀子擅長論說文體;《孟子》中每篇的取名源自開頭的幾個字,故其篇名無實義,而《荀子》中絕大部份的篇名都有實義,它們一般都可恰當地概括全篇的要旨。 以上所說的荀子與孟子兩人的區別都值得注意。他們各自的後學(尤其是荀子後學)發揮、發展了這些區別,並制造了一些新的區別。把荀子和荀子學派適當地區分開來很有必要。《莊子》並非全爲莊子所寫,這早已得到公認。《荀子》中的最後幾篇《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等不是荀子所寫,這也得到公認。但是,除了這幾篇之外,是否還有更多的篇或某篇中的某部份不是荀子寫的呢?本文表明:最能體現荀子學派和孟子學派分歧的《性惡》、《非十二子》之非子思、孟軻部份,確實出自荀子後學之手。正如《莊子》是莊子學派的作品,而不是莊子一人的作品,《荀子》是荀子學派的作品,而不是荀子一人的作品。馮友蘭指出:“像《莊子》、《荀子》這一類的書名,在先秦本來是没有的,所有的只是一些零散的篇章,如《逍遙游》、《天論》之類。漢朝及以後的人,整理先秦學術,把這些零散的篇章,按其學術派別,編輯起來成爲一部一部的整書。其屬于莊子一派的,就題名爲《莊子》;其屬于荀子一派的,就題名爲《荀子》。他們本來没有說《莊子》這部書,是莊周親筆寫的,《荀子》這部書,是荀子親筆寫的。本來他們也没有意思這樣說。後來的人,不知這種情况,就在《莊子》這個題名下,加上莊周撰,在《荀子》這部書的題名下,加上荀况撰。再後來的人,就信以爲真。”(45)荀子學派和孟子學派的對立之形成與演變,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大概從漢代開始,至今還在延續。牟宗三等現代新儒家堅持以孟子爲正統而以荀子爲异端,大陸學者在50至80年代以前者爲唯心主義者而以後者爲唯物主義者,這就是孟荀對立的新發展。從動態而不是静態的角度考察荀孟之別,可以發現:這很像古史辯派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層累堆積的過程。 ①《韓非子·顯學》。 ②《法言·君子》。 ③《荀子·儒效》。 ④《荀子·天論》。 ⑤同上,《解蔽》。 ⑥王應麟:《諸子》,《困學紀聞》卷十。 ⑦汪中:《荀卿子通論》,見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下》,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1頁。 ⑧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三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5頁。 ⑨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89頁。 ⑩《韓詩外傳》卷四,第二十一章。 (11)見王先謙:《荀子集解》,第94頁。 (12)見梁啓雄:《荀子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63頁。 (13)龐樸:《馬王堆帛書解開了思孟五行說之謎——帛書〈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之一的初步研究》,《文物》1977年第10期。 (14)廖名春:《思孟五行說新解》,《中國學術史新證》,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20~422頁。 (15)顧頡剛:《古史辨》(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09頁。 (16)《荀子·解蔽》。 (17)同上,《大略》。 (18)見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485頁。 (19)《論語·季氏》。 (20)《孟子·公孫丑上》。 (21)《荀子·議兵》。 (22)《孟子·公孫丑下》。 (23)《荀子·强國》。 (24)《荀子·議兵》。 (25)《荀子·富國》。 (26)《孟子·盡心下》。 (27)《荀子·大略》。 (28)《孟子·梁惠王上》。 (29)同上,《大略》。 (30)《荀子·王制》。 (31)同上,《勸學》。 (32)《孟子·離婁上》。 (33)《荀子·不苟》。 (34)《孟子·盡心上》。 (35)同上,《滕文公下》。 (36)《荀子·非十二子》。 (37)同上,《天論》。 (38)同上,《解蔽》。 (39)唐仲友:《荀子序》,見王先謙:《荀子集解·考證上》,第6頁。 (40)劉念親原文引用的“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現據宋本改爲“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隆性矣”。 (41)金谷治:《荀子の文獻學的研究》,《日本學士院紀要》卷9號1,1951。 (42)兒玉六郎:《荀子性樸說の提出》,《日本中國學會報》卷26,1974。 (43)Donald J.Munro,The Concept of Man in Earl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77~78. (44)周熾成:《荀韓人性論與社會歷史哲學》,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荀子非性惡論者辯》,《廣東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 (45)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第2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