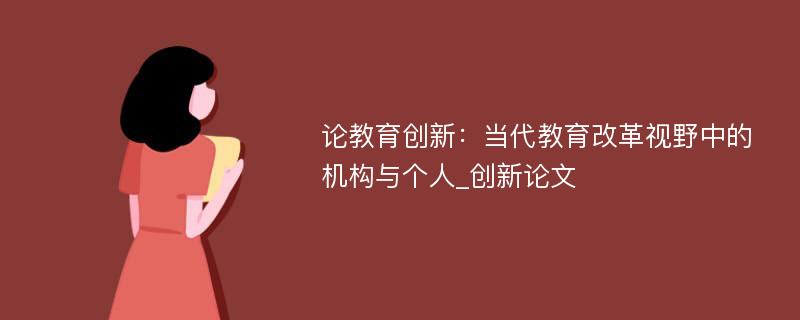
再论教育创新——当代教育改革视野中的制度与个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改革论文,视野论文,当代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7)01—0040—04
一、现代性“个人观”与“创新型人格”的形成
教育学关注的创新型人才的形成问题是以教育的真正发生为前提和基础的。所谓教育的真正发生,指的是所有外在的教育行为和环境对学生发生作用,并真正使其内在素质的建构和成长发生变化——学生不能只是“受到(receive)”了教育,而根本没有“接受(accept)”教育——更不能在走出校园之后在社会中仅仅是去扮演一种没有生命自我的“工具人”的角色,否则,一切教育行为都是“劳而无功”的“隔靴搔痒”式的忙碌。而教育的变革正是为着人的这种有生命力、创造力的“积极人格”的解放而来的。然而,在教育的发展历程中,个体地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应的观念转型,一度是作为近、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分水岭”显现的。
所谓“现代性”,它首先意味着个人从传统的各种禁锢中解放出来,获得谋划自己生活的自主性: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其次,在中世纪“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而现在“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1]。因此,这种现代性个人观意味着:它要使每个富于生命意义的人从传统的各种禁锢中解放出来,自觉地统筹和驾驭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积极彰显生命活力、谋划个人生存状态。从而它也构成了现代社会之现代性意识的核心部分,并成为当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不能不提及和把握的“要素”之一。历史的实证已经太多,已经不允许我们再作“含蓄”的回避或是“暂时”的隐讳了。
在中国,传统之“礼”所维系的等级森严的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下,个体对于“公”、“集”和“整体”及其代表的统治者只有敬畏和服从,个体的存在和发展以家族和整体的发展为转移,个体的人格以对“礼”的认同为前提,这就事实上造成了对个体的吞没。有人或许会担忧这会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正如胡适对其所推崇的“易卜生主义”即“健全的个人主义”的解释,包括两个要点:“第一,必须使人有自由意志。第二,必须使人担干系,负责任”[[2],(466)],这从某种程度上给出了我们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的一种建树。不仅于此,胡适还区分了三种个人主义:一种是假的个人主义,或称为我主义;一种是独善的个人主义,采取出世避世的方式在社会之外寻求理想生活;一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亦称个性主义,其特性是独立思想,且对自己的思想信仰的结果负责任”[[2],(539—540)]。而这种“负责任”的“独立”个性,正导致了教育持续不断地“真正发生”,从而在个体的内部能够建立一种可生发性很强的建构体系,为创造的发生提供了可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教育的使命和生命首要的就是要寻到并使这种真正的个人观在每一个生命个体身上彰显出来,成为当代教育下生命个体存在之人格中的一种特质。因为这种真正的个人观,“犹养成一种独立之人格,自助之能力,若吾国家族的‘个人主义’,则私利于外,依赖于内,吾未见其善于彼也”[3]。可见,近代中国生命教育的先驱者们对传统中国对于家族式的个人主义的诊断不无道理,这也正是长久以来“创新型人才”之不出、诺贝尔奖“无缘”的病灶所在。所以说,要使生命个体成为“创新型人才”,首先要成为真正的生命意义上的“人”;而要成生命意义上的“人”,就必须葆有“生命”的独立性、自主性和成长权。这正如梁启超所强调:“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两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4]。可以想象,一个没有生命意义上的“人”的教育,怎敢对它奢求什么“创新型人才”?!
是故,要企望“创新型人格”的形成,首先需要摆脱那种使学生“受教(receive)”而不“接受(accept)”的窘境,真正重建和弘扬现代性的“真正的个人观”。惟其如此,教育才能让人有生命、有思想、有灵魂,让“人”有真正意义上的“个性”、“人格”,让人成其为“人”(而不是“工具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才能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生命实践”活动。惟其如此,人才拥有了其接受教育的内在的“积极”环境;唯其如此,教育才能不再游离于“人”之外而教育,教育才能重返其生命原点、回归其价值起点,为学生的人生打下基础。这个基础“应该包括学生终身学习的愿望、兴趣和能力。学生终身学习的愿望、兴趣和能力的培养和发展是比他们学到了什么更有意义的。……应该包括发展学生独立地、有尊严地面对世界的品质和能力。这就需要学会质疑与独立思考——不轻信、不肓从、不唯书、不唯上,在理性的基础上来思考别人思考过的问题。这就需要学会有效的自我表达——能够充分地、体面地表达自我。”[5]
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尽管内在生命主体的生命彰显很重要,但仅有内在环境的“积极”是不够的,我们必需同时具有与之相配套的外在“弹性”机制作保证,方能在“成事”中“成人”。
二、教育制度改革、创新与“创新型人才”培养
众所周知,人的活动要以思想观念的更新为前提,人的任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教育制度改革活动也不例外,它要以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变革为前提。如前所述,我们必须首先彰显并弘扬那种“真正的个人主义”的观念,让其在每一个生命个体身上散发出生命的智慧的光芒,教育的活动才能“出新”。这是因为,只有人们观念上更新了,才能以新的眼光、新的视角去审视各种制度,并把对制度的创新作为自己的一种自觉行动。不仅如此,创新性也是人的能动性的最高体现:人之为人,就在于他的活动是一种创新性的“生命实践”活动,这也正是“生命教育”所强调的题中之义。这种创新性的本质表现在制度创新上就是,它不仅要赋予新制度以新规定、新要求、新标准、新组合,而且旨在追求一种高效优化的社会制度。惟其如此,是谓制度创新。
进一步而言,人的创新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或异想天开的自由行为,而是对社会发展中人们的行为,对人、财、物等关系的新的规范,既要克服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制度因素,又要保留发挥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制度因素,从而使制度更具科学性。这种克服和保留,不仅要实现对原有制度的补缺、丰富和完善,更是一种高层次的发展,因而是教育制度发展过程中的质变。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制度创新,即说教育制度主体以新的观念为指导,通过制定新的行为规范,调整主体间的权利平等关系,为实现新的价值目标和理想目标而自主地进行的创新性的活动。可见,“创新型人才”之培养的价值与理想的指向,在为教育制度主体提供明确的方向和目标的同时,也为教育制度的创新带来了新的契机和活力。事实上,制度既是创新的结晶,也是生命主体创新生成的外在“弹性”环境,中国教育制度的创新和变革正是由于其“创新型人才”的呼唤而显得尤为紧迫的。反过来而言,如果我们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不需要变革和创新现有的教育制度机制的话,那么,我们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也根本不会成为一种“问题”。
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性来看,制度创新要遵循两个方面的向度:一个是社会发展的向度;一个是人自身的发展的向度。这两个向度应该而且能够统一于制度建设的实践之中的问题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为什么能统一于制度创新中呢?或者说二者统于制度创新的机理是什么?从人的发展来看,人的发展与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制度是人造的,人和制度不可分离,制度为人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和规范,并影响着人的发展和其才能的实现,尽管在现实世界中,制度并不总是表现为对人的发展的关心和爱护。然而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人的发展、社会发展与制度的发展是相统一的,这也正是现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真正意义所在。与此同时,我们的教育“要帮助学生与他人、自我、自然建立积极的、建设性的关系。”[5]
回到“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问题上来,它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准单向度”或“首向度”能够完成的——恰恰相反,“创新型人格”必须以“人”的发展的“准单向度”或“首向度”为基础的统一才能最终在个体身上凝结并形成个体富有创新活力的生命素质。这是因为,一切创新是以个体的“人”的内在素质的可能和外在机制的可能为依据的。换言之,即一切创新是“真正个人”的彰显和表达,一切创新是个体内在的“创新型人格”的自然流露。
三、“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与个人的人格统合
1.创新型人才与主体意识
说到人才培养,不能不谈到教育;谈到教育,又不能不谈到学习。问题是,就当前的终身教育热潮而言,其所指对的终身学习的概念,正是对教育和学习本义的一种回归和还原,而它所强调的内容,再一次印证了以上的论述。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必须照顾到“人”的这种“主体意识”的独立性和实在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学校教育中我们要积极保护这种“意识到自我”的“主体意识”,而且在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中我们更要大力弘扬这种“元认知”,惟其如此,“人”才能够不断地认识并发现自我的“认识的需要”,从而拥有“发展的追求”,从而使教育中的主体成为自己(而不再被异化)。是时,生命意义上的“个人”方才开始意会到“开放的心态”之所指。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逻辑:没有“主体意识”,就没有“主体人格”,而没有“主体人格”就不会有“创新型人格”。
而承接着这种“开放的心态”的学习观继续往下追问,我们会发现与之对应的一种教育价值观:“最好的教育应该开发人类理解的潜能和宽容的精神”[6]。我们长期以“社会发展”的向度来要求没有“个体”的人进行“学习”或“创新”,事实上,这种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无法超越的禁锢,在这种极度的不自足而又渴求自足的两种力量的相互拉扯之下,个体发现不了内在自我的“积极”所存,发现不了外在环境的“弹性”所在,也就无法应对和进行自我解困,更谈不上积极性适应或创造性适应:常常是一走出学校,就像是换了“另外一套思维”一样,学校教育所积累的没有“消化”掉的个人化的知识,完全不能成为他应对“变局”的智慧营养和行动力量,于是,在这种极度的“智慧饥饿”的状况下,学生只有“背叛”;而对于一种没有“生命实践”追求的教育而言,学校就会变成单纯的“工厂”,只能成批生产很快就过时的劳动力“工具”(而非生命意义上的“人”)——而对于这样一群没有“智慧营养”的生命体而言,大众交流成了一种最有力的媒介,左右着其思想及行为,而许许多多传媒中的暴力、堕落和轻浮猥琐,正在污染而不是在净化人类的精神……可想而知,他们的处境是多么危险,他们的将来会是多么可怕,这样的民族又会是多么令人担忧。
这再一次印证了在当今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教育变革和素质教育兴起的历史缘由和逻辑起点。
2.创新型人格是弹性人格、积极人格的统合
当教育的命题回归到个人的身上时,我们的一切问题都清晰了起来。而面对“变人”的教育的话题,人格似乎成了走入“人”本身的一道瓶颈。这是因为,人格是存在于个体身心系统中的一个动力组织(dynamic organization),乃是决定个体行为与思想特质的所在(Allport,1961)。在西方,柏拉图首先提出了灵魂的三分法:其一是欲望。身体有欲望,如饥、渴和性的需要。其二是激情(或情绪)。如恐惧、爱和愤怒。其三是理性。它专注于内省,它延迟或禁止直接的欲望满足。而弗洛伊德根据柏拉图的灵魂三分法把人格进一步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事实上,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和教育而言,他首先须要直面的问题是——“认识自己”:自身的人格结构及其内在运行机制。黑格尔说:“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一切独立的人格都是首先要自主、自立、自尊、自爱、自律的人格,创新型人格首先要具备这些品质。
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讲,人格是人的内部生理机制、人的外部行为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两股抗争的力量。一股力量是消极的;另一股力量是积极的。如果教育单单只是以满足于帮助人们消除问题人格或人格中所存在的消极方面,那么,教育就是僭越或充替了生理卫生的价值领域;而事实上,教育有其自身独特的视角和立场,那就是人的生长和发展(而不仅仅是保健和平安),使生命个体成为一个有能力去不断发展和实现自我的人。
从社会学的层面看,人又是社会的人。他必须同时明白自身生命的“可能”和“有限”,而要做到处理好这两股力量的“中庸”,需要一种人格上的弹性,即弹性人格。这恰如外在制度环境所要给予的“弹性”所指。这是因为创新型的人格的最大快乐在于最大程度地运用“理性”能力,而绝不是“欲望”和“激情”。美国UCLA教育心理博士陈曼玲(1992.1)认为[7],人格上的“弹性(Resilience)的意义是指:其一,环境虽然艰难,仍有好结果;其二,在威胁之下,仍维持竞争力;其三,能由创伤中恢复过来,涉及个人的软弱、环境压力及保护因素三者间的互动弹性人格的特质:高自尊与自我效能感(Self-esteem and Self-efficacy)。班杜拉也说:“人类的健康与成就需要一种乐观与弹性的自我效能感”。反过来说,教育的理想乃在达成个体不断“学习”和不断成长的目标,学校教育必须超越单纯知识教导的视域,落实“终身学习”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践履“生命实践”的教育使命。
从教育学的视角看,它所关注的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机制及其所形诸的素质成果,只有人的积极性和自主性的发挥,才能使一切外在的影响刺激成为个体生命活动的营养和原料。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认为, “个体的发展主要应归因于他们投身于满意而高兴的活动、保持了乐观主义的心态和以积极的价值观为生活理念,在这过程中,积极人格特质则为其提供稳定的内在动力”[8]。因此,积极人格特质主要是通过对个体的各种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加以激发和强化,当激发和强化使某种现实能力或潜在能力变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工作方式时,积极人格特质也就形成了。不仅如此,人格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中也强调了这样三种积极的人格特质:其一,主观满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也称主观幸福感),既是一种人格特质,也是一种心理体验,指主体主观上对自己已有的生活状态正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生活状态的一种肯定态度[9]。也即是主体在认知上和情感上对现在的自我生活状态及周围环境的内在认同。其二,自我决定性(sefl-determination):自我决定性是指“个体自己对自己的发展能做出某种合适的选择并加以坚持。其三,乐观(optimism):乐观人格特质是指个体对自己的外显行为和周围所存在的客观事物能产生一种积极体验;乐观虽然具有一定的天性成分,但人的本性只为乐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基准线。在西方,Seligman,Abramson,Petersonlg等人强调,乐观主要还是后天形成的一种人格特质,它虽然在不同的人身上存在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但大部分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而形成“习得性乐观”[10]。而一个人一旦形成了乐观人格特质,那他常常就会把生活环境中所面临的困难归因于外在的因素,在任何环境条件下他都会朝好的结果去努力。可见,这在相当的程度上为教育学旨在“变人”的“生命实践”活动提供了一种极富实证意义的心理学解释。
一言以概之,人必须立足自我去“积极”建构“我”世界,而人又是社会的人,他无法超脱于世俗的“你”世界之外,“大隐于世”的哲理需要“弹性”。事实上,一切的创新首先是“我”世界能够与“你”世界构成“相遇”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懈的“我”建构的结果。所以,一种创新型人格,既要以“弹性人格”积极把握和开创适宜其发展的外在生态人文环境,同时需要以“积极人格”保持内在世界的一种安适与积极,如此,教育之“人”才能“思入”和“晋入”其所想要的创新之境界。
收稿日期:2006—1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