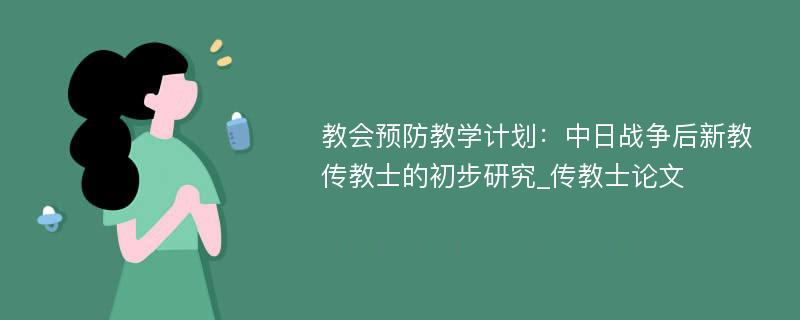
教会防范教案:甲午战后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廷论文,新教论文,甲午论文,传教士论文,战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08)06-0104-08
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加剧的进程中,民教冲突实际起了使危机提速的作用,1895年的四川成都教案和福建古田教案就是最初的信号。不过民教冲突对民教双方来讲往往是两败俱伤,得利者主要是利用传教士的血和生命勒索利权的列强政府。因此,尽管传教士与官方经常处于对立状态,但从利害原则来讲,清政府和传教士都是不愿意看到或卷入冲突而是希望防范和避免冲突的。但这一点尤其是传教士希望避免教案发生在我们研究中基本被忽略,实际上却是真实存在的。1895年在华新教传教士集体策划并实施的直接给皇帝上书行动,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为我们了解传教士和清政府在应对教案危机上的所作所为及晚清政教关系走向提供了线索。
传教士文献显示,传教士非常重视这次上疏。①中文著述中则仅有王树槐在《外人与戊戌变法》中从维新运动角度提到此事,但基本未涉传教士上书主旨。[1]顾长声在给李提摩太写的传记中则称李去北京是“政治投机”,是个人行为,对传教士集体上书清廷未置一词。[2]所以,本文拟缀合中西史料,查考此次上书的缘由以及传教士与清廷高层对教案原因及防范教案上认识的异同,探讨其对晚清政教关系转向的影响,以补清史研究之阙。
一、起因
传教士集体上书发生在公车上疏之后。相比后者的轰动效应,这次上书规模小,影响也小,但它改变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直由外交官代表传教士与朝廷交涉的模式,是官教直接接触的起点。实际上传教士打算直接与清廷接触由来已久,因为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华传教以来,传教士一直面临着一种困境——尽管有列强政府、外交官以至炮舰的支持,但仍必须依赖清的各级政府在传教现场的保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然而从将近半个世纪的教案看,传教士和地方官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彼此抱怨不断。[3]在传教士们看来,地方官员对教案处理不力且有失公平,因此,传教士一直希望清朝中央政府能消除对基督教的疑忌、树立对基督教的正面认识,并使各级地方官员履行职责,保障传教士传教和中国平民信教的权利。
早在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有446名传教士参加的第一次在华基督教差会大会上,传教士们就指出清政府对基督教的敌意是导致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并提到一些官吏也希望充分了解基督教及传教士传教的目的,因此有人提议直接向皇帝上书,“说明基督教差会的性质及它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最后大会成立了李提摩太、林乐知等组成的七人委员会。李、林之外,另外五人是阿什莫尔博士、布劳格特博士、约翰博士、穆尔主教、沃瑞博士。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请愿书,一是表示感谢——“感谢中国政府在过去给予我们的保护”;二是“把对基督教的诬蔑之词呈送官府,指出除非查禁谣传,否则会有严重后果”,“请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禁止谣传,并让通国知道事情真相”;三是“说明我们所信仰和传播的是什么,说明我们所到之处都在教导忠诚、和平、慈善,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福祉,而不是追求别的”。传教士希望这份文件直接提交给皇帝,并通过皇帝下令给各省督抚并县级官员,发布告示,以使文人学士能了解“基督教真理和仁慈的本质以及他们为中国民族最根本利益服务的倾向”。②用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就是“解释基督教会来中国的真正目的,并要求保障宗教自由”。[4]222这个委员会后来拟了一份很长的报告。但清的政治体制中并没有类似欧美的代议机构,没有接受民意表达的常规渠道,传教士直接给朝廷上书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而1890年正好是教案低谷,[5]32因此传教士完成上书报告后,一直没有采取行动。
但1891年在芜湖及整个长江流域,爆发了反对新教传教士的骚乱。传教士们在各种报纸上大量登载对传教士有利的声明,并且强调传教士在赈灾和医药方面所做的种种善事,竭力为教会事业辩护,但仍然感到“我们正处在一个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的边缘”。1892年湖南在籍道员周汉刊播揭贴,伪造公文,鼓吹反教,在社会造成很大影响。[5]551-5541893年6月两名瑞典传教士在湖北麻城宋埠被“共殴毙命”,引起传教士的恐慌。[4]223[5]565-5661893年9月,李提摩太专门去汉口与杨格非等讨论上书事宜。不过随后的1894年又是重大教案的低谷,此事再度被搁置。[5]38甲午对日作战失利,民众把怒火转移到传教士身上。[6]1895年6月四川华阳爆发打毁教堂案,传教士纷纷走避。随后8月1日爆发福建古田教案,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史荦伯夫妇等11人被杀,其中包括数名儿童,这使传教士们大为惊慌。李提摩太写信给上书委员会的成员,敦促他们立即赴北京同最高当局接触。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并赋李提摩太以全权,赴北京与住在当地的上书委员会成员惠志道和刘海澜协商给清廷上书事宜。李提摩太离开上海之前,参照1890年请愿书,拟了一份短稿,得到在沪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等人的赞同。李提摩太还征集了英国伦敦会、内地会、美国监理会、美国公理会、美国长老会等差会的20位有影响的传教士的签名,使上书有了英美在华差会的代表性。征得签名后李提摩太随即赶赴北京上书。[7]137在请愿书上签名的20位传教士是:慕维廉、杨格非、惠志道、裴雅谷、仕文、耶十谟、林乐知、李修善、刘海澜、娄士、包尔腾、金护迩、赫斐秋、谢卫楼、史嘉乐、戴德生、狄考文、文书田、李提摩太、李佳白。[4]223
二、游说与上疏
1895年9月李提摩太抵京,发现起草1890年给皇帝请愿书的传教士布劳格特回国休假去了。传教士们商量后同意把李提摩太起草的那份文字少的报告呈交总理衙门,布劳格特起草的那份篇幅长的请愿书(装订成书籍样)同时呈送。因为两份文书都要由传教士的中国助手润饰和誊抄,所以一时来不及呈报。而此时恰是康有为及各省举子大规模上书被都察院所拒之后,李提摩太可能认为此时呈报结果难料,决定利用这段时间接近和游说总理衙门大臣,为上书探路和铺路。
当时总理衙门有恭亲王、翁同龢、李鸿藻、孙家鼐、张荫桓等八位大臣。李提摩太决定先拜访李鸿章。早在1876年李鸿章签烟台条约期间,部下染痢疾,李提摩太曾经送奎宁等药物给李鸿章。1880年9月李提摩太经过天津时,曾受邀与李鸿章见过一面。1887年李提摩太与李鸿章在烟台再次见面时讨论过改革中国教育。[4]188两人有数面之交。9月17日,李提摩太拜访李鸿章,原想请李鸿章写信,请李鸿章引荐他到恭亲王那里去,但在与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白梯克(美国人)谈话时,白梯克认为由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引荐更合适。白还建议他拜访翁,并建议李提摩太把过去与曾国荃、张之洞及其他高官来往的经历告诉翁同龢。9月23日下午李提摩太再次拜访李鸿章。李鸿章告诉李提摩太清廷“现在的”掌权者是翁同龢,建议李提摩太给翁同龢写一封信,说明自己已经在中国待了多年,曾经参加过赈济灾荒和民众启蒙的工作,因而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并且告以有要事求见。9月26日,白梯克邀请李提摩太在塔利饭店用餐,顺便把李提摩太介绍给席间碰到的10位翰林。9月27日,李提摩太拿着写给翁同龢的信草稿,又拜访李鸿章,并请他帮助修改信件。李鸿章与李提摩太谈了话,并就应该如何与翁同龢交谈及如何在中国官场周旋,向李提摩太提了一些建议。
不过,10月12日李提摩太先去见了李鸿章的老乡、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谈了一个多小时。李提摩太认为“他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李提摩太还参与了强学会活动。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说:“时英人李提摩太亦来会,中国士夫与西人通,自此会始也。”[8]李的种种改革议论可能给康印象甚佳。10月17日康有为到北京伦敦会教堂拜访李提摩太,后来还将自己的著作赠送李氏。[4]234可见李氏的社交活动相当成功。
直到10月26日,按照翁同龢的安排,李提摩太才在总理衙门见到翁同龢。翁建议去“一个更加秘密的地方会谈”,把李提摩太领到同文馆的一间房子。在场的,翁、李之外,只有汪鸣銮一人。汪是翁的得力助手,也是总理衙门大臣之一。李提摩太给翁同龢带去了《海国图志》和《皇朝经世文续编》,把两书当做文人学士反对基督教的证据。李认为这两种书都带有对基督徒的最荒谬的敌意。《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说,基督徒把华人的眼睛挖出来,配以铅粉,炼制白银,外国传教士因此而致富。《皇朝经世文续编》则宣称,传教士制作迷幻药,使妇女发狂。李提摩太向翁同龢指出,这种种诽谤的目的在于制造反对外国人的骚乱。李提摩太还说左宗棠、王文韶等大官都为这些著作写了序言,这就更加扩大了这些书的影响。李提摩太说:“当普通人读到这些诽谤——包含在通俗性的印刷品中、带有中国高官签名认可的对基督徒的诽谤——时,我们不敢想象他们会不受到蛊惑而发起暴动,屠杀基督教徒。”据李提摩太记录,当时翁同龢说李提摩太“在中国住的太久了!”“他被我的观点所征服了。”接着,李提摩太又历数中国一千年来在宗教问题上所遇到的困扰——先是佛教徒迫害道教徒,接着道教徒又迫害佛教徒,自相攻伐,国无宁日。而宗教自由一旦得到各方认可,整个国家的和平便指日可待。李提摩太对翁同龢说:“基督教徒们现在向政府所请求的不过是不被干涉而已。”据李提摩太称,在听完这番话后,翁同龢当即表示,“如果就这些的话”,“我看不难照办”。[4]227-228《翁同龢日记》也提到了10月26日在总署见了李提摩太,“未初晤英教士李提摩太,豪杰也,说客也。”看来翁对李提摩太印象很好。李提摩太在谈论基督教问题时还谈到中国改革问题,所以甲午新败后倾向改革的翁同龢请李提摩太写个折子,谈谈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中国最急需进行的改革是什么。翁同龢还在日记里大段记录了李提摩太的话。[9]2843
李提摩太这些外围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见到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恭亲王奕訢。老于官场的李鸿章并没有给李提摩太写推荐信,只是修改了李提摩太自己写给恭亲王的信。在10月30日,恭亲王和其他七位大臣终于在总理衙门接见了惠志道、李提摩太。据李提摩太后来说,恭亲王是他见过的最“蛮横”的人,说“恭亲王让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一把椅子上,以此来表示对我的轻视”。谈话一开始,“恭亲王就提到了教民,称他们是中国的垃圾”;恭亲王“理所当然地”认为:“教民们所遭遇的所有麻烦,都是他们卑鄙愚蠢的行为所致。”李提摩太向恭亲王请求允许他表达一下基督徒的看法,恭王表示他表示愿意聆听。李提摩太陈述道:“刚才提到的对基督徒的指控实属莫须有,以这种指控为依据的中国政府的做法是不公平的。我在中国的不同省份生活了多年,亲眼目睹了教徒所做的诸多善行,因而了解事实的真相。而您,住在北京,只能相信口耳言传,得到的只是虚假信息。人们都对我说,如果王爷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您的正义感会使基督徒所遭受的苦难最终结束。我来到这里,并不是以个人身份,也不是作为代表一个国家的使者,而是代表全世界所有基督教国家的所有基督徒,来请您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所有针对基督徒的未被证实的指控。如果我们真的有罪,我们不想免除正义的惩罚;如果我们是无辜的,我相信王爷会让我们得到正义,得到中国的其它宗教所享有的同样的自由。”奕訢当场并没有什么表示。据李氏记载,奕訢离开后总理衙门大臣之一的李鸿藻就走过来,“感谢我这么直率地跟王爷谈话,并对我说:‘在我们中间,没有谁胆敢像你这样反驳王爷,但既然你已经提出了你的请求,态度又是如此恭敬,他是不会生气的。你这次来会有成果的。’”[4]229翁同龢日记中的记载是10月31日“李提摩太先来见恭邸”。[9]2845
见过奕訢后,惠志道和李提摩太紧接着拜访英、美、德三国的驻中国公使,向他们解释传教士上书总理衙门的目的,寻求公使们的支持。德国公使因没有德国传教士要求他们采取行动,所以拒绝与李等合作。但美国公使田贝一向是传教士的热心支持者,他于11月12日致函总理衙门,说明传教士代表此行的目的并请求接见,还按照中国官场的规矩,称“李提摩太系英国上议院议员,秩中国一品。惠志道系美国人,美本民主之国,教士品虽不同,其尊则一,皆得觐见各国君主,及与各大臣往来”。11月14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亲自陪同两位传教士正式到总理衙门上书。传教士们当场向大臣们再次陈述意见,总理衙门收下了传教士的两份文书,并允诺上奏光绪皇帝。传教士们酝酿五年之久的上书计划至此终于实现,终于使清廷高层直接听到传教士们为基督教、为自己,特别是为历来遭官府厌恶、受官府鄙视的中国基督徒所作的辩护。③
三、上疏内容和清廷反应
传教士上书有中英文两种文本。英文本登在《教务杂志》上,中文本《陈管见以息教案疏》(以下简称《教案疏》)刊于1896年7月的《万国公报》。上书开宗明义:“愚人诬陷教民,扰害教堂,隐忧方大。谨陈管见,冀杜乱萌,而敦睦谊”,恭折请求“二圣”明鉴。
《教案疏》进一步解释上书的原因。《教案疏》说,世界万国的政教关系是“相生”“相成”的,“朝廷苟为教会设立妥善章程、民间断无龃龉之事”,反之必然“猜嫌疑忌、纷然并起,必致别致事端”。基督教从唐宋元明都是“准令任便传教,与他教不分轩轾”。在“圣朝”更得到“圣祖仁皇帝”“一视同仁,尤加优待”,只是在雍正朝“禁止传教”。在道光末年“立约通商”后传教重新开始。但天津教案、长江教案,特别是最近的四川成都教案和福建古田教案,令传教士“扼腕惊心”。虽然1890年上谕和奏章中都说有“不逞之徒,捏造无稽滥语,籍端滋事”,但在实际执行中既未“严行办理”,也没有严禁“谤书”。这怎么能平息“乱萌”呢?因此,他们不得不“仿照西例,联名敬乞皇上慈恩,饬下总理衙门会同教师,速议保护教会章程”。《教案疏》特别指出,最近教案的根源是新刻《皇朝经世文续编》和《海国图志》等书有“诋谤教会之语,诬陷教民,累牍连篇”。这些书有大官作序,而且广泛发行,读书人看了怎么能不起而攻击教会教民呢?
那么,《海国图志》等书说的是不是事实呢?《教案疏》首先扼要介绍了《新约全书》记救主耶稣与亲灸门徒之遗训:“其大旨略云:上帝君临万国,父爱万民,覆帱之下,谊属同胞,必以讲求忠孝,为立身之大端。又必思效法救主,仰体上帝不忍斯民陷于罪恶苦难之心。愿万国万民,化争为让,化恶为善,化愚为智,化贫为富,不独享承平于光天化日之下,更沐神贶于永生不灭之中。”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因此设立教会,在道德方面,每七日“共聚一堂,阐扬天道,使人知仰赖神贶,以克私念”;在慈善方面,“则有施医养老育婴之事”;在教育方面,“则有书院义塾等类”。至于“教会规条,尤属严明,凡酗酒谎诈赌博淫恶之徒,一概不准入会”;“间有匪人混迹,……既知必斥。”
《教案疏》举例说明凡信教之国“养民、新民、安民诸大政,固皆赖救世教以日增而月盛也”。这些国家的“名臣硕彦”都是“热心乐道人”。传教活动还给非洲、太平洋岛国、印度、日本带来了进步。在中国,传教士“已经将西国经史并格致机器等书译成华文,又将中国经史译成西文。更设书院学塾,教华人以西国有益之学。而四书五经仍不偏废。通商各埠,及内地所设各医院,皆以治病至精之法治之。遇有灾荒,助赈不遗余力”。有些教士“因放赈而捐躯,仍有起而继之者”。另外一些传教士则“查水旱各灾之缘起,并贫弱之根由,拟有补救预防之法,足令各省每岁增收数千万金。”如果中国“早采其言,不致如今日受困之甚”。结果是基督教行于何国则何国兴,不行于何国则何国衰。“各国史册,班班可考。”
关于中国人常常怀疑传教活动的政治性,《教案疏》专门说明传教活动的非政治性。传教士来华“非奉本国帝王命令,乃以其乐善不倦之故”,因此得到本国官民上下“尊重而爱护之”。传教士“常恭祝皇上,以及官民,咸有一德,克享天心”,“聿臻郅治”,表达传教士对中国政府的忠诚。如果像《海国图志》、《皇朝经世文续编》说的那样,基督教怎能得到其他大国的尊信呢?传教士还声明,他们的活动不怕人考查,“特恐人之不考察耳”。传教士们模仿清廷大臣奏疏的口气写道:“臣等以为,在京大臣或外省督抚暨通国绅士,如有疑义,不妨循中国旧制及各国常例,准令中国官民人等与教士往来常见,然后乃无捍格之虞,而凡百皆有益无损矣”,否则“隔阂不通,久必酿成教案”;而到那时“外国不得不向中国理论”。
最后传教士提出三点请求:一是删除《海国图志》、《经世文续编》中谤教之文;二是传教士为中国办理有益之事不得被视为异端,而且“无论官民,如愿入教,悉听其便,万不可迫之使之背教规,皆当实准奉教,无容歧视也”;三是传教士既为中国求益而来,“应令各处官绅采访各国教养善法,凡有益于民者,不分中外,务期和衷商办”。传教士还着重说明,以前朝廷确实出示保护教民,但社会上流言认为这非朝廷本意,仅是西国要求所致,所以“教案仍见继起”。“臣等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天恩,俯准以上所求三事”,命令各省官员认真办理,保护教民,“教案亦可永息矣”。[7]132-137
传教士费尽心机,这篇上疏用历史与现实、教义与传教士的行为及其他中西实例论证了基督教是好的宗教,传教对中国有益,清廷应该禁止谤教文献的流行,应该真正实行宗教自由政策,以“永息教案”。那么清廷是如何评估这份文书和传教士的上述行动呢?
1895年11月30日,也就是在传教士上书后半月,恭亲王奕訢领衔给光绪写了“奏为代递英美耶稣教士条陈中国教务折”,实际上是对传教士上书的答复。可能出乎传教士意外的是,这个奏折除了重复当年弛禁天主教时就说过的“劝人为善”的说辞外,传教士大谈特谈的基督教本身的内容及对国家社会有益之处一字不提。奕訢首先提出的是,传教载在条约,只是当日只载明“安分传教、习教之人等一体矜恤保护,并未议及不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应如何科定罪名”,所以就有了“教民倚教士为护符,教士纵教民为奸恶,民教相仇,辗转报复,各省教堂之案层见叠出,至近年而益甚”。对于传教士的“目击时艰,情殷挽救”,他表示“其志可嘉”,但马上指出传教士的条陈“只论传教之益,不计传教之弊,殊欠周密”。恭亲王对付传教士所提要求的办法就是乘传教士“该意就商之际,为因势利导之方”。
那么怎么应对传教士的三条请求呢?关于传教士要求“各种诬蔑教会之书,请一律划除一条”,奏折认为,“民间匿名刊刻之书,造言生事,本干例禁,即《海国图志》、《经世文续编》等类,亦属私家记载,其中谤教之文不难概予销毁”,但奏折又说“特以止谤,莫如自修”,关于挖眼剖心的说法,朝廷“多方谕禁,不在止息”。现在传教士说不怕人考查,那今后“凡有教堂雇佣华工、或养育民间幼孩,均须先向地方官报名注册,以备稽考”。如有辞工病故,也报明地方官,“如此则群疑顿释,谤者不期禁而自禁矣”。
关于传教士要求“中国人民如愿入教,悉听其便,不可逼之,使背教规一条”,奏折声称,传教写进条约,“准其传习,亦执(何)从而迫之背教”,根本就是没有的事。然后奏折不加区别地痛骂“惟传教者,既兼容并包,奉教者即不无倚势怙恶,种种妄为,擢发难数”。如今传教士折内既称“凡酗酒谎诈赌博淫恶之徒,一概不准入会,间有匪人混迹,经久必斥”,那“嗣后华民入教,亦须开列姓名籍贯,报明地方官查明从前并无案犯之人,方准注册教籍”。同时又强调说清政府对民教争端一贯是“务持其平”。
关于传教士所说的“为中国求益而来,应令各官绅采访各国教养善法和衷商办一条”,奏折称“中国现正讲求制器、练兵、开矿、炼铁诸大政,西士之有技艺者,恒不惜重价敦聘,况教士既有善法,岂有不望相助之理?”但奏折认为传教士“良莠不齐,往往袒护教民、干预公事,挟诈侵权、无所不为”。传教士既然说“有如此情弊,即当公议驱之回国”,那“嗣后即照该教士所称办理”,而“其有安分传教者,地方官绅不妨与之往来,以礼优待”。
因此,在恭亲王和总理衙门大臣看来,这三条都不难办到。恭亲王奏折中还说:“近来该教中颇喜读孔孟之书,其颖秀者,亦能略窥大义,著书立说。”“如此则崇正黜邪,中西不期和而自和矣。”不过,奕訢等对这三条都有自己的看法。尤其奕訢本人早在天津教案后就与文祥提出过“传教士章程”,但被各国拒绝。因此他打算利用这个机会继续与传教士协商“重订章程,颁行各省”。因为是传教士主动提出,所以各国公使“当无异说”。“耶稣教既愿重订,天主教当无异说。”至于传教士请求“带领引见”向皇帝面递条陈事,则被否定。光绪当天的朱批是“该衙门酌复办理”。[5]620-622
将奕訢的奏折和光绪朱批放在一起看,总理衙门应该“酌复”此事,有进一步协商和解决教案问题的意思,但实际上后来并未有进一步的行动。传教士的期待并未实现。据李提摩太在上书当场的感觉是总理衙门多数大臣“都倾向于答应我们的要求”。[4]230李事后记载说:“几天以后,皇上谕示总理衙门,要他们与传教士协商,直到问题妥善解决。12月初,两位总理衙门大臣向我们保证,很快就会发布政令,同意我们在请愿书中提出的要求。”这两位大臣,一位可能是翁同龢,还有一位是李提摩太提到的是汪鸣銮。亲自上书的刘海澜、李提摩太当时非常乐观。他们随即在报告中写道:“我们怀着对上帝的感激和愉快的心情向大家报告: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些问题的汉人大臣们都是非常理性的,没有人比翁同龢再如此。他们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所请求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准备‘让教民享有自由’,如果事情这样进行下去,我们的麻烦也立刻就此结束。”④但两位大臣提到的“政令”最终没有发布。李提摩太晚年写的回忆录的解释是:“这时出现了两件事,改变了解决问题的进程。汪鸣銮,曾经是总理衙门中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突然退缩了,这削弱了支持请愿书的那一派的力量。”另一个因素据李说李鸿章告诉他:“法国公使出人意料地反对皇帝同意任何由传教士提出的要求,因为这涉及到了传教士是否有权直接与中国政府交涉的问题。”[4]231
事情真相到底如何?事实上李提摩太等在京上书之际,清廷帝党与后党的分歧已经初露端倪。李说的汪鸣銮的退缩,实际是1895年12月3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汪鸣銮和长麟同时被慈禧太后以“信口妄言,迹近离间”的罪名“革职永不叙用”。[9]2856这使得上书的要求失去一个有力的支持者。但把清廷对此无所作为都归之于汪的被解职是夸大了汪的作用。因为据李提摩太自认支持自己的翁同龢,其地位远比汪重要,也没有继续采取行动。在汪鸣銮被免职的当天李去拜访了张荫桓,不过张看来并没有对此表示支持。[4]239因此,李提摩太毕竟是外国人,他认为总理衙门大臣都对其表示同情实际是一种误读。因为从清廷方面看,传教士所对基督教教义的说明以及列举的对中国的益处的说明,在奕訢等奏折中被指责为“只论传教之益,不计传教之弊,殊欠周密”。[5]620双方看法的分歧太多。其实传教士说的第一条,中国官员也有相同的看法。早在1891年9月时任驻英法德公使的薛福成给朝廷上的“处理教案治本治标之计折”中,就指出:“耶稣之说,亦以仁慈为宗旨。近者禁黑奴有会、禁鸦片有会,彼以虐人之事、害人之物尚欲禁之,岂有残酷至挖眼剖心而欧洲各国习不为怪者?即彼之精于化学医学者,亦谓无心眼入药之理。”薛还认为:“斯必灼知旧说之讹传,然后此案乃可下手,否则在事大小官员,先怀疑虑,……将何以晓彼愚民?将何以禁彼匪党?”[5]490-491薛是有出国经历的人,对基督教有较多的了解,眼界较宽,而且头脑清醒,所以对基督教的介绍和评价就比较客观和公正;而清廷中枢人物只有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创巨痛深的教训后才有这种认识。至于第二条关于教民权利,刘海澜和李提摩太感觉只是满人“看上去下了决心认为教民全是坏蛋,对他们来说,与任何与教民有关的人谈话是最痛苦的事情”。⑤其实汉族官僚也是如此。翁同龢记载了张荫桓曾驳斥李提摩太的关于教民的看法,而李“不甚服”。[9]2863翁1898年9月26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在致谭钟麟的信中谈到广东“惠潮械斗”的一方“此辈多教民,教民巨患,岂特滨海哉!”[10]翁本人对教民的偏见也是牢不可破。
但李提摩太仍不死心,还和刘海澜去一起去英美驻华公使馆活动,“希望各国公使一致行动,争取让中国政府同意请愿书的内容,并且请他们在请愿书的基础上再加上一条要求:不论什么时候,凡给予罗马天主教徒的特权,应当同时推及基督教徒”。[4]231但最后公使没有什么跟进的行动,传教士上书之事也就到此为止。
四、翁李交谊与清廷政策走向
不过,传教士上书并非一无所获,他们能进入清廷决策机构与王公大臣等坐而论道本身就是政教关系的积极变化。他们给政府官员留下了比较正面的印象,尤其李提摩太与翁同龢发展出了一段交情。李提摩太上完书并没有离开北京,而是继续在京城活动。翁同龢以总理大臣之尊数次与李会面,日记中流露出对李相当欣赏。1895年12月13日,“见李提摩太,并刘海澜。海澜者,会文书院总办也,在京廿余年,颇揽借账事。余与之谈道,次及政事,旋及教案。余以二端要之曰,教民何等人当斥,教士何等事应退,令彼拟条约共商。……李读书明理人也”。[9]28581996年1月2日,“未正见李提摩太、刘海兰,民教相安事”。[9]28632月14日翁同龢“拜客数家”,其中有李提摩太。[9]28752月24日“未刻送英教士李提摩太,长谈。伊言须富民、富官、归于学人要通各国政事。其言切挚,赠以食物八盒,绸三端而别,留一照像赠余”。[9]2878李提摩太也记下了这天的事:“2月24日,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翁同龢派人把他的名片送到我在伦敦会的住处。按中国的风俗,这是非常正式的问候。我回赠他我的名片,并感谢他的厚意。没想到,他就在外面,有重要的事情要同我商量。这是空前的举动,此前没有一位中国的总理大臣到传教士的住处拜访过。我们就宗教宽容和政治改革问题谈了一个小时。首先,他为朝廷没有发布批准传教士请愿书的政令向我表示歉意,说他的上司不想支持他。我请求不要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区别对待,并强调倘若能做到这一点,一切麻烦都将不复存在。他谈的第二件事是问我能不能帮助强学会,因为政府打算恢复它的合法地位。对此,我的答复是,如果强学会不能对中国做一些切实有用的事情,我不想跟它发生任何联系。”翁同龢还派人送李四匹丝绸和八盒点心。李说:“这些,加上孙家鼐送我的一对花瓶,我倍加珍惜,因为它们是友情的标志。”[4]231事实上,李提摩太后来被聘为改革维新的洋顾问与翁同龢等对他的熟悉是有关系的。
其实除了这种私人情谊之外,传教士集体上书和李提摩太、刘海澜的大力游说也在悄悄地发生影响。翁同龢的未刊资料中记载了1896年2月19日(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七)翁对传教士上书的建设性意见。翁摘录的上书要点是,“中西历代安置各教之策:一各教相安则兴,如英、日本;一各教不安则危,如罗马、土耳其,俄亦然。”翁的旁批认为解决教案问题除上书中的三条外,应该有“教士犯法即令回国;中官若不保护教民立时革职;设中西合办教案公署”。⑥但翁的这些建议并未实行,也未写进日记中,可见当时是有阻力和压力的。但在1898年6月(光绪二十二年五月)的上谕称“凡有教堂州县,务当谆饬地方官,实力保护。平日如有教士谒见,不得有意拒绝,使彼此诚信相孚。从教之人,自不致藉端生事。一面开导百姓,毋以薄物细故,轻启衅端。即使事出仓卒,该管官吏,果能持平办理,亦何难消患未萌”。⑦在这里看得出传教士集体上书对朝廷政策的些微影响,但这种影响依然有限。晚清官员中的许多人即使本身不仇教,但官场遇事因循拖沓,处置民教冲突不及时、不彻底,常常使民事变成刑事、小事酿成大事。此外,即使新教传教士主张克制,天主教方面也未采取与新教传教士一致的行动,而官教防范教案的真正合作更是在义和团运动的强力震撼之后。
收稿日期:2008-02-08
注释:
①见The Chinese Recorder,February,March,April;《万国公报》第九十册(光绪二十二年六月)。
②The Chinese Recorder,February,1896年第62-63页。
③The Chinese Recorder,February,1896年第62页。
④The Chinese Recorder,February,1896年。
⑤The Chinese Recorder,February,1896年。
⑥翁同龢未刊资料:《正月初七李提摩太信》,翁万戈先生提供。转引自纪振奇、谢俊美《翁同龢与近人教案及在华传教士的交往》,《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⑦德宗景皇帝實録(六)/卷四百二十/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下。
标签:传教士论文; 翁同龢论文; 李鸿章论文; 总理衙门论文; 和硕恭亲王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清朝论文; 甲午年论文; 海国图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