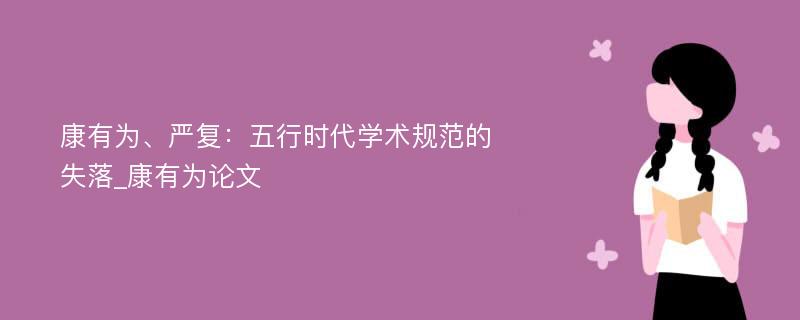
康有为与严复:戊戌时代学术规范的逸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有为论文,学术论文,时代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戊戌时代的中国学界与思想界,康有为与严复是两位轰动一时的风云人物。(注:日·稻叶君山在《清代全史》下卷(中华书局本,第4章第30页)中这样写道:“此时(指清革新时代)重要之著作,如康有为之孔教论,严复所译之《天演论》,当首屈一指。自曾国藩时代所创始之译书事业,虽有化学、物理、法律各种类,然不足以唤起当时之人心。至此二书出而思想界一变。”)康有为是戊戌时代今文公羊学之主将,严复则为迻译西方哲理之开山,治学各有所异,然而两人不仅在当时的影响同为最深且巨,而且在其他某些方面亦表现出不少惊人的相似之处。
康、严同是戊戌时代思想最为敏锐的学者。对于戊戌时代特有的症候,对于这一时代成为数千年历史之根本转捩,两人有着同样超乎常人的特殊警觉。正像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惊呼中国正面临“四千年之变局”(注:参见《康有为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335页。)那样,严复也预告了这一数千年未遇的“世变之亟”的到来:“呜呼!观今日之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本文所要讨论的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是,康有为与严复又同是戊戌时代以学术求“经世致用”的两位先锋,且两人都在以学术求致用的祈向中,对以求“真”为指归的学术规范有所逸越。
戊戌时代的学术是开启20世纪现代中国学术之枢纽。作为19、20世纪之会合,从实质上看,戊戌时代与20世纪在学术与思想上更为接近,共成一个脉络系统。探析康、严逸失学术规范的表现与原因,旨在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经常同样出现的学术的求用与求真的矛盾、对这一矛盾与学术规范之阙失的某种内在的关联,能够进一步引发日后更为深入的思考。
一
甲午之役后,康有为叱咤于政界,为倡言变法维新,四年内共七次上书,终于以策士出任,在戊戌变法中领衔主角。
康有为的学术活动,尤其是他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不但与他的公车上书、策动变法的政治行动同样震动天下,而且两者息息相关,融成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他实在是清末经世致用学术思潮最为突出的代表。
康有为的学术立场与学术旨趣十分鲜明,就是通经致用。年轻时,他便对宋明儒空言性理、清儒终生埋首考据十分不满,将之均斥为“无用之学”:“宋、明国朝文章大家巨名,探其实际,皆空疏无有”;“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注:参见康有为:《我史(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四年戊寅,二十一岁”条下,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820页。)字里行间,他以是否“有用”作为学术褒贬的准绳,已是十分清楚。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给弟子梁启超等人讲学时,就将“务通变宜民”的“经世之学”定为学术宗旨,并标举公羊学的素王改制为旗帜:“六艺之学,皆以致用”;“孔子经世之学,在于《春秋》。《春秋》改制之义,著于《公》、《谷》”(注: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8页。)。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公羊学与现实政制关系最密,而孔子学说如夏葛冬裘,是“随时救民之言”。他始终坚持“致用”的标尺,以此衡量下来,三代以后只有西汉经学“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谏,以洪范说灾异,皆实可施行”、“近于经世者也”(注: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页。),此后经学变异,“相率于无用”;尤其是清儒治经只注重音韻训诂,“学者尽数十寒暑,疲力于此,尚无一心得。所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也”(注: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7页。),以此求道,何异于“磨砖而欲作镜,蒸沙而欲成饭”(注: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页。)。况且在他看来,清儒所治的古文经早已被西汉刘歆所遍伪篡乱。所以,康有为一方面自创学派,定下学规,在治学方法上吐弃汉学宋学,而以公羊学微言大义法,明“古圣贤创法立制之精义”;另一方面,他制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旨在把汉以后两千年之经学宣判为“伪经”,从而证明以今文公羊学进行学术变革的必要,并进而创造出孔子托古改制的素王形象,为自己的维新变法寻求精神上的强大支撑。
粗看起来,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以下简称“两考”)是在“办天下古今之案”,辨今古文经之真伪与意义。其实,康有为决不是为经学而治经案。这“两考”的主题正是由他经世致用的立场所决定、依照以经术文饰政论这一求用致向而精心构筑起来的。
“两考”的总体思路是:1.将六经证明为孔子所作,将《春秋》阐发为孔子素王改制之说;2.将秦朝焚书考辨成未尝殃及儒术,六经因而从来无所亡缺;3.至于从孔壁中发现的古文经,乃是西汉的刘歆为了辅助王莽篡汉国,事先赝造古文、并进而伪窜群经而成;4.由此揭明刘歆伪造古文经是为了废公羊学、湮没孔子改制之真义,从而造成了两千年经学习非成是,丹黄乱色,甘辛变味,真伪不明。就这样,康有为计划以《新学伪经考》破古文经之伪,以《孔子改制考》创今文派改制之大义,一破一立,相呼相应,旨在寻端释绪,肃清旧案,进而烘托出孔子托古改制以创大同之说的“万世师”与“大地教主”形象。
然而,正是由于康有为将学术定为经世的工具,将致用视为学术的目的与褒贬的依据,这一致向导致了他的学术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范现象。
首先,康有为的“两考”的上述四个主题,并不是他从大量史实中抉微爬梳而证出的结论,而是因他以布衣倡导变法维新,深感事大骇人,恐遭遇“非圣无法”之罪名,迫切需要掩蔽于孔子素王改制大旗之下。从这一求用的实际需要出发,他的“两考”结论早已成竹在胸,他早在办案之前便已定案,即将孔子改制作为断案之秤星:“天下古今之案,奉孔子为律例,若不通孔子之律例,何以办案?若能通之,则诸子廿四史一切群书皆案情也。……一日抱案而不知律,则无星之秤尺,无为断案之地”(注: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页。)。他从廖平、刘逢禄、魏源、邵懿辰等人论说部分古文经有刘歆篡动迹象中受到启发,集其大成,先行敲定刘歆罪名(并罪加几等),再设计制作了上述一套判案思路。他曾这样坦作夫子自道:“仆之忽能辨古今者,非仆才过于古人,亦非仆能为新奇也,亦以生于道、咸之后,读刘、陈、魏、邵诸儒书,因而推阐之。”(注:《康子内外篇》(外六种),中华书局1988年8月版,第166页。)至于对孔子改制的考证,他也是同样先设计好主题与证词。他曾这样教诲康门弟子:“提出孔子改制为主,字字句句以此求之,自有悟彻之日。若于孔子微言大义有所通入,则把柄在手,天下古今群书皆可破矣。岂非其道至约。其功至宏乎?”(注:《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30-31页。)这两段话,颇为真切地透露了康有为名为考证然而先入为主,颠倒考证学先有事实后有结论之程序的意向。
从学术流变来看,康有为的“两考”力求主题突出而且意义重大,这固然可视为是对清儒治经碎义逃难的一种反拨。然而,他的考证以自己太强的主观先期介入、先行预设,从而置清儒考证重证据在先的必要规范于悍然不顾。
上述这两段自述所概括的精神与方法,在学术史上颇有点类似于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只不过康有为的假设比起胡适来更为大胆、离谱、主题重要,而求证则逊于其谨慎;康有为的通经致用与胡适的实用主义也颇为接近;而且正像胡适曾将历史比作一位百依百顺任人打扮的听话女孩一样,康有为也同样地“视一切历史为刍狗”(注:《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卷,第61页。)。这里似乎有一种学术史上的困惑:求实用的倾向倘若过于强烈、以至被崇尚为立说之依据的话,学术上的失真是否便自然会相随而至?
康有为在学术规范上的第二种逸犯,是他的“两考”诸主题不仅是先于考辨而立,而且几乎全都是凭胸臆为断的虚构;为了使这些虚构得以成立,康有为不惜曲解一系列史实,致使《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在学术上出现了种种不可思议的问题。如,康有为不顾刘歆主持校定宫廷藏书之职为时仅数月,指控刘歆在此短短期间不但从伪作《左传》开始,株连扩大,遍伪《乐经》、《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周官》、《费文易》、《尔雅》等等群经,甚而还伪作《汉书》,增窜《史记》、《楚辞》数十条;为了辅证此论,康有为甚至捏造证据,指探刘歆伪造古文,私铸钟鼎彝器埋藏于地下。诸如此类违悖常理与逻辑的诡谲之论,几如天方夜谭,不仅被章太炎斥为怪迂之说,连康门亲炙弟子梁启超也认为“于事理之万不可通”(注: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70页。),然而却在“凡古文经均刘歆一人伪篡”的预设前提之下递相出现,制造出被朱一新认为是“凿空武断,使古人衔冤地下”的冤假错案。又如,为了助证“孔壁既虚、古文自赝”的逻辑需要,康有为蔑视史实,发明出“秦焚六经未尝亡缺”的论断,不惜为秦火翻案。为了定《春秋》是孔子微言大义的改制之作,康有为称“文字不过其符号,如电报之密码,如乐谱之音符,非口授不能明”(注: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71页。);又如将孔子学说牵强附会成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院、选举、民主等同出一辙。凡此种种“不轨于典籍”而驰聘的议论,在学术上不仅被章太炎目为“大言欺世”的“恣肆”之论,即使是梁启超亦不得不批评其师“枝词强辩”、“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注: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70页。)。令人深思的是,在康有为身上出现的种种这些“逆乎常纬”的失范,深究其背后的动因,固然一方面是因其主观创作欲太强的个性所致,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实在是由于他的经世之心过于浓烈:因为他必须得到这些结论。他必得借助这些惊世骇论,才能扬起“公羊”之帆,以“驶自己的维新变法之舟”。
康有为在学术规范方面的第三种逸失,是他虽然擎举公羊今文学之旗,却不守今文学之家法。今文经学的治学法如康有为自己所概括的,是“微言大义”法,及以经术直接治理国家。然而在“两考”中,康有为使用的却是自己痛诋“无用”的清儒考辨法。这种杂糅古今的作法在壁垒森严、门户水火的今古文之争中自然招来非议。章太炎评论康有为是“立说不纯”,自乱家法,并因此告诫自己的弟子:“以经治经,则宜守家法,不可自乱途辙”(注:转引自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二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而当时的保守势力指责康有为“杂乱抄撮”,则更多地是对他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那一套糅进孔子学说的做法十分不满,惊呼康是“阳尊孔子,阴主耶稣”;“其貌则孔,其心则夷”(注:《翼教丛编》卷1,第11页。)。
康有为在今文家规方面的逸犯,从一定角度看,其实倒是他能兼采众说、不拘一家的表现,而这也和他的经世求用的治学意向有相当联系。他正是在早年途径香港与上海,目睹欧风美雨东渐的新气象、并接触了一些由制造局译出的西洋科学书而自以为得“枕中鸿秘”后,思想才为之初变的。他的经世求用的志愿也因而一开始就带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流行色,并在甲午之后,更有所突进,“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他之所以在方法上杂糅古今,则可能是因为当时古文经派仍据正统派位置,考证法尚风行于天下而未衰,要在学界崛起,假途于考证似亦不失为一条能扩大影响之捷径。总之,只要能从中考出自己所需要的结论、达成自己的经世意图,今文公羊学也好,古文考辨法也好,西洋科学也好,基督教也好:一切只不过是手段。
综上所述,康有为在经世致用宗旨的驱动下,孤心苦诣,欲以《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托出石破天惊之论,为自己的维新变法的荆棘之途开出一条路来。他的“两考”在思想界震古铄今,真的掀起了飓风,喷发了火山,使人心起了大惊愕,得到了一次思想解放。然而在学界,因他求用之心太切,这“两考”在学术史上,在开启疑古思潮之先河的同时,却留下了不惜动辄越规失范的种种荒唐:他的“两考”无法经得起学术上真伪之考验。而康有为本人,只因其学说诡入诡出,失于求是求真,流于怪迂奇袤,以致被时人绰为“野狐”(注:翁同酥曾指责康有为是:“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翁文恭公日记》,第34卷,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3页。)。
二
如果说康有为主要是利用传统经学这一中国学术原本固有的最大资源大加创便发挥、以期“自创一学派,而归于经世之用”(注:《清代学术概论》,第73页。)的话,那么严复则是通过引进西方哲理社会科学这一崭新的思想资源,特别是以《天演论》迻译西方进化论,振聋发聩、轰动天下,使优胜劣败、物竞天择之理不仅震动当时中国思想界,而且直入整个社会的坊间民心。
曾留学英伦的严复,其经世致用之心的强烈,丝毫不逊于康有为。他在甲午后迻译《天演论》,实在是因为感到“胸中有物,格格欲吐”(注:严复:《与长子严璩书》(一),王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册,第780页。),痛感于“今日之变,固与前者五胡、五代,后之元与国朝大异,何则?此之文物逊我,而今彼之治学胜我故耳”;痛感于“治国固以人心风俗为本,如今中国之人心,虽与之德之陆旅,英之水师,亡愈速也,呜呼!衮衮练兵购船何为者”(注:严复:《与吴汝纶书》(一),《严复集》第3册。),痛感于“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注:严复:《与张元济书》(1898年)。)。他要通过迻译,祛翳揭蔽,使国人洞识中西实情,惊悟“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第43页。)这一“天演之秘”。
这一迫切的求用心理使严复的《天演论》在学术史上别居一种十分特殊的双重地位。就思想史而论,《天演论》的影响可以说早已越出学术界,直接深入社会人心,远较当时任何其他学说的影响更为广阔而深刻:“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注:《辛亥革命前十年讨论选集》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46页。);然而,《天演论》在译坛的学术规范上,则可以说是屡屡无辙而行,多有失真之处,引起当时及后来颇多学者的微词。这一似乎并不十分谐和的双重角色其实非但并不矛盾,而且从一定角度看,可以说其思想史上的深刻的影响恰是因学术上的失真改作而造就。
严复《天演论》的翻译在学术规范上的阙失,其表现是一为求用,二为求达,皆宁可失真。
严复是从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一书翻译成《天演论》的。赫胥黎根据自己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讲演,扩充改编写就此书,其主题线索是把整个宇宙自然界视为“大宇宙”,将人类社会视为“小宇宙”,强调人类社会的进化与自然界的进化既有联系又有根本不同:人既是自然界物竞天择的产物,是大宇宙的一部分,又是它的最终征服者;自然界采取的是物竞天择的进化形式,造就了人“自行其是”的天性;与之相反,人类社会的进化要靠人的“自我约束”这一“人为的人格”,要靠伦理过程-社会结合的逐渐强化。赫胥黎在此书中并由此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泛用生存斗争解释社会发展规律提出了批评,明确主张以“伦理的进化”建立一个完美的、进步的“小宇宙”,以对抗生存竞争的大宇宙:“社会的文明越幼稚,宇宙过程对社会进化的影响就越大。社会进展意味着对宇宙过程每一步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种可以称为伦理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局,并不是那些碰巧最适应于已有的全部环境的人得以生存,而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得以继续生存。”(注:《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73年中文版,第57页。)
应当说,赫胥黎原著中强调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各有不同的进化形式的旨意是十分清晰的,而严复对赫氏强调“天行人治必相反”亦十分了解,且行文中时有提及。然而,严复对此书的翻译在题目上就只取了原题的前一半,即只将“进化论”译为“天演论”,而将另一半“伦理学”干脆舍弃不译。这当然并非出于疏忽。因为严复之意本不在于渲染赫胥黎所持的人类社会应依靠伦理进化的主张,他“怀铅握椠,辛苦迻译”此书的本心,是为了“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注:严复:《〈天演论〉自序》。),是为了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发为惊天动地的呐喊,是为了替濒临亡国灭种之虞的中国撞响长鸣的警钟:一句话,是为了以物竞天择之“理”,求自强保种之“用”。
职此之故,严复不仅将赫胥黎原书题目中重要的另一半随意笔削而去,而且在正文翻译中亦常常改动原著之精神旨意。如在前半部分的翻译中,他将赫胥黎特别留意限定于自然界的“物竞天择”的进化,常常以己意改撰,扩为整个人类社会均受此同一规律支配笼罩,在正文的翻译中增入了下述原文所无的意思(以着重号标出——笔者):“物竞之水深火烈时平则隐于通商庀工之中,世变则发于战伐纵横之际”(《导言十五·最旨》);“凡兹运行之理,乃化机所以不息之精。苟能静观,随在可察。小之极于跂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导言二·广义》),即将政俗与人文列为均受物竞天择支配。在《导言四·人为》中,他亦擅自加入自己的意思:“彼苍所赋畀,且岂徒形体为然?所谓运智虑以为才,制行谊以为德,凡所异于草木禽兽者,一一皆秉物则,无所逃于天命而独尊。由斯而谈,则虽有出类拔萃之圣人,建生民未有之事业,而自受性降衷而论,固实与昆虫草木同科。贵贱不同,要为天演之所苞已耳,此穷理之家之公论也。”在《导言十六·进微》的翻译中,他也增加了赫胥黎原文中并无、且与赫氏所强调的“猿与虎的生存斗争方法与健全的伦理原则是不可调和的”正相悖反的意思:“唯物竞长存,而后主治者可以操砥砺之权,以砻琢天下”。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一开头,就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此后,“信、达、雅”几乎就成了公认的译事典则。实际上,严复本人在此三者中最不重视的是“信”,他所孜孜以求的,是“达”;骎骎为力的,是“雅”。他认为:“为达即所以为信也”(注:《天演论·译例言》。)(于此可见他将“达”列于与“信”同等重要);他又说:“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注:《天演论·译例言》。)(这又显然已把“达”高置于“信”之上了)。前述那些本非赫胥黎所意的文句在严复《天演论》所译中屡屡出现,正是他着意求达己意所致。不光如此,他在译文中还常穿插进中国的古事古理,加以附会。如在翻译赫胥黎认为善恶本身也在不断演衍进化一段中,加入“尧、桀、夷、跖,虽义利悬殊,固同为率性而行、任天而动也”(《论十五·演恶》);在《导言十三·制私》中,严复将赫胥黎原文引用圣经《旧约》中的一段故事也改为以中国古代之人与事解释:“李将军必取霸陵尉而杀之,可谓过矣。然以飞将威名,二千石之重,尉何物,乃以等闲视之,其憾之者犹人情也。”在试译中(后作了修改)更是充满了大量的“孔子曰”、“易曰”之类的插入,以至于连直夸《天演论》“体势高峻,直摩周秦诸子之壁垒”的吴汝纶,也觉得不对劲,不得不提醒他:“执事若自为一书,则可纵意驰聘。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原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为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入式,……究不若纯用原书之为尤美。”(注:吴汝纶:《答严又陵》(丁酉二月初七日)。)
严复的《天演论》对照赫胥黎原著,不仅在题目上有删削、行文上有附益、宗旨上重“达”轻“信”,而且体例上也颇不精审,甚为芜杂。《天演论》每篇末几乎均附案语,有介绍比较与他书异同的,有评骘得失的,有借题发挥的,严复自称以此“嘤求”与“丽泽”。有些案语的字数甚至超过本文,如《导言二·广义》、《导言三·趋异》、《导言十五·最旨》、《论九·真幻》、《论十·佛法》、《论十一·学派》,均是如此。不光是《天演论》,严译名著除了少数几部外,大都不是忠实于原著、讲求“信”的译本,而是有增有删、有取有舍、有评论有改造的“达旨”之作。他在《名学浅说》序言中这样承认:“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
严复对自己的《天演论》为求达而“有所颠倒附益”、在“真”上有所阙失并不讳饰。他自称《天演论》:“题云达旨,不云笔译”;自评为“取便发挥,实非正法”;并告诫后人不宜仿效:“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注:《天演论·译例言》。)。严复之所以如此,乃是为了通过这种改作甚至创作,演绎成一部借赫胥黎之书“使人怵焉知变”的惊世之作,于时局痛下针砭,以“自了国民之天责”。一句话,就是为了经世致用。
严复不仅为了求“达旨”之用而在翻译的学术规范上宁可逸越,而且还为了求“雅”,亦不惜乎在“信”上失“真”。他主张,文章须“求其尔雅”,“期以行远”(注:《天演论·译例言》。),并认为“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注:《天演论·译例言》。)。也就是说,译笔越古雅,越经得住时间考验,才容易“达”;文体越晚近越俗,不仅难以做到“达”,而且不易长久,“若蜉蝣旦暮之已化”(注:严复:《与梁启超书(一九○二年)》。)。因此,严复不顾中西古今文体文字的差异扦格,对于赫胥黎、斯宾塞、穆勒等这样一批西方19世纪学者的著作,在翻译中刻意摹仿先秦文体句法乃至遣词。他喜欢遣用汉以前的古词以对译西方近代学理的新词,如,从《庄子》中找到“幺匿”一词,以对译“单位”;将“全体”译成“拓都”;将“有机物或生物”译成“官品”;将“单细胞生物”译成“单幺”;将“自由”译成“自繇”;将“归纳”译成“内籀”;将“演绎”译成“外籀”;将间接之知译成“谟如”;将“三段论”译成“演联珠”;等等。他的译作不仅文词力求渊雅,而且十分讲求音韵铿锵,桐城气息甚浓,被吴汝纶誉为“今赫胥黎之道,……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注:《天演论·吴汝纶序》。)。
然而,原本明白易懂的原著被严复这样一译,毕竟变得艰深,正像梁启超后来所批评的,“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梁批评了严复这一文人积习,认为“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才能使学童受其益,才能播文明思想于国民,并顺便再度宣传了“文界宜革命”(注:梁启超:《绍介新著〈原富〉》。)。
对于梁启超的善意批评与建议,严复颇不以为然,申言道:“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声明自己的译作就是写给“多读中国古书之人”看的,而不是“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注:严复:《与梁启超书(一九○二年)》。)。他更认为“文界复何革命之与有?”除了理想与学术,其他方面谈不上有进步;如果采用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近俗之辞,只能取便市井乡僻之人,这对于文界来说,是“陵迟,非革命也”(注:严复:《与梁启超书(一九○二年)》。)。这位将西方进化论首播中国、力倡“物竞天择”之理无所不在的严复,就这样轻率地断言“文界无革命”,陷自我于矛盾之悖境;而他的那些古词古语,则早已被白话文革命“物竞天择”掉了。
对于严复的译著重“达”、重“雅”而不甚重“信”,对于他在学术规范上的上述疏慢或逸失,当时及后来的学界均有不少人提出了批评。傅斯年认为:“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这是因为他不曾对于原作者负责任,他只对自己负责任”;“严先生那种达旨的办法,实在不可为训,势必至于改旨而后已。”(注:转引自《严复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37页。)张君劢对严复的评价是:“以古今习用之说,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学虽美,而义转歧”;又说:“严氏译文,好以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思想,故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注:转引自《严复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38页。)。
在文体上,除了梁启超指出严复“刻意摹仿先秦”之偏颇,章太炎也不满于严复的译作八股气十足:“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注:章太炎;《〈社会通铨〉商竞》。)黄遵宪也向严复投书,提出了希望他一“造新字”、二“变文体”的要求,并引用了学术史上佛经内典之翻译、元明之演义等别成文体的事实,主张文界即使无革命也要有维新(注:黄遵宪:《与严又陵书》,《严复集》第5册附录三“师友来函”,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故适则说:“那种简单的古文体,无论怎样变化,终不能应付这个新时代的要求,终于失败了。失败最大的是严复式的译书。严复自己在《群己权界论》的凡例里曾说:‘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这是他的译书失败的铁证。”(注: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背景及其内容》,《胡适思想小品》,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严复的《天演论》,这本中国首译西方哲理之第一书,就这样以它的巨大思想影响和它在学术规范上的不无阙失之憾,一起载入中国学术史册。
三
康有为与严复对学术规范的轻慢与逸失,考察起来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所致。
甲午战争引发的戊戌时代,是数千载中国学术史由旧向新、由传统转向现代的一个根本折点。戊戌时代之称为世变之亟,与其说是社会和政治涵义上的,毋宁说首先是学术层面上的。这不仅是因为戊戌学界对于甲午世变最感痛深,更因为在这一巨创中,学者们看到了引动中西、乃至中日国势逆反、乾坤倒转的枢纽,已决然不在声光化电、船坚炮利的形下之迹中,而必须从学术的“器”的层面突破、向“道”的领域追寻。一场声势浩大的数千年中国学术史的根本变革之局正在徐徐全幅拉开帷幕。最先强烈感受到这一学术大转折、并率先对此作出反应的,正是以康有为、严复为首的感觉锐敏的一代戊戌士人。
戊戌时代又是学术史上一个苍黄不接的过渡时代。昔日古朽的学术殿堂在已经开始的时代沧桑之变中风雨飘摇,岌岌危而将倾,而新的学术地基与领域则尚未及辟成建立。章太炎形容这一时代的焦灼不安为:“既乱易治也,既治易守也。若夫疆蒌未亏,人民未变,鬼神未亡,水土未絪,糟者犹糟,实者犹实,玉者犹玉,血者犹血,酒者犹酒,而文武恬熙,举事无实,枭狐窃柄,天与之昏,是为大乱之将作。”(注:章太炎:《变法箴言》,《经世报》第1册。)梁启超则将处于这一学术交替时代中急于求知识于域外的学者比喻成“久处灾区之民”,形容他们在这一“学问饥荒”之际,“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可代。”(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89页。)这种学术过渡时代的转换性质,这种焦灼不安的时代心理,这种“学问饥荒”中生吞活剥的特定场景,使戊戌这一个大过渡时代中的新的学术成果因此而难免多有驳杂、牵强、幼稚等不成熟处;而原有的学术规范与传统学术的整体一起,在时代的狂飚惊雷中受到了剧烈震荡。这种新与旧的断裂与交替,是导致过渡时代特有的规范失序现象的第一重原因。
正是由于戊戌时代这种旧学派权威将坠未坠、新学派系统欲成未成的过渡性质,在精神领域却造成了学术与思想“无定于一尊”的格局。原先潜伏着的诸子学、佛学等传统学术的支流已日渐涌动,尤其是甲午之后代表西方学术命脉的西方哲学、史学、文学等学说思潮冲破藩篱、汹涌而入,与佛学、子学一起,形成了当时几大思想资源数川会合的特有学术景观,学术界因之洋溢着格外旺盛的自由研究精神。以康有为、严复为代表的戊戌学者充满了“挥斥方遒”的激昂意气和活跃的创作精神,使此时的学术界在精神气象上展现出一派葱葱郁郁的方春之气。然而,元气淋漓的同时,与学者各人的气质情性亦有相关,却也难免在学说上时有任逞胸臆、逸越规范的情况发生。如康有为,如严复,均表现出不受旧有家法或应有规则的拘范,倾向于采用非常之手段以推陈出新,以逸越常轨之途径开辟新的学术疆土。这种强烈的创造力特征,使他们往往情不自禁地视学术研究为一种激情创作。这是造成此时学术规范易于失落或逸出的第二重因素。
最后,检视戊戌时代学术大变局中的规范失落,最不能忽视的因素乃是晚清经世致用学术大潮的涌动。
早在清学之初,出于对“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为诘”的晚明理学空谈心性的拨乱反正,以顾亭林为首的清代儒者已经发起过一场讲求“经世之务”的学术运动。顾亭林曾将这场运动的宗旨概括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时之务者,一切不为。”(注:《亭林文集·与人书三》。)也就是说,清初的经世致用,一是关注时务,强调“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二是矫正晚明束六经不读、专从事于游谈之流弊,强调“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注:《亭林文集·与人书三》。),倡导攻研六经。
乾嘉以还,清儒在研读六经中为求真解,带动以研求名物典章制度为对象的考证学日益发达精善,进而一统学界天下。道咸以后,考证学纷纭于不可究诘之名物制度,与晚明空言心性一样走入究途末路。延及清末,不仅是学术本身的发展需要再度来个反拨,而且随着外患日急,激成变局,思想与学术界为之大怵,经世致用的呼声更为迫切,卓然形成了激荡的思潮。戊戌这些思想敏锐之士,比起清初之儒来似乎更为忧危天下,有着更为强烈的求变心理,为谋求民族的自强保种,指天划地,慷慨激昂,以规天下之大计,“人人胸中,抱一眇者不忘视、跛者不忘履之观念”(注:日·稻叶君山:《清代全史》下卷,中华书局版,第4章第30页。)。自戊戌至五四,学者社会多有骁将直接涉足政界,便是这一经世致用大潮风起浪涌的明证。这一强烈的经世致用倾向在学术上造成的后果是,求用与求真在19、20世纪之会经常发生矛盾,在不少讲求致用的戊戌时代学者身上,都可清楚地看到求用被置于求真之上的迹象,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有康有为以公羊文饰政论,严复以“达旨”译述《天演论》以警世。这也实在难怪,因为一方面,求用在当时成了如此普遍而强烈的社会心理与社会需要(注:康有为即如是说:“余有一弘愿,愿以其身为蓐葳,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期有济于世而已”。(《与沈刑部子培书》),《康子内外篇》,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89页。),另一方面是因为,正像梁启超总结自己当时的治学所弊时所指出的,当时的“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注:《清代学术概论》,第81页。)。
康、严的学术规范之逸失固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这些阙失与这些原因,却能启发人对于学术的“求真”与“求用”的关系,对于应有的学术态度与学术追求,作更为深入的思考。事实上,当时有些学者对此已有一定关注与探究。
梁启超曾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真理者”(注:梁启超:《学与术》,《饮冰室合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2页。);严复自己也说过:“学主知”,“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注:《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5页。)。在人文历史领域,学术的本质在于,它是人类理性认知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兴衰更替、对历史上出现的思想与理论的起伏升降的真正原因及一般规律作客观的知识的探究,在不断考察、累积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系统的知识形态建筑,因此,它的内在的基本要求就是“求真”:讲求史料对于客观事实的真实与对应;讲求分析程序合于逻辑规范之真恰与确当。学术以求真为指归,有其自当不移的独立的、客观的知识价值,它的基地、它的基本特征就是独立性与客观性。它独立于研究者当时的历史文化情势:它以自己为目的,“无暇外慕,是为己者也”(注:《严复集》第2册,第275页。),“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者”(注:章学诚:《与朱少白论文》,《章学诚遗书》卷二十九,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35页。)。故它在本质上并未将“求用”纳入自己的内在宗旨:“学者将以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注:章太炎:《与王鹤鸣书》,《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有用无用并不是它从根本上必须关注的东西,也不能成为衡量与评判它的真正标尺:“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注:章太炎:《与王鹤鸣书》,《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如果一定要从“用”这个角度来观察学术功能的话,可以说,它就是庄子所说的那种“无用之大用”。
学术的客观性则要求它的研究者对于史料之积累具有良好的知识价值信念与素养,无有成见,空所依傍,无我而依他起信。学术研究者应如法吏判狱,无偏无党,对之进行实证的而非臆度的、实事求是的而非主观意向的分析,而这就要求一系列学术规范的支持及制约:“今之学者学为匠也。为匠者心有规矩绳墨,模形惟肖,审谛如帝,用弥天地,而不求是绝之。”(注:章太炎:《与王鹤鸣书》,《章太炎全集》,第151页。)
至于“求用”,正如上述,它并不是学术本身之内在必须,而是一种外来的需求。它与学术的独立性与客观性可以一致:只要研究者能以求真求是为“第一义谛”,并严格地将之作为必守的前提与准则。但较多的情况是,求用追求的主要是一种经世效应,并往往确能在现实中达到轰动一时的效应,因而在思想史上常常留下辉煌的、或显赫一时的记载;然而与此同时,求用的另一面却在学术研究中不时倾向于逸越规范,从而导致研究的失真。求用者往往以学术为手段,“为我而求其益损”,因而太有成见,常以自己的价值判断先期介入,以致对知识体系价值联系的因果分析造成干扰,强求之以就我,甚至以个人好恶任意剪裁或编造史料,影响了对思想系统的完整合理的理解,甚至出现种种不可思议的夸诬,造成“明学术而学术转歧”。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某种二律背反,在这方面得到了引人注目、发人深省的呈现。
在比较康、严学术规范逸失的同时,顺便要提及的是,或许是严复对学术的独立性与客观性有一定的认识(见前述引文),他在学术转歧的路上,毕竟没有像康有为在“两考”中那样,走得那么远,陷得那么深。
标签:康有为论文; 严复论文; 孔子改制考论文; 新学伪经考论文; 清代学术概论论文; 国学论文; 学术规范论文; 天演论论文; 梁启超论文; 赫胥黎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