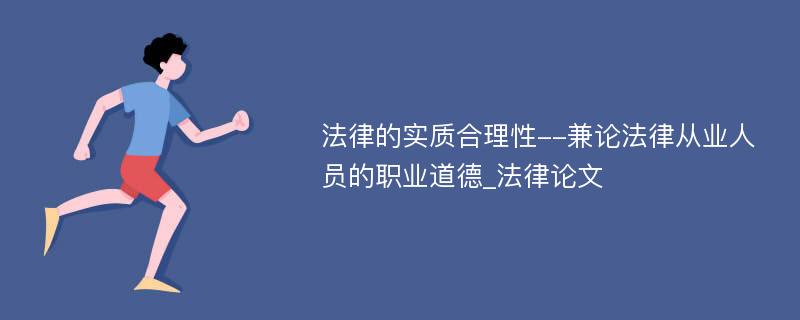
法律的实质理性——兼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伦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律论文,业者论文,伦理论文,实质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从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的分梳来看,法律(注:谨言之,“法”与“法律”之内涵与外 延均不一。本文意在探究法与法律之共有品性,职是之故,并未对法与法律作区分。) 理性是法律之所以为法律的内在逻辑品质,同时并为法律的外在技术品质。作为法律的 外在技术品质,法律理性表现为经由诸如程序公正、法律推理、法律论证以及各种具体 部门法的一系列智性制度安排和种种法律技术,包括法律语言、法律技巧和法律形式, 赋予人世规则与人间秩序以明晰、确切、稳定、可预测与可操作等技术秉性,使人世生 活得有可恃的凭依,而将法意与法制曲连沟通,世道人心与制度架构打成一片。法律的 生命之源由此潜转为规则之流,法意人心藉诸具体的规则形式,成长为遮庇人世生活的 人间秩序这一参天大树。通常所说的法律之为一种对于未来情形的“预测”或“预言” ,其意在此。此即法律的形式理性。
作为法律的内在逻辑品质,追根究源,法律存在的最为根本的理据在于它是人世生活 的规则,堪为对于人世生活的网罗和组织,而蔚成人间秩序,从而为居民的洒扫应对提 供一个规则之维。就日常运作的表象来看,则法律以对于诸种现实难题的规则性梳理为 务,从而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应对生计的历程中,垒砌块块“石头”而已。如此这 般,使大家的日子过得下去,并力争过好,同时为未来提供可得循依的成例成规。职是 之故,“规则性”是法律的最为根本的属性,是法律之所以蔚为人世生活的规则的根本 原因所在。对此属性的深刻体会与领悟,构成了法律从业者的规则意识,作为对此属性 的主体呈现,它形成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其他各项职业伦理的基础。由此,为了保守和 护持规则性,则常态之下,法律应当永远是对于生活本身固有情形的忠实表述。“观俗 立法”,循沿生活的常识、常理与常情,是立法的最低也是最高标准,也是法律从业者 的职业敏感的特殊性所在。换言之,任何法律总是现实的规则,立于生活现实并对生活 现实作出自己的反映。从而,不是别的,正是“现实性”使得法律区别于道德与宗教。 相应的,现实主义或者说现世主义,成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禀性。
当我们说“现实”的时候,不仅意味着当下的,同时并略略带有前瞻的意味。现实不 过是过去与未来在当下的暂时呈现,在时间的维度中,同样曾经是未来而又必将是过去 。法律是现实的产物,即说明必须对此两头均有所照应,而尤当照应到未来。但是,未 来究竟如何,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终只能经由鉴往察今而隐约推论。法律关乎社会组 织方式与人世生活方式,为了不致发生法律规定与现实生活两相脱节,甚至悖情逆理、 伤天害理,损害到已为成例成规的生活本身,因此,一般常态下,此种前瞻只能是“略 略”为之。毕竟,如后面正文将要阐释的,法律乃是“当下的一个重要的规则性存在” 。职是之故,作为对此前瞻的牵制而确保立法不过是对于生活本身的模写,法律较生活 本身通常总是“慢半拍”,以对既往成例成规的记录而昭示当下和未来以循沿的轨迹。 换言之,法律天然具有“保守性”,守成的态度因而成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理性。凡此 种种,其宗旨其目标,均不外为人世生活缔造或者看守人间秩序,而达成一个理想而惬 意的人世生活。正是在此,法律不仅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并为一种意义体系,自有价 值追求蕴涵其中。对于此种价值的确信不移,直至达到以其为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担当 的程度,构成了称职的现代法律从业者的世俗信仰。如果说现实性使得法律区别于道德 与宗教的话,那么,此种“世俗信仰”则又使其与道德和宗教——神圣的超越性精神源 泉——永远保持内在的血脉联通。由此,铁面的现实与高悬的理想,在理想的法律中获 得了完美的统一,法律的理性之维与德性之维和谐不悖,法律因而成为人世生活的人间 秩序。
由此,规则性、现实性、时代性、保守性和价值性,构成法律的实质理性的基本内涵 ,成为法律理性的内在逻辑品质。相应地,法律从业者作为“行走着的法律理性”,其 职业实践、志业担当和天职践履,都应当是或已经是法律理性的落实与体现。因而,正 像程序公正、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和法律形式、法律语言等是法律理性的技术外化,规 则意识、现世主义、时代观点、守成态度与世俗信仰,作为法律从业者对于法律理性的 内化,构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伦理与实践伦理。总之,作为人类理性的规则投射, 正是法律理性而不是别的什么,使得法律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也使得法律从业者社群 区别于其他职业或志业社群(注:职业社群与志业社群的区别在于,前者仅为共同职业 者的结合体,并非以共同精神为必备条件;后者镇为具有共同精神诉求者的共同体。因 此,建筑或畜牧业从业者分别可谓一种职业社群,而诸如绿色和平组织,乃至于“哈马 斯”,则为志业社群。当然,职业本身也含有志业的成分在内。)。
本文循沿上述理路,紧紧扣住事实与规则、人生与人心、法制与法意等基本关系,主 要以晚近以来渐次形成的“法律文明秩序”(注:关于宗教、道德和法律三个文明秩序 的分梳,参详於兴中《作为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载《清华法治论衡》第一卷,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44页。),即发端于西方,而以“现代化”一言以蔽 之的近代工商社会这一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下,特别是中国语境下一个世纪来的法律生 活经验为根据,以历史和价值相结合、叙述与分析并行的方法,分别依次探讨上揭法律 的实质理性的基本内涵,剖析与之相对应的法律从业者的基本职业伦理。藉由这一讨论 ,追问究竟什么是理想而惬意的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
一、规则性与规则意识
法律是一种人世生活的规则。就晚近历史来看,所谓人间秩序,很大意义上,实即法 律秩序,亦即经由法律网罗、组织生活而编织起来的人世生活。在此语境下,作为法律 公民,法律从业者是规则的寻索者和整合者,是法律“意义”的生产者和阐释者。
首先,其为规则的寻索者和整合者,在于从纷纭复杂的实际社会生活中,抽象、整理 出生活本身所固有的一般关系,并将其转换、凝练为规则形式。立法,不过是将大家心 中所有而笔下所无者,忠实记载下来,实现从事实到规则,再从规则到事实的过渡,不 管它是非成文法;而司法,乃是经由对于此种记载的复述,让规则长上声音的翅膀,将 法律的内在伦理力量变而为法律的逻辑力量和技术品质,实现由事实到规则的衔接。
其次,其为法律“意义”的生产者和阐释者,就在于如此作业的同时,即是在“赋予 ”规则以意义,甚至赋予生活本身以意义(注:有关规则的“意义”及其“赋予”性质 ,参详下述“现实性与现世主义”一节。)。而一项立法之所以堪称规则,正在于它是 含蕴了如此意义的法律,是以如此意义为航标为灵魂的人间秩序。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大凡法律所预设的实效的实现,必以其颁行不致引发大规模的社会震荡为前提。导致人 心普遍失衡,人世生活无所凭依的立法,不足以堪当“规则”的重负,也是对于意义的 湮灭和亵渎。它不是规则,而是对于规则的背叛;它不是“言法律之所言”,而是僭越 的“矫诏”。从而,它在造成普遍的“有法不依”的尴尬的同时,还必然会遭致“伤天 害理”的意义评判。
凡此规则与事实间的种种特性,源自法律或规则的确定性。此处的“确定性”,无论 在应然、实然或拟制的意义上,都不仅意味着与“事实”相对应的规则世界的和谐、匀 称与圆融,而凡此均不过事实世界的映像,一定意义上的映像;而且,它还意味着此种 本体意义上的和谐、匀称和圆融,可以经由立法、司法乃至于“守法”,以及三者间的 互动,在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意义上获得完满的表达和体现。虽然包括美国的批判法学运 动在内,晚近以来对于这一点不无质疑,但是,细予审察便可看出,其于此种确定性的 证伪,其实揭露的是本体论意义上对于确定性的拟制的虚妄,但却无法否认从本体论到 认识论和实践论意义上,其应然的正当性与实然的现实性——一定程度上的现实性。实 际上,其所欲颠覆的是西方法律传统中,准确而言,是普通法传统中数百年来的对于法 律的确定性的过度的褒扬、坚执的迷信,与实际生活对于这一确定性的诸种嘲弄所造成 的种种不和谐、不匀称与无法圆融的尴尬关系。而确定性本身,尽管具有拟制的虚妄性 ,但却并非虚假的存在。毋宁,它是近世人类对于法律的“信仰的姿态”的不打自招( 注:参详后述“价值性与世俗信仰”部分。)。绝然否认这种确定性,便是否定了包括 法的确定性在内的生活条理的存在本身,从而是对否定者自身及其言说本身的彻底否定 。
因此,法律的实质理性作为法律的内在逻辑力量,经由一系列制度安排,赋予人世规 则与人间秩序以明晰、稳定、确切、可靠以及可操作等技术秉性,从而使人世生活得有 可恃的凭依。也就因此,大凡足以被称为“规则”的法律,必能就进入法律领域的事实 的发展结果,向人们预为描述,预作说明。法律的明晰、稳定与确切,是法律之为“可 靠”的前提,从而“可操作”——每个人能够据其安排而对自己的身心作出相应措置, 不管其为法律实践还是日常起居——的保障。真正良好的法律,堪称规则的法律,应当 具备这一内在逻辑力量,赋予人们根据法律按图索骥的可预见能力。霍姆斯指出法律及 其研究之旨乃在预测,即对公共权力经由法庭而作出何种反应作出预测,而几乎法律思 想的每一新的努力的全部意义,均在于力使此种法的预言更为精确,并将其归纳、综合 成为一个圆融自洽的体系,含义亦在于此(注:O.W.霍姆斯:《法律之道》,许章润译 ,《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秋季号。)。
正因为此,人们在研习法律之初就应当明了并有所思想准备的是,法律从业者应将自 己的个性色彩归纳入、体现在对于法律、法学的学科域界和学术纪律的规范之下,以对 法学和法律的基本学术纪律的服膺为个性伸张的前提。有些时候,甚至会出现以对个性 的压抑和泯灭为代价的情形。任何规则总是对于人性的顺导与压抑的合一,法律作为规 则,同样具有这一特点。因为法律所预设的“人类形象”,乃是作为平均数的一般人, 常人,“中人”,而非形形色色、个性昭然的现实的个体生命。法学是关于规则的知识 与理论,不幸濡染此研究对象的特性,要求以对法学的学科特性的服膺为展示学术个性 的前提,原因在此。为什么诸如巴尔扎克这样的心智最终必得放弃学习法律,而以诗思 论政、礼治安邦的中国古代士大夫们则通常将治律委诸知识分子下层的刀笔师爷,亦可 于此求解。在“通向正义之路”中,丹宁勋爵曾经告诫读者:“起步伊始,君当牢记, 有两大目标需要实现:一是领悟法律乃是正义的,一是务使其得被公正施行”(注:Alfred Thompson Denning,The Road to Justice.London:Stevens and Haynes,1955,pp.6—7.)。转借这一用意,“规则性”应是法律从业者细予领会的法律理性的重要内 涵,而“规则意识”则为法律从业者“起步伊始”所当养成的职业伦理。
二、现实性与现世主义
法律的产生与人类的生计息息相关,是特定地域居民应对生计的手段之一。围绕着生 计打转,使实际生活本身走得通,走得稳妥踏实,而安抚一方水土,是法律的终极理据 ,也是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规则的最为深切而终极的存在原因。实际上,作为一个基本 的历史事实,它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切典章文物的最为原初的历史发生论图景与合法性源 泉。
因此,现世主义,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现实主义,亦即现实的态度。但它不止乎现实, 它并且还是一种同情的态度。即法律从业者作为人世生活的一分子,由设身处地、推己 及人、能近比譬的格局中,思考、对待法律之为一种人世规则和人间秩序。这里,法律 从业者需要深深铭记并时时用来警策自己的事实是,为生活本身所固有,从而能够将生 活组织起来的最为深厚而宏大的力量,不是法律,不是法学,也不是“行走着的法律理 性”,而是叫做“生计”的这一燃眉之急。通常情形下,生计之道无他,其最为基本的 ,乃是日常生活中流转不息、显隐有度、从而谕示着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要做人的 常识、常理和常情也!而且,常常是区域性、时代性的常识、常理和常情,使日子大致 过得下去,心情基本平顺,而为日常洒扫应对所必需的流程和章法。我们的父兄辈如此 行事,我们的邻人如此行事,我们自己如此行事,我们的子孙还可能如此行事,“从来 就这么着”的起居之“常”,日用之常——就是习俗,也就是法律,而为生计之规则, 存在之形式。实际上,所谓法律,从其为规则及其意义的合成体的最为原始的意义而言 ,正是对于人世生活中的常识、常理和常情的理性主义归纳与形式主义展现。
此处所强调的不过是诸多思想家们早已表达过的。马克思说法律没有自己的历史,其 历史存在于社会生产方式之中。因此,“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 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 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而在此 之前,萨维尼亦曾慨言,“法律并无什么可得自我圆融自洽的存在,相反,其本质乃为 人类生活本身。”法律之有生命力,此为由来;法律之为良法,此为一端;而法律之无 效,之失于为民众所广泛信受,亦正在于其失却“表现和褒扬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 “如果说有什么应予谴责的话”,如萨维尼所言,“当是法律类如一种乖戾专擅之物, 而与民族两相背离”。(注: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24—33页。)纵观人类历史,多数法学流派,不管彼此之 间如何捍格不凿,但对此“事实与规则的基本历史图景”,大致还是认可的。所以,卡 多佐才会说,“如果一个法官打算将自己的行为癖好或信仰癖好作为一个生活规则强加 给这个社会的话,那么,他就错了。”(注: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 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7页。)岂止是错了,根本就是“置车于马前”。
但是,正像人类的历史是一个“层累地”形成的时间与意义过程一样,法律与法学的 历史同样是“层累地”形成的。此过程既是一种自然历史阶段,同时并为所谓的“理智 化”或“理性化”的进程。从一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就是人类在漫漫的时间之维中将自 己的理想烙于规则之体,从而赋予规则以意义——极具地域性特征的形形色色的意义。 正是在此,实际生活本身的意义出现了转型、变换甚至扭曲,规则所实际承载的与应当 赋予的意义之间,规则所固有的与实际展现的意义之间,以及对于同一意义的不同解读 之间,在不同时空之间,呈现出巨大的隔阂甚或对立。天长日久,渐渐习而不察,视为 当然;俟有感知,常常已然积重难返,人世生活的事实与规则之间遂出现了巨大紧张。 此亦即梅茵爵士在论述所谓发生于“进步社会”中的法律拟制,而实则不惟“进步社会 ”,实乃存在于全体人类社会中的那种情形。即“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是常常或多 或少走在‘法律’的前面的”,因而,其间永远存在“缺口”。(注:亨利·梅茵:《 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5页。)笔者于此欲加陈说的是,人类 精神的丰富多彩,此为一端,而人世生活竟然背叛自身,规则围剿事实,同样在此一端 。人类历史上诸多恶法的存在,有悖常情的奇怪法律规定,类如“一个女性证人的证明 力等于半个男性证人”、“禁止青蛙在夜晚十点以后鸣叫”等等,虽然作为此规则的事 实的社会生活可能已然发生重大变迁,因而,早已有人感觉其失于偏异,但却居然相沿 不废,不完全是人类的私见或恶的作业的结果,很多时候,乃是这种转型、变换甚至扭 曲所造成的,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法律之为规则,得益于此“理智化”或“理 性化”过程,而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法律对于理性的偏离和法律理性本身的扭曲,亦 同样为此过程的结果。这是人类创造和利用自己的创造物,同时却又为其所害这一普遍 悖论的又一例证。
有鉴于此,为了避免这种隔阂、扭曲或对立,法律理性应将自己的生命之源深植于生 活本身,直接诉诸人生与人心,即诉诸如何过好自家日子、妥贴安排生计的日用之常, 将其归结为与生计关系的意义评判。就具体的操作而言,法律从业者应当从生活本身省 视规则,在包括“法律实践”在内的起居之中,体会基本的人情世故,包括自己在内的 普通居民的想法,对自己所要处理的论题,力争作设身处地的同情的了解和理解。通情 达理本身,就是理性(不是理智)的最高境界。所以梁漱溟先生才会说,理性非它,“吾 人所有平静通达的心理”,一种“清明安和之心”;理性不仅是“人类心理顶平静清楚 的时候,并且亦是很有情的时候”,所谓“平静通晓而有情”也!也就因此,漱溟老人 乃一言以蔽之,“人情即理性”。而从否定一面来说,“理性就是强暴与愚蔽的反面, 除了这两样之外的就是理性。”(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 和《与丹麦两教授的谈话》,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1992 年,第181—314页;第3卷,第123页;第5卷,第571页。)就此,我们也许可以说,最 好的法律乃是最能体贴人心、照拂人生的规则,是最为有利于居民根据自己的常识、常 理和常情,安排过好自家日子的规则。一句话,同情的态度底下的最好的法律,倒恰恰 是理性的规则,而理性的规则,也就是对于生计本身最具同情态度的法律——不是物理 、逻辑或数学的“理”意义上的理性或理智,或者不仅仅是它们,更应是“平静通达的 心理”与“清明安和之心”意义上的理性。考虑到人类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创造力与骇人 破坏力总是成正比,而人总是靠不住的,总是具有将私利作无限扩张的本能,或许,体 贴人情世故,一般情形下秉持常识、常理和常情,立法以不要太“伤人”为限,是避免 上述理智化或理性化的遮蔽所导致的“隔阂、扭曲甚或对立”,防止稀奇古怪的规则和 恶法出现的一条基本途径。正像对于法律的无条件服从一样,从生活本身和人情之常省 视法律,同样是法律的实质理性的固有内涵和必然要求。
也就因此,法律的事业,由于它通常所遭际和面对的是人类的麻烦与苦难,因而是一 个需要同情与悲悯的所在。凡此人类情感,不仅与其职业不相矛盾,相反,恰恰为其职 业理性所内涵,构成其职业理性的内在的超越性紧张关系。人性永远存在瑕疵,注定了 人永远是不完美的。要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作神作圣,超过了事实的许可。但是,另一 面看,如果说人、人性同时却又尚有堪称完美之处的话,则在于人类总是正视此种缺陷 ,并力争臻达完美。法律和其他种种规则的出现,不仅是基于人性本恶的理性预设,同 时并彰显了人性向善的德性预期。人类的法律形象,永远总是基于性恶预设而来的对于 性善的预期的集合体。如果说凡此预设与预期不过是法律这艘航船的舵盘的话,那么, 法律理性乃是策舟前行的风帆和引领前行的灯塔。“现世主义”的“现世”,正是在这 样的预设和预期下的人世生活。
三、时代性与时代观点
法律是时代的文化命运的规则写照,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法律是对于特定时代的文化 命运的悲剧性写照。时代的文化命运,也就是一时期一地域的全体居民的总的生存条件 与生计状况。之所以说法律是时代的文化命运的规则写照,就在于法律不过是而且永远 总是对于特定时代的生存条件与生计状况的法律呈现,希望对此条件和状况酌予梳理而 赋予其规则性,但却无以挣脱这一总体条件的制约。所谓超前的法律,通常都是不具可 操作性,因而常常乃为无用的法律;而之所以说法律是对于特定时代的文化命运的“悲 剧性写照”,则又因为置此总体条件下,任何法律不仅只能对此生存条件与生计状况作 出大致近似的描述,而且此种描述总是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因而,其本身即 如其欲描述的对象一般,将会随着这一时代的消逝而渐遭淘汰。生活之树常青,而法律 总是“临时性”、“过渡性”的;惟一婉转沿承的,是涵育于生活之中而借助法律现形 的规则本身。正因为此,法律从业者所思所虑的时代文化命运,亦即此整体命运的地域 性生存条件,长程历史中某一时段的生计状况。正常情形下,或多或少,法律从业者总 是将对于法律现象的思索,纳入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化命运的整体观照之下,以对这 个时代与民族生活的总体语境和根本精神的体察,在事实与规则间恰予措置。
在这方面,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法律史可谓一个生动的例证。自1840年以降,特别是甲 午后变法以来,中国社会的总的时代特征乃是一个“变”字。实际上,如王伯琦先生19 55年所论,“自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整套的西洋最新立法”,以“改头换面或照账 誊录”的方式全面移植进来(注:王伯琦:《当今中国法律二大问题的提出》,《王伯 琦法学论著集》,(台北)三民书局,1999年,第294页以下。)。在此建设现代民族国家 ,而以“社会—文化转型”一言以蔽之的长程奋斗中,中国固有的法意和法制悉遭批判 与抛弃,而引植的西法却又与固有的人生和人心颇多捍格不凿,以致于百年来的中国法 律,多数时候,既缺内在的伦理品质和逻辑力量,亦乏外在的技术品质。而一个缺乏规 则之维的社会,其不断调整与整合的过程,乍看之下,却以乱象面世,其因在此。正是 在此文化与社会急剧转型的大背景下,不难想见,一切的法律措置均具有“临时的”性 质,也就是说,均处于试验和调整状态。此间百多年的试错与整合,乃在为此后渐次成 型、堪称规制的社会组织方式与人世生活方式,预做安排。之所以自“钦定宪法大纲” 以降,中国递次出现了14部宪法,而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自颁行以来,已 然通过了十七条修正案,乃至于1949年后三十年间为组成一个健全社会所需的诸基本法 律居然全盘阙如,此为原因之一。法律的“时代的文化命运”,其例莫若如是。
由此观之,百年间的一切法律措置,不论其为引植西法的“文化移植”,还是“乡村 建设”中的本土努力,今日以“接轨”为准绳的种种言说,包括法律领域的“接轨”, 乃至于对于“本土资源”的倡导和关乎“人生与人心”的强调,起承转合,相反相成, 均为其一部分一环节。因而,其间的一切制度安排均为应对“一个大的历史时段”中的 一时一地之需而设,均为“过渡性的”,也就非为虚言,而是“不得不然”了。所谓“ 一个大的历史时段”,即此百年文化—社会转型,也就是“历史三峡”(注:参详拙文 《法律:民族精神与现代性》,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5期。);而正如唐德刚先生根 据“历史三峡”这一总体语境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在此社会转型期,任何伟大的革 命都有其局限性”(注:唐德刚:《九十年后回看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明报月刊》( 香港)2001年第1期,第41—45页。);同样,任何立法,特别是像宪法这样的事关社会 组织形式和人世生活方式的大经大法,也都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一定意义上, 也可以说有其临时性、权宜性。相较于清末以来中国已然有过14部宪法,自1932年以来 ,毗邻的泰王国已然有过16部宪法。双方具体情形不同,实际还是基于社会—文化转型 这一各自的“历史三峡”而发,不得不然!所以,这个“过渡性”,最为要害,对此“ 过渡性”的体认,是这个时段法律理性的“时代观点”的重要内容。
实际上,在此一百年间,对此时代悲情及其原由的充分自觉,是这个时代优秀法律从 业者的共同特征,并构成其前赴后继的积劳积慧之精神源泉。蔡枢衡教授感言清末变法 之后的中国法律秩序的内容是外国工商业,而不是中国的农业;其根据是高度发达的外 国工商业社会,而不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表现为具体过程,则清末以还三十年间中 国的立法,依蔡氏所言,起初完全是在比较各国立法的氛围中产生出来的,后来的立法 理由中虽然常常可以看到“斟酌中国实际情形”的语句,事实上却实在没有斟酌过什么 ,也没有多少可供斟酌的资料,所以实际上依然没有超出“依从最新立法例”的境界。 而此种“唯新是求的精神实在是无我的表现,也就是次殖民地的反映。”(注:蔡枢衡 :《中国法律之批判》,正中书局,1947年,第67页。)王伯琦教授曾经慨称:惟法律 之规定为一事,社会之进步为一事。超前之立法,虽足以启迪社会之意识,究不能变更 社会于一旦……在正常情形,社会前进,法律终须落后,如何使法律紧随社会而不致脱 节,原为立法司法及法学方面最重要之任务。吾国情形,适得其反,法律超前,社会落 后。(注:王伯琦:《民法总论》,(台北)国立编译馆,1963年,第18页;并见《当今 中国法律二大问题的提出》。)因而,如何发扬现行法律的精神,启迪社会意识,使社 会意识与法律精神两相融和,依王氏所言,乃为急务。这也同样是一种对于时代命运的 自觉。正像马克斯·韦伯以“理智化”或“理性化”为晚近西方法律的发展作结是一种 对于其时代命运的自觉,批判法学锋芒所向直指这种“理智化”或“理性化”的负面, 亦即哈贝马斯所谓的法律对于生活世界的“过度殖民地化”,也同样是一种自觉。大凡 健全的法律理性都能保有这一反思能力,必秉有“时代性”,法律从业者的职业理性必 秉有“时代的观点”;而优秀的法律从业者,其中主要是法律思想家们,乃是其时代的 文化命运的法律喉舌。
四、保守性与守成态度
凡法律之被奉为规则,绝大多数乃是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逐步实现的。实际上,今日 我们所能看到的各种人文类型下的种种法制,不论是涉关社会组织方式,通常所谓的公 法规则,还是作为法律文明秩序下“生活的百科全书”,涉关人世生活方式的私法规则 ,多是经过时间之轮碾压后,历经淘汰,剩留下来的人世规则。所谓的“法律传统”, 即此人世规则及其脉脉法意的绵绵延承。一般而言,它们广为信受,比较定型,作为一 种框架性的结构,尽可以容纳事实与规则的种种变数于其中,而保有一个使得人世生活 大致得以维持下去的人间秩序。正如既往的人世生活已然昭示的那样,在未来的人世生 活中,伴随着事实的生灭过程,必定也还会有进一步的筛选,而有规则的生灭。通常所 谓的法律之循时而变,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人世生活本身在对规则酌予甄选。也就是说, 不是法律在循时而变,或者说,不仅仅是法律在循时而变,而是人世生活本身在对法律 的用舍、存废表明自己的态度,作出自己的选择,法律面对变局,不得不“循时而变” 。很多时候,即便是在社会变迁更为剧烈的今日世界,这也是一个常常以世纪为计算单 位的长程历史。其间,事实将会如何发展,应当向哪里迈进,多数时候均有待观察。因 而,法律之“循时而变”,为保险起见,也就是不致因率尔操觚而致率兽食人,通常总 需左顾右盼,比事实慢半拍。情形常常是,从事实与规则的互动,而致力于理想而惬意 的人间秩序与人世生活的建设这一语境而言,“慢半拍”不一定就是坏事。
的确,既然法律之成规则并且逐步成型,关键在于其与事实保持相当协调,蔚成人世 生活的规则形式,那么,一旦砥砺成型,便成人世生活的规则之维。在此情形下,辄言 立废,不仅会造成规则的紊乱,使得人世生活无所适从,更主要的是,其必伤害作为规 则之所以立基的事实,即生活本身。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通常情形下,总是先有事实, 后有规则,而规则,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不过是使各种“事实走得通”的法子(注: 梁漱溟:《中国党派问题的前途》,《梁漱溟全集》第6卷,第578页。),我们今日不 妨说,也就是使日子过得下去,并尽量争取过得好一些的生计之道,生存之道。
在人类法律史上,依靠规则为事实开道,藉规则制造事实,从而在一个新的生活平台 上缔造新的事实与规则的互动,实现规则所欲达成的理想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亦非绝 无仅有。但是,毕竟,虽时有发生,却洵非常例。通常,这一情形只发生于乱世,或者 ,出现于类似近世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社会—文化的整体剧烈转型时段。对此,我们需要 清醒意识到,这是一个“革命性”的非常时段,并非常态,随着社会或文化转型的渐次 完成,其必渐归常态,循事实与规则的固有互动关系展开。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 人来说,过日子图的是个安稳与安全,除非迫不得已,否则,“革命性”的举动不能当 饭吃。事实上,随着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渐上轨道,这一事实与规则的良性互动,在近 年来的中国实际法律生活中已经渐露端倪。刑法的修订即为成功的一例,而诸多单行法 规的出台,亦多少较前慎重,多少体现了对于事实与规则的固有关系的尊重。这一切不 仅说明立法者对于事实与规则互动关系的体认和同情较前深刻,而且也说明了随着生活 渐归常态,“活法”与“立法”之间事实与规则的固有逻辑渐成主宰。
关于这一点,东西法律学人多有觉悟和指陈。王伯琦先生曾说过,“论法律的性质, 原是一种保守力量。在普通情形,道德当然超前,法律总有落后性,这样才可以维持社 会的安定。”(注:王伯琦:《当今中国二大法律问题的提出》。)也就因此,“实际政 务上最保守的一环,应当是司法。”(注:王伯琦:《法律上实务与学说的距离》,《 王伯琦法学论著集》,第220页。)在总结西方法律传统时,一些西方法律学人对此也表 达了类似的看法。以私法的演变为例,由于法律本身的产生方式和法的渊源通常总是被 人们视为一种既定而先验的、几近神圣的存在,因而,其变革亦难乎其难;其次,法律 必须具有自我正当性,因而必须拥有其权威,导致法律乃属典型的“慢半拍”。凡此两 项,形成了法律的“生就的保守性”(注:Alan Watson,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Private Law.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gs University Press,2001,p.264.)。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笔者意欲重申的是,法律的事业是照料和治理人类生活的劳作, 而人类生活自有其规则,自有其浑然天成的一面,而且人命关天,人命就是天命,因此 ,除非必须,否则不要轻易奢言所谓的“变革”,无端变来变去,拿生活本身开刀。中 国农村二十年来施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是政策,也是法律,是关于土地所有权 与使用权的基本法制。其基本效用的发挥,尤其是在施行初期,端赖一个“五十年不变 ”。相反,近几年中时有所闻的地方政府出尔反尔,撕毁合约,动辄改变这一基本法制 的恶行,与苛捐杂税一起,使农民对于这一土地制度的延续性与有效性深感疑虑,不仅 妨碍了这一基本法制效用的发挥,实际上,已经使得农民频临破产。当然,导致这一问 题的原因并非仅此而已,但是,它提醒我们,在事实与规则、法意与人心间大刀阔斧、 雷厉风行,是改革家革命党街垒战士的作风,是大革命时代的时尚;而小心翼翼、如履 薄冰、谨慎护持,才是法律家的本色,是绝大多数乃属平常日子里的常言常行,常规常 矩。前者狷狂,后者郑重;前者为人世生活挥洒豪情与热血,展示野心与抱负,后者则 为此演出提供舞台,力图将此壮举纳入不致洪流冲毁堤坝、泛滥成灾的地步。它们各守 自己的疆域,共同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多姿多彩。如果彼此越位,结果只能是事实与规则 俱焚。
因此,法律从业者如同一切人类生活的建设者,应当对传统抱持必要的尊重甚至敬畏 。法律既是传统的产物,而且是传统本身。不仅每一种法统总是特定人文类型传统这一 “家族之树”的分枝,而且,法律生命的肥瘠荣枯,紧系于其所属人文类型传统的盛衰 存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包括法律传统在内的一切传统,不仅意味着时间之维上的 一个“过去”,而且构成了时空之维上的“当下”。就法律传统而言,它是“当下的一 个重要的规则性存在”(注:Martin Krygier,Law as Tradition,in S.Panou,et al (
eds.),Philosophy of Law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Thought12[th] World Congress Proceedings.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 Wiesbaden GMBH,p.180.)。如果说十 二世纪以降,欧陆法律家们呕心沥血研读罗马法,嫁接传统,对于我们具有诸多启示的 话,则中国的法律从业者,研修法律的念书人,应当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具有基 本的了解和理解。实际上,通观历史,通常而言,多数法律从业者都是——都应当是— —“保守主义者”。因为法律从业者起居其间而构成其工作对象的乃是事实与规则、法 制与法意和人生与人心,而这一切如前所述,动辄“人命关天”,因而法律从业者的一 个基本职业特征,就是不得不小心谨慎从事。而就近代中国语境下法律法学领域的“保 守主义”思潮来看,从沈家本时代关于悖德违礼诸条是否为罪、应否入律的争论,到陈 顾远氏等对于法律传统中民族文化精神的申说,而至今日对于“本土资源”的强调,以 及笔者此刻的用意,抛开作者各自的思想、文化资源不论,一定意义上,实际均一本于 此基本职业特征,或反映了这一基本职业特征。
就此而言,二十世纪最后几年间出现于中国法学论坛,而被命名为涵义非常暖昧的“ 保守主义”思潮的理论取向,是第五代法学家群体学思渐精、法意趋于成熟,特别是经 由在“东西文化”中辗转反侧的精神炼狱后,逐渐表现出来的“文化意识的觉醒”,是 法理法意中觉醒与张扬的中国文明或中国文化意识。一句话,是现代中国文明法律智慧 的体现。实际上,它反映了中国法律从业者从借助他人眼睛看待中国问题,到从中国本 身的事实与规则、法制与法意和人生与人心来省视这一切的一个新的努力的开端。正像 有人在论及近世西方民法法系国家的法典化运动原因时所指出的,“当罗马法已经明显 地不能满足当下社会的需要,并且(这一现象已然)引致人们的高度关注,关于本地法律 ——早已存在的法律——的书籍就会应运而生。……而成功的法典化,至少就其形式而 言,必得等到本地法制成型才可实现。”(注:Alan Watson,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Private Law.pp.258—259.)转借此意,或许可以说,同样,秉持此种理论取 向的,一如世纪初年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多数都对西方社会和文化具有一定的了解,其 中一些益且对于西方社会有过较长时期的实地观察与参与。作为对于西方“文化洗脑” 所表现出来的诸多不良后果的意识、警觉和忧虑,实际上,他们所倡导的乃是中国的法 意与学思的平等言说权利。而且,此刻的言说,较少情绪色彩,更加平和而理性,视野 也更为宏阔。“保守主义”云乎哉!
五、价值性与世俗信仰
在法律的逻辑品质背后,隐含着的是法律的伦理品质,而逻辑品质之所以能够换形为 逻辑力量,正在于其秉有道义力量。换言之,法律的规则性及其本身作为一种规则体系 ,意味着法律同时必将是一种意义体系。法律的实质理性意义上的“价值性”,意即在 此。正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对于其所含蕴的逻辑与价值的“信还是不信”的问题。而 保有对于法律的“信”即秉持法律信仰,恰恰是法律文明秩序下,法律从业者的基本职 业伦理。
那么,“法律信仰”或者“信仰法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于整个国民来说,信仰 法律,意味着相信法律应当是、可能是、并且正是公平、正义的规则,是我们的内心信 念的忠实表达和外在行为的最佳框范;信仰法律,意味着认可法律作为规则对于事实的 组织和网罗,即对于自己的生活的描述与厘定的准确与允当,因而,法律成为一种自然 的规范,也就是生活本身天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信仰法律,意味着明了法律是维系人 世生活、达成理想的人间秩序所可能有的较不坏的选择,而为人类对于自身生活善加调 治的人类德性的展现,阳光下善的光辉;信仰法律,意味着坚信法律的伟大力量,循沿 法律规则,失衡的人间秩序必将复归均衡,因而,法律不过是将对于行为与结果间的特 定因果关系及其预测呈现于世,使得人们对于自己的举止作出一定的预期,从而妥贴措 置;信仰法律,还必然意味着时时以天理人情省视俗世的规则,对一切恶法深恶痛绝, 时刻准备着为法律而斗争。
这里,可以看出,当我们使用“信仰法律”时,是指对于法律作出一种“信仰的姿态 ”。也就是说,经由拟制性地认定法律实际当然具有——其实很多时候应当具有——的 种种规则的属性,赋予法律以这些属性,从而也就是要求法律具备这些属性;同时,并 确信此种“信仰”状态为全体居民所共享,成为全体居民心灵生活的一部分。之所以很 多时候法律信仰乃是对于法律作出的一种“信仰的姿态”,就在于它意味着确信法律是 被广泛而普遍地为同一法律辖治下的居民所信奉而遵循着,或者说,是对法律获得广泛 而普遍的遵循这一状态的拟制性确信,也就是对于法律的普遍有效性之拟制性确信不移 ,从而,便是在赋予法律以普遍有效性。“拟制性”意味着“假戏真做”,做得认真, 做得久了,便成“真戏真做”,从而确信不移。因此,这种确信,一方面促使自己循随 同一方队的同一鼓令迈步,同时,并会促使他们对于别人的行为产生同样的期待。而由 于期待落空所造成的失落、不协调与异化感,必会催生出实现这种期待的期待。这里, 便也就埋伏了将法意与人心、人心与人生一线勾连的契机。在此,经由主体的“信仰” 活动,法律的应然与实然的分裂不再具有绝然对立的意义。实际上,这种“信仰”活动 促进法律的实然不断接近法律的应然理想状态。从而,法律由此获得,或者说,最终被 赋予普遍有效性与“合法性”。马克斯·韦伯所谓“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 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因为,“对个别人或若干人强令的服从,是以对强令者或者强 令者们具有某一种意义上合法的统治权力的信仰为前提的。”(注: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第1卷,第157页,转引自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 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用在此处,亦称恰切。
需予注意的是,与对于超验实体的神学信仰相比,法律信仰是以相信法律是我们生活 的恰切的规则,并确知其(实在法)永远有待完善为特征的。而对于超验实体的神学信仰 所设定的信仰对象,则是绝对完美无缺的,是超越因素本身。对于法律的此种认识论定 位,将法律描述为一种人世规则和人间秩序,不仅不曾阻隔其超越性质,恰恰相反,此 种批判性省视,是法律与诸如天道、天理或“自然法”等超越性因素之间得以沟通的必 经环节。前文说信仰法律必然意味着时时以天理人情省视俗世的规则,其意在此。因而 ,对于超验实体的神学信仰是不容怀疑的,而法律信仰则以“批判性省视”为前提。
的确,为什么法律必须具备“信仰”要素?为什么“信仰”要素是法律本身获得合法性 的条件或前提之一,并且是法律从业者应有的职业伦理,也是生活在现代“法律文明秩 序”下的一切居民应有的心灵状态?凡此诸端,确乎耐人寻味。尤其是在经过发端西洋 ,而席卷全球的所谓“除魅”洗礼的今日,不管承认与否,事实上“信仰”要素依然为 法律所不可缺,不得不令人扪心深思。我们知道,所谓的“除魅”是“现代化”过程的 自然要求,一言以蔽之,它是人类从“存天理,灭人欲”的好高骛远,滑落至承认人只 能是人,从而秉持常识、常理与常情打理日子的彻底的世俗化与功利化,而这一切悉秉 理性为之,因而,伴随着世俗化与功利化的便是所谓的“理性化”。揆诸史实,这一过 程正好是现代民族国家逐渐成型的历史,是首先发端于西洋的人类从神只、家族等“原 始”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并把人变成具体的“个人”,将追求私利最大化予以合法 化的历史。正是在此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两个新的现象。一是人们在摆脱了上述传统依 附关系之后,又不得不结成新的依附关系,即个人于不自觉间成为民族国家这一新的政 治化社团的一分子,而且是无所逃脱的一分子,舍此无法自我定位;二是对于个人私利 的最大化的一切追求活动,不仅是在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单元内进行的,而且还仰赖于民 族国家的政治保护。二十世纪中期以降,随着所谓全球化的加速推展,秉持主权的民族 国家作为其国族利益的合法代言人的国际身份不仅没有削弱,相反,事实上反倒愈益强 化了。从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单元框架之内来看,则政治保护的最为流行的方式,或许也 是最佳的方式,历几百年来的自然选择,乃是法律保护。即从“宗教文明秩序”或“道 德文明秩序”蜕转为“法律文明秩序”。由此,随着民族国家成为政治忠诚的核心与顶 点,法律信仰乃成这一忠诚的世俗表达。也就是说,法律信仰体现了对于以民族国家为 形式的政治忠诚,进而言之,最终体现了对于这一政治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正因为此, 法律信仰因而成为一种“世俗的”信仰,而归根究底,乃是一种法律的文化认同,或者 说,是文化认同的法律表现。
由此,它牵扯到不同文化形态对于信仰的不同表达方式问题,或者说,其不同的超越 之道。我们知道,“除魅”过程在西方法律领域的结果不仅是造成了法的神性因素的剥 离,而且伴随着法律与道德和习俗的日渐离析,造成了法的历史之维与伦理之维的弱化 甚至丧失(注:哈罗德·伯尔曼:《展望新千年的世界法律》,林立伟译,《二十一世 纪》(香港)1999年第4期。)。如果说在近世西方,这一“现代性”的结果是以“理性” 、“科学”和“个体”等主义开道的话,那么,就中国而言,法律的超越因素的弱化甚 至丧失,乃是基于百年来的全部的法律现代化过程很大程度上乃是对于西法的引进和移 植运动这一历史事实。因此,对于今日中国的法制与法意来说,历史之维与道德之维非 惟弱化或丧失的问题,而是仍然有待继续从新建立,实现移植而来的规则及其意义与本 土的事实—规则及其意义的粘连和整合,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真正反映当今中国人的人 生与人心,堪称当今中国人世生活的规则的现代汉语法律文明。
中国式的法律智慧中的超越之道,具有不同于其他文明类型的特点。笔者曾就此做过 初步论述(注:参见拙集《说法·活法·立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275—297 页。)。总括其意,即在中国法律传统中,法律与其神圣性超越源泉的沟通不是以西方 式的自然法与实在法式的尖锐对立,毋宁天理、人情与国法的交缠互动来实现的。天理 、人情与国法是一个从超验世界向经验世界的递次过渡,经由人类的知性、理性和德性 ,人世规则、人间秩序与超越意义、神圣源泉既泾渭分明、神人永不可混淆,又不即不 离、若即若离,神、人永远存在沟通的可能,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遂联为一体,打成一 片。前文曾谓法律信仰以“批判性省视”为前提,意味着时时以天理人情省视俗世的规 则,对一切恶法深恶痛绝,时刻准备着为法律而斗争,即为这一理路的自然展开。其间 ,于应对日常生活的细琐世俗事务中一步步体会和践履的工夫与功夫,将超越意义、神 圣源泉落实为人人得可领略的生活的常识、常理和常情。因而,人情中即有天理,天理 不外乎人情却又超越乎人情,法律遂为人生之凭依与人心之镜像。而总括而言,法律不 外乎是使“事实走得通”,把事情办成,让日子过得下去的人世规则与人间秩序。信仰 ,坚定的信仰,自在其中,本无需大张旗鼓地嚷嚷。正是人情中即有天理,天理不外乎 人情却又超越乎人情的这种中国法律中世俗层面与超越因素的交缠互动格局,使得法律 信仰能够动员人性中的无限力量,而使法律成为一种世俗信仰的对象,饱含着人类对于 人间秩序的情感寄托和信念诉求。在《餐馆物语》中,大卫·马梅曾经写道:“如果你 将宗教中的信仰(faith)排除,那么,你就是在糟蹋星期日的早晨;如果你将法律中的 信仰(believe)排除,你所有的只是讼累;而如果你取消了庆典中的仪式,你所有的不 过是‘总统日’。”(注:David Mamet,Writings in Restaurant,转引自Sanford
Levinson,Constitutional Faith(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卷首题词页。)的确,若问“法律如何信仰”?则大体如斯。
结语
本文探讨了法律的实质理性的基本内涵,或者说经由此一探讨,设定了法律的实质理 性以如此内涵。这种运思过程本身,即生动地说明了所谓法的理性,不论实质理性还是 形式理性,不仅是法之应然“固有的”,同时更是经由法律信仰等等因素而被“赋予的 ”,也就是“拟制的”。拟制性地“确信”其之具有如此理性内涵,正反映了对象本身 “客观上”具备这些属性。反过来说,正因为凡此属性均为对象本身所秉有,不论是现 实的还是现实可能的,因而,拟制性的“确信”乃是对于其客观属性的发掘与发现、展 示和宣谕。也正是此间这一内外交错情形,使得法律具备了自己的逻辑品质、技术品质 乃至于伦理品质,而适成所谓法律或法。
就其内在关联来看,自规则性而至价值性,是一个渐次递升的理性位阶,并藉诸价值 性而通达“法的价值”,亦即法的伦理品质论域。与此相应,自规则意识而世俗信仰, 同样是一个法律从业者的职业化理的渐次递升的实践理性位阶。凡此构成了法律与道德 、宗教既相区别,又血脉联通的人世生活景观。而保守性与时代性、现实性与价值性两 两相对共存于法律,规则意识必受世俗信仰的审视,正如守成的态度必与时代的观点难 避龃龉,正说明了法律内部与法律理性自身存在着巨大的紧张。这种紧张非但无损于法 律之为一种人世生活的规则性存在,相反,成为法律自我发展与完善的推进装置。凡人 类精神存在即意味着存在本身即为煎熬,法律及其理性的存在便意味着它们永远有待完 善而又潜存着无限趋善的可能。正是在此,法律、法律理性和人世生活,遂有了“意义 ”。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包括实质理性在内的法律理性,不仅是一种职业理性,更是一 种实践理性。其为职业理性,在于首先它是法律从业者应有或实有的职业伦理的直接源 泉,并构成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类似于摩西十戒般的“天条”;其为实践理性,则是因 为它是法律在解决无所逃避的现实生活实际问题过程中渐次形成的,因而,其在担当以 规则来网罗和组织事实,从而妥贴安置事实这一基本任务时,具体表现为能够将事情办 成,从而使日常生活过得下去为最低也是最高的要求的。正是为了适应这一要求,法律 自我衍生出上述种种内在属性和职业伦理要求,以满足将事情办成,使日子过得下去这 一社会功用和价值期待。
在著名的《法理学》中,约翰·W·萨茫德爵士在论及“法理学的价值”时曾经指出, “有关新的法律问题的答案,只可能通过对于当下的社会需求的思考,而非一味沉湎于 过往的凝练的智慧中,才能找到。”(注:Salmond,On Jurisprudence.London:Sweet
and Maxwell,1966,12[th]ed.,p.5.)转借这一语式,则宏观而言,不仅法律职业与法律 智慧的兴起源于“当下的社会需求”,而且,具体来说,法律理性的提炼与弘富,同样 是“当下的社会需求”的产物,也就是应对当下的生计与生存的结果。“当下”各不相 同,法律理性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与地域特征。正是作为事实存在的地域性社会生活本 身,对于使得生活得以维系和延续的其内在规则性的需求,促成了法律和法律职业的诞 生;也正是对于此种规则性的合理性的追求,使得法律理性成为法律及其仆人——法律 从业者——的精神内涵与技术禀赋。此处所谓的合理性,也就是合目的性,即对于人类 追求合理而惬意的理想人世生活这一愿望的顺应和踔厉。从而,法律理性不仅是“当下 的社会需求”砥砺成型的结果,而且,它反过来成为法律的伦理品质,进而意味着在“ 法律文明秩序”格局中,它径直成为生活本身的向度之一。也就因此,法律从业者不仅 是法律的仆人,而且是法律的守护者,进而意味着他们担负着人世生活的守夜人的角色 。如果说生活本身涵育出规则,那么,法律从业者就是规则的接生者;如果说不是别的 ,正是法律理性,使得法律适成法律或法,那么,不是别的,正是法律理性,特别是其 逻辑品质,将法律从业者整合成为一个职业与志业共同体,完成了仆人、守护者和守夜 人的三位一体。
2001年9月初稿,2002年9月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