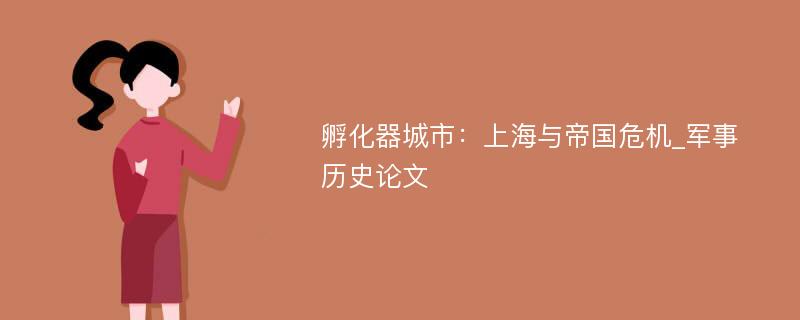
孵化器之城:上海与帝国危机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孵化器论文,帝国论文,之城论文,上海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上海巡捕的辖区总是非常繁忙。街道拥挤,到处是黄包车、小推车、摩托车、电车,和经常将它们淹没的步行者、小贩、闲逛者、游手好闲者、不守交通规则横穿马路者与街道行人。1941年这座城市的人口将近400万,都在忙碌着,就像当初的巴别塔之城一样人声嘈杂。根据1935年的一次官方统计,这座城市至少有52种语言,这还不包括那些没有国籍人的语言,以及名声不太好却很管用的洋泾浜英语。监狱爆满,法庭人满为患。②日程总是满满的。负责管辖公共租界的欧洲国家警察的便携日记本上的各种纪念日和节日有满满的三页。1943年的版本中出现了一些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本来不包括的一些节日,因为这代表了1941年12月8日占领了该座城市的日本的所有节日,而此前的版本已经可以看到其中的许多节日。③这不是一本提醒一位上海警察应该记住的有趣节日的备忘录,也不是一本多文化指南。这是一个安全备忘录,提醒某天是事件的爆发点,巡捕的假期将被取消,值班人员将翻番。这个人满为患的城市的这个日历充满了麻烦。那是召唤巡捕出动,挥舞警棍,设置路障和检查沙包,为发生最坏的情况做准备。这些日期通常记录着充满争议的过去,预示着充满争议的未来,因为日子总是周而复始,不可抗拒。
这些日子对上海巡捕的实际工作意味着什么?让我们以日本占领上海之前的8月9日为例。1940年8月6日,上海工部局巡捕房制服股(uniform branch)的捕头传阅一本六页的、应对1937年8月9日中日冲突爆发三周年的“预防措施”纲要。5日晚上,随着实施宵禁,所有的人员在防暴队的支援下,突击茶馆、旅馆和酒店,拘留“所有已知的嫌疑人,闲散人员”,“那些不能给出满意解释……他们为何出现在公共租界的人”。所有的人将被拘留,等待高级警官决定是否释放他们。五座桥被关闭;21个街道路口设置好路障;巡捕和军人检查另外4座桥上的交通。万国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作为“特别”志愿警察被动员。五国的国防部队在主要街道巡逻。那些成为炸弹袭击目标的报馆设立了特别岗哨。④战前,在这些纪念日之前进行动员已经成为公共租界生活的常规特征了。这当然反映了1937年之后上海公共租界的非正常状态——已经成为一个被日本人控制的领土所包围的尚未被征服的孤岛。不过,上海公共租界照常运转,照常运转意味着要应对许多不平静的日子。
那时的上海既像任何一个国际大都市,又不像任何其他国际大都市。它是一个“复写”的城市,被不同的司法结构和管理机构所重叠,是一个到处是边界的城市。城市多样性本身并不奇怪。1920年的纽约市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外国出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个比例还要高。不过,这些城市的居民都受一个法律制度的管辖,而上海有多个层次的法律。现在,这个狭小城市不像任何城市,在这个相对很小却很拥挤的中国舞台,每年上演了数量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的帝国和共和国以及它们的敌人的仪式性生活的场所。这通常被当成是四海一家的证据:友好的国际交往,愉快地以多种语言相处,来自不同社群的外交官和领事们以及名流忙于参加彼此的展览和游行,满口陈词滥调,举杯为彼此的友好和好运干杯。这里就是一个其乐融融的中国微型联合国,预示着世界大同的到来。⑤不过,这种国家的表演常常具有竞争性,而有时有敌对或革命的目的。上海是中国人、印度人、越南人和朝鲜人反帝活动的场所,也是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共产第三国际以及俄国纳粹党分支活动的场所。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它是“日本共产党形成的坩埚”⑥,活动分子密谋,学生学习,间谍躲藏,而巡捕监视和搜查。
上海的这种特殊性孕育了众多的活动及反动,并为此提供了场所。本文分析这个城市所孕育的五个不同层面的活动,探讨它们如何互相作用,并略述它们产生的后果。在此之前文章概述了上海以及它的公开和秘密政治生活形成的三个主要因素:空间、法律和时间,对于后者更确切地说是日历。本文揭示了将这座城市分割开来的物理和行政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产生的限制和创造的机会——可能没有哪个地方像上海这样清楚地、多语言地——生动描绘了民族主义和这个城市如何交叉。它不是一个熔炉,却产生强烈的热,改变了各种民族主义和它们敌人的目标与影响范围。
在20世纪,对中国人和世界而言,上海越来越是一个观念,不过它同时也是一个(破碎的)物理场所,一个节点,一个矢量。不过,它还是一个空间。在基本层面,上海是一座城市,并且一直是唯一的一座城市。尽管上海行政地位很低,却是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南京条约》于1843年开放了对外贸易。由于当地人拒绝将房屋租给新来的外国人,因此在老城墙东北的河边划出了一块英国人居留地。不久,法国人也到来,并获得了自己的居留地。英国的居留地不断扩大,与美国的合并,并成为“公共租界”。这个租界不属于任何一个外国管理,而是由一个选举产生的工部局来管理。工部局的代表权根据国别分配(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各占多少)。法国居留地则另搞一套,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成为法国帝国的正式一部分,由印度支那总督管辖,总领事和一个顾问委员会来管理租界。⑦
老城和城外的新郊区由形式不断变化的、分割比较厉害的行政机关管理,直到1927年新成立的国民党民国政府设立了单一的大上海特别市(Special Municipality of Greater Shanghai)。此举的目的是争取对外国租界的控制权,并为接收它们做准备。⑧这两个外国租界的主要特点是它们不断扩大,正式成为比原来的小地点大很多,并且还渴望扩得更大。它们购买租界以外的土地,铺设道路,并享有警察等权力,企图进一步将它们和邻近的土地并入租界。⑨
上海刚开埠时只是一个地位并不突出的一般港口,却明显地拥有更大的国际贸易的潜力。外贸、战争和叛乱改变了这一切。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清朝难民进入租界,商业的重要部分转向为这些新社区服务,这里租金丰厚,租住时间长。这正是房地产投机者所梦想的。在上海近代史中,难民的涌入从没间断:他们来自上海郊区和长江三角洲。20世纪20年代,难民来自俄罗斯,30年代来自欧洲。战争一如既往地促成了上海的经济繁荣,也遭遇了一次或两次萧条。⑩上海成为19世纪中国的新的中心以及20世纪中国的舞台,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它进行重塑。(11)该党很自然地成立于上海。这里是中国工业、金融、教育和文化中心,它吸引了来此读书的学生,吸引了劳工,1895年后吸引的是工人。这里也是那些到海外去求学的人离开之前和回来之后就业时经常逗留的地方。这里也是中国的出版业中心,诞生了报纸、杂志、教科书和翻译书籍。随着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上海再一次繁荣。1912~1920年之间,上海的国际贸易值翻了一番,制造能力大大提高。(12)1927年之后,国民政府的行政首都建立在南京,距离上的接近让政客和官僚很方便到上海度假。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也梦想到这里来。
这座繁忙的城市由三个行政当局来管理。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上海有5个有时甚至是6个不同的警察管辖区,如果算上江海关警察(Maritime Customs River Police)管辖的海港是7个。(13)其中的两个区域因主权曾发生过血腥的、至少是激烈的争议,因为几个国家声称拥有这些区域,因而有警察权。三个市政委员会都有自己的地方法规和附则。不过,它们在一个城市中的外国和中国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显然,这存在巨大的游戏空间,很容易利用两个区域之间不同的政治气候,在“边境”之间跳来跳去。尽管各国的警察协商了“当即追回(hot—pursuit)”协议,但是这却滋生了一种充满诡计的选择定居地和重新选择定居地的文化,而缺乏统一的行政管辖权,当然也催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呼风唤雨的黑社会。(14)战争带来了进一步变化和形成了新区。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后,上海的战事席卷了北部的中国管辖区域,日军控制了公共租界的北部和东部区域,多数的日本人都住在这里。
我们还必须提到上海的河流,特别是河边的外滩,也就是它的堤岸,它被看成是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也是一个重要的纪念场所和相当于一个公共场所。外滩之所以重要,原因是这座城市实际上缺乏其他公共空间。上海没有广场和公共草地。尽管有私人花园,但是只有外滩可以充当一个附近的公共场所。因此,外滩是一个展示的场所,一个介绍的场所,因而也是一个持续竞争的场所。常常在外滩对面的水面上、黄浦江的下游停泊着列强的战舰,其中还有鸦片船、茶叶帆船和其他商船、内河炮艇,英国的中国舰队(British China Station)或其他欧洲的亚洲舰队。上海的空间特性不仅形成了它的地方政治,而且为各种国际政治和来源于亚洲和欧洲等其他地方政治的上演提供了场所。
法,法律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空间很重要。不过,与这些除非在紧急情况下才围起来或设置出入口的自然边界和畸形物重叠的是多重管辖权,它们在高峰时达到20种左右。(15)因此至少有20套不同的法律和市政法规在这里施用。为何会这样?第一,这两个区域不是殖民地。这里的中国居民不是殖民地臣民。在某种程度上,随着时间和方式的变化,中国公民通常在整个上海都由中国的法律管辖。当然,有时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被外国当局给予了一种保护。为了保护它的自治权,同时也因为对某些当时的政治思想抱有同情心,公共租界成为中国居民的缓冲地带。他们可以从这种没有多少法律依据的准身份受益,为中国的活动提供空间,不过这种空间很不保险,外国当局随时可能变脸。(16)
来自那些得到承认的列强——也就是那些与中国有正式条约的国家的外国人是他们领事的臣民,无论他们生活或工作在哪个区域,或被逮捕。(17)许多人在这个区工作,在另一个区居住。巡捕的工作包括,某人在某个条约国被捕后毫不耽搁地通知相关国家的领事机关。他的笔记本里有这些领事机构的地址。(18)并不是所有外国人都有这种地位,而是居住在这个城市中的人数最多的条约国的公民才有(俄罗斯人除外)。这为法律双方中精明的商人提供了护身符,不过更显然为犯罪提供了机会,为玩弄治外法权提供了机会。一家在租界路上的赌场可能是西班牙人所有,法国人租赁,美国人转包,墨西哥人管理,俄国人、西班牙人、英国人和中国人做员工,占用律师资源和妨碍巡捕有效执法(这看来有点荒谬,但实际上有据可查(19))。不过一家中文报纸同样在美国领馆注册,因为由一位美国公民出版足以部分规避中国的新闻法律,防止警察的检查。
中国境内的这个条约体系是一个奇怪却又真实的条约、协议、草案和优先权的体系,从自然和法律上创造了新空间,一个有着许多不确定性的中国边疆区域,因为条约的文字不能考虑到中国沿海世界的所有新情况。在大多数外国人眼里,条约的优点不在于它们在同声传译的纸张上设计了什么,而是它们没有提到什么。模糊就是力量。
赌场的事例表明,尽管可以很清楚地定义英国人或荷兰人,但是英国人(在租界)的存在,和日本人或法国人一样无论是从设计或机遇来说都是多国的。英国人将锡克教徒带到城内做警察,信德商人也来了,塞法迪人早就从孟买来到这里。(20)这些英国人包括东南亚的华人、澳大利亚和西印度华人,他们既是大英疆土的臣民又是华人。法国人带来了越南人。在中国的“日本人”可能是朝鲜人甚至是中国人。国籍身份也不固定。国籍有可能出于实际需要被延长;也可能被某些个人或团体放弃。国籍也可能被人假冒,通常是被在20世纪初在这里做妓女的东欧妇女所使用,原因是上海的外国人喜欢妓院里的“美国女孩”。由于出现了这样的丑闻,美国当局最终进一步澄清事实,并限制那些真正美国公民的美国身份。(21)领事权在某些情况下不仅是设立一位有法律课本的领事。日本人在中国发展了一种成熟的领事警察,在城市中设立了一个大型分遣队,从而又增加了一层警察权。(22)这些法律管辖权和实际的结构有时会互相作用,并可能导致冲突。它们对上海任何部分的管理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挑战,也提供了许多独特的机会。
我们回过头来看日历。上海居民虽然生活在一个城市中,却受不同法律的管辖。有各种指南和手册(vade Mecums)帮他们指点迷津。尽管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们实际上按不同的日历生活。中国的民国政府从1911年开始纪年,因此1943年就是民国32年,除此之外,它以格里历(西历)来纪日:12个月和52周。这是一个有关现代化和自觉的民族现代化的问题。实际上,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使用两套历法,其中的农历是非法的,在1928年之后正式被“现代的”西方的阳历所取代。上海巡捕房检查公众使用旧历法,执行民国政府的法律,没收出版商的(非法)日历。(23)这种禁止的目的是一种自己制定的“现代化”中国文化的计划。1911年后,民国政府为了在中国人中培养共和思想,试图摒弃农历,因为后者被认为与20世纪的中国不合时宜。(24)不过,农历仍决定了每年大部分的生活和商业周期——节日还债,给员工发红包,放假。民国的第一位总统在1912年1月1日正式就职,故意挑选了一个重要的外国日期来纪念新中国秩序的开始这样一个重大事件。(25)
西历年本身已经成为许多日历的来源。(26)每一个正式活跃在上海的外国带来了它的语言和节日:王室生日、圣徒纪念日、共和国纪念日和国庆日。不过,新的中国政府当时也通过日历来刻意为民族主义行为划出这样一个地盘。(27)它从增加对国外的共和民事文化的理解和在自己的家门口展示它为起点,这从很多方面来看也是共和计划中最显而易见的成功之处之一。它的敌人通过每一枪、每一次轰炸或侵略“火上浇油”,因为他们在这个民族主义的日历上标红了新的日期,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日期不仅是纪念日而是行动的场所。
1928年,也就是新的中国政府下令使用西历的那一年,政府也开始设立官方的全国性节日,其中多数是“国耻日”,实际上多达26个,只有12月份没有。5月份对警察来说是最繁忙、最残酷的月份,1日、3日、5日、7日、9日和30日都被占满了。(28)因此官方的民族主义被这些西历中的日期,而不是被农历中的日期所标记。每年有了一个新的政治节奏,特别是在中国的城市中可以感觉到。
国耻日被认为是引发自觉活动的日子。只要有一个公共节日,就可能有隐蔽的事件。发生在这些日子中的事件可能是由政党领导的或者是民粹主义活动的结果。届时将举行会议,唱歌和表演戏剧,散发传单。通常人们总担心这些节日被“激进元素”所破坏,游行者行进到纪念地点,即使有的纪念地点设立在公共租界之外,游行也会象征性地通过穿过外国控制的街道来拉开帷幕。巡捕制定了一套通用的“纪念日”例行程序,或多或少作为前期的情报或更大的政治情况,这是有必要的。(29)
因此,空间的简单和空间的复杂以及法律地位的简单与复杂的并行,在这个华东城市创造了机会。现代化的计划为弄懂政治性年份提供了一个框架,实际上也为其成为恰当的政治性年份提供了框架。只要新的共和政府号召过的,就有人响应,纪念那些日子,等待这些纪念日,等待开始行动。隐藏在这些日子之间或后面的是其他日子,被遗忘的屠杀,秘密的国庆日。穿越这三者的当然是上海的人民,1935年人口普查中的52国的国民。这种多样性本身并不是舶来品,而这个城市的经济力量被不同的国家集团所把持的事实也是这样。不过,上海的情况有不同之处:首先,国籍和通过控制市政管理的正式权力的联系,即市政政治的国际化;其次,正式的条约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上海安置非大都市的国民,以削弱他们的对手;第三,上海作为难民避风港的功能及其在不同的区域以不同方式运行的功能。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警察日历中的五个层面的活动:殖民者的民族主义、“世界主义”(或帝国内部的团结)、帝国主义和其他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的活动。
第一个层面虽然似乎最狭隘,并最不引起注意,却与外部环境密切联系,并隐藏在所有上海其他的发展中。这是上海本地殖民者自发的民族主义的发展,一种“上海人”的身份,一种英国殖民者或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变种,与那些罗德西亚、纳塔尔和英帝国自治领属的民族主义更相似。他们是说英语的亲英分子,有自治野心。这种观点认为,上海应该是一个自由城市,一个自治城市共和国,不受英国或其他外交限制。与其他多数条约口岸不同,上海租界不受领事管辖。持这种观点的人积极维护租界的主权不受中国政府的法规管辖,也不受口岸领事的管辖。这类人只有在危机时刻才向英国政府救助,平常则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行事。这看起来有点荒谬,不过外国领事对董事会的控制从立法上来说较弱,并且规定不怎么明确。董事会从自己的角度,根据其外国选民的意愿颁布法令。这是对条约没有准确执行的结果,这样的梦想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都为当地的外国当政者和利益所追求。总体来说,只要公共租界市政当局将货物运往英帝国,维持了稳定,英帝国容忍它的地方特殊性和不正常,对它的浮华和自作主张不以为然,任其放任。但是如果它没能做到这一点,最明显的如1925年5月,警察开枪打死了12名示威者,引发全国范围的反英反帝国主义运动,英国政府就试图介入。(30)
这种身份有一定明确范围。尽管它是“世界主义”的主要鼓噪者,并且在其他国家的人当中有支持者,但是他们基本都说英语。它展示了一个新兴的说英语的殖民地国家的所有特征。这种雄心勃勃的地方主义试图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利益共同体上,他们纠合了许多中国和外国在当地的精英,综合一部分中国人的利益形成它的自治观点。虽然这种事业永远不可能成功,但是却被其他国家的集团所追捧,因为他们的被边缘化的身份让他们非常脆弱,特别是俄罗斯人。
这是一种“白人”民族主义,根植于一种狭隘的利益共同体,不过正如在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种族和帝国团结是上海:外国机构的一部分,这就是我要阐述的第二个层面。“血浓于水,”美国海军准将乔西亚·塔特纳尔(Josiah Tatatnall)不带个人偏见地写下了这句著名的话,为自己积极而中立的介入1859年中英两国军队在大沽口炮台的战争辩护。(31)当普法战争的消息在1870年8月10日传到这座城市后,主要的英文报纸的反应清楚地宣布:
在上周一场欧洲大战的消息将租界分隔之前,上海很少有人会充分知道最近的事件如何将他们和国内思想与行动分隔开,以及这种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情绪是多么强烈。这种半惊奇半不信的感情一直伴随在人们彼此之间的日常交往中,在其他情况下听到这种消息,他们会处于一种你死我活的仇恨中,这可能是上海不同于其他地方之处;人们的意识也是如此,在这个文明的尽头,在没有丧失爱国主义的情况下,意识被其他目的和方法所取代。
“最近的事件”指的是当年6月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公民在天津被杀,上海的“特别的”爱国主义常常被谈论。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它是大都会标准的一种“扭曲的回声”,但同时也说明它是一种殖民地标准,这种标准常常与“祖国的方式”不同。(32)不过,上海的法国人在当年的8月15日仍兴致勃勃地庆祝拿破仑日,显然是受到了战争消息的鼓舞,而作为回应,租界的德国人在第二年3月庆祝了皇帝的生日,并举办了一个展示胜利的派对。但是在官方层面,团结得到了维护,尽管受到了考验。尽管法国领事赞颂“法国的荣光”,但是指出联结“各社区和各国家”——欧洲白人社区的关系应该得到维护。他颇有说服力地引述上海的英国法官的呼吁,让居民记住,“尽管你们可能是敌对政府的子民,但是你们彼此的关系具有一种更亲密和神圣的特征。”这就是“白人”和基督教文明的“神圣特征”。(33)
上海外国人的公共大都会生活从许多方面来说是一种必要的止痛剂。它实行一种夸张的世界主义,目的是以多种方式限制对这个城市中占人口绝大多数比例的中国人造成的冒犯和牺牲(尽管这在政策讨论中有时是一个明确的考虑)。实际上,上海多数情况都是遵从贝塞尔·弗尔蒂(Basil Fawlty)的明智的格言,不提及战争,至少不公开提及正进行的战争。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里(译者注:中国东北),巡捕和当地法律附则被用来压制中文报纸讨论日本人(非常多的出版物是以外国控制的利益登记)。(34)1938年之后,它也压制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难民批评纳粹政权,“鉴于公共租界的国际特征。”(35)实际上它只执行最有限的地方公共事件。最著名的是1893年庆祝(上海开埠)二十五周年庆典(应是作者有误,1893年应是上海开埠五十周年庆典——译者注)。(36)公共租界的公共活动常常仅限于每年的游行和检阅志愿部队,以及葬礼。万国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是一个有统一指挥的“世界主义的”武装组织,不过它是按国籍来组织的,每个队都穿自己国家的制服。(37)在面临危机或遭灾之后社群团结一致。1896年一艘德国军舰“伊力达斯”号(SMS Iltis)刚刚从上海驶出,在山东海岸沉没;在上海一块由英国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捐赠的河岸边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座纪念碑。虽然它是一个德国的纪念碑,并且后来被赋予德国社区的特殊功能(在英雄日)服务于德国的参观者,但是它的揭幕显示了公共、多国和社区的团结。(38)
没有一个以年为周期的对上海狭隘世界主义身份的展示。总体来说,上海的外国人社群在他们汇集在上海跑马总会(Shanghai Race Club)举行春秋运动会时,最能显示他们的世界主义精神和利益。此时他们说草根的最简单的通用语。此时他们无疑很快乐。
第三个层次已经隐约提到——在一个国际城市中表现国家身份。这有多种因素。首先,将殖民据点整合到更大的殖民体系中常常对地方利益很重要,地方利益需要至少从表面上让本地不正常的东西正常化,确保外交官(地方利益常常对他们不信任)不要忘记他们任务的重要性。王室或拥护共和的名流的来访是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方式。访问上海的有爱丁堡公爵(1869年)、俄罗斯阿列克谢大公(1872)、干诺公爵(1890)、普鲁士亨利王子(1898)、日本伏见宫贞爱亲王(1907),以及前美国总统格兰特将军(1879)。外国人社区盛装全体出动,游行、致敬、岸边点燃灯笼、宴会和讲演。有音乐、欢呼声,常常有烟花,并常常有一些纪念碑在外滩揭幕或奠基。干诺公爵为英国外交官巴夏礼(Harry Parkes)的纪念碑揭幕。亨利王子为“伊力达斯”号的纪念碑揭幕。(39)一些不那么著名的人到访也很重要——例如,查尔斯·戈登1880年的到访。这些公共事件当然不仅是关心自己的借口;也不仅仅是为在文明的尽头的生活增加一点乐趣和色彩,它们是为了更广泛地传递一个信息:上海在英国、德国、法国或其他世界,也在当地的地位和意义。
更加常规的是上海的每一年都有各国侨民庆祝王室生日和国家节日的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7月4日和14日,以及规模更小一点的英国人的帝国日(1903年登基之后)。战舰经常进入港口运送海军陆战队员,壮大这里的人数,增加一些军事色彩和风格。皇家纪念日和加冕用节日来纪念,而王室人员的去世则更加庄严。一本当地画刊《上海社交》(Social Shanghai)的1913年8月期就显示了这样的日常生活。以下是7月4日和14日的报道,后者有一个火炬游行和烟花燃放,此前6月纪念威廉二世皇帝登基25周年的庆典中,外滩的建筑都装上了灯火通明的电灯,还有游行和感恩节礼拜活动。(40)这其中显然有竞争的因素在内,这正如万国商团中的武装一样。英国人的游行越轰动,德国人的灯光越明亮,而帝国的对手和清政府官员也更加肯定地得到信息:英国和德国政府(对这个殖民地的)重视。
所有这些已经够频繁了。特别是在新帝国主义阶段,海外的社区试图将它们归入帝国范围,将它们纳入严格的王室和名人出访的范围,帝国思想、仪式和新传统的隐喻的范围很重要。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两次大战的间歇期,共和思想与帝国沙文主义也成为冲突的根源。世界主义的标准被证明不适用。例如,1854年,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建立了万国商团,到20世纪初它已经成为租界防务计划的一个常规的形式,并且具有重要的功能。在1914年到]917年期间,中国是一个中立国家,因此它的租借地也保持中立。(41)德国人和英国人,法国人和奥地利人仍然生活与工作在公共租界。1914年8月8日的《北华捷报》社论说,“没有比在战争的黑暗日子中,决定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尊重彼此的感情,更能体现聚集在上海的不同社群的爱国精神。”“共同利益”是他们“在上海的传统。”(42)在此后的三年中,他们不得不忽视彼此,以最少的接触来找到办法以协商这个城市的街道和商业。这很困难,不仅是因为许多利益,特别是德国和英国的利益紧密交织在一起,他们各自社交的中心都在外滩上,而且因为公共生活的融合。万国商团的德国连队继续训练,在心照不宣的协议下,协约国和中立国家的万国商团武装在上海的不同地方练习彼此射击。在文明的尽头,这些东西也被文明化了。
随着一战的结束,白人团结的梦想开始了。1918年12月1日凌晨,“不明身份者”——主要是法国海军士兵——推倒了“伊力达斯”号的纪念碑,粉碎了这个显示白人世界主义的美好象征。(43)德国俱乐部被中国政府没收,后来变成了一家银行。11月21日,一个精心安排的歪曲世界主义的集会和装饰用来纪念公共租界成立,作为三天庆祝活动内容之一,一个胜利大游行穿越了公共租界。(44)电车被改装成装饰了战胜国旗帜的花车,其中一辆上一只紧握的拳头抓着一个“德国目标”的气球,另一个球上“靠胜利保持自由。”康科迪亚总会(Club Concordia)悬挂着一幅标语“Hun Club”,上面画着一个戴着德军尖顶皮革帽(Picklehaube)的人举着手投降。因此,世界主义在外滩投降了。
战争期间国庆日的公共纪念是其官方的事务,但是当时变得越来越有所指了。这些日常的功能常常服务于他们某个时段,蕴含着政治形势而在公众意识前时隐时现。1927年的国王诞辰日,英国军队在上海跑马场上演了两夜场面壮观的夜间表演操,在表演“1812序曲”(1812 overture)期间,作为表演的一部分“烧毁”了克里姆林宫。在中国革命高潮时的这种反共意味,与两个月后国民党在1927年4月对共产党的血腥清洗,意图都很明显。忠诚和帝国“精神”通常很少通过戏剧方式在帝国日和国王诞辰日来展示:这展示了必胜信念。(45)
欧洲人中逐渐增长的分裂和紧张关系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出口。电影院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当英国士兵游行并火烧克里姆林宫时,意大利和法国军人被动员起来为国家的荣誉受辱而争斗。法国士兵对1928年上演的《万世流芳》(Beau Geste)不满,而法国外交官也在世界各地试图阻止这部片子上映。意大利士兵在1929年1月袭击了另一家电影院,抢走了电影《马路天使》(Street Angel)的拷贝,并将其公开焚毁。(46)半公共的电影院空间成为斗争的场所。不久之后,这个地点发生了一次类似的袭击,袭击者是中国人,针对的是一部反华的电影。(47)电影院在公共租界开辟了一个新的斗争公共空间。
帝国内部冲突的尴尬和问题显然是租界生活和政治的一个特征。外国社区内的反帝活动问题也是我的第四个层面。上海巡捕房特别处(SMP Special Branch)一个文件提到1932年3月(译者注:应为4月)29日日本天皇生日的各种安排。这不完全是一个常规的活动,因为中日在上海的短暂冲突刚刚结束,日本人显然打算将它当成是一个胜利游行,不过除了士兵的人数,这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相当普通的国家事件。(48)日本驻华公使,总领事和高级军官等人聚集在公共租界内虹口公园,部队将由此经过,日本人的社区也参加了;在检阅以101响礼炮结束之后,孩子们将在下午举行比赛。(49)这通常是国庆日做的事情。士兵游行,而孩子们常常有个集会。一位23岁的朝鲜人尹奉吉却搅和了这些事情,他用炸弹袭击了这里的军政要人,炸死2人,重伤多人。作为日本臣民,尹奉吉能够进入公园——中国人在当天以安全为由不准入内——不过,他利用了他在上海的治外法权身份,他和大约1000名在上海的朝鲜居民已经宣誓效忠韩国临时政府。朝鲜临时政府是在三一独立运动失败之后于1919年成立于上海。(50)
要么是出于故意的政策,通过部署人员或鼓励社区移民,要么是通过它提供的吸引力或机会,帝国在上海的存在常常是多国的。这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弱点。殖民地臣民来到这个殖民保护伞下的城市,它也因此成为反殖民活动一个重要和令人担忧的场所。上海至少有一个这样的流亡政府,尽管它们内部自相残杀,存在战略性冲突和矛盾,但是它在中国和东三省发起活动。(51)朝鲜人是这个难民城市中的难民。朝鲜人可以以日本国民的身份进入,可以安全呆在法国租界,但是不可以在公共租界,因为日本在那里有条约权,巡捕房被迫联系日本的领事警察袭扰这些朝鲜人。(52)他或她可以发展同中国人或其他人的关系。上海的巨大人口和行政边界的漏洞意味着整个城市仍可以被穿越,尽管要谨慎一点。在一个东亚中心从事这样活动的优点显而易见——上海是一个离日本领事警察更远的城市,但作为一个人员、思想和出版的十字路口,却并不那么集中。直到1937年,随着日本在更大的上海战役中获胜,朝鲜人才搬出这个城市,与中国中央政府迁往西部。
印度人因不同原因来到上海,他们在这个城市的政治地理也不同。他们在那里大多数是殖民安全人员,而不是难民或经济移民。锡克族人是上海巡捕房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上海更广大的安保部门的重要部分,为个人和公司充当私人保镖。(53)有关薪水和工作条件的骚乱不断发生,1914年之后对英国人而言逐渐严重的问题是卡德尔运动(Ghadr Movement)中的反英民族主义,在一战期间德国的行动给这些革命者帮了忙。1915年一位担任警务处处长的英国人这样抱怨,尽管当年已经在那里逮捕了“许多人”,上海仍是“那些不敢进入英国领土的叛乱煽动者的天堂,”即便如此,他还是反对与英国的印度情报机关进行任何实质性的积极合作,后者于第二年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以保持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国际”特征。(54)八年后,尽管已经引进了试图控制印度人运动的新规章,他抱怨那些公开“有布尔什维克倾向的人……能够在上海发表他们的观点和形成不和与警报……而不受惩罚。”(55)他们可以从中国管辖的闸北安全地这样做,反英的印度青年团(Indian Youth League)就设在那里。
1927年,印度政府在上海设立了一个情报分支机构,与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密切合作,监视印度的民族主义活动者。印度民族主义活动分子与国民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令人担心是有理由的。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特别处在1927年成立了一个印度股,截至1929年夏天它已经积累了1000人的档案,其中125人是“危险分子”,另有1000人的照片。这种严格监视直到1930年才被取消,不过来自印度青年团和其他英国鞭长莫及的团体的威胁一直持续。(56)对英国人而言,锡克族人是拥有殖民权力的人物,在上海的街道上无处不见。中国居民常常是激进的种族主义者,对他们的存在反感。中国民族主义者可以在他们的社群中找到同盟者。锡克族人也是英国人持续焦虑的根源之一。
这两个例子是最突出的,但还有其他例子。越南共产党的特工通过贿赂殖民军队在这个城市活动。正如1900年代“美国女郎”(American girls)迫使美国收紧领事权对国民的管辖一样,同样,朝鲜人和锡克族人的活动吸引了新的帝国机构,促成了新的法规和在帝国内部与帝国之间形成了新的殖民网络。它们自己之间的竞争可能受到限制,同时又被支撑上海公共租界的法律和管辖权的灰色区域所妨碍。有时在他们认为有需要时,他们会采取粗暴和有预谋的行为,不过总的来说被法律限制。
最大的担忧是尽管存在冲突却自鸣得意地称白人团结一致。如果存在亚洲人的团结一致,以及一个反殖民的团结怎么办?当然,的确存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上海是反殖民再好不过的孵化器。1929年3月1日,朝鲜宣布独立十周年之际,300名上海的朝鲜人聚集在法国租界的一个浸礼会教堂。一位巡捕房的朝鲜警探记录了临时政府的领导人如何向他们发表演讲,一位中国台湾的革命者的信也由一位印度青年团成员宣读。信件这样说,“协会的成员希望朝鲜和印度独立,因为我们是境况相同的兄弟。”(57)听众中的一些朝鲜人穿着中国国民军的制服。这是帝国的噩梦:跨民族主义运动的反帝团结,亚洲人与亚洲人对话。将这份报告交日本当局,并将备忘录送给特别股的负责人。不过日本当局或许已经有了这份报告(不仅仅是它们在巡捕房有间谍)。尽管直到1933年它的人数才超过40人,日本领事警察一直在壮大,最终人数超过了巡捕房特别股。它们被分成不同的组,分别负责中国台湾、朝鲜、俄罗斯和日本(主要是共产党),以及中国人的事务。(58)
当然,当一位男子持有比利时和加拿大两国的护照,不过后来又称有两个不同的瑞士身份时,成为玩弄上海最著名的游戏,不过他也是一位受过良好训练的共产国际分子。雅各布·鲁德尼克(Jakov Rudnik),在众多的假名中,也被称作牛兰(Hilaire Noulens),在上海组织和运作共产国际远东局,直至1931年暴露和被捕。(59)有哪个城市更适合这样做的。共产国际在这里开了一家合法贸易公司,在德国领事馆登记,鲁德尼克的作用是为那些从东亚和东南亚吸收,并经过这座城市前往俄罗斯接受培训,前往殖民地的特工和新招收人员提供后勤服务,为他们筹措资金和提供住宿。像他和佐尔格(Richard Sorge)这样为前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和外国激进分子和同志做间谍的特工,和任何其他人一样,尽可能利用这个特殊的城市。(60)
反殖民主义得到了帝国的敌人以及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帮助。德国特工帮助武装印度民族主义者并提供资金,法国人似乎间接地怂恿或至少保护了朝鲜的(独立)运动,尽管后者一直忙于政治内斗,直到它似乎也与共产国际运动联系起来,而共产国际更加严格。如果向日本人施压有用,那么为何不让他们继续下去。(61)日本人更系统地建立了一个赞助或买通不同国家和民族主义团体的策略。这是半泛亚思想和半实用主义的颠覆。所有的列强都投入时间和资源来监视他们自己的殖民地臣民,和在他们中做宣传工作。
除非出于它们自身的需要,例如将人员从一个殖民地调往另一个做安保人员,殖民地的政治治安将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防止被殖民化人民的融合上。上海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挑战。印度青年团可以安坐在闸北,并可以向南京派出代表。国民党可以利用与印度国民大会的关系。日本特务可以支持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或“独立的”澳大利亚联盟(Australia League)的活动。朝鲜人可以躲在法国城镇中。共产国际可以秘密地成立,从德国大都市贸易公司的办公室,或者从牛兰“教授”在上海许多地方租赁的安静房间中将东方点燃。
将第五个似乎最明显的上海、也是大多数中国居民的民族主义层面留到最后似乎有点奇怪。不过,尽管它起着在更广的背景下扼要重述的作用,但是这是一个如今已经说烂了的故事。我这样做的目的是想突出它的特征是如何被前面描述的层面作用、激励和影响。
狭隘的白人殖民者的民族主义有持久的影响。中国精英从早在1881年就抗议工部局有关进入市政场所的政策,这个故事直到今天还在继续。(62)非精英居民因为上海关于独轮手推车的规定发生骚乱。虽然公共租界成为一些反清活动的安全避难所,不过外国对中国的争夺引发了民族主义者挽救中国的新努力,租界本身也成为20世纪初新抗议的场所和原因。公共租界当局在实行自治过程中过于自信,以及殖民主义自鸣得意却常常不称职的行为,时常导致一浪接一浪的民族主义反应和斗争。最著名的是1905年有关司法主权的骚乱和1925年5月30日警察开枪导致的骚乱、抵制和总罢工。(63)不过,还有其他类型的,包括政治煽动导致的经济纠纷,以及有组织犯罪反对殖民权的斗争。民族身份或种族歧视导致的强烈差异,也引发中国人的抵制和抗议。民族政治运动在上海找到了最激进的家——种族移民法的更新导致了1905年的反美抵制运动,《凡尔赛条约》的不平等导致的1919年的“五四”运动。(64)上海的以下空间有助于这种活动的发展:它的法律漏洞和灰色区域;举行秘密会议的公园;茶楼、咖啡厅、电影院、酒店和书店。
这些不断重复的事件和运动的后果是矛盾的。一方面,一系列反应、联系、联盟和抗议仪式出现。每一起爆炸都有相似的反应。不过,这些联盟很难持久,上海的民族主义政治因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而各自为政,因而被削弱。(65)没有持续的民族联盟针对外国当局。不过,显然这些运动中给人印象最深的1925年五卅运动表明,一个如此合作的运动将如何不可避免地改变这个城市的政治。即便如此,学生和商人、劳工和资金都知道做什么:如何举行一次抗议集会,如何布置会场,打什么标语和口号,改编民间歌曲,印发传单,组织抗议和罢工,并派宣传队上街。他们知道如何发送公用电报、获得媒体报道和为被捕的人找律师。这都已经植根在上海日常的政治文化中。(66)这并不是说它支配着上海政治文化,因为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商业文化可能还是上海的主要特点。当然,对那些不满上海这个特点的人,上海不是一个政治活动之都,而是性和浮华之都。学生被描绘为不负责任的享乐主义者,而不是年轻的民族主义革命者。革命活动的兴奋、欢乐和时髦需要记住。(67)不过,在一些背景后面,总潜伏着一位锡克族,日本宪兵队,坐在黄包车中的醉醺醺的水兵,港口里的军舰,提醒人们有发生意外和冲突的可能,带来民族主义抗议的各种东西。
第一个结论是,碎片化在上海创造了机会。这些层面的活动互相交叉和互相联系,并互相促进。如果“世界主义”是赝品,是种族驱使的“神圣团结”的委婉说法,然而一种城市纪念的共同时尚逐渐流行起来了。德国、法国、英国和民国的中国的纪念仪式都看起来很相似,并在相似的场合下发生:有致敬和游行,演讲和建筑在白天用旗帜装饰,晚上则灯火通明,最初是用煤气火焰,后来用霓虹灯。有灯笼游行——灯作为一种媒介无处不在,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们容易注意石头和雕像,但不太注意易逝的照明。在纪念碑附近有仪式。看起来都差不多。这是一个结论:上海形成了这个共用的纪念仪式节目。
第二个结论是,通过针对他们的战争、警方命令和计划、对德国纪念碑的破坏,以及后来日军占领期间对英国纪念碑的破坏,我们也明白了这些仪式和象征的重要性。雕像被拆除,街道被改名,建筑被没收和重新搬迁。
第三点也回到警察身上,回到上海殖民时期的内在矛盾上。这个特殊地方的优点,随着这种通行证固有的危险不断增长,以它自己的“目的和方式”不断得到弥补。上海的这种漏洞需要不断改进警察制度,因为如果你是一个阴谋的搜寻者、一个情报官员,它似乎会威胁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随着新帝国主义的出现,帝国对手和敌人利用这座城市的潜力通过代理人互相攻击。对有关各方而言,他们敌人的敌人,从近期看可能是他们的朋友。在上海他们可以找到相对的避难所、交往、转移资金、组织运送武器或人员。一切皆有可能,这本身或许就是一座城市的定义。因此,1916年之后,随着情报和警察机构的壮大,他们开始互相联络,共享情报和警告,派特工到上海,建立一个系统来应对这座城市令人高兴的、破坏性混乱。帝国拒绝真空。这些行动产生了一个庞大的跨国家、跨帝国的网络。一位情报历史学家断定,唯一可比的“国际秘密组织”实际上是它的主要敌人——共产国际,不过总体上,反共和反民族主义的“帝国监视系统”将印度、英国和欧洲帝国和美国的机构联系起来,占了上风。(68)在加强日本国内、军方和外务省特工的关系时也存在这种情况,从而发展了一种“横跨东北亚的跨国家的政治安全制度链。”(69)
如果这种种族团结的“神圣纽带”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粉碎,安全机构以功能性的监视联盟得到了重组,目的是保卫殖民统治的共同遗产。即便将金融、人员,以及制度不足和其他猜忌、不胜任、这个城市自由运行的想象对发展所造成的限制等等都考虑在内,这个“冒险者的乐园”、“待沽之城”(City for sale)、“东方的巴黎”想到这个城市中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潜伏着间谍,警察监视着他的门和坐探,而在办公室内职员们将它们都打印下来并归档,向新加坡、香港、东京、英国发送电报,互相介绍情况,试图形成这个城市的政治和这个地区的政治。上海巡捕房特别处持续和系统地建立了它的庞大档案,增加照片和指纹,检查旅客名单,建立卡片索引。1931年它破获了共产国际,却从没有抓住佐尔格。它的档案也是本文主要的根据,以及它应对街道骚乱的一些策略,在“二战”之后复活,指导了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它的研究人员在20世纪50年代仍通过这些档案进行研究,并指导了塞浦路斯和新加坡的殖民统治。(70)上海培养了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者;它为团结,为联系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它也培养了它们的管理和争执,在监视、记录、分析和镇压中,以他们自己的国际的、谨慎的团结,为警察和情报机关本身超越空间和时间联系提供了机会和要求。
利益冲突声明:
本文作者声明,本文的研究、著作权和/或出版没有潜在利益冲突。
资助:
本文的研究得到了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奖(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award)(RES—062—23—1057)的资助。
注释:
①本文的另一个版本发表于《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第38卷第5期,塞奇出版社(SAGE Publication)2012年9月。
②上海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年度报告……1941》(Annual Report…1941(Shanghai:Kelly & Walsh,1942)),第32、35页。
③参见卡罗尔·格拉克(Carol Gluck):《日本的现代神话:明治后期的意识形态》(Japan's Modern Myths: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上海巡捕房警察1943日记(个人收藏)。
④美国国家档案记录局(U.S.NATIONAL Archives & Records Administration),记录组263(Record Group 263),“上海巡捕房特别部档案”(Archives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Special Branch”)(以下简称为:NARA,RG 263,SMP),NZ97/1,处备忘录No.332,“1940年8月9日~14日,当地爆发冲突纪念日采取的预防措施,”1940年8月6日。这一年的“七七事变”周年日首次取代了1915年的“二十一条”纪念日,国耻日被取消。
⑤卡尔·克劳(Carl Crow):《洋鬼子在中国》(Foreign Devils in the Flowery Kingdom),纽约:哈珀兄弟出版社1940年版(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0);格林(O.M.Green):《中国的外国人》(The Foreigner in China),伦敦:哈软森出版社,1943年版(London:Hutchinson,1943)。如果觉得上面这些还有限,参看,如布莱纳·古德曼(Bryna Goodman),“有关一个半殖民地主题的即兴演讲,或,如何解读一个跨国城市社区的庆典”(Improvisations on a Semicolonial Theme,or How to Read a Celebration of Transnational Urban Community),《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9,No.4(2000):889~926;以及毕可思(Robert Bickers):《争夺中国:清帝国的洋鬼子,1832~1914》(The Scramble for China: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1832~1914),伦敦:艾化—莱恩,2001年版(London:Allen Lane,2011)),第11章。
⑥埃里克·埃塞尔斯特罗姆(Erik Esselstrom):《跨越帝国边缘:外务省警察与日本在东北亚的扩张主义》(Crossing Empire's Edge:Foreign Ministry Police and Japanese Expansionism in Northeast Asia),夏威夷大学出版社(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9),第123页。同时参看俄罗斯的纳粹:约翰·斯蒂芬(John J.Stephan),《俄罗斯的法西斯:流亡中的悲剧与闹剧,1925~1945》(The Russian Fascists:Tragedy and Farce in Exile,1925~1945),纽约:哈珀—罗出版社,1978年版(New York:Harper & Row,1978)),第83~87页有关党的“上海论文”。
⑦张琳德(Linda Cooke Johnson),《上海:一个新兴江南港口,1683~1840》(Shanghai: An Emerging Jiangnan Port,1683~1840),张琳德编,《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第151~181页;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上海:中国进入现代的门户》(Shanghai:China's Gateway to Modernity),阿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第109~121页。
⑧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Shanghai,1927~1937:Municipal Power,Locality and Modernization),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上海警察,1927~1937》(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拍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伊懋可(Mark Elvin),“上海的行政”(The Administration of Shanghai),伊懋可和施坚雅编(Mark Elvin and G.William Skinner):《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in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第239~262页。
⑨克利福德(Nicholas R.Clifford):《帝国的宠儿:上海的西方人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汉诺威:新英格兰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Hanover: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1)。
⑩阮玛霞(Marcia R.Ristaino):《最后的容身之港:上海的侨民社团》(Port of Last Resort:Diaspora Communities of Shanghai),汉诺威;新英格兰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阮玛霞(Marcia R.Ristaino):《钱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The Jacquinot Safe Zone:Wartime Refugees in Shanghai),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11)最新对上海比较精辟的综述只有白吉尔:《上海:中国进入现代的门户》。
(12)《对外国商业开放的港口10年一度的贸易、工业等报告……1912~1921》,海关,中国“上海”(“Shanghai,” in China.The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industries etc.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1912—21),上海:海关统计股,1924年版(Shanghai: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Maritime Customs,1924),Vol.II:2;白吉尔:《上海》,第295页。
(13)有关这一点存在争议,不过的确有河港警察组织。
(14)布赖恩·马丁(Brian G.Martin):《上海青帮:政治和有组织的犯罪,1919~1937》(The Shanghai Green Gang: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1919~1937),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
(15)鲍明钤(M.J.Bau):《中国对外关系:历史及概述》(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China:A History and a Survey),伦敦:尼斯贝特出版社,1922年版(London:Nisbet,1922),第291页。
(16)参见上海出版的《苏报》案,由于外国列强的保护不受清的管辖,而《申报》则不是这样:J.拉斯特(J.Lust),“苏报案:早期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插曲”(The ‘Su—pao’ Case:An Episode in the Early Chinese Nationalist Movement),《亚非学院院刊》(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27,No.(1964):第408~429页,以及冉玫烁(Mary Backus Rankin):《早期的中国革命者: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902~1911》(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1902~1911),(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第4和第5章;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G.Wagner),“危机中的申报:国际环境与郭嵩焘与申报的冲突”(The Shenbao in Crisis: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Guo Songtao and the Shenbao),《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20,no.1(1999):第107~143页。
(17)这些列强的实际数量随着全球政治和中国的外交主动权的演变而变化:威多森(W. H.Widdowson)编撰的《1938年警察指南和规章》(Police Guide and Regulations,1938(Shanghai,n.p.,1938),pp.103~104)给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房警察列了14个(国家)。
(18)参见《1938年警察指南和规章》,第103~104页。
(19)毕可思(Robert Bickers):《帝国造就了我:一个英国人在旧上海的往事》(Empire Made Me: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伦敦:艾伦—莱恩,2003年版(London:Allen Lane,2003)第117页。
(20)参阅,如克劳德·马可威兹(Claude Markovits):《印度商人的全球世界,1750~1947:信德商人从布克哈拉到巴拿马》(The Global World of Indian Merchant,1750~1947: Traders of Sind from Bukhara to Panama),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齐亚拉·贝塔(Chiara Betta),“从东方人到想象中的英国人:上海的巴格达迪犹太人”(From Orientals to Imagined Britons:Baghdadi Jews in Shanghai),《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37 no.4(2003):999—1023;伊莎贝拉·杰克逊(Isabella Jackson),“南京路上的王公:上海通商口岸的锡克族警察”(The Raj on Nanjing Road:Sikh Policemen in Treaty Port Shanghai),《现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同上,2012)。
(21)芭芭拉·布鲁克斯(Barbara J.Brooks),“中国通商口岸的日本殖民公民资格:帝国秩序下的韩国人和台湾人的位置”(Japanese Colonial Citizenship in Treaty Port China:The Location of Koreans and Taiwanese in the Imperial Order),毕可思和安克强编(Robert Bickers and Christian Henriot):《新边疆:东亚帝国主义的新社区,1842~1953》(New Frontiers:Imperialism's New Communities in East Asia,1842~1953),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第109~124页;艾琳·斯卡利(Eileen P.Scully),“作为特权的卖淫:“上海通商口岸的‘美国女郎’,1860~1937”(Prostitution as Privilege:The “American Girl” of Treaty—Port Shanghai,1860~1937),《国际历史评论》(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20,no 4(1998):第855~883页。
(22)埃里克·埃塞尔斯特罗姆:《跨越帝国边缘:外务省警察与日本在东北亚的扩张主义》。
(23)上海市档案(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上海工部局记录(Records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以下简称SMA),U1—4—2546,“警察日历中据称是非授权的抓捕和毁灭”(Alleged Unwarranted Seizure and Destruction of Calendars by Police)[1935~36]。
(24)潘淑华(Poon Shuk Wah),“民国时期广州节日的重塑”(Refashioning Festivals in Republican Guangzhou ),《现代中国》(Modern China )30,no.2(2004):第202页。
(25)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共和国民的塑造:中国的政治仪式及象征符号,1911~1929》(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6) 参阅,如邦妮·布莱克伯恩和列奥弗兰克·霍尔福德—斯特文斯( Bonnie Blackburn & Leofranc Holford—Strevens),《牛津年鉴》(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Year),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7)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的农历每60年有一个循环,因此若干年后可能被认为是吉祥或凶险,促使或至少为某些行动提供额外的观念性前提。1900的庚子年正是那个循环的一个过渡年,就是一个例证。根深蒂固的大灾难将来临的预期促成了导致华北地区反基督教和反外国人的义和团运动的政治气候。有关这个话题,参阅邝兆江(Luke S.K.Kwong),“中华帝国晚期有关历史和时间的直线观点的出现”(The Rise of the Linear Perspective on History and Time in Late Imperial China),《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73 (2001):第157—90页。
(28)柯岚安(William A.Callahan):《中国:悲观的乐观主义国家》(China:The Pessoptimist Nation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第70~71页。
(29)“当这样下命令之后在周年纪念日指导被遵守”(Instructions To Be Observed on Anniversary Days When So Ordered,1932年4月29日,copy in Conf.Memo No/ 119,September 3,1936,NARA,SMP,D 7333,“国耻日——5月9日——纪念”(Humiliation day——May 9th——Observance),1933年5月10日,NARA,SMP,D 4851。
(30)参见毕可思(Robert Bickers),《上海人: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区的形成与认同,1843~1937》(Shanghailanders:The Formation and Identity of the British Settler Community in Shanghai,1843~1937),《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59(1998),第161~211页。
(31)毕可思:《争夺中国:清帝国的洋鬼子,1832~1914》,第173页。
(32)参见白吉尔:《上海:中国进入现代的门户》,第84~129页的讨论。
(33)《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以下简称NCH),August 18,1870:119,120,132—33。同时参阅梅朋、傅立德(C.H.Maybon and Jean Fredet):《上海法国租界史》( 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Fran? aise de Changhai),巴黎:普隆出版社,1929年版,(Paris:Plon,1929):第352~354页。
(34)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上海歹土:战时恐怖主义和城市犯罪,1937~1941》(The Shanghai 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第115页。
(35)作为代理警察处处长,H.M.Smyth在1940年的信中这样写道:给马克·西格尔格的信(Letter to Mark Siegelerg),1940年8月21日,NARA,SMP N309。
(36)毕可思;《争夺中国:清帝国的洋鬼子,1832~1914》,第300~304页。
(37)没有对万国商团的研究,不过可以参看寇尼(I.L.Kounin)编:《上海万国商团85年》(Eighty Five Years of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上海:大都会出版社,1939年版(Shanghai:Cosmopolitan Press,1939)。
(38)毕可思(Robert Bickers):“动人的故事:上海通商口岸的雕像和纪念碑,1860年代至1945”(Moving Stories:Statues and Monuments in Treaty Port Shanghai,1860s~1945),正在写作中,2011。
(39)有关这个纪念碑及其揭幕,参阅布鲁诺·纳瓦拉(Bruno Navarra):《中国与中国人》(China und die Chinesen)(Bremen:Max Nossler,1901):第529—534页。
(40)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的社交16:2,《上海社交》(Social Shanghai)(1913)。
(41)徐国琦(Xu Guoqi):《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司和国际化》(China and the Great War: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ion),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42)《北华捷报》,1914年8月8日,第407页。
(43)毕可思:《动人故事》。
(44)《北华捷报》,1918年11月30日,第532~539页。
(45)《北华捷报》,1927年6月11日,第472~473页;1928年5月26日,第334页;1928年6月9日,第426~427页。
(46)NCDN,1928年2月22日,第11页;1929年1月10日,第13页。更广泛的分歧参看如:戴维·斯特劳斯(David Strauss),“法国的反美情绪的产生:法国知识分子和美国电影业.1927~1932”(The Rise of Anti—Americanism in France:French Intellectuals and the A merican Film Industry,1927~1932),《流行文化学刊》(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10,no.4(1977):第752~759页。
(47)萧知纬(Zhiwei Xiao),“南京十年期间的反帝与电影审查,1927~1937”(Anti—imperialism and Film Censorship during,the Nanjing Decade,1927~1937),《跨国华语电影:身份认同,民族性,性别》(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Identity,Nationhood,Gender),编辑鲁晓鹏(Sheldon H.Lu),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第35—57页。
(48)唐纳德·乔丹(Donald A.Jordan):《中国火的轨迹:1932年上海之战》(China's Trail by Fire:The Shanghai War of 1932),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
(49)NARA,SMP D3566,“日本天皇诞辰日,官方庆祝”(Birthday of H.I.M.the Emperor of Japan,Official Celebration)。有关袭击的文件SMP D3586从档案中遗失。
(50)这不是朝鲜人第一次在上海搞暗杀。1922年3月3名男子试图暗杀日本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失败,结果却杀死了一名美国旅游者:埃塞尔斯特罗姆:《跨越帝国边缘》,第69页;《北华捷报》,1922年4月1日,第26~28页。
(51)罗伯特·斯卡尔皮诺、李钟石(Robert A.Scalpino and Chong—sik Lee),“韩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一)”(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Communist Movement (I)),《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no.1 (1960):第21页。
(52)威尔斯、金山(Nym Wales and Kim San):《阿里郎之歌:中国革命中的一位韩国共产党人》(Songs of Ariran:A Korean Communist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旧金山:兰帕兹出版社,1972年版(San Francisco:Ramparts Press,1972):第113页。
(53)杰克逊,“南京路上的王公”。
(54)上海工部局(SMC):《1915年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1915):24a;理查德·柏柏尔威尔(Richard J.Popplewell):《情报与帝国防御:英国情报与印度帝国的防御,1904~1924》(Intelligence and Imperial De fence: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the De fence of the Indian Empire,1904~1924),伦敦:弗兰克—卡斯,1995年版(London:Frank Cass,1995):第271~272页。
(55)上海工部局(SMC):《1923年年度报告》:28。
(56)NARA,SMP D8/8,“印度股”(Indian Section),1929年6月17日。到1936年,保留了250个有关“叛乱煽动者”的文件,280多个有关“同情者”,3500多个其他引起警察注意的个人:“第四股(Section 4),印度股(Indian Section),特别处(Special Branch)”,1936年2月11日。
(57)NARA,SMP D74,“韩国会议”,1929年3月4日。
(58)NARA,SMP D4812;埃塞尔斯特罗姆:《跨越帝国边缘》,第120~122页。
(59)弗里德里希·立顿(Frederic S.Litten),“牛兰事件”(The Noulens Affair),《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138(1994):第492~512页;魏斐德:《上海警察,1927~1937》,第144~151页。
(60)有关佐尔格和他的世界,参看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一起叛国事件:尾崎秀实与佐尔格间谍网》(An Instance of Treason:Ozaki Hotsumi and the Sorge Spy Ring)(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也可以看查尔斯·威楼比(Charles A.Willoughby):《上海阴谋:佐尔格间谍网》(Shanghai Conspiracy:The Sorge Spy Ring ),纽约:多顿,1952年版(New York:Dutton,1952)。上海巡捕房实际上怀疑佐尔格是苏联特工:NARA:SMP D 4718。
(61)柏柏尔威尔:《情报与帝国防御》,第258~296页;魏斐德:《上海警察,1927~1937》,第66~72页。
(62)毕可思、华志坚(Robert A.Bickers and Jeffrey N.Wasserstrom),“上海的‘狗与中国人不得入内’牌:传奇、历史与当代的象征”(Shanghai's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 Sign:Legend,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ymbol),《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142(1995):第444~466页。
(63)理查德·里格比(Richard w.Rigby):《五卅运动:事件与主题》(The May 30 Movement:Events and Themes),福克斯顿:道森出版社,1980年版(Folkestone:Dawson,1980);克利福德:《帝国的宠儿》。
(64)蒂娜·艾拉克西宁(Tiina Airaksinen):《在南京路上爱你的国家:英国人与上海五卅运动》(Love Your Country on Nanjing Road:The British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赫尔辛基:仁瓦尔学院,2005年版(Helsinki:Renvall Institute,2005)。
(65)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民国时期的社团与城市变化”(Civil Society and Urban Change in Republic China),《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150(1997):第326~328页。
(66)华志坚(Jeffrey N.Wasserstrom):《20世纪中国的学生抗议:从上海的角度》(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 View from Shanghai)(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亚瑟·沃尔德隆(Arthur Waldron):《从战争到民族主义:中国的转折点,1924~1925》(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67)参见萧剑青:《漫画上海》(上海:经纬书局,1936)中描绘的学生;参看如革命学生回忆录,可见一些革命活动如何开始是个人与性放纵的舞台:王凡西(Wang Fan—his):《中国的革命者:1919~1949的回忆录》(Chinese Revolutionary:Memoirs 1919~1949),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68)理查德·阿尔德里奇(Richard J.Aldrich):《情报与抗日战争:英国、美国与特工的政治》(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Britain,Ame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Secret Servic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0~22。不过,正如阿尔德里奇所指出的,这个系统在应对日本时几乎完全失败。
(69)埃塞尔斯特罗姆:《跨越帝国边缘》,第69页。
(70)这些档案很抢手:参看NARA,RG 226,1—261—30A,“上海警察档案的被卖”(Sale of Shanghai Police Files),1949年4月22日,OSS华盛顿。有关这些档案的后来情况,如中情局人员的便条仍粘在NARA SMP D4825上,表明这个档案1956年在不同的办公室之间(使用)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