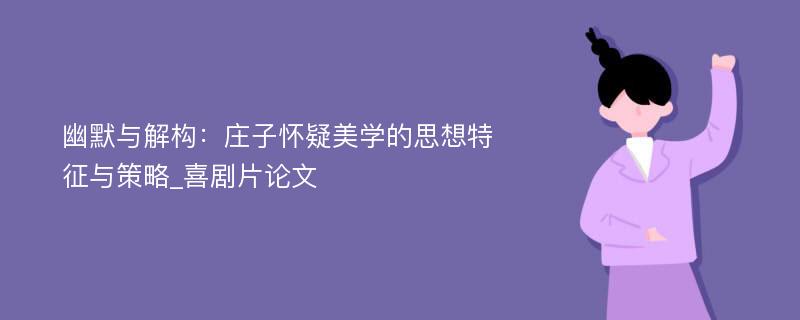
幽默与解构:庄子怀疑论美学的思想特性和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怀疑论论文,庄子论文,美学论文,特性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6)03-0005-07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16.03.001 庄子是一个非常富有幽默感的哲学家和诗意气质的人。幽默一方面体现庄子的想象力和生命智慧,是其表达思想的必要方式和风格,另一方面,幽默是庄子解构和批判的精神工具;再一方面,幽默是庄子的想象和智慧的必然性结构和必要补充。 一、幽默的美学阐释 幽默在逻辑上可能表现为矛盾和悖论,呈现为令人发笑的荒诞。笑和幽默之间不能简单作逻辑等同。笑是幽默的结果,然而,笑不能等同于幽默。西方美学史上,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从心理深层寻找幽默感的动因,他试图从“感情消耗的节约”的角度考察幽默的性质。他在《论幽默》中说:“幽默的本质就是一个人免去自己由于某种处境会得到自然引起的感受,而用一个玩笑使得这样的感情不可能表现出来。”他进一步阐述幽默的特征“幽默具有某种释放性的东西;但是,它也有一些庄严和高尚的东西,这是另外两条从智力活动中获得快乐的途径所缺少的。……幽默不是屈从的,它是反叛的。它不仅表示了自我的胜利,而且表示了快乐原则的胜利,快乐原则在这里能够表明自己反对现实环境的严酷性。最后这两个特性——拒绝现实要求和实现快乐原则使幽默接近于回溯的或反拨的过程。”[1]依照弗氏的阐释,幽默是幽默者处于窘迫处境采取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的摆脱,它试图获得一种优越的地位来战胜自己的悲哀和恐惧。因此,幽默和喜剧的本质不同在于,幽默可以包含自我的窘迫、悲哀和痛苦,然而,主体可以依赖自我的智慧和勇气克服它,从而赢得假定性的优越地位,因此,超越原则是形成幽默感的逻辑前提和心理保证,也是推动幽默感焕发的精神工具。弗洛伊德由此巩固自己对于幽默的结论:幽默是通过超我的力量对喜剧作出的贡献。他进而将幽默和喜剧做出区分:幽默的快乐永远不会像在喜剧或玩笑中达到那样强烈的快乐,它永远也不会在发自心底的笑声中得到发泄。因此,幽默是轻度的喜剧,有理性节制的笑。里普斯(Theodor Lipps,1851-1914)认为,喜剧性在幽默中吸收了具有肯定价值的要素时,它便获得审美的意义。幽默是喜剧感被制约于崇高感的情况下产生的混合感情,这是喜剧中的并且通过喜剧产生的崇高感。他将幽默划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假如我看到世界上渺小、卑贱、可笑的事物,微笑地感到自己优越,假如我尽管这样,仍然确信我自己;或者确信我对世界的诚意,那么,我是在狭义上幽默地对待世界。 其次,假如我认识到可笑、愚蠢、荒谬事物的卑劣性、荒谬,把我自己、把我对于美好事物以及对它们的理想的意识和这些事物相对立,并且坚持和这些事物相对立,那么,我借以观照世界的幽默,是讽刺性幽默。“讽刺”就意味着这种对立。 最后,假如我们不仅认识到可笑、愚蠢、荒谬的事物,而且同时还意识到这些事物本身已经归结为不合理,或者终将归结为不合理,意识到一切“不合理”归根到底不过“聊博宙斯一笑”,那么,我这时借以观照世界的幽默,是隐嘲性幽默。这里,应有的前提是“隐嘲”以“不合理”的自我否定为特征。[2] 里普斯对于幽默的分析和阶段划分,对于幽默特性的揭示主要从分析主体的感受出发,从价值立场和认识态度为幽默感的形成寻找原因,以对不合理现象的自我否定性为逻辑前提。庄子的幽默在一般的美学形态上,符合弗洛伊德和里普斯的论述。但是,庄子的幽默更加凸现出哲学的智慧和诗意的想象力,更富于审美趣味和艺术格调。借用里普斯的概念,从形态上看,庄子的幽默所谓“狭义的幽默”比较稀少,更多是“讽刺性幽默”和“隐嘲性幽默”,尤其是“隐嘲性幽默”更为众多和鲜明。 二、哲学化的喜剧 庄子的幽默充分展现出哲学化的喜剧效果。从幽默和哲学的历史渊源考察,幽默在天然形态上和哲学存在密切的联系,古希腊的哲学充满幽默的智慧或智慧的幽默。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对话录”文体,以人物之间的提问与解答、诘问与争辩、立论与反驳等充满机锋的言谈,淋漓尽致地展示出哲学的魅力,挥洒着幽默的光彩。先秦哲学中,孔子与弟子、庄子与惠子、庄子与虚拟的意象、孟子与梁惠王之间的对话,哲思之中发散着智慧和幽默。先秦轴心文化的幽默传统,一直影响后世。魏晋的清谈风气和玄学兴起“竹林七贤”的旷达闲散和诗意情怀,使哲学、文学、幽默三位一体的交融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如果说《世说新语》中有诸多精彩的哲学与文学相互渗透的幽默,那么,禅宗中不少的语录、灯录、公案、话头、机锋等,呈现出佛教哲学的智慧和幽默。《五灯会元》、《高僧传》等典籍中记载了丰富的佛学幽默,弥散着宗教的智慧和灵感,启思人生和艺术。从哲学和幽默的逻辑联系看,幽默是超越喜剧的“哲学喜剧”和“智慧喜剧”,幽默带来富有哲学意味的笑和智慧的笑。庄子的幽默,寄寓着深刻的人生智慧,表现出一种哲学化和美学化的喜剧。 从幽默和逻辑的关系看,幽默体现为逻辑的悖论、矛盾或荒谬,它常常打破和颠覆日常的逻辑经验。古希腊哲学家芝诺(Zenon,约前490-前436)的“飞矢不动”命题,是古老的反逻辑命题,也是充满幽默感的哲学命题。孔子有关“夔一足”争论《庄子·天下》所记载有关惠子的论题,其实也内含庄子的思想成分。诸如“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合同异”、“飞鸟之景未尝动世”、“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等论题,公孙龙的“坚白论”和“白马非马论”,西方哲学史上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的“罗素悖论”等,这些哲学命题呈现反逻辑的特征,包含幽默趣味。在《庄子》文本里,许多有意背离逻辑和逻辑混乱的语言、行为,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物形象,造成幽默情境而引人发笑。值得眷注的是,庄子的幽默常常呈现对立的现象,揭示事物或主体内部的矛盾和悖论,或者以辩证思维阐释司空见惯的现象,发表出人意料的观点,达到解构和嘲讽的喜剧效果。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①(《庄子·逍遥游》) 狙公赋茅,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庄子·齐物论》)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应帝王》) 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庄子·骈拇》) 商大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谓也?”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曰:“请问至仁。”庄子曰:“至仁无亲。”(《庄子·天运》) 《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走,鱼闻之而下入,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庄子·至乐》) 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庄子·山木》) 庄子以鲲鹏和蜩、学鸠的对比,揭示两种不同的生命境界,让人发出会心一笑,在笑之后却体悟到人生的某种哲理。尽管不同存在者的能力以及所能达到的生命境界不同,但是它们都具备各自的生存意义和内在快乐。“朝三暮四”的寓言,在笑声里揭示“休乎天钧”和保持“两行”的意识,守护事理的自然均衡才是庄子的主旨。“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为其凿七窍,最终害死友人的寓言,表现良好的目的和善的动机却带来悲剧的结果这样的观念。“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庄子呈现两种有趣的对立现象,以佐证“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的哲思。孔子对于虎狼之“仁”的阐释,打破常规思维和价值定论,以悖论方式陈述令人惊异颔首的道理。《咸池》和《九韶》优美古乐,演奏给动物和人,产生极度反差的审美效果,意在说明同样事物运用于不同的对象,获得截然不同的结果。美丑颠倒的“逆旅小子”,忍俊不禁的回答颇有哲学家的气质。庄子以寓言或现象对比的方式,揭示事物和内心的矛盾或悖论,以幽默的方式达到喜剧化的审美效果,寄寓着哲理和智慧,同时对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审美观进行反讽和解构。 三、幽默是虚构的寓言 和喜剧相比,幽默有更大自由的虚构空间。如果说寓言的审美特性就在于它的假托和虚拟的叙事,那么,幽默往往从寓言这一文学载体中得以生成。这在先秦寓言中,尤其在庄子的寓言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先秦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留下包括寓言在内弥足珍贵的哲学与诗的丰厚遗产。《孟子·公孙丑》中的“揠苗助长”,《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的“郑人买履”、“买椟还珠”、“卖不死之药”、“画鬼”、“郢书燕说”,《韩非子·难势》中的“自相矛盾”,《韩非子·五蠹》中的“守株待兔”,《吕氏春秋·去尤》中的“亡鈇者”,《吕氏春秋·察今》中的“刻舟求剑”,《列子·天瑞》中的“杞人忧天”,《列子·黄帝》中的“朝三暮四”,《列子·汤问》中的“两小儿辩日”,《战国策·齐策二》中的“画蛇添足”,《战国策·楚策一》中的“狐假虎威”,《战国策·魏策四》中的“南辕北辙”,《战国策·燕策二》中的“鹬蚌相争”等,这些寓言以虚构的叙事创造风趣的幽默而成为“典故”或“成语”,深刻地影响着华夏的文化传统。庄子“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庄子·寓言》庄子的寓言无论数量、思想内涵和美感趣味,都卓尔不群,尤其是蕴含丰富的幽默情趣: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秋水》)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庄子·秋水》)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秋水》) “子独不闻夫埳井之蛙乎?谓东海之鳖曰:‘吾乐与!出跳梁乎井干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则接腋持颐,蹶泥则没足灭跗。还虷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乐,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时来入观乎?’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絷矣。于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夫不为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此亦东海之大乐也。’于是埳井之蛙闻之,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庄子·秋水》)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骛,扬而奋髻,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庄子·外物》) 以上寓言已经成为文学和哲学的经典文本。“庄子钓于濮水”故事。以庄子自身的比喻性叙述话语,有趣地呈现甘愿隐逸江湖而不愿出仕的逍遥者形象。从美学上看,文本寄托的思想意义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庄子话语所弥散出的幽默感和喜剧色彩。“惠子相梁”与上述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文本精妙处不在于庄子的隐逸情怀,而在于庄子借以讲述的极富幽默感的寓言故事,它既是对惠子的讽刺和嘲笑,也是对政治和权力这两个共生对象的冷漠和蔑视,故事元素和审美符号所达到的精彩幽默已经远远大于思想内容。“濠梁之上”这则故事重在论辩,它呈现的幽默更富有智慧色彩和哲理性。庄子和惠子的逐步深入、各不相让、反诘驳论的方式不禁令人开怀一笑,胸襟飘拂和愉悦感油然升腾。这既是语言游戏也是思辨游戏,更是智慧游戏和审美游戏,借助于两者的语言游戏达到幽默感的生成。“埳井之蛙”的寓言,属于里普斯界定的“隐嘲性幽默”范畴。如果说“隐嘲”以“不合理”的自我否定为特征,显然,最后“埳井之蛙闻之,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达到自我意识和理性反思的境界,这一幽默隐藏着启迪性意义。“任公子钓鱼”的寓言,以极度扩张的故事元素,营造幽默的喜剧情境,赞赏“任公子”这一审美符号的恢弘博大的人生境界,对那些“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的人物予以嘲讽,让接受者在品味幽默之中滋生价值感和审美意义的评判。 庄子的寓言以深邃的人生哲理和空灵飞扬的智慧给予后世无限的启迪和想象,令人理解幽默的真谛和美感,体悟到幽默之中所隐藏的诗意和精神价值。相比较,西方寓言中同样包含妙趣横生的幽默和寄托一定的思想观念。伊索(Aisopos,约公元前6世纪)寓言中“狐狸和葡萄”、“乌龟和兔子”、“夜莺和鹞子”、“狐狸和伐木人”等篇目,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寓言中的“乌鸦和狐狸”、“青蛙想长得和牛一样大”、“鹤和狐狸”、“狮子和驴去打猎”、“群鼠的会议”等,克雷洛夫(1769-1844)寓言中的“执政的象”、“四重奏”、“驴子和夜莺”等,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寓言中的“末日的欢呼”、“忙碌的哲学家”、“新鞋子”、“教授的答辩”等篇目,都是富有幽默感和智慧的文学杰作。莱辛在《论寓言的本质》一文中认为“凡是诗人虚构的、联系着一定目的的情节都叫做他的Fabel(在这里的意义是:故事),因此诗人虚构出来的贯穿于他的史诗、他的戏剧中的情节,便是他的史诗的Fabel、他的戏剧的Fabel……寓言也是一种虚构的故事,它旨在达到一定的目的。”[3]1308莱辛进一步探讨了“复合寓言”:“它所要我们形象地看出的真理,还进一步用在一个的确发生过的事件或者一个假定是的确发生过的事件之上。”[3]1309庄子寓言充满着莱辛所论述的复合寓言,包含着深刻有趣的哲理和幽默。 寓言和幽默的相辅相成的逻辑关系,只有在虚构的美学意义上才能寻找到合理的解释。幽默除了和寓言这种文学形式相联系之外,它的另外一个密友就是漫画(Cartoon)。漫画成为最适合于担当幽默感的绘画种类,一度风靡全球的卜劳恩(E.O.Plauen,1903-1944)的《父与子》漫画就是典型的例证之一,中国现代漫画家丰子恺的《护生画集》也是堪称经典的幽默杰作。从一定意义上考察,丰子恺的漫画也可以窥见庄子思想的投影和其幽默的精髓。 四、幽默是承担痛苦的微笑 幽默和悲剧、痛苦存在潜在的联系。而正是这一点构成和喜剧之间鲜明的差异性。这在庄子的幽默中表达得十分显著: 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归到鲁东门外,适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阙然,数日不见,车马有行色,得微往见跖邪?”孔子仰天而叹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头,编虎须,几不免虎口哉!”(《庄子·盗跖》)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胜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见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夫!(《庄子·列御寇》)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至乐》)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人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徐无鬼》) 庄子刻意虚构孔子和“盗跖”的会见故事,孔子见盗跖等于自入虎口,担当了生命的危险却留下一个无伤大雅的笑话。庄子对孔子给予轻度的讽刺和嘲笑。这是苦涩和悲哀性质的幽默,它也许告诉众人“道不同不相谋”的哲理。一般幽默所包含的嘲笑都是针对他者的,而只有智慧超然和境界高妙的心灵才显露自我嘲讽的气度。庄子显然具有自嘲的勇气和喜好,上述的自嘲是面临死亡的自嘲,是面对死亡的幽默,展现庄子的审美情怀和人生气度。庄子濒临之际,摒弃弟子准备的厚葬,选择以节俭方式回归自然,以诗意的态度坦然地面对死亡和安葬,他应对弟子的语言充满了幽默感和淡淡的诗意,甚至流露出一丝快乐的情绪“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庄子话语所内蕴的幽默,消解面对死亡的痛苦和恐怖,带来的是对于死亡的超然态度。妻子亡故,依照常理庄子应该寄予悲哀的情感,然而,庄子却“方箕踞鼓盆而歌”,招致挚友惠施的批评。庄子却给予常人意想不到的解释,认为生死是自然现象,两者之间的转化符合天命,而痛哭的表现却违背自然之性。所以,庄子这里的幽默是承担着痛苦的微笑,是生命智慧和诗意的可爱显现。“运斤成风”的故事,表达庄子对惠子的深切怀念,然而,怀念的方式却包含着幽默而不是痛苦,在微笑之中寄托着澹澹的忧伤。所以,庄子的幽默能够将痛苦转化为淡淡的快乐,能以微笑抗拒痛苦和悲哀,这既需要内心的勇气,也需要生命的智慧。从这个意义讲,庄子的幽默在哲学层面和美学层面上,它的价值和境界是高于喜剧的。 从后世的美学影响看,鲁迅的《阿Q正传》,无疑具有悲剧的美学性质,但是,它完全可以称之为经典的幽默作品,也是面临痛苦和死亡的幽默,所谓“含泪的笑剧”或“含泪的微笑”。所以,可以把幽默表述为:“精致之喜剧”或者“喜剧之喜剧”。它是智慧的会心一笑,惊鸿一瞥,也是轻度的笑,无言的笑,沉默的笑,是消解痛苦和恐惧的笑。这种笑是哲学化的,也是诗意的和美学化的。这些幽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于庄子幽默的继承和延伸。近代以来,流行一种中国人缺乏幽默感的说法,无疑是偏颇和片面之论。从历史上,华夏民族是最富有幽默感的民族之一,先秦典籍里珠散玉落的寓言故事,尤其是庄子的幽默渗透着哲学意蕴和艺术美感。司马迁《史记》里的“滑稽列传”,魏晋时代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邯郸淳的《笑林》,而后世的幽默性的著述更为兴盛。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竭力推崇中国人的幽默感,认为华夏民族在本质上是富有诗意感和幽默传统的民族。华夏民族的幽默感逐渐降低和幽默趣味的世俗化也是客观的事实。这一方面归结为近代几百年的历史,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承载了过多的悲剧和痛苦,专制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压抑,幽默感必然在历史和现实的重轭之下归于潜藏和消解;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状况的改观和文化语境的变迁,幽默感逐渐恢复和增强。但是,经济原则和欲望意志却悄悄改变文化传统中富有哲学意味和诗意情怀的幽默感,而代之以粗俗和无聊、消解正义和价值的变态幽默或病态幽默。这是必须正视和警惕的另一种倾向。 庄子的幽默也具有黑色幽默的美学性质,面对着死亡和痛苦,依然保持一颗快乐和超然的心灵,保持人格的高贵和诗意的气质。对于痛苦的承担和转换在现代主义的“黑色幽默”(Black Humour)文学文本上表现得比较鲜明,黑色幽默又被称为大难临头的幽默或者绞刑架下的幽默,也有人描述为“绝望的喜剧”。海勒(Joseph Heller,1923-1999)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和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的《第五号屠场》,可谓黑色幽默的代表之作。黑色幽默小说具有寓言的风格,采取极度夸张和虚构的手法写作,故事的离奇编造性却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反思的基石之上,时间与空间的自由切换,消解崇高和英雄的冷峻叙事方式造成独特的审美效果,这一切都使黑色幽默更呈现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4]比照西方现代文学的黑色幽默的美学特性,庄子的幽默以短小精悍的寓言见长,充满灵动的想象力和艺术虚构,表现形式上自由洒脱,深邃的思理交映着生动精妙的话语,给人无限的审美快感。 ①参见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54年版,以下所引《庄子》原文皆出于此版本,下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