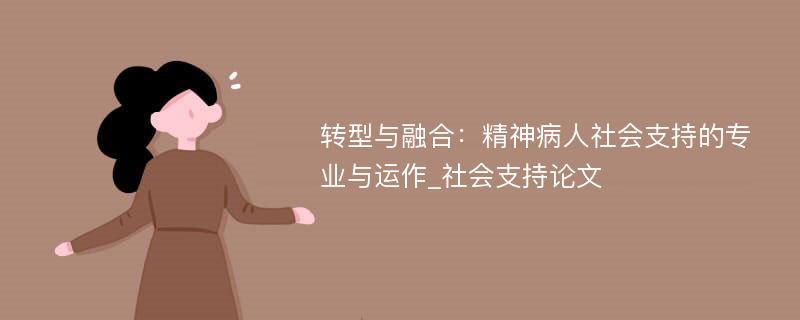
跃迁与整合:论精神病患社会支持的专业性与操作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支持论文,病患论文,操作性论文,专业性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01年世界卫生报告》显示,全世界上约有4.5亿各类精神和脑部疾病患者,平均每4个人中就有1人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段产生某种精神疾病①。该病的行为特征会构成社会治安的隐患,由此精神疾病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精神健康便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成为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研究的热点。本文以151例精神病患者为中心,围绕其生活的自然社区,对428人(城市216人,农村212人)进行调查和访谈。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研究精神健康的社会支持,并试图将现有的理念性支持跃迁至操作性支持,以实现理念性与操作性的整合。
一、精神疾病的社会建构
我们认为精神症状出现和诊断的实质是一种社会建构。除目前对精神疾病的医学解读外,还应有三种解读,即世俗解读、社会科学解读和社会文化解读。
医学解读。医学上认为精神疾病是肌体在内外环境不利因素影响下,导致认识、情感、意志等精神活动以及行为出现不同程度障碍的疾病。通常经过临床面谈评估和判断个体心理社会功能是否缺损,并寻找行为、情感和认知等方面的证据。1994年美国精神病协会将精神疾病定义为:发生于某人的临床上明显的行为或心理症候群或症状类型,并伴随痛苦烦恼,或功能不良,或者伴有较多明显的风险。且这种症候群或症状类型不是对于某一事件的可期望的、文化背景所认可的心理反应。他们认为判断精神疾病有五大指标:第一,主观痛苦:个人必须抱怨,情绪悲痛、躯体痛苦、不舒服、失去控制、有与个人价值违背的决定;第二,受损的社会心理功能:个人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洗澡、穿衣、吃饭)或无法完成普通的社会功能(工作、生活、人际关系的互惠)或自我毁灭;第三,怪异行为:个人采取没有工具性目的的行为和实质性地偏离其亚文化功能的行为;第四,感觉失能:个人的触觉机制有问题,即视觉、听觉、味觉、触觉或与共享社会环境所发出的刺激不一致;第五,思维混乱:个人的认知是错误的、不现实的、与文化共享的认知不一样。严重精神病人符合上述所有标准,然而有些人只符合少数标准,或仅符合第一标准,那就可能是生活问题或是社会偏差行为。
世俗解读。在一般人看来精神疾病与“不正常行为”或“反常行为”紧密相联,反常行为是行为人的行为异于常人。其建构过程是群体面向单一个体的情境,当个体行为持续异于大多数人的行为,就会被建构为精神疾病。世俗解释的基本假设是:大多数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言行就是正常的,反之则是“病态”的,是精神病。无论这“一般”所代表的是科学、正义还是伪科学、非正义。世俗解读常常与个人利益、情感纠缠在一起。当某个人的行为损害了自己利益时或自己憎恨对方时,常将对方建构为精神疾病者。而“病态”与“常态”界限模糊,常易导致误诊以及故意迫害②。如此人们对“生活挫折”的反应很容易被判断为精神疾病的表现,这样可能掩盖了矛盾和冲突。
社会科学解读。在学界精神疾病是个人行为、心理或生物学功能失调的表现,被视为“迷思”和“隐喻”③,是一种“将偏差行为归因于个人的社会建构”,行为主义者反对用医学词汇、标签和心理问题来界定的假设,认为环境因素导致了适应不良行为的出现。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家批评科学方法在精神疾病研究中的应用,认为评估精神疾病不可能是客观的,因为所有评估都取决于与案主的互动过程。评估与判断的参照标准可能是模糊的常规模式,所以,精神疾病概念存在于生物事实和社会价值的边界。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冲突过程中所产生的张力,社会冲突结果形成的社会与心理对峙,特别是社会结构中的规则与资源对个体的挤压,以及个体缺乏对规则和资源的转化手段,使得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缺乏所需的资源。张力、社会与心理对峙、社会结构挤压、社会资源的严重短缺所产生的个体负性体验,不仅直接成为个体精神疾病的社会致病因素,而且也间接地形成个体发展的制约因素与深刻经验。个体常将自身的经验重新解释、编码、转译为个体对强关系角色的种种深切期待,在与强关系互动中表达期待,传递情感。过度的情感表达,使强关系群体转变为压力群体,进而成为个体精神疾病的强关系致病因素。因此经强关系互动诱导,宏观结构的隐匿性“病根”显现于微观互动。强关系中的负性生活事件与负性体验,成为诱发个体精神失衡的原因。
社会文化解读。社会的文化价值、习俗、规范和期望,对人的行为具有引导功能和分化作用。社会文化引导行动者的行动,使之符合文化期待,并排斥不符合文化期待的行为,被排斥的行动者则可能被建构为精神疾病。文化价值、规范、习俗、期望等文化内涵的科学性与道德性有时很模糊,常遭遇挑战。在哥白尼时代,因“地心说”被建构为精神病患者。我们调查也发现社会文化的包容性程度与精神疾病的建构率呈反比关系,即文化的包容性越高,则精神疾病的建构率越低。正如本次对知识分子社区、产业工人社区、富人社区、机关社区和农业社区等5类不同类型的社区实证调研,我们发现产业工人、知识分子社区的包容性相对较高,机关社区的包容性相对较低。这表明亚文化群体包容性特征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生活环境,也决定着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环境是支持性的还是压制性的。
二、患病角色的社会再构
精神疾病的患病异于其他疾病,该病常导致患者向低层流动,最终归于社会最底层。个体一旦被建构为精神病患,其话语权就被自动剥夺,其就医行为也失去主体性。如果说精神疾病是一种社会建构,那么个体罹患精神疾病的结果则是社会的再次建构。患病角色的社会再构是建立在对精神疾病概化基础上的社会区隔,其再构的方法为“标签”与“污名”,经过社会再构,患病个体被置于“异端”而陷入重重危机。标签理论认为:精神病人是破坏社会规范的人,当异端越轨行为被社会人士发现,随之便被贴上病态的标签。病态标签的“污名化”机制通过对患者本人及其家属的压制,形成社会惩戒。
那么患者是如何被社会再构的?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患者较少被寄予希望,获得同情与帮助,同时也出现社交退缩或人际交往行为笨拙等问题,被毫无选择地困于患者角色,孤立无助,不能自拔之中,就连其家属的正常人际交往也会受阻或断裂,并影响人们对家属的社会评价。在职业、经济、社会压力的交互作用之下,患者及家属往往会出现强烈的耻辱感、自卑感、孤独感,言行均十分谨慎。患者家属在长期的生活煎熬中,对患者欲罢不能、欲爱不成,处于矛盾、痛苦与绝望的情感之中。
美国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理论家沙利文认为,在人类本质的社会性问题上,一个人出生后,就生活在一个复杂、变动的人际关系之中,这种人际就是他的社会性,人的人格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才能存在,人在表象、记忆、幻想中实现和保持这种关系。也正是在这种关系中,精神病得以萌发,得以诊断,得以治疗,得以恶化,得以康复。
三、精神疾病患者的社会支持
世卫组织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认为,精神病不是个人的失败,如果有失败,失败在于我们与患有精神和神经疾病的人之间的反应方式上。在我国,对“精神疾病”通常以生物学叙述方式为主导,强调精神病学家和医药的地位,结果精神科医生以药物治疗的形式“提供照顾”,而案主被动“接受”照顾。这加剧了两者在知识和权利上的不平等,构成了案主赋权的障碍,也使精神健康领域的社会支持研究与实务成为医务工作者的独角戏,尽管他们是支持系统中的重要角色,但是单一角色无法支撑、维系精神健康所需的支持网络。我们认为既然引起精神疾病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社会,那么“所有改良方法都必须到社会结构里去寻找”④。
那么我国的社会支持做得如何?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国内学者对社会支持研究有两种倾向性。第一,将社会支持与弱势群体紧密相连。认为社会支持是一定社会网络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者进行无偿帮助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为⑤。面向弱势群体的供给性行为虽可界定社会支持,但在两个层面具有将社会支持“层次化约”⑥之嫌。仅将社会支持对象限于“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⑦,尤其将经济弱势作为弱势群体产生的主要原因和特征,可能忽略其他资源形式上的弱者。对于精神病患者而言,精神资源的不足或劣势更是关键性的。如果将社会支持固化在弱者或弱势群体(贫困者)身上,客观上必然切断了其他社会成员满足社会支持需求的路径。从社会工作的视角来看,即使再强势的人,也会有面临困难和问题的时候,需寻求社会支持,使问题控制在自身能够掌控的范围,从而减少个体从强者退化为弱者的风险。
第二,将社会支持限定为无偿帮助,把有偿支持排除在社会支持系统之外。在社会工作机制比较健全的国家,许多社会工作服务都是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他们会根据所提供服务的性质和接受服务者的经济状况来决定服务是否是“无偿的”。总之,社会支持与弱者概念的双重“层次化约”的后果,在心理上抑制了人们对社会支持的需要,在现实行动中制约了人们对社会支持的使用。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受吉登斯观点⑧ 的影响,我们将社会支持定义为,一种社会资源被动员和使用的过程与结果。社会支持是资源被动员,并被组织化和系统化的操作过程,它既是获得资源的结果,也是获取资源的过程。这一界定更容易使被支持者获得力量感,他们不仅在社会支持的成果中享受快乐,也能在与支持者的互动过程中体验幸福。如此,社会支持不仅对于精神病患者的康复具有意义,也可使人们更有效地预防精神疾病的发生。
对于个体而言,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是以个体为中心,由“亲缘”、“医缘”和“德缘”三个界限清楚的支持圈所组成,并可分别归类为“原生支持系统”(亲缘支持圈)和“次生支持系统”(医缘支持圈和德缘支持圈)。以家庭为核心,依靠血缘和姻缘关系所维系,形成“亲缘支持圈”,是患者的第一支持圈。支持者因血缘或姻缘关系,而承担支持责任。本次调查发现,当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多数受访者会寻求家人的帮助,也最愿意接受家人的帮助(57.5%)。当遇到挫折或打击时,受访者最多地选择向家人倾诉(65.9%)。这是“帮助意愿”和“实际帮助水平”最高的支持网络。患者因病而寻求医学救助过程中形成的专业支持圈,为“医缘支持圈”是患者的第二支持圈。支持者因职业特点而必须承担职业照顾之责,具有医学取向。“德缘支持圈”是由“他者”——被认为是道德高尚的“好心人(或机构)”构成,向患者或其家庭提供帮助与支持,也可称为“他者支持圈”,是患者的第三支持圈。这一支持圈在法理和情理中均无直接的照顾责任。他们之所以会成为患者的支持圈,是基于其同情心,并由此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利他性动机。我们认为该支持圈的存在对于患者及其家庭是极具意义的,因为它们是脱离“自然责任”而存在,又与患者的终极目标——回归社会相联系,获得他人的接纳与认同。自然责任又分为“伦理责任”和“法理责任”。“亲缘支持圈”主要基于“伦理责任”而形成,虽然有法理责任作为帮衬——当负有伦理责任的人不履行自己的责任时,法律将干涉其行为,强迫其履行责任。“医缘支持圈”主要基于“法理责任”而形成,作为医生或医疗机构必须履行其治病救人的法律责任,同时也会受到医学伦理责任的规制。唯有“德缘支持圈”既非源于伦理责任也非法理责任,而是出于道义。
为此本次调查特以“德缘支持”为重点,结果显示患者及其家人出现了较为强烈的机构性资源的需求。服务于精神病患者的机构,尤其是由社会工作者参与和组织的专业化机构,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效能性,尤其具有非政府性质的机构的非营利性、自发性、持续性、利他性和慈善性等特征,可满足案主从生理康复到心理康复、社会康复和职业康复的系列服务需求;能与人们“单位制”情感需求相契合,使机构照顾彰显出优势和魅力。机构性资源中所提供的精神健康服务实施已成为精神健康社会支持操作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四、精神疾病社会支持的专业性
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缘起于人们维系精神健康的需求,依赖于资源系统的供给。需求是社会支持的接受端,而资源则是社会支持的输入端。对于精神病人而言,他与正常人有一样的需求⑨,可简单归纳为:生活照顾需求、经济援助需求、思想关心需求和医学治疗需求。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蒂钠·罗森布鲁姆等提出,人在精神创伤之后的基本心理需要是“安全、信任、尊重和亲密关系”⑩。本次调查资料显示,精神病患者,在经济需求、祛除污名、赋予话语权、知识需求、治疗需求、相信潜能、适宜的家庭、和谐的社区、机构照顾和拒绝治疗等十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这么说康复者的个体康复经验与团体活动、家属资源、案主系统的人际资源、医疗资源、社区资源、社会工作者资源、政府资源等资源的有无与丰富程度,以及个体与资源之间的有效链接程度,直接影响到个体需求的满足程度。正如受访案主V71所获得的来自亲人和邻里的大力支持帮助,通过对自己病情和康复经验的反思,发现在保持个体精神平衡与获得外在支持之间的关联性,自觉加强和提高自我修复和平衡能力。这种能力对于预防和矫治心理失衡具有超凡的积极意义,以至于重新恢复了精神世界的平衡;案主S1在宽容性的社会支持环境中,不断学习新技能、适应新环境、应对新刺激,在平衡与失去平衡的循环中,使她形成了习得性自我强化机制。所谓习得性自我强化机制,是指个体在失衡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与人际环境的互动,其需求得到关注与满足,而使其逐渐趋向平衡;当个体处于平衡状态,如果个体不注意保持与人际互动,其需求便得不到关注和满足,从而使其逐渐失去平衡。个体在往复中学习到一种经验,趋利避害,并将经验自觉地运用到后续的应对失衡和保持平衡的行动中,被强化。当个体发生精神疾病时,或个体应对和适应紧张环境时,将产生特殊的社会支持需要,当这种需要没有获得满足,可能导致个体精神世界的失衡,加剧其精神失衡状态,从而增加了社会运行的风险因素,进入恶性循环。总之动员和整合满足个体需要的社会资源,是促进其维持精神健康的基石。
调查显示除家庭外,精神疾病患者的需求均直接指向社会,依赖于适宜的社会环境,需求和资源的社会性决定了社会支持的“非自决性”。在社会支持的建构中,社会性特征易使社会支持在自发中陷入虚无。调研发现,尽管建立精神健康社会支持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人们在精神健康方面获得的有效社会支持服务却十分微弱。发达国家在长期的精神健康社会支持研究和实践中,逐渐凝练出专业化社会支持的经验,将缥缈的社会支持的社会性根植于专业性的培基上。虽然,根基尚不很扎实,但已经初现端倪。
所谓专业性社会支持是以患者系统康复(包括生理、心理、职业和社会康复)为目标,融入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机制,将社会工作价值、理论和实务技巧运用于社会支持的服务实践,具有针对性地全面、系统地满足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的康复需求。该支持应包括下列要素:支持者、介入伦理与理论、介入方法与技巧、工作程序和功能等。支持者必须为接受过社会工作专业训练的、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社会工作者。在美国,精神健康社会工作除需有秉持保密、接纳、案主自决、个别化、沟通、自我认识、妥善处理情感转移等七大伦理原则之外,必须在主观上对精神病患者持有宽容的态度,能够灵活运用人在情境理论、问题解决理论等社工理论,充分了解精神病人及其家属的特殊需要,理解和处理患者的问题和困扰。能够超越理论的界限,把理论融合在一起,以达到最好地帮助患者及其家属的目标。从方法上看,专业性社会支持包括个案社会工作、团体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行政。运用个案工作方法在病人的诊断、照顾、治疗和人格重建过程中,负责辅助病人及其家属,收集患者的与精神疾病有关的生活史、家庭心理动力的资料,并加以分析和评估,为治疗小组的诊断提供依据;协助病人及其家属了解病人的疾病与反应,解除其因患病所引发的焦虑和困扰,引导他们善于运用并接受现有的治疗。与病人及其家属探讨生活中影响病人正常社会功能及妨碍治疗的因素,并协助他们谋求改善的有效途径,进而帮助病人发展比较健康的人际关系;开导病人及家属改善不理想、不合乎现实的态度,积极挖掘患者的潜能,以强化其在环境适应上发挥较具有效能的适应方式。以社会团体工作方式进行心理、社会生活教育,以促进社会生活再适应能力,人格的重建、人际关系的改善,以及心理疾病的预防等目标。社会工作者常代表病人或其家属,从事临床小组与社区之间的联系与协调工作;开发运用社区或社会资源,并参与社区卫生保健服务计划以适应病人及其家属的需要和增进其福利。社会工作者参与政府卫生行政中有关精神健康法规的设计、宣传和执行,以有效发挥社区心理卫生功能。从程序来看,专业的社会工作支持包括接案、预估、介入、评估、结案和追踪随访等程序过程。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一般功能包括:个案研究与诊断,对病人家属的心理辅导,对轻度病患的个案治疗,辅导病人再适应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开发运用社区或社会资源,参与心理卫生训练计划,参与团体、社区精神卫生咨询和推广工作,参与医院或机构的重要行政计划与决策,进行相关调查研究,参与精神健康法规的设计与执行。
社会支持服务的操作性是构建专业化社会支持体系的基础。离开操作性,社会支持的专业化便无法实现。因此,社会支持的操作性命题成为精神健康领域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界的共同使命。社会工作介入方法与技巧、工作程序和功能等要素不仅是专业化社会支持的内涵,也是操作性社会支持的具体途径。操作性命题在具体的支持性实践与理论研究中被不断的拓展和延伸。WHO在其一系列的报告中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性策略,如将精神疾病治疗纳入良好的常规医疗保健,保证治疗精神病药物的可及性;制定具体的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健康政策,提高用于促进精神健康的卫生预算;进一步拓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照顾,培训卫生工作者,提高其认识和处置一般精神疾病的能力;开展公众的精神健康教育,以减少精神病的污名,鼓励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寻求帮助,加大对研究的经费投入等指导性操作策略来缓解精神疾病。正是在社会支持的视角下,有研究认为常规治疗(TAU,Treatment as Usual)既无害和也无效,无效的支持服务通常不会导致巨大的消极结果,但患者退出服务的比率非常高,因而存在自杀、攻击和伤害风险,恶劣的结果并不能被掩盖。如果我们不去收集用以测量有效性的信息,而掩盖自己所提供服务和公共服务的无效性,案主可能并不知道他们接受的是无效服务(11)。因此,对常规治疗作质量和有效性进行监测的疗效评估反馈系统(MFS,Measurement Feedback Systems)成为操作化发展的措施之一。总之无论缘于研究还是实践,专业性支持中,所有操作性策略的终极目标与评估指标必须归结为有效性,但是离开操作性前提,目标与评估将被悬置。从国际学术性研究成果来看,专业性社会支持的操作化发展趋势日渐明显,但是有关操作性社会支持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细致地探讨和实践。而该实践对我国的社工实践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 Mental Health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Special Report).Encyclopedia.World News Digest.Facts on File News Services,Oct.2001.Web.26 Feb.2010.http://www.2facts.com/article/xn05760.
② T.Scheff:Being Mentally Ill (2nd ed.).New York:Aldine,1984.
③ T.S.Szasz: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The New York:Delta,1961.
④ 乔治·辛普森在涂尔干的《自杀论》一书中的“编者前言——自杀的根源”中所述,钟旭辉译,[杭州]哲学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⑤ 陈成文、潘泽泉:《论社会支持的社会学意义》,[株州]《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6期。
⑥ 亚历山大认为当研究者武断地认为一种层次的特性最重要,并且用它来进行本来有多层次特性的社会学研究,就发生了层次化约。
⑦ 陈成文:《社会弱者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⑧ 吉登斯认为“资源能以不同的形式被动员起来,通过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权力的运作来操作行动与实现结果”,参见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⑨ 王志英:《当今精神科护士的角色功能》,[北京]《中华护理杂志》1998年第7期。
⑩ Dena Rosenbloom,Mary Beth Williams,Barbara E.Watkins著:《精神创伤之后的生活》,田成华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页。
(11) Bickman,L.(2008).Why Don't We Have Effective Mental Health Services.Adm Policy Ment Health,35(5):437-439.DOI:10.1007/s 10488-008-01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