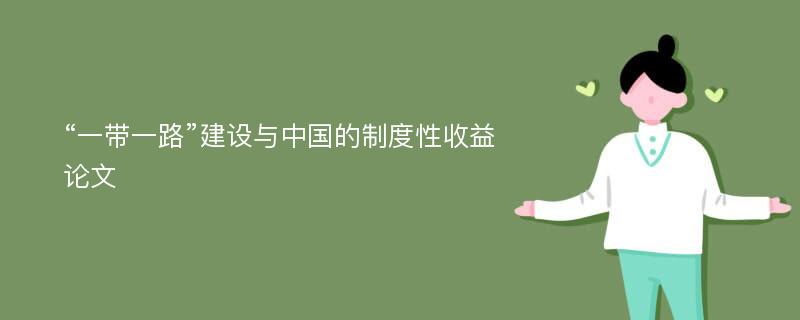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的制度性收益
杨 剑 张 明
【内容摘要】制度性收益是通过制度调节或变迁获得的收益。在维护现行国际制度平稳运行的同时,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合作增进与国际制度的良性互动,向制度提供者和受益者兼具的复合身份转变,进而获得制度性收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而获得的主要制度性收益包括:在区域治理和领域治理中,来自中国的制度方案增加;中国倡导的机制性安排的增加促使一些区域发展问题和挑战得到较好应对;中国与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的互动因为这些制度的存在和完善而更加顺畅;中国相关实体借此可以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更广泛领域获得更加持久稳固的制度保障等。“一带一路”建设所形成的制度和合作机制具有动态性、实践引导性和情景针对性等特点,这些都是体现制度有效性的关键因素。以盟国体系为基础的旧的国际秩序的干扰,以及沿线一些国家的文化或制度安排与“一带一路”制度建设之间潜在的摩擦,是“一带一路”制度建设面临的挑战。中国应在制度建设中注重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建构,重视制度建设的兼容性。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 国际制度 制度性收益
“制度(institution)是权利、规则、原则和决策程序的集合,它们引发社会实践,为实践的参与者分配角色,并指导实践者彼此间的互动。制度是各层级社会组织治理系统显著的特征。制度之下的机制(regime)是解决功能性议题或区域问题的特定制度。机制构筑了制度的合理子集。”[1]“一带一路”建设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最佳实践。它的实施必将对国际关系中的权利、规则、原则和决策过程产生深刻影响。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并使之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一直是中国外交的努力方向。这种努力是对现行国际制度的完善。国家作为国际制度的基本参与主体,既受到国际制度制约,同时又有可能对国际制度的变迁施加重要影响。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有可能通过国际合作对国际制度加以修改和完善,解决国际社会普遍关切而既有国际制度又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这显然也有利于该国与他国关系的互动和发展。这些都属于制度性收益范畴内需要讨论的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国际合作是实现并获得制度性收益的有效实践平台。五年多来,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资金融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已经形成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合作机制。这些具有制度建设意义的实践,是推动全球治理制度变革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责任感。[2]
制度性收益是指通过制度调节和变迁而获得的收益,中国是现行国际制度的受益者。目前,在继续维护现行国际制度的基础上,中国可以通过区域性和领域性国际合作增进自身与国际制度间的良性互动,引导形成国际关系中的制度共识,并从过去国际制度参与者的单一身份向国际制度提供者和受益者兼具的复合身份转变,进而获得制度性收益。这些制度收益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在全球区域治理和领域治理中,来自中国的制度方案增加。二是因为“一带一路”机制性安排的增加,一些区域发展问题和挑战得到较好应对。三是因为这些机制性安排的推广和运用,中国与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进程将更加顺畅。四是因为制度的变迁和改善,中国相关实体可以获得更加长久稳定的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交流的实际收益等。
本文拟从全球发展议题制度变迁的需求、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可能获得的主要制度性收益、制度变迁的和平路径以及获得制度性收益所面临的挑战等方面展开相关讨论。
一、“一带一路”建设与制度性收益
与国际制度的互动是一个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反映其对现行国际制度关于权利、原则、规范的认知,遵守程度以及对制度变迁的动力、方向的认识。这种互动关系虽然相对稳定,但也会由于综合国力的上升以及新的国际问题的出现和变化而产生调整的需求。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实力的增长以及全球治理对制度类公共产品新需求的扩大,中国与国际制度间的互动关系逐渐转变,呼应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也逐渐提升。这种转变不仅可满足中国自身利益的需要,同时也可回应国际社会在相关问题上对中国的期待。
(一)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是中国获得制度性收益的机遇
当前,治理赤字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3]在技术进步、环境变化和社会发展三大要素驱动下,既有国际制度已无法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这就使得全球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进而引发全球层面的秩序紊乱,一些欠发达地区不仅长久未能跟上现代化进程,而且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的能力也相对滞后。因此,开发和推出更多更好的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需求的全球公共产品是改善治理赤字现状的有效手段。
中国并非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唯一提供者,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兴大国,中国在相关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出现了社会危机,联合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建立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伙伴关系的倡议在西方发达国家遇到了“逆全球化”及“经济民族主义”的阻挠。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则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有了新的期待,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治理方法和路径也让很多发展中国家体会到了中国之于它们的借鉴意义。在此背景下,中国既要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也应更为理性看待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现实地位和角色,更多地面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为实现区域和全球有效治理做出自己的贡献。
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与制度性收益具有正相关关系,从传统大国的实践看,一国在全球影响力和塑造力的提升速度曲线与该国提供公共产品的成长曲线具有一致性。一个国家的全球影响力反映的是其在国际关系中推行自己主张并受到拥护的能力,而全球塑造力则反映其推进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创设国际议程和塑造国际制度的能力。全球影响力和塑造力的提升都为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制度提供了制度性收益空间。中国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对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际声誉以及增强和平崛起的正当性均可产生积极的正面作用。这不仅有助于回应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热切期盼,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进而获得制度性收益。
(二)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获得多方面制度性收益
第一,“一带一路”区域治理中国制度方案增加。习近平主席在论述全球治理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份额和治理机制改革,积极参与制定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推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4]习近平主席讲话中的目的指向很明确,就是要推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不公正不合理安排,为此,努力争取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和世界文明发展方向、富有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不断增加。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的治理方案逐渐演变为区域治理制度和机制,其运作则能证明中国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制度性收益。
第二,因为“一带一路”建设机制性安排的增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一些区域发展问题和挑战将得到较好解决。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包含中国与特定国家在双边之间实现发展共赢的目标,也包含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区域发展层面贡献中国力量的效果。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机制性安排,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区域发展目标做出了制度性贡献,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机制化合作实质上就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特别强调的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关系合作。2012年9月,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差距问题工作组发布题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让言语成为现实》的报告,来自联合国系统的各方面专家在报告中认为,围绕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全球合作中的新进展乏善可陈,并且首次存在倒退的迹象。报告表达了对“建立促进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进展缓慢的不满。报告指出:“任何人都不应假设全球科学和企业创造力分布与全球收入分布相称。由于一些地区依然贫困,而机遇又青睐于富裕地区,因此,全球潜能未得到开发,因而既没有科学突破和发明,也没有实现创新的商业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必须努力克服这些制约因素和解决不平等问题。”[5]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全球伙伴关系进展乏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在2011年首次开始下降。他代表联合国敦促发达国家不要把财政紧缩的负担转嫁给穷人或穷国。而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对联合国倡议的有益呼应。通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改变了自身面貌,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成为联合国完成其千年发展目标最有成效的国家。如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在区域层面建立起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的伙伴关系,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在解决全球性和区域性发展问题上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第三,通过相关机制性安排的推广和运用,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进程变得更加顺畅。制度性收益的一个重要含义是指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改善给相关利益攸关方和权利攸关方提供激励的程度,其体现在降低交易费用、减少外部性和不确定性等方面。来自不同文化制度背景的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在一个共同空间中为实现共赢目标必然会产生制度上的交互过程,这个过程是新制度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完善后的制度性安排会更加有利于相关行为体的顺畅互动,减少制度摩擦和信息不对称。“一带一路”建设不论是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还是贸易畅通,都包含着中国经营模式与“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法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互动和兼容过程。来自中国的一些制度性安排作为新的国际制度资源,在引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过程中必然存在调整和适应问题,同时还存在制度性安排与当地法律等制度环境兼容的问题。这个“引入—适应—兼容”的过程完成得越顺利,中国与相关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就越顺畅,进而一些建设项目的成功就会越显著。例如:中国与俄罗斯、巴基斯坦、蒙古、老挝、尼泊尔、新西兰、沙特阿拉伯、叙利亚、越南等国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共同建立“一带一路”会计准则合作机制并发起《“一带一路”国家关于加强会计准则合作的倡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与49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知识产权机构共同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务实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与相关国家税收管理部门签署《“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谅解备忘录》。[6]这些围绕知识产权、会计制度、海关制度和税收征管等方面对接协调机制的行动,会大大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的人员、资金、货物、信息交流的便利性。
第四,因为相关制度的变迁和改善,中国有关实体可以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获得更加长久稳固的实际收益。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主张的制度方案将在更大地域范围内得以推广。“当国家间的制度秩序不同,从而在不同国家间做生意或转移生产要素的人要承担不会在同一国家内发生的成本时,就会产生国际性制度接轨成本。”[7]因此,基于共同制度的交往与合作有助于以最低成本促进交易和缓解冲突。“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硬联通”的过程,也是推动制度“软联通”的契机。在制度“软联通”的进程中,中国国内制度标准能够更为顺利地兼容国际制度。跨境交易的人民币结算,部分沿线国家对中国知识产权审查结果的认可等,都说明了中国国内的标准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认可。此时,中国以及中国商事主体在走向全球时能够有效避免制度差异所带来的“阵痛”,有效降低制度性接轨成本。国际标准是企业迈向国际市场的通行证,也是国际制度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公司自身实力不断增强,中国技术质高价廉,越来越多的海外市场开始接纳中国的技术、商品与服务。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公司的企业标准逐渐上升为国际标准,大大增强了中国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例如,中国铁路技术的海外输出已经不再仅局限于基础设施建设或整组列车的海外销售,而是逐渐实现了基建、设备设施和中国标准的全套输出。此外,中国企业所主导的通信行业、互联网行业技术标准得到越来越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承认。例如,华为5G通信技术系统以技术标准、操作系统和管理方式为内容的技术制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落地生根。
4.2 随着发酵时间的延长,不同混合青贮中主要微生物的数量均呈逐步减少的趋势,发酵至第11 d时,25%的青贮饲料中乳酸菌达到最高峰;50%、75%、100%的青贮饲料中乳酸菌数量在第20 d时达到高峰。之后乳酸菌数量缓慢下降,75%的青贮饲料中乳酸菌数量下降较慢且数量最多。综上所述,75%的青贮饲料有利于甜高粱混贮饲料的制作。
式(8)为t阶段依据重量等级船舶贝内集装箱重不压轻的约束,其中,θk(t)为集装箱k(t)的重量等级。
(三)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国内开放制度再升级
国内制度是一国参与国际事务并推动国际制度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础。与国际制度不兼容乃至相悖的国内制度,不仅会妨碍国家参与国际制度安排,也会阻碍有效的国际制度的建立。因此,无论是过去中国打开国门让自己的生产要素加入全球分工体系,还是当前通过走出去建设“一带一路”,中国都需要建立完善的、与国际制度相兼容的国内制度体系,为参与国际制度提供国内制度基础和保障。
全球化是推动国家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影响着国家的制度体系。[8]在国家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对国内制度进行适应性调整。中国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制度收益,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国内相关制度的再升级。为配合“一带一路”建设和“走出去”战略,中国国内制度需要在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内进行完善和提升,需要与国际制度有更全面的衔接和兼容。这既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与之相关的制度收益。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将更积极主动地完善国内制度。过去,在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为适应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和开展贸易的合理要求,中国以在地需要为目标调整各项国内制度,扩大开放,进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进行的制度调整就说明了这一点。现在,中国开始主动走向国际市场并更多以投资者身份出现在世界面前。这时,中国将通过自身在外投资和经营中所形成的内外联动使中国的国内制度更好适应国际经济贸易环境。例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优化境外投资综合服务而制定并施行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等,都是中国为实现“走出去”目标而完善国内制度的体现。
在解决商事争议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开始建立了国际商事法庭,并颁布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具体实践必定会促使中国立法和司法工作适应“一带一路”建设实践的特点,体现出打通内外两个市场和内外两套制度体系的特点。制度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缓解不同行为体间的冲突”[9]。国内立法和司法协调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的调整,将有效缓和“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之间和参与国商事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在实践过程中,中国仍需内化“一带一路”倡议下所形成的各项国际制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所新订的国际条约或合作协议等都是对中国国内制度的补充和完善。截至2019年4月30日,中国已经与131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87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0]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还将与更多的国家就相关制度议题达成共识。
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借参与全球治理之力完善国内制度体系,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国内制度将被国际制度同化。恰恰相反,“一带一路”建设将有助于中国建立更加开放、更具先进性的国内制度。面对新时代的战略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需要借鉴吸收一切有益的制度成果。
二、国际制度的和平变迁:中国获得制度性收益的路径选择
制度变迁源自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技术动力,“一带一路”的制度建设也有其发生的动力来源。就当前而言,全球技术和市场变化对于制度变迁有较大影响,“规则导向”和对发展有效性的追求,则助推国际制度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实践中,我们还需注重一般原则与具体合作实践的结合,注重秉持开放包容态度,推动更多主体参与国际制度建设。
(一)“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国际制度变迁的动力分析
有的研究从国际关系的历史经验得出结论,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新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之间的挑战与遏制最终会导致战争,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24]。美国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成为人们热议的“课题”。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强调制度变迁的和平性有利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当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由资本、市场、技术、资源等体现的国家实力获得提升后,该国的确会获得对国际制度变迁的巨大影响力。如果这个国家提出的方案代表着先进文明发展的方向,代表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向,那么它所引导的国际制度的变迁就容易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总体目标没有变,那就是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25]。在新型国际关系中,合作共赢是核心理念。实现合作共赢,就是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推动形成包容性发展的国际制度体系。
第一,“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部分来自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旷日持久的全球危机对国际发展合作产生了新影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连续多年未能走出低谷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断增加。20国集团在2011年11月召开的戛纳会议上表示,有必要为发展和全球公共产品寻找新的资金来源。2011年11月29日,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次援助实效问题高级别论坛上,与会者一致同意建立“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关系”,为此确立了一个一致认可的发展合作框架。该框架的捐助方除了昔日的发达国家外,首次涵盖了南南合作方、新兴捐助方、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民间组织和私人资助者。[14]
第二,全球技术和市场的变化也构成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当今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间的间歇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是信息技术,它的应用让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走向信息化。因为网络平台的存在,远程教育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得到新技术的职业培训。如果资金和技术条件具备,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希望在下一次工业革命中成为创新基地,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获得更佳区位配置。但是一些技术发达国家控制着资本、技术、市场、知识产权和规则制定权,并顽固地将世界其他国家作了两种定位,一类被塑造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球生产提供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国家,另一类国家则成为全球生产的原料供应者。一些发达国家人为地阻碍知识分享和技术转让,以安全理由限制发展中国家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得技术和知识。因此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共同期待,那就是改变不合理的世界经济分工格局。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示范作用激发了发展中国家对新型国际合作的期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积极学习国际制度和融入国际制度的过程中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在大规模的社会学习过程中,不断内化世界先进的管理经验、规则和制度。[15]中国融入国际制度不仅增加了其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也促进了中国自身的发展和转型。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通过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中国获得了快速发展所必需的资金、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资源,快速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从国际制度发展的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国际制度与中国具体的发展实践相结合的制度发展过程,它是国际制度与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相结合的结果。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治理经验的积累,使得全球治理的工具箱中又多了一种选择。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诸如气候变化、资源环境、生态危机等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既有的国际制度已经无法解决和应对这些挑战。此时,中国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实践平台,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和利益嵌入到新的制度性安排之中,与志同道合者一起推动国际制度变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规则导向”,追求发展,推动国际制度公正合理化
2018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把握世界经济发展方向探索治理思路的五个方面内容,其中包括开放导向、发展导向、包容导向、创新导向和规则导向。关于坚持规则导向完善全球治理问题,习近平主席指出:“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变革过程应该体现平等、开放、透明、包容精神,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16]“规则导向”是“权力导向”的对照,以规则为基础加强全球治理是实现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习近平主席还强调指出:“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搞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合则用、不合则弃。”[17]“规则导向”提倡对制度的遵循与尊重,提倡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并在制度的框架内解决问题。
当然,在加强制度建设的服务功能的同时,需尊重当地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教信仰和民俗习惯,同时还要尊重一部分暂时不能从发展中获利的当地民众的利益和诉求,保持政策沟通,促进民心相通。
(三)对发展问题解决的有效性是“一带一路”制度落实的关键
另外,中国将“一带一路”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相联系,可以更广泛地吸收当今世界围绕发展和治理已经产生的许多先进理念和制度工具。各参与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将最大程度缓和彼此间的分歧而推动符合各方利益的合作,进而实现整体的共同发展。
第五,国内旅游演艺发展的大背景。在张家界旅游演艺发展起步之初,国内旅游演艺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突飞猛进的阶段。张家界在不断借鉴国内其他成功旅游演艺的过程中,深入挖掘湘西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演艺品牌。
“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各参与国建立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促进区域合作蓬勃发展,通过召开峰会或者定期会议,建设各类信息交流平台以及签署各类双多边协定的形式,促进相互间的合作。随着交往的日趋频繁,国际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需求增加,并愿意根据国际制度的规则去行为。[22]理论上说,以硬法形式存在的国际法律制度,如条约和协定等,具有较强的规范作用和强制力。但是,从既有实践情况看,“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制度以硬法形式存在的较少,大多以行动计划、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倡议、声明等软法的形式呈现。尽管这些文件不具有正式的法律约束力,但相关行动计划、倡议等软法文件的形成预示着各方已经就某些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有助于为各方的后期行为确定行为指南,也有助于为硬法规范的形成奠定基础。这恰恰体现出“一带一路”制度建设的实践性特点。
从过去五年的实践来看,“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制度和合作机制具有动态性、实践引导性和情景针对性的特点。动态性是指相关制度和机制自它们建立之时就开始不断随着目标、环境和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实践引导性指的是“一带一路”制度建设的依据源于其多行为体广泛的实践活动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规制;情景针对性指的是“一带一路”制度建设要对不同的情景做出调整,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将一般的规则和原则与具体合作实践相结合。这些都是衡量制度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兼蓄更多国际制度资源
国际制度资源是软权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对国家而言极为重要。[23]“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试验平台,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起步阶段。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过程,积累建立国际制度的经验,体会国际制度解决区域和全球发展问题的内在机理。通过共商共建和共享这样的互动过程,同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等各种合作方一起协商和构建,从而学习和掌握更多的国际制度资源,为未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打下坚实基础。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使得中国有机会以主导国的身份推动建立更多的国际制度。“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制度规范来促进实践,例如多边投资协定、自由贸易区、金融监管、货币体系合作等。这些国际制度的建立,都将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积累更多的软权力资源。这种软权力资源在国际制度“规则转向”的背景下,不仅有助于降低中国以及国际商事主体在国际市场间的交易成本,还有助于在步入国际市场时得到更安全更公平的制度保护机制。
在“一带一路”的制度建设中,中国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发达国家仍然是国际制度的主要参与者,一带一路”倡议在进行制度建设时始终秉持开放与包容的态度,力求让更多的国家、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参与进来,这就决定了“一带一路”倡议将推动更多的主体共同参与国际制度建设。
因此,对不同开关状态(S1和S2,S3和S4,S5和S6)分别注入脉冲信号,当开关关断时,分别由二极管D4和D5,D1和D6,D3和D2进行续流。两种开关组合开通和续流时的电路和端电压示意图分别如图5和图6所示。
{XmlDocument xmlDoc=new XmlDocument();//定义一个XML文档对象
制度变迁可被视为一个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20]美国学者奥兰·扬(Oran R. Young)从有效性视角对国际制度进行讨论并认为,“只有当一种制度达到其运作能促使行为体改变其行为的程度时,才能说是有效的。如果一种制度的运作能够经受个人和集体行为因时空转换而发生的显著变化的考验,该制度就是有效的。”[21]“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以经济合作为主的国际倡议,如果其下的国际制度能够促成全球发展和区域发展中参与国之间以及参与国商事主体之间的合作,且这种合作能够促进发展并保持活力与稳定性,那么则应当认为是有效的。
这天晚上,布鲁诺从睡梦中惊醒,只见铁门上的粗链眶眶一声落了下来,门洞里走进两个举着蜡烛的教士:“布鲁诺先生,主教大人有请!”他知道又要审讯了,便不慌不忙地披衣起身,跟着走出门去。
(五)制度变迁的和平性有利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制度变迁概念源自制度经济学。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是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人物。诺思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过程。[11]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变迁动力源泉是“变化着的相对价格与偏好”[12]。与之相匹配,制度变迁的过程就是“一种相对价格的变化使交换的一方或者双方感知到改变协定或契约将能使一方甚至双方的处境得到改善,因此,就契约进行再次协商的企图就出现了。在此情况下,有希望改进自身谈判地位的一方就极有可能投入资源去重构规则。长此以往,规则就能被改变,或被弃之于不顾,或不被实施。”[13]也就是说,制度变迁是一个为寻求收益而对既有制度重构的过程,它的发生源自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动力。“一带一路”的制度建设也有其发生的动力来源。
全球最大的政治就是发展。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和其他区域性的发展合作来构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不仅开创了区域合作新模式,也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贡献。如何呼应“一带一路”倡议,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回答。大多数发达国家政府也已经明确认识到“一带一路”建设的世界意义,并表示愿意参与其中,共同努力,促成全球发展大业。然而仍有极少数欧美发达国家处于困惑之中。这些困惑很大程度源自它们自身长期形成的霸权影响力思维,源自它们对全球治理权曾经的垄断以及对非西方国家整体发展的不适应。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媒体以“解构式”的传播方式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妖魔化,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部分国家和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忧虑和质疑。[28]部分西方媒体将“一带一路”倡议形容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29],或冠以“债务陷阱”、“中式全球化”等标签。[30]这些不当宣传无疑会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民众心理产生负面影响,加剧源于文化和制度的摩擦。
3)数据连接层:该层次将业务逻辑层的请求转换为HTTP请求与Web服务器交互,并获取结果返回给业务逻辑层。
成锐说,铆工又称为冷作钣金工,其工作内容主要是把板材、型材、线材、管材等,通过焊接、铆接、螺栓连接等加工方法制作成钢结构的一种制作工艺。在这些工序中,铆工是金属构件施工中的指挥者,要对放样、号料、下料、成型、制作、校正、安装等工艺非常了解。
三、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获得制度性收益面临的挑战
尽管“一带一路”建设对世界经济和区域发展以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有很大促进作用,但是由于这涉及全球政治格局走向民主化和多元化的结构性权力的变化,守成大国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可能形成的制度方案的竞争会采取排斥措施。“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经济贸易等诸多领域,而各参与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和法律体系等亦不尽相同。此外,来自其他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国际制度方案的竞争也会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影响。因此,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以获得制度收益也必然会面临某些困难与挑战。
(一)以盟国体系为基础的旧国际关系的掣肘
国际制度的变迁与国际制度的竞争相随相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加大了对中国和平崛及参与国际事务的遏制力度,这对中国获取“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性收益将产生极大的干扰。
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金融发展水平薄弱,人力资本存量较低。尤其是当前,西部地区作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进方和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如何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因此,现阶段从人力资本视角研究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揭示如何实现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对于我国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2017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政府将当今世界描绘成一个“异常险峻”的世界,强调美国的领导权和优先地位,并将中国列为“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对来自非西方的制度改进方案表现出了极大的排斥态度。该报告认为,中国“试图根据自身利益改变国际秩序”并“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26]这表明,当前的美国政府更多以潜在或现实竞争对手的眼光而并非合作共赢的眼光认识中美关系。这种冷战思维必然会强化美国对中国的限制,特别是美国通过强化盟国体系,要求其盟国不与“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以此阻碍“一带一路”倡议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进展。正如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曾经所言:“全球治理制度缺乏的是竞争者的存在。要使治理体系的权威能够被接受,使其有效率并受人尊重,那么就必须要有某种联合起来的力量来制约权力的任意使用或谋取私利而使用权力,保证权力的使用至少是部分地为公益着想。”[27]美国等少数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态度说明,它们无法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应对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反而拘泥于美国影响力与中国影响力的此消彼长。
从中国的角度看,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将把重点放在沿线国家普遍关心的发展问题上,并不会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去构建所谓的盟国体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强调多方合作主张,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等方式来实现目标。对既有国际制度,中国承认其发挥的作用,同时认为应当加以改进和完善。为了实现在和平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结伴不结盟”,以经济优势互补和相互发展需求为基础建立和发展伙伴关系。中国既建立了与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如中国与柬埔寨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也建立了与一些发达经济体的伙伴关系(如与瑞士之间的“创新战略伙伴关系”、与芬兰建立的“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等),而且不以合作对象国是否为美国的盟国来划界。中国用发展带动安全问题的解决,用合作促进和平。在“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因为欠发展,许多地区的居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一些地区民族冲突、宗教冲突甚至恐怖主义袭击频频发生,如中巴经济走廊所经过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等。而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则给这些地区重新带来了发展的希望。这些都表明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制度变迁的路径是和平的。
(二)多种国际制度方案的竞争态势对“一带一路”制度建设的影响
除美国外,欧洲大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在推进诸多与中国存在竞争关系的区域合作倡议,如日本的“新丝绸之路外交”、欧盟的援助开发计划等,刻意抵消“一带一路”倡议所形成的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制度和机制安排的影响。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大多有自身的一体化合作机制和制度体系安排,如东盟、非盟和海湾合作组织等。有些国家甚至处于多重制度体系的叠加区域。这些地区性的国际组织有自身的制度建设目标和方式。因为它们是在地的域内组织,成员间存在较强的认同感,在区域合作的制度建设上已经拥有了多年的磨合与运作经验,因此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制度倡议的“兼容”也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再则,在全球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它们或注重气候变化问题,或关注劳工、妇女、当地居民权利的保护,或强调自然环境和动植物的保护。它们对于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也都有着自己的治理方案和远景设计。总体上讲,这些制度方案和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是相通的,但是对于权利、责任的原则,对于事物的轻重缓急和政策安排主张有所不同。
如果欧洲和日本的应对方式是提供与中国类似的、以促进当地发展为目标的经济振兴和基础设施发展计划,建立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双边和多边机制,这实际上是符合“一带一路”共商共建的精神和目标的,是制度之间的良性竞争,应当乐观其成,甚至开展合作。例如中国与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都已经就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协议并在实际推进之中。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性组织的制度和机制方案,我们应通过政策沟通和战略对接增加制度的兼容性和包容性。对于许多非政府组织,“一带一路”的实践更会倾听它们的声音,吸收它们的一些正面理念和制度性安排,使之变成“一带一路”建设的正向推动力,而不是阻力。
(三)沿线国家的文化和制度因素与“一带一路”制度建设的摩擦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参与程度是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的体现。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程度直接决定了中国所提供的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制度能在多大的范围内得以推行,也决定了中国能在多大范围和多大程度上获得“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性收益。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100多个国家,并跨越多个地区,因为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社会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所以开展“一带一路”制度建设也必然需要和沿线国家进行文化和制度上的磨合。文化和社会制度因为植根于历史传承的土壤而具有某些滞后性,对于新的外来引进文化和制度的兼容和吸纳会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制度建设实践中,更多的是通过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来促进机制和制度改进,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来确定双边的和小多边的合作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自下而上通过发展中国家合作实现的制度变迁路径。这些制度设计不仅没有颠覆性,而且体现了包容性,以及对时代发展和解决全球与区域发展实际问题的针对性。
(1)为验证本论文提出的SRBM算法预测评分的准确率,就硬聚类算法(K-means聚类算法)、隐语义模型(LFM)、自编码器(autoencoder)、RBM以及SRBM算法在不同数据稀疏情况下准确率进行了分析比较。如图8所示。
制度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的发生和发展一定要顺应某种社会需求。“一带一路”制度建设顺应的是沿线国家对发展的迫切需求。需求越迫切,沿线国家对新制度的接受度就越高。因此,为了获得更多的制度性收益,中国必须重视“一带一路”制度建设的服务功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表明,凡是对发展需求越迫切的国家,在促进当地制度与“一带一路”制度衔接方面就越积极。越是能够促进信息、资金、人员、货物、技术流通的机制安排,就越容易受到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欢迎。
“一带一路”倡议基于参与国间既有的双多边合作机制和国际制度,通过制度探索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制度合作也有效地回应了参与国对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制度的诉求。“一带一路”建设实际上解决的是联合国主张的发展问题和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方既包括了中亚、中东、非洲、南亚、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参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因此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和代表性。国际制度的合法性程度决定了该项国际制度在方案竞争中的竞争力,其中成员方之间利益与权力分配的公平性以及成员方参与的广泛性,权利公平性和成员参与性是合法性的基本指标。[18]“一带一路”倡议对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制度的回应,使得其自身更具国际制度的竞争力,因此也能够为国际社会包括中国自身带来更为丰厚的制度性收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并成为区域发展主要公共产品的提供国,是中国国际领导力日益提升的体现,也将“有助于国际制度谈判的成功”[19]。
此外,城乡规划还有点瑕疵,还需整理。例如:大道两侧还有居民区,斑块农田路、渠、林散乱等。同时,耕地的多重功能作用宣传力度不足,特别是农作物具有生态氧吧的作用没有及时做好宣传。
四、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制度性收益的策略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要把获得制度性收益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并系统思考制度性收益的获得和保有方式及路径。当前,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获得制度性收益还处于初始阶段,围绕制度建设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以及其他结构性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一)重视制度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建构
“如果没有一种连贯的思想体系,制度就不可能生根滋长;如果产生制度的思想衰退,制度就不可能保持有效。”[31]国际制度是国际社会成员参与国际治理和全球治理所形成的制度化成果。换言之,制度建构即通过把认同、利益和规范社会化,进而转化为一种相对稳定的认同与利益结构的过程。[32]从制度建构的层次看,治理哲学处于顶层位置。这是国家治理或者国家参与国际治理和全球治理所具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意义的系统理论。
中国领导人围绕全球治理和应对全球性挑战,提出了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当然,将治理理念落实到具体的制度中去还有很漫长的过程。无论是全球治理还是“一带一路”建设都有很多制度、机制和组织需要建立。“议程设置能力”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获得制度性收益的短板之一,如何让“一带一路”的具体制度建设不与最高治理理念脱节,其中关键的环节就是重视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建构。
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民主、天赋人权、保护竞争、保护财产等价值体系构成了其治理哲学的主要内容。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对建构国际制度的价值体系有帮助作用的词汇包括人道主义、可持续发展、尊重与平等。这些词汇,上可以衔接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和对国际秩序的哲学思考,下可以成为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制度方案和行动计划的依据。西方国家对他国内政进行武装干预时常常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名义,并冠以“人道主义”标签。知识体系是形成制度技术层面结构的基础,可以为某种制度提供说服力和逻辑支持。知识体系可以转化成一系列包括规范、层级管理、裁决、检查等环节的微观技术系统,从而构成一种权力关系的结构网络。相关的例子有国际上基于生物洄游规律的知识体系所建立的海洋养护制度等。
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在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方面相互认可的行为体往往会对彼此间所倡导的国际制度产生共鸣。一方面,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践去感知国际社会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界和决策界也要努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治理哲学与具体的制度建设之间建立中国方案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进而指导相关制度和机制的生成和发展。通过增强价值体系的先进性和知识体系的说服力来提升中国制度方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被接受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通过互增信任减少隔阂,进而形成有关国家间共同体般的归属感。通过坚持不懈的文化教育交流、政策沟通和战略对接,中国版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就能获得更多“一带一路”合作方的认可,进而更多地体现在制度建设之中。
(二)在解决发展问题的过程中与相关利益和权利攸关方共商共建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同时也是突破困境的过程。随着合作的深入推进,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会逐渐消除,中国的价值理念和知识体系也将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进一步推广。这些都有助于中国在参与国际制度建设时争取积极有利地位。
一方面,若A∈ξ-1(O),即ξ(A)∈O,{ξ(A)}∩O≠Ø,显然clY{ξ(A)}∩O≠Ø,由clY{ξ(A)}=clYf(A),于是clYf(A)∩O≠Ø,易证f(A)∩O≠Ø,于是A∩f-1(O)≠Ø,又A∈csX,A∈cs(f-1(O))。
“一带一路”建设的规模和地域涵盖范围达到了空前水平,在“一带一路”的制度建设过程中,中国既要积极与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等各利益攸关方进行协调,也要同工会、性别公平组织、当地居民社区等一些重要的权利攸关方保持良好沟通。“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国际机制建设,其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建立和维系最大规模的赢家联盟来实现目标,而不是相反。要维持数量规模庞大的成员持久并积极地参与合作机制,这一机制的成员们在其中对于公平性、自主性和合法性的感受是很重要的。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应继续坚持与沿线国家的战略衔接与融合。习近平主席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33]中国应通过与沿线国家的战略对接,总结彼此间所面临的共同议题,进而找到共同需求和形成共同合作的预期,凝聚合作的向心力,以最大程度达成制度共识。
L-阿拉伯糖又称L-树胶醛糖、果胶糖,其形态为白色结晶,对热和酸稳定,广泛存在于植物中如玉米皮、甘蔗渣[1]。L-阿拉伯糖具有很强的非竞争性抑制蔗糖吸收的功能,能够减少吸收蔗糖带来的血清中葡萄糖浓度升高,其甜度是蔗糖的一半,可作为一种新型的低热量功能型甜味剂[2]。已有研究表明,L-阿拉伯糖具有调节血糖吸收、降脂、促进肠道消化排毒、防止龋齿等功效[3],近年来不断被开发应用。
(三)依托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机构共同推进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还应协调好与既有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在推动国际制度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时,中国应提高“一带一路”倡议与既有国际制度的兼容性。这有助于为中国争取更广阔的缓冲空间,以最大程度减少国际制度竞争所引致的“摩擦力”和“副作用”。
中国应当依托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机构共同推进制度变迁,同时将“一带一路”中的机制性安排嵌入到联合国的全球发展目标中去。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正式通过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是一系列新的发展子目标的集合,在千年发展目标到期之后继续指导2015—2030年的全球发展工作。通过对照不难发现,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几乎都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目标相吻合。[34]这些发展目标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也反映了当今全球治理的主要任务。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执行干事海德拉指出:“一带一路”确实能够加强合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动员资金、资源,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合作,促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35]在机制合作方面,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已经与相关国家及机构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中国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需要从机制上更好地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连接,提升机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这也将使“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制度建设能够获得最大多数国家的共鸣与支持,并积极参与到制度建设中来。建立在这样一种恒久的共识基础上的制度往往也更具稳定性和有效性。由于国际制度的守成国与新兴崛起国之间所固有的战略不信任和意图不确定的困扰,守成国往往可能采取阻击、拒绝分享知识和资源、孤立或反对等手段而加以阻挠。[36]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下,新兴国家所意欲创设的国际制度与既有国际制度的兼容性越强,就越能尽量少遭受守成国的阻挠,进而也就越容易打破所面临的制度困境并获得相应的制度收益。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联合在一起,共商国际制度、共享制度收益,有效推动了国际制度的和平变迁,并将对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乃至中国自身的制度建设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一带一路”倡议为国际制度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通过为各参与主体设定规范,有效地减少了区域发展过程中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而推动参与主体间的制度化、规范化合作进程。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包括中国在内的沿线参与国也将更多地享受到“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制度性收益。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among Lancang-Mekong Countries
ZHANG Li
Abstract: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Mechanism (LMCM) is born of water, connected by water, and thrives by water, which is a distinct feature for China in its regional cooperation. The key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among Lancang-Mekong countries lies in how to let the role of water to connect and flourish the Mekong river area, and how to avoid disputes for water in the coastal states.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historic breakthroughs that the LMCM has mad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water resources cooperation platform, water disaster response, in-depth cooperation with the Mekong River Commission, and the water resources capacity building since 2016. The author also points out that behind the Mekong River water cooperation and water crises, we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the water resources are the lifeline and bond for cooperation. It also analyzes the role of water resources in building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among Lancang-Mekong Countries. In order to handle the new water crises, China could implement several strategies: to emphasize the significance of water resources cooperation in LMCM, to further promote the Five-Year Plan of Action on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2018-2022), and design the Five-Year Action Plan on Water Resources Cooperation, to increase the diversity and transparency of water resources projects and beneficial groups, to lay out the pattern of healthy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actor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region,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voice of Mekong water issues, and to give full play to multilevel think tanks interaction.
Keywords: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Mechanism,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water crises, China’s response
【作者简介】 杨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长(上海 邮编:200233);张明,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D81 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9)04-0039-22
【DOI编号】10.13851/j.cnki.gjzw.201904003
[1]Oran R. Young,Governing Complex Systems:Social Capital for the Anthropocen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17,pp. 27-28.
[2]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2017年10月28日,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王毅谈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目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网站,2017年10月19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503111.shtml。
[3]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新华网,2017年5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
[4]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83页。
[5]联合国:《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让言语成为现实》,纽约2012年版,第5页。参见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pdf/Chinese%20version%20MDG% 20Gap%20Report%20%202012_Web.pdf。
[6]参见新华社:《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新华网,2019年4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4/28/c_1124425293.htm。
[7] [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32页。
[8] 同上,第472页。
[9][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第145页。
[10]参见:《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中国“一带一路”网持续更新信息,https://www.yidaiyilu.gov.cn/gbjg/gbgk/77073.htm。
[11]参见[美] 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改革》1995年第3期,第52页。
[12][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韦森审校,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13]同上,第119页。
[14]联合国:《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让言语成为现实》,第8页。
[15]David Armstrong, 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p.184.
[16]陈贽、缪晓娟、郑晓奕:《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1月18日,第2版。
[17]《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8年11月1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1/17/c_1123728402.htm。
[18]参见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外交评论》,2016年第1期,第31页。
[19]参见Oran R. Young,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Formation: Managing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3, No. 3, Summer 1989, pp. 349-375.
[20]祁怀高:《国际制度变迁与东亚体系和平转型——一种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54页。
[21]奥兰·杨:《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棘手案例与关键因素》,载詹姆斯·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页。
[22]参见张楠:《中国进一步参与国际机制的思考》,《学理论》2011年第3期,第31页。
[23]关于软权力的概念,参见Joseph S. Nye, J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5, No. 2, Summer 1990, pp. 177-192;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No. 80, Autumn 1990, pp. 153-171。
[24]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急剧崛起震惊了陆地霸主斯巴达。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战争无法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因为这场战争由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早被描述,故被称作“修昔底德陷阱”。
[2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6]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 2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27][英]苏珊·斯特兰奇:《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和非国家权威》,肖宏宇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28]参见黄俊、董小玉:《“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传播困境及突围策略》,《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2期,第121页。
[29]Enda Curran,“China's Marshall Plan,” August 9, 2016, https://www.bloombergquint.com/china/china-s-marshall-plan.
[30]扬之:《“谁动了我的奶酪”——浅析欧美对“一带一路”的心态变化》,观察者网,2018年3月31日,https://www.guancha.cn/yangzhi/2018_03_31_452189_s.shtml。
[31][美] 奥兰·杨:《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棘手案例与关键因素》,第212页。
[32]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p. 391-425.
[33]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34]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分别是:目标1:无贫穷;目标2:零饥饿;目标3:良好健康与福祉;目标4:优质教育;目标5:性别平等;目标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目标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目标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目标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目标10:减少不平等;目标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目标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目标13:气候行动;目标14:水下生物;目标15:陆地生物;目标16: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目标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35]张娜:《发挥“一带一路”作用促进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12月12日。
[36]参见刘玮:《崛起国创建国际制度的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9期,第84页。
[责任编辑:孙震海]
标签:“一带一路”倡议论文; 国际制度论文; 制度性收益论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论文; 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论文;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