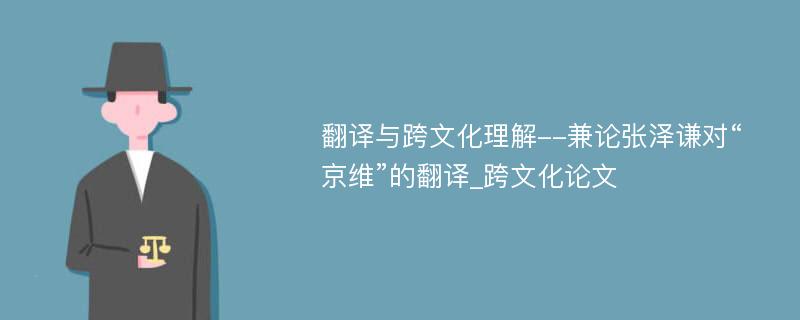
翻译与跨文化理解——张泽乾著《翻译经纬》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纬论文,读后论文,跨文化论文,张泽乾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泽乾教授新著《翻译经纬》已于1994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立足于人类文化发展中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相互交流、相互传递的历史与现状,总结古今中外译论研究的积极成果,吸收现代哲学、科学和艺术的有关理论与方法,借鉴文化学、符号学、传播学、语言学、信息论和系统科学方法论等,在翻译史与翻译论、翻译学与翻译术的结合点上提出和回答问题,对翻译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尤其是翻译中的跨文化理解问题做了富于哲理和启发意义的思考和探索。概括起来,《翻译经纬》具有以下五大特色:
1.确立翻译研究的合理方法 方法是客观规律的主观运用,是主体逼近和达到客体的桥梁和工具。一种研究能否达到客观、取得成效并成为科学,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建立或获得了既符合客观规律又符合主体需要的科学方法。对翻译的研究也不例外。《翻译经纬》一书,开宗明义,提出翻译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并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的比较研究方法和层次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独具特色的经纬论交叉研究方法。作者认为,比较法侧重于历史的、逻辑的分析,层次法侧重于结构的、静态的分析,而交叉研究法则吸取二者之所长,并进一步向着主体性、多向性、运动性和对应性方面发展。它强调以翻译术和翻译史为经,以翻译学与翻译论为纬,以翻译观为纲,并以之作为它们的连接点、交汇点,使翻译研究中的史与论、术与学在翻译观的层面上内在地统一起来,这就有助于突破过去译论研究中的平面化、静态化、单一化的局限性与片面性,把翻译研究建立在更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之上。
2.建设开放性的研究体系 体系是研究方法的逻辑展开,也是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逻辑再现,它既体现和规定着研究的范围和视野,也制约和引导着研究者的思路和视角。建立具有最大开放性的包容性的研究体系,是科学研究的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尺。
正是依据于自己提出的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也依据于自己对翻译活动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理解,《翻译经纬》一书的作者提出了自己具有较大开放性和包容量的研究体系。全书含《翻译史》、《翻译观》和《翻译论》三编,形成有机体系。对翻译史的考察实际上分为人类文化交流史和古今中外译论史这两个方面。作者分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个阶段,考察翻译在人类文化内部传播和沟通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又在古今中国与西方译论的对比分析中总结翻译思想的历史发展,从而为翻译观的研究奠定了历史的基础。翻译观是该书颇具创意的重要部分,作者从哲学观、科学观和艺术观这三个基本层次中全面分析翻译研究的指导观念,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翻译的指导功能,强调整体的和动态的科学观念对翻译研究的积极作用,强调翻译中的艺术创造和审美评价等,使翻译观与对当代人类文化的整体结构和演变趋势内在结合起来,展示出一种高屋建瓴的宏大视野。翻译论则立足于解决翻译中的一系列前提性和根据性问题。作者先后提升出翻译的必然与局限、层次与等级、过程与性质、原则与标准、技巧与技法、风采与风格、欣赏与批评、功能与价值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在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理论层面上进行系统分析,在不少问题上发前人之所未发,读后给人以颇多启示。
3.探究异语转换的可能性问题 翻译的直接对象是一定的言语符号体系。用一种语言符号系统去标示和说明另一种语言符号系统,达到语词,语义、语用的等值和等效转换,是翻译者的基本任务。那么,这种转换何以成为可能,又如何达到科学呢:这无疑是翻译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翻译经纬》抓住原语与译语的关系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原理,提出并深入探讨语言的可译性和可译度的问题。作者认为,翻译是译语对原语的重构与再现,是对创作的二度创作。原作者和译作者之间在认识和体验社会生活上的共通性,人类在思维和语言方面的同一性,是语言可译性的基本依据。但语言的可译性又是有限的、相对的,不可译性是绝对的、无限的、没有止境的。超越翻译的极限和局限而强化翻译的效能,是翻译工作的重要目标。从语言学上看,翻译可分为语符形式、语义内容和语用修辞三个基本层次,翻译的等级则包括词级、句级和篇级三个等级,翻译活动就是通过语法信息转换、语义信息转移和语用信息传输,而分别在语词之间、语句之间和篇章之间建立起对应和等值关系,使译语达到对原语的全息语义结构。
4.剖析跨文化理解的等值性问题 从形式上看,翻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直接从事的是异语交往和异语交换,从内容上看,则实际上是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和文化形态之间往返穿梭,其目的在于达到不同文化内容和文化信息的传递与理解。语言不是无意义的符号体系,而是有着特定文化指称和文化意义的文化载体。翻译一定的异语作品之所以必要,正在于它以自己的特殊形式记载和表达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内容。因此,语言的可译性和可译度问题,本质上是不同体系的文化信息的可流通性和可流通度的问题。译文的可读性正在于它真实、全面、准确、传神地转达了原语的文化内容。正是在这样的高度,《翻译经纬》一书明确指出等值性是翻译的核心。翻译中的等值性,就是原作与译作之间在文化内容方面的对应性、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可靠性等,这是翻译者在理解原作和创造译作中的重要目标和主导原则。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异,在发生学意义上根源于各种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人种和语言等,在形态学上表现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思维、交往和情感方式之中,并在政治制度、社会心理、思想观念等方面表现出来。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由于自己所受的文化教育和文化熏染,在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中,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己的文化定势和价值尺度来衡量、理解和评价其他文化,并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愿望作为一种文化定势而倾注到对象之中,从而造成巨大的心理反差甚至冲突,这就是文化的隔阂和文化冲突。它们妨碍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坚持翻译中的等值性原则,就是要克服这种种语言的尤其是文化的隔阂与屏障,通过语言转换守恒和自律调节等方式,使译语与原语之间做到形式对应,语义等值,风格协调,去争取逻辑性、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去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去创造出神入化的“信、达、雅”的理想境界。
5.强化翻译主体的创造意识 翻译是一种高强度的重构性,再现性和创造性活动,翻译中的语义等值、信息守恒和跨文化理解,都只有通过翻译家高度自觉的反映性、选择性和创造性活动才能得到实现。翻译家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对原作的审读与剖析,对原语向译语的转换与重组,对译语的语言形式、语义内容和艺术风格的再创造,都不可能是消极的、被动的,而只能是积极的、能动的。因此,强化翻译主体的创造意识,既是翻译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翻译经纬》一书借鉴我国哲学关于主体性理论研究的积极成果,对翻译中的主—客体关系做了比较具体和细致的探讨。作者认为,通常所说的翻译中的人、物、场的关系,也就是翻译主体、翻译客体和翻译场的关系。翻译主体包括交际活动系统、认知活动系统和审美活动系统;翻译客体主要包括语言符号系统、语言概念系统和文体风格系统;翻译场则可分为语言场、思维场、审美场。这三者之间都通过表层结构、深层结构和中介结构这三个基本层次而相互连接,构成翻译系统。翻译主体在翻译系统中具有主动的积极的和支配的地位,它的任务不仅在于重构和再现原作,而且要求逼真、传真、存真地进行再创造。因此,它既是科学认识的主体,也是艺术实践的主体。翻译是包括翻译主体在内的翻译群体在科学再认识基础上的艺术再创造活动。
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人类文化发展呈现出统一性与多样性同步增强的进化趋势,翻译在跨文化理解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在客观上要求翻译研究的相关发展和超前发展。相应地,建立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张泽乾先生从翻译哲学、科学和艺术的范畴对此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在这一方面无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