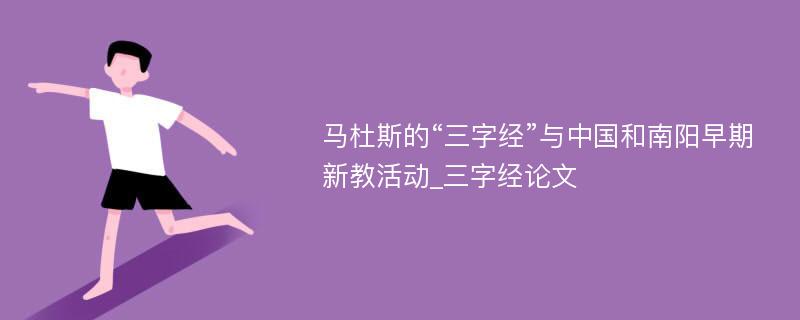
麦都思《三字经》与新教早期在华及南洋地区的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洋论文,新教论文,在华论文,三字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12-0112-08
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Medhurst,1796-1857年)是19世纪来华传教士中对中国社会、文化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① Jane Kate Leonard曾依据伦敦会档案专门研究麦都思早年在巴达维亚、槟榔屿、新加坡等地的传教经历。[1](P47-59)然而其论述主要集中在传教策略方面,对麦都思的重要中文著作,即基督教《三字经》并未给予充分关注。与基督教三字经体著作有关的近年研究主要有:美国学者Evelyn Rawski撰写的《三字经》与教会学校基础教育状况的文章,日本学者吉田寅对新教《三字经》的资料考察,以及黄时鉴先生对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的各种版本《三字经》的考辨。② 笔者因近些年来多次查阅欧美等地对华传教机构档案,自忖前人研究中所触及的相关文本、作品的社会流变过程还可以得到更为细致的剖析,尤其是基督教《三字经》作为异质文化而生长于本土社会的历史背景,另有待进一步挖掘。比如,麦都思为何借用中国传统蒙学三字经体以改变一般布道手册的写作风格?基督教《三字经》又是怎样通过麦都思的阐发而成为早期新教在华传教的重要文本?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剖析新教传教士如何依托文本与社会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将自身理念的表达付诸与中土文化的对话实践过程中。
一、背景:三字经体布道手册的产生
在欧美基督教“福音振兴运动”(Evangelical Revival)热潮的推动下,英国伦敦会于19世纪初向中国指派新教传教士。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于1807年到达广州,开始为传教活动做基本的准备。几年后,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年)受伦敦会的指派来华协助马礼逊的工作。米怜于1813年抵达澳门,然而由于当时在广州、澳门一带的传教活动受到清廷的限制以及澳门葡萄牙天主教势力的影响,遂将其活动重心转移到南洋一带。在爪哇、巴达维亚、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米怜与当地的其他几位伦敦会传教士一同访问华人社区,开办教会学校及印刷所,在撰写布道文本的基础上开展传教活动。③
布道手册的撰写对于新教在华与南洋一带传教活动的开展可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新教来华传教的早期,机构、人员、配备等都相对缺乏或不甚稳定,书面文本便成为传教士与慕道者之间沟通的主要载体。书面文本甚至可以有效缓和新教早期在华传教人手缺乏、地域限制等不利局面。④ 19世纪初期,伦敦会虽然只有马礼逊一人在广州、澳门两处活动,然而在他与南洋的米怜等人的合作下,一些作品得以在广州、澳门以外的地方出版,使中文宗教读物的印刷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相对稳定的进展。⑤
作为来自异地的新教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寻找契合本土文化的一条路径,布道手册的撰写事实上也成为“异土”与“本土”两者产生关联的一个重要突破点。研究教会史的学者认为,最初来自伦敦会的几名传教士,在传教理念上秉信以布道手册为基础文本的福音传授方式,原因在于对文本的逐字认读能够直接唤起慕道者对于自身原罪的觉醒,之后慕道者便会进一步听从布道者对文本的阐释而寻找拯救的途径。[1](P49)米怜本人以及其他几位后来加入到“恒河外方传教团”(Ultra-Ganges Mission)的新教传教士们,⑥ 一般都会随身携带新近印刷的布道手册,定期走访广东南部沿海的船民或南洋地区的华人团体及教会学校。然而不久后米怜等新教传教士便发现,纯粹以讲授基督救世为中心的福音传道法并不能与他们的预期效果相符。[2](P160-163)特别是华人群体的地方文化及方言特质,加上南洋华人劳工及土生后代们识字水平普遍不高等,都给直接布道带来阻碍。[3](P315、335)
最初将布道手册与中国本土文化直接关联起来的是传教士麦都思。麦氏于1823年在巴达维亚印刷出版了以基督救世为中心内容的基督教《三字经》——从标题中就可以看出,作者在创作形式上套用了中国传统蒙学读物《三字经》的文体结构。[4](P27)尽管此前欧洲汉学家对中国传统《三字经》有过翻译和介绍,⑦ 然而这种通过中文的三字文体表达西方宗教思想的书写方式,为麦都思所首先采用。这一作品的产生,并不是一种机械的“形式”与“内容”的叠加: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将欲要传达的基督教教义构建在一种有韵有序的中文三字结构中(当然,文本的功能有多处类似于中国传统《三字经》),其创作过程内含了一个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转化”过程。自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后不久,便开始注意收集中国本土文化的信息,包括学习中文、购买中文书籍等,并进一步将各种信息编入字典、词汇手册等参考书中。在1812年出版的Horae Sinicae(《中国通俗文选》)一书中,马礼逊便将当时中国地方上流传的《三字经》作了介绍与翻译。在全书的开篇,马礼逊提到:“此书辑选了中华大帝国的普通民众最为普遍阅读的书籍,……此书应当会为英国大众所接受,因为针对这个非同寻常的国度在近二十年里所引发的关注与好奇,它或可增添些许兴味。”[5]然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马礼逊撰写的其他宗教作品中,并未见其将布道精神与中国文化作任何直接的关联。
麦都思于1817年受伦敦会的指派到马六甲,协助米怜管理印刷事务,后于1821年前后转至巴达维亚传教。[4](P25)麦都思的第一部中文作品是《地理便童略传》,1819年由马六甲印刷所出版,借问答体介绍世界地理、人口与宗教概况,虽为学校用书,却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作品。1823年在巴达维亚出版的《三字经》是麦都思撰写的第一种布道手册。通过对伦敦会档案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麦都思之所以在撰写第一种宗教作品时便采用了中文蒙学读物的三字结构,与其早年在南洋地区华人社团中的布道经历有关。根据自己的旅行与传教经验,麦都思发现福音派的布道理念与实际的地方民众信仰有着诸多无法契合之处,比方说,华人以宗族与宗庙形式为本的祭祖传统致使非同姓家族的人很少会愿意定期聚会听道。⑧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南亚的华人团体多为福建各港发舶商船的随船移民,经研究,闽人约占70%-80%,其次为粤人,皆对各自的乡族群体有强烈的宗族、语言认同。[6](P168-172)传教士的记述表明,南洋地区的这种方言混杂状况无疑给直接布道与口头传教带来障碍。[2](P164)使用以中文为书面语的布道手册当然可以避免方言的问题,然而文本不宜太过复杂,因为大多数华人的识字水平十分有限,相对简单、基础的阅读文本反倒能够成为传教方式的有效突破。⑨
二、文本:麦都思《三字经》的主要内容
1818年前后,麦都思于马六甲的相关工作经验令其进一步注意到中文识字课本在南洋地区的使用情况。中国传统蒙学读物《三字经》、《千字文》等不仅是明清时期幼学教育的基础,在南洋华人移民后代的识字教育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根据负责人米怜的记录,马六甲印刷所在1819年出版了麦都思的《地理便童略传》1100册后,还加印过中国传统蒙学读物《三字经》1000册。[2](P271)这两种课本都在马六甲的华人学校中有所使用,且需求渐长。及至1820年代初,由当地政府参与建立的几所华人学校的学生数目已逾200人,加上义塾(free school)学童,总数达到400人上下。[3](P317)除了《三字经》以外,当时在马六甲较为普及的还有米怜用中文编写的一些宗教启蒙读物。特别是一种叫作《幼学浅解问答》的布道手册,据载在当地的三所华人学校中使用,且每周的课程中都有教师用本地方言作书面讲解以及师生关于基督教概念的“问答”练习。[3](P312)虽然米怜以“幼学”为名取其“基础”、“入门”之意,然而因为全文篇幅较长(32页)并涉及诸多基督教概念,读懂《幼学浅解问答》不仅要求读者有较高的识字水平,亦需要慕道者对宗教教义有一定的领悟能力。所谓课堂上进行的“问答”练习,很可能只是师生两方依照文本的问答体形式而进行的“一问一答”式的诵念,很难积极评价学生在问答过程中的实际理解力和接受效果。“布道手册”与适合在教会学校教授的“中文布道手册”并非等同的写作类型。在结束了马六甲的工作之后,麦都思开始尝试调整布道手册的写作方式,即试图寻找一种适用于学校场合授受,并在识字要求上相对宽松的文本形式。于是,一种仿效中国本土蒙学教育的课本读物便成为早期新教传教工作的一个重要起点——麦都思编写的基督教《三字经》既遵循福音派逐字解读布道文本的传统,又可以覆盖较大的受众范围,尤其是针对那些初入教会学校识字水平有限的华人学生。
作为“恒河外方传教团”的主要成员之一,米怜于1820年出版了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一书,详述了伦敦会在华及南洋传教第一个十年的事迹。米怜于1822年去世,没有对1820年以后的新教宣教出版物作详细记载,所以有关麦都思编印的基督教《三字经》以及后来的多种重版的介绍只能在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67年出版的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一书中见到。简要说来,麦都思以“尚德者”为名于1823年在巴达维亚印行《三字经》第一版后,1828年在巴达维亚又印一版,共17页。此版于1832年在马六甲再次重印,1839年又在新加坡加印了一个内容相同的小字版。稍加修订后,麦都思的《三字经》于1843年又在香港出版,封面注“英华书院藏版”,共16页。[4](P27)这些版本的不断出现,当然与麦都思本人早年在南洋的活动路线有关,但同时也间接证明了这种三字经体布道手册的确一度曾经于南洋的教会学校中普及。据Evelyn Rawski对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部分版本所作调查,这些版本前后虽有版式上的略微调整,内容和字数却大体一致。[1](P146-149)条约港口开埠后,麦都思移居上海,《三字经》于1845至1856年在上海、宁波、厦门等地还有几个相关的重版、修订版及注解版。1845年的《新增三字经》,以及1852年福州亚比丝喜美总会所出之《三字经》,作者亦皆为麦都思,内容和字数也大致相同,只是个别用词偶有区别。[4](P27)麦都思之后,其他在华新教传教士也相继编写了内容不尽相同的三字经体布道手册,比如1861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印行的《真理三字经》,1865年Chauncey Goodrich所著之《三字经注解》,以及1870年Charles Hartwell在福州出版的《圣教三字经》等,其中一些文本还以地方土话写成。各种版本的出现以及在各地教会学校中的流传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可见《三字经》于新教在华传教过程中的影响及地位。
麦都思的《三字经》,每三字为一点读,用字浅白,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正如《圣经》的开篇《创世记》,麦都思的《三字经》也是从神造人及万物讲起,并赞美神之力量伟大,以及世人对神的感恩:
化天地,造万有,及造人;真神主。
无不在,无不知,无不能,无不理; (第1页a)
至公义,至爱怜,至诚实,至圣然。
神为灵,总无像,无可坏,无可量;
无何始,无何终, (第1页b)
尽可敬,尽可恭。
凛其威,感其仁,万人乎,颂赞神。
神造人,如其像,性为善,心为良。 (第2页a)⑩
在前四句的12字中,麦都思将Deus的译名写做“神”,承袭了新教在华传教以“神”对应God的概念书写体系,并与16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等人使用的“天”、“上帝”作了严格区分。(11) 麦都思在首句“化天地”中使用的“天”字乃与“地”相对,“天地”两字连用泛指宇宙万物,不再是耶稣会用来指Deus的“天”或“天主”之意。“真神主”三字虽与十八九世纪新教布道文本中常见的“the living and true God”有一定的关联,然而就中文书写的格式来看,麦都思在用词上显然也有一番斟酌。前文已经提到,在麦都思之前,马礼逊与米怜分别著有中文布道文本。马礼逊在其1812年在广州出版的《问答浅注耶稣教法》的开篇便讲到“原创造天地万物者系止一真活神也”,即使用“止一真活神”对应“the living and true God”,并将“真”放于“活”前。[7]米怜在1816年出版的《幼学浅解问答》的序言中也使用了“真活神原造他者”一语。[8]麦都思则在《三字经》的开篇用了“真神主”一词,虽没有将“活”字纳入,却凸显了“真神”这一概念在异土传教的重要性。
在讲完神造人的事迹之后,麦都思进一步以三字形式构架新教布道文本中的基本内容,即人被神逐出伊甸园,以及人是如何背弃神,原罪是如何形成的,人区别于神的本质之所在等。一些重要的概念也相应提出,比如第4、第5页集中讨论的“身体”、“灵魂”,以及“灵”、“肉”、“身”等:
曰身体,曰灵魂,此二者,需晓分;
彼为肉,此为灵,一会死,一无罄。
身不省,生不久,灵不理,若千秋。 (第4页b)
马牛羊,鸡犬等,无灵魂,无来生;
肚饥饿,寻其粮,食到饱,更无想。 (第5页a)
禽及兽,缘下贱,无何恶,无何善。 (第5页b)
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灵魂”这一概念时,麦都思于有限的文本空间内加入了一些自己的话语。这里提到的“禽及兽,缘下贱”便是一般布道手册中所没有的。在马礼逊已经刊行的中文布道手册(以及他所使用的底本《威斯敏斯特教理小问答》)中,并没有论及“马牛羊鸡犬”等禽兽是“无灵魂”而不分善恶的。麦都思在《三字经》中突出人与禽兽的分别,目的在于能让他的受众在诵读的过程中感到“人”的地位的特殊性,并使“赎罪”、“拯救”等后文提出的见解更具说服力。文本后半部分的布局也紧凑有序:第6页即出现“耶稣”的名字,并讲述耶稣如何拯救世人;第9页则开始讲授信仰的要点,人如何向神赎罪等。第12页出现“教士”这一名称,并解释传教士的职责乃“传神志,解圣书,醒觉世”。这也是一般布道手册中所没有的,其作用多是为了突出早期新教在华传教过程中布道者自身的地位和作用。最后几页则集中描述“世间末,万死活”的情形,并叙述什么样的人将升天得福,什么样的人会落苦受难。全篇以“有恒心,常畏神,至于死,福无尽”12字结尾。
三、形式:三字经体的功能及影响
相比于1810-1820年代新教传教士在广州、澳门及南洋等地已经出版的宣教文本,麦都思的《三字经》篇幅短小,内容直白。《三字经》在成文过程中,很可能受益于麦都思的中文助手朱德郎的合作翻译。(12) 在麦都思之前,马礼逊、米怜等人在各自中文助手的协助下曾经完成过一部分宗教刊物的印制,在文本层面上对新教在华及南洋一带的传教工作起到了奠定作用;然而同时,一些直接阐述教理的宣教文本因其缺乏中西方共通的文化背景而令读者感到晦涩难懂。米怜1815年到马六甲工作后不久,便以马礼逊的《问答浅注耶稣教法》作为华人教会学校的宗教课本。此布道手册的开篇除了提出“三位一体”等概念之外,亦对基督教文本传承,新、旧两约的区别,以及两约在文字上与希腊、希伯莱传统的不同等问题一一作解。虽然一开始学生们在每个礼拜日都反复读念此书,然而米怜作为讲解者却认为,《问答浅注耶稣教法》更符合成年信众的理解深度。[2](P151)不久后,米怜便开始尝试撰写适合年幼学生使用的布道手册,即翻译当时英国教会为幼童编写的初级文本,并以《幼学浅解问答》为名。[9](P47-49)虽然作者在序中指出,“此小部书欲以为人父母师傅教子弟者之略助耳”、“自六七八岁以上皆可学此幼学书”,[8]然而这恐怕仍然是针对原布道手册的英语读者而言的。经翻译之后,全书共计165个问答,并以文言进一步讨论教义。有学者就此评论米怜的写作风格十分书卷气。[1](P53)
马礼逊与米怜的这种写作手法,用今天的话来评价即秉承了学院派的正宗。马礼逊的《问答浅注耶稣教法》乃是根据《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Westminster Catechism)为底本而翻译、编写成的中文问答体布道手册,当然作者在内容辞句以及问答顺序上作了适当的调整。《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有大、小两种,即Westminster Larger Catechism和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简称《大问答》、《小问答》),均作于1647年,属欧洲归正宗(Reformed Churches)中流行最广的一种,遂为18世纪在苏格兰长老会(Presbyterians)及安立甘宗(Anglicans)中遵奉的教理问答。(13) 马礼逊青少年时期在纽卡斯特(Newcastle)跟随长老会的牧师学习神学时定对其有深刻的理解。而作为第一个来华传教士,马礼逊首先用问答体写作中文本的宣教手册也十分合理,因为教理问答本来就是基督教各派教会对初信者传授基本教义的简易教材。然而,跟麦都思的三字文体相比较,马礼逊的《问答浅注耶稣教法》虽然在文体和内容上遵从了《威斯敏斯特教理小问答》,在字句上却因问答体的关系而略显繁复。
下面即选马礼逊《问答浅注耶稣教法》、米怜《幼学浅解问答》以及麦都思《三字经》中关于神造万物、无所不能的相关段落进行比较。马礼逊1812年所著《问答浅注耶稣教法》:
一、问,原创造天地万物者,系谁乎。
答曰,原创造天地万物者,系止一真活神也。
二、问,是止一真活神者之外,另有别神否也。
答曰,是止一真活神者之外,并无别神。(14)
……
九、问,神有所不能,所不知,所不在,是否。
答曰,神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到处而在。惟在天上而显著已焉。(15)
米怜1816年初版的《幼学浅解问答》:
十五、问,神于其本性,果如何耶
答曰,神于其本性,乃是个纯灵无像,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始无终,又至智、至能、至圣、至怜、至公、至真者也。
麦都思1823年《三字经》在开篇第1页的四列中即涵盖了神造万物无所不能的意思:
化天地 造万有 及造人 真神主
无不在 无不知 无不能 无不理
麦都思首创的三字经体,无疑是对当时既有的问答体布道手册的一个形式上的突破。这种三字一句的结构,便于口授与逐字记忆,更适合在学校教念,学生跟读。作者行文尽量做到押韵,可能也是为了跟读者诵读记忆之便。相比之下,问答体一问一答,对宗教概念的阐释丝丝入扣,有一个层渐引入的启发过程,但文本一般偏长,更适合少数人聚会时的面对面布道。由于文本精炼,言简意赅,三字经体也有利于一些基本概念在文本的开篇即直接提出,之后亦可适时反复、加强。麦都思本人甚至特别倾向这种文体,因为三字成句的结构虽然容纳的基本信息有限,然而在布道的时候,反倒给自己进一步对文本的阐释提供了更大的空间。(16) 因字数少,篇幅短,三字经体的布道手册对读者的识字要求也不是特别高。(17) 同中国传统《三字经》带给华人蒙学教育的影响一样,基督教《三字经》仿照传统中国《三字经》的文体形式并因袭其文本的社会功用,成为一种适合在学校使用的宗教启蒙读物。这可以从麦都思《三字经》的多次重版以及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的传播情况看出。
除了成为教会学校使用的启蒙读物以外,麦都思的《三字经》对南洋一带华人劳工及船民的识字水平也起到一定的辅助推动作用。前文已经提到过恒河外方传教团定期在华南沿海以及南洋各地分发书本及布道手册的经历。麦都思的基督教《三字经》于1823年及1828年两次印行之后,也有相关的发放记载。伦敦会在新加坡的传教士J.Tomlin详细记录了1828年底的一次将麦都思的《三字经》传发给一个海南船民的经过:这个船民主动上门拜访,因为不怎么识字,所以想求一书以便请他人辅教。因为此人多次前来,态度诚恳,于是Tomlin就将麦都思时出版不久的基督教《三字经》送予他。[10](P53)这虽是出于传教士的单方面表述,然而从中可以看出麦都思的《三字经》对无太多识字基础的华南沿海船民的间接影响。
麦都思的《三字经》作为一种传教文本与识字途径的结合,也给新教传教在南洋地区所面临的文化竞争提供了有利的一面。米怜、麦都思等人在马六甲、巴达维亚等地传教的时候,不得不使用英语、中文及马来语三种语言编写宗教读物,以吸引来自不同族群的读者。[3](P311)面对努力争取的闽粤客籍华人信众,传教士们力图使其布道文本凸显出相对于佛、道、儒及地方信仰的独特优势。另外,前文已经提到过,南洋地区的华人家长送孩子上教会学校的首要目的在于为他们寻求一个中文识字的机会。显然,相比于当时其他纯翻译性质的布道文本,基督教《三字经》的这种摹仿中国蒙学读物的形式更易融入当地华人学生的教育传统——对于读者来说,在宗教内容同样陌生的前提下,简约明了的文本形式便显现出其优势所在。及1830年代,求学于新加坡教会学校(Singapore Institution Free Schools,又称义塾书院)的华人学生,仍多带有中文识字的目的,对文本中宗教精神的理解反倒是连带性的。(18) 这便给麦都思的《三字经》在新加坡教会学校中的流传提供了一个契机,以至于1839年在新加坡又加印了一个内容相同的小字版。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沿海贸易港口开埠之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在复杂的文化环境中争取到自己的信众,而麦都思编写的基督教《三字经》无疑成为一种有效的文本应对方式——通过“形式”与“内容”的结合,麦都思的《三字经》在保持布道手册主旨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形式的调整将蒙学三字读本的功能融入到宗教思想的传播过程中。
四、结语
作为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于1807年抵达广州后不久便致力用中文撰写传教文本,包括布道手册的写作以及《圣经》篇章的翻译。大约十多年后,一些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及南洋一带工作的新教传教士开始放弃严格遵循宗教文本的直接布道方式。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如果要让中国人接受福音,则首先要向他们展示西方文化的精深,并显示其与中国文化可互作参比之处——此即来华新教传教士于1820-1830年代集中撰写外国史地文章的溯因。与此同时,布道手册的撰写仍然是新教传教工作的重点,它甚至成为来自异地的传教士主动寻找契合本土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与编写史地文章这种相对迂回的文化层面上的工作相比,撰写“身兼两重功能”的布道手册——即既保持了布道手册原有的精神内涵,又能借助形式的变化而影响到一个较大的受众面——对于新教传教士来说,将更有效地发挥文本特定的社会功用。这便是麦都思首创的基督教三字经体著作的历史突破意义之所在。
从主旨和内容来看,基督教三字经体著作与中国传统蒙学读物《三字经》并无几处共通——新教传教士将两者关联在一起,主要是针对两个方面的问题:1.同作为启蒙读物的文本;2.结构与形式上的可借鉴之处。这种文本性质上的相似恰恰为外来事物借助中土文化的衍伸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个意义上,麦都思的《三字经》不单在形式上有效缓和了中文口授与识字水平之间的对立,在内容主旨上也充分体现出新教传教士对异文化的一种观察视角,以及在与异文化对话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主动性。
综上所述,基督教三字经体著作与19世纪初新教在华及南洋地区的活动有着特定的“文本”与“社会”的对应关系。从文本之社会性这一角度考察可以看出,对外来概念、思想的书写,并非文本自身所能够衍生出的一种单一脉络——文本的成型过程,必受到各种社会思潮及背景的牵制。在早期的受众对基督教文本的思想背景知之甚少时,三字的结构形式无疑成为复杂内容的有效依托。然而,当19世纪中后期新教传教逐渐深入开埠口岸之后,三字经体著作显露出了形式对于充分表达内容的局限,一些教会学校更倾向于使用直接翻译的布道手册。有的教会人士甚至开始反对将中国蒙学读物《三字经》列为教会学校的基础中文识字用书,[1](P148-151)因为这种方式限制了识字范围,使学生无法深入阅读宗教文献。(19) 因而,就19世纪基督教三字经体著作的发展脉络而言,其“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与分离恰恰彰显出文本背后的社会思想的转变过程。
注释:
① 学术界至今尚无对麦都思本人的全面传记性研究。麦都思的生平及著作概况,参见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e: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p.25-40.
② Evelyn Rawski,“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Mission Enterprise”,in Susanne Wilson Barn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eds.Christianity in China: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pp.135-151;吉田寅《宣教師版の〈三字經〉資料的考察》,《異文化交流》第13号,1993年5月;黄时鉴《〈三字经〉与中西文化交流》,《九州学林》2005年第2期,第79-82页。
③ 关于米怜早年在南洋的活动,参见Robert Philip,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he Rev.William Milne(London:John Snow,1840),第七至九章。
④ 从广义上来讲,这里的“书面文本”还包括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编写的世俗类读物及期刊。比如米怜1815-1821年在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虽仍以宗教传播为目的,却大量编入了与西方科学文化有关的知识,其目的在于通过让读者了解西方文明而进一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域宗教上的隔膜。
⑤ 米怜于1815年赴马六甲时,与马礼逊一同订立的有关建立布道站的十项决议中,有三项是与中文印刷及翻译编写宗教读物紧密相关的。具体情况,特别是1815年至1819年马礼逊、米怜等早期新教传教士在南洋一带的印刷活动,参见William Milne,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pp.137-139、267-287.
⑥ 关于“恒河外方传教团”的设立及活动,参见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63页。
⑦ 在1812年马礼逊所著Horae Sinicae中收入的英译San-tsi-king,the Three Character Classic之前,有一个俄译本的《三字经》,作于18世纪后期。参见黄时鉴在《〈三字经〉与中西文化交流》一文中的研究。
⑧ 参见伦敦会档案(LMS Archives),Incoming from Penang,9 October 1820.更多关于麦都思早年传教工作的情况,参见其著述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 (London:John Snow,1838).
⑨ 英人占领马六甲(1641年)、取得槟榔屿(1786年)、短期统治巴达维亚(1811-1816年),继而开埠新加坡(1819年)后,大力招募闽粤华侨为劳工,这些华人移民及土生后代就是伦敦会传教士在南洋地区所关注的中文布道手册的阅读对象。传教士们同时也寄希望于这些人日后将布道手册及精神传回到闽粤一带的家乡华人中。
⑩ 笔者在这篇文章里用于分析的文本是1843年香港英华书院藏版的《三字经》,此版与麦都思之前于1823-1839年出版的各版内容大致相同而版式不一。原文为两句一列,自左往右,标点系作者后加。
(11) 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其1811年广州出版的第一种中文布道手册《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中就用“神”对应God,而标题中“神道”一词指Divine doctrine.
(12) 传教士的中文写作与其中文助手的作用是研究有关基督教中文文献最初成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19世纪几位主要来华新教传教士的中文写作过程的研究,参见Patrick Hanan,“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The Writing Process”,in Patrick Hanan ed.,Treasures of the Yenching,pp.261-283.文中提到麦都思的中文助手朱德郎的一些信息。
(13) 即Westminster Larger Catechism and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小问答》的内容不仅比《大问答》要来得简略,问答也仅有107对,而《大问答》一共有196对问答。
(14) 相应在《小问答》中的是第5对问答,即:Question 5.Are there more Gods than one? Answer:There is but one only,the living and true God.
(15) 相应在《小问答》中的是第4对问答,即:Question 4.What is God? Answer:God is a Spirit,infinite,eternal,and unchangeable,in his being,wisdom,power.holiness,justice,goodness,and truth.
(16) 参见伦敦会档案(LMS Archives),Incoming from Batavia,1 September 1824.
(17) Evelyn Rawski在她的文章中对麦都思1823-1855年所编各版《三字经》的字数已有一个大致的统计,为948字,与中国传统《三字经》1000字左右的篇幅相仿。
(18) 参见庄钦永先生对新加坡义塾书院的研究《1819-1844年新加坡的华文学堂》,载庄钦永《新甲华人史史料考释》,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版,第165-196页。
(19) Evelyn Rawski的研究表明,麦都思等人的基督教三字经体著作,所用之汉字与中国蒙学读物《三字经》只有30%到50%的重合。也就是说,即使教会学校的学生掌握了中国传统《三字经》中的所有汉字,也只能认读三字经体布道手册中最多一半的汉字,更不用说进一步阅读其他基督教文本了。
标签:三字经论文; 马礼逊论文; 传教士论文; 新教论文; 麦都思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基督教教育论文; 国学论文; 马六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