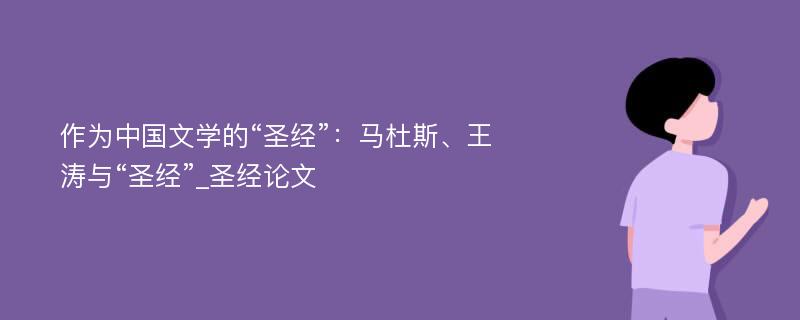
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圣经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委办论文,王韬论文,麦都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0-02-28
[版权说明]本文英文版原刊于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63,No.1(2003),pp.197-239,已获中文版权授权。
一、前言
19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翻译时代之一。如此时代,要么发生一种文化欲施加影响于另一种文化的现象,要么就是另一种更普遍的现象:一种文化自身致力于向外探求新知识。而在19世纪的中国,这两种现象彼此交织,相互共存。鉴于当时是西方率先冲击中国,所以一般而言是西方启动了晚清的翻译活动。但在后来,无论是通过像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同文馆这样的机构,还是通过一些个人,更多时候则是中国人自己在推动着翻译活动的发展。不过,无论是谁率先启动了晚清的翻译活动,翻译几乎总是这样一种工作:它至少涉及两个人,一人对西方语言极为熟悉,而另一人则对中文文法写作颇有技巧。这种两人或多人的翻译活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这取决于每个译者对对方语言熟悉的程度,同时也取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
迄今为止,19世纪由西方人率先发起的这种中西之间的翻译组合之最杰出者,当为《圣经》的翻译。尽管《圣经》本身就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不对称的声调、风格和形式,就与其注释文字对中国人来说完全陌生一样——《圣经》翻译还是吸引了不少译者,而且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不同译本。在这些《圣经》中文译本出版前后,都曾遭遇过诸多批评(这主要是因为与《圣经》有关的翻译理论及翻译实践问题在19世纪已被提出)。无论我们怎样估算它们对阅读者所造成的影响,这些译本还是得到了大量的出版传播。
19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至少有五种《圣经》(新旧约全本)全译本由新教传教士完成并出版①,这些译本之间的主要差别并非是在教义方面。吸引每个翻译组从事一种新的《圣经》译本翻译的原因,似乎在于他们对前一任译者的译本中的语言选择或翻译原则不太满意。这里所谓的“语言”,笔者指的是各种文言,因为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尚无一种完整的官话本的《圣经》全译本出版;而所谓“翻译原则”,则是指译本在原文表达之准确度与中国读者的接受趣味之间所达成的一种妥协②。简言之,我们试图使用那些明确的——因此也是难以让人满意的——术语。而不同翻译文本之间所存在着的差别,主要来自于“自由翻译”还是“直译”两种不同翻译模式之间所存在的难以根除的紧张冲突。
《圣经》的翻译很少是仅仅一个二人组合式的工作模式。几乎每一个不同的《圣经》译本,其翻译团队中都不止一位传教士,而每一位传教士也至少有一位中国助手。最早的一部《圣经》中译本1822年出版于印度的塞兰坡(Serampore),这个译本的翻译团队人数不多:包括传教士马希曼(Joshua Marshman)及其合作者拉萨(Johannes Lassar,一位从澳门来的亚美尼亚人),还有马希曼的一位来自广州的不知名的华人助手,再就是马希曼的儿子约翰也不时参与其中。与这个译本的翻译团队在人数上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圣经》的第四个中译本,也就是1852年出版的新约“委办本”和1854年出版的旧约“委办本”,囊括了数十位翻译者。《圣经》的不同部分被分派到不同口岸城市中的不同传教会分别翻译,之后,来自于各个口岸城市的传教会所选派的代表以及他们的华人助手汇聚在上海,审订并完成译本定稿。至少有八位译者(四位传教士及其助手)负责审订完成新约的最后译本,至少六位译者(三位传教士及其助手)负责审订完成旧约的最后译本。
译者团队之间的自然竞争,只在为了获得各自所属差会的经济资助时才凸显出来。在这些差会中,来华时间最早同时也最重要的,当属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不过这些差会距离传教士们甚远。这些差会通过遍布全英国、美国及欧洲大陆的教堂获得经济上的援助。这些差会存在的唯一理由,就很可能是印刷并尽可能广泛地发行传播《圣经》。在一种新的《圣经》版本成功出版问世之前,它必须要获得至少一家《圣经》公会的支持。而且,一旦一家《圣经》公会资助了一个版本,它也就不大会再乐于出版一个替代性的《圣经》文本,除非新文本比前一个文本更为出色。
《圣经》在传教士们心目中的独特地位影响了他们对待《圣经》翻译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圣经》乃天授,至少在理论上如此。他们也相信只要拿起《圣经》来读一读,就足以转化一个人。如此以来,作为一种基本原则立场,大多数传教士都拒绝过于偏离原希伯来语或希腊语《圣经》的原词与句法。有些人在翻译其他著述时漫不经心,而翻译《圣经》的时候则是竭尽所能,努力探询如何用中文来表达《圣经》原文之精神特质。
最初两个中文译本差不多是同时完成的,其中一个是马希曼和拉萨两人在塞兰坡完成的译本,另一个译本是马礼逊和米怜两人在广州和马六甲完成的。在这两个《圣经》译本工作团队之间,存在着某种让人感到有些紧张的竞争,尽管这种竞争得到了控制,他们还是都力争首先翻译完,以成为《圣经》的第一个中译本。最终,马希曼和拉萨在1822年设法出版了他们的译本,比马礼逊—米怜的译本早一年。译者们的工作赢得了极高赞誉。不过,那些通晓中文的人将这两个译本拿来进行比对研究时,发现这两个译本语言都相当笨拙滞涩。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就曾这样评价马礼逊—米怜的译本:“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怎么评价马礼逊和米怜两人的努力都不为过,然而任何一个中国学者都会意识到他们译本之不足。正如预想的那样,原本想逐字逐句地翻译,结果译文的风格却沦落为一种不合习惯的粗鄙表达,其中夹杂着一些不规范雅顺的用语。”③伟烈亚力这里所谓的“条件”,不仅是指翻译的逐字逐句这种状况,而且还包括他的如下所言,那就是马礼逊和米怜聘请来帮助他们汉译《圣经》的华人助手“在中国文人圈子里名不见经传”。
对马礼逊—米怜译本的不满很快就表现出来。早在1826年,马六甲的两位传教士高大卫(David Collie)与修德(Samuel Kidd)就提议再出一部更为雅顺并附有阐释注解的《圣经》中译本④。不久,远在巴达维亚宣教的麦都思(1796-1857)试图说服马礼逊合作对其新约译本进行共同修订,不过他并没有成功。于是,在1834年8月,马礼逊去世不久,麦都思就着手开始完成一个全新的《圣经》中译本,而不仅仅是修订。在完成了整部新约及部分旧约的翻译初稿之后,麦都思说服广州的传教士们参与到他的整部《圣经》的中译工作中。为了进一步获得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对该项目的支持,麦都思于1836年回到英国,可传道会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尚未译完的旧约由郭实腊接着完成,并于1838年出版问世,但印数甚少。鉴于此,这一译本亦可称为麦都思—郭实腊译本。最后,1843年,也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所造成的余劫之中,麦都思决定一意孤行,于是一次新的合作翻译行动启动了。来自新开埠的口岸城市的传教士们聚集到香港,拟订了一份翻译准则,这份准则也就催生了后来所广为人知的“委办本”汉译《圣经》。
这一译本因其出色的译文风格而赢得了高度赞誉⑤。该译本后来多次再版重印,直到20世纪20年代依然流行。由于该文本坚持使用后来被传教士称为“深文理”(high wenli)也即“标准文言”来翻译,它要比其他任何《圣经》中文译本都要更为中国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阶层读者所接受——其实,该译本也是第一部以中国知识精英为诉求对象的《圣经》中译本。不过,不少传教士发现,该译本并不能作为原文本的忠实译本,部分原因在于为了确保译文的文学品质所采取的翻译方法⑥。人们一般认为该译本的行世应当归功于麦都思,他是那些“委办”代表们的精神领袖,其次应当归功于其主要文学助手王韬(1828-1897)。本文将通过对“委办版”《圣经》译本的考察,来探讨麦都思与王韬两人对此译本之贡献⑦。
二、麦都思的《圣经》汉译之路
差不多早在“委办”代表们着手《圣经》汉译之前二十年,麦都思有关《圣经》翻译的那些想法就已尽人皆知了⑧。在1827年或1828年,他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过马礼逊《圣经》汉译本“外国的、蹩脚的风格”,同时也将自己翻译的《马太福音》前五节的译文寄给了马礼逊,并告知对方“译文(较之马礼逊译本)略有改动,或许有助于提升改进(马译本)之风格”⑨。据麦都思说,马礼逊回复道,他们两人之间有关《圣经》汉译的思想差异太大。“如果要将两人的翻译思想兼顾在一起,照此断难完成一种译本。所以我(麦都思)最好着手翻译自己的译本。当然,这并非是我所愿为,因为与马礼逊相比,我在中文方面的修养还远不够,同时也希望在将来某个时候,他会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到这项工作上来。”
早在1834年,麦都思已经开始他自己的《圣经》汉译工作,并编译了一部《福音调和》(Harmony of the Gospels)⑩。这是一部根据福音编纂而成的有关耶稣生平事迹的译本,其中每段都附有适当的注释。显而易见,这并非只是对马礼逊译本对应部分的简单修订,而是一部全新的译本(11)。在四月之前,麦都思已经将最初20页、双面打印的译文印刷了出来(12),而且他也将此向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写信作了汇报(13),这显然标志着他有意以此为基础而完成一部《圣经》汉译本。他告诉公会说,他也许在努力让译本适合阅读方面走得过远了,他亦不免为此感到担忧。倘若如此,在一部新的《圣经》汉译本中,就需要在他自己的译本与马礼逊的译本之间求得平衡,这个新译本需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圣经》思想之原意得到准确表达,同时纯粹的中文风格也需要保留”。可以确证麦都思将这一译文样本寄给了马礼逊,因为我们从马礼逊1834年5月16日的日记中多少带有些妒忌的反应中可以获知:麦都思“想让那些中国异教徒接受《圣经》。完全忘记了那些基督徒——恐怕所有的基督徒——有多么讨厌这一译本,觉得它是多么有名无实。在他看来,借助于他那种标准提升了的风格,他就能让《圣经》汉译本成为一部相当受人欢迎的客厅读物”[1]517。
麦都思承认,他之所以选择一种调和的翻译形式,是为了在不直接挑战马礼逊的情况下,尝试一种全新的翻译风格。“我着手翻译了《福音调和》,其中我尝试一种新的翻译风格,以便更适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这样既不用重复劳动,亦不会妨碍我们那深受敬重的友人的劳动成果。”(14)麦都思殷切期待《福音调和》能够成为一种新的《圣经》汉译的范本。就在马礼逊去世后不久,他在一处文字中这样说道:此译本即将问世,就此而言,“那些本土读者和欧洲的汉学家们对此译本的长处不会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的”(15)。他说,倘若此译本受人欢迎,他不仅会再出第二版,而且还会计划译完整部《新约全书》。如果那样的话,麦都思保证自己将会全心与美国传教士们合作,而且也会跟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合作,相互交换译稿,并相互批评指正。他重新申请准许再访广州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促成此事。1835年4月1日前,《福音调和》第二版也已在印,而且麦都思也宣称,他的福音翻译已经接近全部完成,他希望自己能在几个月内完成全部《新约全书》的翻译(16)。
至于上文中提到的“美国传教士”,麦都思主要是指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当时裨治文得到了美国《圣经》公会的一笔资助,用于《圣经》的翻译再版。在致所属差会的一封信函中,裨治文对麦都思翻译的《福音调和》作了一番描述,并接着汇报道:“我们目前正在这里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进展缓慢,如履薄冰。我们是从《路加福音》开始翻译的,一直在努力使这些译文更加信达,也使之更为符合中文遣词造句的习惯,同时每一处也都竭尽可能严格忠实于希腊文本。”(17)一两个星期之后,裨治文注意到,马礼逊父子、郭实腊还有广州其他一些传教士达成了一致,在马礼逊—米怜译本修订之前,不需要再在任何新的《圣经》译本上劳精费神(18)。马儒翰也在协助修订译本,裨治文也向他所属的差会建议,他们想请马礼逊来领导做这项工作。译经所需要的必要经费资助并不是问题,美国《圣经》公会慷慨答应支持,而马礼逊也赞同他儿子马儒翰参与其中。之所以聘请马儒翰,在今天看来,或许部分原因在于他精通中文,不过这也得到他父亲的许可与支持。
随着译本修订工作的推进——《路加福音》在1834年秋天完稿(19)——裨治文获悉麦都思获得批准前来广州参与此事(20)。麦都思是1835年6月到达的,来后很快就投身于《新约全书》的翻译工作中。裨治文评价说:“他现在的主要精力就在于《圣经》中译本的修订,我也跟着他从早到晚不得休息。”(21)有时候麦都思说自己是在“修订”《圣经》汉译本,有时候他又说自己是在“翻译”或“重译”《圣经》。而裨治文也是在“修订”与“重译”之间摇摆不定(22)。
如果说广州的《圣经》汉译本修订工作已启动的消息刺激了麦都思,让他加速了自己的计划的话,那么,1834年8月1日马礼逊的病逝进一步刺激了他,促使他加快了自己的计划实施。在三个月内,麦都思即向伦敦传道会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同意他对《圣经》汉译本作一个全面完整的“修订”。他对可能因此挑战到像受人敬重的马礼逊这样的传教士兼汉学家的地位所带来的风险一清二楚。但他还是辩护道,这项事业太重要了,容不得任何耽搁。“(马礼逊)现如今已经长眠,作为对他的回报,不容那些婆婆妈妈的想法来干扰我们认真考虑如何将《圣经》翻译得更有文采,更为中国读者所接受。”(23)几个月之后,他对马礼逊的译本提出了一份详细的批评意见,也提出了一个整部《圣经》新的汉译本的翻译计划,其中说道:
(马礼逊的新约)译本到处可见许多小字注释和虚词(副词或介词——译者注),这些在原文中当然无可厚非,而且在西方语言中也是必要的,但是在中文里就并非必不可少,如此繁文冗词只会害意,不仅无助于让译文更为畅达,反而只会让其晦涩难懂。确实,《圣经》中存在着某种特殊的风格,许多人也认为这让圣书增添了某种高贵庄严,不过,这些或许只是得益于人们精神上的联想而已,而且,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风格,还在我们童稚时代,就已经被教导来如此看待《圣经》圣书,渐渐地,我们对《圣经》的这种希伯来式的书写风格也产生了敬仰。(24)
对于《圣经》汉译的合适风格问题,麦都思有一个清醒认识。对此他后来曾阐释道:“现如今一个中国人要写一封信,或一篇文论,或一篇公文,一定会借用古人或中世纪的理学家们那种简洁、精炼与综合的风格。”接着他对马礼逊—米怜译本表示了公开不满:“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鼓动过要重新翻译中文《圣经》,而现在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就此再说点什么。已经几年过去了,对于听到中国人说他们对我们现在这一《圣经》汉译本不大满意,我也已经习以为常。他们都认为我们这一译本风格生硬、言辞粗鄙、句子过长、复杂难懂,而且其中有大量未经翻译的词语,在那些中国读者眼里,这一切都给他们一种外来蛮夷之印象:不少人在翻过一两页之后就将其扔到了一边。”他说,这也是促使他翻译自己的《福音调和》之原因所在。
在广州,麦都思一直试图找到一条船,而不是跟着一个鸦片贩子一起深入中国沿海地区去考察。即便在此期间,他也忙着自己的重译工作。在1835年8月24日的一封信中,他说广州的传教士们向他提出了建议(25),还说四福音书“也已经交给了当地几位有学问修养的士子,以便他们审读”(26)。显然,在重译本印刷之前,马儒翰通读过不止一次,而且郭实腊也已经审读过《创世记》和《出埃及记》。在1835年11月1日沿海考察归来之后所写的一封信中,麦都思表示自己需要找几位中文老师和抄写员,以加快《新约全书》的翻译进度(27)。“目前我跟郭实腊先生和马儒翰一道,正在就四福音书的翻译修订做些收尾工作,而且也已经完成了从《使徒书》到《雅各福音》的结尾的翻译。”(28)郭实腊和马礼逊完全认同他的翻译准则(29)。1836年1月前,麦都思与他的助手们已经修订完成了整个《新约全书》,另外还完成了旧约全书中的《出埃及记》(30)。他建议将前者大部分带回到巴达维亚,并在那里出版一种平板印刷版本。至于余下的旧约全书部分,他愿意与郭实腊分工协作;先各自准备自己分担的部分,然后再交换译稿。他希望能在即将到来的返回英国的旅程中完成自己所承担的大部分工作。而这些即将展开的工作显然是一种新的翻译,而不仅仅是修订译稿。
在麦都思回到英国之前,先前出版的新约部分遭到了伦敦传道会马六甲分站两位传教士毫不留情的评论(31)。(该评论结尾这样写道:“如果还有一种译本声称自己忠实于原文,其实又最不忠实于原文者,那就是这部新的《圣经》中译本。”)麦都思事先并没有将新约译稿初稿送到马六甲去——这是一个策略上的失误,这一点他后来才意识到。这两位马六甲的批评者就是传教士伊文斯(John Evans)和戴尔(Samuel Dyer)。伊文斯是这次批评的背后主导,他是一位古典学教师,当时年仅30岁,曾向伦敦传道会提出申请一职位(32)。此时他略懂中文,不过从未尝试过中文翻译,其目的只不过是要拿中文译本与希腊原文进行比较而已。在对这一“过度”批评的反驳中(33),麦都思尚能够表明某种程度上伊文斯与戴尔两人根本没有读懂他的中译本。与此同时,他们的来信却已经寄达伦敦传道会,而这给麦都思的翻译事业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
麦都思代表他自己、郭实腊和马儒翰的申请也于1836年10月28日从伦敦的哈克尼(Hackney)寄出(34)。申请中附有一份对马礼逊翻译的《马太福音》汉译本的评价,另有一份对《路加福音》与《歌罗西书》第一章的新旧译本的比较,还有一份儒家“四书”的第一部分的自由翻译和直译两种不同的翻译样本,这两种翻译样本旨在“显示中文风格的独特性”。
在向马礼逊和米怜表达敬意的同时,麦都思也强调了自己所承担的工作的“困难与棘手”,然而,无人能够拒绝“上帝的事业”。由此可以看出,他已经对自己当初评价马礼逊的观点作了一定的调整。他还提到了美国《圣经》公会现在在《圣经》汉译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以及马礼逊的儿子在此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不过,他也引述了几位中国人对马礼逊—米怜《圣经》汉译本毫不客气的批评议论。这些中国人包括朱德郎,他是麦都思的一位助手,并跟麦都思一道去了英国,另一位中国人是梁阿发,一位由马礼逊施洗并授予神职的华人牧师。他们描述马礼逊的《圣经》中译本大量使用非习惯用语,晦涩难懂,外来语色彩浓厚,句子僵硬,而且啰嗦冗长,尚不地道成熟。梁阿发还补充说:“如果此译本的读者预定为中国人的话,那此译本必须经过彻底修订,否则,它根本达不到最初计划的目标。”
据说,现存译本最大的问题就是其使用非习惯性用语的译文特色。传教士们所撰写的那些宣道小册子,要比他们所翻译的那些《圣经》中译本更为华人读者所接受。因为那些宣教小册子的风格更接近真正的中文,相比之下,《圣经》中译本在语言风格上则显得外来色彩尤为浓厚。依照麦都思的观点,一种特殊的中译本就必须使用熟言习语。“因为中文是一种惯用语(成语)语言,而且词语中的习惯用语搭配现象要比其他语言都多得多”。马礼逊—米怜译本过多地使用虚词,这些虚词是为了支持原文句子的语序,甚至当语序并不自然的时候也依然使用;而且译文中到处可见关系从句,而这在中文中是极为令人讨厌的,如此等等。对此,希伯来语法需要避免,而那种比喻修饰的语言一般也需要转为平实。而且,依照《圣经》公会的原则,既然《圣经》出版必须“未经任何注释或评论”,那么为了准确考虑,就需要使用未经修饰的中文对应词来取代直译的方式。同时也需要对中文韵文的节奏予以高度注意,用麦都思的话来说,即需要注意“句子的对称”。他还为自己随身带的一位华人助手进行辩护,并总结说要想真正得到中国士大夫阶级的认可有多么困难。“我们在中国没有什么好指望的,除了被憎恶,就是带有傲慢的鄙视。”麦都思的《福音调和》和新译本,用他的话说,不过是在一位中国译者的帮助下,朝着最终译本的方向迈出的最初几步而已。“毕竟,最好的翻译还是由一位当地人完成的;而当我们可以得到一位有学问、态度虔诚的中国人,且这位中国人对本国经典修养深厚时,毫无疑问他就可以完成这种翻译,有了这样一种译本,此前我们所完成的再好的译本也只有为之让路了。”在他们那个时代,麦都思的上述观点意见相当超前,与当时大多数《圣经》英译本的观点不一致,直到1970年,才有新的《圣经》英译本的出版。至于1611年的钦定《圣经》英译本以及1885年的改进本,据说“译者们觉得,要做到译文忠实,这就需要他们尽可能将原文的特点予以重组再造,譬如说词序,句子的结构和间隔,甚至还需要对语法进行不规则处理”[2]132。这也是麦都思的批评者们的立场。
1836年11月25日,麦都思的建议引起了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编辑委员会的关注(35)。伦敦传道会的几位代表也受到特别邀请而出席。麦都思的建议被极为刺耳的回话拒绝了,还被谴责为“企图用人的话语来替代上帝的语言”(36)。作为替代,委员会敦促伦敦传道会对马礼逊—米怜译本进行修订,并承诺承担相应费用。作为对麦都思的进一步打击,委员会还建议将他的助手朱德郎立即遣送回中国,其费用由传道会承担。他们甚至还敦促已经出版了的新约译本必须禁止继续流通传播。
委员会对于麦都思建议的愤怒拒绝,用麦都思的翻译原理并不能简单地加以解释,也不能从伊文斯和戴尔对他的攻击中得以解释,这是麦都思试图用自己的译本取代马礼逊—米怜译本而招致恼怒的结果(大概这种恼怒也蔓延到了那位伟人的儿子身上,因为他也参与到了麦都思的上述企图之中)。委员会成员中有些还是马礼逊的老友,尽管他们不懂中文,但在他们看来,马礼逊的译本是符合教会教规、达到了经典的标准的。委员会秘书乔伊特(Joseph Jowett)试图就有些委员的反应向麦都思作出解释:“(马礼逊的)工作被死亡之手终止了,对此无人能够阻挡,当他的位置由其他少数几个人来取代的时候,这些人最初只是试图对他的工作作些改进,但却公然提供了一种新的译本来取代马礼逊的译本,而那些资助当初是提供给一位准备充分、受人敬重的老朋友的,而且所得到的出版授权、平板印刷等所涉及的费用,也都是由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提供的。这就是委员会中有些委员所表达的感受,我向你保证,要想劝阻这些委员放弃他们强烈的决心和感受并非易事。”(37)
为了努力掩盖自己内心的愤怒,麦都思尽力拟就了一份冗长的“就计划中的《圣经》中译本修订致伦敦传道会董事们的一份备忘”(38),这份备忘用不到四分之一的篇幅谈他自己有关《圣经》中译本的修订建议,剩下的篇幅都是在为他自己的翻译以及传道会对他的指责辩护。备忘开篇即重述了那种指责他的翻译,不过是“企图用人的话语来替代上帝的语言”,紧接着又为阐述一词进行了大胆辩护(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印刷本中,“转述”一词又被小心谨慎地改换成了“自由翻译”)。在翻译原则中,“转述”(“自由翻译”)早就允许使用了,麦都思辩解道,更不用说在钦定版英译《圣经》的翻译实践中了。问题之关键,“在于译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偶尔偏离原文的那种构词法”。
在麦都思看来,就《圣经》中文翻译而言,应该给予译者更多自由,因为中国读者完全缺乏对于《圣经》的基本知识,而且他们更“偏好自己的习词熟语和构词法,他们根本不会去翻阅一本粗鄙的或外国风格的书”。麦都思还以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具有革命意义的翻译理论作为自己申辩的支撑。坎贝尔的这部著作名为《四福音书,译自希腊文,附前言、注释、批评以及阐述》(1788年),该书前言中的第十篇专门讨论了翻译问题。坎贝尔在此文中列举了译者必须遵循的诸多要求,其中第二条即为“在自己的译本中所传递出来的,要尽可能多地与原文作者天才性的语言创作、其精神以及方式……原文作者风格的典型特征相一致”[3]340。第三条是:“要注意,译文要尽量接近原文的品格,看上去要自然顺畅,不要给批评者留下任何把柄,让他们指责译者在译文中用词不当,或是词不达意,或是晦涩难懂,或是结构上不合语法规则,或是译文粗鄙等等。”在后来的辩护中,麦都思还不时呼吁要去关注中国人的语言“特质”,这种特殊的语言特质应当成为译者遣词造句的指导。麦都思虽未将自己的上述翻译观点作为一种原创性的理论,但在他后来的“委办版”《圣经》中译本的翻译实践中却体现了出来。
麦都思的“备忘”强调了需要一种新的、尊崇对方习词熟语的翻译,接下来又将话题转到了传道会对他的建议的拒绝上,他将此视为由自己陈述观点的方式不当所造成的。他将自己和马礼逊的译文连同英文白话译文一并作为附录送呈。不幸的是,尽管马礼逊的中文译文看上去因其外来语汇而显得难看,可是将其译成英文白话后读起来却很顺口;相反,麦都思的中文译本读起来相当顺畅,但译成英文之后看上去却很难看。
“备忘”一事并非此次争辩的结束。数月后,马儒翰致信传道会,对此前他们所作出的结论提出抗议(39)。他申辩说,根本就不是麦都思自负地想去尝试一种新译本。他父亲的《新约全书》出版问世时,他在中国呆了只不过七年而已,此后,《圣经》中译的外在条件得到了不少改善,能够得到的帮助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他父亲亦曾考虑过原译本在修订之外的其他可能性,并在1834年4月致信给他时说,“要是有空闲和精力的话,我倒宁愿将《圣经》重新翻译一遍”。马儒翰呼吁并期待出现一种新的使用中文习词熟语的译本,这种译本应当就像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脑袋”,最后,他还对伊文斯和戴尔两人的中文知识进行了猛烈的毫不留情的抨击。
与此同时,伦敦传道会一位前传教士修德也对麦都思的提议发起了攻击,修德当时为伦敦大学中文教授。他的冗长论辩(共21页印刷页,并附支持材料)标注的时间是1836年12月23日,这距此事已过去一个月,伦敦传道会已无暇顾及(40)。顺便一提的是,同样是这个修德,十年前也曾提议,在马礼逊—米怜译本基础上出版一个更符合中文习词熟语特质的译本。修德对麦都思提议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无疑是与他对马礼逊的忠诚有关,或许是因为他不喜欢麦都思,不过他对《圣经》翻译所采取的态度,则有可能源于他确实对此有兴趣。“一个翻译者的目标,并不在于让一个《圣经》中译本看上去就像是出自一个中国人之手,而是要让那些希伯来作家们依然能够去描述他们自己的方式、风俗和习惯。”他也提出将基督徒的观念等同于中国人的观念的危险性:“我个人的经验是,要说服那些中国人不要试图将上帝的教义与他们自己的信仰教义等同起来殊非易事;而当我们用他们的语汇来指示那些精神对象的时候,使用的频率越高,就越是增加了这种困难。”修德声称,新的《圣经》中译本“不过是为了愉悦异教徒,此乃该工作之主要特征”。“所谓忠于原文,从来就未曾被说成是修改变更的原因所在。否则的话,我们不是将《圣经》堕落成为异教徒的信仰和实践,并将那些作为上帝表征和超越存在之呈现的圣迹降低到等同于那些愚昧、迷信之人的无知思想了吗?”
还在英国期间,麦都思就出版了他的《中国:现状与传教前景展望》(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一书。在此书中,麦都思再次提到了《圣经》的中文翻译这一话题[4]549-551。他疾呼道,目前急需对马礼逊—米怜译本进行修订,还重复了修德对马礼逊—米怜译本极为审慎的批评,不过并没有提到修德对于他自己译本的攻击。接着,他又提出了一些容易引起争论的建议,认为需要对马礼逊—米怜的译本进行综合性修订:要确立翻译原则;要明确中文的真正语言特质和精神;要找到一种适当的、准确的、习词熟语式的语言形式;而且还要对不同合作者的翻译草稿进行比较,这种比较“要由那些有学术修养的而且已经受洗皈依了的中国人来作”。不过,他并没有提到自己那个呼吁重新翻译《圣经》的提议并未成功,还惹恼了修德。而在马礼逊遗孀编纂的《马礼逊回忆录》(The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41)中,附录有修德的一篇论文。在此论文中,修德表达了不少他早先未曾发表过的观点,并指责了麦都思的蓄意曲解。
根本就没有人对马礼逊—米怜译本进行所谓的修订,原因大概是除了麦都思还有他的同事之外,再无其他传教士能担当此任。正如上文提到过的,1843年,那些得到了《圣经》和传教团体支持的新教传教士们在香港聚会,同意进行全新的《圣经》中译工作。《新约全书》被分解成几个部分,再分包给在香港和新的口岸城市里的译者委员会。之后,从各中心口岸再选出一位代表组成一个代表委员会,委员会的代表们在上海集中,确定出最后的译本。可未曾预料到的是,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却悬而未决。其一,究竟该如何翻译God,代表们对此始终无法达成一致,究竟是像马礼逊—米怜那样翻译成“神”,还是像麦都思那样翻译成“上帝”。最终该问题责成由一个分委员会予以解决落实,该分委员会由麦都思和理雅各组成。对麦都思来说不大妙的是,理雅各倾向并坚持用“神”来作为God一词的中译,因此该问题也只能暂时被搁置起来(理雅各最终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不过那时已时过境迁,对麦都思而言已太晚了)。其二,有关翻译语言、风格和原则等的规定也过于含糊不清:“所有翻译成中文的《圣经》……必须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在意义上保持高度一致;与此同时,也允许使用中文里的习词熟语,也要注意符合中文语言风格。”(42)有关God一词的合适中文翻译,也就是所谓的“术语问题”,对于新教传教士们来说,成为他们最大的世纪之争(43)。而有关翻译的话题却导致了代表委员会的解体,并催生了基于不同翻译准则的数种不同《圣经》中译本的诞生。麦都思自己始终处于两种论争之中心,事实上,也可以说正是他那些为其所坚守的个人观点招致了这两场论争。
翻译问题包括两个各自独立的话题,用传教士们的术语来说也就是译文风格与翻译原则。“译文风格”,指的是译文所用的中文的文言水平。当时所谓“浅文理”(low or easy wenli)(44)与“深文理”的表述尚未普及,不过不少传教士已经意识到中文存在着不同文学水平之间的差异性。而“委办版”中译《圣经》后来被说成是用“深文理”的中文翻译而成,其实这不过是个标准的文言译本而已。有些传教士反对该译本的语言风格,因为他们想让这个译本尽可能为更多的中国读者所接受,甚至不惜为此而牺牲其所谓的优美文笔(45)。为此,麦都思刻薄地认为,那些传教士们之所以反对该译本,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对其传教士同胞的中文著述之外的文言知之甚少而已(46)。
其实,几乎还在“委办本”中译《圣经》完成之前,对于“深文理”的《新约圣经》中译本的不满就已经出现了。还在1850年3月,上海当地的传教士委员会就对此译本提出了反对意见,并建议他们所选派的代表在即将启动的《旧约圣经》的中译中,倡导一种“平易的翻译风格,这样那些受过一般教育的人也能够读懂”(47)。尽管这种倡议并没有得到其他地方委员会的响应和采纳,但这显示出在该话题上正在不断增加的压力。
“翻译原则”是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该问题基本上涉及翻译文本的定位问题,包括从译文的准确性到文本的接受度等诸多方面。麦都思对于中译本的读者接受度的强调,以及他用“上帝”来作为God的中译的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中国早期文献中,“上帝”一词指的是“至高无上的天主”(supreme deity),这与麦都思的信念相吻合——同时与其他人的信念,尤其是伦敦传道会的一些人的信念也相吻合——那就是这些人坚信,早先的中国人已经有了关于上帝的知识。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已经确定的中文术语,“上帝”这个词对中国读者来说似乎也是可接受的。那些反对麦都思的人则拒绝接受所谓中国人已经有了本源性的有关上帝的知识的观点,他们倾向于将《圣经》中的God翻译成中文里更通用的术语“神”(God,spirit)。
围绕着翻译原则问题所发生的尖锐分歧,分裂了《新约全书》翻译的代表委员会,但这种分裂尚未公开化,直到《旧约全书》翻译工作启动的时候。在五位选派代表中,其中三位——麦都思、施敦力(John Stronach)、小米怜(W.C.Milne)——来自于伦敦传道会。施敦力与小米怜两人似乎受到麦都思有关语言风格和翻译原则观点的引导,在有关“术语问题”上与麦都思立场也一致,他们在麦都思起草的有关这些问题的信函上都签上了各自的名字。委员会的另外两位代表分别为裨治文和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除了投票,文惠廉从未出席任何一次会议,他对此所作的解释是,他不堪这种神经系统之“严重困扰”,对他来说,这让他根本无法持续开展自己所承担的工作(48)。这种紧张与不安妨碍了文惠廉的《圣经》翻译工作,但并没有妨碍他就汉译《圣经》的术语问题与翻译原则问题撰写一些引起争议的小册子,对此,麦都思与小米怜都曾毫不犹豫地指出过(49)。因此,在后来的日常翻译工作中,唯一能够听到的就只有裨治文的批评声音了,而且他也声辩说自己对所谓“简洁的译文风格”的反对常常为人所忽略(50)。而在麦都思和他的同事们看来,裨治文的贡献微不足道。他们私下也是这么议论的:“即便是他不参与到代表委员会中来,‘委办本’《圣经》的中文翻译亦不会有任何不同。”(51)在《旧约全书》已经着手翻译的时候,小米怜在一封书信中这样描述裨治文的作用:他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要更为无用,人也显得不怎么积极主动”(52)。
尽管有关翻译术语问题的争论引起了代表委员会内最初的不和,但这并非是导致委员会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最终导致伦敦传道会让它的代表们退出代表委员会的原因,是文惠廉的缺席以及裨治文看上去的无所作为和毫无帮助。在发出一连串的催促之后,伦敦传道会的董事们在其1850年7月22日的会议上,督促他们的传教士们将自己的旧约《圣经》独立翻译完毕,不要“与其他任何差会的传教士们掺合在一起”(53)。起初伦敦传道会的代表们并不大愿意撤离委员会,因为他们坚信,如果《圣经》中文译本是一种共同合作的结果的话,“可能在印刷的时候,就能够获得更多《圣经》公会的资助,而且在出版之后,也会有更多的传教士乐意使用并传播这一译本”(54)。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八月份接到差会发来的最新一次毫不含糊的指示之前,他们已经着手翻译旧约《圣经》,并将其作为已经扩大了的代表委员会的工作的一部分。
委员会两位新任代表克陛存(Micharl Simpson Culbertson)和叔未士(Jehu Lewis Shuck)帮助在伦敦传道会及其选派的代表们之间打圆场,因为要是他们站在文惠廉和裨治文一边的话,他们就可以否决麦都思及其同事们所作的决定(55)。后者的气馁和沮丧在他们私下往来的信件和报告中清晰可见:“叔未士和克陛存来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来了解《圣经》是在如何翻译的”,三人在写给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的信中如是说(56)。“叔未士先生跟我们在一起待了六个月,克陛存先生则只待了一个月,不过很遗憾的是,他们对《圣经》是如何翻译的并没有多少了解。”“我们无法不相信这一点,那就是对于中国语言的特性与精神,很大程度上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因此,1851年2月伦敦传道会的代表们最终决定听从他们传道会的要求并撤离翻译组,并不让人感到有多么吃惊。从他们的信件可知,他们这样做并非是因为与委员们在翻译原则和翻译风格上存在什么分歧,而是因为他们的那些合作者要么显得无知,要么就是喜欢找茬阻挠翻译工作。很自然的是,他们并没有将这些公开说明出来,只说他们是在遵循传道会的意见行事。
在双方向其他在华传教士以及《圣经》传道差会等作了一番解释和陈述之后,最终文惠廉、裨治文和克陛存这一方又将翻译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他们呼吁《圣经》中译应该更为贴近原文,而且要用简单易懂的口语,这一观点在当时可能会得到大多数在华传教士的青睐。当初,麦都思并不认为存在所谓翻译原则上的分歧——难道裨治文和文惠廉他们自己不是代表中的一员吗?——麦都思认为,攻击不过是文惠廉和其他传教士为了赢得《圣经》公会支持他们独立翻译《圣经》的计谋和策略而已(57)。不过,面对那些毫不掩饰的批评,麦都思最终被迫进行自我辩护。
说到术语问题,两个主要人物——文惠廉和麦都思——的个性都参与到了翻译争论当中。文惠廉为了让人信服他作的那些解释和理由,显示出他更像是一个政客,一个总是能够持续掌控自己给别人所留下的印象的人。当然麦都思也是这样看待他的,因为当文惠廉准备前往伦敦的时候,麦都思曾告诫伦敦传道会要提防他,并说文惠廉特别擅于“花言巧语”,而且“凭借其如簧巧舌获益多多”(58)。相较之下,麦都思远非一个善于权谋之人,更谈不上是一个纵横捭阖的外交家了,曾经有人描述他“言行方式有些直率”(59)。在作出了足够理由的解释说明之后,麦都思坚信,重新汉译《圣经》之必要性远在顾全马礼逊的所谓“完美”名声之上。当然,麦都思也为自己的直率付出了代价。就在他来到亚洲后的几年间,曾经发生过一件小事,此事足以证实麦都思的这一个性。他是作为一个印刷工被派到马六甲的,不到一年他就被任命为传教士。在给伦敦传道会的一份报告中,他的导师米怜(小米怜之父)却用一种讽刺的话语,对麦都思的这一晋升给予了如此评价:“鉴于麦都思先生发现自己对基督教事业抱有激情,而且天赋异禀,我也就只好建议传道会董事们另派些才能低下者来摆弄那些印刷机器了。”(60)就在被授予圣职之后不久,麦都思就开始向他的导师发起了挑战。他不满于自己被看成是米怜的下属,而且认为米怜盛气凌人,或许对年轻的传教士们还心怀嫉妒。他拒绝了米怜让他在新建的传道学校教授一般宗教课程的指派,他说自己是来宣扬上帝福音的,而且还认为自己的中文水平也要比米怜高(61)。最终,在尚未获得米怜和伦敦传道会许可的情况下,麦都思干脆去了另一传道站——槟榔。对此,米怜向伦敦传道会解释说,在过去两年中,自己与麦都思“有些小分歧”。不过他也建议对此应该宽容:“他并非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人——给予他你最真挚的劝告吧——提醒他将来不要对类似琐屑之事掉以轻心——至于这件事,就让它到此为止吧。”(62)几年之后,在觉得自己的中文水平已经相当了不得之后,麦都思自负且公开表露出了对文惠廉和克陛存的鄙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裨治文也不屑一顾。他那本有关翻译争论的小册子,充满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上的义愤——文中尤其指责文惠廉的翻译不真诚,全然不顾翻译者的责任,而且使用一些小伎俩——其用意不过是为了诋毁麦都思那些有关翻译的观点而已。
关于翻译问题的论争,见诸给国内传道会及在华传道机构的信函、一些文章和小册子中。1851年4月,一篇有关传教士们撤离“委办”翻译组的匿名报道出现在《中国丛报》上(63);接着是伦敦传道会的三位传教士对此所作的回应,对各种陈述提出了质疑,并指责裨治文也即该报道的匿名作者泄露了代表委员会机密的会议记录[事实上,该报道的作者是裨治文的同事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不过他否认自己从裨治文处获得了任何事实材料](64)。1851年11月10日出现的一份匿名小册子,则对“委办本”《圣经》中的《创世记》、《出埃及记》以及《福音全书》中一直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部分,提出了具体而详细的批评(65)。1852年6月16日,三位来自伦敦传道会的代表撰写了一份小册子,对上述批评作出了回应(66)。1852年9月,又出现了一份对此作出回应的小册子,作者为文惠廉,自称为“委办本”《以弗所书》的批评者(67)。1852年11月15日,伦敦传道会的三位代表又用篇幅更长的一份小册子,对文惠廉的回应作出了回应(68)。而《圣经·创世记》的批评者克陛存也写了一份小册子,对裨治文的批评也作出了回应(69)。
批评者们的理论立场在裨治文写给他的差会的一封信函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我认为,翻译风格应该是忠实于《圣经》文本,同样应该明了和简洁,尽可能地保持和呈现原文的各种独特性。”(70)为了获得各种支持来反对麦都思和他的同事,克陛存给福州传教士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不得不说,对那些《圣经》翻译者同仁,我们已经失去了信心。首先,我们完全不赞成他们所选择的译文风格,而且我们也坚信,大多数在华新教传教士对此也是不满意的。上帝福音应该是传给穷苦人的,故《圣经》必须用穷苦人易于接受的形式来翻译。而且,比风格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很多方面也没有打算采用忠实于《圣经》原文的中文熟语来翻译。在《旧约全书》最初几个译本中,原文均遭到了破坏,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这应该受到谴责。注意到这一点我们甚为感伤,我们现在并不是指责用那种频繁的松散的转译来替代翻译,而是指责那种词语的完全漏译,句子的部分漏译,以及有时几乎是整行句子的漏译(常见的倒是添加了‘很多误译’)。”(71)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出自《创世记》第七章,其中有两行被缩译成了一行:“我们知道这是蓄意为之”。另一个例子是第九戒,被译成为“勿妄证”,这种翻译倒是与“不可做假证”很吻合,但“对邻里”部分却被略去了。“我们不明白,一个基督教传教士怎么能够如此翻译,其中误译、漏译现象俯拾即是,这种现象只有在异教徒手上才会如此频繁发生——告诉他那可是上帝之言啊!”
克陛存和文惠廉在其《中文〈圣经〉上海修订本相关论文》中所提出的大部分批评相当无聊,因此,麦都思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这些指责视为不过是用代词替代名词,或者将修辞风格转换成为一种平易语言这样的小问题而已。不过,对于那些文本漏译问题之类的指责,麦都思却不大好应付。“如果两个句子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或许几乎是相同的观点,其中一句就被省略了。”在《创世记》第七章的例子中,诺亚遵循上帝之指令,将各种动物选择一对送到方舟上。在“委办版”译本中,第15和16句被合成了一句,略去了重复部分。麦都思对此指责所作出的回应是:“这样翻译是为了避免同义词的简单重复,否则这在中文里只会词不达意。”(72)在致伦敦传道会的一封信中,他详细解释道:“在已经说了‘所有动物都被雌雄成对地带进了方舟’之后,一定还要加上一句‘他们都雌雄成对地进去了’吗?”(73)而在克陛存的回应中,他并不认为被删减的形式表达了完整的意思,不过,他进一步声辩道,即便它表达了原文完整的意思,这种改变也是不正确的。“对于《圣经》的谦恭尊崇,难道不是如此要求我们,一个得到启发的作者将同一个意思表达了两次,而在翻译中也应当表达两次吗?”(74)对大多数传教士而言,这一辩驳是无法抗拒的,但对麦都思而言却并非如此,因为他坚信每种语言都有其独特性。
至少从1836年麦都思怀有如此信念以来,有谁能说他对《圣经》中译的观点发生过变化?他新翻译的译本明显不同于旧的译本吗?毫无疑问,第二个译本大大不同于第一个译本。两个译本都旨在通过使用为人所熟悉的表达方式和避免使用外国短语来满足中国读者,但是,尽管1836年译本(以及此前的《福音调和》)的目标是使用最简单的文言,而“委办版”译本的目标在于使用一种标准的文言,这样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中国人亦能够欣赏译本。很少有人会对像克陛存和文惠廉这样的批评者的争论产生同情,不过他们对于翻译的不同“风格”的观察也并非毫无根据。
在他自己的声辩中,麦都思将新译本的语言风格描述成为“朴实得体的”、“朴实简洁的”或“朴实平易的”,他的意思是说,新译本不仅符合好的文言,而且也符合一种好的汉语散文标准,这种标准要求超越一般简单的词汇与句法,还要能达到简洁精练、平衡及“句子的匀称”等。在某处解释中,他说自己和同事们“努力在使用一种学者式的风格,这种风格既不会违背士子的优雅品位,同时也能为那些初通文墨的广大民众所理解接受”(75)。不过,麦都思最为重要的声辩在于坚信“任何一位通读过我们所翻译的《新约全书》的读者,承认这种译文确实是一种中文书面语,并认为我们的译本是一种用中文完成的有价值的作品”(76)。为了吸引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读者,麦都思明确提出,他的《圣经》译本必须被认为是一种中国文学作品。
麦都思处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的有利位置。在整个“委办本”的翻译过程中,他的伦敦传道会同事伟烈亚力,也是上海传道站的一员,曾断言新约中译本“可以被视为麦都思的作品”,而旧约全书中译本的完成,大多也归功于他的“能量与热情”[1]35。麦都思的声音无疑是“委办版”《圣经》中译本翻译中的代表声音。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已经准备好不惜冒犯他的那些传教士同胞,更不用说那些《圣经》公会了。但他自己对于中文散文的判断,从三十余年后的中国来看,确实未曾对其风险予以足够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他相信他的那些华人助手们的良好判断(77)。
三、作为《圣经》译者的王韬
很久以来,麦都思就对其华人助手的文学素养予以密切关注。曾经帮助他完成1836年译本翻译的刘自春,是一位秀才出身、“热心于中国经典”的士子。麦都思这样评价他:“他母语精熟,可以对改进译本中的习词熟语提出不少建议。”(78)[4]296而另一位年轻的士子江庸之,在“委办本”翻译之初即已成为麦都思的助手。麦都思这样评论他:“他在术语运用和语词表达方面学识渊博、精准得当,我们认为在校订《圣经》翻译中他起到了很大作用。”(79)麦都思也高度评价了历史人物徐光启(1562-1633),这位学者给利玛窦的中文著述提供过帮助。对于徐光启,麦都思评价“他是一位极富才学与影响的士大夫”。他特别提到了徐光启给予利玛窦文学上的帮助:“他对语言的精确把握,让他在帮助其引导人(宗教上)利玛窦的著述中呈现出一种干净精致的风格,有助于更高层级的读者接受。”(80)[4]227对于麦都思而言,其《圣经》翻译的主要助手王韬在翻译中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就同徐光启对利玛窦的帮助一样。
当传教士们获准能够进入通商口岸时,麦都思对“士大夫阶级”的关注似乎亦增加了。1845年,应一位已经归化的基督徒的建议,麦都思从上海出发,到中国内地作了一次冒险旅行。他成功地装扮成中国人,一路未被识破,直到江西婺源,目的就是为了去见当地书院里的那些儒家学者。一周之中,他就“下榻在这些学识渊博的学者之处,并与他们就宗教及基督教信仰等话题进行了长久且有趣的讨论。那些儒家学者也愿意承认基督教体系的完美出色,以及救世主的高贵品格;不过,对于基督教的排他性以及福音中的那些宣传,他们却表现得极有保留。尽管担心不会有什么决定性的好的结果,我还是将那些基督教真理平静地告诉了他们,而且使有些人心里引发了巨大震荡”(81)。在此期间,为了教化这些人,麦都思赶写出了《耶稣教略》(82)。
在参与“委办本”翻译时,麦都思的助手是一对父子:王昌桂和王韬。从1847年“委办本”开始翻译时,王昌桂即已开始协助其工作,不幸的是,王昌桂于1849年亡故,当时“委办本”的《新约全书》翻译只完成了三分之二,麦都思遂选择了他的儿子作为继任人(83)。王韬协助翻译完成了《新约全书》的剩余部分以及整部《旧约全书》,且在上海宣道站做译员直到1862年。是年,因为给太平军一位将军的进言书被发觉而遭缉拿。他幸运地从上海逃离出来,栖身香港。在香港,王韬帮助理雅各翻译整理中国经典,并由此成为一位文论家和中国报业之先驱。
所有关于王昌桂在《圣经》翻译工作中的贡献的信息,以及不少有关王韬的信息,都来自麦都思1854年10月11日写给伦敦传道会的一份报告(84),其中一项是关于王韬的归化受洗。在这份报告中,麦都思讲到了王韬父亲对《圣经》翻译所作出的贡献。麦都思在其报告中也附上了王韬申请受洗的英文译本。
王昌桂是一个以教授中国经典为生的书生。大约在“委办本”《圣经》翻译启动之时,他应邀前来上海。麦都思之所以提到他,只是因为他是王韬之父,不过说他协助翻译了《新约全书》中直到《罗马书》部分。麦都思是这样描述他的:“他饱读经书,可说是一座‘活图书馆’(‘字典’一词被划掉),但他尤为坚定地信奉儒家思想,并声称‘生为圣人弟子,死亦圣人弟子’,直至病故。他确实未曾改变自己的观点(此处还附加有‘据我们所知,他是暴病而亡的’一句)。我们为他的离去而忧伤,不仅是为他,也为我们自己,因为很难再找到一个能顶替他的人。”笔者注意到在另一地方唯一一次提到这位父亲的,是麦都思在王昌桂死前一个月所写的一封信中。信中说:“我相信可以担保翻译的准确性,因为,我很高兴有一位博学且精通本国文学的人协助我们的翻译工作。”(85)
王韬被选中可能还得益于其他翻译助手的推荐。麦都思将他描述为“一个奇才,虽然在学问上尚不能与其父亲比肩,但在将所学运用到极致方面却要高出于其父。据说他的文风典雅,而且思想圆通”。他的工作和作为远远超出了预期。“他不仅在那些比其年长的助手中赢得了尊重,而且因为其勤勉习惯,还承担了大部分的前期准备工作,经过少许修订之后,这些一般都会为其同事借鉴采纳。就这样,他完成了新约教义部分和整部旧约。《约伯记》、《箴言》翻译中可以见到的那些优美表达,以及整个译本简洁流畅的文风,都要归功于王韬。”
在翻译过程中,王韬对基督教义没有表现出什么个人兴趣。不过,在译本完成之后,当那些仅仅因翻译目的而聚合在一起的译员助手们亦星散而去之时,王韬却身染重病,且唯求一死。“他的良知被唤醒了,”麦都思告诉我们,“他一直忙着翻译的那些真理,在他的思想中鲜活起来,他决定皈依基督教义”。王韬要求马上接受洗礼,不过传教士们却担心他的愿望还挨不到他的苦难结束,所以让他能够再等待一年,看看在此期间,他是否依然能够不改变自己的意愿。接受洗礼后,麦都思说:“王韬又受雇来修订所有的圣歌中译部分,并让这些圣歌译文文雅且富有诗意,不仅其译文形式不至于为那些文人雅士所排斥,而且就其教义而言,也不会为人所反感拒绝。”如果说麦都思翻译的圣歌集(86)尚被称为“我们的中文圣歌”的话,那么,经过王韬之手的圣歌集《宗主诗章》(87),与其说是修订,还不如说是一种全新创作。对此,一些圣歌中所包含的富有中国特色的主题,譬如报答、报应、孝悌、父子关系、主仆关系、认命思想等,都可以印证。
圣歌集并非是王韬因为皈依基督教后完成的唯一书面作品,他也重写了麦都思一本有关清明节献祭的小册子(88)。其《野客问难记》于1854年出版,是对原作的扩充和改写,其叙述方式与原作迥然有别(89)。用麦都思的话说:“他对我们原作中的拜坟、祭祖部分彻底重写,这些话题需要在中文方面审慎地处理表达,而王韬恰能将这些问题处理得当,并更正了先前中国人所持有的不少错误观念。”王韬乐意重写那些宣教小册子,而不是修订它们,这与他的自信态度是一致的,这种态度同样适用于他对待《圣经》文本的态度(90)。
麦都思和他的同事们对王韬抱有很大期望。他们认为,凭借王韬新确立起来的信仰,还有他的文学素养,他一定能成为将基督教教义传递给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理想译者。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王韬自己亦作如是观。之所以将王韬的洗礼申请附在报告中,麦都思是想向伦敦传道会表明“王韬思考基督教之时的真实思想”以及“他究竟是如何思考未来的”。无论是对于王韬的思想还是对于《圣经》翻译来说,洗礼申请都是重要的,不过,因为王韬申请书的书法难以辨识——在微缩胶片上整篇文章已难以辨识完整——所以我只将其作为附录。
自从美国学者柯文(Paul Cohen)认为王韬不仅参加了教会的一些活动,而且还曾受洗,有关王韬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学者们[5]19。在其受洗申请被发现之前,有关他参加教会活动的证据,就是其日记中的一些记录,但这在他生前并未出版。在一些信件中,王韬曾就那些说他为外国传教士服务的指责进行辩护,说这不过是迫于生计而已,不过他从未提及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也没有提及他父亲亦曾为宣教站服务一事。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尽可能不让他那些友人知道此事(91)。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1858年之后,在他的日记中所出现的与基督教文本有关的记录都是负面的,这与一个基督信仰者的言论大相径庭。
在他的病情之外——王韬认为自己患的是肺痨——导致其思想在1853年明显转化的还有另一原因。柯文曾指出,在王韬生病期间,威妥玛(Sir Thomas Wade)的中文老师应龙田曾来拜访麦都思并询及宗教教义问题。应龙田刚从英国回来,此前他跟随英国驻沪新领事威妥玛去英一年,当应表示自己对受洗有兴趣的时候,威妥玛即将其引见给麦都思,以便予以引导。对王韬来说,应代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类型——曾经畅游过西方,如今又希望皈依处于领导地位的西方宗教。两人成为密友后,王韬把应讲给他听的那些旅途见闻写成了一本小册子《瀛海笔记》(92),应的基督教信仰肯定对王韬有所影响。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改变了自己对基督教的认识?1855年,应龙田移居广州;1856年底,王韬的导师、对其皈依基督教起了很大作用的麦都思离开了中国,不久就去世了。柯文曾经提出,王韬为19世纪50年代后期英法联军侵华感到困扰。这段时间,从王韬的一些往来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外国列强的威胁越来越感到忧虑。另外一个因素,可能就是管嗣复的影响。
管嗣复乃桐城派大师管同之子,他曾帮助医生—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翻译一些医学论文,两人合作是从《西医论略》开始的,这是一本关于西医外科的著述,于1857年出版。王韬日记显示,他与管在1858年结为知己。早在1859年,尽管管嗣复很想谋一份工作,但他还是拒绝了裨治文向他提出的协助翻译《旧约全书》的请求,理由是这会与他的儒家信仰背道而驰[6]77-78。为了鼓动管接受这一邀请,王韬曾对《圣经》内容予以了冷嘲热讽,并将中国助手的工作意义降到最低。他说:“译书者彼主其意,我徒涂饰词句耳,其悖与否,固于我无涉也。且文士之为彼用者,何尝肯尽其心力,不过信手涂抹,其理之顺逆,词之鄙晦,皆不任咎也。”听了王韬此番言论,管嗣复给他上了一堂道德课,管走之后,王韬说自己为失去立场而参与到基督教文本翻译工作中感到羞愧。
这一时期,王韬所写的两封信揭示了他与上海宣道站的外国人之间已生疏离之感(93)。两封信中他都引用了《左传·成公四年》中的一句话,即一位臣子进言鲁公不要与南方的楚国结盟时所说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无论如何,从王韬的洗礼申请来判断,他的基督教信仰尽管发自内心,但更多的是关乎伦理原则,而非宗教信仰。尽管让传教士们尤为困扰的华人祭祖习俗对于王韬来说不存在任何问题——他轻而易举就接受了传教士们只敬拜创世主的思想——但他认为所有宗教都有其“玄想与奥义”的观点,表明他是在尽力与基督教教义保持距离。在劝诫传教士勿攻击孔子时,王韬曾颇为超脱地说:“各修其道其教,各得其善果。”
这些观点已经包含他日后所持的宗教世界主义的端倪。在《原道》一文中,王韬提出,新的现代交通技术所带来的世界不断增加的联结,同样预示着全世界在精神上的联结[7]35-36。全球宗教显然会忽略那些彼此之间不可调和的“玄想和奥义”,转而关注一种共同的道德标准。在另一篇文论中,王韬称赞欧洲新的实证主义“宗教”,肯定它不是去关注敬拜上帝或灵魂,或对于来世的信念[7]253-254,而是对个人责任及真理追求的关注。这种思想的信徒被视为中国古代圣贤的追随者。王韬的世界主义显然与他的儒家思想有很多共同之处。
洗礼申请显示出王韬希望自己在汉译《圣经》工作中能起到作用。他所提到的徐光启给予利玛窦的帮助,尤为说明了这一点。在王韬看来,利玛窦需要一个像徐光启那样的文人帮助他,以使他的著述能够得到受过良好教育之士的青睐。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的一些著述为中国人所推崇,甚至还获准入藏国家藏书机构。当把早期来华耶稣会士的成功与当时传教士相提并论之时,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耶稣会士不乏“睿智杰出之士”的辅助。相比之下,新教传教士们尚未物色到合适的合作者,而且“饱学之士”偏偏又被那些教会里的“无知无能之人”排斥在外。“他们中的哪些人能够因为自己对新的信仰的阐述而让自己脱颖而出?”
王韬呼吁能有一位知识精英来宣传福音,可被聘用来参与译经的助手,“一般而言知识并不广博,对经籍义理亦不过略知皮毛”。其结果,他们那些出版物也就速朽而不会为人提起了。
这最终涉及好的文笔问题。为传教士们所推崇的平易风格是不够的,我们认为一种特殊的、富有文学特性、“光彩优雅”的风格在译文中同样需要。“如果将平易简洁的风格与光彩优雅的风格合二为一,作品就会变得优美且值得反复细读玩味。”一部著作“既要彰显那些反复强调的原则,也要凸显其表现方式,即兼顾形式的华美与内容的真实”。那些出自新教传教士们之手的著述,尽管内容完美,但“文风粗鄙”,只能让读者昏昏欲睡。更为甚者,为了让那些劳力者和匠人们能读懂,有些著述甚至是用地方方言撰写的。但是,如果一部著述兼顾形式华美与内容真实,“就会获得文化修养更高的阶层里的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同样,那些劳力者和匠人最终亦会受其影响。王韬最后提议说自己会写出这样一部书:“我倒乐意来写一本关于宗教的书,来揭示基督教之奥义。”
四、翻译之样本
要想对《圣经》“委办本”获得某种印象,仅靠引用那些批评意见和回击批评的意见是不够的,还需要去考察那些文本的译文样本,无论其篇幅多短小。笔者从《约伯记》中摘录的一段,也被麦都思视为王韬最为成功的翻译之一。下面即第三章的第一部分,内容包括约伯绝望的哭喊,因为他强烈希望自己不曾降生在人世间。对《圣经》“委办本”的每一行,笔者都附有一句相应贴切之英文,英文摘录自最近出版的玛索拉版《希伯来圣经》[8]285-286。
1、2.约伯诅其生日,曰:
After this,Job opened his mouth and cursed his day of his birth.He said:
3.我生之辰,不如无此辰,我生之夜,不如无此夜。
"May the day of my birth perish,and the night it was said,'A boy is born!'
4.孰若是日晦冥为愈,孰若上帝不降以福,勿烛以光。
That day——may it turn to darkness; may God above not care about it; may no light shine upon it.
5.何如幽暗阴翳蔽之,叆叇覆之,日蚀谴之。
May darkness and deep shadow claim it once more; may a cloud settle over it; may blackness overwhelm its light.
6.何如是日之夕,惨澹昏暗,不入年期,不进月数。
That night——may thick darkness seize it; may it not be included among the days of the year nor be entered in any of the months.
7.何如是夕,不诞婴孩,不闻欢声。
May that night be barren; may no shout of joy be heard in it.
8.凡能诅日,持咒招鳄者,当以是日为不吉。
May those who curse days curse that day,those who are ready to rouse Leviathan.
9.何如是日昧爽,明星不现,待旦不得,天无曙色。
May its morning stars become dark; may it wait for the daylight in vain and not see the first rays of dawn.
10.是日,母氏育我,致遭艰苦。
For it did not shut the doors of the womb on me to hide trouble from my eyes.
11.母宁堕胎而死,即不然,诞而身死气绝。
Why did I not perish at birth,and die as I came from the womb?
12.母曷提携我,乳哺我。
Why were there knees to receive me and breasts that I might be nursed?
13.浸假当时无生,我今可宴然安寝。
For now I would be lying down at peace; I would be asleep and at rest.
14.国王议士,当年所筑之陵墓,而今安在。
With kings and counselors of the earth,who built for themselves places now lying in ruins.
15.元戎巨富,金银冲栋,而今乌有,我欲与之同归于尽。
With rulers who had gold,who filled their houses with silver."
这里将省略掉那些有问题的例句:第5行中文翻译的“谴”字是难以阐述其义的;另第8行,原版《希伯来文圣经》可以有多种不同解释。
在其他翻译中,我们也注意到存在许多省略和缩减,尽管这些删减本身并无大碍,不过一旦被删除了,亦足以让这种翻译偏离原文。在第1行中,“After this,Job opened his mouth”都被省略,未曾翻译。第3行中,“the night it was said”,“A boy is born”被改变了,略去了口头声明,亦未提及约伯的出生。在第13行中,《圣经》原文中为平行句:“now I would be lying down at peace;I would be asleep and at rest”,但在译文中被压缩成“今可宴然安寝”:“I could now be sleeping peacefully”。
在第13、14和15行中,译文则主要使用的是添加和扩充方法。第13行中,“For”一词被增译为“浸假当时无生”(“If I had not been born at that time”),而第15行中的“With”一词则被扩译为“我欲与之同归于尽”(“I wish to return with them to oblivion”)。第14行和第15行中的平行句“而今安在”和“而今乌有”在原文中都没有,均为译者所添加,相对应的意思是“Where are they now?”
译文段落显示出中文行文对仗的强烈倾向,也就是在语义、句法及音韵方面的对仗。在第3行中,为求对仗而更改了原义;第15行中,不仅增添了两个对仗句“而今安在”和“而今乌有”,而且为了与上文中“kings and counselors”(“国王义士”)对称,“rulers who had gold”亦被改译为“元戎巨富”(“great generals and rich men”)。
为了避免引发读者的不快,原文形象化的语言特色也被调整了,事实上是弱化了。第7行中,“May that night be barren”被简化成“不诞婴孩”(“Not bear a child”)。第10行中,“For it did not shut the doors of the womb on me to hide trouble from my eyes”被大大地弱化,译成“是日,母氏育我,致遭艰苦”(“that day my mother bore me,causing me to suffer these agonies”)。第12行中,“Why were there knees to receive me and breasts that I might be nursed?”一句亦被弱化了,译为“母曷提携我,乳哺我”(“Why did my mother take me in her arms and nurse me?”)
译者在此所主要关注的,正如整个“委办本”《圣经》中所关注的那样,显然是为了保证中文的行文流畅,便于读者接受,同时也不至于偏离《圣经》原文太远。这种翻译避免了那种忠于原文的僵化译法,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那种形象化的语言为代价的。概言之,这种翻译风格符合麦都思所提出的“简洁而明快”和“简洁而准确”的标准。
王韬父亲协助翻译的《新约全书》前三分之二内容,与王韬所负责翻译的《圣经》余下部分在风格上明显不同。直至《新约全书》的结尾部分,尤其是《启示录》中,译者所采用的是过于自由的风格,这种自由风格在前面《约伯书》的译文中可以看出。例如,英文钦定版《启示录》第21章开篇,在我们看来已经足够口语化:“And I saw a new heaven and a new earth:for the first heaven and earth were passed away; and there was no more sea”。主张翻译要忠于原文的裨治文和克陛存用朴实无华的汉语直截了当地翻译道:“我见有新天新地,盖先天先地已逝,亦不复有海。”(94)可以比较“委办本”译文:“始造之天地崩矣,海归乌有,我则见天地一新。”(“The original heaven and earth crumbled,the seas returned to the void,and I saw a heaven and earth entirely new”)。为了更合乎逻辑上的理解,译文改变了从句顺序(“大海消失”与“天崩地裂”对称)。此外,新引入的词“崩溃”和“化为乌有”,要比它们的同义词“消失”和“不复存在了”在中文中更为自然(语气更强)。同样,“天地一新”亦要比“有新天新地”更为地道(也更有气势)。
对“委办本”的大多数批评集中在由王韬负责翻译的《新约全书》的后面部分和《旧约全书》(95)。在很大程度上,王韬比其父亲更愿意而且能够把《圣经》翻译成他所认为的人们可接受的中国式散文。
注释:
①这些译本包括:拉萨(Johannes Lassar)和马希曼(Joshua Marshman)的《圣经》(1822);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米怜(William Milne)的《神天圣书》(1823);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和郭实腊(Karl Gutzlaff)的《新遗诏圣书》和《旧遗诏圣书》(1838);“委办本”《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1854)以及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与克陛存(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的《新约全书》与《旧约全书》(1863)。上述所列年份,当为《旧约全书》翻译及出版的年份。教义方面的主要分歧来自于浸礼派,他们之所以选择不参加“委办本”《圣经》的翻译,原因在于他们无法接受所提出的有关“施洗”这个词以及其他一些词的中文翻译;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依然选用拉萨和马希曼的中文《圣经》译本(Marshman是一个浸礼派),直到Hosiah Goddard和William Dean合作推出了一个新译本。
②这些术语主要使用于描述性的翻译学研究领域,相关内容可参见G.Toury,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5,Chapter 3。
③"The Bible in China," Chinese Researches,Shanghai:Mission Press,1897,p.100。伟烈亚力的原文最初发表在1868年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上。
④“马礼逊—米怜《圣经》中译本修订计划,附阐义注释,新旧约每部前并附长篇导读,另附边注。”在前伦敦传道会(LMS)档案、现世界传道会(CWM)档案中的中国人事“马礼逊”条下,保存有一份该修订计划草稿。参见1826年11月18日向伦敦传道会提出此建议的书信,收录于世界传道会档案,马六甲,来信。世界传道会档案现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所有。高大卫和修德的建议一直没有被批准。
⑤罗香林在其《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对此类赞誉多有列举,参见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香港)新亚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1963年版,第43-45页。
⑥如费启鸿(George Field Fitch)在《教务杂志》(1885年8月)中写道:“就《圣经》这一新的文理翻译本而言,委办本的特点在于其优美的中文,不过也正是因为要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自由式翻译,很多情况下,译文不过是对原文的释义而已。”惠志道(John Wherry)更为委婉地说:“一方面,对那些关注心灵的读者而言,钻石因为其镶座而黯然失色,而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为熟悉的韵律所蒙蔽、并不关注精神心灵的读者来说,则很容易错把基督当孔子。”参见J.Wherry,"Historical Summary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criptures,"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 7—20,1890,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Press,1890,p.52。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对此问题也这样总结的:“翻译基督教经典的难点在于,翻译者既要适应中国人的阅读品位,又不能超越其时代。”他接着说:“那些最近的译本中,至少有一种(就是‘委办本’)以其古典品味著称。”参见W.A.P.Martin,"Remarks on the Style of Chinese Prose," in Hanlin Papers,Shanghai:Kelly and Walsh,1894,p.261。
⑦有关《圣经》后期翻译之研究,参见I.Eber,The Jewish Bishop and the Chinese Bible,Leiden:Brill,1999;J.Zetsche,"The Work of Lifetimes:Why the Union Version Took Nearly Three Decades," in I.Eber,S.Wan & K.Waif(eds.),Bible in Modern China: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Sankt Augustin: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1999,pp.77-100。
⑧麦都思的翻译方法是与他所使用的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一致的。他是第一位将基督教内容用少儿“三字经”形式来改写的传教士。他也曾用《论语》的文体形式来阐释基督教道德真谛,可参见麦都思《论语新纂》(Analects:A New Compilation)。
⑨1835年4月1日麦都思致伦敦传道会的信函。见世界传道会档案,巴达维亚(现雅加达),来函。
⑩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有一复印件。
(11)1834年4月14日裨治文致美国海外传教会总会(下文简称ABCFM)的信函(“一种全新翻译”)。裨治文说麦都思给他来信的日期是1834年2月18日。美国海外传教会档案保存在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基本微缩文献库(Primary Source Microfilm)中大部分档案可查阅,此封信函见第256卷胶片。
(12)1834年4月10日麦都思致伦敦传道会的信函。见世界传道会档案,巴达维亚,来函。
(13)麦都思致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以下简称BFBS)的信函摘录附在他4月10日致伦敦传道会的信中。
(14)麦都思于1834年10月27日写给伦敦传道会的报告。见世界传道会档案,巴达维亚,来函。
(15)同上。
(16)1835年4月1日麦都思致伦敦传道会的信函。见世界传道会档案,巴达维亚,来函。
(17)1834年4月14日裨治文致美国海外传教会总会信函。见美国海外传教会总会档案16.3.8(第256卷胶片)。
(18)1834年4月26日裨治文致美国海外传教会总会信函,同上。
(19)1835年1月9日裨治文致美国海外传教会总会信函,同上。
(20)1835年3月26日裨治文致美国海外传教会总会信函,同上。
(21)1835年7月14日裨治文致美国海外传教会总会信函,同上。
(22)1835年1月9日裨治文致美国海外传教会总会信函,同上。
(23)1834年10月27日麦都思致伦敦传道会的报告。见世界传道会档案,巴达维亚,来函。
(24)1835年4月1日麦都思致伦敦传道会的信函,同上。
(25)麦都思致伦敦传道会的信。见世界传道会档案,巴达维亚,来函。
(26)1835年8月24日麦都思致伦敦传道会的信函,同上。
(27)麦都思致伦敦传道会的信函,同上。
(28)同上。
(29)关于郭实腊的态度,见麦都思、施敦力和米怜写的小册子《对文惠廉博士之“对‘委办本’〈新约全书〉中〈以弗所书〉第一章翻译的评论”之回应》,(上海)墨海书馆1852年版,第37页。“当他协助出版巴达维亚版《圣经》中译本时(如1836年麦都思和其他人一起翻译的《新约全书》),他唯一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怎么能弄懂某些特定语词。”后来,在修订《旧约全书》译本时,郭实腊又回归到了一种更为直译的方法。有关马礼逊的态度,见1837年7月25日他致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的信函,其中一份复印件存于世界传道会档案,华南,来函。
(30)1836年1月9日麦都思致伦敦传道会信函。见世界传道会档案,华南,来函。
(31)见1836年4月27日伊文斯、戴尔致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编辑秘书约瑟夫·乔伊特(Joseph Jowett)信函之复印件,此件收录在“拟议新译中文《圣经》相关文献”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档案中。伊文斯、戴尔4月25日致郭实腊的信函亦附其中。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档案由剑桥大学保存。
(32)见伊文斯致伦敦传道会的受洗申请。世界传道会档案,申请者文件,编目281。伟烈亚力曾在报告中夸张地说伊文斯是英国“极有成就的古典学、数学、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教授”,见A.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with Copious Indexes(1867),Taipei:Cheng-Wen Publishing Co.,1967,p.76。伊文斯声称曾自学过一点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
(33)《麦都思对伊文斯与戴尔来信之意见书》,1836年11月19日,此意见书附在“拟议新译中文《圣经》相关文献”中,见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档案。
(34)“就新版中译《圣经》致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的备忘录”,见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档案。
(35)见1836年12月19日伦敦传道会东方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预备会记录,收于世界传道会档案,“记录”。麦都思是此次会议的特邀嘉宾。
(36)关于决议,见1836年11月25日“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关于此前编辑分会会议论文等之决议”,收录在“拟议新译中文《圣经》相关文献”中,见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档案。
(37)1836年12月19日约瑟夫·乔伊特致麦都思的信。见世界传道会档案,1836年12月19日委员会会议记录。在1843年1月3日致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的信中,乔伊特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观点。委员会在麦都思的建议中发现,“如此影响广泛的非议曾经受到马礼逊博士——一位绝对受人信赖且兼具剑胆琴心双重品质者——的影响,在他自己看来,这种翻译风格轻率鲁莽,所以我们也担心委员会会因此倾向于新的翻译”。见M.T.Hills,"The Chinese Scriptures,1831-1860,”收录于American Bible Society Historical Essays,Vol.7,Section III-G(July 1964),p.25,该论文集未曾公开出版,收藏于美国《圣经》公会图书馆。
(38)麦都思的手稿是在世界传道会档案1836年“家书”中被发现的。标注日期为1836年12月18日的文印本,收录在“拟议新译中文《圣经》相关文献”中,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档案。麦都思为米怜所写的讣告描述了他的同事对于拒绝其建议的反应,见The Evangelical Magazine and Missionary Chronicle,September 1857,p.526。
(39)见1837年7月25日马儒翰致伦敦传道会信函。收入世界传道会档案,华南,来函。亦见于1836年10月10日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致函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档案,信中明言支持麦都思的翻译工作。李太郭声称旧版翻译“过多西化习语”,而且“是从英文译本翻译而来”。郭实腊曾邀请他(李太郭)帮助翻译《旧约全书》。“我支持希伯来语的《圣经》,郭实腊为中文版《圣经》辩护。”此摘录收藏在世界传道会档案,华南,来函中。
(40)参见“就新版中译《圣经》致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的备忘录”,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档案。
(41)修德论文标题为《对于马礼逊博士的文学工作之评议》,参见S.Kidd,"Critical Notices of Dr.Morrison's Literary Labours," in E.Morrison(ed.),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Vol.2,London:Longmans,1839,pp.71-72。
(42)《中国丛报》第12卷第10期(1843年10月),第551页。
(43)1847年7月5日,就在“委办本”《圣经》翻译刚开始之后几天,裨治文即建议采用“神”。代表们不能就此达成一致,翻译工作就搁置下来,笔战却在继续。随后,从1847年7月到11月,先后有六篇论文在小范围内进行辩论,直到11月22日开会时,依然未能达成一致。代表们一直休会到1848年1月,他们准备了一份公开声明,接着继续翻译。那些论文出版之后,很多在华新教传教士也卷入了争论之中。参见麦都思、施敦力与小米怜的《对“中文〈圣经〉上海修订本相关论文”的评论之批评》,这是一份小册子,标注日记为1852年6月16日,收录于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档案。
(44)“文理”是19世纪外国人对中国文言文的一般称呼。
(45)常常还是这些传教士,他们坚持使用直译,其结果尽管语言简单,但译文读起来并不通畅。
(46)参见1838年11月17日致伦敦传道会信函。收录于世界传道会档案,巴达维亚,来函。
(47)会议记录保存在美国海外传教会总会档案中,裨治文和伊丽莎(Eliza Jane),“文论与通信”,第2档案盒,案卷10。
(48)见文惠廉《对“委办本”〈新约全书〉中〈以弗所书〉翻译的评论之辩护》第10页,这是一份1852年在广东印刷的小册子,收录于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档案。
(49)《对“中文〈圣经〉上海修订本相关论文”的评论之批评》。见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档案。
(50)1851年4月7日广东地方委员会会议记录。见美国海外传教会总会档案,裨治文“文论与通信”,第2档案盒,案卷13。委员会支持裨治文有关《新约全书》的翻译观点,并要求新版翻译“简洁明了,更忠实于原文”。
(51)1851年3月31日三人致伦敦传道会信函。见世界传道会档案,华中,来函。
(52)1850年9月13日小米怜致伦敦传道会信函,同上。
(53)1850年7月22日伦敦传道会秘书蒂德曼(Arthur Tidman)致小米怜信函。见世界传道会档案,发函。
(54)1851年2月20日三人致伦敦传道会信函。见世界传道会档案,华中,来函。
(55)1851年2月20日三人致伦敦传道会信函。见世界传道会档案,华中,来函。
(56)1851年11月11日三人致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乔治·布朗(George Brown)信函。复印件收入世界传道会档案,华中,来函。
(57)《对“中文〈圣经〉上海修订本相关论文”的评论之批评》。见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档案。
(58)1852年7月17日麦都思致伦敦传道会信函。见世界传道会档案,华中,来函。
(59)有关其生平,参见J.Stratford,Great and Good Men of Gloucestershire,Cirencester:C.H.Savory,1867。
(60)1818年5月10日米怜致伦敦传道会信函。见世界传道会档案,马六甲,来函。
(61)1820年9月21日麦都思致伦敦传道会信函。见世界传道会档案,槟榔屿,来函。
(62)1821年1月2日米怜致伦敦传道会信函。见世界传道会档案,马六甲,来函。
(63)第20卷第4期(1851年4月),第216-224页。
(64)《中国丛报》第20卷第7期(1851年7月),第485-488页。杂志编辑(威廉斯)仅就回应中的主要指责予以概述,并用自己的评语对这些指责表示了认同。最初16页打印信件(“致《中国丛国》编辑的一封信”)收录于世界传道会档案,华中,来函。
(65)“中文《圣经》上海修订本相关论文”。见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档案。
(66)《对“中文〈圣经〉上海修订本相关论文”的评论之批评》。见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档案。
(67)《对“委办本”〈新约全书〉中〈以弗所书〉翻译的评论之辩护》,广东,1852年。见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档案。
(68)代表委员会《回应文惠廉博士“对‘委办本’〈新约全书〉中〈以弗所书〉翻译的评论之辩护”》,(上海)墨海书馆1852年版,另有10页前言,标注日期为1852年11月15日。此信与理雅各致伦敦传道会秘书的一封公开信装订在一起,是为“委办本”《新约全书》的翻译风格和原则进行辩护的。
(69)《对汉译〈圣经·创世记〉和〈圣经·出埃及记〉修订评论的回应》,广东,1852年。
(70)引自E.J.G.Bridgman,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New York:Randolph,1864,p.186。尽管裨治文一直倾向于适当直译,但他的观点最终却变得相当偏激。
(71)美国海外传教会总会档案,裨治文《文论与通信》,第2档案盒,案卷11。我认为这封没有署名、日期标注1851年5月22日的信,实际上是克陛存写的。
(72)《对“中文〈圣经〉上海修订本相关论文”的评论之批评》。见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档案。
(73)1852年5月10日,三人致伦敦传道会信函。见世界传道会档案,华中,来函。麦都思略微错说了重复部分。
(74)《对汉译〈圣经·创世记〉和〈圣经·出埃及记〉修订评论的回应》,广东,1852年,第13页。
(75)1851年3月31日三人致伦敦传道会信函。见世界传道会档案,华中,来函。
(76)《对文惠廉博士辩护之回应》,第21页。
(77)1856年出版的官话本新约《圣经》得到了来自南京的助手们的帮助,他一定给了这些助手们翻译自主权。此译本因为译本中的南京方言俚语而遭到抨击。参见J.Wherry,"Historical Summary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criptures,"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 7—20,1890,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Press,1890,p.55。
(78)在麦都思的翻译中,刘的名字是Lew Tse-chuen。
(79)麦都思1846年4月10日致伦敦传道会信函。见世界传道会档案,华中,来函。在麦都思的翻译中,江的名字是Tseang Yung-che。
(80)麦都思也一般性地赞扬耶稣会士们的作品“文风清新典雅”。请注意麦都思曾摘译过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的《专论缫丝与养桑》。
(81)麦都思1845年6月30日致伦敦传道会信函。见世界传道会档案,华中,来函。在《中国内地一瞥——1845年在中国丝茶产区旅行见闻》(墨海书馆1845年版)中,麦都思对此次旅行有完整描述。
(82)大英图书馆藏有艾约瑟1858年编的版本。
(83)王韬1848年墨海书馆之行常被引用,其实他是来探访父亲的工作之地。
(84)1854年10月1日麦都思致伦敦传道会的报告。见世界传道会档案,华中,来函。
(85)1849年6月30日麦都思致伦敦传道会信函。见世界传道会档案,华中,来函。麦都思所指的翻译乃其在术语问题上的引用之源,在这方面他显然得到过王昌桂的帮助。
(86)标题为《养心神诗》,时间是从19世纪20年代直到19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有一份复印件。
(87)大英图书馆有一份1855年的香港版本。其中收录有81首赞美诗,另有若干关于三位一体的诗篇。
(88)标题为《清明扫墓之论》,初版于1826年。
(89)大英图书馆藏有1870年版本。
(90)除了为伦敦传道会所作的其他大量翻译外,王韬继续修订基督教教义。艾约瑟和杨格非请王韬为他们润色1860年在苏州递交给太平军头领李秀成的神学论述。如艾约瑟所言,“王韬让神学论述的文风合乎叛军头领期待,读起来抑扬顿挫”。参见P.A.Cohen,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54。引自 The Missionary Magazine and Chronicle,No.24(1860),pp.271-278。有关王韬在非宗教著述翻译方面的贡献,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277页。
(91)王韬也不让传教士们知晓他的私生活,以免批评其放纵。1853年夏,当病体康复时,王韬写了一本怀念上海风月场所女子的书,即《海陬冶游录》。
(92)在王韬1853年第六个月的日记中,他写到自己正遭受穷困潦倒之困扰。而在第七个月的日记中,他提到了应龙田的到来。参见王韬日记《蘅花馆杂录》手稿中的《瀛壖日志》,第28-29页,现存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一复件。
(93)见王韬1859年1月21日、2月27日分别写给朱雪泉和周弢甫的信,《王韬日记》第64-67页和第81-84页。第二封信表明,王韬对外国文化的态度已从一种文化交流策略退守到一种文化孤立主义。
(94)见裨治文与克陛存的《圣经》译本。有趣的是比较麦都思1836年《新约全书》中译本里这句话的翻译方式:“当时,我看新天,新地,盖初有之天地过去,后未有海矣。”此译文与裨治文和克陛存的译文一样直译口语化,语言简单,甚至还带有一些方言。
(95)文惠廉指责《圣经·创世纪》开篇翻译中存在“不可原谅的自由翻译”,见其《对“委办本”〈新约全书〉中〈以弗所书〉翻译的评论之辩护》第18页,1852年,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档案。裨治文批评“委办本”《新约全书》“忠实原文不够,缺乏原文简单朴实的风格”,不过宣称《旧约全书》“在这些方面更难让人满意”。参见他1851年10月1日致函美国海外传教会总会的信,信中提到了上述争议。需要注意的是,王昌桂确实作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变,即便这些改变并非像其儿子的改变那样具有实质性意义。倘若将“委办本”《圣经·马可福音》中的第一章到第四章,与著名翻译家严复1908年翻译的《圣经》同样章节进行比较,将受益匪浅。严复的译本在大英及海外《圣经》公会存有一本,相比较之下此翻译比“委办本”更为贴近原作。施福来(Thor Strandenaes)从语言学的角度对马礼逊翻译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12节、《圣经·歌罗西书》(Colossians)的第一章,与“委办本”同样章节作了详细比较,也参考了白日升(Jean Basset)的手稿本(此手稿本马礼逊常常用到)。参见T..Strandenaes,Principle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as Expressed in Five Selected Vers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Exemplified by Matthew 5:1-12 and Colossians 1,Uppsala: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1987,pp.22-75,161-166。
标签:圣经论文; 马礼逊论文; 传教士论文; 文学论文; 麦都思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新约全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