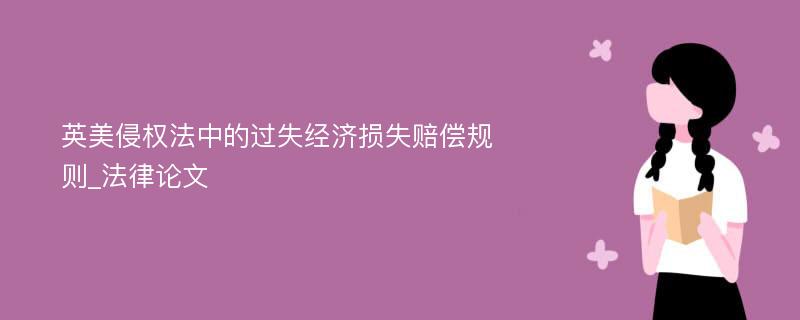
论英美侵权法中过失引起的纯经济上损失的赔偿规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失论文,英美论文,损失论文,规则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纯经济上损失(pure economic loss)是英美法上的一个常见概念,它是指并非因原告的人身或(有体)财产受到损害而引起的经济损失。① 在性质上它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损失或者金钱损失,也就是说,它与原告所遭受的人身或者财产(有形)损害没有关系。② 纯经济上损失有两个重要特征:一则纯经济上损失是一种经济利益的损失,二则纯经济上损失并非是人身或有体财产受到损害而间接引起的损失。
由于纯经济上损失的独特性质,经过上百年的发展,英美法对纯经济上损失的赔偿已形成一套独特的处理机制。在英美侵权法下,纯经济上损失通常可以通过下列三种途径获得救济:(1)故意引起的纯经济上损失通常可以获得赔偿;(2)可以以违反法定义务(breach of a statutory duty)为由要求赔偿纯经济上损失;(3)依“过失”侵权行为请求纯经济上损失的赔偿。如果说在故意侵权行为和违反法定义务两种类型的侵权行为中纯经济上损失一般可以获得赔偿的话,对过失引起的纯经济上损失则没有这样明确的结论,它是英美法上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在英美侵权法的历史上,一般认为过失引起的纯经济上损失不能获得赔偿,③ 然而这一排他性的一般规则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例外。
一、对英国法的历史考察④
(一)1875年至1931年:排除性规则的建立
在这一时期,过失引起的纯经济上损失通常难以获得赔偿。在1875年的Cattle v.Stockton(1875)L.R.10 Q.B.453、1877年的Simpson v.Thomson(1877)3 App.Cas.279和1911年的Societe Anoyme de Remorquage a Helice v.Bennetts[1911]1 K.B.243(Commecial Court)这三则判例中,原告都是因为第三人的财产受损而遭受纯经济上损失,但其诉讼请求都被拒绝。在其他案型中也同样有着这样一个排除性规则,如原告因第三人的伤亡而遭受的纯经济上损失,除非可依死亡事件立法或普通法下的因他人原因失去仆人服侍或失去伴侣服侍之诉获得赔偿外一般不能得到救济;在期租或程租的情况下,承租人因船舶受损而遭受的纯经济上损失也不能获得赔偿,但光船承租人却可以,因为他对船舶享有占有的利益。
(二)1932年到1964年:排除性规则的弱化
1932年发生的Donoghue v.Stevenson一案正式确立了“过失”侵权行为类型,在该案中,Lord Atkin提出了著名的“邻人原则”:“法律的作用在于限制请求权人的范围及其救济的程度,当‘你必须爱你的邻人’的道德规范成为法律规定时,你就不可伤害你的邻人。当法律提出‘谁是我的邻人’的问题时,其答案必须严格认定,当你可合理预见你的作为或不作为将影响邻人时,应采取合理的注意措施,以避免结果的发生。然而在法律上谁是我的邻人?答案是:当我从事该系争作为或不作为时,可合理地预见将因我的行为,密切、直接而受影响之人,均是我的邻人。”⑤ 即以“可预见性”作为检验注意义务的标准。
在这一时期,纯经济上损失的案型逐渐增多并开始冲破排除性规则的束缚。1947年的Morrison Steamship Co.Ltd.v.Greystoke Castle(Cargo Owners)[1947]A.C.265,[1946]All E.R.696是一则共同海损分摊案件,在该案中,一名法官就倾向于否认排除性规则的存在。
这一时期最经典的判例便是Hedley,Byrne & Co.Ltd.v.Heller & Partners Ltd.[1964]A.C.465,[1963]All.E.R.575了,它确立了过失不实陈述的案型。在该案中,Hedley Byrne被Easipower Ltd.雇来进行一次广告宣传活动,它通过自己的开户行向Easipower Ltd.的开户行写信询问了其资信状况,该行回信说,Easipower Ltd.的信用良好,并附带声明银行对此不负责任,后来这封信的内容被证明存在不实,Hedley Byrne因Easipower Ltd.破产而向法院诉请Easipower Ltd.的开户行赔偿他遭受的损失。上议院认为,因为被告银行于陈述时附带声明了免责条款,因此不对原告负损害赔偿责任,但它同时认为,若无该项免责声明,银行就应承担责任,并不因原告所受之损害为纯经济上损失而有所不同,此外,上议院还认为除发生于银行与客户之间这种场合外,纯经济上损失的责任在其它场合也可能成立。⑥ 同时,本案也改变了Donoghue一案所确立的认定“注意义务”的标准,而确立了新的标准——“特殊关系”原则(a special relationship),Lord Delvin认为“当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种合同关系、信托关系或相当于合同关系时,关于言辞的注意义务就产生了。”⑦ 这种“特殊关系”原则的成立要件包括自愿的义务承担、特殊关系、专门技能和合理信赖。
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排除性规则受到了强烈的挑战,许多纯经济上损失的案例都获得了成功,但这项排除性规则并非已被Hedley Byrne一案推翻,Hedley Byrne一案只是该排除性规则的一个例外,它并未确立一项新的原则,纯经济上损失的赔偿问题仍是摆在法官面前的一项棘手的任务。
(三)1965年后:纯经济上损失案型的多样化和处理规则的不确定性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更新的纯经济上损失的案型,法官在该问题的处理上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在每种类型中,都会出现不同的意见,也会出现不同的政策考察因素。
在1966年的Weller & Co.v.Foot And Mouth Disease Research Institute[1966]1 Q.B.569,[1965]3 All E.R.560一案中,Widgery法官认为原告之损害本身“可预见”并不足以形成注意义务,只有被告的行为有直接侵害原告人身或财产的可预见的危险性时,被告始负有避免纯经济上损失发生的义务,一旦被告的注意义务成立,原告即使未受有有形损害,亦可请求赔偿经济损失,但是就纯经济上损失可预见本身并不能形成注意义务。⑧ 本案实际上又重新确认了排除性规则,并将“对直接有形损害的预见性”作为“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在以后的一系列案件中,纯经济上损失的赔偿问题都遭到否认。
1.电缆案型
1966年的Elliot v.Sir Robert McAlpine & Sons Ltd.1968年的Electrochrone Ltd.v.Welsh Plastics Ltd.及1971年的S.C.M.(U.K.)Ltd.v.W.J.Whitt all & Son Ltd.等都是“电缆案型”,在这几个判例中,法官都确认纯经济上损失不能获得赔偿,但所采用的理由却不尽相同。在British案中,Lord Justice Lawton采用的是“直接损害”(direct injury)的概念,在后面两个案件中Lord Denning 承认这只是个公共政策问题,并以“远隔性”(remoteness)作为判断标准。
2.公共机构责任案型和产品责任案型
(1)责任的确立和发展
1970年的Ministry of Housing v.Sharp[1970]2 Q.B.223,[1970]1All E.R.1009一案则是个“公共机构责任”案型,在该案中,被告,一个土地抵押机构的办事员,向一块土地的买主提供了一份官方证明但因过失未披露土地上存在着有利于原告的土地抵押,买主对土地抵押并不负责,因而原告诉请该办事员赔偿损失。在该案中,法院根据Hedley Byrne一案的原则支持了原告的请求,但未提及纯经济上损失问题。
在接下的几年里,“公共机构责任”案型和“产品责任”“案型又出现了快速的发展。1977年的Anns v.Merton London Borough Council[1978]A.C.728一案成为此时期的一个经典判例。在该案中,法官认为,地基所存在的缺陷导致的房屋沉降和墙体裂缝构成“物质的有形的损失”,(作为公务人员的被告)应赔偿的范围是将该房屋恢复到不再危及居住者健康安全状况所需的费用和因搬家而引起的花费,但后者只有“在建筑物对居住者的健康安全构成现存的或迫近的危险时(present or imminent danger)”才能提起诉讼。⑨ 在该案中Lord Wilberforce提出的检查注意义务的两阶段法(a two-stage test)。
(2)责任的倒退和否认
1986年的The Mineral Transporter[1986]A.C.1和Leigh & Sillivan Ltd.v.The Aliakmon Shipping Co.Ltd.[1985]Q.B.350,[1986]A.C.785两案对Junior Books案来说也不啻于两次重重的打击,两起案件都涉及海事问题,都因被告的过失行为而使原告在与第三方订立的合同中遭受损失,但原告的诉讼请求都被驳回了,从而使1947年的Greystoke案的适用受到了限制,法院在对待纯经济上损失案型的态度上又退回到了1875年的Cattle一案所持的限制性的立场上了。在The Aliakmon案中,Lord Brandon并评论说将Anns一案确立的原则用来重新讨论法院已解决了注意义务问题的情形是个错误。⑩
在这以后,1989年的D & F Estates v.Church Commissioners[1989]A.C.177一案,也对Anns案和Junior Books案提出了挑战,该案亦是一“产品责任”案型。该案由于被告是建筑商,并未涉及公共机构的责任问题,对Anns案尚未构成直接冲击,但法院判决建筑的瑕疵是种纯经济上损失,而不是物质的有形的损害,则是对Anns案判决的直接否定,(11) 同时,Lord Bridge认为Junior Books一案建立在当事人双方的特殊关系的基础之上,它并没有为侵权法制定一条一般的适用原则,也即暗示它只是Hedley Byrne一案所确立的“合理信赖”原则的一个应用而已。在本案中,值得注意的是Lord Bridge提出的“复杂结构”(complex structure)理论,也即建筑物的瑕疵若引起建筑物其它不同部分的可见损害,如建筑物地基存在缺陷而引起墙体裂痕时,地基的缺陷属纯经济上损失,但墙体裂缝却是有形财产损害,可以获得赔偿。(12)
虽然D & F Estates一案并未直接否定Anns案的判决,但此后上议院于1991年对Murphy v.Brentwood B.C.[1991]1A.C.398一案所作的判决则正式推翻了Anns案的结果,并对“复杂结构”理论进行了修正。上议院遵循D & F Estates一案的判决认为原告因墙体裂缝而低价转卖房屋所受损失为纯经济上损失。因它是由房屋本身的缺陷引起的,而不是由原告的其他财产受损害而引起的,故而根据排除性规则不能获得赔偿。上议院支持了“复杂结构”理论,但又作了修正,即若一件财产可分为几个独立的不同部分时,由一部分的缺陷引起的其他部分的损害则可以根据Donoghue一案确立的“邻人”原则(可预见原则)获得赔偿,但上议院坚持认为在本案中不适用该理论,因房屋墙体的裂缝不能认为是和有缺陷的地基不同的独立损害,这实际上修正了D & F Estates案的判决。(13) 此外,上议院在该案中表现出的更保守的一面,则是它否认产品瑕疵的修理费用可以获得赔偿。Murphy案之所以出现倒退并非是基于对“水闸”理论的考虑,因为在瑕疵产品责任的背景下,并不存在不确定的损失,其范围限于瑕疵产品本身的价值,也不存在不确定的原告,其范围仅限于产品当时的所有人。其背后的政策考虑因素是担心对“合同相对性”原理的颠覆并因而破坏当事人在交易时建立的预期,因为若允许瑕疵产品的买主仅因产品的瑕疵(非缺陷)而对制造商提起诉讼的话,将使制造商承担无限的不断流转的瑕疵担保责任,不再受“合同相对性”原理的约束了。(14)
(三)不实陈述案型
在Hedley Byrne一案后,过失不实陈述案型获得长足发展,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判例。Q中1980年的Ross v.Caunters[1980]Ch.297案和前述的Ministry of Housing v.Sharp案、Junior Books案一起构成过失引起的纯经济上损失案型发展的高峰,这三个判例都未依赖Hedley Byrne案所建立的较为狭隘的原则,而是直接建立在Donoghue一案所确立的较宽泛的原则的基础上。在这几起判例中,应当注意的是Caparo一案,它修正了Anns案对注意义务提出的“两阶段检验法”,而充实了“三阶段检验法”。所谓“三阶段检验法”,即指在检验注意义务时要注意考查以下三个要素:(1)被告能否合理地预见到原告会遭受和已发生的损失同样的损失,即所谓的“预见可能性”要素;(2)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足够的密切关系(sufficient proximity);(3)让被告承担注意义务是否公平、合理(just and reasonable)。(15) 同时,Caparo一案还标志着以一条一般性原则来决定注意义务是否存在的尝试的终结,上议院在该案中表明了对传统的类型化方法的偏爱,即通过对已有的判例的类型化来解决注意义务的认定问题。(16)
(四)小结
通过以上的介绍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英国法在过失引起的纯经济上损失的赔偿规则上经历了一个波折反复的过程,在1931年前英国法一直坚持的是一条排除性规则,1932年的Donoghue案后出现对该规则的大突破,确立众多可诉请赔偿的新案型,特别是以1964年的Hedley Byrne案为标志确立不实陈述案型,在此后英国法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不确定的发展时期,排除性规则又被重新确认,已出现的案型纷纷被否认,特别是1973年的Spartan Steel案和1991年的Murphy案否认了“电缆”案型和“产品责任”案型、“公共机构责任”案型中原告对其所遭受的纯经济上损失的赔偿请求,使得现在的英国法院只承认过失不实陈述案型这样一个排除性规则的主要例外,虽然此间曾以Anns案、Ross案、Sharp案和Junior Books案为代表掀起了一阵不小的高潮。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所贯穿的主线便是对“注意义务”所采用的不同判断原则了,以Donoghue一案的“可预见性”标准到Hedley Byrne案的“特殊关系”标准,再到Anns案的“两阶段检验法”直到Caparo一案确认的“三阶段检验法”,不同的判断标准宽严尺度不同,使得纯经济上损失案型的发展呈现出波折反复的状态。但现在英国上议院并不打算赋予“三阶段检验法”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或精确的定义,而只将其视作对已有判例中“注意义务”存在情况的描述手段,在具体判断个案中的“注意义务”时,上议院所采用的是类型化的方法,即以既有判例为基础将之类型化作为决定现决案件中“注意义务”是否存在的指引。(17) 可以说,英国法现在对纯经济上损失的赔偿问题采取了一种消极的限制态度,它为在已有判例之外发展的新的案型留下了很小的余地,使得纯经济上损失案型在英国处于停滞发展的状态。
二、对美国法的历史考察
美国法和英国法一样也存在着一条对过失引起的纯经济上损失不予赔偿的排除性规则,但同样受到了各种挑战。
美国法中关于纯经济上损失的早期判例中比较突出的是1927年的Robins Dry Dock & Repair Co.v.Flint 275 U.S.303(1927)案。在该案中,Holmes法官认为,“对被害人之财产或人身之侵害行为,并不因此便使加害人对其他与被害人有契约关系之人负损害赔偿责任。法律之保护并未扩张到如此地步。”(18) 该判例虽未区分有形损害和纯经济上损失,亦未建立一项明确的排除性规则,但以后的法院在援用时均作如此的解释。(19)
但20世纪20年代后,纽约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确立了过失不实陈述的案型,突破了排除性规则的限制。这些判例如1922年的Glanzer v.Shepard 233 N.Y.331,135 N.E.275(1927)、1924年的Natl Iron & Steel Co.v.Hunt 143 N.E.833(1924)和1927年的Internet Products Co.v.Erie Rd.Co.244N.Y.331,155N.E.662(1927)。在1927年的判例中,法院认为,“过失不实陈述责任只有陈述人负有注意义务时始成立,而注意义务之成立,牵涉到若干因素之考量。陈述人必须知道咨询人之寻求系争资讯,是为了某种重要目的,且接受该资讯之人有意信赖之,如果该资讯发生错误,信赖人将会受到身体或财产上的损害。最后,当事人间无论是具有契约或其他类似的关系,都必须是在道德或良知上,足以使一方当事人有权利信赖他方之陈述,同时为陈述一方负有注意义务。”(20)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判例是1931年Cardozo法官所作的Ultramares Corp.v.Touche 255 N.Y.170,174N.E.441(1931)案。但该案后来受到质疑,1958年的Biakanja v.Irving 49 Cal.2d 647,320P.2d 16(1958)是一“不实陈述(遗嘱)”案型,在该案中,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请求,并对Ultramares一案提出质疑,重新检讨了以“契约相对性”原则认定“注意义务”之妥当性,并以“利益衡量”取代“契约相对性”原则,推动了纯经济上损失案型的发展。在该案中,法官认为,“在具体个案中,决定被告是否对无契约关系之第三人负有注意义务,须从政策面加以考虑,并牵涉到若干因素衡量之问题。例如系争交易行为试图影响原告之程度,对原告造成损害之可预见性,原告受损害之盖然率,被告行为与原告所受损害间之密切关系,对被告行为之道德非难,以及预防将来损害发生之政策考虑。”(21) 1968年的Rusch Factors Inc.v.Levin 284 F.Supp.85(1968)一案更是直接针对Ultramares一案提出针锋相对的挑战。法院认为,“会计师过失为错误之财务陈述时,应对所有事实上预见信赖该陈述且有限的特定多数人负过失责任。”(22) 该案受到英国法上的Hedley Byrne一案的影响,突破了“契约相对性”原理的约束。
除过失不实陈述案型外,加州最高法院于1979年也突破“契约相对性”原则,发展出新的纯经济上损失案型,即J Aire Corp.v.Gregory 24 Cal.3d 799,589 P.2d 60,157 Cal.Reptr.407(1979)一案,在该案中法院遵循Biakanja 一案提出的“利益衡量”原则,认为根据被告行为与原告损失间的关联性,原告之损害是可预见的。因此被告负有注意义务,法院放弃了传统上对有体损害和纯经济上损失之区分,而认为损失之种类与损害赔偿问题并无关连,进而称传统上对“注意义务”之限制,已被“预见可能性”所取代。(23) 1985年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在People Express Airlines,Inc.v.Consolidated Rail Corp.476 U.S.858(1986)一案中也允许了新的过失引起的纯经济上损失类型也可以得到赔偿,该案同时也强调应以“预见可能性”作为对“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
此外,美国法中还存在其他纯经济上损失的案型,如“产品责任”案型、“油污”案型及“雇员人身伤害”案型,但就第一个和第三个案型来说,大多法院都表现出排斥的态度,一般不允许纯经济上损失的赔偿。(24)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86年作出的Easter River Streamship Corp.v.Transamerica Delvaval Inc.476 U.S.858(1986)这一判例。
整体上,美国法虽然也存在一条过失引起的纯经济上损失不能获得赔偿这样一条排除性规则,但它在该原则的突破上并不像英国法那样趋于保守,并且存在很多波折反复,而是采取了颇为开明的态度,并且倾向于采用Donoghue一案所确立的“预见可能性”理论来判断过失引起的纯经济上损失类型中的“注意义务”能否成立,这显然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标准,可以由此衍生出许多过失引起的纯经济上损失案型,这表现了美国法院一向的开明态度。在立法上,纯经济上损失案型也有成文化的趋势,特别是在第二次侵权行为法重述和油污责任法案等法律文件中有突出体现,这也是美国法和英国法相比颇为突出的一个特点。
三、英美法处理过失引起的纯经济上损失时的政策考量因素
英美法院之所以区分有体损害和纯经济上损失予以差别待遇,并在过失引起的纯经济上损失的赔偿问题上举棋不定,出现前后波折反复的现象,乃是在这些判决背后存在着深厚的政策考量因素。正如Lord Denning法官在前述Spartan Steel案中所作出的判决理由中明确指出的一样,被害人能否请求经济上损失的损害赔偿,根本言之,是政策的问题,无论是以“注意义务”的有无或损害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来决定被告的责任,均属基于政策的考量,旨在适当限制被告的责任。在本案判决中,他提出五点政策考量因素。(25) 然而这样明确地表述出判决背后的政策考量因素的情况并不多见,法官常常是以抽象的概念和原则作为理由构成,而很少提及这些政策考量因素,实则法官常常是先通过这些政策考量因素得出结论,然后再为这些结论去寻找合理的概念和原则来进行解释。为了真正理解英美法中的这些判例,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些判例背后隐藏的政策考量因素。
(一)“水闸”理论(flood-gate)
该理论的经典表述是Cardozo法官于1931年的Ultramares 一案中所作出的判决理由:“如果因为轻率、不假思索之失误,未能从表面假象中发现真实,就课以过失侵权行为责任,将会使会计师面临在不特定时间中,对不特定人员负不特定责任之危险。”(26) Lord Denning在Spartan Steel一案中也提到这一点:“若被害人对于此等意外事故,皆得请求赔偿经济上损失,则其请求权将漫无边际。真实者固属有之,但难免伪造、灌水、膨胀,不易查证。与其让主张损害赔偿者受此引诱,被告遭此劳累,不如认为非因人身或所有权受侵害而发生的纯经济上损失,不得请求赔偿,较为妥适。”(27) 这种“水闸”理论的考虑在前述不实陈述案型、电缆案型中表现尤为明显。然而这种理论却会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在现代社会,大规模的责任事故会经常发生,如美国三哩岛核电厂事件、印度波帕化工厂氯气外泄事件、日本水俣事件等,这些事件中受害人数众多,受损数额也很庞大,法院却未不驳回诉讼,为何对同样不能确定受害人数和损失数额的纯经济上损失案型却要予以种种限制?其二,对那些人数有限,损失也易确定的纯经济上损失案型,如商品自爆事件、建筑物自身存在缺陷案件,法院为何也表现出迟疑及至否定的态度?(28)
(二)“抑制”理论(over-kill)(29)
该理论与“水闸”理论有着密切关联,在损失不能确定,受害人数亦不能确定的情况下,若对加害人施加过重的责任,则他会过分谨慎地采取不必要的防范措施或放弃一些增进社会福利的活动以避免不确定的责任,如此则会浪费稀缺的社会资源,阻碍交易活动的顺利展开,削弱社会福利的改善。因此,为避免过分的“抑制”效应,责任必须有个明确界限,既要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补偿,又不能给加害人施加过重的负担,阻碍经济秩序的流转,这样,过失引起的纯经济上损失不能获得赔偿这样一条排除性规则从实用角度看有助于提高法律和商业上的确定性,但另一方面它也损害了法律的公平性。
(三)优越法益因素(30)
法律制定之目的即在于保护人类的各种法益,即对人类有特定价值的有形或无形的事物。但是基于道德上或经济上之考量,并非所有事物都具有相同的价值,如此便形成一套价值体系,使得某些法益优于另外一些法益。通常人们认为人身法益要优于财产法益,财产法益中的有形财产价值要优于一般的财产利益,因而人身损害和有形财产损害较之经济上损失更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有体损害是永久的,人身损害甚至无法以金钱完全弥补,而经济上损失只是丧失可得预期之利益,并不尽然构成社会损失。这在一个市场发育尚不完善,经济流转尚不充分的社会中固然正确,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个人的人身法益和有形财产尚是求生的必要条件,较之一般财产利益更值得法律保护。然而在市场充分发育,经济流转秩序完全展开的今天,仍以这种价值体系来判断法律保护的侧重点则未免有点不合时宜了,虽然人身法益仍然是个人生存的最重要条件,然而一般财产利益并不比人身法益、有形财产利益的价值重要性低,反而在有的情况下会超过后二者,如被宣告破产就比摔断一条腿更严重,对企业来说一般财产利益,如债权、知识产权、商誉权等的重要性较有形财产更为突出。
(四)对侵权责任和契约责任相互关系的考虑(31)
契约是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它旨在规范特定人之间的信赖和期待,旨在保护当事人通过契约可能获得的经济上利益。当事人可以约定具体的履行条款、免责或限责条款来合理分配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和风险,来分配经济上损失的承担,使双方能够在所得利益和所付代价间取得平衡。法律相信当事人理性的结果,并不主动去干预这种自愿的利益分配格局,因而契约责任对纯经济上损失的保护比较充分,并且以之为主要目的。而侵权法在于规范一般人之间的关系,但由于第三人范围之广,其所受损害亦会漫无边际,故侵权法主要保护他人的人身权和物权(有形财产权),而一般不涉及对一般财产利益的保护。在当事人之间存在契约或者可以通过契约获得救济时,法律便不会通过适用侵权法来救济受害人,以免使加害人所承担的责任因其无法预见损害和受害人的范围而不堪重负。若当事人没有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契约或没有通过责任保险来分散风险的话,法律就会让他自己承担可能发生的经济上损失,仅在当事人间因“约因”的限制而未形成合同关系或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合同关系”或当事人之间存在信托关系、信赖关系或对受害人不予救济则显然违反公平原则时,法院才会通过侵权法来救济当事人,弥补契约法上存在的缺陷,而且法院也不会使加害人承担比有合同关系存在情况下更重的责任。可以说,对纯经济上损失而言,法院更倾向于用契约机制来进行保护,仅在契约法不足以保护的情况下,才扩展侵权法来进行保护。这也是英美法中有过失引起的纯经济上损失不予赔偿这样一条排除性规则存在的原因所在,特别是在“产品责任”案型中,前述East River一案的判决理由充分体现这一点。
但应注意的是,若当事人双方都是商人,用契约机制来解决纯经济上损失固属妥当,但对一般消费者而言,在当代经济中已处弱势者地位,他们既无高超的谈判能力,也无足够的法律、经济知识来充分保护自己,仅用契约机制来对他们提供保护则显得并不适宜,此时如何协调契约法和侵权法的关系便不能不重新被考虑了。在英美法中,侵权法已经开始侧重对纯经济上损失的保护并逐渐侵蚀契约法的领地了,这使得合同法和侵权法的界限出现模糊,有学者称之为“contorts”。在1995年的Henderson v.Merrett Syndicates Ltd.[1995]2 A.C.145案中,英国上议院明确表明了自己对该问题的看法。它认为侵权法的地位更为基础,在当事人间没有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它可以补充合同法的不足,而且,尽管合同中可以修正和塑造若无合同关系时应适用的侵权责任的内容,但只要侵权责任并非与合同相抵触,它就可以在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也予以适用,仅在通过合同可以认为当事人的目的是要限制或排除侵权责任时才产生前述例外(侵权责任与合同相抵触的情形)。
(五)保险因素
在现代社会中,意外事件层出不穷,使得保险事业获得飞速发展,大部分意外事故均可通过保险机制获得救济,在纯经济上损失的情形,由加害人投保第三人责任险或由被害人投保意外事故险均可使之获得补偿,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所着重考虑的便不再是“因何人之过失而造成损害”,而是“何人处于负担损失之较佳地位”了。如Lord Denning在Spartan Steel一案中就认为,电力中断等意外事故所生的经济上损失应由受害人承担,一则此种损失在很多受害人之间进行分配不致形成过重负担,反之,若加之肇事者身上,则不堪重负;二则此种损失可能已由受害人,特别是受害企业,投保了意外事故险,从而可以得到合理的分散。新西兰上诉法院在1978年的Scott Group一案中则认为过失不实陈述引起的纯经济上损失由作出陈述的会计师承担更为合适,因为他能够很好地投保第三人责任险。
上面我们考察了英美法在处理过失引起的纯经济上损失的问题时所考虑的五个主要的政策考量因素,在英美法下这五个因素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经常被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量,法院在考察这些因素可能会有不同的侧重,因而所作出的判决也难免出现冲突反复。总体上,英美法院的法官既想对当事人所受的损害予以救济,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并阻遏违法行为的产生,又疑惧因此而可能产生的诉讼泛滥,阻碍经济流转,在这两端之间,法院始终在寻求合适的责任限制办法实现法律价值的平衡,其类型化的判例正是这种努力的最好表现。
四、英美侵权法中过失引起的纯经济上损失的赔偿规则对我国侵权法的启示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英美侵权法中,除了故意和违反法定义务引起的纯经济上损失一般可以获得赔偿外,对过失引起的纯经济上损失一直存在着一条不予赔偿的排除性规则,这主要是基于对“水闸”理论、“抑制”理论、优越法益因素、侵权责任和契约责任的相互关系及保险因素等方面的考虑,但基于法律公平正义的理念,这一排除性规则不断受到新的判例的冲击,英美法系的法官通过对“注意义务”判断标准的创制,发展出许多新的案例类型来救济受有纯经济上损失的当事人,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不实陈述案型,而这种类型化的技术也有助于控制采用一般性的概括原则所可能引起的判决的不确定性,但由于英国和美国在“注意义务”的判断上所采用的标准不一样,在发展纯经济上损失类型的态度上也明显不同。此外,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在侵权责任和契约责任相互关系的问题上,英美法的态度也逐渐由“禁止竞合”向“允许竞合”转变,侵权法开始侧重对纯经济上损失的保护并逐渐侵蚀契约法的领地了,这使得合同法和侵权法的界限出现模糊。
虽然纯经济上损失的赔偿问题尚未引起我国侵权法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但英美侵权法对这一饶有兴味的损失类型的处理方式确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也应当逐步在司法实践中将这一损失形态具体化、类型化,完善我国的民事责任体系。
注释:
① 阿拉斯泰尔·穆利斯和肯·奥利芬特:《侵权法》,麦克米伦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47页(Alastair Mullis and Ken Oliphant,Tort Law,Macmillan Press Ltd.,1993,p.47.)。
② D.F.比亚斯和B.S.马克西尼斯:《侵权法》,牛津大学出版社印刷所1999年第4版,第88页(D.F.Bias and B.S.Markesinis,Tort law,Clarendon Press,4th ed.,1999,p.88.)。
③ 罗伯特·所罗门和布鲁斯·费尔特尤申:“纯经济上损失的赔偿:排除性规则”,《加拿大侵权法研究》,刘易斯·克拉尔编,多伦多巴特沃斯出版社,同注①,穆利斯书,第22页。(Robert Solomn and Bruce Feldthusen,“Recovery for pure economic loss:the excluisionary rule”,Studies in Canadian Tort Law,edited by Lewis Klar,Butterworth,1977)。
④ 历史脉络主要参考了前引③,所罗门文,第169页下。
⑤ 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1999年自版,第57—58页。
⑥ 同注①,第54—55页;邱琦:《过失不当陈述之研究》,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1992年硕士论文,第115页下。
⑦ 《杰克逊和鲍威尔论职业过失》,斯威特和麦克思韦出版公司(Jackson and Powell on Professional Negligence,Sweet & Maxwell,4th ed.,1997,p.14.)。
⑧ 同注引⑥,邱琦文,第21页。
⑨ 同注⑥,穆利斯书,第48—49页;[英]斯蒂芬森·W·海维特:《产品责任法概述》,陈丽洁译,中国标准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
⑩ [英]戴维德·豪沃思:“英国法中的经济损失:寻求统一”,《纯经济上损失的民事责任》,克鲁沃国际法律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第30页;同注⑥,穆利斯书,第19页。(“David Howarth,Economic Loss in England:the Search for Coherence”,Civil Liability for Pure Economic Loss,edited by E.K.Banaka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Ltd.,1996,p.30.)。
(11) [英]马克·伦尼和肯·奥利芬特:《侵权法:课文和资料》,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15—317页。(Mark Lunney and Ken Oliphant,Tort Law:Text and Material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15—317.);前引⑥,穆利斯书,第49页。
(12) 同注(14),豪沃思文,第32页。
(13) 同注⑥,穆利斯书,第53—54页。
(14) 同注(18),第52页。
(15) 同注⑥,邱琦文,第63页。
(16) 卡伦·M·霍格:“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法中的过失与经济损失”,《国际法与比较法季刑》第43卷1994年,第117—118页[Karen M.Hogg,Negligent and Economic Loss in England,Australia,Canada and New Zealand),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vol.43(1994),p.117—118.]。
(17) 同注,第118页。
(18) 同注⑥,邱琦文,第22页。
(19) 同注⑥,第22页。
(20) 同注⑥,第128页。
(21) 同注⑥,第130—131页。
(22) 同注⑥,第131页。
(23) 同注⑥,第24页。
(24) [美]加里·施瓦茨:“美国侵权法中的经济损失原则:对最新经验的评价”,同注(14),第108—114页(Gary Schwartz,The Economic Loss Doctrine in American Tort Law:Assessing the Recent Experience)。
(25) 王泽鉴:“银行征信科员评估信用不实致银行因超额贷款受有损害的民事责任”,《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8),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页下。
(26) 同注⑥,邱琦文,第129页。
(27) 同注(32),王泽鉴文,第273页。
(28) 同注⑥,邱琦文,第26页。
(29) 同注⑥,穆利斯书,第45—47页。
(30) 同注②,比亚斯书,第88—89页;同注⑥,邱琦文,第26页。
(31) 同注②,比亚斯书,第90页;同注①,穆利斯书,第45页;R·P·巴尔金和J·L·R·戴维斯:《侵权法》,巴特沃斯出版社1991年,第422—423页,(R.P.Balkin and J.L.R.Davis,Law of TortsButterworth,1991,p.422—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