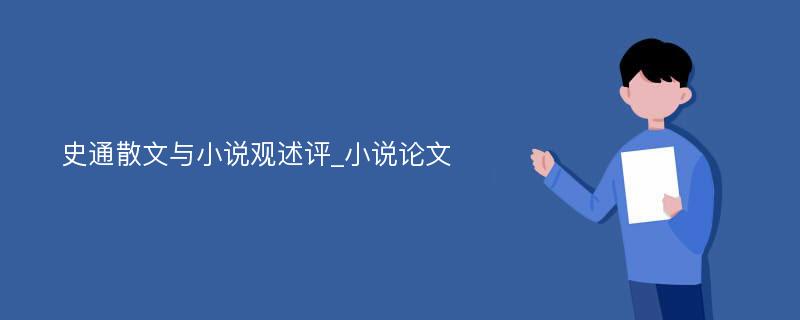
《史通》的散文观与小说观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散文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287(2000)04-0101-04
《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著。共20卷,49篇(内篇36,外篇13)。刘知几在《自叙》里说:“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以降,迄于《文心》而往,因以纳诸胸中,曾不芥者同东施效蒂芥矣。”在《史通》所含万殊千有的丰富内容中,除史学以外,最主要的是同史学关系极为密切的文学,其中关于散文和小说的论述内容丰富,对后世影响极大,本文拟就这两方面的内容作一些评述。
《史通》的散文观
刘知几的散文观的提出是针对当时绮靡,华而不实的文风的,大多受到修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启发,其观点涉及散文的内容、形式、风格及创作等方面,有以下三点:
1.力主实录。刘知几在史学上力主“实录直书”,痛诋靡丽的史体。因此在文学上也就对当时绮艳的文风深感不满。在史学和文学上都主张“斥饰崇质”。对靡丽繁缛的文风和竞奔趋附的文人特别厌恶,对藻艳的史体非常反感。他“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并且“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史通·自叙》)在《自叙》篇里,刘知几把自己和西汉的扬雄相比。由于受杨雄的影响,他在《史通》里一再称诗赋为雕虫小技。看重有裨于政教的实用之文,而轻视虚矫无实的诗赋(主要是指当时“丽以淫”的艳诗和骈文)。《载文》云:
“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又说:“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
这种注重实用的文学观点,同唐初修史者如魏征,李百药、姚思廉等史家所发表的意见毫无二致。
刘知几既然重视先秦时代助教化、资劝惩、淳厚质朴的文字,自然就要对以后的矫饰失实,积弊难返的骈丽文风痛加抨击。在论及史乘不应该载录浮华之文时,他在《载文》里说:“爰自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他认为丽辞对语言、音韵声律不仅有害于史乘的“实录”,而且在文学创作中也有害于作品的真实性。他对当时文士的厌恶、对淫靡文风的激愤,几乎近于偏执。
2.强调简约。刘知几从“实录直书”的基本观点出发,既排斥华丽辞藻,也不容忍繁言缛句,力主文风简约。他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叙事》)他认为六朝以来的史书,因追求华丽的辞藻或工整的句式,导致史书繁芜、叙事不能简要。他提出“简约”的主张,是针对当时文坛的积弊的。但是他所崇尚的“简约”,并非疏漏、阙略,而是“简而且详,疏而不漏”(《书事》),即所谓“文约而事丰”(《叙事》)。
刘知几在《叙事》篇里还提出了一个比“简”更高的境界——“晦”。他说:“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夫能略小而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浦起龙对“用晦之道”作了这样的解释:“简者词约事非,晦者神余象表。词约者犹有词在,神余者唯以神行,几几无言可说矣。”所谓用晦,就是要求语言精炼、含蓄,意在言外,耐人寻味。尚晦用简的主张,虽然是从修史的角度提出的,但它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唐以后古文学长期讨论的繁、简关系问题即萌蘖于此。
3.关于模拟古人。刘知几就如何学习和模仿古人的问题,提出“貌同心异”和“貌异心同”两种不同的学习方法。他说:“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模拟之下也。”(《模拟》)所谓貌,就是形式,语句词藻;所谓心,就是内容,精神实质。他认为学习古人最好做到神似,而切不可只求形似。同这一观点相联系,他提倡用当时代的语言(包括口语)撰写史书,反对“皆依仿旧辞”(《言语》)。他认为单纯从语言方面模仿古人,结果只能是“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有损于史书记言的真实性。
刘知几的上述观点多是就修史提出的,对后世史学产生过重大影响,为后世史学家广为接受。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这些观点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刘知几针对当时文坛流弊大加挞伐,在扫除六朝淫靡余风的过程中曾起过摧陷廓清的作用。他崇高真实质朴。厌恶虚饰;排击追求对偶、拘忌声病的骈文,标举“五经”、“三史”为文章楷模,要求文章内容真实,形式质朴,切合世用,“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载文》)。他的这些主张同古文运动的斗争目标和根本宗旨是一致的。如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韩愈反对骈文,重视散文;“非一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惟陈言之务去”;“为文宜师古圣贤人”,但要“师其意而不师其词”等等,都和刘知几的观点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可以说刘知几是古文运动的先驱。
《史通》的小说观
刘知几《史通》中的《杂述》、《采撰》等篇在今天看来也是系统论述小说的重要文章,对文言小说的分类、小说的虚实关系等问题有较为精辟的论述。
1.文言小说的分类。刘知几在《杂述》中第一次将文言小说进行分类,他将文言小说分成十类: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刘知几从史学的角度出发,认识到史书和小说同属记事体。史书记载国家大事必有所阙,故有偏记小说崛起,因而其分类的特点,在于抓住记事这一特征,除正史以外,所有“记事”的作品,都归入小说,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小说的范畴。他依稀认识到小说与社会发展、社会生活的关系,把小说门类繁多的创作现状,归之于“爰及近古,斯道渐烦”,说明小说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体现了朴素的唯物史观。
应该指出的是,刘知几从史学的角度概括小说记事的特点,界定小说范畴,在小说创作未成一体之时,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因不懂得记事体有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而抹煞了小说的文学性。如他把郡史、家史、邑簿、地理书之类划入小说,使小说一门更为芜杂。另一方面,他认为小说乃“史氏流别”,是正史之补。因而分类与史籍紧密相连,以致不少门类多有交叉。“偏纪”旨在补正史之阙;难入正史的人物,则由“小录”别载,收录遗逸的归为“逸事”、清言高议,集诸“琐言”。此四类其实皆可说是从正史派生,互有交叉而属同一类。因为“偏纪”不离人事,“小录”则附冀正史,“逸事”、“琐言”,各有侧重而已。因此,忽视其中的文学性差别,从史学的角度辨别,则四类同为补阙,合为一类,方能与其他类并提。如果剔除“补史之遗”的观点,而代之以叙事文学的标准,那么,严格地说,十类中只有“琐言”、“杂记”和部分“逸事”作品,才属古小说的范围。刘知几的分类,体现了当时部分批评家对于“小说”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其范围远远大于今天的小说概念范畴。
2.小说与史传的关系。在小说与史传的关系问题上,刘知几认为小说乃正史之所遗,“补正史之遗阙”。他在《杂述》中说,“逸事”类小说的产生,是因“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小录”类小说的产生,缘于“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独举所知,编为短部”。刘知几论十类小说的基础理论观点,即“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把小说的起源归之于史,认为小说内容属正史所缺漏、遗逸、或不采的人事。前史所遗,后人所记,便有小说一家。由此出发,刘知几亦认为小说“推详往迹,影彻经史”,能与正史相参行,能起到与经史互补的作用。《杂述》云:
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纪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并行相参,其所由来尚矣。
刘知几认为小说补经史之遗缺,自成一家,与正史并行相参。在他看来,小说是相对于正史的不可缺少的文体。作为一个史学家,他虽以记事实、正风规、扬名教、有益于社会的标准要求小说,但却坚持小说不可偏废的观点。他在《杂述》中说:
盖语曰: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虽复千门万户,波委云集,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刘知几认为小说创作很杂,好坏难以一言蔽之,如与经史典籍相比,确实难以比肩。但小说好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能够广闻而博识,且能从中窥得六经、史传所没有的东西。尽管丛残琐碎的小说,良莠不齐,精芜并杂,“书有非圣,言多不经”,但主要还在于读者自己的选择。刘知几从史学角度论析小说不无局限,但他对小说所持的基本态度是可取的。竭力坚持小说不可偏废的主张,对当时和以后的小说批评影响很大。后来的小说批评家继承这一理论并加以发扬,用来抬高小说的价值,为小说争取文学地位。另一方面,通过附骥于史传来肯定小说,使得古代小说创作长期依附于史传,内容和形式长期挣脱不了史籍的桎梏,又影响了中国小说的成熟。
3.小说的虚与实的关系。刘知几是一个地地道道主张小说实录的理论家,对小说记载神鬼之事颇有非议。《采撰》评小说云: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夫以干、邓之所粪除,王、虞之所秕糠,持为逸史,用补前传,此何异魏朝之撰《皇览》,梁世之修《偏略》,务多为美,聚博为功,虽取悦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
这里,刘知几认为《世说新语》、《搜神记》之类的志人志怪小说,所记并非经国大事,只是怪力乱神之说,仅能取悦于“小人”,君子是不屑一顾的。
应该注意的是,刘知几不属于排斥小说的一类理论家,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承认小说“自成一家”,肯定小说“良有旨哉”,客观上推动了小说的发展,虽然坚持一“实录”标准要求小说、评判小说,容不得小说“全构虚辞”,但却并非完全排斥鬼神之说。他在《杂述》中说:
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可见,刘知几对于杂记小说记述神鬼魑魅之事,并不反对。这显然有悖于他一贯坚持的“实录”主张,但他似乎并不以为有矛盾。在他看来,谈神鬼怪异之事并不违背“实录”,小说的这些虚幻的描写,如果有益于“益寿延年”、“惩恶劝善”的宗旨和效应,则与实录的作品无异。如果小说“苟谈怪异,务述妖邪”,其间并无有益于社会的宗旨和效应,那才属于荒诞虚妄,真正违背了“实录”原则。由此可见,刘知几一方面坚持“实录”主张,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反对虚构。在他那里,小说的实录与虚构是矛盾统一的,统一的根本点就在于小说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效果。
4.关于小说的史鉴功能。刘知几是从“实录”和“小说乃正史之补遗”的主张出发来论证小说的社会功能的。认为小说能与正史参行,就在于它自身的功能与正史有相通之处。《杂述》中说:
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
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
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
家史者,事唯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
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其有足以新言而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
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雅阙骃所书,殚于四周,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矣。……
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徒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
于是考兹十品,征彼百家,则史之杂名,其流尽于此矣。
刘知几把小说分为十类,认为都属“史之杂名”,因此,尽管他对部分小说不符合正史规范表示不满,但他也看到部分小说合乎正史规范而产生的社会作用:“实广见闻”。正因为认识到小说的这一功能,所以他指出:
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至于此乎。
从本质上讲,刘知几仍然认为小说不可与周孔章句、迁固之纪传相提并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正统文学观,另一方面则是尚处于雏形阶段的小说确实难以与《史记》、《汉书》相媲美。但刘知几反复强调小说“自成一家”,具有与史籍相通的“实录”精神,能与正史相参行,有着“实广见闻”的社会作用,能使读者“博闻旧事,多识其物”。可以说是客观正确地评价小说的认识作用。但也仅止于此,他看到了小说的认识作用,而不知小说有审美教育作用,有愉悦功能。
刘知几从史学的角度论述散文和小说等文学体裁的有关问题,其立场观点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作为文学体裁,散文和小说有着不同于史书的特质,其文学性明显高于史书等记事性的文体。以史的标准衡诸散文和小说,必然抹煞其特质,显得偏颇。但结合当时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刘知几的观点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是不可抹煞的。
收稿日期:2000-0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