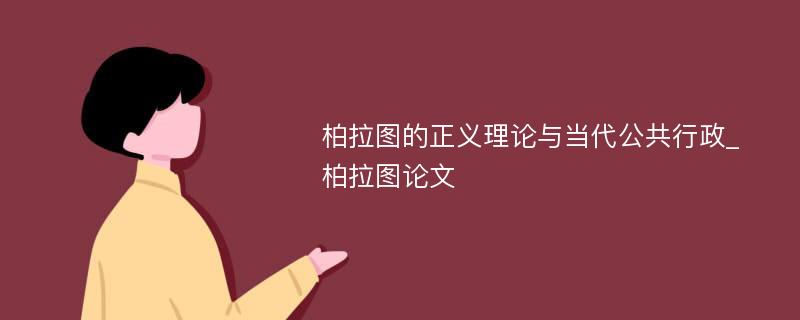
柏拉图的正义理论与当代公共行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柏拉图论文,正义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6)06—0022—04
柏拉图理想国家的主题是正义,在他看来,一个能使公民们道德上臻于完善的国家必须是一个正义的国家。柏拉图通过理性的正义将个人正义与国家正义结合起来,主张只有当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都得以实现了,一个幸福、和谐的城邦才能由理想变为现实。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一部正义论,其正义理论不仅奠定了西方正义学说的基础,而且也为我们实现社会治理中的公共行政正义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理论借鉴。
一、正义是超越利己性原则对整个国家和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的追求
《理想国》开篇便对“什么是正义”问题进行了探讨。柏拉图通过对几种关于正义的观点的一一反驳,阐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正义。在柏拉图看来,正义是一个超越了经验的、具体的、个别的、功用的概念,正义是体现城邦以及全体公民的利益的客观的、普遍的理性概念。
首先,柏拉图反驳了克法洛斯正义就是欠债还债的观点。柏拉图认为:“有话实说,拿了人家东西照还这不是正义的定义。”[1](P6) 因为,有些时候有话实说欠债还债是正义的、天经地义的,而有些时候却是不正义的。“譬如说,你有个朋友在头脑清楚的时候,曾经把武器交给你;假如后来他疯了,再跟你要回去;如果竟还给了他,那倒是不正义的,把整个真实情况告诉疯子也是不正义的”[1](P6)。又比如债主如果是敌人,而敌人对敌人所欠的无非是恶,因此而“还债”也不是正义。“有话实说,有债照还”作为人们经济生活、人际交往的一条原则是人们维护其自身利益所必需的,但由于它不能普遍适用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情形,不能在普遍意义上为城邦和全体公民所共享,因此“有话实说,有债照还”不是正义。
接下来柏拉图反驳了玻勒马霍斯“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的观点。玻勒马霍斯认为医生把医疗技术给予病人、舵手对付航海风浪维护同船人的平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正义的人“在战争中联友而攻敌的时候”就是“把恶给予敌人”[1](P8)。柏拉图指出:依此观点,医生在没有病人的时候、 舵手在没有航海的时候、不打仗的时候,正义便成为了无用的东西了。玻勒马霍斯不同意这样的结论,认为正义在平时也是有用的。柏拉图又在此基础上推出“正义平时在满足什么需要,获得什么好处上是有用的”和“正义仅仅对于无用的东西才是有用的,那么正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了”的悖论[1](P9—11)。另外,朋友和敌人往往是难以区分的,有时候所谓的朋友只是看上去好的人而实际上是真的坏人,有时候所谓的敌人只是看上去坏的人而实际上是真的好人。如果“把坏人当成好人,把好人当成坏人”岂不是会将“帮助坏人,为害好人”当成正义了?最后,“把恶给予敌人”也不应该是一个正义的人所为的,因为“伤害任何人无论如何总是不正义的”,一个正义的人是不能用他的正义使人不正义的,而且“人受了伤害便变得更不正义”了[1](P12—15)。因此,“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就是从个人功用出发,把正义当成了一门技艺或一种能力,同其他的技艺一样,它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以上悖论,从而不能为城邦和全体公民所普遍遵从。
色拉叙马霍斯提出了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的观点。柏拉图对于这个世俗的见解也进行了驳斥。色拉叙马霍斯认为:“在任何国家里,所谓正义就是当时政府的利益。政府当然有权,所以唯一合理的结论应该说:不管在什么地方,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1](P19) 柏拉图当然不能同意此种观点并进行了反驳:首先,正义是强者的利益,也可能是弱者的利益,如同牛肉这样的美味对身体强壮的运动员有好处,对身体弱的人也有好处一样,都是正义的。其次,正义是强者的利益,也可能是强者的损害。因为政府有时也可能会出现错误,服从政府安排,便会造成对统治者利益的损害。所以,正义有时是不利于强者的统治的。最后,“任何技艺都不是为它本身的,而只是为它的对象服务的”。统治也是一门技艺,“在任何政府里,一个统治者,当他是统治者的时候,他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属下老百姓的利益,他的一言一行都为了老百姓的利益”[1](P24—25)。所以,认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是不能成立的。
为了证明色拉叙马霍斯提出的“不正义”比“正义”更有利的观点是错误的,柏拉图首先证明了“正义的人又聪明又好,不正义的人又笨又坏”,因为“正义者跟又聪明又好的人相类似,而不正义的人跟又笨又坏的人相类似”[1](P36)。紧接着柏拉图又进一步指出,既然“正义是智慧与善,而不正义是愚昧无知”[1](P37),那么,显而易见,正义比不正义更强有力。为了能说服色拉叙马霍斯同意自己的观点,柏拉图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国家、家庭、军队等团体或者个人,不正义只会使他们不能一致行动或自相冲突,彼此为敌或与自己为敌,并与正义为敌。绝对不正义的人,是绝对做不出任何事情来的。另外,柏拉图还回答了“正义者是否比不正义者生活过得更好更快乐”的问题。由于心灵是有德性的,如果心灵失去了特有德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心灵的功能。正义是心灵的德性,不正义是心灵的邪恶,“那么正义的心灵正义的人生活得好,不正义的人生活得坏”[1](P42)。所以正义者是快乐的,不正义者是痛苦的,不正义是绝对不会比正义更有利的了。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假借苏格拉底与对手的辩论,对对手提出的种种关于正义的观点进行了分析与驳斥,证明对手的观点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正义。因为柏拉图所规划的城邦生活是一种公共生活,而不是个人利益算计和争夺的现实的雅典社会样态,一个正义的国家应与普遍正确的原则相一致,它不是为了某一阶级或利益集团而建立,而是以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为目标的。这就内含了正义必须是一种超越个人利益关系的,客观的、普遍的,体现城邦和全体公民共同利益的理念。
二、正义就是社会各个阶层固守本分、各尽其责
柏拉图首先从个人生存的非自足性,论证了城邦中的人们结成共同体的需要。他说:“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请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作城邦。”[1](P58) 人们只有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共同体即城邦,才能满足自己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其次,柏拉图对城邦正义作出了规定。柏拉图指出:“我们在建立我们这个国家的时候,曾经定下一条总的原则。我想这条原则或者这一类的某条原则就是正义……这条原则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1](P154) 柏拉图这种按人们的不同天性进行“分工”的理论既是出于效率的考虑,更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城邦正义。他指出,只要当人们按其天赋安排职业,弃其所短,用其所长,让他们集中毕生精力专搞一门,并在适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这样就会每种东西都生产得又多又好”[1](P60)。为了实现“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1](P155),他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将人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前者包括统治者和统治者的“辅助者或助手”,后者主要指农夫、技工、商人等劳动者。一个正义的国家的公民必须严格地划分为这三个不同的等级。人们必须以分工为基础,各司其职。每个行业和阶层对国家都是极端重要的,当这三个阶层的人们“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的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一个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1](P156)。反之,如果这三个阶层的人们不守其职、不尽其能,互相僭越,那么,这样的国家便违背了正义,其结果只能是国家的灭亡。总之,正义就是社会各个阶层固守本分、各尽其责,一个正义的城邦——理想国,就是一个各人按照天性,做自己应做的本分工作的共同体。
柏拉图对正义城邦建立的必要、何谓城邦正义以及如何实现城邦正义的讨论都是围绕城邦生活中的人们必须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而展开的。城邦的存在和正义的体现就在于个人对于城邦的责任,如果个人不履行各自对城邦的不同责任,相互僭越,城邦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更无正义可言。城邦对公民个人教育与训练的内容和形式的安排,也是为培养能够承担城邦责任的公民服务的,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公民良好的心性品德和各种技能,使其能更好地履行对城邦的责任。柏拉图对正义城邦统治者即“哲学王”的最后认定,也并非出于个人的偏好,而是在充分论证了真假哲学家的不同禀赋的基础上,认识到只有真正的哲学家具备立法和管理国家的才能和智慧,才能够履行实现城邦正义的职责。
三、正义就是灵魂和社会的和谐
在柏拉图的正义理论系统中,城邦正义是与个体正义相对应的。他之所以先谈城邦的正义性,是为了“以大观小”。如果找到一个具有正义的大东西(即城邦)并在其中看到了正义,便能比较容易地看出正义在个人身上是个什么样子了。柏拉图认为,人可分为灵魂和肉体两部分,而人的灵魂有三种品质,即理性、激情和欲望,这三种品质又与三种德性——智慧、勇敢和节制相对应。个体的正义就是灵魂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和谐,就是人的理性、激情和欲望保持在各自的限度之内,从而求得各不同部分的和谐统一。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理智体现出智慧,类似于城邦的统治者,起着领导作用,是为整个城邦的利益而谋划的,所以它在个人灵魂中应该起统帅作用。激情类似于城邦中的辅助者,体现出勇敢,服从于理性,并辅助、协助理性对灵魂的统治。欲望如同农夫、技工、商人,在灵魂中占据最大部分,欲望的满足会使人感到快乐,但欲望同时又是贪得无厌的,欲望过分强大会导致邪恶,因此,欲望必须受到理性和激情的控制而受到节制。在柏拉图那里,个人正义就是人的灵魂各个要素的统一,就是人的各种美德的和谐一致。柏拉图对人的灵魂的界说,并不是说某一个阶层只拥有灵魂的一个部分或只拥有一种美德,而是表明,理性、激情和欲望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智慧、勇敢和节制,在不同阶层中分别居于突出的位置,占统治地位。与城邦正义理论相类似,柏拉图主张个体灵魂的这三个部分也应该各行其是,保持和谐,这样的人方为正义的个体。这种内部的分工与和谐,不是外在的“各做各的事”,而是一种内在的和谐有序。“这就是说,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他应当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1](P172)。只有当人们将自己心灵的这三个部分合在一起加以协调,仿佛将音乐中的高音、低音、中音以及其间的各个音阶合在一起加以协调那样,使所有这些部分由各自分立的状态变成一个有节制的、和谐的整体时,他才能够相信并称呼凡保持和符合这种和谐状态的行为为正义的好的行为,而把破坏这种和谐状态的行为称作不正义的行为。
对柏拉图而言,身处社会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除了要追求自身心灵的和谐,更应该为实现城邦的正义而努力,两者是和谐统一的。在他看来,城邦正义和公民个体的正义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两者不能单独实现和存在。只有在一个正义的城邦里,公民个体才能实现灵魂各个部分的和谐,才能过上正义、幸福的生活。另一方面,城邦正义又不是空洞抽象的,它是通过城邦中每一个公民的正义来实现的。没有城邦的正义,城邦中的个人无法拥有正义,离开了城邦中的个人正义,则不可能实现城邦正义。实现城邦正义的过程同时就是培养个人正义的过程。在理想的城邦中,人与人、人与社会是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无论是统治者、护卫者还是农夫、技工、商人等劳动者,都是国家的公民,都是国家的普通一员,都要为共同的国家目的服务。统治者、护卫者和普通劳动者一样,没有任何特权,不能谋一己私利,不仅如此,他们还要为国家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以努力维护城邦的公共幸福。
四、柏拉图正义理论对当代公共行政的启示
柏拉图正义理论的核心,正如他在《理想国》中所规划的那样,是他对雅典民主制度的批判。他通过对雅典民主制度各种弊端的揭露,得出常人是不能理智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结论,并认为只有少数具有哲学智慧的人才能成为国家的统治者。虽然他的这种用等级统治来实现正义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极大的空想性和阶级局限性,但这种等级的分别是按能力而不是按继承下来或任意谋取的特权来划分的,他所努力构建的是一个人尽其才、人随其愿的和谐社会,认为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因此,柏拉图的这种理想可以被看成是对雅典民主制内在缺陷的一种反应和矫正,但由于他不想用制度性的防范措施来实现这种统治,而是走了一条“既是知识精英又是道德精英”统治的道路[2](P180),所以他同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其自身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最主要的缺陷在于这种理想在智慧和理性的背后隐藏着强力、极权这些非理性主义的东西”[3](P110)。将城邦正义主要寄托于极少数拥有理性和智慧、知识和道德的“哲学王”身上,仅仅依赖于他们的道德自律,确实是有着极大的风险的。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一直以来柏拉图的正义思想会受到种种非难。但柏拉图超越对正义经验性的认识,主张对正义进行理性的思考,并在理性正义的基础上构建理想国家的思想无疑是值得后世借鉴的,尤其是其正义理论中,有关正义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追求、正义是固守本分各尽其责、正义的目的是实现人的灵魂和社会和谐的思想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其合理性,对当代公共行政尤其对当代公共行政正义的实现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当代公共行政中,存在着许多重要的价值,既有与官僚组织信念有关的效率、能力、专业技能、责任等,也有与国家信念联系在一起的公共利益、社会公正、制度的价值等。任何一种政体,或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公共利益”理解的视角都会有所不同,但公共利益的根本含义却无可争议地在于,它以“公共”或“公众”为主体、导向和依归,社会制度的设计和安排都必须要以公共利益而非有限的特殊利益作为基础,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切行为的目的。柏拉图关于正义是超越利己性原则对整个国家和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的追求的认识,即便是作为统治者的哲学家也“不是为学术帮派的一己之利而是为公共幸福服务”的,并且“只有不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谋取共同体幸福的人,才能做城邦的最高统治者”[2](P179) 的思想,无疑为当代公共行政正义作了一个明确的注解,表明社会公共行政的设立和运作、行政权力的行使、行政决策的制定以及行政人员一切的作为与不作为只有以“公众”及其利益为宗旨,只有无条件地反映并服务于公共利益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才是正义。
柏拉图关于正义就是社会各个阶层固守本分、各尽其责的思想,是一种以社会为导向的基于责任的正义。当然,柏拉图的基于责任的正义所关注的只是个人对城邦的责任,缺乏城邦对个人的责任,这是由于他的责任思想是针对当时雅典城邦由自由所导致的放纵与无序、公民责任意识缺乏这一现状而提出来的。正如柏拉图认为保卫者的职务不是一种个人优先权、特权,而是一种政治责任一样,他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自觉地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服务、奉献,统治者、辅助者和劳动者一样,没有任何特权,不能谋一己私利,各自应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当代公共行政是责任行政,公共行政人员的主观目的,应以“尽职履行公务”为前提,就是要做好“分内应做之事”。美国著名的行政伦理学家特里·L.库珀将这种责任归结为“客观责任”,要求公共行政人员要对公共利益负责。他指出:“所有的公共行政人员的行为都要以是否符合公众的利益为标准来衡量是否是负责任的行为。”[4](p71) 不仅如此,公共行政人员还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德性修养,使自己达到内在各组成部分的和谐一致,表现为一种自身品质与其本性与职务相一致的和谐状态,以更好地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这是一种与“客观责任”相并列的,根植于“我们自己对忠诚、良知、认同的信仰”的“主观责任”[4](P74)。在这里,柏拉图的“正义就是个人灵魂的和谐”这一观点成为当代公共行政人员“主观责任”的内在要求。个体的正义就是灵魂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和谐,就是人的理性、激情和欲望保持在各自的限度之内,这一思想正是当代公共行政人员实现“我们内心的禀性使我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为”[4](P75) 的体现。
柏拉图的正义理论告诫人们在现世的生活中应该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而一个正义、和谐、幸福的城邦的基础,就在于城邦中各个阶层的人们都能努力尽到对城邦的责任。库珀也说:“保持高度的主观责任是重要的,它不仅有利于整体感、自尊心和认同感的培养,也有利于履行我们的客观责任。”[4](P78) 公共行政人员客观责任的履行与其内心禀赋相一致,不仅体现为其自身的和谐,也会极大地促进其所维护的社会的有序与和谐。这不仅是公共行政人员的重要职责之一,也是公共行政人员在其行政管理、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应时时牢记恪守的准则。在这里,我们看到柏拉图的正义理论中所蕴涵的行政正义的思想内涵,虽然存在一些局限性,仍能给我们许多启示,仍然值得我们在其正义理论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基金项目(2005BZX001)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06—0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