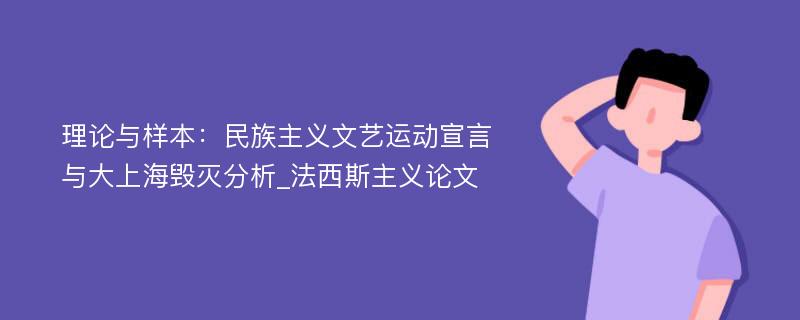
一个理论与一个样本——《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和《大上海的毁灭》并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上海论文,样本论文,宣言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九三零—三四年中国文学的动向》一文中,迟田孝对1930-1934年间的中国文坛有过如下综述:“中国文学之现代的动向,由于一九三零年二月自由运动大同盟之思想的统一,三月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结成,以及反对左翼文学的民族主义文学之发生,大体上方向已经决定了。即是说,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与国民党的文学政策的二大分野的对立,可以说是代表中国最近的文艺思潮的东西。”①可以说,1930年代初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和左翼文艺是相伴相生的,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也不免陷入各自的理论困境之中。在民族主义文艺的创作中,大都努力将民族和文艺绑缚在一起,受到广泛关注的有黄震遐的《黄人之血》《大上海的毁灭》《陇海线上》,万国安的《国门之战》《刹那的革命》《准备》等。这些作品都宣扬了文学上的民族主义,有意思的是,它们针对的不仅是左翼文学的阶级性质,而且也有对国民党内各种五光十色的文艺的统一诉求。就其政治含义来讲,也是为国民党消除异己以及政治上的全面统一鼓噪呐喊。通过下文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和黄震遐的小说《大上海的毁灭》的分析,本文力图说明,以民族主义为旨归的民族主义文艺,在实践中的民族内涵也许并未跨越国家甚至是政党的界限,它们所欲正当化者,与其是一致对外的自我防卫,不如说是对内的统治诉求。在具体的创作中,当真正的日本强敌来犯,民族主义文学所表现出的无力和对强权的崇拜也让其民族主义产生了自我消解的意味。 “理论之堕落”:《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 众所周知,为了和左联的大众文艺相对抗,国民党旗下的前锋社迅速出台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下文简称《宣言》)②。在这篇据说是“花了重赏而始起草完成的,又经过许多人的讨论,并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加以最后决定的”③宣言中,认为在这个万花缭乱的文坛缺乏一个“中心意识”,而这个中心意识便是民族精神,从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文艺主张。虽然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招致了来自各方的批判,但是重新认识这些批判仍然是有意义的。借用茅盾对《宣言》的主要内容的分析,可以将其分为四个部分: 一.早已被西欧学者驳得体无完肤的戴纳(Taine)的艺术理论的一部分; 二.十八世纪后欧洲商业资本主义渐渐发展以来欧洲各民族国家形成的过去的历史; 三.十九世纪后期起,直至现代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故事; 四.欧洲大战后文艺上各种新奇主义——如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的曲解。④ 首先,《宣言》虽未明言,但是茅盾等人都认为它是剽窃了戴纳的“种族,环境,时代”理论,因此“艺术作品内所显示的不仅是那艺术家的才能,技术,风格,和形式;同时,在艺术作品内显示的也正是那艺术家所属的民族底产物”⑤,这一论断正是戴纳理论的改头换面版。我们知道,在19世纪后期戴纳的理论在文学批评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产生了大批的追随者。但是,戴纳的这种从外部进行文学研究的弊端也早为很多西方的学者所诟病,并且,在30年代世界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背景下,种族主义的论述也很容易成为侵略主义的借口,而实际上,民族主义文艺作家黄震遐的《黄人之血》正是借用了这个资源,大肆地鼓吹昔日黄种的蒙古征服白种的俄罗斯的荣耀。 针对《宣言》中提出的戴纳的种族论,胡秋原也从三个方面指出它的弊病:“第一,种族论不能说明一种族艺术家之相同;第二,事实上,已无纯粹之民族,即以汉族来讲,已不知经过多少次之混合了;第三,实际上,民族只是一个地理上政治上的名称,一种抽象的存在,在今日,民族与国家成了一个东西,实际上只是统治阶级所统治的地域与人民之名称。”⑥胡秋原比较真切地认识到了戴纳种族理论的局限性,并通过将民族历史化来指出民族的非单一性和想像性。因此,民族主义者将民族的构成和民族的精神看作是固定的存在,从而作为提倡民族主义文学的依据,自然也就漠视了民族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并且民族主义者将民族和现代国家看作是同一的东西,也便有为现实中自己所统治的国家立论张目的嫌疑,自然由此所招致的批判也就不绝于耳了。 在《宣言》中,为了说明艺术最初的意识就是从民族的立场所形成的生活意识里产生的,民族主义文学提倡者们不惜引经据典,纵论古今。埃及的金字塔和人面兽以及希腊伟大的建筑和雕刻等都被看成是其民族精神的产物和展露,而文学的原始形态也是基于民族的一般意识,如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日耳曼的尼贝龙根,英吉利的皮华而夫,法兰西的罗兰歌,及中国的诗经国风等都是代表,因此“文艺的最高使命,便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⑦。不过这种以偏概全的历史观很快便被指摘出来,胡秋原一针见血地指出:埃及的人面兽和金字塔并不是埃及民族天生就有的,而是埃及帝国建立后才产生的,并且到了埃及分裂时代以至新帝国时代,埃及的艺术又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而反映希腊宗教观念的维纳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才称为女性之理想的丰姿,至于掷铁饼手显示希腊人爱好运动的精神已经是古典时期以后的事情。⑧因此,所谓的“爱好运动的精神”,维纳斯的“女性之理想的风姿”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为了配合有产者组织确立时代之美和市民社会的艺术目的才被归纳进所谓的民族精神的。也就是说,民族文艺不是天生的,而是伴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而被赋予的,民族主义文艺的提倡者们力图把民族意识和民族文艺的起源挂钩,用民族文艺来包办万花缭乱的文艺,用民族的中心意识统摄阶级意识,其所内涵的排他和清洁意识是很明显的。实际上,民族主义文艺提出之后,也利用国家权力对一些左翼刊物和左翼人士进行绞杀,以此达到用民族文艺统摄整个文坛,进而达到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摇旗呐喊的目的。 接着,在《宣言》的第三部分开头这样写道:“民族主义文艺底充分发展,一方面须赖于政治上的民族意识底确立,一方面也直接影响于政治上民族主义的确立。”⑨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文艺的发展必须有待于政治上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正如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现象一样,民族主义也是现代的产物。宣言中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谈起,列举了欧洲各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然后是从19世纪后半期直到现代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故事,但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的“民族独立运动”和现代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很大的差别。前者是各国摆脱封建诸侯的统治进入现代国家行列的运动,而现代的菲律宾、印度、越南、朝鲜等的独立运动则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二者虽然都因此产生了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作品,但却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因此民族主义文学混淆二者的区别,将之通通纳入自己的民族主义论述之下,除了为国民党立国找到历史理论的根源之外,在30年代的世界情势下,最重要的是掩盖了被压迫民族内部的差别,即在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内部也存在着两个斗争的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的工农大众。也就是说,如果在法国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国家形成的时代,民族主义代表的是革命的力量,那么到了资本主义晚期的帝国主义时代,民族主义则具有了两面。单纯的民族主义运动,如果没有了群众运动的参与,其结果必然走向民族主义的反面,变成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民族主义,而中国此时的民族主义也只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才有积极的意义。如此,民族主义者们所宣称的“民族主义的目的,不仅消极地在乎维系那一群人种底生存,并积极地发挥那一群人底力量和增长那一群人底光辉”⑩中的“一群人”便不得不被认为是少数人而已。 《宣言》的第四部分,为了说明民族主义文艺对于政治上民族国家的建立的促进作用,便又将民族主义文艺和其所属的民族意识对号入座,比如德意志的表现主义,俄罗斯的原始主义,法兰西的纯粹主义,意大利的未来主义以及巨哥斯拉夫的现代艺术等。与前陈对民族意识的起源做后设的判断不同,民族主义文艺所列举的这些主义,都是现代主义的一部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达,这也就意味着其所标榜的民族主义文艺和现代主义是不可分割的。然而,《宣言》中这种分类不仅无视各种现代主义发生的不同历史时期,并且也忽视了同时存在于不同民族的类似思潮,比如就前者来说,表现主义发生于战败后的德国,表现了小资产阶级提倡自我的反叛精神,但是随着社会斗争的激化,新的思潮又继之而起,因此表现主义并不能表现德国民族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就后者而言,未来主义出现在资本主义崩溃期中的意大利,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一种狂热,他们颂扬机器、技术、速度、暴力和竞争,但是未来主义并不是意大利的专属,在差不多同时期的苏联,未来主义也是新生事物,它包括了在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一批无产阶级诗人提出的主张,他们一样反传统,但与意大利未来主义的一支沦为法西斯政党的鹰犬不同,苏联的未来主义则是赤色的。因此,所谓的民族文艺思潮和民族国家的意识并不构成直接的对应关系,需要和具体的历史变化联系起来。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单单为了为自己的理论宣言背书,不惜抄错了时间表,难怪会漏洞百出,招致非议了。 《宣言》中另一个很重要表现就是其法西斯主义性质的暴露,而这一点也为茅盾、胡秋原等人所指出。左联执行委员会在1930年8月4日通过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中,也非常明确地把民族主义文学派称为“文学上的法西斯蒂组织”(11)。毫无疑问,很多事实都表明了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艺的提出也和当时盛极一时的法西斯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作为当时传入中国的多种政治思潮的一种,它被翻译为:棒喝主义、法西主义、法西斯蒂、汎系主义、法西斯主义、法西士提等。初入中国时,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讨论和反响。直到1931年5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会议的开幕式上,正式提出对“法西斯蒂”的看法,才形成了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潮的高潮。蒋介石在演讲中认为当时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虽形式互异,而其理论立场除传统的君权神圣说,不外乎三种: 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以唯物史观为立场,依定命主义做推论,认国家及统治权系与阶级,以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12) 从这一段不难看出蒋介石对法西斯主义的向往态度。实际上,在1920、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是很流行的国际思潮,很多国家都把它看作是一个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有效的社会政治模式,蒋介石和德意日等国一样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是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与很多左翼知识分子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走向末路的标志不同,民族主义文学认为法西斯主义所鼓吹的物质主义和机械主义是中国摆脱落后进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精神动力。而上文中所述法西斯主义的主旨之一是“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这也为国民党以国家的名义所施行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大开方便之门,并为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基础,因此当时鼓吹和呼吁贯彻法西斯主义的浪潮一度甚嚣尘上。 就创作上来讲,虽然《宣言》中并没有给出一种具体的民族主义文艺的类型,不过在《前锋月刊》的第五期“编辑的话”中,似乎也隐约向我们传达了民族主义文学主要致力的创作目标是“战争文学”: 一方面世界弱肉强食的趋势日益亟亟。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尚在风雨飘摇之中,而民众的精神,反日趋消极和沉闷,这是多么危险?我们要在文艺上唤起民族奋斗的精神,那么富有兴奋刺激性的战争文学,在目前是极端需要的。(13) 的确,从他们所刊登的小说来看,几乎都是当时国内战争的写照,从黄震遐的《陇海线上》《黄人之血》《大上海的毁灭》,到万国安的《国门之战》《刹那之间》《准备》等等,几乎都是将国内发生的战争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力图发生其通过文学唤起民族奋斗精神的作用。然而不管战争是以什么样的名义进行的,实际的动机如何,它都是有效的社会动员的手段,并且也是体现一种与科技和机械的进步相适应的人类的行为方式。关于战争在法西斯主义的话语系统中所能产生的精神作用,本雅明有过如下的论述:“法西斯主义一贯地使政治生活审美化……为使政治审美化所做的一切努力,集中于一点,即战争。因为战争不仅可以在维护传统的财产关系上最大程度地为群众运动设立一个目标,而且可以被用于提供一种被技术所改变的艺术上的满足感。”(14)法西斯主义擅长把战争等政治动员做审美化的处理,从而战争不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展现,而是调动由技术所引发出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此,战争不再是人类反思自己生存方式的手段,而是技术改变所带来的艺术上的狂欢。换言之,所有的这一切将政治审美化的处理,不过是为了在维护既有的社会关系的前提下,使大众丧失自我反思的能力,在自我毁灭中去获得“审美体验”,从而达到使现存的诸多关系都变得永久化的目的。 黄震遐等人的战争文学中这种将战争审美化的特征就非常明显,它们大多以民族战争为内核,以现代主义的创作形式为外衣,将法西斯主义和现代主义做到了充分地融合。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处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之下,这种特殊情境和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发生的情境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在黄震遐的创作中,我们便不难看到一种矛盾和话语困境,他一方面崇尚由战争的技术所带来的艺术美感,因此无限地崇尚征服的快感,但是又不免在技术和军事的落后所导致的战败的情况下产生自我的怀疑,因而其创作中的民族主义信念便又总是因为飘忽而产生意外的效果,其创作的《大上海的毁灭》便是典型的例子。 战争的审美化:《大上海的毁灭》 在19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与大众文艺的交锋中,黄震遐(1909-1974)因发表《黄人之血》《陇海线上》《大上海的毁灭》等成为当时左翼攻击火力最集中针对的民族主义文艺作家。其代表作之一《大上海的毁灭》最初是在《大晚报》上发表,1932年由大晚报社结集出版,后来被编入魏绍昌主编的“海派小说”专辑系列里。小说是以1931年上海淞沪会战为历史背景而创作的,在这部小说中,黄震遐将目光放在了十九路军抗日的上海与资产阶级颓靡和迷乱的上海,这两种脉络下的上海所产生的张力就提供了两个主题:一个是反日的民族主义和军事主义的主题,另一个是由对机械和技术等生产力的崇拜所产生的现代性后果的主题。我们知道,1930年代的上海有着特殊的身份,它既是一个高度工业化、国际化的现代大都市,同时也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和租借地,因此置身于此的人们一方面享受着这种现代化和机械化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在这种充斥着各种暴力、色情和屈辱的环境中感到虚无和幻灭。与当时的新感觉派作家对上海的描写不同的是,黄震遐的《大上海的毁灭》由于特殊的战争小说的背景,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作为现代主义的上海的相似性与作为一种衍生而来的去民族化的自怨自艾的中国现代主义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上海和战争的结合提供了一种在西方的唯美的堕落和左翼的革命的上海之间的另一种可能性。因此,我们在小说中可以发现一方面是反日的民族主义主题,另一方面是对电影、军事等机械、技术的生产力的崇拜而产生的颓废情绪,而这种情绪的来源也暗合了法西斯主义对技术主义的追求。正如一位评论者在分析本雅明对法西斯文化的贡献时所说的那样:“唯美主义,颓废派及其表现原则是法西斯文化观念和实施政治审美化的源泉,这是他的重要贡献之一。”(15)在展开这些分析之前,首先对小说的内容做一些介绍。 《大上海的毁灭》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旷野与都会”,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十九路军后期的战败和撤退,以及资产阶级少妇露露的上海生活,并由此引出了主人公草灵的失踪以及留下的日记。第二部分“某便衣兵的日记”,主要是以草灵的日记为依托讲述了他参加抗日便衣队被捕,被救出以后和少妇露露的恋爱故事,然而最终露露又重新回到丈夫怀抱,草灵黯然离开。最后一部分“一切毁灭”,讲述主人公草灵回到闸北,在日军发起总攻时战死在上海东方图书馆的屋顶上。小说的重点是主人公草灵参加便衣队的经历以及获救后和露露的情感纠葛,表达了小说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主题以及对上海都市生活的享用以及最终的幻灭。 故事在第一部分借用上海的“他者”,在会战中奋战了五天的汤营长,离开上海“回到自己那些同类的地方去”(16)之前所发的感慨,来表现“一·二八”事变中的大上海里两种不同生活的对比: “十九路军打得这样苦,而这些人在租界里却如此安乐!” “大上海已经玩过了,而所得的印象却只有肤浅,不自然,丑恶”。 自己和这些人似乎是站在两个地球里,一个是诚实,友爱,牺牲,流血,另一个却是浮滑,欺骗,夸大,狂饮纵欲。 虽然,汤营长也会作深一步的解求:“这次所见的只是代表大上海的上流人物而已,下次来,总要看那些下层的情况才是。”(17) 小说借用汤营长的这段话表达了两种意思:首先他道出了上层阶级的腐败和糜烂:一方面是严肃的军事的斗争,而另一边却是荒淫和无耻,这就是半殖民地上海的两面性,也是给新感觉派小说提供了现代主义素材的大上海。除了对这些“上流人物”的“浮滑,欺骗,夸大,狂饮纵欲”的描写而外,总要看看“那些下层的情况”才是。小说中,在情妇露露跟丈夫到杭州去以后,草灵早上起来见到一些工人,他试图和他们交流,但他们以为他是学生,洋行的,写字先生等,没有人会以为他曾经是便衣队,由此他也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在这群以劳力换取食粮,用鲜血争夺自由的人前,我依旧是一个陌生的,代表着其他团体的外人,一个专会说话写字的骗子,一个没用的废物。”(18)在和底层民众交流失败之后,他又在一个清晨来到一个少年宣讲堂的门口,他看到意气如云的青年在开会,便觉得:“到底,我还是属于他们”。然而他后来看到他们混乱的辩论,便又说:“不!我也不属于这个团体!”(19)小说中充满了这种动摇和矛盾的对白,一方面是对“迷信着张飞关羽式大刀”的民众的期待和疏离,另一方面是对“躲在外人保护下的苏秦张仪们”的夸夸其谈的批判和失望。也就是说,小说中的军人像是一个孤立的爱国的群体,与之对比的是下层民众的愚昧和上层阶级的生活的糜烂。 对这种境遇的思索,他通过草灵劫后余生之后和他所“敬重的象父亲一样”的林医生的一段对话来表达: 我看见许多和自己一样的青年拿起了枪,冲过去,倒下,那一种慷慨激昂的愤气上冲霄汉,自己遂不觉深深感动,卒于也照样地拿起了枪,投入这同一的漩涡里去。 是非得失,已全在澎湃着的热血之中消灭,一切的经验,学理,智慧,也全被那唯一的力量——责任心——所蒙蔽,那时大家只晓得是中国人与中国,别的都顾虑不到,这样,我们才肯去做那危险的事,去死! 然而,现在我已很悲哀地发现,当初那些去死的人,虽然是一大群一大群地在机关枪下滚着,但比较起来,仍是极渺小的一部分,而且,这些人牺牲流血的结果,丝毫与大事无济,亦不足鼓励他人——尤其是因为,已经没有了这种人!(20) 因为只晓得是“中国人与中国”于是才投入战斗,但是这种牺牲于事无补,改变不了失败的命运,而林医生的回答则将之归因于上海的特殊性: 在近今的这个社会里,已不复有什么忠诚,义勇,以及责任心的存在,一切的人,都是为了自身直接的利害才去奋斗。所以,象你所说的“中国与中国人”这句话,一世纪以前,在欧美当作天经地义的,来到中国,尤其是来到这现社会制度之下的上海,就有点顾虑不到,也无足轻重的趋势。即使要做,也只是在形式与面子上去用功夫,决不会拿性命来搏,血肉来换,十九路军的抵抗,为的是他们有这种力量,把握,同时,也有点带着南省人愚笨的血气,所以才肯这样地大大牺牲一下;商人们在物质上的接济,也是有点因为不得不如此,而且,稍微损失一点,亦无足轻重,自然何乐而不为?独有那些单凭一股勇气,以性命相搏的人,才是最可敬而最可悯的份子,因为,离开了大众,神不知鬼不觉地到战场上去拼命,虽然是慷慨激昂地死,却也是多么枉然地死啊! 总之,你所说的忠诚,义勇,以及责任心,都只是些被遗弃的,忘了的道德,在大上海绝对不适于用,所以,这些道德是被遗弃的道德,而信仰这些道德去死的人便也是被遗弃的人。(21) 黄震遐借用林医生的口吻一方面否定了所谓的“中国与中国人”的“责任心”在上海这个特殊的地域的适用性,因此信仰这些道德的人就是被遗忘的人,这就大大地消解了小说反日的民族主义主题,也就是说所有的爱国的民族主义因素,如“忠诚”、“义勇”以及“责任心”这些公共的情怀在上海这个地方都变成了与资产阶级的个人利害相关的行为。黄震遐的目的当然是依此表达物质主义的“大上海的毁灭”这个主题,但是也就顺便削弱了小说所欲表达的民族主义主题。 另一方面十九路军的孤军奋战固然也有“政府的不争气”,也有“民众的偷安,苟且”以及“智识阶级的空谈大论”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物质和技术的落后: 的确,政府是没有多派援军来,使得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单独在近代的重兵器下逐渐消灭。然而,事实上很明了地告诉我们,政府即使派十万,二十万,或百万的援兵来,而遭难的依然要以民众为大多数。无论那一次,过去的历史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是物质居劣势的交战国,苟非有多数民众来填补战场上的空隙,一天天像大批原料似的投进熔炉里去消耗着,这个交战国的结果就往都是惨败。所以,在近代战术运用下的悲惨战斗,若单靠有限的常备军去堵塞敌人的进路,实在只是空谈,梦想,故即使政府加派二三十万大兵到淞沪战场之上,而其抵抗期亦最大限度只能维持半载,敌人仅需以其常备军之半数与我支撑,在物质上就可远胜我军十倍。(接下来就是对十九路军六十一师与敌人第九师团的两军实力比较的统计(22))(23) 这也就是说战争的胜败不在于“忠诚”、“勇敢”、“责任心”等等人心因素,而是物质的优劣或者军备的好坏,作为主体的人和技术形成了一种异化的关系。这种对战争的技术性的强调也是法西斯主义的内在结果,从战争中期待那种由技术改变之意义所感受到的艺术满足正是本雅明所说的法西斯主义将“政治审美化”的一种概括。战争,“体现了一种尤其与机械相适应的人类行为方式”。然而:“战争用它的摧毁一切表明,社会并没有充分地成熟到使技术仅成为它的手段。而技术也没有充分地把握社会方面的自然力。帝国主义战争在其最恐怖的特征中是由强大的生产手段与其在生产过程中的未充分运用这个矛盾决定的。”(24)这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享受技术带来的美感,并利用技术去摧毁一切阻碍,而战争只不过是一种承载形式,信仰技术或者说科技决定论的后果就是认同这种战争的逻辑,并且通过一种内在的“艺术”化的方式来表达这种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当黄震遐在《陇海线上》面对装备落后的阎冯军阀和地方“土匪”,威风凛凛地驾驶着德国造的BMW的轻甲机车扫荡而过的时候,他已经同化于殖民者的逻辑和已经获得的“中央军”的正当性。然而到了大上海,面对装备优良的日本军队的时候,他又变成了一个被殖民者,但是这并没有对导向自己亡国灭种的帝国主义的批判,反而将之归咎于机械和装备的失败,当他抛开战争的政治因素而不厌其烦地展开两军实力对比分析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认同了一种殖民的逻辑。也就是说,首要的不是反思战争的正义性与否,或者深处被殖民地位的国家如何来通过自我奋斗获得民族的解放和独立,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如果中国的军队实力强大的话,他也很高兴加入西方帝国主义的队伍。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所谓的将“政治审美化”的法西斯主义战争实际上就是试图发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对半殖民地的中国来说,如果认同这种技术决定论就是天然地丧失了自我反省的政治能力转而认同了帝国主义战争的逻辑。 实际上,我们看到,此处黄震遐也并非完全无意地充当了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供货商,他的思想里一直深埋着一种“征服”逻辑:“历史是一条长而且狭的石级,征服是一个清道夫,清道夫一级一级地走上石级去,每走一级便将这一级的灰尘一扫而光,于是结果历史(石级)便即面目一新了,石级是历史,灰尘是人类,清道夫便是征服,世界如果没有征服,历史便永远被昏沉懦怯的人类所掩,没有进步,没有文化,也简直可以说没有历史。”(25)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征服的历史,“世界永远使弱肉强食的,一个勇武的民族被懦弱的文化所同化后,它底灵魂便即灭亡,反过来,如果一个懦弱的或是笃信宗教的民族,被勇武的民族的兵力所征服后,它的躯壳虽暂时失去自由,而它底精神与灵魂却往往因此得救。”(26)一个“懦弱的民族”被“勇武的民族”所征服反而可以因此而得救,黄震遐以此证明了西方的“艺术文化”优于“宗教文化”。因此,我们会看到他从对日战争的失败所看到的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努力加入这种先进的“艺术文化”行列的迫切。更明显的在于:“世界没有反抗和革命的,世界只有征服,征服是平等的,无论什么民族都有资格来互相征服,所缺乏不过是‘好自为之’而已。”(27)这也就消解了一切弱小国家反抗和革命的努力,“好自为之”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他天然地认同这种既定的国际秩序而缺乏反思的能力,而这种用文化来定义征服就是典型地将政治或战争审美化的例子,由此我们也仿佛听到了意大利未来主义者马里内蒂在对埃塞俄比亚殖民战争时的宣言:“我们认为:……战争是美的,因为它借助防毒面具、引起恐怖的扩音器、喷火器和小型坦克,建起了人对所控制的机器的操纵。战争是美的,因为它实现了人们的梦寐以求,使人类躯体戴上了金属的光泽。战争是美的,因为它使机关枪火焰周围充实了一片茂密的草地。战争是美的,因为它把步枪的射击、密集的炮火和炮火间歇,以及芬芳的香味和腐烂的气味组合成了一首交响曲。战争是美的,因为它创造了新建筑风格,例如,它创造了大型坦克的建筑风格、呈几何状的飞行编队的建筑风格以及来自燃烧着的村庄的烟气螺纹形的建筑风格和其他许许多多风格。”(28) 在临近小说的结尾,黄震遐根据这种技术主义的优劣论得出了一个结论: 十九路军打,是告诉我们说:除掉空谈以外,还有些事好做! 十九路军胜利,只能增加我们苟且,偷安,与骄傲的迷梦。 十九路军死,是警告我们活的可怜,无趣。 十九路军失败,才告诉了我们非努力,还是做奴隶的好。(29) 这段对技术主义后果的分析也遭到了鲁迅的痛斥:“这是警告我们,非革命,则一切战争,命里注定的必然要失败。现在,主战是人人都会的了——这是一·二八的十九路军的经验: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胜,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民族英雄’对于战争的祈祷是这样的。而战争又的确是他们在指挥着,这指挥权是不肯让给别人的。战争,禁得起主持的人预定着打败仗的计画么?好像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呜呼,我们的‘民族英雄!”(30)鲁迅由此认为十九路军的战败是当局事先计划好的投降,不得不说,鲁迅虽然有借题发挥之嫌,但是他仍是抓住了黄震遐文章的要害,那就是不抵抗而言败的所有借口都是托词,因而其所塑造的“民族英雄”也就变成了一个戏子,保家卫国的民族主义也就变成了谎言。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草灵最后的战死也有象征意义。由于上海的半殖民地性质,使得他不能完全地沉浸在机械和技术所造成的大上海的迷幻的世界里,但是他又深陷在这种由技术所支配的法西斯主义的逻辑中不能自拔,所以当他从情欲享乐的温柔乡里跳出来的时候,完全找不到方向,最终在这两种状态之间的摇摆中走向了自我毁灭。这种现代主义式幻觉所产生的毁灭感,在黄震遐的小说《陇海线上》也有表现,比如在他所在的国民党的中央军与冯玉祥的军队对战之余,夜晚遭遇到了河南当地老百姓,他们表现出对“我们”的那种“顽固的,无可劝解的”“杀气腾腾的”厌恶,让他因此产生如下的幻觉: 每天晚上站在那闪耀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样样都使我想到法国“客军”在非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31) 也正是这段文字遭到了来自于左翼阵营的一致批判,而火力最强的当属鲁迅: 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的战士,站在野蛮的非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法国人对于非洲的阿拉伯人,就民族主义而论,原是不必爱惜的。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灭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蒙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顿民族了的缘故。(32) 鲁迅的话里有几个意思:首先,黄震遐的这段表白将自己游离在中华民族之外,一跃而变成了拉丁民族,那么他与中国老百姓的敌对关系自然可以说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而从另一个方面讲,觉得自己“好像是腊丁民族”的黄震遐说明了中国军阀只是帝国主义的爪牙,而和民族解放运动毫无关系。在最后,黄震遐更将这场“中央军”“讨逆”的战争和美国的放奴运动相比拟,认为是一种“不朽的光荣”,但又说这场运动只是一场“互相残杀的内乱”,这种前后不一致严重偏离了自己所欲表达的民族主义主题。因此可以说,《陇海线上》是一部“民族主义”主题先行的小说,但是又是一部不停地瓦解这个主题的小说。 需要注意的是,黄震遐在《大上海的毁灭》中对这种类似于法国“客军”(Légion Trangère,今译法国雇佣军)(33)的幻觉也有过交代,他说这来自于他看过的一部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法国军官在非洲的沙漠里迷了路,躺在沙漠上做了一个怪诞、美丽又恐怖的让人颤栗的梦,梦醒后这个军官便失了魂,后来在一场战争中因为又出现了梦中的幻觉而被人射死。黄震遐借用这种幻觉也许要表达自己对战争的“生与死间不容发时的狂乱”(34)后所不时生发出的那种“虚无”、“无聊”的感觉而已。然而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黄震遐对法国的客军的专门探讨和论述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位民族主义文艺作家的真面目。在《从“客军”讲到杂种人》一文中,他追溯了“客军”的历史,指出了他所认为的“客军”精神: “客军”的精神真可代表西洋文明,我们中国人替自己国家当兵纳税还怨天怨地,西洋人竟替别国大打其仗,只要认定这一国的宗旨趣味和自己相同,便不惜牺牲一切而为之效力,世界本来是没有什么叫做“边界”的“国家”,只不过是民族们保存自己风俗语言财产利益的一个区域而已,“客军”的“国家”就是他们的“宗旨趣味”,进一步言,他们的“宗旨趣味”就是他们的“财产利益”,因此便无不奋战到底,至死不屈了。 这段话将《宣言》中所宣扬的民族主义的内涵彻底消解掉了。从黄震遐这段话可以看出,民族主义并不是表达民族认同感的唯一形式,也不是爱国的唯一形式,“宗旨趣味”也就是“财产利益”才是民族认同的唯一标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说,民族主义者也许并未跨越民族的界限,而是针对一个统治体的内部而提出的,而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将民族问题纳入到阶级问题的框架之中,民族主义文艺的虚伪性便昭然若揭了。 ①[日]迟田孝:《一九三零一三四年中国文学的动向》,林国材译,《华北月刊》第3卷第1期,1935年2月。 ②《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见《民族文艺论文集》,吴原编,正中书局1934版。 ③④石崩(茅盾):《“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前哨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⑤⑦⑨⑩《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民族文艺论文集》,吴原编,正中书局1934年版,第134、136、136、140页。 ⑥胡秋原:《阿狗文艺论——民族文艺理论之谬误》,《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吉明学、孙露茜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⑧参见胡秋原《阿狗文艺论——民族文艺理论之谬误》,《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资料》,吉明学、孙露茜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1)《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文化斗争》第1卷第1期,1930年8月15日。 (12)刘健清:《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7年版,第104页。 (13)《前锋月刊》第1卷第5期,1931年2月10日。 (14)[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郭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15)安斯加·希拉赫:《文化作为法西斯统治的帮凶:本雅明对法西斯主义症候的诊断》,《论瓦尔特·本雅明》,郭军、曹雷雨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 (16)(17)(18)(19)(20)(21)(23)(29)黄震遐:《大上海的毁灭》,大晚报社1932年版,第91,92,299,300、301,205,206~207,313~314,317页。 (22)此为黄震遐对交战双方军事实力的分析: 战略单位一师 人数我一万人 敌两万人 步枪 我六千枝 敌一万二千枝 重机关枪 我七十二挺 敌一百六十八挺 轻机关枪 我一百五十挺 敌五百挺 野炮 我十二门 敌三十六门 迫击炮 我二十四门 敌五十门 平射炮 我无 敌五十门 野战重炮 我无 敌七十二门 重炮 我无 敌三十六门 飞机 我无 敌六十八架 战车 我无 敌二十四辆 (24)(28)[德]本雅明:《战争美学》,《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郭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70、68~69页。 (25)黄震遐:《征服的血痕》,《申报本埠增刊·艺术界》,1929年5月13日。 (26)(27)黄震遐:《宗教·艺术·与征服》,《申报本埠增刊·艺术界》,1929年3月16日。 (30)鲁迅:《对于战争的祈祷》,《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31)黄震遐:《陇海线上》,《前锋月刊》第1卷第5期,1931年2月10日。 (32)晏敖(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前哨·文学导报》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 (33)参见黄震遐《从“客军”讲到杂种人》,《申报本埠增刊·艺术界》,1929年4月29日。 (34)《编辑的话》所附黄震遐的信,《前锋月刊》第1卷第5期,1931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