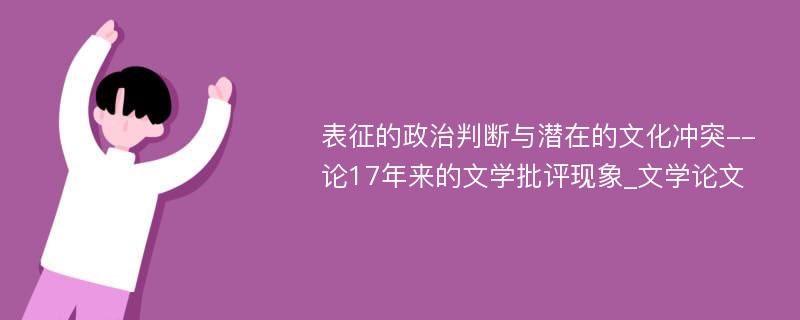
表象的政治判定与潜在的文化冲突——十七年文学批评现象片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表象论文,冲突论文,现象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03)03-0090-03
建国十七年文学批评中存在一个现象,那就是作家们严格遵循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新中国文艺创作总方针,满怀虔诚与热诚倾情写作,力图为新中国文学尽一份绵薄之力,且其作品也常常得到读者与文艺界广泛的好评。但随后气候突变,严厉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批评者从主题、人物、情节乃至细节条分缕析,运用强有力的政治术语和令人生畏的政治评判,给予作品程度不同的批判,有些甚至是全面的否定。比较突出的例子有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萧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对《战斗到明天》(白刃)、《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碧野)、《红豆》(宗璞)、《在悬崖上》(邓友梅)、《小巷深处》(陆文夫)、《西苑草》(刘绍棠)等小说的批判。当时,即使得到了从读者到权威文艺理论机构比较一致肯定的杨沫的《青春之歌》,也未逃脱被严厉批评的命运;倍受推崇的政治抒情诗,譬如郭小川的《望星空》,也遭到了苛刻的指责。时至今日,历史已做出了公正的结论,上述被批判作品都载入当代文学史册,有些作品还被重新结集出版。当年的批评者有的还对那段历史进行了反思与自省。譬如批判过萧也牧的康濯先生在1979年5月为《萧也牧作品选》作的序言《斗争生活的篇章》里写到:“当时有的文章不实事求是的一顿批评,不顾总的倾向而全部予以否定,甚至还波及作者其他作品”,“我个人那一次也不实事求是地写了文章批评萧也牧,这更是我近年来早在引以为训,感到难过,深有自咎的。”[1]
回顾十七年的文学批评史,类似上述文学批评的现象何以如此频繁、普遍、持久地发生,从而造成了我国当代文学事业不小的也是不应有的损失?笔者认为,除了今天文艺界公认的政治上的因素以外,不同文化背景下构成的文化心理冲突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文化冲突在审美选择上的反映
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可以先把被认为是显示了十七年创作实绩的小说作品排列出来,从而得到一个明确的参照系数:《创业史》、《三里湾》、《保卫延安》、《红旗谱》、《红日》、《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林海雪原》、《红岩》、《苦斗》、《苦菜花》、《上海的早晨》、《风雷》、《艳阳天》、《风雪之夜》、《我的第一个上级》、《黎明的河边》、《李双双小传》、《党费》、《百合花》、《谁是奇迹的创造者》[2]。这二十部作品中农村题材的有十部,军事题材涉及到农民的有两部(《黎明的河边》、《百合花》)。从上述数字与比例看,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为小说主人公,着力展示农民的命运、意愿、欲望,是十七年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向,也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显著特征。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内在的规律,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大国,时至今日仍然如此。从五四新文学到新时期文学,以农民生活为创作母题而取得骄人成就的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可以列出一长串的名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农民构成了革命的主体力量,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表现他们的命运、业绩、愿望和感情,是新中国文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革命过程中无数人的奋斗与牺牲,革命胜利后的喜悦与生活,也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十七年的文学作品以农村生活、农民命运为题材的作品占主要的篇幅,是符合社会生活逻辑规律和文学发展规律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表现什么”与“如何表现”是艺术创作两个不同的审美范畴,同一审美客体运用不同的价值评价会创造出审美内涵迥异的艺术意象。在十七年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普遍的审美观念:农民的思想是先进的,理想是远大的,品质是纯洁的,道德是高尚的,情趣是健康的,甚至体格都是强壮的,容貌也是美丽的,在对他们的描写和塑造上,作家们赋予了中国贫苦农民优秀的品质和完美的性格,寄寓着当时人们最美好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但是,不管是从生活的真实还是从艺术的真实上看,这种创作观念以及作品显然存在偏颇与不足。熟知新文学时期乡土小说,尤其是鲁迅先生乡村小说的读者肯定会考虑这样的问题:两千年封建制度残害下的中国农民,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在精神、思想、道德、灵魂乃至体格诸多方面产生如此深刻的质变呢?五四新文学前辈笔下的生活极端贫困,感情充满悲怆,饱受精神奴役创伤的中国农民,一夜之间到哪去了呢?我们怎么去正确理解“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呢?十七年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文艺批评,就缺乏这方面的思考和探索。十七年的文学批评中,人们一般是用农村文化的视角审视中国社会,用乡村文化的审美情趣衡量、评判文艺作品,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化心态和审美情趣的冲突。新文学三十年大量作品被否定,不能不说是这一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而十七年中蕴涵有城市文化意象、情结的作品遭到指责、批评也是必然的了。
现在来看十七年里遭到严厉批判甚至导致作家政治生命窒息的作品: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刘绍棠的《西苑草》。这几位作家都是小知识分子,作品人物也都是小知识分子,是城市文化铸就的人物形象,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在一波接一波的批判运动中首当其冲。作者在小说里写到了主人公回到了儿时成长的城市,又置身于舞厅、霓虹灯、爵士乐、地毯、沙发这些熟悉的事物之间,有亲切之感。批判者认为,作者“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独创和提倡一种新的低级趣味”,“向读者推销廉价的趣味”,判定小说主人公李克是一个“假装改造却又原形毕露的洋场少年”,作者城市文化情结的流露被视为是不能容忍的趣味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和彻底否定。《红豆》中的知识分子的缠绵悱恻、矛盾苦涩的爱情历程也遭到批判,批评者认为:“作者未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来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一当进入具体的艺术描写,作者的感情就完全被小资产阶级那种哀怨的、狭窄的、诉不尽的个人主义感伤支配了。”上述其他几部爱情小说都遭到了类似的批判,知识分子、城市市民丰富和复杂的爱情生活的描述一般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健康的,格调不高的,甚至在道德上都有所质疑。这类指责同样也表现在对《三家巷》、《苦斗》、《青春之歌》的批判上。这些非难与批判,态度是认真的、严肃的,感情是真挚的、激愤的,恰好说明它们反映了持乡村文化审视眼光的批判者与城市文化孕育下的生活观念、感情生活的距离与隔膜,乡村文化心理在这里构成了根本的行为动因。郭小川的《望星空》是一首在一定程度上持知识分子写作姿态的诗,虽然该诗“与当时的流行的‘颂歌式’的政治抒情诗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与当时沸沸扬扬的‘大跃进民歌’也有某种共同的情绪背景”[3],但诗中的某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与批判现实的思维特征。全诗虽仍是歌颂“人定胜天,建设美好幸福的人间天堂”的时代主题,但在行文中,作者面对浩瀚的星空展开了人生、宇宙的哲理联想与严肃思考,“对人类的生命现象作了诗意的、隐含了某种忧郁和痛苦的自我反省。在这种忧郁与痛苦里,既折射出五十年代后期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跃进造成的严峻后果的时代背景,表现了作者对历史挫折的严肃思考和感应;同时,也寓意了在历史的挫折面前,革命者对自身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思考。”[4]诗人的思考在当时的时代狂热情绪中显得格外理性与宝贵,这种忧郁与痛苦是独立意志与自由思想的残存与显露,但诗人这可贵的思想品质马上受到了批评与责难,被认为此诗宣扬了人生渺小,宇宙永恒的消极情绪,表现了极端陈腐,极端虚无主义的感情,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政治性的错误”。其实,批判者敏锐感受到并十分在意的恐怕首先不在该诗的内容,而是作者在诗中体现出的独立思考的思想品格。乡村文化深层心理中的从众、盲从心态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的思想品格发生了碰撞,批评者本能地感觉到了异端。在全国上下一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的声浪中,这种反“超人哲学”的陌生的具有叛逆性质的思维方式才是真正不能容忍的。乡村文化心理与城市文化形态的距离与隔膜发展到六十年代,随着阶级斗争理论的不断升级,逐渐强化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猜疑和敌视,城市似乎已成为罪恶的渊薮,城市生活方式被看作是销蚀无产阶级斗志、与无产阶级抗衡的武器。以被当时评论界极力推崇的两部话剧《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为例。《千万不要忘记》中,电机厂年轻工人丁少纯,比较讲究吃穿,借钱买毛料衣服,下班打野鸭,这些城市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行为是已留存不多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残余,但这些微不足道的生活琐事却让人如临大敌,被当作资产阶级争夺青年的严重事件,被看作是应当千万不要忘记的阶级斗争的具体体现;《霓虹灯下的哨兵》则是把上海繁华的南京路描述成危险的境地,处处埋伏着糖衣炮弹,无产阶级稍有疏忽,哪怕只是扔弃一双破袜子,就有可能被资产阶级侵蚀俘虏。“霓虹灯”象征资产阶级,“哨兵”象征无产阶级,仅凭这二元对立的剧名,就可体味到作者的猜疑与隔膜心态。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十七年很多文艺批评者眼中,文艺作品中所描述的城市文化孕育、催生的人文景观、生活方式、思想感情都是陌生的、颓废的、异端的、具有危险意义的,都应予以否定与摈弃。在政治屏蔽一切的时代背景下,批评者缺乏其他的思想资源与话语体系,都也仅仅只能从政治的角度去判定、去结论,他们运用政治术语去加以框范,运用政治标准去衡量,运用政治批判去加以否定,直至形成了一以贯之的文学批评思维定势。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心态的隔膜,由隔膜产生的猜疑,由猜疑产生的排斥,由排斥产生的在政治上予以扫除的决心,由这种决心催生出了一波又一波的文艺批判运动。
二、文化环境的变化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影响
文学是文化的精粹表征,是一国国民思想、精神、感情、情绪的综合载体。反之,文化是孕育文学的母体,其对一国或一民族的文学的影响也是深远且巨大的。文化环境的变化,从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文化主体发生的深刻变化,自然会对文学面貌产生直接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建国以后,文学创作所倚赖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建立了高度统一且具有权威性的文艺组织,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与中国作家协会。全国的作家艺术家被高度地组织化和行政化,多元化的创作观念和文学活动归为一体,中国文学艺术的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理论得以全面迅速地贯彻执行。文联和作协的成立,为管理和指导全国的作家艺术家创作和批评,为新的思想艺术理论的全面实施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第二,在解放区文艺的基础上,制定了全国作家艺术家应予遵循的文艺创作总方针,解放区文艺的创作实践和经验被作为文学方向和衡量文艺创作成功与否的尺度,全国的文艺创作被纳入一体化的轨道。第三,作家艺术家的构成发生了“整体性的更迭”,“与‘五四’及以后的作家多出身于江浙福建(鲁迅、周作人、冰心、叶圣陶、朱自清、郁达夫、茅盾、徐志摩、夏衍、艾青、戴望舒、钱锺书、穆旦、路翎等)和四川、湖南(郭沫若、巴金、丁玲、周立波、何其芳、沙汀、艾芜)不同,五六十年代‘中心作家’的出身以及他们写作前后的主要活动区域大都集中于山西、陕西、河北、山东一带。‘地理’上的这一转移与文学方向的选择有关。它表现了文学观念的从比较重视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从较多注意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的变化。这会提供关注现代文学中被忽略的领域,创造新的审美情调的可能性,提供不仅从城市、乡镇,而且从黄河流域的乡村,从农民的生活、心理、欲望来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的视域”[5]。这一点很重要,“从农民的生活、心理、欲望来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的视域”,是这部分作家、批评家创作的主要努力方向和成果,十七年里文艺界发生的每次批判运动也几乎都是由他们构成主体力量。文学新格局的形成促进了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有力地配合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作家艺术家的政治与经济地位较之建国前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为作家艺术家全力投入文艺创作提供了稳定的保证。但从十七年的文艺创作实践分析,也存在不足和局限。比较明显的就是由于将极具个性的、多元的文学创作观念和文学活动用同一的文艺理论与审美原则作为最高的、唯一的标准,这就造成了很多文化价值取向单一的文艺作品。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来自黄河流域广大乡村的作家艺术家,与新文学时期西南和东南沿海城市知识分子作家不同,他们的文化观念与文化性格源自深厚的农村传统文化,其生活感悟与创作题材皆源自乡村社会,因此在文学创作中,他们倾情表现乡村生活,细致描述农民的日常生活,满怀挚爱的塑造完美的农民形象;在文艺批评中,他们则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用乡村文化观念审视和衡量任何文艺作品,潜意识地将与乡村社会生活迥异的事物、与乡村文化审美情趣相悖的审美对象视为异端,尽管在实际运作中他们可能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这就造成了持乡村文化心态和观念的文艺批评与蕴涵城市文化观念与审美情趣的作品在文化意识上的误读与冲突。而逐渐形成的一体化的文艺观念则为这些误读与冲突提供了权威的衡量尺度与批评规范,提供了系统的批评话语。客观上看,解放区文艺以及与之相伴生的文艺理论是产生在中国农村,特别是西北乡村,产生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异常激烈的年代,整体上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地域与时代的强烈影响与制约。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文艺创作的中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面对更为复杂的城市社会现象和人群,面对文化取向多样、知识水准较高的读者群,解放区文艺创作观念与批评标准显然应当随之调整、充实、完善,因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保持蓬勃生命力的活的灵魂。但囿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和主观认知水准,民族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年代形成的文艺观念,规范了文艺创作的多样化审美取向,且成为文艺批评的唯一理论资源,这就不难理解蕴涵有城市文化价值内涵的作品为什么总是遭到全面系统批评了。
三、文化隔膜的生活现象以及一点思考
地势地貌、气候物象、生活资源、生产方式、风土人情,诸多因素构成了特定的文化环境,每一个人生活其间,其思想、行为、感情、意识就与这一环境形成同构,进而积淀为稳定的文化心理,成为每一个文化分子漫长人生中认识客观世界,衡量万事万物的座标体系和价值尺度。在中国农村与城市相当隔绝的十七年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隔膜的情景。如农民讥讽城市女性烫发,是“头上顶着一个鸦雀窝”,城市文艺工作者下乡演出咏叹调,大嫂们对美声唱法充满了惊讶和不解。20世纪60年代初,首都剧院演出芭蕾舞《天鹅湖》,有家权威报纸登出评论员文章,指出那些女演员露出白白的大腿,“我们工农兵不爱看!”这些现象说明,两大文化板块相互隔绝极易造成隔膜,这里不存在不同阶级政治观念的差异,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这是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差异形成的隔膜,是任何国家任何政治制度管理下不可避免会产生的文化现象。如今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城乡交通、资讯交流、信息传播日益发达,城乡之间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趋同也日益加强,城乡文化形态的差异和文化心理隔膜不再有那么远的距离了。而在十七年的文艺发展历程中,人们对这一点是相当缺乏认识的。当时,只要对某部作品的阅读产生分歧,无论是批判者还是被批者,都是在政治与阶级的概念与范围里展开思考与论争,这实在是十七年文艺批评中的一个盲区。不可否认,当初有些作品被批、被封杀,确实是政治上的因素,比如《保卫延安》、《刘志丹》等作品,但那不是作品本身的问题,而是不可抗拒的政治情势,这是题外话。今天看来,当时很多作品如从文化学的角度去考虑,从文化隔膜、文化碰撞的层面去审视、去解释,不少创作与批评上的问题是比较容易争论清楚的。
近十年来,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东西文化、南北文化不断地碰撞、交融,正汇成一股不可逆转的文化潮流。顺应这一世界潮流,跨入21世纪的中国正敞开胸怀,与国际社会全方位地接轨。有鉴于此,以宽广的胸襟与视野,以有容乃大的睿智,吸掇采撷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应是今天文艺批评工作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和应采取的积极姿态。
标签:文学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城市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文艺论文; 红豆论文; 青春之歌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