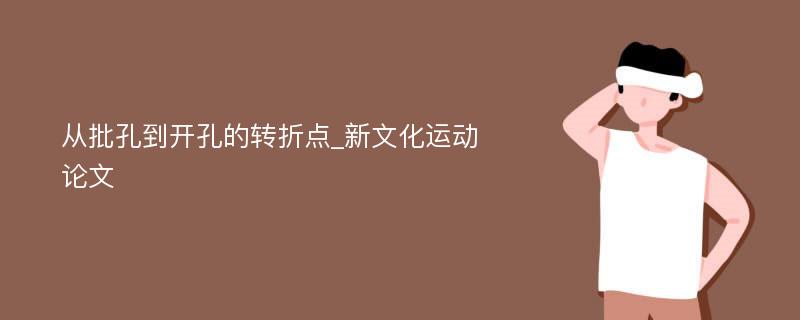
从批孔到释孔的转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孔到释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1)03-0026-06
发生在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距现在已经80多年了,但如何评价这场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仍旧是当今学术界感兴趣的热门话题之一。在众多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著中,都触及到当时的思想家关于孔学(或称儒学)的看法问题。有相当多的论者盛赞“打倒孔家店”的彻底反封建精神,也有不少人持相反的观点,指斥“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的“文化断层”,还有一些学者把“五四”精神界定为“激烈反传统主义的泛滥”。这些说法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我们看来,又都不够全面。实际上,“批孔”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方面,其另一个方面则是“释孔”。综观80多年来中国学人对于孔学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从以批孔为主到以释孔为主的过程。
一
所谓“释孔”,就是以同情的态度看待儒学,肯定它在现时代的文化价值,并且根据现时代的精神需求对儒学作出新的诠释,使它成为现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以传统文化理解、评判新文化的时代风潮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主流思潮是以新文化理解、评判传统文化,其目的是“再造文明”。因此,如何以新思想、新文化观察和分析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家伦理,就成了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主题之一。但是,“批孔”与“释孔”是始终相互联系着的两个方面:在那些激烈批判孔学的思想家的思想深处,存在着重新诠释孔学的倾向;而在大多数维护孔学的思想家的思想深处,也必须考虑新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存在着化解孔学消极因素的倾向。顽固坚持封建主义立场而一味“尊孔”者也确有其人,不过这些人已经没有资格列入有价值的思想家的行列。大量事实表明,批孔与释孔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任何一位有造诣的思想家都会把审视儒学作为自己思想的出发点,否则他就没有跻身于思想家行列的资格。他受到时代精神的感召,不能不承认传统的儒学的确存在着过了时的、陈腐的因素,对此必须认真地加以清理,因而他必须要做一番“批孔”的工作,为新思想的引入和发展扫除障碍。被人们目为现代新儒家开山的梁漱溟,面对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喊声,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为孔子说话”,对儒学表示同情。人们常常注意到梁漱溟对于孔学的同情的方面,却容易忽视他对孔学的批判的方面。其实,他并不主张把儒家思想原封不动地拿出来,而必须“批评地拿出来”,意即对其加以分析、有所改造。他并不讳言儒学的局限性,提出著名的“中国文化早熟”说。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对文化早熟作了这样的解释:“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的,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发出来,而影响了全局。前者是循序而进,后者便是早熟。”[1](P267)梁漱溟所说的“早熟”,带有“病态”的意思,是指中国文化没有经过完善的科学文化阶段、没有完全解决好人的生存问题就进入了关注人与人的关系的伦理文化阶段。据梁漱溟分析,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存在着“五大病”:(1)幼稚——中国文化实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或显露幼稚;(2)老衰——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传到后来,生趣渐薄;(3)不落实——西洋文化从身体出发,很合于现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出发,便不免理想多于事实,有不落实之病;(4)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5)暖昧而不明爽。可见,梁漱溟与当时顽固的守旧派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是一味地为传统文化护短。他对于传统文化里缺乏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非常痛惜,明确主张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
与梁漱溟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不同,西化派的思想家在“五四”时期高高举着“打倒孔家店”的旗帜,在思想界发起声势浩大的批判儒学的思想运动。尽管如此,他们也不能不承认中国有着绵延数千年的悠久的文化传统,而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作为一笔丰厚的思想遗产,如何获得现代的思想意涵,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因而他们必须由“批孔”转向“释孔”,探索新文化与传统文化沟通的渠道,为新思想的引入和发展开辟道路。胡适在“五四”时期发表了大量抨击孔教的言论,但是也发表了大量对儒学表示同情的言论。胡适抓住性善论这一中心来剖析孟子的思想体系,认为从中可以引申出的第一个有价值的论点就是凸显了个人的位置,把个人看得十分重要。他引述孟子的“大丈夫”之说以为证据:“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胡适很欣赏孟子的这个观点,评论说:“因为他把个人的人格看得如此之重要,因为他以为人性都是善的,所以他有一种平等主义。”[2](P297)从性善论可以引申出的第二个有价值的内容是孟子的教育哲学。正因为人性是善的,所以孟子强调教育不能是被动的、逼迫的,而只能是主动的;强调教育应该是本来善性的充分发挥;强调教育的目标是辅助善性的自我实现。胡适对孟子的教育哲学评价也很高,认为孟子提出的三大要点“都于后世的教育学说大有关系”,“这是标准的教育法的原理”[2](P300)。从性善论可以引申出的第三个有价值的内容是孟子的政治哲学。既然大家在“人性善”这一点上是平等的,那么在处理君民关系时就应当以“善”为最高原则,所以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胡适认为孟子的这种说法“带有民权的意味”。
由上述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个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会通、把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加以会通的思想文化运动,它内在地包含着“批孔”与“释孔”两个方面的内容。这种“批孔”与“释孔”相伴的现象,贯穿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全部过程之中。研究这一现象,总结各个思想家的理论思维成果和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在新世纪正确解决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化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
“批孔”是中国现代哲学思潮的生长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掀起全面清算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运动。这一运动固然有许多形式主义的缺点,但并没有严重到造成中国“文化断层”的程度。他们推翻旧式儒学在思想界的权威,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他们倡导白话文,找到了表达新思想新内容的新形式;他们高扬科学与民主,呼唤个性解放,拒斥封建专制主义,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觉醒程度达到了新的水平。正是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才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主义旧思想的统治地位,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传入与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儒家思想的改革提供了前提。“批孔”要求的提出,表明“五四”时期进步的思想家开始以清醒的、批判的眼光审视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弊端,勇敢地探索中国哲学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揭开了中国哲学思想发展新的一页。“五四”以后的30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潮水般涌入中国,在中西交融的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家哲学、中国实证哲学三大思潮逐渐形成,构成现代中国哲学的新格局。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唤起了追求真理的热情,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条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唯物史观引入中国以后,迅速地传播开来,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在传播唯物史观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有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李大钊。1919年2月,李大钊帮助《晨报》改版,增设“自由论坛”、“名著介绍”等专栏,开辟宣传唯物史观的园地。同年5月,他又在《新青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配合“五四”运动宣传唯物史观。1919年9-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上连载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按照自己的理解第一次向中国学术界较为系统地绍述唯物史观。以后,他又陆续发表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宣传和介绍唯物史观以及社会革命论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仅1919年的后半年,全国各地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报刊达200多种,出版有关唯物史观的著作数十种,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实证哲学的发展方向。在中国哲学史上没有实证哲学的传统,它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并且传入的时间很晚,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第一个实证论者还应当从胡适算起,他在美国亲炙于杜威,回国后撰写长文《实验主义》发表在《新青年》上,系统地介绍实用主义哲学,并且终生信奉实证哲学,至死不渝。胡适以实用主义为思想武器,向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发起冲击,宣传科学思想和人权观念,成为“五四”时期思想界的骄子。正如艾思奇所评论的那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价值,可以说远不及他的‘拿证据来’的实验主义精神之价值。实验主义在今日,谁也知道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它能一变而成唯心论哲学。但在当时,作为与传统迷信抗战的武器,还不失为历史推进的前锋。胡适在当时之能成为得意人物,不是因为有什么系统的大贡献,也不是如某人所说,能给中国人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只是为了实验主义的历史的意义和价值罢了。”[3](P62-63)这可以说是中肯之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现代新儒家哲学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和实证哲学思潮,都采取批判传统哲学中的消极因素的方式,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现代新儒家与此不同,它采取维护传统哲学积极因素的方式,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如果仅仅抓住这种不同,便把现代新儒家划入新文化运动反对派,显然是不合适的。诚然,现代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对实证哲学思潮都有所批评,但他们并不反对倡导科学和民主,并不反对白话文运动,并不否认传统哲学实行现代转换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翼。现代新儒家的开山梁漱溟清醒地认识到,守旧派一味地株守旧学是无济于事的。他说:“旧派只是新派的一种反动,他并没有倡导旧化。……他们自己思想的内容异常空乏,并不曾认识了旧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怎禁得起陈先生(指陈独秀)那明晰的头脑,锐利的笔锋?”[4](P152)梁漱溟认为儒家思想必须善于从西方哲学中寻找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和思想方法,才能走出困境,这一点也是所有现代新儒家的共识。
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期,中国现代哲学格局明朗化,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现代新儒家思潮(或称文化保守主义)、实证哲学思潮(或称自由主义思潮)竞长争高的局面。1949年以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大陆占有主导地位。现代新儒家哲学思潮和实证哲学思潮在大陆已不再独立存在,但仍保持着潜在的影响力,而在港台地区依然薪火不断。因此,从总体上看,直至今天中国仍旧保持着三大思潮并峙互动的格局。
三
“释孔”方式的不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哲学思潮之间的差异。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现代新儒学思潮、实证哲学思潮三大派来说,尽管他们各自的学术立场不同,理论观点有异,但都面临着如何看待“孔学”,即儒家思想的问题。如何立足于时代的要求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材料并使外来文化与固有文化相结合,是当时思想界的首要任务,所以,三大思潮都把重新解释孔家思想当成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来抓,都力图通过重新释孔而为各自的发展开辟道路。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儒学的封建主义思想倾向时,也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弘扬儒学的文化价值。人们往往注意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对儒学的批判的方面,而忽视了他对儒学的同情的方面。其实,他并不否认儒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他指出:“孔子生于古代宗教思想未衰时代,其立言或假古说以申己意。西汉儒者,更多取阴阳家言以诬孔子,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之伦理之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之今世,而在宗法封建时代,诚属名产。”[5](P211)孔学在今天已失去其合理性,绝不意味着他在历史上不具有合理性。陈独秀在《孔子与中国》中写道:“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5](P526)在这里,他试图把孔子思想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对其做出冷静的、中肯的评价。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明确地对儒学做出肯定性的评价,认为在孔子的思想中包含着“以人民为本位”的精华。他说:“孔子的基本立场既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因而他的思想和言论也就可以获得清算的标准。大体上他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6](P87)孔子“以人民为本位”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倡导的“仁”的观念。据郭沫若考证,“仁”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在春秋以前的古书里,在金文和甲骨文里,都找不到这个字。“仁”字虽未必是孔子创造出来的,但它特别为孔子所重视,并且构成他思想体系的核心,乃是不争的事实。郭沫若引证了《论语》中孔子关于仁的大量论断,得出的结论是:“仁的含义是克己而为人的利他的行为。简单一句话,就是‘仁者爱人’。”“他的‘仁道’实在是为大众的行为。”[6](P88-89)郭沫若高度评价孔子的仁学,认为孔子发现了人,主张每一个人不仅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
中国实证论者早期以“批孔”为主导,后来则转向以“释孔”为主导,不过始终没能从根本上扭转全盘西化的倾向。胡适在“五四”时期曾表示拥护“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他在20世纪30年AI写作作《说儒》时已经走出激情,试图以客观、平和的心态研究儒学,认为孔子把柔弱的儒改造为刚毅的儒,对于中国文化做出重大贡献。晚年的胡适基本上已经放弃“打倒孔家店”的偏激态度,对儒学表现出更多的同情。他不再把中国传统文化同近代文明对立起来。1953年胡适在日本接受东京一桥大学首席教授上原的采访时说:“我个人的看法是近代的进步并无背离中国古代的思想。不仅如此,近代的进步与古代纯粹的中国传统的想法完全一致。”他所说的“纯粹的中国传统的想法”是指儒家“正德”、“利用”、“厚生”等,他认为其中包含着“涵养人性之善”、“增进人民的幸福与有用”、“使人民享受丰裕的生活”的意思,这同近代以来科学与技术进步的理想是一致的。
现代新儒家学者力图推进传统儒学的发展,但始终摆脱不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情结。冯友兰自述,新理学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宋明理学讲的。岂止冯友兰,任何一个现代新儒家学者都是如此,他们都努力从西方哲学中寻找思想材料和思想方法,力图对儒学加以改造。在现代新儒家构筑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中,不难找到柏格森主义、新实在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康德主义的影子。他们继宋明理学之后,对儒学作了重大的改铸,使之获得了现代理论形态。如果把孔孟荀算作儒学的第一发展阶段,汉代经学算作第二个发展阶段,宋明理学算作第三个发展阶段的话,狭义新儒学可以说跨入了儒学的第四个发展阶段。现代新儒家取得了值得肯定的理论思维成果,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思想局限,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本位文化优越论的情绪。
由上述可见,三大思潮都致力于建立各自的儒学观,试图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十分复杂,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难题。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思想家们一直没有停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至今仍然没有终结。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在如何评价儒学方面曾一度走过弯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思维教训;实证主义思潮和现代新儒家思潮在港台地区占有相当大的市场,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思维成果,但影响也十分有限,总结其思想教训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三大思潮之间的交流逐渐活跃,呈现出互动的局面。
“批孔”与“释孔”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五四”时期进步思想家对儒学中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否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孔”精神并没有过时,在今天仍需要继承和发扬。长期以来,人们常常过分强调“五四”时期进步思想家“批孔”的一面,而忽视了他们“释孔”的一面。其实,他们在“批孔”的同时,也作了一些“释孔”的工作,尽管不够深入,仍有总结和研究的必要。事实证明,离开“释孔”而一味地“批孔”,非但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而且违背思想文化的发展规律,必然流于粗俗的攻击和谩骂从而导致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文革”期间的所谓“批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释孔”作为对儒学正面价值的阐扬,内在地包含着对其负面价值的清除。从这个意义上说,“释孔”也离不开“批孔”。“批孔”可以以文化运动的方式展开,而“释孔”却是一项细致、深入的理论研究工作,搞运动是无济于事的。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进程看,儒学研究的重点逐步从“批孔”转向“释孔”。“释孔”是一项比“批孔”困难得多的浩大工程,要想完成这项工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还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在新的世纪,三大思潮互动的局面仍然会保持下去。随着中国的统一和“一国两制”的实施,三大思潮将会有直接平等对话的可能;如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重新解释孔家思想,将会有更深层次的讨论。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其思想影响力永远不会消失,怎样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相信,经过科学的、合理的解释以后,儒学将同市场经济兼容,同科学与民主兼容,同马克思主义兼容,从而获得积极的理论价值。
收稿日期:2000-06-01
标签:新文化运动论文; 儒家论文; 孔子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国学论文; 胡适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孟子论文; 梁漱溟论文; 新青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