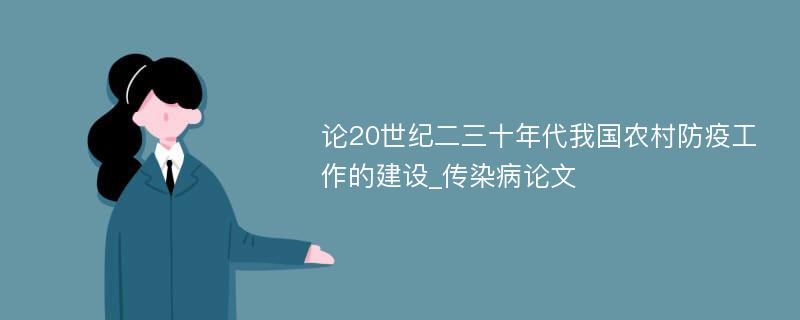
试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防疫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防疫论文,三十年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8)5-215-05
新文化运动后,卫生防疫已被精英阶层视为振兴民族、复兴国家的一项急务而广受关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十分重视卫生防疫,将其列为国家建设的基本内容。在政府主导、精英示范下,乡村社会的防疫观念逐步嬗变,综合防疫能力随之提高。本文拟从政府行为与社会力量两个视角,来考察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卫生防疫建设的推进过程,进而揭示其中的特点和规律,以求抛砖引玉。
近代中国,绝大多数人口集中在乡村,乡村及乡民是防疫建设的重点、难点。清末新政期间,防疫作为一项关心民瘼的“惠政”曾在天津、北京、济南等大城市推行过,但广大县、乡则近乎空白,“多无卫生组织”。①辛亥革命爆发,国家长期内战不已,政府更迭频繁,民智建设相当薄弱,文盲遍布乡野,多数地方的公共卫生设施“甚为简陋”,传染病大面积流行的态势不仅得不到有效遏制,且愈演愈烈,并有“阻碍民族复兴之可能”。②资料显示,当时中国的死亡率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以上,每年非正常死亡的乡民高达510万,不仅如此,活着的人体格也“不能与健康民族相比”,这种“愈格死亡(的现象)年复一年”。③有识之士曾大声疾呼“民族分子贵精不贵多,一百羸弱愚蠢之国民反不若五十健康受教育者之有用”。④所以,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实施卫生行政,用科学手段防控传染病,挽救国民生命、增进大众健康已成为时代主题。
一 乡村防疫中的政府行为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卫生防疫作为一项基本内政在全国推广。当局认为这既是“关乎民族健康及经济建设”的首要事业,也是“跻其民族国家于强盛之域”的前提之一。⑤卫生部官员指出,防疫头绪尽管很多,但“最重要者,必须中央政府有关于传染病完整法令之颁布”,省、市有行政人员的严密执法,积极普及防疫知识,使老百姓充分“明了传染病之危险”,构筑统一的防火墙,进而制服桀骜不驯的瘟神邪鬼。⑥
(一)乡村防疫体系的设计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卫生部(1931年4月改称卫生署),负责督办地方防疫建设。与以往不同,当局在注重城市的同时,对乡村防疫建设也比较重视。1932年,内政会议要求各省参照《市卫生行政初期实施方案》,依据地方情况,筹设县立卫生医药机关,以此作为推广乡村防疫事业的职能部门。1934年,全国卫生行政技术会议通过了《县卫生行政方案》,令各县在政府驻地设立主管地方卫生行政和技术实施的中心机关——卫生院。依据人口及地域特点,卫生院下设卫生区,区下设卫生所,所下设卫生分所,组织相对完善,目的在求“工作之普遍”。⑦
县卫生院职责有实施预防保健,监督各卫生所及其分所采用新技术,训练卫生初级助理人员,考核卫生工作人员,编制各卫生机关概算和决算,推广民众卫生教育,调查地方性疾病及统筹统发医药卫生用品等。卫生院院长一般由受过公共卫生训练、且具有临床经验的医师来担当。院长之外另设医师、公共卫生护士、助产士、检验员、药剂士、卫生稽查事务员等职。日常工作有办理门诊治疗、住院治疗、巡回治疗及农村救济等事项。如遇特殊情况,比如发现有传染病流行的趋势,还要第一时间内采取排查、隔离等应急处置措施。
县卫生院建设标准分甲、乙两种,甲种建筑费2万元,设备费3千元;乙种1万元,设备费2千元。推广之初,鉴于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卫生部建议各县可根据实际财政状况因地制宜地落实上级要求,未必整体划一,经济上确有困难的还可暂用公共房舍或庙宇,“通融举办”,以后再“徐图改进”。卫生院每月经费为600-1,400元,分配比例是薪金60%,办公费10%,购置费20%,其他10%。乡、镇卫生所开办费为400-780元,经费每月180-300元;卫生分所开办费为100-140元,每月经费为50-100元。⑧
卫生所隶属于卫生院,设主任一名,由受过公共卫生训练的医师充任,另置护士、助产士及卫生稽查员各一人,协助主任工作。卫生所职责有:其一,定期推进预防天花的种痘及其他免疫注射,处置转诊病人,监视及上报辖区疫情;其二,改良井水、处置粪便、灭蚊除蝇、改善居住环境及监督店铺营业等;其三,监督卫生分所日常工作,督促落实基层防疫事项;其四,推行妇婴卫生及新式助产工作,力争降低妇女及新生儿死亡率;其五,举办生命统计,编制卫生防疫资料等。⑨
卫生分所是第三级卫生行政机关,负责辖区内初级防疫保健事务。比如,处置普通病号、办理免疫注射、改良井厕卫生、监督报告传染病发生及流行情况、推广科学接生及妇婴保健新法等。分所置护士一名,由接受过短期公共卫生培训的青年充任。为节约经费,分所大多附设于乡村小学之内。通常情况下,百户以上的村落设卫生员一名。⑩
(二)乡村防疫体系的推广
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在谈到乡村卫生事业时说,“卫生建设的第一桩紧要事业,便是设立乡村医院”,“不但医病,还在防病”。(11)卫生署长刘瑞恒指出,“乡村卫生不良,殆为我国贫弱之主因”,所以,要复兴民族,就必须大力推行县乡卫生行政,这是各种救济方案中的急务。(12)1931年江淮流域大洪水过后,各地疫情空前加重。1932年还出现了全国性的霍乱大流行。“存在决定意识”,严峻的形势迫使各级政府加快落实防疫措施。在卫生署推动下,许多县开始筹设卫生院,举办乡村防疫。率先实施的有:江苏的无锡、盐城、句容、仪征、常熟、萧县、金坛等9个县;浙江的武康、诸暨、丽水、海盐、寿昌等7个县;江西的高安、萍乡、浮梁、吉安、临川、弋阳、丰城、进贤、安义、东乡等20余县;广西有百色、龙州、柳州、宜山等4县。1934年4月,卫生署要求各县普遍设立卫生院、卫生所及卫生分所,以便使卫生医疗事业“普遍于乡村”。此后,又有一批县陆续设立卫生院。到1936年,江苏江宁,山东邹平、荷泽,湖南长沙、醴陵,陕西华县、榆林、三院等县均已仿办。(11)县卫生院的设立是政府对内职能向农村延伸的重要措施之一,这既为乡村应对传染病流行提供了可籍的手段,也为构建科学的防疫网络提供了重要平台,有助于及时发现并处置疫情,进而保护乡民的生命和健康。为深入分析问题,下面以江苏、河南、河北及湖南四省的乡村防疫为例,略作考察分析。
1.江苏。尤其是苏南,明清时就是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近代,受到西方文明的浸润,上海、苏州等城市的卫生防疫事业起步较早,但广大乡村却十分滞后。五四运动前,江苏多数地方没有县医院,乡村防疫体系更无从谈起。1921年,泰县、盐城、句容等县才开始设县立医院。1927年后,江苏成为国民政府所在地,现代化事业受到空前重视,卫生防疫也被推到前台。1933年后,江苏决定在全省设县立医院,令财政充足的县,直接将戒烟所改成医院,禁烟工作退而为次;财政困难的县可暂时选择在戒烟所内附设诊疗部、接生站等机构,尽快开展服务于乡民的防疫工作。到1935年1月,全省已设县立医院19所。1936年6月,省政府又颁布《江苏省各县县立医院规程》,督促各县推广乡村防疫,通令所有没设医院的县一律将戒烟所改为县立医院。
随着卫生院的建立,各县防疫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展开,一改往昔落后的局面,其中一些县、乡的工作还搞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武进县农村改进委员会通过开办卫生展示会、筹设民众诊病所、推广免费疫苗注射、举办夏令卫生运动会、取缔露天厕所以及检查饮食卫生等活动,来推广乡村防疫设施,增强民众的防患意识。⑤针对夏季传染病高发情况,该县特颁布《夏令施诊所通则》,在人口稠密的集镇为乡民进行免疫注射,措施得力,“颇见功效”。(14)镇江县为解决贫困乡民治病难的现实问题,特筹集资金在丹徒镇设立卫生事务所,办理该镇“一切卫生行政及疾病之预防及治疗事宜”。随后,又在许多村庄设立卫生分所,以弥补乡镇防疫力量的不足。到1936年1月,葛村、姬庄、湖溪乡及丁冈村等地各添设卫生分所一处。由县里振医师、护士前往巡诊,指导家庭及公共卫生,“举行卫生谈话”。此举深受乡民欢迎,远近乡镇到丹徒卫生事务所就诊者逐渐增多,平均每日约50人。巡回医疗队每月诊治800人左右。起初,镇江乡民对疫苗接种存有疑虑,一度“畏缩不前”。为打开局面,政府加大宣传力度,让事实说话,不久,畏难情绪就消失了。1936年春,种痘6,159人,霍乱预防注射2,906人;白喉注射2,225人;伤寒注射216人;伤寒、霍乱混合疫苗注射2,202人。此外,为使当地乡民免受恶性疟疾的蹂躏,省民政厅还拿出专项购置“防治疟疾特效药品,组织防疟队,分赴各乡镇从事扑灭”,以尽快绥靖乡野。(15)
2.河南。内乡县防疫工作搞得比较出色,有一定代表性。该县除在县、乡建立卫生保健组织——卫生院外,还将原来的民团军医处改建成平民医院,直接服务于乡民。1934年11月,平民医院移至县城,聘请中、西医生坐诊,并购置大量药品,以“极低廉之费用,为人民治病”,一般诊病只收挂号费,除此之外不再“另收药资”,出诊也免费。住院者每人每天仅收2角钱的膳食费,药费较低,贫困患者还可酌情获得减免。除疗病外,平民医院还仿效河北定县乡村建设派的实验方法,“襄助办理公共卫生”,以推进乡村防疫事业的发展。(16)同年秋,县政府还在赤眉镇设立公共浴池一所,“籍作提倡”定时沐浴的社会风气,(17)引导人们重视个人卫生,以减少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
3.湖南。省立农民教育馆除与湖南卫生实验处合作,聘请医生对乡民普遍施种牛痘外,还针对夏秋季节传染病猖獗的形势,筹集专项资金,购买“金鸡纳霜”、“救急散”、“五积散”及“神功济众水”等中西特效药,分发到贫苦患者手中,使之有所凭借,以免坐以待毙。为防止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的发生及流行,省农教馆特发起了捕鼠灭蝇活动。办法是每消灭老鼠一只或苍蝇百头即给奖券1张,定期“凭券开奖”,头等给奖4元,二等1元,三等以下也分别给奖。这项活动深受农民欢迎,参加者十分踊跃,各区发出的奖券多者千余张,少者也五、六百张,效果理想。此外,其他像卫生讲演、环境清洁等防疫工作也因其喜闻乐见,故有“颇多效果”。(18)
4.河北。省立乡村民众教育馆一面向县、乡、村推广防疫保健组织,由其“专司治疗、防疫、种痘”等基础性的日常事务;一面倡导发展体育活动,借此提高民众身体素质,增强抗病能力。提倡者认为球类、田径比赛等活动明显欧化,在城市还有部分适用对象,但“绝不适于农村需要”,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武术套路在民间较为盛行,又确有强身健体之功效,倒是“普及乡民体育之最好方法”。为此,他们特拟定国术会组织简章,在各地成立国术会,向乡民推广这项健身方法。由于组织得力,故“成绩甚佳”。(19)
综上所述,中央和地方对乡村卫生防疫建设都有很大决心,并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民生的具体工作。但由于多数县财政困难,许多防疫措施无法深入实际。以河北定县为例,全县有40万人口,6个区,472个村庄,而年人均收入仅30元,平均每人每年医药费0.1元,仅在县城内有两名没有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执业医生,半数村庄只有半农半医的草医和识字不多的中医为乡民看病。(20)(备注:1932年的统计数据)定县如此,其他县也相差不多。现状主要是历史造成的,一朝一夕难有大的改变。不久,中日关系趋向紧张,严峻的形势迫使决策层将精力用于对付时局,乡村防疫事业还没来得及深化,就被搁置一边。江苏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各项现代化事业大都走在全国前列,其防疫建设虽有成绩可言,但多数县在人力物力方面“均感缺乏”,实际工作“尤漫无边际”。(21)江苏如此,其他省份可以想见。
二 乡村防疫中的精英行为
在国民政府进行乡村防疫建设的同时,一些知识精英也在积极推进这项关系国运兴衰的社会改造事业。乡村建设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坚持深入农村,将推广卫生防疫作为拯救农村的重要内容。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发展,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2)的确,在政府提倡、精英推动下,中国乡村防疫走出了一条“由点到面”、“政府行为与精英行为”相结合的新路子,其经验足可为后人法。
(一)乡村建设派
1.总体思路和方案。梁漱溟曾指出,“乡村有许多应当改良的事情:妇女缠足、男子早婚、吸食毒品、好赌博、不清洁等等坏习惯,说起来实在很多,都应当赶快改除”,“南京有个卫生署是专注意公共卫生的,他们对于流行的传染病——如霍乱、伤寒、发疟子等症,都极力加以研究,想法子预防或治疗,但他所研究出来的方法,也必须依靠各地乡村有组织,才能推广呀!”如果乡民散漫没组织,夏天虽有传染病流行,而不能把详细情形报告上去,卫生署也无能为力,“就是有防范的办法,也没有法子传送到乡村”。(23)应当说梁氏说出了中国乡村推行防疫建设的实际困难。自晚清始,大批士绅离土居城,乡村日益走向破产,乡民失去了组织,这就导致教育难以普及,而教育落后又使国家政策得不到有效贯彻。在他看来,要推行乡村防疫,首要问题是强化乡民组织。另一位乡村建设派领袖晏阳初也指出,乡村问题集中表现为“愚、贫、弱、私”四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四种教育入手,即: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教育。其中,“弱”是指大多数民众身体不健康,毫无卫生观念,其“生命的存亡,简直付之天命,所谓科学的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到”。如何扭转这种不利局面,晏氏认为关键工作有二:其一,是普及乡村卫生防疫教育,改变乡民对传染病麻木不仁的现象;其二,完善政府卫生防疫职能,创建农村医药卫生制度、普及公共卫生,削减农民医药开支,以保证每个乡民“都有受得科学医药治疗的机会”。(24)
1929年9月,晏阳初等人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实验区设立卫生教育部,聘请卫生专家担任顾问委员,组建地方卫生委员会,研究“中国乡村卫生实施之方法”、以促进“民族之健康”。晏氏所以选择经济贫困、人才匮乏的定县作为实验地区,其目的是想在此探索出一种“可为中国普通各县所能采取”的“治疗与预防同炉共治”的新型乡村防疫模式,进而向全国推广。他们遵循的原则大致有五。其一,将卫生防疫工作与平民教育运动相结合,并“与其它部分之工作互相连锁,打成一片”,以求收到系统效应;其二,采取政府主导、社会互助方式来实施“政治化医学”,以求全面普及医疗事业,力争尽快摆脱“有钱治病、无钱待死”的窘境;其三,重点落实防疫宣教工作,以造就乡民的“社会公共卫生之良心”。非遇特殊情况,一般不采取强制手段落实防疫措施,以避免产生“一时成功较速,然不能有深久之影响”的消极局面;其四,根据当地经济文化状况,从关乎当地切身利益且具体可行的小事做起,然后再循序渐进;其五,根据当地乡村经济状况,实施有偿卫生服务,让人们“出价得之”。
2.具体措施。定县乡村防疫工作内容主要有三。即:普及传染病预防工作、推广疾病治疗方法和培训乡村卫生人员。传染病预防工作包括环境改良、防治传染病、增进营养、体格训练及举办公共体育运动等。推广疾病治疗方法包括收治入院病人、随时出诊、巡回诊疗及农村救急等。培训乡村卫生人员,主要通过举办特别训练班,采取就地取材方式,培养卫生视导员、临床护士、卫生调查员、接生婆、农村救急员及学校卫生教员等专门人才。
(1)防治天花。20世纪初,疫苗注射法对防治天花、白喉等烈性传染病的疗效已十分显著,许多城市在推广该法后,不少烈性传染病基本被遏制。但在广大乡村形势仍非常严峻。定县预防天花沿用的是旧式种痘法,该法危险性大,成功率不高。为扭转这种局面,晏阳初等人筹集经费,延聘专门人才,开办种痘人员培训班,将受训人员派到乡村去普及种痘。但是,由于风气未开,乡民对此有顾虑,特别是年轻妇女。为化解民众猜疑,乡村建设成员先在平民学校宣传,接着开村长会议,“晓以种痘意义”,由他们带头引种,以作表率。为收普及之效果,晏阳初等人还联合县公安局、教育局,借助这些部门的信誉督促开展种痘。由于措施得力,全县一月之内就有21,000人接受天花疫苗注射,因无“意外之危险发生”,先前狐疑顿时冰释,免疫注射理念很快为民众所接受。这就为随后实施锡克氏试验和毒素抗毒素混合液注射等先进防疫措施提前扫清了障碍。
(2)推广新式助产。遵循消毒清洁原则的新式助产法,可规避脐带风、产缛热等妇婴传染病。在没有推广新式助产法之前,定县乡村接生工作全部“操于目不识丁的老媪”之手。这些人缺乏产科卫生知识,皆令产妇在土炕上分娩,“以污棉烂布,任意擦拭”,断脐剪刀“从不消毒”,伤口多用土泥敷抹。所以,妇女产缛热、婴儿脐带风“在在皆是”。倘若遇到难产,“非束手无策,即施行极粗劣之手术”,因此送命者不计其数。这种形势十分紧迫,必须尽早解决。乡村建设派确定的初级目标就是力争在每村设一名新法接生员。为此,定县乡村建设实验区卫生教育部令每村派出一至二名略通文字的妇女到部接受为期一月的培训,学习初级“实用接生法与妇婴卫生”常识,结业后再回村承担助产工作。该法不仅经济实用,因为接生员直接来自当地村民,他们有赖以为生的产业,不专以接生维持生计,而且定县还有馈赠接生婆的习俗。所以,接生人员乐于立足乡村、服务乡农。此外,为应付难产、多胎等特殊情况,乡村建设派还在县城开设了为期两年的助产士培训学校,培养高级助产士,用以“料理较难之生产”及指导监督乡村接生工作。(25)
(3)增进民众健康。严复曾说,中国民众多数“顑颔不饱,阴消潜削,乃成羸民,疾疫一兴,如风扫萚,男女老少争归北之邙是也”。(26)的确,健康的肌体是抗御病疫的首要条件,舍此再先进的防疫措施也无济于事。可是,中国乡村多数家庭濒临破产,生活十分艰苦,甚至连基本生存条件也无法正常保障。一位政府官员曾这样评述北方乡民的生活状况:他们的基本食品是米、豆、高粱、小米及其他淀粉食物,蔬菜、大蒜就算富有营养了,至于“牛奶、肉类、鸡卵则为数甚少……作者曾在北方一乡村亲见一家,其儿童无不面黄肌瘦,一望而知为病者。有二周岁之婴儿,望之如有六个月者。此种情形,在我国乡村中极为普遍,皆因营养不足之故也,儿童如此,成人亦然。”(27)乡村建设派的精英们对此亦有清醒认识。他们将推广羊奶作为改善乡民营养的基本手段,建议一家养一只瑞士羊。这样,每日可得四磅羊奶,既可为家庭增进健康,又可“专为儿童及病人之用”,可谓益处多多。据当时研究,1-5岁儿童每两天至少吃一枚鸡蛋,才可以保证身体的正常发育。为此,晏阳初等人积极进行鸡种改良,以提高产蛋量。经过反复实验,新品种母鸡产蛋量提高了二至三倍。此外,为合理搭配营养,同时推广的还有黄豆浆、青菜及水果等。上述做法无需乡农太多投入,就可在农户家中实施。这就为改善乡民饮食状况开辟了切实可行的渠道。
(4)普及卫生教育。为养成乡民卫生习惯,乡村建设派设计了一整套卫生教育方案,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环节入手,指派专人负责实施。家庭卫生教育主要是劝导家长和家庭主妇树立防范传染病意识,不要心存侥幸;整饬茅厕,驱除蚊蝇,保持环境卫生;树立家庭卫生及妇婴保健观念,养成儿童卫生习惯等。学校卫生教育主要是针对学龄儿童及男女青年,向他们传授基本的卫生知识,督促其养成防疫观念,并通过这一群体,影响其所在家庭和周围人群,进而改变乡村社会风气。社会卫生教育一般通过平民学校进行,主要是普及节制生育、夫妻保健等方面的知识,以减少性传播疾病。这些宣教工作对经济、文化水平都极低的内地乡村而言是切实可行,因为它投入少,而见效彰。知识就是力量,它的传播不是“量”的减少,而是“量”的膨胀。普及防疫知识显然是提高乡民防疫意识的一条捷径。
(5)建设防疫保健网。1932年,晏阳初延聘刚在美国获得公共卫生学士学位的陈志潜到定县做农村建设实验区卫生教育部的主任(28)。陈氏在考察后指出,要兴办有效的乡村防疫体系就必须从实际出发,“打破素来国人纯粹抄袭外人之心理……以求得中国环境中创造中国人解决社会问题之方法”。因为中国乡村极端贫困,故推行防疫建设“绝不能求其设备完全,规模宏大”,一切计划“当以最经济之组织,推行最简单之事业”。(29)为达此目的,他们不是等病人上门,而是将工作深入到田间地头,随时矫正乡民的卫生问题,对可能发生的疫情尽早实施干预。不久,晏阳初、陈志潜等人将定县13个村列为卫生防疫试点,推广乡村防疫网。主要措施有三。其一,培训卫生保健员。陈氏认为乡村卫生相对简单,“能用普通人代办者,必须尽量利用之”(30),以减少开支。乡村保健员一般年纪在20-35岁之间,由各村平民学校同学会遴选充任。保健员上岗前要接受短期卫生技能培训,以求胜任常见工作。其职责有宣传卫生常识、实施门诊治疗、推广种痘、改良水井以及转送病人等。其二,建立保健所。该所为管辖数村的区级部门,设医师一人,多由医学院校的毕业学生充任。另外,还聘用护士、工役,协助其开展工作。职责范围有培训监督保健员、日常门诊、推行卫生教育和防治传染病等。其三,设置保健院。保健院有男女医师各1人,助理医师2人,护士8人,药剂师1人,检验士1人。此外,还置总务书记和助理员。医护工作者均是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专门人才。保健院除负责收治转诊病人、主持全县防疫工作及培训保健员外,还与平民教育学校、成人教育合作,向民众普及卫生防疫知识。(31)
由于切合实际,乡村防疫保健网建设推进较快。1935年,定县乡村防疫保健网已发展到6个区,培训村保健员220名,“约覆盖半数的村庄”。保健院收治住院病人600多人,实施手术260例;保健所治疗6.5万人。村保健员每月急救、治疗患者达14万人次,种痘14万人。许多重病患者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天花、黑热病、新生儿破伤风、产褥热等病的威胁”,而是普遍得到及时救治,“各种肠道传染病也大大减少”。1934年华北霍乱大流行,“全县只发生少数几例,没有一人死亡”。可贵的是,防疫保健网人均年经费仅0.1元,成本极低,“即便是比较穷的社区也能承受得起”。(32)由于优势明显,1934年底,卫生署将其在全国推广。
除河北定县外,乡村建设派还在其他县、乡推行过类似的卫生防疫工作。如:1934年,乡村建设派在江西万家埠设立实验区,筹设经费、聘请专家,组建保健所,有组织地向乡民灌输防疫知识,“以减轻疾病之痛苦”,并动员学生组成卫生巡回演讲队在区属各村“巡回演讲”,并翻印发放《传染病之预防及消毒方法》、《夏季卫生要点》及《灭蝇方法》等宣传材料。(33)中华职业教育社在荻山实验乡进行的种痘、疫苗注射及其他公共卫生活动都成效显著。(34)此外,梁漱溟在山东菏泽、邹平等地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亦开展了较全面的卫生防疫工作,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从乡村建设派的良苦用心看,他们是多么希望改变日益濒临破产的乡村社会呀!从具体实践看,乡村建设派将组织乡民与教育乡民成功地结合起来,使其在乡村建设中相互受益,显然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二)其他社会力量
除乡村建设派之外,还有一些知识精英及社会团体热心于乡村防疫事业。
1.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五四”运动后,多数知识精英认为,改造国民须从改造国民卫生习惯入手,因为“优良的卫生状况是社会生命力的来源”。1932年8月,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北平市公安局及宛平县士绅设立卫生事务所,置卫生股,着手卫生实验,次年,募集社会资金创建乡村医院,加大了免疫注射、整饬环境清洁、推广新式助产法以及医疗施诊等工作的力度。所有这些大都得到了各界的理解与支持。以整饬街道环境为例,就是由当地商会提供资金支持,区公所负责运输,军政部织呢厂供给灰料,东北军某旅部负责修筑,一星期即告竣工。为维持日常卫生,商会还出资雇用了保洁员,专司其职。(35)
为唤醒村民卫生防疫意识,卫生事务所派出护士深入乡村进行“家庭拜访”,发放防疫图画、传单。此外,社会学系还与宛平县合作,仿行北平乙种学校卫生制度,在乡镇小学推广诊治疾病、身体矫正、卫生讲演及预防注射等活动,收效也不错。1932年,夏季卫生运动大会在县城召开,商会、驻军、公安分局、镇小学及当地绅士名流均派人参加,会后举行街道扫除,分发标语,以营造重视卫生防疫的舆论气氛。(36)
2.齐鲁大学乡村服务社。1930年前后,齐鲁大学在章丘县龙山镇就已设立诊疗所1处,易文士医生每周两次到诊所视察疗治。易医生服务热情、技术高超,深受广大乡民欢迎,一年时间治疗2,711人次。这为扩大科学防疫思想在乡村的影响创造了条件。不久,齐鲁大学医学院、理学院还与省民众教育馆合作,在该地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公共卫生运动,向村民宣传卫生防疫知识,活动深受乡民欢迎,“结果非常圆满”。此外,齐鲁大学生物系还在龙山附近作蛔虫、钩虫等肠道寄生虫的实地调查,以便找出问题症结,拿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尽早为乡民解除病疫困扰。
3.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合作成立乌江县农业推广实验区,下设卫生组,负责防疫,具体工作包括外出宣传、预防注射、产婆培训、婴儿健康比赛、训练理发匠、街道清洁及赠送苍蝇罩灯等。其中,婴儿比赛安排在圣诞节期间举行,比较引人注目。卫生组将1-8岁的儿童按年龄分成8组,进行比赛,每组取前两名,各奖锦旗一面,其他参赛儿童也有相关奖品,“所费仅数元,参观来宾约二千人”,颇具影响。另外,针对该县儿童秃顶多的现状(比例高达20%),卫生组展开深入调查,研究发现秃顶主要是由头癣、头癞等皮肤病造成的,此类病大多由“理发匠所用之刀所传染”。为扫除此类传染病,实验区特地举办理发师培训班,规范其操作行为,以免再殃及无辜。(37)
结语
中国乡村自晚清就开始走向解体,乡村社会无序状况日益加剧,教育、规范民众行为已变得十分困难。而卫生防疫又是一项群众参与性很强的近代化事业,只有调动起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易感人群,构筑更为安全的隔离带,从而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政府是动员并组织群众的基本力量,倘若其参与力度不够,则必然会影响卫生防疫事业的深入和发展。我们知道,政府社会职能的运转是以财政为依托,内忧外患的处境使国民政府长期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内职能的履行。资料显示,国民政府的卫生行政职能在城市实施已经显得十分勉强,至于农村则是无能为力。在此种情况下,一些关心民族未来和前途的知识精英,放弃城市的安逸生活,坚持深入乡村,以先进的防疫思想和手段来拯救濒临破产的乡村社会。这就为推广乡村防疫事业开辟了又一途径,从而弥补了政府行为的某些不足。与吃财政饭的“士大夫”集团不同,体制外的“士君子”群体致力于乡村防疫事业依据的是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们更多的是取自“义”。不过,二者仍可以协调一致,一面一点,共同推动了乡村防疫的进程,进而形成了“政府—社会”间的良性政治互动。这是近代中国的新现象,为传统社会所罕见。
传统观念认可“以吏为师”,“士人”(知识阶层)的言谈举止对普通百姓的日常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五四运动后,不管是在朝的“士大夫”,还是在野的“士君子”,他们大都开始以国民身份自居,热心倡导并积极推行卫生防疫的新理念和新手段。这对开启民众观念,树立防疫新风尚以及发展完善乡村卫生防疫事业是有着促进作用的。随着具体实践的深入,到1930年代初,中国乡村形成了以政府防疫为主,精英试点为辅的乡村防疫格局。
考察民国时期防疫建设给人的启示是深刻的。越是近代化水平高的事业越是需要社会成员的普遍参与,不然只能事半功倍,枉费心机。瘟神是人们的共同敌人,抗御传染病,营造一个安全的生产生活环境是绝大多数人的一致愿望,亦是共同利益所在。现代防疫手段彰显出的科学精神一经实证,是很容易为民众所接纳的。所以,乡村卫生防疫事业的推进没有像废科举、兴学堂、倡民主、鼓自由那样在社会上引起太大争议和波动,原因就在于此。中国要走向近代化,实现社会转型,必须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模式。消化吸收这些源自国外的先进成果并不是由某些人或某些群体的主观意愿所能决定的,而是需要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某些利益集团的政治胸襟。那些符合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现实利益的急需事物往往比较容易进入人们的视野,并较快推广开来,正如这乡村防疫事业。
注释:
①(13)《申报年鉴》1936年,申报馆售书科1936年版,第1293、1293-1294页。
②③④⑥(12)(27)李廷安著:《中国乡村卫生问题》,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7、4-5、64、39-40、序言、10页。
⑤⑦⑧⑨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行政院公报》第34册,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443、443-444、444-445、446、446-447页。
(11)吴小龙:《卢作孚的思想遗产》,《博览群书》2003年第9期。
(14)(17)(19)(33)(37)《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载《民国丛书》第4编第16册,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371-372、368、270-271、431-432、527页。
(15)(21)《江苏省政述要·民政·社会行政(1933年10月—1936年9月)》,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97辑,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第52-53、50-51页。
(16)(18)(29)(30)章元善、许仕廉编:《乡村建设实验》第2集,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359、215、460-461、464页。
(20)(28)(31)(32)《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6集,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51、641、645-467、64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4页。
(23)《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67页。
(24)晏阳初:《中华平民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载乡村讨论会编:《乡村建设实验》第1集,中华书局1934年版。
(25)《大公报》1931年7月23日。
(26)严复:《如有三保》,胡伟希选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版。
(34)(35)(36)乡村工作讨论会编:《乡村建设实验》(第1集),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88、85-86、118-1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