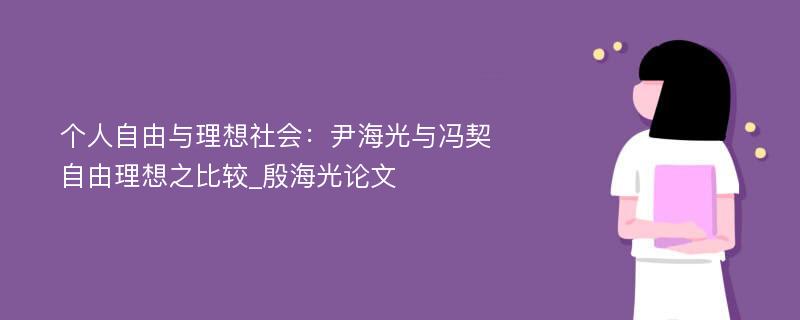
个人自由与理想社会——殷海光与冯契自由理想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想论文,自由论文,社会论文,殷海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后五四”人物的现代哲学家殷海光和冯契,都曾经是现代哲学家金岳霖的学生,但是他们二人的政治理想、学术取径十分不同。在政治上,一个选择了国民党,一个选择了共产党;在学术上,一个选择了西方现代经验学派的自由主义,一个选择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最终都把自己的学说归宗到对自由问题的研究上面,成为本世纪50年代之后海峡两岸关注自由问题的典型哲学家。从表面上看,殷海光选择了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曾极力地批评共产党政权下的社会主义理想,其社会理想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冯契的社会理想应当是水火不相容的。然而,从他们二人晚年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及其致思原则来看,却有可以通约之处:那就是理想社会必须建立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使个人尽可能地在社会中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与独特性。本文正是试图通过对这两位思想个性极不相同,学术取向颇具差异的思想家有关自由理想的可通约性的比较,来探索当代中国自由理论的建构工作,希望从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启示。
一、“健全的自由”——殷海光的自由理想
作为“后五四”人物的殷海光,一生皆以自由为宗,但他所追求的自由与“五四”时期所强调的“外在自由”颇不相同,这种自由一方面带有一定的经验主义色彩的理性自由特征,另一方面又带有传统士大夫的精神超越气息。特别是晚年在思想上部分地认同了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质,又亲眼目睹了现代西方文明的种种缺陷之后,殷海光对自由的认识则更为圆融,在继续强调“外部自由”,坚持对各种“镇制”制度进行无情批判的基础上,稍有偏重地对“内部自由”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其自由思想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从否定性的角度来认识就是:既不完全是经验主义学派自由观的中国版,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特别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们所强调的内在精神自由,而是立足于现代文化基础之上反观现代文明弊病之后所提出的一种“健全的自由”观。从肯定性的角度来认识就是:反对一切形式的“镇制”,努力使人处在一种既无暴力威胁、经济胁迫,又无任何意识形态专制的社会之中,使人能充分地展示自己有正面价值目的的和可控制的创造性。这就是殷海光本人所说的“现实化的自由”。
一些谈论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的文章,都特别注重他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关系而比较忽视他个人的创造性一面,这是失之偏颇的。实际上,他对“现代神话”的批判,对个人精神自由内涵的深度开掘,对自由的伦理基础的探讨,已经逸出了经验主义学派有关自由认识的精神视域。由于他对现代西方文明弊病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再加上周围的朋友和学生的影响,促使他把眼光投向了传统,力求把西方自由思想与中国传统中所蕴涵的自由精神结合起来,在继续批判各种“镇制”对自由的压抑的同时,稍稍地把中心偏向了对个人“内在自由”的关注,十分强调“内在自由”的价值。这与其中年特别强调外部自由的思想稍有不同。在《自由的伦理学基础》(1965年)一文中,他十分重视对人的内在力量的培养,并且把这种内在力量与“孔仁孟义”结合起来。他说,这种“内在力量”“可以是孔氏的仁,可以是孟氏的义,可以是佛家慈悲。”(《殷海光论文集》(二),第784页)他甚至这样说:“问题逼到最后,如果人对生死问题有所透视因而对死亡无所恐惧,那么任何镇制手段都会失效。这样,极权制度就会冰消瓦解。”(同上书,第785页)这种过分地看重个人“内在力量”或曰自由意志的思想,显然与正宗的经验主义派所强调的对生命的保障和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思想的看重是有所出入的。但这种“内在自由”恰恰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人格思想在现代中国自由思想家中的延伸。
为什么晚年的殷海光如此地关注“内在自由”的问题?这要从殷所处的时代环境中寻找答案。殷认为,“处近代以降,许多新出的因素腐蚀着一般人的这种‘内在力量’,许多利用‘人的弱点’来建造权势的投权人物,斫丧着人的这种‘内在力量’……使千千万万的人无个性地溶解在一个大的集体里面毫无保留地供其鞭策。”(同上)正是由于自由主义所面对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专制的形式发生了变化,故尔自由主义者的言语中心也会发生变化。殷氏说道:“世变推移所及,真是洪水滔滔,满街都是失落人。”现代社会利用一种“正面”的形象来掏空人性的内涵,使“启蒙时代”以来所追求的“个性”变成空壳,所以殷海光在继承经验主义关注“外部自由”的思想传统的同时,特别地关注了人的内在自由问题,在反对各种政治极权的同时,用相当浓重的笔墨来反对现代社会文化中的各种“镇制”力量。这是正宗的经验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所不太注意的(当然约翰·穆勒曾经注意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统治的问题,暗涵了对现代大众文化专制的批判内容),但却又是现代自由主义者所必须加以关注的现实问题。殷海光对此问题的关注,既表明了他的自由思想的个性化的一面,也恰恰反映了自由主义思想自身的一个优点:那就是具有与时俱进,不盲从先贤,不死守教条的特点。他曾十分痛心地说,保有“自由的个性”的人物,在现代社会成了迂阔而不识时务的人,其结果是自寻苦恼。近代世俗文化在借助自由发展个性的名义之后,已经以另一种方式来背叛“启蒙精神”,在初步脱离了权力的异化之后,又正走向金钱和物欲的异化之中,使人患上了另一种“道德贫乏症”。正是为医治这种“道德贫乏症”,殷才特别强调“内在力量”,企图以此来挽救现代人的堕落。
由此,殷海光把“内心自由”看作是“一切自由的起点”。他认为,从道德意义上说,“所谓‘内心自由’即是我们的道德主体意志克服了人的欲念。……推而广之,人要得到自由,必须克服他自己,让自己作自己的主宰,而不‘随尸壳子起念’。这便是中国传统所谓的圣贤工夫。”这种话,如果单独地拈出来看,仿佛有某种程度的禁欲主义倾向。实际上是殷海光为了强调“内心自由”重要性的一种合理的逻辑引申。因为自由的本质意义绝对不应该含有把人变成动物的自由这一层意义,他只应该是指人提升自己的人性以进乎神明的不断精进的行为及其过程。
关于内在自由或曰内心自由的说法,殷海光有时又把“内心自由”称之为“开放心灵的自由(Freedom of open-mindedness)”或曰“心灵不作囚徒的自由”。在他看来,要达到心灵自由的境界,在认识的层面上往往是比较困难的。他说:“一个人想要他的身体不作囚徒浅而易行,想要他的心灵不作囚徒则非有超越他的时代和环境的才识及训练不可。一个人要看布在海边的铁丝网只需一瞥即可,一个人要发觉被布置在他头脑中的铁丝网,一定得做许多聪明的反思。”按照传统的“知行合一”的理论来看,即使是能发现头脑中的铁丝网,但要真的逃出这种铁丝网的束缚仍需费一番工夫。因为,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囚徒的生活。特别是在深厚的专制文化传统中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多人更是具有这样一种“身心软骨综合症”的特征,有时即使是发现了这种“铁丝网”也无力去冲破,更有甚者还要对这种生活加以美化。由此,我十分赞同殷海光的这种说法:“我们要发现心灵的牢房则是一件很费力的事。而且,即令费了很大的气力发现了自己的心灵牢房,有勇气‘逃离牢房’而别建新屋的人则少之又少。在风雨飘摇之秋,中国文化份子一般地是依恋他们住惯了的心灵牢房。”(同上书,第772页)
为了使心灵获得自由,砸碎这种心灵的牢房,殷氏仔细地辨析了这种牢房的特征。他把这种牢房分为两种:“一种是未经批评的崇古”,“将古人无条件地奉若神明”;另一种是“时代的虐政”(tyranny ofthe time)。对这两种牢房,殷氏都给予了猛烈的批评。这种批评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就思想的现实性来说,后一种批评其意义尤为重大。因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反对崇古的思想潮流比较强劲,此种牢房不再构成对当代知识分子心灵的威胁。最能构成威胁的则是“时代的虐政”。正如殷先生所说的那样,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特别地“崇拜权利”,除此以外,别无所好,“于是无论什么无根之谈,只要强力推销,总会有市场的。那些挟威力以俱来的口头禅,可以禁锢人心,横阻了一切理知的追求和客观的讨论。就中国来说,半个世纪以来,一阵又接着一阵的‘意见之风’,从根儿上拔起了真理的幼苗。”(同上书,第773页)要抗击这种“时代的虐政”,就必须依赖人的内在自立精神。而这种自立精神和内在思想的自由正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根本优势。面对现代社会人的“内在自由”精神丧失的现象,殷海光十分痛心地说:“人的视力不及飞鹰,体力不及水牛,善走不及奔兔。可是,人脑的会思想,则是已知的一切动物所不及的。……然而,人把最精彩的这一部分装进各种各样的牢房,减低思想的效率,甚至使它失去作用。这种损失实在太大了。极权制度更把人的思想之流筑起堤坝,强迫千万人的思想从一个观念出发,照权势规定的方向,流向预定的目标。由此造成的损失,不止残害一代的人。”(同上书,第773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殷海光的自由思想是有自己的个性特征的,他的自由思想并不简单地就是经验主义自由思想在中国的现代翻版。
以上,我们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揭示殷海光的自由思想的个性,突出了其“内部自由”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殷海光不重视外部自由,甚至忽视“外部自由”的重要性。事实上,尽管殷海光十分强调内部自由的重要性,但他丝毫没有忽视外部自由的意思。在讨论内部自由与外部自由的关系时,殷海光说道:“心灵自由(内部自由)是自由的起点,而且没有‘心灵自由’就没有‘外部自由’。可是,由此推论不出,有了‘心灵自由’就有‘外部自由’。”(同上书,第774页)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心灵自由’不是‘外部自由’的代用品,而且也不能是。”“我们不可能在一个‘运动’里训练人的‘心灵自由’。”(同上书,第774页)但是“内部自由”如果没有“外部自由”保证,则“这种内心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萎缩的自由”。(同上书,第774页)这种自由至多只是一种“自全的行为”,像道家所追求的“全生保身”的消极自由。而“当着一个时代的人为‘外部自由’而奋斗但情势不利时,唯心的哲学家板起面孔责备大家浮动,劝人要追求‘内心自由’,这是一种冷血的逃避主义。”由此可见,殷海光一点也没有轻视外部自由的意义。他对中外古今一切专制政治的批判,就是他追求“外部自由”思想的表达(此点我们将放在后文再说)。本文只是为了揭示殷氏自由思想的个性才着重论述其对内部自由关注的一面。通观殷海光本人有关个人自由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就是追求一种健全的自由才是他自由思想完整的表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是:“自由必须从内心起始,从各个角度并以不同的程度,投向人生的实际生活节目。这就是自由的现实化。有而且只有现实化了的自由,才是健全的自由,我们所追求的自由,应须是这种自由。”(同上书,第775页)
二、“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冯契的理想人格
80年代以后,冯契是大陆学术界比较早地谈论人的自由问题的哲学家之一。冯契的自由思想除了在学术渊源上与殷海光不同以外,另一方面的重要差异是:冯契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谈论人的自由问题。但是,其理论的最终落脚点却是个人的自由,且是大多数平民的自由。这就与殷海光自由思想的努力方向有了“殊途同归”之妙。
冯契的自由观是与他整个哲学体系所追求的“转识成智”的“智慧学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使人在面对自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时变得更智慧些,从而使人在自然和社会之中变得更自由些。这种自由理想主要表现在他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价值追求之中。何谓“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呢?冯契是这样界定的:“我们现在讲自由人格是平民化的,是多数人可以达到的。这样的人格也体现类的本质和历史的联系,但是首先要求成为自由的个性。自由的个性就不仅是类的分子,不仅是社会联系中的细胞,而且他有独特的一贯性、坚定性,这种独特的性质使他和同类的其他分子相区别,在纷繁的社会联系中间保持着其独特性。”(《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第320页)这一“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与古代的圣贤人格、英雄人格都有所不同,具有这种人格的人不是全智全能的圣人,而是普普通通的人,他有缺点,会犯错误,且不承认人有终极意义的觉悟,不认为人能拥有绝对意义的自由,而只承认人在性与天道的交互过程中,不断地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从而获得人的自由。因此冯契的自由观,主要是从哲学认识论角度来谈人的自由问题,不像殷海光既从伦理学,又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谈论人的自由问题。他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也可以说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谈论人的自由问题。他认为:“人天生并不自由,但在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的过程中,人由自在而自为,越来越获得自由。”(同上书,第12页)因此,在冯契看来,自由之于人而言并不是一先天给定的东西,换句话说,人的自由不具有本体上的意义。如果有人一定要把人的自由个性上升到本体的高度,那就必须将其限定在人所创造的价值领域里或在“我所享受的精神境界中”;当且仅当“‘我’在我所创造的价值领域里或我所享受的精神境界中是一个主宰者。‘我’主宰着这个领域,这些创造物、价值是我的精神的创造,是我的精神的表现。这样,‘我’作为自由的个性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但是,这种本体不是说“‘我’成了同物质一样的本体”(同上书,第320~321页),因为人只有在“精神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自由”。这样,冯契就把人的自由问题限定在一个历史的过程之中,并且也突出了自由的精神性的意义。而也正是在后面这一点上,殷海光所强调的“内部自由”一面在精神气质上与冯契有了可以沟通之处。因为,从本质上说,冯契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理想,恰恰偏重的是人的内在精神自由。
由于冯契所继承的思想传统和他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殷海光有较大的不同,其“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理想所要集中批判的对象是古今的一切权威主义、独断论思想和现实中兴起的拜金主义。从精神气质上说,冯契继承了“启蒙哲学”的理性主义思想传统和人道主义精神,同情广大下层民众的生活。他深深地感到,初步摆脱了权威主义影响的广大市民阶层,在新的拜金主义思潮面前面临着重新沦为金钱奴隶的危险;而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由于“文化大革命”灾难深重的影响,历史上的权威主义、独断论的阴影仍在徘徊,广大的平民阶层如何培养自己独立的人格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何在权威与金钱面前保持适度的张力,将是每个平民所要解决的重要人生问题。但是这种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不是高不可攀的圣贤人格、英雄人格,而是基于人类平等和彻底解放的理想而建立的一种适合普通大众的理想人格。这种人格具有独立不苟的道德精神,具有批判现实和世俗各种流行观念的思想能力,因而也是一种开放的人格。就此意义上说,“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与殷海光所追求的“开放自由的心灵”恰好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立足于自由理想而对现实展开的批判
尽管殷、冯二人的自由思想资源不同,理论旨趣各异,一个偏重于对专制及各种现代极权主义政治的批判,一个偏重于自由理论的哲学探讨,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都立足于人的自由之实现的理想而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妨碍人的自由的东西进行了批判。
(一)殷海光对极权政治与镇制制度的批判
殷海光特别重视康正的个人自由。他把具有这种自由特性的个人看作是社会的“最后原子”。在《自由的伦理学基础》长文中,殷氏这样说道:“个人是最后的社会原子”,“一个人不能分开,不能分成几个人。个人不是一个抽象项(abstractum)。社会中感到苦和乐的最后单元是个人。有而且只有个人才知道国邦的光荣或耻辱,构成文明,尊重价值,尤其是创造伟大思想的是个人。”(《殷海光论文集》(二),第754页)殷海光甚至这样说:“在这个地球上,个人的自由愈大,则文明的程度愈高。”(同上书,第754页)“个人自由”程度的高低就成为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尺。正因为对个人自由的无比重视,并力求使这种自由在现实中得以展开,殷海光对中外古今的一切“镇制”的行为和制度,给予了系统的、有力的批判。他是这样说的:“自由的最大克星是镇制。如果没有镇制,那么自由就不会发生问题。”(同上书,第775页)那么,什么叫“镇制”呢?殷海光是这样界定的:“镇制是镇制者所施展出来的一种力量,或藉力量所布置出来的一种蛛网状的形势,使被镇制者不得不随着镇制者的意向作反应。”(同上书,第777页)出于对个人的自由的珍视,殷海光仔细地研究了各种“镇制”形式,他把古今中外的“镇制”分为三类:一是赤裸裸的暴力,二是各种神话力量的控制,三是经济。所谓赤裸裸的暴力乃是指“单纯物理能力”,如“巨棒打得人发痛,刀砍在人身上致死,子弹打来人倒地,一按按钮整个城市化为废墟,都是单纯的物理能力。”这种“单纯的物理能力自古即构成镇制的基础。”“经济从生物逻辑上构成镇制,受到这种镇制的人可以经常在生存的威胁之下,甚至基本生存完全失去依凭,以至于未流血而死。”(同上书,第781页)
在对这三种“镇制”的分析中,殷海光对神话控制的分析最具启示意义。他把“神话”概念泛化,把一切通过意识形态和观念的方式统治人的思想并束缚人的行为的统治方式都看作是神话控制。上古利用“自然神话”,中古利用“君权神话”,近代以来则用主流的意识形态。而他对现代的意识形态神话的批判特别深刻。他说:现代神话“从心灵上构成镇制,这种镇制力可以使冒犯的人感到自卑,感到孤独,感到心神震动,以至于不能自持。”(同上书,第781页)
尽管这三种“镇制”的作用、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孤立的,“暴力、神话、经济可以交替使用。”从而构成一种“镇制”的网络。
应当说,殷海光对“镇制”的批判是比较深刻、有力的。在吸取了哈耶克等人的思想的基础之上,亦有他个人的一定的发挥。那就是他的自由思想比较详细地批判了一种“镇制”制度,而不仅是对一种主义或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不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则有一定的误解,把现代以来的教条化、简单化的伪马克思社会思想当作了马克思思想的本身。但我们正可以从这种误解的批评中好好地反省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的过失,为实现并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作出努力,并从中找到现代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形态的沟通之处,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真正成为融全人类所有文化精华的理论体系。
(二)冯契对拜物教与拜权教的双向批判
与殷海光的生活背景和面临的现实问题不尽相同,冯契从“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角度出发,主要是对生活中仍然存在的权力崇拜和金钱崇拜现象给予了深入的批判。他首先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指出了人“异化”的原因。他说:“异化的力量,从社会发展史来看,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基于人的依赖关系的权力迷信,另一个是基于对物的依赖关系的拜金主义。”(《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第241页)这种“异化”力量,在当代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负面作用的诱发,在一些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其害的冯契,正值又看到了市场经济之初部分中国人的种种异化现象,对此率先从理论上给予了深刻的批判,成为大陆上较早系统地谈论人的自由问题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没有仅仅停留在表象上来批评当代中国人的异化现象,他认为,由于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特别擅长权术,阳奉阴违,使得很多人根本上无人格可言。“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沿袭了这种不好的传统,败坏人们的道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助长人们的权力崇拜心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一些人又滋生出金钱崇拜的心理,沦为金钱的奴隶。针对这种新的情况,冯契提出了培育“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理想,以抵抗现实社会对人性的扭曲。尽管冯契没有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批评现实生活中种种阻碍人的自由的势力,但他由对现实中的异化现象的批判,并上升到对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教条的批判,则是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的。他认为,一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为人目的”,“有一个很根本的观念被忘记了,共产主义事业正像马克思说的要‘由于人’和‘为了人’。这个事业要通过新人来建设,而且这种建设是为了使人成为新人。”(同上书,第309页)这些人忽视人的价值,从而也就忽视对人的教育,“忽视提高人的素质”,这种行为其实“是对民族犯罪”。(同上书,第309页)这种批判既显示了作为哲学家的冯契具有超人的胆识,但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当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学术自由气氛。这一批评言论的公开发表,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这一事实的存在,则从另一侧面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正在努力纠正教条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违背马克思原义的错误做法,努力地使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具有生命的活力。而且也表明社会主义不一定就要与自由理想* 相悖。冯契对当前中国大陆社会的批评是极具针对性的,而且也具有相当强的前瞻性,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四、一种通约性之探寻: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自由观之沟通——当代中国自由理论建设之思索
在现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等人极力反对在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寻求沟通的今天,我仍然在冒险地寻求服膺个人主义自由观的殷海光和信仰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冯契之间,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自由观之间的沟通,似乎有点不识时务。然而,在我看来,结在近代人道主义之藤上的两大思想硕果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不同,但在追求个人自由和理想社会的价值目标上是一致的。正因为这种价值目标上的一致性,使得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了方法上的可互补性,也使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划出了一条深广的鸿沟。正是基于这一基本理由,使我产生了要将殷海光与冯契,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进行通约之寻求的研究企图。殷海光与冯契有关自由之论述,其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异既是两个思想家个人价值取向、人生信仰的不同,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差别的具体表现。今天,我们应当在学理层面对自由作点深入的研究。我们应该追问,为什么信奉自由主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民族问题上并不坚持自由主义的原则?他们的国度内为什么有较大的贫富悬殊?为什么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都走过了集权主义政治时期的弯路?公有制的经济为什么没有高效率?摆脱了经济剥削的广大工人、农民并没获得马克思当初所预想的自由?我在此仅把问题提出而暂时还没有能力给予回答。
众所周知的是:马克思以后的自由主义者,不管其学术立场如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极力反对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尽管他们反对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观点又有差别,但都一致地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剥夺了个人的财产,从而在根本上剥夺了个人的自由。由于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简单化甚至是歪曲性理解,以及毛泽东晚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摧残,使得社会主义的名声扫地,也扭曲了人们心中有关社会主义理想的形象,致使人们忽略了社会主义思想在近现代社会变革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今日的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超越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的毛病,除了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逻辑在起作用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得力于社会主义者的有力批评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纠正。没有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就很难有今日国际社会之间的平等与和平的思潮。(此观点受顾准的影响。)在这一方面,自由主义的建树是甚少的(尽管自由主义在这方面也有论述,如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一书中对此就有较详细的论述)。但是,自由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种种过失的批评也是深刻的,对社会主义的一套经济制度能否保障人的真正自由的怀疑也是有深刻启示意义的,但这一切仍不足以否定社会主义理想及其制度存在的价值。认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必然会导致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并无学理上的根据。而且,我们也不能把斯大林的过失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身,不能简单地就把他说成是超法西斯主义。更不能把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失误完全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这里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在起干扰作用。
殷海光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批评基本上师承哈耶克等人的思想,他说:“近代共产主义者鼓动人众不分青红皂白,成就大小,以及能力强弱,盲目要求平等,这根本是替自己的嫉妒心找安顿。近代共产党人之鼓吹平等,完全是利用大家的盲目的不满之情绪,掀动下层分子翻身。”(《殷海光论文集》(二),第759页)而共产主义的所谓“经济平等”的建构,“则可从墙脚下把自由控空。”(同上书,第761页)这些批评并没有完全切中共产主义理论的要害,但他对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失误的批评则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且,这种批评与马克思主义者冯契对教条马克思主义“忘记人”的行为的批评有殊途同归之妙。这种奇妙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说成是一种思想的巧合,而应该看作是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终极价值理想与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理想有一致之处。这种致思原则上的共通性,就在于自由主义者殷海光与马克思主义学者冯契,都把个人自由与社会理想紧密地结合起来了,都把个人自由的实现看作是理想社会的标志。如殷海光说:“在近代文明自由开放的社会里,每一个人享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每个人能够无虞威胁地表达他的意见,……一个文明、自由开放的社会之造成和进步,是靠在光天化日之下实现的。”(同上书,第764页)冯契说:“个性要全面发展,同时要求社会制度能够实现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统一。要有这样的制度使人摆脱对人的依赖和对物的依赖。争取这样的社会条件和争取个人的全面发展是统一的。”(《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第326页)殷海光认为:“把人当人”是“自由的伦理学基础”。冯契在谈论自己的智慧学说时则说:“应该把人当作目的,当作一个个独立的人格,这样才能自尊无畏,同时也尊重别人。没有这个出发点,便不可能真正了解别人。”(同上书,第202页)他甚至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来谈论每个个人的价值。他说:“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entity)是个体,而不是殊相的集合。这样的个体是有机的整体,是生动发展着的生命,是具有绵延的同一性的精神。”(同上书,第203页)事实上,殷海光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持肯定的态度。他说:“近世以降,马克思等人所讲的经济史观及社会主义搅起的气流,至少间接地使‘资本主义’的‘劳工阶级’的生活获得相当的改革,社会地位获得普遍的提高。”(《殷海光论文集》(二),第779页)因此,我们并不能完全地把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就自由主义所具有的人道主义的态度这点来说,* 他们的思想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有相通之处。就殷海光本人的自由思想来看,就他一再强调个人的“内心自由”,强调对现实作独立的思考和不间断地批评的精神来看,其自由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精神亦是相一致的,因为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就是对现实作不间断的批判。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殷海光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冯契二人在有关自由的问题上的论述有某种程度的重合现象,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实际上,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可以在多方面沟通。首先,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它成为一个静止的教条,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一劳永逸的规则。”(哈耶克:《到奴役之路》,1997年中文版,第24页,王明毅、冯兴元等译)这一原则正与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是一致的。其次,还在于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的宗旨是:把个人的自由看作是社会的最高目标。第三,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国际和平主义者,这一点与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理想也十分一致。最后,从其理论的历史来源看,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是发源于近代以来蓬勃兴起的人道主义思潮。
有一点恐怕是自由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历史性误会,那就是把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社会理想看作是对个人拥有财富的剥夺。其实不然,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是要致力于消灭一种凭生产资料来剥削他人劳动的“私有制”,但并不反对个人对财富的合理占有。就其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来说,它是承认按劳取酬的社会分配原则的,这在实际上亦是承认个人拥有自己的财富及其对财富的支配权的。它所追求的是人人都能通过正当的劳动获取社会财富,这种财富正是自由主义者所说的“私有财产”。就共产主义理想本身来说,它正是要消除那种在人身上起生物作用的财产对人的影响,通过社会革命剥夺大私有者的财产,使人们不能凭借生产资料来剥削他人的劳动和自由,使社会财富的占有更加合理,从而使得每个人在真实的社会活动中获得全面地发展自己才能的机会。而就自由主义者来说,则是希望通过人人拥有一定的财产来保护自己的自由。当然,共产主义前期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如何确保公有形式下的社会生产资料不被一些当政者变成自己用以控制其他公民的权柄,这的确是当今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所要认真探讨的重要理论课题(当今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关结点正在此处。我们既不能把像北京首钢公司之类的国有大公司一夜之间变成个人所有的私人公司,也不能确认这一大批国有财产究竟归谁?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属于人民实际上是既属于任何人又不属于任何人,谁来真正关心国有企业呢?)。人民如何才能真正起到当家作主的实际作用呢?用什么样的制度来确保人民对执政党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确保属于人民的财富不被某些人暗中偷走呢?这是当前社会主义改革中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就无法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就无法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就不能用令人信服的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当承认,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如何发挥人的自由创造才能方面,还处在探索、研究之中。但不管怎么说,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不是自由主义的天然敌人,反之亦然。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天然敌人乃是专制主义和各种蒙昧主义。专制的基础是愚昧,专制又产生新的愚昧。因此,无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还是实现自由主义的社会理想,都需要一个开放而讲理的社会,都需要人民具有很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很高的道德素质。建构当代中国的自由理论,应当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当然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之间是有体系性的区别的。但在我看来,这种体系性的差别不是价值目标上的,而只是在实现个人自由的方式方面的方法论体系的差别。共产主义要彻底地消灭私有制度,实现财富公有,使人在社会中免除经济上的被剥削的地位,从而使人获得自由。自由主义则要坚决地保护每一个人的私有财产,使人人都拥有足以免除被人剥削的私有财产,从而保证人在社会活动中的自由。在今天看来,这两种看似水火不相容的理论,其实在价值目标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追求人的解放,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这是一切进步理论的必备内容。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探讨殷海光的自由思想与冯契的自由理论之间的共通之处不是一种穿凿附会的思想游戏。如果说,自由在往昔的社会只是个别人才有资格追求的金枝玉叶,在今天,自由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而且也将是人类永恒追求的最高价值。从最高价值的这一层面来看,自由就是道家理想中的“道”,儒家理想中的仁,佛家理想中的如来,西方一切宗教中对任何民族都一视同仁看待的上帝。准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各种进步理论之间所蕴涵的的内在沟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