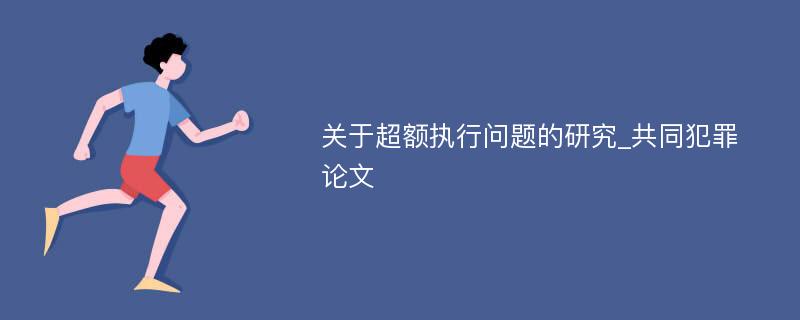
实行过限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2-0058-07
一、实行过限的理论与实践
实行过限,又称共同犯罪中的过剩行为,是指实行犯实施了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关于实行过限,我国《唐律》早就有规定。《唐律》对实行过限虽未设一般性规定,但对于个别罪名则特别明示了处罚原则,例如:《唐律·贼盗》规定:“其共盗,临时有杀伤者,以强盗论,同行人不知杀伤情者,上依窃盗法。”[1](P936)据此,参与共同盗窃而非谋议盗窃者,对他人之临时起意杀伤人,如知情者应负同一责任,如不知情者,仅负盗窃之罪责。国外,不少国家的刑法典中也有处理实行过限的一般原则。如:俄罗斯刑法典第36条规定:“实行犯实施不属于其他共同犯罪人故意之内的犯罪,是实行犯的过度行为,对实行犯的过度行为,其他共同犯罪人不负刑事责任。”[2](P88)泰国刑法典第87条规定:“……但依犯罪之性质,犯罪人仅于其就犯罪结果之发生明知或有预见始负加重刑罚之责任者,其唆使人、宣传人、颁布人或从犯依加重刑罚之犯罪负责,亦以其就犯罪结果之发生明知或有预见为限。”[3](P594)此外,德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在共同正犯之间意思联络不一致的场合,共同正犯者只对故意范围内的行为负责。对过剩部分,除了实行过剩行为的人之外,其他共犯不负责任。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共同正犯对于犯意之联络,应以原计划为范围,对于超越之部分,不负刑责[4](P217)。
和大多数国家的规定相反,《意大利刑法典》第116条第1款规定:“当实施的犯罪不同于某个共同行为人所希望的犯罪时,如果结果是他的作为或不作为的结果,他也得对该犯罪负责。”但在意大利学术界对此多持批评的态度:“刑法典第116条用明确的表述形式规定当实际实施的犯罪不同于某个共同犯罪人希望的犯罪时,该行为应对实际实施的犯罪承担客观责任,即仅仅根据行为和结果的因果关系来认定刑事责任,按此逻辑,一个在外为盗窃犯放风的人就可能为盗窃犯们在房内强奸女主人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种极端严厉的规定实际上是滑向了要求主体为他人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边缘。因为这无疑是将他人起意实施、主观上与主体无关的行为反根据纯粹客观的联系就当作主体所希望的行为来处理。”[5](P332)在意大利,司法实践处理该问题时,一般采取了一种较为缓和的方法,他们认为,如果要共同行为人对某一他所不希望的犯罪承担责任,该犯罪的结果就必须是行为人能预见的结果。
实行过限实质上是一种共犯之间意思联络的不一致问题。意思联络不一致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一方误解了另一方的犯罪意图,例如甲、乙共同对丙进行抢劫,甲只想用一般暴力或仅仅用威胁的方法迫使丙交出财物,而乙却杀害丙之后再获取财物并且认为甲也有这种想法;其二是在实行犯罪的过程中,正犯实行了超出原来预谋的故意的过限行为即实行过限,如:甲、乙商议入室盗窃,甲在外放风,乙入室盗窃中临时起意将女主人强奸。应该说,研究过限行为的目的旨在对共犯正确定罪量刑,即在实行过限的场合,对实行过限行为的责任是由全体共犯共同承担,还是由实行过限行为的实行犯本人承担。
意思联络不一致的情况下各个行为人能否构成共同犯罪,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1)具体符合说。此说认为,如果行为人之间的意思联络不一致那么就缺乏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共同正犯就不能成立,因此对共犯人应分别按其所构成的犯罪处理。(2)构成要件重合说。此说认为,在行为人的意思联络不一致场合,原则上应阻却共同正犯的故意,但如果这种不一致在构成要件上有部分重合,则在重合限度内肯定共同正犯的故意成立。(3)罪质符合说。此说认为,在行为人意思联络不一致的情况下,如果彼此所认识的犯罪有一部分在罪质上相同,那么其罪质相同部分的共同正犯成立。[6](P239—240)
具体符合说因为具有较清晰明确的具体客观标准,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较容易认定,但依具体符合说可能过于缩小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围,导致处理上的不平衡。例如:甲、乙预谋共同盗窃,甲在外放风,乙入室盗窃,但乙在盗窃中被户主丙发现,乙为抗拒抓捕,掏出随身携带的弹簧刀,将丙刺死,由于乙的行为发生转化,故其行为构成抢劫罪,关键是对甲应如何处理。依照强硬的犯罪共同说,甲与乙不构成共同犯罪,但如果否认甲、乙成立共同犯罪的话,那么对甲的行为就无法作为犯罪进行处理。因为若将甲的行为单独认定为盗窃罪处理的话,就要求甲实施了盗窃罪的实行行为。然而本案中,甲却没有实施任何实行行为,但如果不对甲的行为进行处理的话,那么又会出现不合理的现象,即:如果乙在丙处仅实施了盗窃行为,那么甲属于共犯,而乙实际上在丙处实施了更为严重的犯罪,甲反倒不是共犯了。而事实上,应当肯定甲的望风行为对乙实施的抢劫行为来讲客观上是起到了促进作用的。又如:甲教唆乙伤害丙,乙接受教唆后在对丙实行伤害的过程中,因遇丙的反抗一时恼怒而将丙杀死。在此案中,乙超出了共同犯罪故意的范围,实施了过限行为,无疑构成故意杀人罪,而对甲至少也要定伤害罪。依具体符合说的话,就将甲、乙二人的行为完全割裂开来,作为纯粹的单纯的犯罪看待,那么就属于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情况,按照我国刑法第29条2款规定,对甲一般要从轻或减轻处罚。但事实上,乙不仅已经实施了甲所教唆的犯罪,而且实行了比甲教唆的罪更为严重的罪,那么对甲从轻或减轻处罚显然不妥[7](P433)。所以具体符合说明显存在缺陷。
而罪质符合说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具体符合说的刻板呆滞的缺点,给人们处理该类问题时一定的灵活性,但正是这种灵活性却使得罪质符合说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罪质符合说认为,各人所认识的犯罪并非只有在构成要件上相同才能肯定共同故意的成立,而只要在罪质上相同即可。这种认识实际上就是把行为人之间本来存在着的犯不同罪的故意解释为共同犯罪故意,无疑是抹煞了共同故意的质的规定性,随意扩大了共同犯罪的范围。另外何谓罪质相同,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根本不可能会有一种统一的客观的标准。因此在具体的司法操作中势必会带来一定的混乱,故罪质符合说也不可取。
我们认为,相对而言构成要件重合说较为合理。根据我国刑法的概念,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这表明只有二人以上相同的故意实施了相同的犯罪行为才能成立共同犯罪,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当二人以上的故意内容与行为内容完全相同时才能成立共同犯罪。构成要件重合说以部分犯罪共同说(多数学者认为部分犯罪共同说不至于使罪名和法定刑分离,不至于损害构成要件的定型性)为前提,认为二人以上虽然共同实施的是不同犯罪,但是这些不同的犯罪之间具有重合的性质时,则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共犯,这样即使二人以上分别持A罪或B罪,但他们至少在就重合部分的犯罪具有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既然如此,就应根据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认定其为共同犯罪,依构成要件说处理。类似上述甲在外望风,乙入室盗窃后转化为抢劫的案件,处理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甲的行为是乙盗窃行为的帮助行为,乙的第一个行为是盗窃的实行行为,二者在构成要件上有重合部分,在盗窃的限度内有共同的意思联络和共同行为,故甲与乙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甲是盗窃罪的从犯,应当适用刑法总则有关从犯的规定;乙虽然实施了盗窃行为,但其后来由于抗拒抓捕使用暴力将丙刺死,使得行为性质转化为抢劫罪,而不能以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数罪并罚。构成要件重合说从理论上较好地回答了各行为人在意思联络不一致时是否成立共同犯罪的问题。
由于共同犯罪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犯罪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也存在着不少特殊情况,必须结合不同犯罪的具体情况具体加以认定。
二、实行过限的认定
1.组织犯的实行过限
组织犯这一共同犯罪人的种类是苏联刑法学者提出来的,1952年《阿尔巴尼亚刑法典》最早将它在立法上加以反映,随后为1960年《苏俄刑法典》所采用。1996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33条第3款规定:“组织犯罪的实施或领导犯罪的实行的人以及成立有组织的团伙或犯罪集团或领导这些团伙或团体的人是组织犯。”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组织犯的概念,但在刑法理论和刑法条文中都是肯定组织犯的。
一般情况下,组织犯对于犯罪计划中的一切犯罪都是明知的,但实行犯在实行犯罪过程中有时会发生一些超出计划的犯罪的行为,即实行过限。对此英美判例中有这样一条原则,同谋犯对实行犯在实行共同犯罪计划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当然的和可能的后果承担责任,这一原则实际上是把共同犯罪计划和共同犯罪意图划等号,因而过于严厉,带有明显的客观归罪色彩,因而逐步受到限制。此后取而代之的是“可预见原则”,这种原则认为共同的犯罪意图并不是要对一切具体行为都有相同认识,只要求“能够预见”到为执行共同犯罪计划而随时发生的结果。这就是说,共同犯罪意图就是犯罪参与人对由共同策划决定的犯罪行为的基本性质和由该行为基本性质决定的发展趋向方面有大体一致的认识而不要求对犯罪进行过程中的一切具体情节都有相同认识。[8](P158)因此,在英美法系刑法中,对于超出计划的犯罪行为,根据各方面的情况若组织犯的确“能够预见”的话,那么就这些“超出计划的犯罪行为”组织犯要承担责任。
我们认为,“可预见原则”对于我国刑法理论处理组织犯和实行过限问题时是值得借鉴的。我国有学者认为:“如果犯罪集团中的个别成员实施了不是犯罪集团预谋的犯罪行为,超出了这个集团犯罪活动计划的范围,就应当由这个成员单独负责,组织犯对此不负刑事责任。”[9](P385)对此我们不敢苟同。组织犯是共同犯罪故意的肇始者,行为的策划者,是共同犯罪的核心,对整个共同犯罪起着支配制约作用。由于组织犯在共同犯罪中的这种性质,对实行犯超出组织犯组织计划范围的行为,如果组织犯对该实行过限不可能知道,主观上就不存在罪过。因此,组织犯通常只对其组织、指挥、策划范围内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对实行过限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组织犯已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并且至少在意志因素上放任了这种行为的发生,那么他对这种行为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这也是我国构成要件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必然结论。例如甲在组织乙、丙对丁的伤害活动中,明知乙和丁有仇,并且知道乙在情绪激动时容易失控而仍让乙参加,结果乙将丁刺死。毫无疑问,甲对丁死的后果是有认识的,并且又有意放任了其发生,实质是一种间接故意的主观心态,尽管丁的死是一种实行过限,甲对这种加重结果仍应承担责任。
有学者认为,依照我国刑法26条第3款“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的规定,我国刑法典对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定罪采用全部罪行负责说,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就是集团成员所犯的全部罪行之和[10](P111)。基于这种认识,势必得出在犯罪集团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实行过限问题的结论。我们认为,不能将“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同“集团成员所犯的全部罪行”等同起来。二者虽然在多数情况下其外延是一致的,但也不能排除少数情况下的确存在集团成员实行了超出集团犯罪故意之外的行为即实行过限。如果组织犯因不能预见而对此无认识的话,则只能由实行该过限行为的犯罪分子自行承担刑事责任。例如,甲安排乙、丙入室盗窃,乙、丙在得手后又放火将失主的房子烧毁。对乙、丙的盗窃行为甲应承担责任。但对于乙、丙的放火行为,因为缺乏主观上的犯意联络,并且事前也不可能预见,若组织犯甲对此也要承担责任,有违罪责自负原则之嫌。
值得注意的是,组织犯不仅存在于犯罪集团中,而且还存在于一般共同犯罪中。在这两种不同情况中,认定组织犯对“超出犯罪策划外的犯罪行为”是否“能够预见”存在区别。由于犯罪集团的特殊性质,其中的组织犯应是较一般共同犯罪中的组织犯犯罪经验更为丰富,对其他共犯的个人情况、性格特征等各方面因素也更为了解,故对实行犯是否可能实施与犯罪集团所计划的犯罪有密切联系的其他随附性犯罪应有更深刻的认识能力,因此其“预见可能性”明显要高于一般共同犯罪的组织犯。在具体案件中应根据一些实际情况加以充分考虑,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分析。
2.共同实行犯的实行过限
实行犯在大陆法系国家称之为正犯。如1810年《法国刑法典》就使用了正犯的概念。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一般称之为实行犯,现行1996年《俄罗斯联邦法典》也继续沿用实行犯的概念,该法第33条第2款规定“直接实施犯罪或者直接与其他人共同实施犯罪的人以及利用年龄无刑事责任能力或本法典规定的其他情况而不负刑事责任的人实施犯罪的,都是实行犯”。我国刑法典没有明文规定实行犯或正犯,但在条文中还是暗含了并且在理论上经常使用这一概念,“实行犯,就是自己直接实行犯构成要件的行为或利用他人作工具实行犯罪的人”[11](P544)。
实行犯是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行为的直接实施者,在共同犯罪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共同犯罪人的意图的最终实现都要依赖实行犯的实行行为,共同实行犯在共同实施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行为时,当其中的某实行犯所实施的行为超过事先计划,若其他实行犯对此自始至终不知,则应由直接实施过限的实行犯对过限行为负责。例如甲、乙二人商议入室盗窃,二人入室后分别在不同的房间内搜索,乙在盗窃中用刀子将户主屋内的真皮沙发及几幅珍贵油画划破。对此甲全然不知,故对乙故意毁损财物的行为不负刑事责任,这是典型的实行过限,理论上对此并无分歧,认定时应不会有困难。
在处理共同实行犯的实行过限问题时,存在意见分歧的是:当共同实行犯中有人实行过限,而其他共同实行犯知情但未采取任何阻止行动,对此应如何处理?有论者认为“如果其他实行犯当时在场其在客观上表现为作为即积极参与或予以协助,或不作为即不予制止,袖手旁观,从而对实行犯产生精神支持或鼓励,对被害人形成心理压力或恐惧,说明其在主观上处于积极追求或放任的态度,这种行为属于临时起意的共同犯罪,不属于共犯过限。凡参于实施的实行犯都应承担刑事责任”[12](P43)。我们认为,若其客观上表现为积极参与或予以协助时属于临时起意的共同犯罪行为,这一点是合理的。但如果共同实行犯中的某一个实行犯临时起意实施了超出共谋范围的犯罪行为,其他实行犯虽然知情,但并未参与,但因其在现场而对该实行犯产生精神支持或鼓励,对被害人形成心理压力或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实行犯是否对该超出共谋范围的犯罪行为负担刑事责任呢?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例如:甲、乙二人共谋强奸妇女丙,在强奸行为完成后,甲临时起意,在未同乙商量的情况下当着乙的面将丙杀死,对甲应成立强奸罪与杀人罪数罪并罚,但对乙如何处理,乙是否应当对甲的杀人行为承担责任呢?对此,我国有学者认为,在上述案件中“甲的杀人虽然是临时起意,但乙对此并非全然不知,而是明知甲会将丙刺死,但却采取了一种容忍的态度,因此,尽管乙没有亲手实施杀人行为也应对杀人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并进而认为:“在认定共同实行犯的实行过限的时候,必须注意考察实行犯对某一临时起意的犯罪行为是否知情……不知情的实行犯对此不负刑事责任,如果是知情的表明主观上对该犯罪行为是容忍的,尽管没有亲手实行,也应承担刑事责任,该犯罪行为就不是实行过限。”[9](P384—385)我们认为,在此情况下,仅有强奸的故意和实行了强奸行为,而无杀人故意和杀人行为,却成立故意杀人罪,违反了“无犯意就无犯罪人”的格言。
类似的情况还有,甲、乙共谋盗窃,在共同实行中,乙发现正在睡觉的丙遂将丙强奸,甲看到了并未制止,我们同样不能推定甲先前的盗窃行为必然产生保护丙的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的义务,进行认定甲犯有强奸罪。相反,如果甲真的制止了乙的强奸行为并同乙进行了搏斗,甲的行为恐怕很少人会认为甲是在阻止自己构成强奸罪,更多的恐怕认为是一种立功行为。所以我们认为在处理共同实行犯时采用“容忍说”并不妥当。
另外,有些论者认为:“如果其他实行犯当时不在场,但事后对这种行为予以认可说明这种行为并不违背他们的主观意志,不属于共犯过限,应与该实行犯一起承担刑事责任。”[12](P44)我们也不赞成这种观点。举例来说,甲、乙在不同房间共同盗窃,甲当时并不知乙在盗窃过程中将财物主人丙杀死。甲和丙本来就有仇所以在事后对乙大加称赞,那么甲对乙的杀人行为就要因此负责吗?由于不在共同谋议的范围内,在甲对此主观上并无和乙共同杀人的犯罪故意,客观上又无实施故意杀人行为,当时对乙的故意杀人情况一无所知,仅仅凭借甲一句评价就认为甲和乙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共犯,这样处理显然是过于严苛,似乎是在对“思想”定罪。其实发生实行过限后,其他人往往都会对之进行评价,如果认为肯定的评价乃至不作评价都以不违背其主观意志而不属于实行过限,进而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话,那么就会大大扩张刑法打击的范围,势必罚及无辜。
应当指出,在处理“共同实行犯的实行过限”和“组织犯的实行过限”问题时,我们采用的标准是不同的,对前者我们采用的是“分离说”:即使共同实行犯明知,容忍甚至希望其他实行犯发生超出其原来共同故意的范围,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不谋而合”的默认的故意,对后者我们采用的是“能够预见说”,即组织犯只要能预见到实行犯有可能实行过限却未采取相应措施,就要对此承担责任。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是二者的法律性质的不同:组织犯有对其他共犯的领导、约束和管理的地位和资格,对他们自始至终有着足够的影响和控制力量,所以在对实行犯的过限行为如有预见而放任的话,或应当预见却未能预见时就要承担责任;而实行犯由于缺乏这种资格或地位,势必不能对其他实行犯有充足的影响力,因而在其他实行犯一起完成共同犯罪后,他们之间的共犯关系就此分离,除对先前的共同实行行为承担后果外和他们不再有联系。组织犯和实行犯法律地位的区别不仅在刑法理论上而且在法典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刑法典第26条第1款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第26条第3款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我们看到,组织犯都是按主犯处罚,而且对于组织犯的处罚明显比一般实行犯的主犯要重,所以说在处理实行过限问题上,对组织犯和实行犯采取不同的标准是合理的。
3.教唆犯的实行过限
教唆犯作为共同犯罪人之一较早出现于1810年《法国刑法典》,1871年《德国刑法典》将教唆犯从从犯中分离出来,将其与共同正犯、从犯并列,使之成为一共同犯罪人中的一个独立种类。现行《俄罗斯刑法典》第33条第4款规定:“劝说,威胁或以其他方式怂恿他人实施犯罪的是教唆犯。”我国刑法中,教唆犯是惟一以分工分类法规定的法定共同犯罪人的一个类型。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犯是共同犯意的制造者,他们故意以自己的言行激发他人犯罪的决心,通过他人实施犯罪而实现犯罪意图,在共同犯罪中起煽风点火作用,被教唆的人如果实施了超过教唆犯教唆范围的犯罪行为,这就是被教唆人的实行过限。对此教唆犯一般无须对实行犯的实行过限承担刑事责任。但由于教唆犯罪的复杂性,在认定教唆犯的实行过限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重合性过限和非重合性过限
重合性过限即被教唆者所实行的犯罪与教唆者所教唆的罪之间具有某种重合性的情况下而发生的过限,例如:甲教唆乙抢夺,乙却故意实施了抢劫,在这种情况下,抢劫罪和抢夺罪构成要件不同,但有部分重合关系,如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都获取他人财物。甲只负教唆抢夺的刑事责任,乙则应负抢劫的刑事责任,就教唆犯而言,应视为被教唆者实现了其教唆的罪。
非重合性过限,即被教唆的人除了实行了教唆犯所教唆的犯罪以外,还实施了其他犯罪,例如:甲教唆乙盗窃,乙得手后为了毁坏现场证据,放火将失主房屋烧毁。这种情况下,甲对乙的实行过限的放火行为不应负刑事责任。
(2)明确性教唆、概然性教唆和选择性教唆与实行过限
所谓明确性教唆是指教唆犯明确以某种犯罪为教唆内容,且对犯罪的具体目标、程度等都有比较明确的意思表示。在这种教唆犯罪中,如果被教唆人的行为超出教唆范围,即与教唆犯的意思表示不一致,属于实行过限。教唆犯对这种行为没有主观故意,其刑事责任由被教唆人独自承担,教唆犯只对其教唆范围内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如甲教唆乙、丙假冒公安人员对国家干部丁就其嫖娼问题进行敲诈勒索。丁对乙、丙的身份产生怀疑,并打算报警,乙、丙二人临时起意用水果刀将丁喉管割断致丁死亡,乙、丙的行为明显超出教唆范围,应视为实行过限,甲对此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概然性教唆是指教唆犯对教唆的内容较为概括,对犯罪的具体目标、程度等不太明确或毫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来,只要由于教唆犯的概然性教唆而使被教唆人产生了犯意,无论实施了何种犯罪,没有明显超出教唆范围的都不应视为实行过限。目前,雇佣犯罪在我国属高发刑事案件。如轰动全国的某市政法委书记李某雇凶杀害吕某一案,李为报复吕某,多次同其心腹鲁某商议雇凶“收拾”吕某,属典型的概然性教唆。在这种情况下,受雇人无论杀伤或杀死被害人均应视为在教唆故意内容之内,并不违背教唆犯主观意志,不发生实行过限问题,其刑事责任由教唆人与被教唆人共同承担。
所谓选择性教唆就是教唆犯的教唆具有让被教唆的人在几种犯罪之间进行选择的性质。在选择性教唆的情况下,被教唆的人只要在被选择的范围内实施犯罪行为就不发生实行过限问题。例如:甲教唆乙对丙进行报复时告诉乙可以侮辱诽谤丙,诬告陷害丙,强奸丙和抢劫丙等几种犯罪行为供乙可作选择,乙无论犯了其中的一个或者同时犯了其中的数个乃至全部都不能视为实行过限,教唆犯应对此承担刑事责任。
从上述分析我们知道,概然性教唆范围要大于选择性教唆,而选择性教唆的范围要大于明确性教唆。因此,在明确性教唆的情况下最容易出现实行过限,相反,在概然性教唆的情况下,出现实行过限的机率也就最小。
(3)教唆犯结果加重的实行过限
在教唆犯罪中,有些实行过限属于结果加重行为。如:甲教唆乙伤害丙,乙却失手将丙打死。这种情况下,乙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之罪论处,这一点不会有太多争议。但甲是否要对乙所造成的丙之死之结果承担责任呢?理论上争议较大。国内学者有两种见解,一种意见认为:“教唆犯反对被教唆的人所实施的基本犯罪行为负责任,而对其造成的加重结果不负责任。”[13](P126)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教唆犯对加重结果预见的应负刑事责任。”[9](P427)我们还应注意到,德日刑法理论上和判例上多持一种全面肯定结果加重犯的共犯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二人以上的行为人共同故意实施基本犯罪,不管这些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如何,只要其中的人的行为引起了重的结果,全体共犯人均成立结果加重犯的共犯。[14](P143)依这种观点,只要发生结果加重,教唆人对之都要承担责任。
我们认为,一般来说,结果加重犯这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其基本犯罪本身包含着重大结果发生的高度危险性,教唆犯一般是应当对此有所预见的。但由于现实客观情况的复杂性,重结果由不可抗力或偶然因素而造成的情况不能完全排除,的确存在教唆犯对实行犯引起重结果的发生根本是不可能预见到的情况。如甲教唆乙用麻醉的方法对丙进行抢劫,但乙却投放剂量过小,未能使丙昏迷。乙为了抢劫,使用暴力将丙杀死,获取了财物,对之,甲是无法预料到的,要甲对此承担责任,显然有失公允。在日本,由于判例广泛承认结果加重犯所有形态的共犯,甚至明确将结果加重犯作为结果犯看待,具有客观归责的倾向,一直受到学者的批评。有学者称这种判例是“正当化的不应有的野蛮”、“法律不名誉的典范”[14](P148)。我们也不赞成全面肯定结果加重犯共犯的观点。
上述国内学者的两种观点也为我们所不赞同。我们认为教唆犯是犯意的制造者,由于其教唆点燃了被教唆人通过实施犯罪达到某种目的欲望之火,并通过被教唆人的犯罪活动使得这种欲望之火进一步燃烧,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如果教唆犯在进行煽风点火时不可能预见到会殃及到别的人或物,那么其对这种不能预见的后果是不应承担责任的。但是如果其在点燃被教唆人犯罪之火时,本来可以预见到失控的危险性,但却因疏忽大意未能预见,或已经预见到但却未采取措施,放任甚至希望火势蔓延时,教唆犯对这种教唆故意之外的后果就存在罪过。特别是在结果加重犯的场合,由于基本犯罪本身就有造成结果加重的高度危险性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了加重结果让教唆人承担这种加重结果的责任,也是应该的(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即便这样,也不能视教唆人和被教唆人为结果加重犯的共犯,因为他们之间缺乏共犯所必备的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他们只须对这种加重结果分别承担责任即可)。所以不论是教唆犯对加重结果的“不负责任说”还是“已经预见的负责任说”都不适当地缩小了教唆犯对加重结果负刑事责任的范围。我们认为,在被教唆人造成了加重结果的情况,只要教唆者对这种加重结果应当预见,其对这种加重结果就应承担责任,即使这种加重结果违背其意志也不能免责。我们认为对教唆犯这样处理也是恰当的。这也是教唆犯自身的特点的必然要求。
4.帮助犯的实行过限
帮助犯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称之为从犯,如现行《日本刑法典》第62条规定“帮助正犯的是从犯”。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一般用帮助犯这一称谓,1922年《苏俄刑法典》第16条第3款规定的建议:“指点排除障碍,藏匿犯罪人或湮灭罪迹等的方法,帮助实施犯罪的是帮助犯。”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帮助犯,但在从犯的规定中暗含着帮助犯,即我国刑法第27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这里起“辅助作用”的实质就是帮助犯。由于帮助犯是在其他共犯的犯意已经产生之后而为其他共犯实现犯意提供精神上或物质上的帮助,表明帮助犯的行为是有明确指向的:其一般是在知道实行犯要实施某种危害行为的情况下才对实行犯予以帮助的,如果实行犯超出帮助犯的犯意实施了其他犯罪,则出现对帮助犯而言的实行过限问题,帮助犯对被帮助的人的过限行为不负刑事责任。
有学者认为,在共同犯罪中,如果实行犯实施了超出帮助犯所意图侵害的对象,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只能由实行犯承担[12](P43)。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属于打击错误,是“对不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对象的认识错误”或称之为“对目的物的认识错误”,是一种对犯罪事实的认识错误而非实行过限。例如:甲、乙共谋伤害丙,甲在外望风,乙入室后,黑暗中将卧室中丙的妻子丁当做丙刺成重伤,依据我国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在这种场合下无论是丙的身体健康,还是丁的身体健康,在法律上其性质都是相同的,行为人行为所侵害的这种身体健康的客体并不因人而异。因而这种对象上的认识错误对定罪不发生影响,不影响行为人故意的成立,也不影响共犯的故意的成立。因而对象的错误对帮助犯的成立不发生影响,甲作为帮助犯应构成故意伤害(既遂)。
由于犯罪具体情况的错综复杂性,在帮助犯的实行过限问题的认定中应进行认真分析研究,以便作出正确的认定。例如,甲、乙共谋盗窃,甲在外望风,乙在入室盗窃中临时起意,将户主丙强奸,如果甲对此一无所知的话,显然是典型的实行行为过限,甲对乙的强奸行为不应负刑事责任;但如果丙在反抗时大声喊叫被甲听到,甲马上也进入丙家,发现乙正在强奸丙,这时乙也发现了甲,二人目光交换后,甲将丙的彩电打开,声音调大,并将屋门关紧。这种情况我们认为甲、乙在目光交换后已达成新的意思联络,形成新的共同强奸犯罪故意,甲是帮助犯,乙是正犯。假如丙大声呼叫,甲进入丙家发现乙正在强奸丙后,将卧室客厅的门关紧,并将自己所骑的摩托车发动制造响声掩盖丙的喊叫,而乙对此并不知情,这种情况对甲的行为如何处理?我们认为应当参照片面共犯理论,以片面帮助犯处理为宜。这种情况下,甲对乙暗中进行帮助,乙虽然不知情,但甲却有帮助乙共同犯罪的故意,又有帮助乙的行为,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按片面帮助犯论是较合适的,否则就对甲不能处罚将会放纵犯罪。
收稿日期:2002-0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