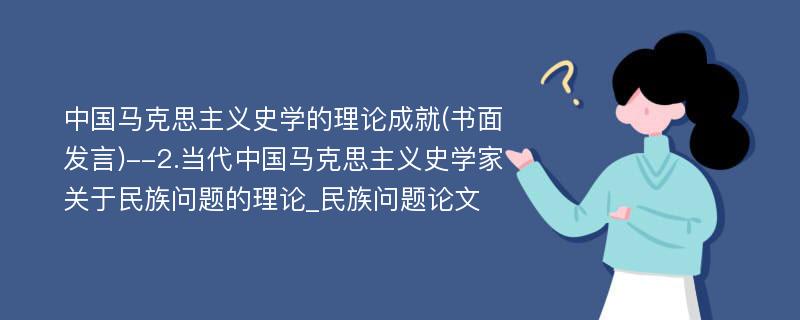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笔谈)——2.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理论论文,笔谈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1-0098-1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民族团结平等、共同发展的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由历史上充斥着民族间压迫、奴役的时代向多民族形成平等、友爱的大家庭时代的转变,这一社会现实的巨变极大地推动着历史研究和民族理论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各民族祖先的活动十分丰富而生动,留下来的史料记载也极其繁富,这就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提供了广阔多样的研究课题。这些学者明确而卓有成效地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民族史的丰富实际结合起来,表现出理论上极为可贵的创造性,他们积极探讨,各抒己见,因此,到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对民族问题积极探讨和争鸣的良好局面。
进入新时期以来,对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更加活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项:一是对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这一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二是论述了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三是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
——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从历史记载来看,古代各民族之间(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既有不少关于民族和好、经济文化交流的记载,也有不少关于战争的记载。有的学者根据其所统计的历史上民族间战争与和好相处二者年份的多寡,或主张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战争,或主张主流是民族和好,双方各有年代依据而相持不下。1981年,在北京举行的民族关系史学术研讨会上,对此更是展开了热烈讨论。会上,以白寿彝、翁独健、谭其骧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另外一种比较超脱的观点,即认为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应该是各民族间关系越来越密切,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历史。这一论点与分析得到了大多数与会学者的赞同。白寿彝认为:“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1](P53)对于这一段话,白寿彝从三个层次进行了论证:第一层,各民族在各方面的不同贡献中相互依赖、相互支援,对促进历史发展是很重要的。第二层,从整个国家历史的发展来看,凡是盛大的皇朝,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是不行的。“李世民当了‘天可汗’,唐朝就特别显得强盛。当时长安成为国际市场,经商的有各少数民族商人,还有许多外国商人。从这些事实来看,大的皇朝,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不跟少数民族搞好关系,是不行的。”[1](P55)第三层,从历史发展的阶段看,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宋元时期广大边疆地区的封建化,都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新的阶段。近代以来,各民族共同反对民族压迫,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大大促进了历史的前进[1](P55-56)。其后,白寿彝在1989年出版的《中国通史·导论》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阐述。
同在1981年民族关系史学术研讨会上,谭其骧也认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长期的经济、文化、政治关系,逐渐发展下来,越来越密切。他说:“我们很赞成前几天翁独健讲的一段话,我们历史上中原王朝跟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主流是什么?是和平共处,还是打仗?我们看不必去深究它,确实有的时期是很好的,和平共处,有的时期打仗还打得很凶。但是,总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我看这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边区各族和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2](P9-10)他还举出明朝与后金、蒙古的关系进行论证,认为通过互市,通过战争,最后需要统一,而清朝之所以能造成大一统的局面并且巩固下来,是顺应历史的潮流,是历史的发展自然形成的[2](P9-10)。
——关于对中国史记载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发展过程的不同形式。正确处理中国史记载的范围,其实质是肃清旧时代中原王朝正统论的恶劣影响,科学地将中国史真正写成各民族活动的历史。封建时代的史家是把皇朝史等同于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尽管史学工作者在道理上都明白封建正统论为谬论,但是在中国史记载内容的实际处理上,仍有一些人摆脱不了陈腐的封建正统论的影响,不自觉地把中国史内容限制在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内,这等于是在“汉族”或“汉族统治者”和“中国”之间划等号,完全背离了“中国史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这一科学要求。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了实质性进展,其中,方国瑜等学者的论点可为代表。方国瑜明确批评有的同志所持的“中国历代王朝有时强盛,有时衰弱,疆域时大时小,写中国史若是按今天中国的版图为范围不合适,应该按各王朝的版图来叙述中国的历史”的观点。他说:“我认为中国历史应该以全中国五十多个民族的历史为范围。”“王朝史不等于中国史。王朝的兴亡不等于中国的兴亡;王朝分合也不等于中国的分合。自古以来只有一个中国。……如果按照那种以历代王朝疆域为范围的说法,那么,在三国时代,又应该以魏、蜀、吴三国中哪一国作为中国的历史呢?”“我国历史这么漫长,有这么多人口,可是我们并没有分成几个国家,这有着十分深刻的内在原因。清朝垮台时,当时中国并没有一个武力强大的政权,可是并没有出现分裂。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挂五色旗,表示汉、满、蒙、回、藏仍为一国。回顾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的历史,我们更加坚信各民族的团结今后一定能不断巩固和发展。”[3]白寿彝对中国史内容的范围亦作了明确表述,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串古今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4](P79)对此,谭其骧也有重要论述。他提出,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应以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为范围,“具体说,就是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2](P4)。这个提法,更为注重历史的依据,强调我们要记住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掠夺走的国土,特别是沙俄通过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强迫中国割让巴尔喀什湖(今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堰塞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淖尔南北,以及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的历史事实。
在几千年时间里,多民族的统一是否有不同的形式?统一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着阶段性?对此,白寿彝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提出了民族统一发展过程经历了四种统一形式的理论,即单一民族的统一;地区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他说:“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这四种民族统一的形式,是按着程序前进,一步高于一步。先是有若干单一的民族内部统一的出现,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然后有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如战国七雄。然后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然后有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4](P91)同时他论述,从历史进程的全局看,分裂局面是暂时的,统一才是历史的主流,而在曲折过程中出现过的地方政权,对于本地区生产的发展和政治、军事制度的创设,也有其历史性贡献。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正确阐明了中国这个具有久远历史传统、幅员辽阔、人口居世界首位的国家在多民族统一进程的层次性,以及统一发展总趋势中所包含的地区性和阶段性特点;辩证分析了中国由于地理、经济、政治及文化特点而形成的统一总趋势与暂时出现的曲折之间的关系,指出分裂局面虽然是历史的曲折,但割据性的地方政权有其历史性意义,不应一笔抹杀。这就为评价历史上少数民族杰出人物的贡献,进一步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恰当说明了社会主义全国性多民族统一既是在历史上的全国性统一基础之上发展的,又有着阶段性的不同,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的各民族平等,中国久远的统一传统至此得到了升华。
——关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这是费孝通于1988年8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作讲演时提出的,其主要表述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5](P131)这段表述揭示出:第一,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五十六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高一层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故此,民族认同意识有两个层次,在多元一体格局中,五十六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第二,多元一体格局经历了从分散到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第三,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发展各自原有的特点。对此,林耀华评价说,在这篇讲演中,费孝通运用了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深刻追溯了中华民族格局的成因并指出了这一格局的最大特点,即一体中包含着多元,多元中拥戴着一体。“从而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他还指出:“在国家的政治统一时,文化多元这个侧面会得到强调并得到合理的体现;而在天下动荡时,政治统一这个侧面又会顽强地上升为各民族普遍认同的当务之急。正是基于这样的体会,我才深深感到‘多元一体’这个概念的提出将大有益于我们今后的学术研究和工作实践。”[6](P910)
[收稿日期]2006-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