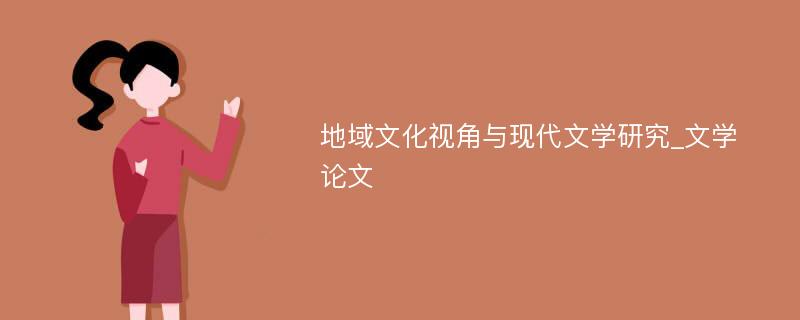
地域文化视角与现代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视角论文,地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887(2003)05-0014-04
尽管一直存在回到文学自身,将现代文学经典化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仍然集中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上。借用新批评的术语,就是集中在文学的外部研究上。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的探讨,触及了文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复杂关联,而出于探讨这种复杂性的要求,“现代文学研究近些年扩展深化了文学与历史、文化语境关系的研究,包括文学与传播、都市文化、地域文化、宗教文化、校园文化、女性亚文化关系研究,甚至可以说,某些探索性的研究,把现代文学主要作为文化现象观照,而不再保守以往以文本和作家研究为主的方式。”[1]其中,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和总结现代文学,一度被寄予了较高的期望,也出版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专著和大量的文学作品,但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至少,同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等相关领域相比,地域文化视角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1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有地区性的现代文学史专著出版。这些地区性的文学史,有的是以政治活动为标准来确定地域空间,如刘增杰主编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2]、冯健男和王剑青主编的《晋察冀文艺史》[3]、文天行的《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4]等等。与此相应,重庆出版社于1985年和1989年连续推出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和《解放区文学书系》等,采用的也是政治标准。有的则是以行政区划为标准来确定地域空间,如《江苏新文学史》[5]、《岭南文学史》[6]等。这些著作以研究某一特定地域的现代文学为目标,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域文化视角,但在具体操作中,对地域文化特色也有所涉及。政治活动实际上也有对地域文化的利用和改造在其中。
进入90年代之后,一方面是大量地域性的现代文学作品被整理出版,另一方面则是研究者开始从真正的地域文化视角出发来研究现代文学,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作品出版方面,几乎每一个省区都整理出版了自己的现代文学书系,而且追求大规模的整体效应。如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大型丛书《贵州新文学大系》,河南大学出版社的《河南新文学大系》等等。这种出版行为虽主要出自地方有关部门的诸种实际考虑,且编辑质量也参差不齐,但就文学史料的保存和搜集而言,却又有着不可代替的贡献。其中,钱理群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7],张毓茂主编的《东北现代文学大系》[8]等大型文学书系的出版,与上述地域性出版物完全不同,既有严肃的学术品格,又有着改变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积极构想,文化的眼光已经取代了政治或单纯行政区域的标准。正如钱理群所言,这些“地方区域文学大系的出版,正标志着一个新的领域正在引起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界的越来越大的关注,这就是‘现代区域文学(文化)’的研究。”[9](P261)
集中体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是严家炎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从1995年到1998年,该丛书共出版了10种。分别是: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费振钟《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逄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魏建、贾振勇《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彭晓丰、舒建华《“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刘洪涛《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马丽华《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这套丛书从策划到出版的操作过程都遵循着严格的学术规范,作者大都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卓有建树的中青年学者,主编严家炎,副主编王富仁、钱理群和凌宇等人,对学科的现状与历史都有着相当自觉的了解。严家炎早在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关注地域文化与现代文学之关系,曾于1989年在苏州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上,提议关注和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与吴越文化”问题。所以,该丛书一面世就受到了高度的重视,被评论界称之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件盛事。”[10]据笔者所知,这套丛书中的不少作者仍然在关注着地域文化与现代文学,且有新的突破。比如《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的作者李怡,最近又有《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11]一书问世,进一步深化和扩大了研究领域。
除这套颇有影响的丛书外,有些省区出版的地区文学史,虽是以地区行政区域为标准来选择对象,但由于特定的地域文化特色,仍然可以视之为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比如贵州民族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20世纪贵州戏剧文学史》[12]、《20世纪贵州小说史》[13],就颇为关注地域与少数民族文化问题。在以后的研究中,这种地域与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研究,由于与地方有关部门的文化利益的关系,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地域文化研究淡化下去后的主要形式,这与史学研究走向空间化和文化研究中对少数民族文化和亚文化的关注,是一致的,但地方文化部门和行政部门的介入,又有可能削弱其中的对话和解构力量,变成一种新的文化霸权策略。
正如严家炎指出的那样,“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的研究,涉及历史学、文化学、宗教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多种学科,难度比较大。”[14]因此,对具体的研究成果与结论之类,没有必要作过多的纠缠。但从文化人类学的原则与方法的立场上看,则可以发现地域文化视角中包含着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仍有待大力发掘。
2
为什么要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一般的看法是因为地域文化因素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某些特征。严家炎认为:“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所以,“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并不是要为各个地区撰写20世纪文学史,而是要选择那些具有明显区域文化特征的重要作家、文学流派或作家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区域文化怎样渗透进了这种文学,为这种文学打上了多么独特的印记。”[14]黄修己也指出,编撰地区性文学史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以其局部的情况,加深人们对于全体的认识”,其次则是保存史实。[15](P385)表面看来,是因为地域文化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所以才要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但实际上,这里不是一个自然的时间顺序问题,真正的原因是为了建构关于现代文学的大叙事。也就是说,建构关于现代文学的大叙事这个先在的目的,引出了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的需要。这里真正起作用的是逻辑预设,而非表面上的时间顺序。这样,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叙事,就决定了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现代文学的可能性,预先设定了这种研究的终点。
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消除大叙事是西方文学研究界的趋势甚至共识。”[1]大叙事是现代性追求的产物,是用时间性来抹去空间性差异,建立一个没有内部差异的同质化时间序列。现代性大叙事以时间来使空间差异同质化,强行将地域差异从空间性存在叙述为时间性存在的基本手段。比如,在历史进步这个大叙事中,东方和西方的差异就被认为是西方处于历史发展的前列,而东方则落后于西方。换句话说,西方位于线性时间的顶端,而东方则位于中部甚至后部,东方惟一的道路是在同一条时间轨道上追赶西方。
西方现代性的扩张方式,就是在非西方世界复制它已有的叙事模式。因此,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实际上与东方国家内部的地域关系是一致的。就中国自身而言,地域差异普遍被认为是发展程度的差异,东部和西部之分就是一例。但实际上,东西部的差异刚好是用历史进步这个大叙事来规划和控制中国内部空间差异的产物。这在政治经济领域里,自有其相应的理由。但就文化而言,则远远不是那么简单。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区域文化往往与少数民族文化相关。在历史上,汉民族就有用少数民族之“汉化”程度来衡量其文明程度的传统。近代以来,“汉化”程度中又混杂进了“西化”程度,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空间性的地域文化差异,不断顽强地冲击着现代性的时间差异,使现代性大叙事变得越来越面目可疑。
实际上,现代性是在后现代的视野中作为一个问题丛生的被反思和被审视的对象浮现出来的。用利奥塔的话来说,先有了后现代,才能有真正的现代性,因为后现代性就是站在现代性之后,审视现代性进入历史的资格。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现代性一开始就被当作了一个固有的标准来使用。关于现代文学的有无现代性之争,争论双方的分歧只是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在现代性时间坐标上的位置之争。这个坐标本身有无问题至今仍在视阈之外。大量“以某某的现代性”为题目的论文,都不约而同地认定,只要具有了现代性,作家或者作品之价值与地位就获得了保证。这一切都没有将现代性当作一个反思和审视的问题来对待。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现代文学所作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也没有真正地走向空间化。
3
在反思现代性的学术潮流中,文化人类学本是最具有活力的一脉。文化人类学的原则是反思性的、批判性的,而非建构性的,张扬文化差异,以空间性特征来对抗和批判现代性的时间性特征,不断地打破和质疑现代性的大叙事,是文化人类学的力量之所在。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实际上改变了人文科学的游戏规则,使人文科学从传统的建构性的寻求客观规律转向了解构性的寻求意义,即将世界的意义从封闭和被压迫中解放出来。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也应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它的目标和任务不是要建立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叙事,更不是去完善和强化这个大叙事。相反,它应是一种积极的对话和解构的力量,将被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大叙事所压抑和忽视了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充分揭示出来。刘洪涛在《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一书中,注意到了汉语文化对苗文化的压抑和控制,分析了沈从文对苗文化的使用之复杂性,这实际上正是地域文化研究所应该做的。黄修已也主张文学史应写出历史的复杂性和内部差异性,并且特别指出应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少数民族文学[16],亦是走向文化人类学基本原则的自觉。以事实而论,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中的不少著作,“在对重要的文学流派、文学群体、重要的有代表性作家作地域文化阐释的同时,其反思的、再评价、再认识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10]将这种倾向上升为明确的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学术原则,是进一步激活与发掘其研究潜能的自然要求。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反思现代性应在两个层次上进行。其一是在中国与西方这个层次上,反思和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质疑现代性中的民族压迫与殖民话语。其次则是在中国文化内部的层次上,反思和批判我们自己建立的大叙事的合法性,质疑中国自身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的缺失。应该说,在目前的文化状况下,后者显得更为重要,也更有意义。因为反思和批判现代性,最终的指向是反思和批判我们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中国人的生活,显然与中国当下性的境遇关联得更为紧密。同时,西方的现代性扩张,是以在非西方世界内部强行复制西方模式为基本形态的,这也要求我们将对西方的批判放到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具体化为对中国文化与文学自身的批判。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将地域文化从服务于建构大叙事的建构性转化为反思性和批判性视角,已有人在着手进行。李怡等人的《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个案。该书不重大西南文化的实体性构成,而是将大西南文化放置于当代中国文化的总体格局中,用中国文化内部的中心/边缘之结构性关系来理解大西南文化的意义,对话和反思的意义都十分明显。
将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批判性的文化力量来看待,除应注意特定的地域文化内部的历时性关系,关注其内部特征外,更重要的是关注它与周围的强势文化所构成的共时性结构。从历时性角度来建构某一地域文化内部的总体特征,由于有方志和相关学术传统的支持,受到了较多的重视。这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体现得较为明显。但这种地域文化的总体特征,实际上是在与中心文化的共时性关系中呈现出来的差异性特征,是功能性而非实体性的。其功能就是质疑和瓦解中心文化的霸权地位,反思和批判大叙事的合法性问题,同时也在这种反思中借中心文化为参照,完成自身的转换与变化。只有确立这种共时性原则,对话才有共同的场域,才能在对话中放弃各自的独白性霸权地位,走向开放与多元。否则,任何一种文化内部都可以建构出关于自身之独特本质的神话,构成拒绝与他者对话,拒绝平等交流的理由。这样,表面上是在对话,实际上是各自沿着自己的历史时间进行独白而已,其结果不过是将西方文化霸权的方式复制过来,建立数量更多的话语霸权而已。
没有共时性的结构立场,任何差异都会被时间性统一起来,重新进入现代性大叙事的封闭与独断之中。
在这样的立场上,地域文化视角实际上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与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结合起来,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最有活力的一个领域,真正实现当初的规划和设计者的期望。
标签: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现代性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人类学论文; 艺术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