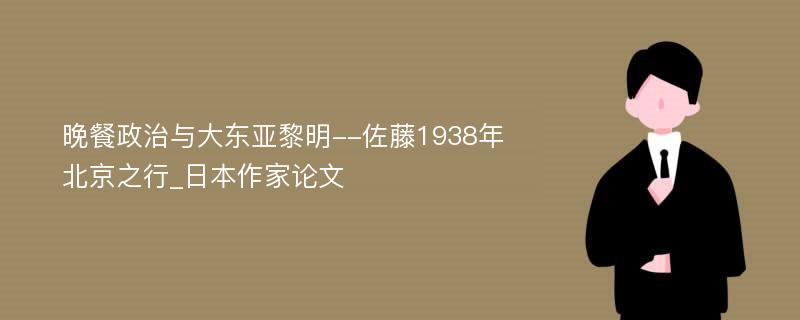
晚宴的政治与“大东亚的黎明”——1938年佐藤春夫的北京之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晚宴论文,之行论文,北京论文,佐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篇拙文中,笔者曾指出,“国际中国学”在研究对象上存在一个有别于严绍璗先生“四层面说”的第五个层面,即:海外中国学家(汉学家)是如何以其涉华活动、创作和言论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发展乃至其母国对华关系的进程(王升远B01)。以日本为例,汉学家的中国研究实绩固应充分承认,但其“协力战争”的丑恶一面也不应被遗忘。战后由于其本人对日本侵华时期相关著述的回购销毁、学术界“为尊者讳”的畸形学术生态以及美国占领等一系列国际政治、文化环境因素合谋,绝大多数日本文化人的战争责任始终未得到彻底的清算。 落实到本文研究对象佐藤春夫(1892-1964)的研究上亦然。1977年,祖父江昭二曾呼吁通过全面的思考建构起具有一致性意义的佐藤春夫论,而不能选择性强调或回避(祖父江昭二 伊藤虎丸等147)。同年,鸟居邦郎将“昭和十年代之后佐藤与战争的关系”视为日本学界佐藤研究“今后的研究课题”中的重要一环(转引自三好行雄175)。然而,自那以后迄今为止的三十年间,学界相关研究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推进。毋庸赘言,严肃、负责的文学史著述须建立在充分、客观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在全集故意遗漏相关作品、年谱编订者对相关史实置若罔闻、创作于战争时期的某些中国题材作品因此人为“蒸发”等情况下,日本学术界是如何描述这位“经典作家”在战争时期的涉华活动及其文学史地位的呢?以日本侵华时期为关注时限,笔者从日本若干重要出版社出版的诸种权威文学事典、作家辞典①中查找佐藤春夫词条,发现其中的诸种论述中既不乏洞见,也有为佐藤辩护嫌疑的说辞;但总的来说,从其中不难发现一个具有共性的问题点:佐藤1938年在华北战场的活动及相关创作被遗忘了。如果说,日本文学研究者的佐藤研究有维护其在日本文学史地位等潜在动机,那么通过日本学者不愿正视的侵华战争这一特定语境下的重要作品之讨论来挑战敲打、考验作为“常识”而被接受的文学史定论也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课题。 一、晚宴的政治:从“惨不尽欢”到“回首自得”确 小川五郎认为,佐藤春夫深度介入战争始于1938年与保田与重郎(1910-1981)的“北支、满洲之旅”(转引自祖父江昭二 伊藤虎丸等156),换言之,时值徐州会战末期的北京之行是佐藤春夫个人史的转折点。回首往事,保田对日本攻入徐州城的5月18日这一天很在意,他表示:“日本文坛认识到事变的重大性,将被赋予的国民责任付诸于行动便是以攻入徐州城为契机的。”② 综合王俊文等学者的考察及笔者对竹内好(1908-1977)日记、佐藤春夫的《半岛旅情记》、《北京杂报》、《蒙疆的话》等文的再考,大致可梳理出佐藤一行为期三周的北京之旅的经历: 五月一日 佐藤春夫作为《文艺春秋》特派员、保田与重郎作为《新日本》特派员,二人在神户汇合,乘关釜联络船金刚丸,从釜山经庆州、扶余、京城等朝鲜各地,又经奉天于五月十四日抵达北京。 五月十二日 竹内好收到保田的明信片,信中称将于十三、四号前后抵京。(竹内好,『竹内好全集』15:214) 五月十五日 佐藤一行在北京投宿北京饭店515室(佐藤春夫,『北京雑報』93)。其后,“在雨中,佐藤春夫、佐藤龙儿、保田与重郎三位在日中实业的全崎氏陪同下”造访了竹内好的家,午后登景山。其后的几日,佐藤一行“历访北京名胜,如东岳庙、国子监、孔子庙、雍和宫和隆福寺等处”。 五月二十日 竹内“与尤君(炳圻)策划”,“招待周、钱(稻孙)、徐(祖正)诸先生,举办一次晚宴”,聚会地点最终定在了同和居。(佐藤春夫,『蒙疆のはなし』205) 五月二十二日 竹内、神谷正男与佐藤一行及樱井中佐参观卢沟桥。 五月二十三日 佐藤“有染痢疾之嫌疑”,入同仁医院。住院的一周里,由竹内看护。 五月三十日 佐藤出院。 六月二日 竹内赴宾馆拜访佐藤。 六月三日 保田清晨出发去了承德。晚上,竹内“拜访佐藤,听他谈了各种话题,关于朝鲜文化的话很有趣”。 六月四日 晚上,竹内“赴宾馆拜访佐藤”,但佐藤与“支那通”村上知行去观剧了。 六月五日 早晨竹内“去宾馆拜访佐藤氏”,“在宾馆里三人(竹内、佐藤、龙儿——王俊文注)共进晚餐。……与神谷君一道送佐藤先生乘六点半的火车离去”。(王俊文90) 以上行程安排使这次北京之行看似更接近“文学之旅”。然而,访者果真是超然于战争之外的吗?佐藤曾明言其不乘飞机、而乘火车经过朝鲜到“满洲北支”这一路线设定的初衷:“历史上我国的大陆进出都是从这个半岛开始的,我决定也遵从这个顺序从朝鲜进入大陆”(『半島旅情記』334),佐藤似乎是将自己视为“进出大陆”的一份子、至少是要以此体验作为其一份子之实感的。在五月二十日写给《文艺春秋》的稿件中,佐藤坦陈:“应报告的是京城的绿旗联盟和新民会的比较考察之类的吧。[……]北京市内游览并非此行的目的,所以尚未参观。”(『北京雑報』92)据此,至少可以说佐藤此行有着较强的政治意味。关于其动机,佐藤本人并未直言。我们先来看看两年后,同行的保田的议论:“当时与我们会面的十几位文化人的情绪中如果说有着某种变动着的东西,又加之各种时势之故,那么佐藤氏的来访至少可以说是使之动摇的契机。[……]文学者进而带着政治任务、以文学者的身份进行活动,在我国史无前例,恐怕在东西方的历史上也无与伦比。”(保田与重郎,『事変と文学者』古今書院版274-281)1939年佐藤的另一番论述也耐人寻味:“对皇道有所认识、有行动力的新日本知识分子”,“大量移居支那”乃“事变后的一大急务”。笔者认为这里的“新日本知识分子”有佐藤自况之嫌。此外,他还指出,“此次事变虽未得到新的领土与赔款,但对于这种人物的教育而言是极有意义的”(佐藤春夫,『文化開発の道』80)。综合佐藤和保田的描述,首先可以做出如下推论:佐藤自身便是其自诩的“对皇道有所认识、有行动力的新日本知识分子”(佐藤春夫,『文化開発の道』80),其北京之行似肩负着政治任务,以文学者的身份在北京的活动,意在引导、动摇留京中国文化人的政治立场与倾向,并扶植、培养周、钱这般的“亲日派”。 如此说来,与留京中国文化人的聚会便是访者的“有心栽花”了。从保田、竹内、佐藤的各自回忆③中,我们大致可以提炼出当晚的主要话题——饮食、鬼怪、拉洋片、文学及对日本的回忆等。尽管每个人的回忆都略有差异,但三人似乎都有意强调同一个问题:晚宴话题未涉及政治。多年后保田忆及此事,一再强调,这是一次纯粹的文学聚会,并非因于“官方意志”,完全是组织者竹内好“个人的作用”;而事变后一直闭门不出的周作人的出席让访者感到“是经过了非同寻常的思忖”,“让周作人敞开心扉的是佐藤的诗人身份”(保田与重郎,『事変と文学者』弘文堂書房版135)。 在组织者竹内好看来,由于宴会的话题“有些‘老人趣味’的,说好听些叫‘北京趣味’,保田似乎对此不满……保田所期待的,现在的北京却没有”(竹内好,『佐藤春夫先生と北京』290)。在关于北京的“现地报告”中,保田坦言: 北京所没有的果敢之剑藏在蒙疆。[……]我见到了几位北京的知识分子。那时我在感到失望的同时品味到了丑恶。那些最高层的知识分子保持着沉默,时而还掺杂着讽刺与谎言。中层者说了些对蒋介石的信任和对日本的要求,这不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而是一种商业交易。他们中的最下层者在我去的时候,正在大声练习着曲艺,练习的不是演技,而是说唱[……]我感觉进入了一个超越阴郁的黑暗世界。(保田与重郎,『北京』80-81) 在“蒙疆”一文中,保田重申:“我对北京文化失望……对北京知识分子更失望。”(保田与重郎,『蒙疆』107)佐藤春夫时候也随即发表了与保田态度相近的评论:“话题始终是关于饮食、拉洋片、文学等无聊的闲谈,虽说未到惨不尽欢的程度,但是总觉得笼罩着一层阴影,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佐藤春夫,『蒙疆のはなし』205-206)正如丸川哲史所指出的那样,“从竹内的角度看来,周作人等人的‘老人趣味’式的款待,可说是经过计算的,实际上那‘亲善聚会’是一种脱政治化的尝试,对照出以保田为首的日本方面试图于聚会中寻求政治意味的天真烂漫想法之间的落差”(85)。但值得推敲的是,三年后,佐藤却改口说:“那天晚上的小集全然没有无聊的欢迎致辞和奇怪的社交辞令,有滋有味,是只有跟悠闲温和的北京文人才会看到的温雅的佳集。”(佐藤春夫,『日華文人の交流』59)显然,几年后,保田与佐藤的立场、态度前后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对周、钱等的“政治沉默”的认识由消极转向积极。 关于此次宴会,笔者要追问两个问题:一、佐藤、保田等为何要见这些留京知识分子;二、对于这次平淡且无成果的晚宴,佐藤、保田的态度为何由“惨不尽欢”的不满转而事后再三追忆且颇为自得,是什么影响了其立场的变化? 佐藤并不糊涂,宴会后他随即表示:“同和居的聚会,周作人、钱稻孙、徐祖正等前辈们也在非正式会面的意义上列席了,恐怕是由于时局之故,避免个人性的会面,而利用这次聚会吧。”(佐藤春夫,『蒙疆のはなし』205)在了解周、钱被中国文化界一致谴责、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保田和佐藤意识到他们的出席“很难得”,表现出“同情之理解”的姿态,这些也影响了后者来华的动机与心态。保田在《事变与文学者》中回忆:“在徐州战末期,我们在北京感受到的支那知识分子微弱的态度变化,若能被更重视一些就好了。[……]尽管微弱,单是向日本敞开心扉这一点,我认为是徐州会战前后才出现的动向。对于这样的心态,佐藤氏的北京访问不可能不创造出一些使之容易动摇的契机,不过那也是由于他们信赖佐藤的文人业绩之故吧。”(保田与重郎,『事変と文学者』弘文堂書房版133)以上引文透露出如下信息:佐藤与保田与周、钱等的会面似乎有意与其讨论中日关系及其个人立场等较为深层次的问题,甚至希望这些“亲日派”能更为旗帜鲜明地表达其对日立场,企图在周、钱等已有事伪倾向的情况下,促使其进一步动摇。强调北京与上海、南京情况的不同,换言之,留在北京的知识分子事实上是更亲日的、更具拉拢的可能性。但是显然,以周作人为首的留京重要人物的动向无疑已吸引了全国文坛的关注、且其投敌行径已受到激烈批判,因此出言谨慎毋宁说是情理之中的,这也是导致保田与佐藤之失望的原因所在。在时隔几年后的情势下,保田对当年自己未能更重视北京知识分子的微妙变化而深有悔意。保田说“我们的政府和军队多少发现了文艺与文士的利用价值是在此半年后”(保田与重郎,『事変と文学者』弘文堂書房版136),返视之,便是他认为其与佐藤作为杂志社特派员的北京之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实验。如果说晚宴的失败是出乎佐藤与保田预料的“偶然”,与留京重要知识分子的会面是“有心栽花花不开”;那么几年后的“回首自得”,毋宁说是佐藤、保田的一种迎合日本军部对华战略的邀功请赏、“意义追加”和相机而动的投机行径。 二、“世界新名胜”:战迹抒怀与“大东亚”想象 当然,作为《文艺春秋》的特派员,及时向国内读者描述、传达北京情状与民风政情动态是其北京之行的题中应有之意。前述行程显示,五月二十二日佐藤春夫一行专赴“事变以来的新名胜”卢沟桥一游,这也是其北京参观的起点。须提醒注意的是,两天前还撰文称其北京之旅意不在“参观”的佐藤春夫,其卢沟桥之行会意在景致吗?在《卢沟桥》中,佐藤如此向读者描述途经广安门时的见闻:“广安门就在这途中。……仰望樱井中佐跳下的城墙,目测高约三丈许。都是儿时看惯了日清战争画报的缘故,看见这样的城墙城门,总有觉得有旭日旗在那里翻卷的感觉。[……]钻过这道城门,出了这不祥之地,驾驶员像注意到了什么。在一眼望去像是洋槐的树影下,一座石碑前供着香花,是标志向井上等兵战死地的碑。我们都脱帽向其表达了敬意与吊念。”(佐藤春夫,『蘆溝橋』222-223)实地重走“加害”之路、向“闯入”中国的战死者表达敬意与哀悼,显见,佐藤对日本发起的侵略战争并无反省与批判。到了卢沟桥,佐藤赞美道:“不管怎么说,这是座颇美的桥,其后在北京看到的风物全无美过此桥者。北京之物都让人愤然,唯独此桥完全是特别的。”(佐藤春夫,『蘆溝橋』226)在佐藤那里,卢沟桥之美是置于不甚美好的“北京风物”之对立面得以呈现与凸显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理解卢沟桥的美好,就必须明了其对立面何以不够美好。在《从陋巷看北京》一歌中,佐藤认为北京是“可爱”的,同时也是可怜的、不吉不祥的,象征着古典中国政治文化秩序的故宫和颐和园让他感到厌倦(佐藤春夫,『陋巷に北京を見る』153-154)。他认为,“北京恐怕是站在净土对立面的,所有精神化的东西都被末梢神经化了”(佐藤春夫,『大陸と日本人』38)。 在《卢沟桥》中,佐藤在引经据典考述了此桥之历史后,断言此处“即将成为世界新的名迹”(佐藤春夫,『蘆溝曉月』234)。毋庸赘言,所谓的“新”显然是因点燃日本全面侵华战火的“卢沟桥事变”在此爆发之故。站在桥头,佐藤兴起而歌,选译如下: 伫立卢沟桥畔而歌 ——赠同行保田、竹内、神谷诸君 [……] 纵使东方傲然升起的朝阳之光, 也无法将这久远的往昔照亮, (古老的中国)一味沉醉在贪欲的梦乡。 石桥长长,栏杆俊朗, 栏杆石狮可否叩问衷肠, 我独自联翩浮想。 乌云低垂,夜半宛平, 无端枪声,织女梦醒。 彼岸喧嚣声欲沸, 且怒且悯,遥望绰绰人影, 手中柄,不轻横。 夏夜短暂,天色欲晓, 怯懦之鸡却已不会司晨。 彻夜无眠的思绪, 投向泛白的东方, 那是我的故乡,日本。 愿大东亚之黎明, 就在今日实现, 雄壮男儿猛然颔首, 共同奋起向前。 踏访古迹,追昔抚今, 浮想联翩,独自一人, 壮丽蓝图吾描画, 虽为梦幻, 往昔定难胜今。(佐藤春夫,『蘆溝橋畔に立ちて歌へる』152-153) 这首典型的“爱国诗”、“时局诗”在艺术性上实在乏善可陈,但作者意气风发的表述所流露出的政治指向性却异常明晰:一、日本是代表了东方之未来的“朝阳”,但却仍无法照彻沉睡的、怯懦的中国;二、战争是中方引起的“无端”挑衅,而日本军队则是克制的;三、“大东亚”已迎来黎明,前途壮丽,未来可期。 祖父江昭二认为,“以‘七·七’事变为开端的中日战争的爆发,[……]佐藤春夫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接连不断地发表同意侵略战争的诗歌。《献给牺牲军人的歌》便是佐藤的战争颂扬诗的嚆矢”(141)。林浩平指出,早在1934年出版的诗集中,浪漫诗人佐藤便曾以题为“擎起满洲帝国皇帝旗——兰之花”的诗篇表达了对(因长期受汉民族统治而)忍辱负重的“逆境之子”——“伪满洲国”之独立与建国的欣喜,通过对以“兰花”为皇室象征的伪满洲国“儿皇帝”之赞赏,表达了对其“父皇”日本皇室的颂扬。“佐藤春夫俄然展现出‘爱国诗人’的相貌应该始于此诗写作前后”(297)。此外,林氏的论文还指出,1939年佐藤春夫出版的《战线诗集》实则是向其前辈、日俄战争时期任陆军军医的森鸥外的战争诗歌《歌日记》致敬之作,但相较于森氏战争诗歌的“平淡”与“写实风”,佐藤则呈现出“陶醉”于战争的倾向(林浩平292-293)。从对“日满一体化”的讴歌,到陶醉于侵略战争、乃至产生了“连吾也成了诸神之一”的幻觉,若将此视作佐藤春夫“爱国诗”写作史上的两个坐标点,那么,《伫立卢沟桥畔而歌》则位处其间:既有“大东亚”梦想的昂扬描绘,又有对战争的“合理化想象”。 读过《卢沟桥》后,作家张承志认为此篇“显出佐藤春夫更多表达的不是随军而是作家的思路”(张承志216)。唯其如此,如果说以上种种可以以日本全面右翼化之时势裹挟下的“不得已”、是战争与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戕害作为辩辞(事实上,佐藤是始终是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马前卒”),那么这篇散文中描述的以下情景凸显出的则是无可推托、任何“主义”和外部因素都无法掩盖的、作为作家个体的“恶”与虚伪。在《卢沟桥》的结尾处,是一行人在一家土产店流连后的归途中,听说店主女儿曾在东京留学三年而作的闲谈: “真想和这样的中国新女性,大谈一番时事啊。” “谈着时事,日支提携最终还要结出亲善之果吗?” “不,想让村姑讲讲龙王庙、长辛店之类读报记住的地名、地图上所没有的村巷细处,再说些百姓议论的感想。” “很遗憾,她今天去北京了,不在家!” ——车上回响着欢声笑语,驶向都门。(佐藤春夫,『蘆溝橋』232) 曾留学东京数年的“中国新女性”仍是“村姑”的表述,自然可视为前述佐藤春夫关于“都市日本/乡下中国”二元模式之说的一个注脚。《卢沟桥》让张承志读过后感觉“如揉进眼中的沙子”,而上述引文则让他感到愤懑与痛苦:“已成故人的作家若是活着,不会轻易接受我说:自视文雅的他,出言冒犯了中国。读着卢沟桥边佐藤春夫写的与女留学生日支亲善的句子,我心里感到的,比读石原的流氓腔更加痛苦。真是这样,我们连喜爱都常常出错。这一篇像一头冰水,浇得我身心寒冷。真是如此,即便是我们敬重的作家,即便是胸怀正义的日本人,言及中国常出口放肆。”张承志对自己“触及日本文学时的失语”是自觉的。谨慎起见,他声称“我的议论唯限于这部集子(《支那杂记》——引者)——不涉及集中未收的‘军事题材’,如我没读过的《战场十日记》、《闸北三义里战迹》,也略过毛病更大甚至招致了郁达夫怒斥的小说《风云》”(215)。张承志对佐藤春夫的敬重源于后者对鲁迅的译介与评价,这本无可厚非;但由此便认为他是“胸怀正义的日本人”则恐怕是因选择性阅读造成的遮蔽与误判。尽管如此,张氏仍一针见血地指出,佐藤伤害了文学的尊严:“与故人争论的冲动,有时会从我心中慢慢涌起。他会同意一种——染上了民族意气的评论么?他会以修养为遮挡,嘲笑评论者的敏感么?”(张承志218)文坛名流将私下低俗轻浮的猥谈堂而皇之地形诸于“流氓腔”文字并刊行于世,且对在公共领域可能出现的反应不以为意,这是嚣张到近乎挑衅的行为。 猥谈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无论其对外宣传如何冠冕堂皇,但日本作家在兵祸之地,对中国女性的猥谈直接暴露出至少在佐藤那里“日支亲善”的虚伪、欺骗性本质;二、“生殖”与“亚洲共同体”的关联,从《卢沟桥》到《亚细亚之子》④乃至将另文讨论的北京题材小说《北京》(原题《老朋友》)是一以贯之的,在佐藤那里,作为“国家”的象征物,中日男女之间的婚姻、生殖行为而产生文化“混血”满足了他对“亚洲共同体”的想象,从中日男女的“融合”,到“日支文化融合”,最终指向所谓“大东亚共荣”,这是不难理解的内在逻辑。 对中国女性的描写、评论不止于此。在诗作“从陋巷看北京”中,佐藤谈到一位“可怜的乳房,就似不堪发掘的古坟”的清瘦幼娼“燕京女孩刘清云”: 闻观其夜宵者言, 形状乃不及狗食, 嬉闹间与其弟争抢, 狼吞虎咽着近乎黑砂糖的食物。 朋友啊,你的心泪谁人知? 这可怜的幼娼, 已成万种病菌的携带者。 惟盼其肺脏肌肤, 莫化成被侵蚀的太湖石。 可爱的单酒窝, 欲见她勿去昏暗的卧榻, 毋宁他日招待她于明亮的餐桌上。 (佐藤春夫,『陋巷に北京を見る』154) 不难发现,佐藤北京观察的视角切换到社会底层空间,试图通过陋巷幼娼透视到中国社会的真实。笔者认为,近代以降日本文化人到中国青楼寻芳问柳的欲望,大致无外以下三种因素的纠葛:一、对异域女性的猎奇与性欲念;二、追寻中国古时“文人趣味”的意图;三、“东方主义”意义上的强势国度男性对弱势国度女性的征服欲。根据时代、作家的差异,过度强调某一种因素有时就会导致遮蔽。落实到佐藤身上,对花柳巷的热情恐怕是“三位一体”的。被描述的对象刘清云生活在卫生状况极差的陋巷、其肮脏、窘困且不健康的“非人化”生存状态与狗无异。尽管有着“我的朋友啊,你的心泪谁人知”的郁结表述,但从结末处邀其“赐食”的“善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居高临下、趾高气扬的姿态,却看不出对中国下层世界由衷的同情与切实的救济。就是这样一位老作家,甚至将“卢沟桥事变”美化为“为了建设而做的必要准备”,当然,他也意识到“在这之后若没有建设,那么日本终将背负东洋之破坏者的恶名”(佐藤春夫,『北京雑報』91)。所谓的“亲善”、所谓的“建设”落实到实践层面却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人”之于“类兽非人”的空洞伪善与旁观的姿态。 三、对话张承志:为何要清算佐藤春夫 不妨直言,整个侵华战争时期,佐藤春夫的志向、活动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法西斯主义的方向是一致的,他是全面协力战争的作家之一。然而战后,相对于不少事实上负有战争责任的文化人三缄其口的低调(是否曾有反省或自我批判暂且不论)相比,佐藤春夫却显得异常高调。据大久保房男回忆,这位战争期间极为活跃的“国策作家”在日本战败之初居然宣称“日本赢得了战争”,针对舟桥圣一对其参与“南方从军”等战时丑行与战争责任的诘难,也只是以“我只是说了我该说的话”(大久保房男223,229)搪塞而过,若无其事。甚至直至1964年5月6日病逝为止,都一直没有对自己曾经支持“圣战”的行为做过任何清算”。而面对这样一位对自己的罪责“若无其事”的老作家,他的中国同行张承志选择了宽容: 对佐藤春夫的开卷,就这么浅尝辄止吧。文学的阅读就是这样,一旦陷入了喜爱,便再不愿容忍一星污点。 沉吟于他古风的日文,我确认了书生的文雅。他对中国古典的深爱感知,应该得到欣赏。他如未曾在暮年获得反思,一定是因为在他的国度,百年强盛传染的傲慢,尚未变成历史长河中汲取的羞愧。我不喜欢洇染了日本文学的,对中国的轻慢、冒犯、侮辱。但我也不愿纠缠不休,向喧嚣于旧时代的每句轻薄,都去兴师清算。 ……我视佐藤春夫对石原慎太郎的怒斥,为他对自己在旧时代败笔的反省。因为挺身时代的大义,永远高于文人的忏悔。合上他的书页,我记住的是他对恶质文字的挞伐,而不是他在卢沟桥边的失言。(张承志220) 笔者固然理解张承志所谓“挺身时代的大义,永远高于文人的忏悔”的表述中的宽容姿态与善意,也对佐藤春夫对石原慎太郎的怒斥表示赞赏,但同时却并不认为战后佐藤的“义举”(事实上,佐藤对青年石原的批评,与其后来对中国的极端右翼倾向是毫无瓜葛的)与战时对中国的“冒犯”、对中国人的亵渎之间存在高下之别,他们之间并非可以相互替代或相互抵消乃至抹杀的关系,也无需张氏站在“国家”的层面为其洗脱、辩护。 事实上,战后初期,在荒正人与小田切秀雄等分别在《文学时标》和《新日本文学》中公布了数十位文学界的“战争协力者”,佐藤春夫都名列其中。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些作家战争责任的追究最终都不了了之,但这并不意味着事情未曾发生、作品未曾写作发表,也并不意味着历史容许遮蔽乃至遗忘。张承志若去读读《亚细亚之子》、《北京》及《东天红》、《战线诗集》等佐藤春夫创作于战争时期的小说、诗作而非选择性地阅读或遮蔽,或许也会从中读出发现这位“国策作家”并非他想象的那般“胸怀正义”,或许也会赞同笔者对其战争时期的涉华活动与创作做出清理与评价乃至要追究其战争责任的要求。战后日本(文化)人战争责任的“虚无化”认知甚至学术界、思想界、教育界的右翼分子全面否认战争的态势,因由众多,但不得不指出,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作为受害方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宽容、“健忘”乃至“超越历史”的“为尊者讳”,张承志的充耳不闻即为典型一例。就像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所说的那样,“看不到过去的人也就看不到现在”;在涉日研究、日本侵华时期中日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中更要有这样一种学术自觉,即:你伤害了我,但不能一笑而过。 注释: ①笔者参考的是伊藤整 川端康成等編:『新潮日本文学小辞典』(東京:新潮社,1968年)524,三好行雄編:『日本近代文学研究必携』(東京:学燈社,1977年)175,日本近代文学館編:『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東京:講談社,1977年)127,大久保典夫 吉田熈生編:『現代作家辞典』(東京:東京堂,1978年)184,『日本文学事典』(東京:平凡社,1982年)168,大久保典夫高橋春雄編:『現代文学研究事典』(東京:東京堂,1983年)103,三好行雄 竹盛天雄等:『日本現代文学大事典·人名事項篇』(東京:明治書院,1994年)161等七种文学史辞典、事典。 ②保田与重郎:『事変と文学者』、同氏『佐藤春夫』より(東京:弘文堂書房,1940年)120、121。须注意的是,这篇《事变与文学者》与下文所引的收入『文学の立場』(東京:古今書院,1940年)中的同名文章,虽均涉及佐藤春夫,旨趣相近,但是内容迥异。 ③笔者综合了以下信息:竹内好,『佐藤春夫先生と北京』290;竹内好:『北京通信·三』(原題『周作人随筆集--北京通信の三』、1938年9月『中国文学月報』第42号)、同氏『竹内好全集』第14巻(京都:臨川書店,1981年)120;保田与重郎,『事変と文学者』弘文堂書房版135;佐藤春夫,『蒙疆のはなし』205。 ④参见董炳月:《“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中对《亚细亚之子》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