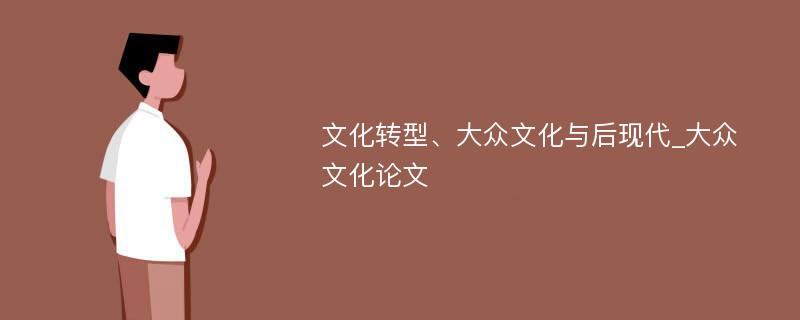
文化转型、大众文化与“后现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后现代论文,文化与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谈论“后现代”?
随着文化激进主义的政治/道德批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进程上又一次创伤性运动,“后现代”、“后现代主义”的推陈出新,成了许多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启蒙”理想失败后祭起的又一面理论旗帜。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大量援引和论争,不仅导致了对于90年代中国文学艺术状况的认识分歧,而且产生了更大规模的有关社会“现代化”诸问题的差异性要求。
在我看来,进入90年代,中国人所面临的最大现实,是社会变革运动及其导致的相应的文化活动转型、价值意识变异、现存体制内部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削弱,而不是所谓“后现代”社会、文化的肆意入侵和大面积围剿。对此,我曾经指出过:“当今的中国社会不仅没有向我们提供多少真切具体的‘后现代性’(Post modernity),相反,在中国,‘后现代主义’由于缺少自己典型的文化语境——多元文化因素的并置,使得80年代末以后的中国文化(包括文艺活动和大众日常生活)进程呈现出令人深感困惑的一面——因而使得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因素和文艺现象都丧失了或根本不存在其典型性。这一切,庶几可以说明,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向现代化迈进的艰难进程之中,其文化价值模式和精神结构还有待形成现代品格或现代性(Modernity)。”〔1〕事实是,在讨论“后现代”问题的时候,许多人常常情不自禁地夸大了当前中国社会里某些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有着某种表象相似性的现象特点,对90年代中国社会的某些文化征候进行大胆的“后现代”释义,而很少有意识地顾及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文化变异特质,更缺少一种对今日中国文化现代化建构的具体策略。
毋庸讳言,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某些可描述的“后现代”文化表象,逐渐从敞开的国门缝里挤了进来。环视最近一些年中国文艺的种种迹象,就可以发现,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连续性变革中,“后现代”的某些价值倾向、精神要求,诸如深度消解、平面化、“解中心化”、文化碎片化、复制性,等等,其作为“后现代精神”的陈述性话语,至少在中国大众接触最广泛、也最频繁的影视、小说创作领域已经开始显山显水。从王朔小说的“痞子化”调侃,到新写实主义在文学文本上对日常状态的主动贴近,从“第五代导演”对“伪民俗”影像编码的集体热情,到各种“戏说”历史的电视连续剧不断成为电视观众的“精神快餐”……在文化表象的连续“拷贝”中,“后现代”在90年代中国文化价值流变的行程中为自己找到了不少热情的回声。然而,如果我们理智地考虑到当前中国文化进程的不确定性、变异性和意识形态上的特殊要求,考虑到80年代末以后中国文艺“后现代”表象的种种虚假性、混杂性和模仿性——仅在小说领域,我们便从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中读解出反抗权威的“后现代性”与执着自我的“现代性”之间的背反,从王朔的《顽主》看到藏匿在一连串肆无忌惮的调侃背后的浪漫主义理想的天真热情,从刘震云的《单位》发现具体生活的琐细无奈与小人物对自身感情的痛苦回忆之间的相互冲撞——那么,我们就能够知道,与其把90年代夸大为“后现代”在中国泛滥猖獗的时代,不如说这个时代是“后现代”不断在各种文本里被复制,但其中却又很少真正体现“后现代”典型特征或“后现代”被多元文化动机、利益所“异化”的过程。因此,在各种学术话语中引述“后现代”问题,真正的关键应该是把对“后现代”现象的讨论,同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所进行的特定“转型”联系起来。这不仅涉及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前途,更具体地说,它真正涉及了我们谈论“后现代”问题的现实语境。
说到这里,问题便很明显了。如果说,“后现代”问题在现实中国文化语境中具有某种“非典型性”,这种“非典型性”的现象存在只是这样或那样地呈现了一些“后现代”的价值表象,那么,谈论“后现代”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是否就毫无意义呢?否!这里的情况仍然涉及到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谈论“后现代”?在我看来,只有从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立场上来把握,我们才能有效地发现“后现代”问题在中国的变异及其特殊意义。
大致说来,90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主要表现在这样两方面:
第一,“前现化社会”向“现代社会”、“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应该说,这是从形态理论角度对当前中国社会状况的唯一可能的描述。它反映出,首先,9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方向,依然指向发展经济的总目标;“经济优先原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根本立足点,同时也是制衡社会转型的客观机制。因此,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所发生、暴露的一切,无不呈现出特定的“经济学意义”。这一点,对于80年代的中国社会历史来说,无疑是一种鲜明的扭转——尽管80年代中国社会同样强调经济变革的必要性,但是,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复杂纠葛,却始终是制约8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政治上的民主、自由、解放理想,更成为其中矛盾冲突的思想基础,它决定了80年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政治化”。这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无缘进入全面“转型”活动的基本原因。这一点,正是我们考察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前提:体制内部的政治变革要求并没有带来社会转型的理实轨迹,相反,以实现当前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活动却成为社会转型的直接迫力。而经济上的落后,则决定了中国社会所进行的,绝不是一步跨入“后工业状况”,它更多着眼于如何走向工业时代的发展前景。其次,社会转型的具体过程,不断强化了经济“现代化”的实际追求,肯定着“现代化”的物质主义理想。这是中国人百年来的梦想,如今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急切。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代化”主要还不是一种文化精神——尽管“现代化”必须凝结成一种精神的价值存在方式;“现代化”更实际地表现为社会转型中的物质积聚,是物质丰裕的社会进步形式。所以,面对西方工业化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种种精神不幸,中国人虽然也若有所思,但是,它们却不能不被现实的经济动机和物质欲望所淹没;一种强烈地期望尽早与西方世界并驾齐驱的现实欲求,使得“现代化”在今日中国始终表现为一种经济社会形式和物质主义的成就,决定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方向。
第二,由“冲突”的文化走向“保守”的文化。这种文化意识和文化形态上的转型,一则联系着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过程,是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迈进中必然出现的价值重构;二则又直接联系了整个80年代中国文化实践的具体经验,是对于80年代那种“两极对抗型”文化模式的强烈反拨。它意味着,中国文化经验开始从政治/道德层面的理想冲动滑入日常层面的现实生活诉求。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贯穿在主流文化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之间的,是一种以“政治/道德一体化”为价值立场的文化对抗运动,那么,这种文化“对抗”的突出特点,就是知识分子“精英”文化意识所强调的“政治/道德批判”与主流文化传统之间的绝对“权力对立”——在激进主义政治/道德理想下,知识分子“精英”文化意识对政治话语权力“中心”的极端追求,与主流文化意识对既有权力的坚定维护,两者间具有鲜明的不妥协性。而80年代末文化激进主义的失败经验,则促使曾经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终于产生了冷静反省自身的要求。文化激进主义之不可行,反过来促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新的文化实践——“文化保守主义”的迅速崛起。在放弃直接文化冲突、取消政治对抗的绝对性上,“文化保守主义”实践运动一方面倡导了价值意识的“非主流化”、“非中心化”,借知识分子的自觉“边缘化”而逐渐消解“政治/道德一体化”文化价值立场的权威主导性,推行温和平常的日常生活意志;另一方面,“文化保守主义”实践运动又充分认同了“三权分立”这一文化分层现实——主流文化话语、知识分子“边缘性”文化话语、大众文化话语分别守护着自身的理想观念,实践着各自的文化利益选择与追求。〔2〕由此, 文化的“冲突”为文化的“保守”所代替,“政治/道德一体化”价值立场的消解最终产生了90年代中国文化心理层面的巨大变异:对政治权威力量的疏离,对激进理想的淡化,对道德至上性的冷漠,以及对于大众日常生活的世俗化读解和当下利益的毫不掩饰的追逐。文化的政治/道德理性被赶出了大众神经兴奋的感觉活动,文化的历史规划被大众日常生活的现实表达和满足所取代。保守主义的文化价值意识通过肯定人的现实生存的直接利益,强化了世俗精神的普遍制约力。
可以认为,90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迄今仍在持续进行之中。“转型”过程本身所遭遇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矛盾,以及各种具体实践上的复杂性,决定了它仍然处在一种不断探求新的运动方向和价值建构的进程上: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以及后工业时代的诸多文化特性,在一种显然缺少相互间内在联系的过程中,却又奇特地相互集合在一个社会文化的共时体系之上。在显层次上,多元文化因素交错并置且又彼此克制;在深层次上,整个社会则处处潜在着文化变异的巨大可能性。在此情况下,谈论“后现代”问题就不能不考虑到,在一种结构不确定的程序交迭、因素混乱的“转型”现实中,任何一种文化因素、现象的运行和演衍,都可能不同程度地遭受其它文化导向性的“攻击”和制衡,从而在自身的归趋上形成不同的精神迫力和价值分裂。因此,90年代的中国,那种产生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体系下的“后现代”文化问题,也绝不可能单一地表现出它的历史必然的逻辑性和规范性,而总是会受到各种“转型”活动的深刻影响和侵入;尤其是,它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进程之于80年代的沉痛反拨性质。这样,站在90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立场上,我们一方面应当看到“后现代”作为某种文化表象的特殊性和混杂性,另一方面,更必须注意到,在“转型”中,“后现代”问题的出现所具有的潜在意识形态倾向:谈论“后现代”本身,便具有在反省80年代文化运动的基础上真正走入90年代风云际变的意义。
二、“后现代”与中国大众文化
在社会和文化转型背景下,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考虑到,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迅速扩张及其“后现代”的意识形态效应。
第一,进入90年代,文化分层的现实运动,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强势崛起与蔓延。如果说,80年代中国文化进程在主流与“精英”、国家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激进“政治/道德批判”两极间形成了一种“对抗型”的文化实践模式,那么,90年代中国文化进程则发生了根本改变——对现实利益的肯定,对大众日常生活价值形态的肯定,对世俗欲望的肯定,决定了以国家意志为宗旨的主流文化和以知识分子人文理想态度为核心的知识分子文化,都不能不更多地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向大众生活的实际立场和具体经验。文化分层的结果,突出了大众在文化上的言说权力及其现实合法化过程;文化价值的判断根据由政治/道德层面转向大众生活层面,转向世俗性的社会共同领域。对于主流文化而言,实现国家意识形态的前提条件,是如何可能在现实中顺应大众利益的基本准则,以使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同大众生活之间具有一定形式的“亲和性”(这在《焦裕禄》、《蒋筑英》、《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等“主旋律”影片中得到了明确的释义);对于知识分子“边缘性”文化话语来说,大众文化的广泛性和普遍效力,及其世俗性的生活体验和日常活动,对于消解主流文化话语的正统性,疏远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乃是一种合法而有力的保障。质言之,在90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进程上,大众文化意志的强力推行,对于任何一方文化权力的实践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基本存在。因而,大众文化本身也已开始逐渐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存在。
第二,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在最基本的价值形态方面,确立了自身的“世俗性立场”:强调日常生活的生存象征意义和现实功能,强调物质满足的感性实践,强调价值目标的“当下化”,强调形象生存的合法利益。这样,对于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而言,其生成和发展过程便具有了某种与“后现代”文化效应的联系(尽管它仍然缺乏“后现代”的典型性),即潜在的“解中心化”生活叙事和显著的“平面化”文化效应。它表明,首先,对于大众的现实热情而言,“政治/道德一体化”价值立场已不复体现其旧有的“中心”合法地位,以往作为日常生活叙事主体的政治/道德话语——无论是代表国家意志的,抑或体现为知识分子人文理想的——已经被放逐出日常生活的价值存在方式;大众日常生活活动作为一个政治/道德文化的“反题”,具有了充分生动的现实性,实现了大众利益的具体化和普遍化。其次,对于大众文化的价值建构理想而言,体现某种深度模式的“政治/道德一体化”所标榜的普遍理性、完善化理想、崇高的生命意义,由于缺乏直接满足日常生活动机和利益的现实性,而只能是空洞无力的浪漫精神装饰,并且也无法真正用以引导和评判现实生活;相反,那些直接指向大众生活的当下利益、表达大众现实要求的各种世俗活动,尽管没有体现任何具有实质深度的价值持久性和精神永恒性,然而,它却有可能通过平凡而富有诱惑性的欲望满足,安慰大众对幸福生活的具体“渴望”,实现大众生活的现实梦想。因而,生存价值和现实活动的平面化,不仅不是什么必须掩饰的粗陋东西,相反,却是文化“冲突”归于平静的时代为大众文化所确立的合法身份。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具有了与“后现代”的某些特殊的“相似”:它以消解“政治/道德”理性权威性的方式,在放逐各种形上思考的同时,肯定了人生意义的平凡性和生存活动的现实要求,突出了日常生活的具体目标;它以对“崇高”价值理想、“英雄”创业神话的拆解,强化了大众世俗欲望的实际追求和满足,提高了世俗性存在的地位;它以大众利益的当下满足,破坏了具有历史主义特征的理想精神模式,把现实活动从精神性高度重新拉回到平常百姓具体感受经验之中。应该说,这也正是目前大行其道的“家庭问题”影视剧所表现的东西:当《孽债》在荧屏下大把大把地赚取观众同情的泪水时,从人们感觉层面浮起的,也许并不是一种对于反人道的、扼杀人性的“文革”历史的沉痛追忆和反思性批判,而是几个普通家庭的感情跌宕,以及人们对于那份人际亲情的面对面的经验。对“文革”的政治批判,在几亿最普通的人群中,流失为一份用伤心的眼泪来拌和的感情债务,而不再是对“伤痕”的控拆和戴厚英式的“人啊,人!”的深长吁请:生存的人性从它的深度中退出,一头扎进了日常世界的感性形象之中,并在《一地鸡毛》中变得《儿女情长》。
从大众文化的汪洋高涨中,我们看到,如果说,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中“后现代”现象的“非典型性”,源自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过程的特殊变异,那么,作为一种表象的存在,90年代中国文化景观中的某些“后现代”现象,便总是以一定形式同大众文化意志的勃兴、大众生活话语的运作联系在一起。因此,一方面,我们对于“后现代”现象的把握,必须具体到现实中国的大众文化层面来进行;另一方面,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本身特定的意识形态性质,又使得目前情势下谈论“后现代”问题,绝不应该成为一种理论话语的游戏方式,而必定反映潜在文化权力更迭与重生要求。
注释:
〔1 〕参见拙著《扩张与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话题》,第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参见拙文《文化经验·文化语境·电影文化》, 载《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