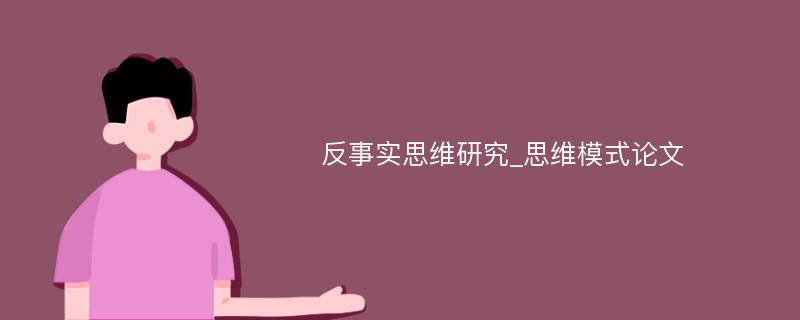
关于反事实思维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实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2.5
思维是人类的高级心理活动,但无论就其过程还是就其对象而言,思维都并非是完全合乎理性的。个人的思维活动受情绪状态、动机水平等非认知因素的影响,而并不像规范模型描述的那样完全按某种抽象规则系统来进行。在现实生活中,思维活动所指向的对象或内容并不都是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件。任何人都有过对已经发生的事件产生与事实相反的思维活动的经历,其典型表现为:“如果当时……,就会(不会)……”。例如,“如果昨晚上不熬夜,今天就不会迟到”、“要是你再努力一些的话,这次考试就能及格了”。这种在心理上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否定并表征其原本可能出现而实际未出现的结果的心理活动,是人类意识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种心理活动长期被心理学家所忽略,仅为一些哲学家所研究。自本世纪80年代Kahneman等人第一次提出“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以来[1],心理学家开始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本文拟讨论这一研究领域的进展情况。
1 反事实思维的类型
反事实思维在头脑中主要以条件命题的形式来表征,包括前提(如,“如果昨天晚上不熬夜”)和结论(“今天就不会迟到了”)两部分[2]。其假设性就表现在前提和结论都与既定事实相反,但在心理上却获得了某种可能性。根据前提的性质,可以区分出三种反事实思维类型[3]。加法式(additive)是一种在前提中添加事实上未发生的事件或未采取的行动而对事实进行否定的反事实思维。例如,在“要是当时带着雨伞就不会被雨淋湿了”这一假设命题中,前提“带着雨伞”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而是在事后回想时加上去的。减法式(subtractive)假设与此相反,它在头脑中假定某个既定事件并没有发生,从而对事实进行否定和重新建构。例如,“要是早一点动身,就不会被淋湿了”。第三类假设是替代式(substitutional),比较少见,指的是假设在前提中发生的是另一个事件。例如,“如果以前努力学习而不贪玩的话,这次考试可能就及格了”。Roese和Olson发现,产生何种反事实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件结果的性质。正面事件通常引发减法式假设,负面事件则多诱发出加法式假设。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人们对于成功和失败有着不同的预期和需要。多数人都渴望成功而厌恶失败,倾向于把成功看成是个人有目的行动的结果,而把失败归因于未能正确地采取行动,所以在对事件进行假设否定时便会相应地排除或增加这种行动以验证自己的假设。此外,一些个体差异因素如自我价值感等也影响到反事实思维的类型。高自我价值感者与低自我价值感者相比,更多地使用减法式假设。这与两类人对成功和失败的归因方式不同有关,也就是说,自我价值感和结果的性质对反事实思维产生类型的影响机制是相同的。
在对某一事件进行反事实思维时,根据其命题结论的性质,可以区分出上行和下行两种假设方向[4]。上行假设(upward counterfactual)是指对于已发生的事件,想象其如果满足某种条件原本可能出现比事实更好的结果。例如,“如果起跑时再快一点,我就能拿到金牌了”。下行假设(downward counterfactual)则是假设一种比事实可能更坏的结果,如“要不是第三名最后慢了一步,我恐怕连银牌也拿不到”。这种划分方法类似于社会比较理论中上行与下行社会比较的划分,事实上,反事实思维与社会比较有着紧密联系,反事实思维过程中常伴随着社会比较。但社会比较是将自己的结果与他人作比较,两个结果都是客观存在的;反事实思维却是把已经出现的结果和原本可能但实际未出现的结果进行对比。上行和下行反事实思维各有不同的诱发因素。一般说来,碰到负面事件,人常常设想事情本可以做的更好一些,容易产生上行假设;正面事件则容易使人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研究表明,在日常生活中,上行反事实思维自发产生的概率远大于下行假设。
上述两种分类方法并不完全独立,而只是考察的角度不同而已。某一具体反事实思维可以同时属于其中的一种,如,可以既属于上行假设,又属于加法式。除了这两种分类取向之外,Kahneman还把反事实思维视为一个从自动加工到精制加工的连续体[5]。他认为,精制假设加工是有意识地在头脑中模拟事实的某种替代方案,需要经练习才能形成;自动加工却是由事件产生而自动引发的,从认知角度就能够加以解释。在自动加工和精制加工之间还存在一些中间类型,因其所需的心理努力程度不同而异。就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来看,心理学家对自动假设加工的研究较多,而对精制加工则很少研究,这可能是因为精制加工产生机制比较明显的缘故。本文所讨论的有关研究也以自动加工为主。
2 反事实思维的产生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人为什么会产生反事实思维?它受哪些因素影响?Roese认为反事实思维的产生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激发阶段和内容产生阶段,被称为两阶段模型[6]。时间顺序是其主要划分依据;激发在前,内容产生在后,激发是内容产生的必要前提。两个阶段各有其不同的影响因素。
2.1 激发阶段
激发涉及反事实思维是否开始产生的问题。例如,某个学生考试成绩不理想,那么他是考虑自己本可以考得更好,还是仅仅只关注当前的实际成绩,这就反映出反事实思维能否被激发。在前一种情况下,该学生很可能通过思考可以获得好成绩,从而进一步在心理上构建出一个假设命题,即假设过程已开始。第二种情况则因为没有对事实的心理否定而很难形成反事实思维。
由事件引发的情绪是影响假设过程的主要因素。其中,负面情绪又比正面情绪具有更强的激发强度,它将人的思维方向引导到如何避免这种负面情绪上来,由此想象出一种比现实更好的(上行)假设情境。Davis等人曾对丧失亲人的被试作过追踪研究。被试在事件(孩子意外死亡)发生后三个星期时的负面情绪强度准确地预测出了5个月后报告的反事实思维的发生频率。越感到悲伤,以后产生反事实思维(孩子本可以避免不幸事故)的可能性越高[7]。Sanna和Turley研究了结果的性质(正面和负面)及预期(得到证实和未得到证实)对反事实思维产生的影响,在从对考试成绩的反应到字谜游戏共三个实验中,都得到了负面的结果比正面的结果更能激发起反事实思维的证据[8]。
影响激发过程的第二个因素是结果的接近性(closeness),指个体在事后知觉到的实现某一目标的难易程度。比如,两位乘客分别差5分钟和差30分钟没赶上火车,尽管事情结果相同(都得等下一班车),但只差5分钟的乘客更容易想到自己只差一点就能够赶上车了,由此产生比另一位乘客更强烈的反事实思维和负面情绪。Meyers-Levy用故事法作过一项研究,给被试看一篇叙述某人忘记续投保险而三天后或六个月后家中发生火灾的文章。结果表明,看到三天后发生火灾的被试更容易引发反事实思维[9]。不仅在时间上的接近,空间的接近(如长跑运动员在中途被别人超出和在即将到达终点时被超出的接近性就不同),甚至数字上的接近(如自己的奖券与中奖号码只差一位或差多位)都容易产生反事实思维。对于下行反事实思维来说,接近性的作用更为关键。因为下行反事实思维很少能自发出现,而如果个体意识到自己险些碰到某一不幸事件时,便很容易产生下行假设。
除了情绪和结果的可接近性以外,其他如对前提事件的预期、对问题的卷入程度等也对反事实思维的激发有一定作用,但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却并不一致。例如,Sanna和Turley的实验表明,结果与预期不符能引发更多的反事实思维[8];而Roese的研究却没得到这一结果。目前对这些因素都在进一步的研究之中。
2.2 内容产生阶段
个体受到激发并关注于原本可能出现的结果后,反事实思维就进入了内容产生阶段。以前面的学生考试成绩不理想为例,是否考虑自己能取得更好的成绩是激发阶段的问题,而一旦他开始思考当初采取何种行动可能会取得好成绩时,就意味着假设命题开始形成。由此也可以看出,激发阶段和内容产生阶段很难加以清楚的划分,对于自动假设加工更是如此。这是反事实思维研究的一个难点。从理论上讲,对于任一事件结果都可以设想出数目近于无限的假设前提条件加以否定,从而产生大量内容不同的反事实思维。但事实上,反事实思维总是遵循一定的规则进行的,有很多因素制约着它对假设前提事件的选择。
前提事件的规范性对反事实思维的内容有很大的影响,真实事件对规范的偏离构成了反事实思维的基础。根据Kahneman和Miller的定义,规范(norm)是由过去经验形成的对某类事件的一般性知识和预期[1]。当个体觉察到某一特定事件异于常规或者和预期不符时,便倾向于运用反事实思维对其进行修正,在心理上使之恢复可能的正常情况。大量实验证实了规范性对反事实思维的这种决定性作用。一个经典的例子是Kahneman和Tversky的研究[10]。在此项研究中让被试读一篇关于交通事故的文章,内容是某人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因车祸身亡。一组被试了解的情况是,遭车祸者回家所走的路与往常一样,但时间比平时要早;另一组读到的却是遭车祸者按正常时间下班回家,选择的路径与平时不同。回家时间过早和走一条平时不常走的路都与规范性有所偏离,结果在要求被试考虑这次事故怎样有可能不会发生时,两组被试都表现出了把事故归结为偏离了规范的倾向,认为如果遭车祸者按往常时间或走以前的路回家就不会发生这次车祸。
对于规范性原则,心理学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前提事件偏离了规范,就可能产生恢复规范的假设;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仅限于结果也偏离规范的情况。Gavanski和Wells提出,假设判断依据的是对应式启发(correspondence heuristic),即特殊结果被认为是特殊前提造成的,正常结果则被认为是正常前提造成的。他们的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通过修正特殊前提来修正特殊结果,如果正常前提或特殊前提进一步向偏离规范的方向发展,则正常前提也会被修正[11]。对应式启发有一定的道理,尽管它只适用于现实生活中一小部分反事实思维的情况,但却指出了规范性原则和Kelly的共变原则以及动物学习理论条件作用之间的联系。
在事件中个人是否有所积极行动也影响到反事实思维的内容,采取行动通常比未采取行动能够引发出更多的反事实思维。Kahneman和Miller的一个实验表明,尽管故事中的两位投资者分别因为转投其他股票和未转投其他股票而损失了同样多的资金,但被试却推断前者会比后者更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而感到后悔。关于是否采取行动对反事实思维的影响作用,Kahneman认为可以用规范性原则进行解释(采取行动是不正常的,未采取行动是正常的)[1]。Roese、Gilovich又分别提出结果的性质和时间制约着这种作用的发挥。人们在成功后倾向于对采取过的行动进行假设,在失败后倾向于对未采取行动进行假设。同时,在短时间内反事实思维更多地注意采取过的行动,但时间一长,则会对未采取行动更加在意[12.13]。
影响内容产生阶段的第三个因素是前提的可控性(controllability),可以控制的前提事件比不可控制的更容易被假设。例如,在Girotto等人的一项实验中,被试对于事件(某人未能及时驱车回到家中)产生的反事实思维主要集中于可以控制的事情(如中途停车吃饭等),而较少涉及不可控因素(如遇到堵车)[14]。可控性与是否有所积极行动的作用有一些重合,一般说来,个人所采取的行动通常被认为是可控的,未采取的行动则多被认为是无能为力的。
3 反事实思维在个体生活中的作用
反事实思维对人的很多心理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包括对情绪、态度、预期、因果判断等都有一定的影响。Roese将其作用概括为两大类:情绪功能和准备功能,并提出了产生上述影响作用的两种机制,即效应比较和因果推论[2]。效应比较以某种反向事件或结果作为标准进行判断,使得结论更加极端。例如,想象一种与事实不同的正面结果会使人对现实结果更加不满意;反之,想象事情差点会更糟糕则让人对现状比较满足。因果推论机制指的是在假设条件命题中,构建前提和结论的因果联系。这两种机制对心理活动的作用有时比较一致,但也可能会彼此冲突。总的来说,效应比较往往引发负面情绪,因果推论则一般起正面作用。
3.1 情绪功能
影响人们对事件情绪和满意度的因素不仅仅是结果的客观性质,更重要的是人对结果的认知解释和比较,其中就包括实际结果与假设结果的比较(效应比较)。进行这种假设比较的可能性越大,即想象出一种可能结果的概率越大,反事实思维对满意度的影响就越大。就影响的性质而言,上行反事实思维多引发负面情绪,使人对未得到更好的结果感到后悔、内疚和自责;下行反事实思维则能使人意识到避免了可能更坏的结果,因而产生庆幸、满足等正面情绪。
对于同样的事件结果,不同的反事实思维可以引发不同种类的情绪。Niedenthal、Tangney的研究发现,对自己的能力、人格等进行反事实思维会较多地产生羞愧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假设则会较多地产生内疚感[15]。Medvec、Madey等的一项研究还发现,对于不同的结果,不同反事实思维引发的情绪甚至可能与结果的性质刚好相反。他们对115名纽约州运动会银牌和铜牌得主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银牌获得者对成绩的满意度要小于铜牌获得者,这与人们通常的想法不一致。其原因就在于银牌获得者往往会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差一点就拿到金牌了”,而铜牌获得者却容易想到“差一点就拿不到奖牌”[16]。
在事件中是否有所行动也影响到反事实思维产生的情绪。很多实验都得到了人们对于因自己的行动而导致负面结果要比因未采取行动而导致同样后果更感到后悔的证据,但这也与日常生活经验不符,一般人们更容易后悔以前未做某件事。出现这种不一致,可能是因为后悔体验存在着一定的时间特征或模式,即在短时间内人们更容易后悔自己做的某件事,随着时间进展,却可能会对未做某事更感到后悔。
除了与事件有关的影响因素以外,一些个人因素也对反事实思维的情绪功能有一定作用,如自我价值感、对未来的关注程度等。Boninger等人的研究发现,对未来关注程度高的人由于会更多地考虑假设性的结果如何在以后能够实现而缓解负面情绪[17]。Roese、Olson的实验证明,高自我价值感者无论是进行下行还是上行反事实思维都会比低自我价值感者体验到更高的满意度[3]。
3.2 准备功能
反事实思维的准备功能主要通过因果推论机制来实现。前已述及,反事实思维在头脑中表现为条件命题“如果…,那么…”的形式。尽管其前提和结论都是假设的,但通过对原本如何就能够避免失败或获得成功进行心理模拟,有可能使人意识到出现问题的真正原因,从而为以后采取相应行动以获得渴望的结果奠定基础。有一些假设也可能转化为未来结果的脚本,并借助于因果推论影响人对未来的预期以及对以后获取成功的希望。在认识到事情原本可能会有另一种结果时,人们容易产生一种坚持或改进原有行为的愿望,并增强对以后处理类似事情的信心。McMullen等人证实了这一点,在他们的实验中,上行反事实思维增强了被试对事件的控制感[18]。
不同类型反事实思维的准备功能有所不同。一些相关研究发现,对学习成绩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的频率与成绩的提高以及改进学习习惯的愿望有一定的联系,下行反事实思维却没发现有这种情况(注:NascoS A,Marsh K L.The effect of upward counterfactuals on subsequent test performance.Paper presented at the Midwestem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Conference,Chicago IL,1996,235-247.)。这说明上行比下行反事实思维具有更强的准备功能。Roese对此进行了直接验证,结果发现,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的被试确实比控制组和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的被试更愿意在以后改进行为方式[2]。另外,加法式也比减法式反事实思维更有利于以后的成功,这可能是因为加法式反事实思维着眼于以前未采用过的新方案,比只关注于既定行为的减法式更为明确、更有创造性的缘故。
反事实思维的准备功能不仅得到了实验证明,在临床上也获得了一定证据。对前额叶皮质损伤病人的治疗发现,他们不能够进行反事实思维,容易重复犯同一种错误[19]。这也说明反事实思维能对行为的计划和执行产生重要影响。
4 反事实思维的研究方法
4.1 故事法
该方法的一般程序是,先要求被试阅读一篇介绍某人因某种行为而导致正面或负面结果的剧情脚本或短文,让其设想自己便是故事的主人公,然后再就这一事件进行反事实思维,或者直接让被试判断主人公会有什么样的思维活动和情绪感受。故事法的缺点在于,研究结果受被试动机、移情能力等个人因素的影响较大。但由于反事实思维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模拟现实情境的复杂性,所以它仍然是研究者运用最多的一种方法。
4.2 跟踪调查法
跟踪调查法在研究中运用的也比较多。在现实生活中某类事件发生之后,研究者通过各种途径与当事人取得联系,调查其在事后对该事件的感受,从而获得相关的资料。Davis和Medvec、Madey的研究便是运用跟踪调查法的两个例子[7,16]。它的长处在于外部效度高,被调查者的反应非常真实。
4.3 实验法
在实验室中创设类似于现实的任务情境,把完成情况(真实成绩或主试有意制造的虚假成绩)反馈给被试,要求他们对结果进行假设,进而测量其情绪反应和行为表现。
4.4 自我报告法
自我报告法类似于追踪调查法,也是针对事实事件进行的研究。不同之处在于,追踪调查法由主试确定所要调查的事件,而自我报告法则是由被试主动回忆个人近期生活中的某件事并报告其相应的想法和感受。
总的来说,反事实思维的研究方法主要就是上述四种。不同方法各有其不同的优缺点,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这是造成理论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如何改进研究方法就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5 未来的研究趋向
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反事实思维的产生机制仍将是今后一个主要研究领域,关于负面情绪引发反事实思维的研究将从目前仅局限于对后悔悲伤情绪的探讨扩展到包括发怒、忧虑等在内的更广的范围。同时,情绪与反事实思维交互作用机制的研究也将进一步深入。反事实思维对各种心理活动的影响则会成为另一个研究热点,其中以对归因推理影响的研究最为突出。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国内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少。我们有必要了解中国人反事实思维的特点,以促进教育、咨询等部门相关工作的开展。
标签:思维模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