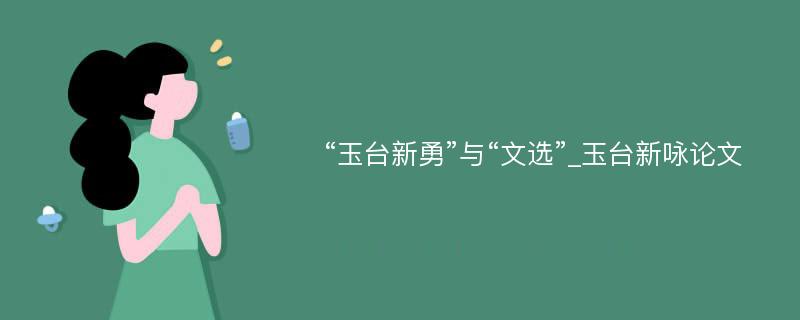
《玉台新咏》与《文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玉台新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选》
一、《文选》和《玉台新咏》编撰目的和编辑体例比较
《文选》和《玉台新咏》都产生在南朝梁时,分别是由萧统和萧纲兄弟二人所主持的两部书。不过前者是诗文总集,后者只是诗歌总集。从编辑的时间看,《文选》编成在先,大约从梁普通三年(522)至六年(525)开始,完成则在大通元年(527)末至中大通元年(529)之间(注:参见拙作《〈昭明文选〉研究》下编第一章第一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164页。);《玉台新咏》编成在后,当在萧纲为太子时的梁中大通四年(532)至大同元年(535)之间(注:参见拙作《〈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再讨论》,载《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三期。)。这一前一后不同的编辑时间,使得二书的编辑目的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文选》的编辑目的主要是为了对前代文学进行总结,同时作为当时人学习的典范,它没有多少政治目的,只是萧统养德东宫时的文德表现。《玉台新咏》的编辑就不同了,它其实带有很明显的政治目的,即一是要取代萧统倡导的文风,二是为艳体诗张本。关于《玉台新咏》这个政治目的,我在《〈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再讨论》一文中有详细的分析,可参看,兹不赘。宫体诗人的文学主张是新变,这一点,是贯彻于几乎每一位宫体诗人的言论中的。比如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批评京师文体“懦钝非常”,而主张“吟咏情性”之作。萧子显更明确地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种文学主张在创作上表现为艳情诗,《梁书·徐摛传》说徐摛 “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是明证;在批评观上则对古代作家作品持批评态度,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所列三体,就是这种态度的表现。因此,从本心上说,宫体诗人对前代作家作品不会给予太多的赞扬,因而作为这种批评态度代表的《玉台新咏》(注:本文依据的《玉台新咏》,均指明崇祯年间寒山赵氏覆宋本。),实际上应该只选齐梁时期作家作品,只是由于萧衍的批评,他们才不得不在前三卷选了一些汉魏作家作品,所谓“大其体”也。即使这样,在比例上《玉台新咏》仍然表现出明显的重今轻古倾向。这一点与《文选》是有很明显的差异的。《文选》的目的是在对前代文学进行总结,这势必要求它要充分重视古代作家作品,虽然在《文选》赋、诗、文三部分中比重有所不同。比如赋的部分,《文选》基本选录至刘宋为止(注:例外的是江淹,但江淹《恨》、《别》二赋也都创作于刘宋时期。),其中又以两汉与西晋为多,充分显示出重古的倾向;诗的部分略有不同,依次为西晋、刘宋和建安三个朝代。这是因为两汉是赋的辉煌时期,而诗则到了魏晋以后才发展起来。文的部分有点特别,总的情况与赋、诗相同,仍以汉、晋、宋为重,但梁代作家有一个人例外,就是任昉,一个人独占17首,因此使得《文选》选文的部分有点详近的倾向。不过,我们以为,任昉一个人的情况是个特例,这并不影响萧统详古略近的批评观。所以说,《文选》和《玉台新咏》,在文学批评观上,是有着重古和重今的区别的。
其次,在收录作家的编选体例上,二书也完全不同,《文选》采取的是不录存者的体例,书中最晚卒世的作家是陆倕,所以我们知道此书最后编成于陆倕卒世之后。《玉台新咏》的编例却是卒世和存世的作家并录,依据我们的研究,《玉台新咏》前六卷为已故作家,卷七和卷八则录当世现存的作家(注:参见拙作《〈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再讨论》。),卷九、卷十分体裁录历代作家作品,与前八卷体例不同。这两种体例实际是为两种不同的编选目的服务的。《文选》不录存世作家,这是采用当时的通例,如《诗品》、《文心雕龙》等,都不对当世作家进行品评,当然是为了便于评价。《文选》应当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这样更有利于文学史评价,从而能够达到预期总结的目的。《玉台新咏》的编选与《文选》目的不同,它没有对古代艳情诗作总结的需要,也不需要进行评价,它的选录古代作品,纯粹是为了“大其体”,其主要目的还是要树立一种新文风,表现新太子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因此,这一点决定了《玉台新咏》当然以当代作品,尤其是以萧纲等人作品为主。今据赵氏覆宋本所录宋本《玉台新咏》各卷所录作品数量可见,前三卷共123首,四至八卷共261首。若就单个卷的情况看,以卷七萧氏父子作品最多,六人共录75首作品,排各卷之首。若以个人收录情况看,当以萧纲为首,他一人在卷七中就收录了43首,若加上卷九、卷十,全书共收80首,由此可见《玉台新咏》以萧纲为中心的编辑宗旨。这个比例在卷九和卷十中也一样,卷九收汉魏晋28首,刘宋10首,齐梁以来共46首其中已故者沈约等人是13首,存世者为33首(注:按,赵本卷九末著录100首,实则89首;卷十著录153首,实则155首。)。卷十改汉魏晋14首,刘宋8首,近代杂歌等民歌20首,齐梁已故者43首,存世者70首,编者详近略古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就《玉台新咏》所录作家看,除了萧衍、萧纲父子入选作品数量占绝对多数外,其余的如鲍照17首,沈约31首(卷九末附《八咏》六首,当是后人所加,故不予统计),谢脁16首,何逊16首,吴均40首,都比存世的宫体诗人作品多,一方面表明了这些作家对艳体诗的写作态度,另一方面也表明梁后期宫体诗的蓬勃开展,的确不是一时来风,而是有历史渊源的。从这一点说,萧纲他们要“大其体”,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关于《玉台新咏》的编辑目的,跃进教授的研究是旨在收录乐府作品,即以能否入乐为标准(注:《玉台新咏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5-97页。)。这个说法很有启发性,的确,南朝艳情诗多在乐府中演唱,而且汉魏以来的清商乐多是女乐,这与艳情诗也比较符合。这个观点是可以讨论的,是否合于事实,有待更进一步的材料来证实。不过说《玉台新咏》均为乐府作品,似乎还值得讨论,比如作品中有不少不为《乐府诗集》所收,明显是徒诗。如陆机、陆云的赠答诗、江淹的《杂诗》等,并没有材料证明是乐府。
二、《玉台新咏》、《文选》对作家作品著录的比较
对古代作家作品展开批评,是齐、梁时期文学独立发展的标志,我们在《文心雕龙》、《诗品》等中都看到了这一点。不过古代作家作品从汉魏以来至于齐、梁,时代已远,真伪莫辨,因此,对作品的认定,是齐、梁批评家一大任务,我们从各家不同的著录比较中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学史观。就《玉台新咏》和《文选》讲,虽然产生时代不远,而且主持者同是萧氏兄弟,又同是太子身份,这表明他们能够利用的材料相差不多,但是我们发现二书关于古代作家作品的认定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古诗的著录上。
《玉台新咏》卷一收录的古诗有《古诗八首》,即:“上山采靡芜”、“癝癝岁云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四座且莫喧”、“悲与亲友别”、“穆穆清风至”;《古乐府六首》:“日出东南隅行”、“相逢狭路间”、“陇西行”、“艳歌行”、“皑如山上雪”、“双白鹄”;枚乘诗九首:“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兰若生朝阳”、“庭前有奇树”、“迢迢牵牛星”、“明月何皎皎”;苏武诗一首:“结发为夫妇”;蔡邕《饮马长城窟行》一首,以上诸诗,南朝时各家著录多有不同。关于《古诗八首》,《文选》有四首与《玉台新咏》相同,即“癝癝岁云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收录在《古诗十九首》中。另外的四首,《文选》不收。《古乐府六首》,《文选》不收。枚乘诗九首,《文选》除了“兰若生朝阳”一首外,均收录在《古诗十九首》中。从以上二家著录情况看,它们主要的分歧表现在对枚乘诗的认定上。从《文选》收录作家情况看,汉代作家被承认的有苏武、李陵、班姬等,但无枚乘。事实上枚乘诗的可信性在南朝时期并不高,除了《玉台新咏》所录为枚乘诗外,尚未见其他人著录。即以《玉台新咏》所录这九首而言,从晋人陆机开始,至刘宋时的刘铄(注:《文选》载陆机《拟古诗》十二首、刘铄《拟古》二首,均以为古诗。)、梁时的萧统及唐初的《艺文类聚》,均作古诗,可见枚乘作诗一说,南朝以迄唐初,都没有人相信。南朝时江淹作《杂体诗》摹拟汉以来作家三十家,汉人有李陵、班婕妤,但无枚乘。又钟嵘《诗品》于汉人也仅评李陵、班姬,亦未称枚乘有诗。《文心雕龙·明诗》则说:“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对枚乘诗表示怀疑。其实不仅枚乘受到多数人怀疑,即使苏武,也只是到了梁代,才有人称其有诗。据逯钦立先生《汉诗别录》说,《隋志》只有《李陵集》二卷,不言苏武集,而宋、齐人凡称举摹拟古人诗者(注:参见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亦只有李诗而无苏武,因此,流传晋、齐之李陵众作,至梁始析出苏诗。所以萧衍有《代苏属国妇》诗,萧统《文选》和徐陵《玉台新咏》也才收录所谓的苏武诗。在这之后如《全北齐文》载君义尚《与徐仆射(陵)书》说:“苏武‘河梁’,叹平生之永别”,可见北朝也是这时才相信了苏武之诗。又庾信入北之后,在《哀江南赋序》、《小园赋》、《赵国公集序》、《拟咏怀》中多次使用李陵、苏武赠别之典,都是梁以后之事了。唐代李善为《文选》所录《古诗十九首》作注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从诗中所涉东都之事明辨非枚乘之诗,所以见出萧统的审慎。至于前人有云,徐陵少仕于梁,为昭明后进,不敢明言其非,乃别著一书,列枚乘姓名,还之作者,殆有微意焉(注:见朱彝尊《玉台新咏书后》,清乾隆三十九年长州程氏《玉台新咏》刊本。)。此语未免不识瑕瑜。不过,既然《文选》已经明言是古诗,何以徐陵还要著录并不可信的枚乘呢?这也可以看出徐陵秉承萧纲旨意,故意要立异的动机。
有意立异还反映在对《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边草”)一诗的认定上,此诗《文选》作为古乐府,《玉台新咏》却题为蔡邕作。与《文选》持相同立场的有《艺文类聚》、《乐府解题》和《乐府诗集》等,不过,《艺文类聚》作为古诗,而《乐府解题》和《乐府诗集》都是作为乐府古辞。其实古诗与古乐府并无太大的区别,当初也就是入乐与否的问题,但在流传的过程中,乐谱失传,古乐府也已不再入乐了,所以古诗和古乐府间的差别就消失了。比如这首《饮马长城窟行》,《古今乐录》引王僧虔《技录》就说:“《饮马行》,今不歌。”(注:《乐府诗集》卷三十八,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1066页。)此诗在齐时就已经不入乐了,所以有的题作古诗,有的题作古乐府。乐府、古诗互称,其例甚多,可参见曹道衡师《乐府和古诗》及拙作《从〈文选〉选诗看萧统的诗歌观》(注:曹师文见其《中古文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拙文见《国学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样看来,题作蔡邕的,似乎仅《玉台新咏》一书,至于《乐府解题》说:“古词,伤良人游荡不归,或云蔡邕之辞。”“或云”者,可能就是指的《玉台新咏》。
三、《玉台新咏》与《文选》的文学观比较
南朝时期的作家和批评家其实都认识到文学要变的道理,所谓“变则通,通则久”(《文心雕龙·通变》),但如何变,却又有区别。萧纲一派主张的是新变,萧子显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统也主张变,他在《文选序》中一开始就说:“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要求变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但是萧统与萧纲不一样,并非一切都以新变为好。他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明确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淫,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这与萧纲是完全不同的态度。这种不同的文学观,也很鲜明地表现在《文选》和《玉台新咏》中。这一点在前文所述二书不同的编选体例中已经表明了,相比较说来,《文选》重古,《玉台》重今。在题材的选择上,《文选》诗类将历代诗歌题材分为二十四小类,收录六十五位诗人四百六十多首诗歌,收录范围广泛,但却不收艳情一类。事实上《文选》连女诗人作品也控制极严,仅收录班婕妤一家。此外,《文选》对产生于民间的文学也并不欣赏,所收无名氏作品仅有汉末古诗,收录十九首。但汉代古诗实际是汉末文人所作,其题材内容和艺术成就是受到魏晋以来文人高度评价的,格高韵古,是合于萧统的文学观的。至于《文选》所收的汉乐府四首(注:李善本《文选》载三首,五臣本载四首,此从五臣本。),与五言诗没有什么差别,事实上《饮马长城窟行》一诗,《玉台新咏》就作为蔡邕的作品。汉乐府中真正具有民歌风格的作品,《文选》并不收录。对于秦汉以来历代流传的民间乐歌,乃至南北朝乐府民歌,《文选》更加不予收录,据此可以见出《文选》重雅正的诗歌观。在这一点上,《玉台新咏》似乎完全不同于《文选》。首先,《玉台新咏》确定以艳情题材为写作和编集的目的,已表示与《文选》的不同。在对作品的选录上,不仅文人作品在收录之列,对历代民间歌谣,也同样收录。我们看到,除了古诗、古乐府以外,《玉台新咏》还收录了历代民谣,如卷一的《汉时童谣歌》一首、卷九的古歌辞两首、越人歌一首、汉成帝和桓帝时童谣歌各二首、卷十的古绝句四首、近代西曲歌五首、近代吴歌九首、近代杂歌三首、杂诗一首、丹阳孟珠歌一首、钱塘苏小歌一首等,尤其是近代清商歌曲,在当时曾受到过批评,但《玉台新咏》却并不反对,这一方面说明了清商歌曲与宫体诗间的确有互动的关系,另一方面,史学家所批评的南朝时“家兢新哇,人尚谣俗”(注:《南齐书·王僧虔传》载僧虔上表语。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95页。)的时俗,在《玉台新咏》中的确有所反映。
作为一部通代文学作品选集,选录哪个时代的哪些作家,以及哪个作家的什么样作品、多少数量,毫无疑问都表现出编选者的总体评价。通过统计,我们看到《文选》收录作家、作品数量最多的是晋、宋两代,其次为建安时期,而收录作品最多的作家分别是陆机、谢灵运和曹植,与其所处时代在《文选》中占的比重相符,这表明了萧统的诗歌观。对比《玉台新咏》收录的作品,数量最多的是梁朝,作家则是萧纲(80首)、萧衍(41首),此外则是吴均(40首)、沈约(31首)、鲍照(17首)、谢朓(16首)、何逊(16首)。这个统计数字很有趣,除了萧氏父子以外,其他最活跃的宫体诗人如庾肩吾、庾信、徐陵等,数量都不多,庾肩吾共11首,瘐信和徐陵仅在卷八中各收录了3首和4首,这的确让人感到不解。不管从什么样的编选目的考虑,这样的选录比例都是不可思议的。唯一的解释,我们认为因为《玉台新咏》编成于大同元年(535)以前,所以这个时候像庾肩吾父子以及徐陵等其他宫体诗人写作数量还不多,而徐摛又不在入选之列,所以便呈现出这样的面貌。就庾信和徐陵所选诗看,能够确定写作时间的是《奉和咏舞》,这当是和萧纲所作。《艺文类聚》卷四十三同题诗中,除了萧纲外,还有刘遵、王训、杨皦、庾肩吾、刘孝仪、庾信、徐陵,其中刘遵、王训均卒于大同元年,所以确定这些诗作于此年之前。另外,庾信《七夕》诗,亦当写于大同以前。按,以七夕为题,晋以后历代多有写作,如刘宋时的孝武帝刘骏、谢灵运、谢惠连、谢庄等人,梁时有武帝萧衍、萧纲、沈约、柳恽、何逊、刘遵、刘孝威、庾肩吾、庾信等人均写作一首、两首不等。这种写作有的是个别行为,也有的是唱和之作,而唱和又可能分为不同的群体,如刘宋时以孝武帝为中心,谢庄就有《七夕咏牛女应制》,即应孝武帝之制,梁时又有以萧衍为中心的君臣唱和和以萧纲为中心的唱和的区别,刘孝威诗即题《七夕穿针和简文》,因此大概可以知道,沈约等人大约是与萧衍唱和,而刘孝威、刘遵、庾肩吾、庾信诸人则是与萧纲唱和。如果将庾信《七夕》诗作为与萧纲唱和的产物的话,则可知作于大同以前,因为一同参加唱和的刘遵卒于大同元年。庾信在南朝的作品,大多都毁于战乱,现存多是北朝作品,所以我们难以确定他在南朝时写了多少艳体诗,《玉台新咏》又为何只选三首,不过徐陵作品存世不少,而且多写于南朝的梁、陈时,其中有不少可以算作标准的宫体,如《春情》这一首:“风光今旦动,雪色故年残。薄衣迎新节,当炉却晚寒。故香分细烟,石炭捣轻纨。竹叶裁衣带,梅花奠酒盘。年芳袖里出,春色黛中安。欲知迷下蔡,先将过上兰。”(注:《艺文类聚》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应该有资格选入《玉台新咏》的,而没有入选,或许是作于大同以后吧!当然,后人用自己的意思揣度古人,是十分不科学的,我们并不赞成这样的分析,更不能作为证据。比如在入选的作品中,有许多都是在一组诗中挑选了几首,像萧纲的《雍州曲》本有十首,但赵氏覆宋本只选三首,说明徐陵对已经问世的宫体诗,也是经过了挑选的。但我们作这样的猜测,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它是在整体事实的基础上所作的合理推断。当然,这种推测要小心,只能作为参考,不能成为结论。同样,用诗歌纪年的方法来确定《玉台新咏》编成于大同元年以前,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多数作品无法确定时间,而且我们也不排除在历代的流传过程中,难免会掺入大同以后的作品。以上所言,只是我们根据《玉台新咏》编辑体例和编辑目的,考定其编成于大同无年以前的前提下,对本书为何收录梁朝当代宫体诗人作品数量不多的一点拟测。《玉台新咏》虽然收录梁朝单个作家诗歌数量不多,但总的数量却远远超过前代诗人,这仍然不影响我们对本书重视当代作家作品的判断。
通过两书的比较,我们还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文选》和《玉台新咏》都不收录北朝作品。《文选》不收,是因为它比较注重作品的艺术成就和在历史上的地位,北朝作家作品,尤其是一些稍有成就的作家,如邢劭、魏收等人,都还在世,不在入选体例,其余则远不够入选标准。《玉台新咏》目的与《文选》不同,它的选录标准是题材本身是否与女性有关,但像北朝作家作品,尤其是北朝乐府民歌中的女性题材不少,比如可与《孔雀东南飞》相媲美的《木兰辞》,也是够格入选的。当梁朝时,北方民歌已经传入南朝,并且在乐府中演唱,所以称作“梁鼓角横吹曲”,这说明徐陵是能够见到的,但《玉台新咏》不选,还是可以看出南朝文人对北朝作品并不欣赏。
《文选》在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隋唐时就产生了“文选学”,从此绵延一千多年,这是《玉台新咏》所不可比拟的。《文选》作为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国诗文总集,保存了秦汉以迄齐梁七个朝代一百多位作家七百多篇诗文赋作品,是后人研究和整理这一段文学的基本文献,又由于唐人李善为其作注,广征博引群书,以至成为训诂之资粮,也是后世“文选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些都是《玉台新咏》不具备的。《玉台新咏》由于选录的主要是艳体诗,为宫体张本,这种诗风在唐初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对《玉台新咏》的流传和研究,都是不好的影响。即使南宋陈玉父在整理刊刻《玉台新咏》之后,特地拉《诗经》以自抬高:“夫诗者情之发也,征戍之劳苦,室家之怨思,动于中而形于言,先王不能禁也。岂惟不能禁,且逆探其情而著之,《东山》、《杕杜》之诗是矣。若其他变风化雅谓‘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终朝采绿,不盈一掬’之类,以此集揆之,语意未大异也。顾其发乎情则同,而止乎礼义者盖鲜矣!然其间仅合者亦一二焉。其措词托兴高古,要非后世乐府所能及。”这也是《玉台新咏》现存各本均受损害的原因。但是《玉台新咏》的价值还是充分值得肯定的,首先它在《文选》以外为后人保存了许多作品,其中有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样优秀的长诗,多亏《玉台新咏》的收录,才得以传世,即此一例,已足不朽;也有如曹植《弃妇诗》、庾信《七夕诗》,本集均不载,今端赖《玉台新咏》的收录才得以保存,其功甚伟。此外,即使那些受到后人非议的宫体诗,作为一个时代文学风尚的产物,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和历史,都提供了真实的材料。更何况《玉台新咏》所保存的宫体诗,有许多还是具有很好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的,这一点也是研究者的共识。其次,《玉台新咏》关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著录,还历史之真相,即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苏伯玉妻《盘中诗》,冯惟讷《诗纪》录作汉人,今据《玉台》可知是晋人作品。当然,《玉台新咏》著录的作家作品并不都可靠,如将古诗作为枚乘作等例,但是它却为我们提供了这些诗歌在南朝时具有争议的历史史实,提供了可供后人进一步讨论的依据,其实这一点的意义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