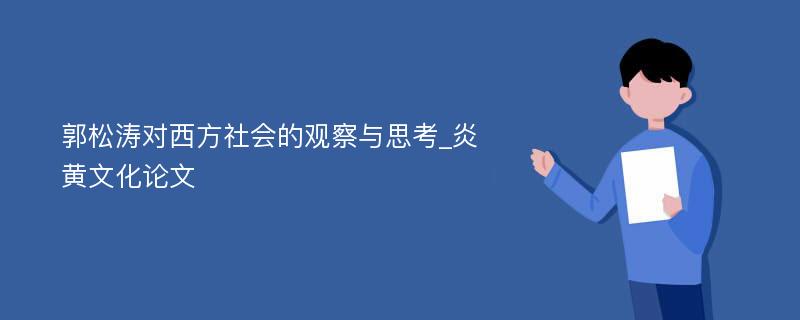
郭嵩焘对西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郭嵩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嵩焘在从事洋务期间,与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官员、军人等就有接触,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已形成一些感性认识。19世纪70年代中期,他在出使英法两国期间,又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历史各个方面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并把这些考察详细地记录在出国期间写的日记和信札中。学术界对郭嵩焘关于政治、经济、教育的观察和思考多有论述,但对他的文明观与中西社会风习方面的比较,探讨得不够,本文兹就这两方面的问题作些评述。
世界文明起源的多元观
在千百年来封建传统观念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士大夫阶级,一直把中国当成唯一的文明世界,而将境外的一切民族都称之为落后、野蛮的“夷狄”。鸦片战争以后,清末的一些士大夫把西方列强也附会于“夷狄”范畴之中,视西方政教为“夷俗”。到洋务运动时期,保守的士大夫把办洋务斥之为“沉迷夷俗”。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也难免受这种夷狄观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其礼教政俗,已不免于夷狄之陋。学术义理之微,则非彼所能梦见矣。”(注:张之洞:《劝学篇·序》。)随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刘锡鸿则自负以“攘斥夷狄”为己任。这种把近代西方诸国一概视为夷狄的看法,是从历史上的夷狄观中引伸出来的。
“洞察是改变观念唯一有效的方法”。(注:爱德华·波尔:《横向思维·序言》。)郭嵩焘根据自己在英法两国两年多的实地考察,他认为对近代西方各国决不能以夷狄视之。他说“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66页。),“西洋之局,非复金元之旧矣。”(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10页。 )他尖锐地指出把近代西洋各国视为夷狄,正如同“今人与奴隶、盗贼同席坐则惭与怒,审知其非奴隶、盗贼也,即惭与怒立释。 ”是一种认知上的错误。 (注:《郭嵩焘诗文集》第202页。)郭嵩焘毫不掩饰自己对西洋文明钦羡心情, 在致李鸿章的信中写道:“(伦敦)此间政教风俗,气象日新。……百余年来。其官民相与讲求国政,白其君行之,蒸蒸日臻于上理……计其富强之业,实始自乾隆以后。”(注:《郭嵩焘诗文集》第188页。)
郭嵩焘还对西方的历史文化做了考察,追本溯源地论证了西方文明源远流长。他指出自古以来世界上就存在有多元文化,他承认世界上有八大文明古国——犹太、巴比伦、亚述、埃及、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34页。 )而泰西学问皆根源于希腊(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47页。),西方言学问皆宗之希腊、 罗马(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384页。)。19世纪中后期, 中国知识界仍然普遍地认为:“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复然出于万国之上。”(注:邵作舟:《邵氏危言·译书》。)既然如此,西方的文学当然是不会被放在眼里了。郭嵩焘与这种态度不同,他多次称赞了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近代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275、374、869、946、873、220、452~453、873页。)
西洋有自己的文化。但这一文化的源头是否在中国呢?郭嵩焘的回答是否定的,即西方文化有自己独立起源的轨迹,它不是由中国文化派生的。郭嵩焘冲破了“文化—源论”,多方面论述在儒学文化圈以外,还有其他人类文明独立的存在,从而动摇了中国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念,树立了全球多元文化观念。郭嵩焘所以承认自古以来世界上就有多元文化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熟悉19世纪西方著名考古学家的成就有关,这些考古学家有爱琴文化的发现者谢里曼,埃及学家、埃及象形文字的释读者商博良,亚述学家、楔形文字的释读者格罗德芬。(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275、374、869、946、873、220、452~453、873页。)
由于树立了世界文化多元观,郭嵩焘摆脱了当时盛行的西学中源说。在洋务运动期间,西学中源说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西方物质文化源于中国和西方部分精神文化源于中国。郭嵩焘却承认中西文化各有源流,自成体系,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存在质的差异。在一定意义上,他所持的这些观点就是对西学中源说的批评与否定。有的论者,如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中即正确指出西学中源说是一种华夏中心观念,但却认为郭嵩焘也坚持西学中源说。张先生的后一看法值得商榷。
郭嵩焘没有鼓吹西学中源说。但他在考察西洋文化发展史时,却经常流露出泰西近古说(近代西方与古代中国的某些事物有相似之处)。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在英国牛津大学见到所学与仕进判分为二,仕进者各就其才质所长,积资任能,终其身以所学自效,认为此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379页。 )郭嵩焘在光绪四年十月致沈幼丹信中又谈到在教育模式上,泰西与中国古代有相似之处。(注:《郭嵩焘诗文集》第196页。 )光绪三年三月二十六日郭嵩焘在伦敦学者基金会上见到学者发言时,“以文辞周旋相尚”,他赞曰“颇有春秋列国之风。”(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190页。 )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郭嵩焘见到英国议院辩论是非则一付之公论时,写道:“《周礼》之讯群臣,讯万民,亦此意也。”(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02页。)光绪四年六月初九日由近代西方广修道路, 郭嵩焘联想到中国三代盛时,尤修此政(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 648页。), 等等,在郭嵩焘的日记中,像这一类的记载与议论很多。
在清末中国,宣扬泰西近古说,并非郭嵩焘的独唱,受欧风美雨影响较大的上海《申报》,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多有宣扬此说的文章。1881年9月27 日《申报》刊载的题为《泰西风俗近古说》一文对此说有专门阐述:“就富强与巧而观之,西人虽较胜于中国,而中国未尝不可武而及之,惟其风气之浑厚尚穆然有太古之风,此则尤可为羡者也。”“泰西自耶苏始开风气至今不及二千年,按之中国尚在中古以前,浑浑噩噩安安敦敦,皆为古时为近。虽制作日新,富强日盛,而古意古风究未甚远。将来日渐开辟,未知其变化若何,而就此时而论则其风俗犹近乎古。”刊载于1881年12月1 日《申报》上的题为《论泰西办案》一文,一开头就说:“泰西风俗近乎古,今泰西凡有词讼必有状师为之辩驳,此法最为古近。”刊载于1899年8月17 日《申报》上的题为《中西行乐不同说》一文,认为“泰西风俗每多近古,即如歌吹之声多重浊而少轻清,此即黄钟大吕之遗响也;舞时步武疾徐踊跃先后,各合节奏,此即缀兆进退之仪文也。”
泰西近古说是时代的产物。洋务运动时期在西学不断东渐的情况下,一些思想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将西方与中国上古盛时进行比较印证,但是“认识以认知为先决条件的,认识某物就是将其归入人们以前已知事物,并通过以前有的知识将其区别开来。”(注:欧文·拉兹洛:《系统·结构和经验》第171页。)这样, 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在进行比较时,把西学与中国之学相比较得出了西学中源说,把西方社会与中国古代社会相比较,得出了泰西近古说。”(注: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第252页。)但从它们的影响来说, 后者的消极影响要小于前者。因为它只是把西方社会某些事物与中国古代的某些事物做了比附,并不否认西方文化独立的起源,也无贬低西方社会之意。它把近代西方的一些言行嫁接到中国古圣人的言行中去,从而增加了令人尊敬的地位,用中国的古裙将西方少女打扮得富有东方式的美感。但从增加了接纳西学的保护色这一角度来看,泰西近古说与西学中源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难能可贵的是郭嵩焘在考察世界文化时,接受了近代意识的文明观。他将近代世界按其进化程度分为三个层次:文明、半开化、野蛮。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被称为“日本伏尔泰”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也持有这种观点,而这种观点又源自近代法国著名史学家基佐。由此可见郭嵩焘认识水平之高。这种文明观的先进性在于对世界上的多元文化,可以用进化程度进行横向比较和历史比较。它又能帮助处于半开化的民族,克服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尺度来评价先进的异域文化习惯性的心理屏障。
根据这种文明观,郭嵩焘敏锐地认识到了中国文化的严重落后。他指出:“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91页。)郭嵩焘这些话阐发了发展的、 进化的历史观,他告知人们:先进与落后可以转化,如按进化程度来区分文野,现在轮到西方人说中国为夷狄了。
社会风习方面的中西比较
基于近代意识的文明观,郭嵩焘确认当时中国处于半开化阶段。由此出发他从微观上展开了中西文化比较,并发现在社会风习上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西方重求实,中国务虚文。
郭嵩焘注意到了西方与中国在学风上的不同;他指出:“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857页。), “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04页。),西洋“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 (注:《郭嵩焘诗文集》第196页。 )郭嵩焘称赞西人“好推求人世事理而不惮烦劳”(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624页。), “治行学问必务求实,非可以虚名假借”(注:《郭嵩焘诗文集》第204页。), “遇事必一穷究其底蕴”(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623页。), “无奇不探,无微不显”。(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774页。 )郭嵩焘多次谈到西人“用心之锐,求学之精”。他对中国的恶劣学风多有批评,认为“中国章句之儒,相习为虚骄无实之言”。(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30页。 )郭嵩焘还屡屡将西方优良的学风与中国恶劣的学风加以对比,指出:“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中国收召虚浮不根之子弟,习为诗文无实之言。”(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 973页。 )“泰西遇事求进无已,中土人无从希其万一也” (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754页。) ;“凡西洋所极意考求者,皆中国所漠视者也。 ”(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313页。)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学风推而广之,又影响到社会风习。郭嵩焘指出西方“其民人周旋,一从其实,不为谦退谦让之虚文”(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34页。), 无无谓之周旋,而在中国却大搞无谓周旋,“以至疲精竭神, 以伪相饰”。(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84页。)
第二,西方倡开放交流,中国崇闭关自守。
郭嵩焘发现西方与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存在有显著的差别。他指出:“西洋以游历交接为义,已成风俗,各国互相款接,不为异也。中国关徼禁不许民人私行出入,无至国外游历者。”(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734页。)“西洋考求政务。辄通各国言之, 不分畛域”(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590页。),各国互相考察不遗余力。 “中国漠然处之”,“以评论西人长处为大戒”(注:《伦敦与巴黎日记 》第733页。),“以考求洋情为耻”。(注:《郭嵩焘诗文集》第216页。 )郭嵩焘严厉批评中国这种闭关自守的风气时写道:“中国人眼孔小,由未见西洋局面,闭门自尊大”,“一意反手关自己大门”,“此最害事”。(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737~738页。)
郭嵩焘认为近代西方与中国在对外关系上风气的不同,有其思维方式的根源。这就是西方“化异己而使之同”,中国“则拒求同于己者而激之使异”。(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30页。 )他这种关于西方文化异使同,中国文化同使异的说法,符合实际。一般来说,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封建顽固派在中西文化之间一直以“立异”为基本价值取向,视中学与西学之间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精神鸿沟,反对将西学引入中国,坚持“用夏变夷”,而坚持不可“用夷变夏”的顽固立场。显然这种把中学与西学完全对立起来,无视和否认中西学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极力排斥西学的企图,只能是“一意反手关自己的大门”。近代西方由于封建制度的解体,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闭关自守环境的消除,因此人们树立了求同的意识,希冀借“同”求“通”,建立世界性的文化。
在对外关系上,郭嵩焘力主开放交流,以学习西方为要务。在思想上他本人就具有“化异使同”的观点。他曾明确指出“夷狄之民,与吾民同也。趋利避害同,喜谀恶直同,舍逆取顺同,求达其志而不乐阻遏其气同。”(注:《郭嵩焘诗文集》第216页。 )他还强调指出“是故洋务者,治国平天下之一端也,其所以为用各异,而其用同。能教化整齐其民,以控御夷狄固沛然有余矣。”(注:《郭嵩焘诗文集》第 217页。)郭嵩焘已把“为用各异,而其用同”当做办洋务的重要方针。
第三,西方重商贾,中国重士而轻商。
郭嵩焘发现在反映社会关系的观念方面,中西方也有差别。他指出:“西洋以商贾为本计”,中国则“重士而轻视农工商三者”(注:《郭嵩焘日记》(四),第320页。),“西洋各国以通商为制国之本, 广开口岸,设立领事,保护商民,与国政相为经纬,官商之意常亲。”(注:《郭嵩焘奏稿》第384页。)“是以国家大政, 商贾无不与闻者”。(注:《郭嵩焘奏稿》第341页。)
郭嵩焘对中国重视士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很注意,为此他回顾了士在中国的演变过程。指出古代的士能耕田、能做工、能屠牲、能捕鱼、能经商,汉代的士有牧猪羊者,有负薪者,有为人帮佣者,有卖药者,他们都是依靠劳动以自食其力的人。然而自从宋儒讲明性理学以来,士的地位愈高,名气愈重,人们越把士看得不同寻常,距之商农三民越悬殊,反而使士成为《周官》里讲的那种闲民,因此,“士愈多,人才愈乏,风俗愈偷,故夫士者,国之蠹也。”(注:《郭嵩焘诗文集》第10~11页。)
郭嵩焘在论述西方重商贾的风气时,以鲜明的态度提出了重商立国的政策。他提出这一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这表明郭嵩焘抓住了学习西方文明成果的关键,“不管他本人的理性认识到了何种程度,这种新出现的建国方略和经济政策以及相应价值观念,它本质上是在中国试图推行资本主义制度,使前资本主义的中国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的先声。”(注: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第125页。)
第四,西方义利结合,中国义利对立,重义轻利。
郭嵩焘在分析涉及传统价值观重要内容的义与利时指出:“中国言义,虚文面已,其实朝野上下之心无不鹜于利,至于越礼反常不顾。西洋言利,却自有义在。《易》曰:‘利物足以和义’,凡非义之所在,固不足为利也。是以鹜其实则两全,鹜其名则徒以粉饰作伪,其终必两失之。”(注:《郭嵩焘日记》(四),第297~298页。)总之,郭嵩焘这是在倡义与利二者的不可分割,从而批判了儒家宣扬的义利对立、重义轻利的错误观点。
郭嵩焘认为西方是将义利结合起来的,他这种看法符合近代西方社会的实际。我们知道,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重利益讲实效的社会,在价值观念上形成了与中世纪神学相对立的思想。中世纪强调人应该追求“至善”,追求上帝,而回避尘世和欲望,达到与上帝同一的思想境界。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一个重视现世利益,重视实效的时代开始形成,宗教改革的结果,使过去人们鄙夷的世俗活动,甚至商业活动具有神圣感和价值感,同颂扬上帝、赞美上帝这个崇高的价值联系在一起了。新教把劳动、赚钱等活动看作是一种天职,马克斯·韦伯认为宗教改革导致了人们“把赚钱视为有义务实现的目的本身,视为神的召唤的思想”。(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46~4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种利用交换的机会取得预期利润的资本主义精神便构成了近代功利主义伦理的现实基础。据此人的一言一行追求自我利益,追求经济利润乃是合法的,也是最大的动机。这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上,而且在道德和评价上也认为是正当的,不可谴责的。
现代从事伦理学研究的学者在探讨经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时,也认为中西传统哲学认识论抱着完全相反的价值取向,即中国重义轻利,西方义利结合。(注:廖小平:《道德认识论引论》第267页。 )由此可见,郭嵩焘在19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相同的结论,实属可贵。
改造中国恶劣的风习
郭嵩焘关于中西方社会风习互有差别的论述,不是就事论事的一般记述,而是寓批判于比较之中,其目的是为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恶劣风习。郭嵩焘的这些论述很重要。我们知道,社会风习中的价值观念的变化非同小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价值观念往往汇成巨大的传统力量,当社会需要迈向新的阶段时,传统的价值观与新的价值观必然发生激烈的冲突,在冲突中传统的价值观就成为各种保守思想的庇护所。因此,价值观念的改造与更新便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决战。郭嵩焘走出国门,迈入西方世界之后,以西方社会为参照系,敏锐地发觉了价值观念改造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他多次说明改变人心风俗事关重大, 指出“风俗人心为立国根本”(注:《郭嵩焘日记》(三)第948页。),“强而无道德,富而无风俗,犹将不免于危乱。今吾民之弱极矣,而道德之消削亦愈甚,贫极矣,而风俗之偷薄亦愈深,此所以为可忧也。”(注:《郭嵩焘日记》(四),第88页。)因此,郭嵩焘认为只是从物质层面学习西方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制度层面、思想层面学习西方。
郭嵩焘关于改造中国恶劣风习的思考,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开了中国国民性讨论的先河。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从根本上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动摇了“中央大国”的自大心理,造成了中华民族的一次最严重的心理倾斜。为了重新寻找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总格局中的地位,郭嵩焘展开了对本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重新认识,走出国门之后,他以西方社会的文化为参照系统,开始在新的层面上认识中国的文化。不仅了解到技术和制度方面不如西方,而且察觉到国民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落后,因此,民族的兴盛和国家的富强要靠国民的觉悟和奋起。这样,郭嵩焘便把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这对向以道德文明自尊的中国来说,确是石破天惊,前无古人之举。尽管在这方面他的探索还不成熟,还不系统。但毕竟开始了国人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素质以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是人的解放在中国的始端。从此以后,中国对传统国民性的反思成了一个常新的课题,它一再拨动着爱国者的心弦。可以说,郭嵩焘是探索中国国民性改造问题的先驱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