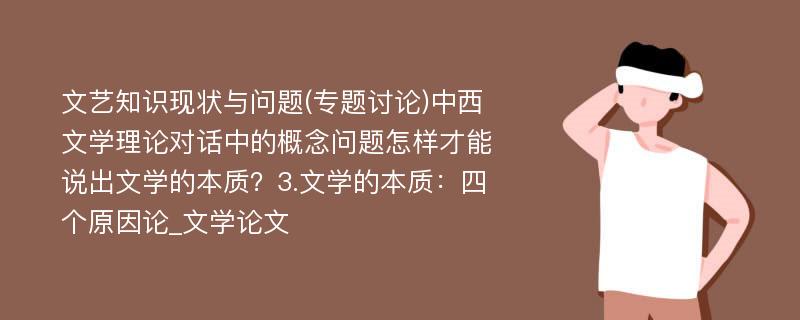
文艺学的知识状况与问题(专题讨论)——1.中西文学理论对话中的概念可对应性问题——2.文学本质的言说如何可能——3.文学本质“四因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质论文,文艺学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专题讨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2—0098—10
中西文学理论对话中的概念可对应性问题
王先霈
王先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一
中国现在文艺学研究中的学术通则、惯例或者叫做“语法”,是近一百年来逐步形成的,并且主要是在欧洲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科思维习性和学术规范的影响下形成的。冯友兰在其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讲到,“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金岳霖当时在《审查报告》里评论说,冯友兰是“把中国的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① 同样的,文艺学或美学、诗学,也是从外国输入的名词。在冯友兰所说的那个意义上,所谓中国文艺学、中国美学、中国诗学,也可以说即是中国的某种学问,可以用西方所谓文艺学、美学、诗学名之者,是“在中国”的文艺学。文艺学不能只是在中国的,而应该是中国的。如何把在中国的文艺学,建设成为真正是中国的文艺学,这是今天讨论的重要课题。
不过,一般所说西方的这些学科,包括西方的哲学,也包括西方的文艺学,并非是单纯的、单一的自足完备体系,无论从历时的演变还是从共时的丛生看,它们都包罗了多种多样彼此不同甚至彼此对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是在欧洲诞生而后传播到全世界的。这些多种多样的文艺学,彼此的观念、方法可能迥然有别,但从思维形式来看,它们是在一个大的学术传统中产生的,有一套公用的话语系统,彼此具有很强的可对话性。其中某些文艺学理论就是在对别的文艺学理论的批判中建立,而批判乃是一种特殊的对话。中国古代的可以用西方所谓文艺学名之的文论,原是在与欧洲理论基本隔绝的文化环境中产生,具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观念体系和术语群,属于与西方不同的另一套话语系统。中国古代文论用于观察、衡估、评述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是有效的、合适的。一千五百多年前钟嵘的《诗品》,评论一百二十多位诗人,写得多么好呀!三百多年前金圣叹评点《水浒》和《西厢》,也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快感,启迪了对作品新的领悟。“五四”新文学兴起,小说、新诗、随笔、话剧、报告文学创作,它们的文体形式和艺术理念,在救亡图存、革故鼎新的背景下,主要是求新声于异邦。因此,用中国古代文论的观念、术语和文学批评文体,用古代那一套话语系统,来评论鲁迅、巴金、郭沫若、徐志摩、冰心、洪深、曹禺、夏衍的作品,就很不适用了。以中国古代的文论语言与西方文艺学、美学、诗学进行理论对话,遭遇着两套话语系统的隔膜,必定甚为困难。于是,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在古代经典与现代实践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断裂。先行者们,几代学人,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断裂。鲁迅早在《文化偏至论》中就提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余英时介绍他的老师钱穆的治学,“分析到最后,是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个大问题,即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②。我们知道,钱穆提出了“民族文化本位”的思想。作为引进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代表,周扬在1958年提出过建立中国自己的、与本国文艺传统和创作实践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口号③。但是,新历史主义有一个说法,叫做社会能量在文学艺术中流通、循环并且增值;反过来说,文化的、学术的民族性成分的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也必须在社会的全面的建设发展中实现。有海外的汉学家认为,近代以来,是“先进的、有活力的”西方,刺激了、带动了“落后的、停滞的”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他们企图用“刺激→反应”的图式来描述这个过程。这里流露了盲目的种族优越感。事实上,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的动力在中国内部,当然也受到外力的强大冲击。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虽然外力的作用非常之大,根本的动力同样是在中国内部。中国现代文明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学术的现代化不能脱离社会全面现代化的进程,而只能在这一进程中间逐步实现。所以,不奇怪,中国的现代文艺学,如何处理外来的、西方的学科惯例和本土的资源的关系,如何处理外来的、西方的惯例与本土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接受实践的关系,依然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在20世纪前期和其后的某些阶段,搬用和套用西方文艺学,曾经造成过不少困难和尴尬。由此产生的困难,既有思维方式上的困难,又有表述方式上的困难。我们的文艺理论批评,站在什么样的体系基础上思考,用什么样的学术语言表达?在文艺学的若干分支,这种困难和尴尬还是双重的、多重的。例如,我们看到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套用西方文艺学框架,还要套用西方女性主义的框架;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无论是白人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还是其他,都没有考虑中国几亿女性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特征,搬用这种理论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女性问题,怎么能得出真知、新知?再以文艺心理学研究为例,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特别是有关文学艺术心理的思想,与西方的现代心理学理论以及西方文艺心理学理论,其理路相距颇远。前者是实证的,依靠实验室里严密的操作;后者是玄思的,依靠理论家的体验和推想。而我们几十年来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却是以1879年在德国建立,之后在美国、法国、俄罗斯等若干国度得到发展的现代心理学的基础理论为参照和指引。台湾学者杨国枢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反省:我们所探讨的对象是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中的中国人,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西方式的,这是一条正确有效的研究道路吗?他联合一批学者,探讨心理学研究之中国化的可能性,以“建立中国人之本土心理学”为研究的主旨。④ 不少的文艺学家,若干年来实际上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建立既是现代的、科学的,又是民族的、本土的文艺学,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我们不可能完全抛开“五四”以来形成的文学理论的框架、术语、体系,而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人日益觉醒的文化自觉,中国的文学艺术家们努力追求的本民族的诗性,都日益紧迫地要求我们处理好文艺学的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今天也有了以前所没有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客观条件。我们不再像前辈那样,因国势颓危,心怀焦虑,而故持偏至之论;也不会再因外敌欺凌而灰心自卑。我们可以把开放的心态和民族的自尊自然结合,探讨理论创新的切实途径和方式。
二
理论创新的关键之一,是正确认识和恰当对待外来的、西方的概念在中国话语中的可对应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起,我们经历过从西方输入的新名词的轰炸,我们经受过术语的滥译滥用,我们感受了正当的学术论争因对基本术语的不同命意而成为聋子的交谈。学者们共同的心声是:必也正名乎!我们迫切需要对术语、范畴的概念内涵取得共识,迫切需要一种使正常的学术交往得以进行的公用的术语词典。
自从有了不同文化体之间的交往,凡引进外来学说,不同的话语系统要进行对话,就会遇到术语转换的困难。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形成的术语向另外的民族、另外的文化圈传输,一大障碍是许多概念不对等,概念不对等导致误读、误解。找到概念、范畴的对应性,是对话得以进行的关键。佛学进入中国过程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有若干经验值得从学科建设方法论角度重新总结。佛学传到中国,是一种外来的学说,历经几百年的艰难磨合,从东汉、魏晋到唐宋,才渐渐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使中国佛学在世界佛学中居于领先的位置。佛学家们用很大的精力从事术语的译解。术语译解的核心是概念的传达,东晋的竺法雅把佛经当中的用语和中国道家典籍用语比拟配合,作为讲说的准则,使中国文人产生亲近感。然而,中国的经典和佛典各自术语的概念内涵相差极大,比拟的办法大失原意。于是,唐玄奘提出了“五种不翻”。现代学术交流中,对含意特殊、微妙的新颖概念,有时也采用“不翻”的办法。例如,德国心理学家提出的“格式塔”,各国大多采用音译,中国虽曾译为“完形”,流行的却是“格式塔”。然而,不翻,采用音译,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南宋僧人法云有《翻译名义集》,把佛教术语逐一举出异译、出处、释义,并作出解释。他认为,“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其所无”。学术翻译要输入此间本来没有的外民族的新颖的概念,这些新颖的概念本是在放送方的话语系统中存在,却必须在接受方固有的话语系统中寻求对全新概念的表达。最早来到中国的天竺僧人摄摩腾,《高僧传》说他“蕴其深解,无所宣述”,他不具备突破两种话语系统间屏障的能力。鸠摩罗什入长安,见“先译失旨,不与梵本相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概念的不对应的弊病。他并且自谦“虽诵其文,未善其理”,推荐佛陀耶舍“深达幽致”,也就是深刻理解概念的深层含义。他们两人合作,“共相征决,辞理方定”,成为佛典翻译大师。译经高僧们翻译术语的重要方法,是把接受方原有的词语改造,注入理论内容。例如,梵语佛经中的“若那”;汉译为“智”;“般若”,汉译为“慧”。汉语中本有“智慧一词,《孟子·公孙丑》:“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秉势。”嵇康《大师箴》:“下逮德衰,大道沉沦,智惠日用,渐私其亲。”智慧本是指聪明或者巧智,而佛经中的智慧,指超越世俗迷幻、物欲蒙蔽,烦恼障断,所知障消,而直接获得的对最高本体的悟解。这样,就把一个普通的词语,转化为表达重要哲学概念的术语。周武帝时道安《二教论》说,“曲士不可以辨宗极者,拘于名也”,批评当时的文人以儒家用语去解释佛经,混淆了不同的概念。如“大智度”,有人译为道。但这和道家的道,“道名虽同,道义尤异”。“菩提大道以智度为体,老氏之道以虚空为状,体用既悬,固难影响。外典无为,以息事为义;内经无为,无三相之为。名同实异,本不相似。故知借此方之称,翻彼域之宗,寄名谈实,何疑之有。”提醒人们,从词语之同,辨析概念之异。近人熊十力著《佛家名相通释》,在“撰述大意”中说,“于繁琐名相,欲——而穷其差别意义,则必将论主之经验与思路,在自家脑盖演过一番,始能——得其实解”。我们现在很需要对文艺学的基本概念术语,作成新的有权威性的新的“翻译名义集”,新的“名相通释”,弄清术语的提出者赋予的本来意义及其后来的演变,以及不同学派对它的修正,纠正术语使用的混乱和任意性。这样,大家对话会顺畅一些,彼此误解会少一些。
不同的术语概念背后是各自独特的理念。以“移情”(Empathy)为例, 这是20世纪引进的西方的心理学和美学概念。“移情”作为一个词,中国古代较少有人使用,更没有形成为术语,但中国人有自己的移情理论。西方心理学中的移情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互通,西方美学中的移情,主要是指艺术家注情于物。中国古代讲移情,首先是从教化观出发,讲移易心志,就是用文学艺术的手段,来潜移默化,转变人的情志,使之合于儒家的人格理想。中国古代特别强调了大自然对人的性情的陶冶作用,其哲学思想基础是天人相感的理论,认为: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九州之地,人的九窍、五脏、十二关节,“皆通乎天气”。这种倾向与道家思想配合,形成中国古代移情理论的最显著特色。同时,它还十分重视人从自然得到形式美的触发、启悟。在中国的传统中,注重心与物的双向互动,所谓“情以物兴”、“物以情观”,“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就是很精炼的概括。画家、诗人的创作意兴,是在物与心相互激发中迸出火花,这样的观念比之于单独强调我情注物,更符合文学艺术思维的特性。宗白华指出,中国古代的移情说,比起德国美学家李普斯的情感移入论,“似乎还要深刻些,因为它说出现实生活中的体验和改造是‘移情’的基础”。他还说,考察对象的构成,改造主体的感情使之能够发现美,中国古人叫做“移我情”;改变客观现象使之成为审美对象,中国古人叫做“移世界”。他提到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表示赞赏的培根的话:物质以其感觉的诗意的光辉向着整个的人微笑;和表示不满的霍布斯的机械论:感觉失去了光辉变为几何学的抽象,唯物论变为厌世论。⑤ 这是在透彻了解中西两种术语背后的思想体系,看准其交切点和歧异处,而后作出的创新的诠释,也是中西文学理论对话的一个很好的范例。
我们还应该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术语作类似的清理,拟出多数人接受的译名,向外国人介绍。例如,气,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孟子的“知言养气”说,王充和刘勰的“养气”说,曹丕的“文以气为主”,韩愈的“气盛言宜”,等等,贯穿在两千年的文学批评史中。这是中国人独创的一个概念。英国艺术教育家米歇尔·康佩·奥利雷在《非西方艺术》一书中说,对于某些专用词语,在别一种文化中、在别一种语言中,“是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完全对等的翻译的,来自某种文化的人也是难以理解另一种文化的艺术之全部含义的。中文里有一个字‘气’,在这里可以译作character或disposition,但在不同的上下文环境中,不同的历史时代还会有不同的意思”⑥。“气”字早已进入日本文字,已故日本汉学家小野泽精一说,日文“气”的概念虽然与中国很多类似,但最基本的,确实“以在日本产生成长起来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对于自然、社会的对应方法为核心”。到了欧美,“气”得到各自的阐释:在德国,重点是生命力;在法国,重点是能量;在英、美,重点是内在力。⑦ 虽然其他国家不存在与“气”完全对等的概念, 虽然中国古代“气”的概念不断演化,内涵极为复杂,研究者们总是从各个角度力求找到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与之对应的本国的术语,促成了中国人这一思维成果为各国学者共同享用。
文艺学研究必须充分重视本土资源,但不应也不可能无视西方文艺学相对严密的体系和相对精确的研究方式。我们可以做的是,力求两者的合理的自然的结合。让我们先在基本术语的诠释上,作一番最基础的工作。有了可靠的基石,才能构筑楼舍、大厦。
注释: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1页,以及下册“审查报告”二,第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② 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见《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③ 周扬:《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载《文艺报》,1958(17)。
④ 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⑤ 宗白华:《美从何处寻》,见《美学散步》,第14、16、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⑥ 米歇尔·康佩·奥利雷:《非西方艺术》,第1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⑦ 小野泽精一等:《气的思想》,第5—7、321、528—53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文学本质的言说如何可能
杨春时
杨春时,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当代文学理论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动向,就是反本质主义:依据解构主义,取消关于文学本质的论说,代之以文学观念的历史描述;同时,运用新历史主义理论,把文学本质还原为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的建构。笔者认为,文学本质问题的言说是可能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正本清源,考察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的解构,然后再考察文学理论(包括文学本质问题)建构的问题。
一
本质主义实际上是实体主义。古代哲学探求与主体分离的对象世界的本质,它相信在现象后面存在着实体,实体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决定着现象世界。因此,古代哲学就把确认实体作为“第一哲学”,把实体当作自明公理,进行逻辑的推演,以揭示具体事物的性质。这就是“一决定一切”的形而上学及其思想方法,从而形成了所谓“本质主义”。本质主义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寻求事物的绝对本质。在实体观念的基础上,产生了形而上学的古典哲学体系。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也体现在文学研究上面。传统的文学研究也是从所谓“世界的本质”出发,来推演文学的本质。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体,因此提出了艺术是理念的再模仿的理论。亚里士多德认为实体是实在的物体和形式,因此提出艺术模仿现实的理论。黑格尔认为理念是实体,因此艺术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切都植根于形而上学的实体论的本质主义。苏联文学理论提出了“文学是现实的反映”说,也是源于物质本体论,认为存在着物质实体,文学反映物质世界,从而是一种变相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
现代哲学抛弃了实体观念,进而摧毁了形而上学。洛克和休谟在经验主义的立场上否定了实体的存在。洛克认为一切知识都导源于直接经验,因此所谓实体是不可知的。休谟认为实体不过是思维产生的错觉,不存在超经验的实体。康德综合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认为认识只能把握现象世界,不能把握实体,把实体列为信仰的对象,从而抽走了实体存在的根据。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范畴“存在”被错误地当作“存在者”即一种实体,而实体不过是一种虚构。分析哲学认为只有可以实证的非分析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而关于实体、存在的论说都只是语言的误用,形而上学的问题只是无意义的假问题。后现代主义哲学更彻底地摧毁了实体观念。解构主义认为语言并没有确定的所指,而只是不断推延的“能指的游戏”,因此也没有终极的意义。新历史主义认为一切都是历史中的存在,是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的产物,不存在超历史的本质。总之,现代哲学认为,不是实体是否存在的问题,也不是实体能否认识的问题,而是谈论实体没有意义。这样,形而上学中所谓的实体、本质、绝对真理等也就被解构了。
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打破了形而上学的实体论本质主义,注重文学观念的历史性,揭示了文学理论后面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有其合理性。中国文学理论受到形而上学本质主义影响巨大,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冲击更为必要。如反映论的文学观,把现实规律当作文学的本质;主体论的文学观,把人性当作文学的本质,都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倾向,因此也不可避免地被解构、被否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的本质不存在,不可言说。这是因为,伴随着形而上学被否定的只是实体论的本质主义,而不是存在论的本质主义;不能言说的只是实体性本质,而不是超越性本质。
后现代主义否定了形而上学,但不意味着取消了形而上学提出的问题。形而上学的存在,根源于人类对终极意义的追求。在现代视野之下,形而上学的终极的存在物——实体被否定了,实体论的本质主义被推翻了,但人类对存在意义和终极价值的追求、追问并不随之消失,相反,它将永远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因此,也将永远存在着一个超越性的领域,如此才有哲学、美学以及宗教的存在。存在主义哲学代表了一种新的本质言说的方式,即存在代替存在者(实体),寻找存在的本质(本真的存在),而本真的存在是超越性的存在。海德格尔批判了把存在等同于存在者的实体论形而上学,但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超越论形而上学,以回答“‘存在为什么在’的在的意义问题”。在传统的形而上学体系中,本体界统领现象界,此岸服从彼岸,这是西方式的天人合一。现代性发生后,天人分离,此岸与彼岸、现象界与本体界分家,本体界只是超越的领域,不再支配现象界,现象界后面也不再具有实体,世界的实体性的本质被消解了。但是,由于超越性的领域仍然存在,因此,超越性的本质仍然存在,只不过它不再是现实世界的根据,而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所谓超越性的本质,是指存在的终极意义,它超越现实存在,是对现实存在的反思、批判的产物。因此,反对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并不是说世界没有本质,也不是说不能谈论文学的本质,而是说没有了实体性的本质,但仍然存在着超越性的本质,这个本质不再与现实世界具有同一性,不再决定现实事物的性质,而是对现实存在的超越,是对现实存在的反思、批判的产物。这就是说,反对实体论的本质主义,主张存在论的本质主义,这才是对反本质主义的正确理解。后现代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消解形而上学的问题和超越的领域,没有也不可能消解超越性的本质问题。超越的领域包括审美、宗教、哲学(这正是黑格尔确定的绝对精神的三种形态)等,它们是对现实存在的超越,是自由的领域。这样,文学的本质问题,也就是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意义问题。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文学没有确定的意义,因此是不能言说的。而我却认为,文学本质在两个层面上是可以言说的:一个是在现实意义上,文学的本质具有历史性,可以作出历史性的言说。一个是在审美意义上,文学具有超越的本质,具有确定性,可以作出超历史性的言说。
文学有两个层次,因此也有两种意义。一是作为基础的现实层面,它具有现实意义,主要是意识形态。一是审美层面,它超越现实意义,具有超越性的审美意义,也就是对生存意义的领悟。文学的现实层面是历史地变化着的,因此现实意义是具有历史性的意识形态。在这个角度上,也可以说文学没有超历史的确定的本质,仅仅具有历史性的相对的本质。文学的审美层面具有超越性,是对意识形态的否定性超越,也是对历史性的超越。在这个角度上看,文学有超历史的确定的本质,这就是审美本质。所谓超越,是生存的一种根本规定,生存不是异化的现实的存在,而是指向自由的超越性存在。因此,现实可以解构,但超越的领域不能解构,审美不能解构,因为对自由的追求不能泯灭。意识形态是社会价值体系,是特定阶级(主要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它具有现实性、历史性。道德、政治、法律等都是意识形态的形式。文学也带有意识形态的属性,这主要体现在文学的现实层面。同时文学也有超越意识形态的审美层面。审美作为自由的生存方式和体验方式,是对意识形态的超越。人类由于有了审美意识(以及其反思形式哲学),才能够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获得精神的解放。文学的自律性源于审美超越性,审美虽然有现实的基础,但又超越现实,在历史的变化中保持着自己的恒定品格,从而使文学具有了独特的本质。
后现代主义消解了现实的实体性,但不可能消解审美的超越性。西方现代哲学的审美主义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审美主义是在现代性发生以后的一种批判性哲学思潮,它不再把理性当作终极真理,不再认为现实中可以实现自由,转而认为审美是最高的境界,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审美主义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形式,是在此岸与彼岸分离后的一种超越途径。传统哲学不认为审美是存在的最高境界,只有神性(中世纪哲学)或理性(近代哲学)才是最高的存在形式。从席勒、叔本华以及尼采开始,理性的权威衰落了,审美成为最本真的存在方式,审美主义发生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萨特、梅洛—庞蒂乃至福柯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走向了审美主义。审美主义的兴起,证明形而上学的问题并没有被取消,仍然存在超越的领域,也仍然需要美学的思考。因此,文学理论就超越了一般知识、意识形态,而具有了哲学—美学的高度;在一定历史水平上克服了话语权力的制约,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言说也就具有了形上的意味。
当我们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局限的时候,必须注意到,现代主义不仅仅是解构主义的一种走向,还有一种建构主义的走向——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在批判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更注重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它批判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和主客对立,而主张主体间性以及人与世界的和谐共处;变启蒙理性的“祛魅”为“自然的复魅”。总之,“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在批判了形而上学的实体论之后,并没有取消形而上学提出的问题,而是试图在现代的基础上重新解答这些问题。这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
时下一些论者,放弃对文学本质的回答,代之以对关于文学本质问题论述的历史描述,以实践后现代主义关于文学本质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和话语权力的建构的思想。问题在于,以史代论并不能解决人们对文学意义的追问,它只能说明历史上的文学理论以及它们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而不能告诉人们现在如何看待文学。我们不能只是告诉人们:以往的文学理论是这样谈论文学的本质,但是我不能接着说下去了,我不能告诉你文学是什么,因为文学没有本质。而且,从外部解说文学的本质,回避了文学理论自身演变的根据,这种解说就是不全面的。文学理论并不是由历史任意捏弄的泥团,而具有自身的规律,它除了适应外部社会文化因素外,还要发展理论自身,修正以往理论的缺陷,以更确切地解释文学现象,这是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不能以文学外部影响取代文学自身的规律,相反,文学外部的影响要通过文学的内部规律起作用。因此,必须在历史上形成的文学理论基础上,接着说下去。解构的前提是有前此的关于文学本质的言说,如果完全回避本质的界定,解构和历史考察也就失去了对象。仅仅解构而不建构,那么从今以后就不仅没有新的文学理论体系,而且也将没有关于文学理论的解构对象和历史考察,这意味着文学理论的消亡。
传统的文学理论都是首先研究“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而这种提问方式,预设了文学是一种客观的与主体无关的文本,而且它具有实体性的本质。历史上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或者从形而上学出发,寻找文学现象后面的实体性本质(理性主义);或者从经验出发,寻找文学文本的共同特性(经验主义)。第一种方式已经被解构主义所否定,第二种方式也走到了绝境。由于文学本身形态多样,特别是现代文学的反传统性,这种共同本质的寻求遇到了愈来愈大的困难。乔纳森·卡勒说:“文学作品的形式和篇幅各有不同,而且大多数作品似乎与通常被认为不属于文学作品的东西有更多的相同之处,而与那些被公认是文学作品的相同之点反倒不多。”① 这就为反本质主义提供了口实,包括所谓家族相似说、 所谓惯例说乃至于取消文学本质的问题等等都发生了。必须首先解决文学理论提问的方式问题。在现代哲学看来,文学不是实体性的存在物,而是作为存在方式的文学活动,因此不是提出“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提出文学是何种存在方式或者文学的意义何在的问题。这种提问方式的改变,实际上是哲学基础的改变,从实体论改变为存在论。这样,文学文本在历史上千变万化,但文学活动、文学的意义却有其恒定性,可以进行定性的研究。
后现代主义认为文学的本质只能是一种没有确定内涵的历史性的观念,只是解构的对象。我认为,任何文学活动都既在历史之中,又超越历史,因为文学既有现实层面,又有审美层面。文学在历史中变化,其现实意义是流动的,没有固定的本质;同时,文学又在历史的流变中保持其超越性和审美意义,这种超历史性就是对生存意义的领悟。因此,文学的本质是可以言说的,它既是历史性的,又是超历史性的。因为文学活动就是从现实存在到超越性存在的过程,就是从现实体验到审美体验的过程。如前所述,文学有现实层面和审美层面(此外还有原型层面,此暂不论),它们各自的意义不同。现实层面与现实存在相联系,具有现实意义,核心是意识形态。审美层面与超越性存在相联系,具有审美意义,而审美意义是对生存意义的领悟。现实意义具有历史性,而审美意义具有超历史性。文学的意义是现实意义向审美意义的转化、升华,审美意义对现实意义的批判、超越,形成一种动态系统。文学的本质不是形而上学的实体性本质,而是历史性本质与超越性本质的统一;文学的意义是现实意义与审美意义的统一。
接下来的问题是,文学有各种不同的形态,它们的意义也有所区别,不能一律视之。这就要求我们具体地分析各种文学形态以及它们各自的意义,从而对不同文学的性质有不同的言说。大体上说,文学有三种基本的形态:纯文学,严肃文学,通俗文学。所谓通俗文学,是指那些与原型层面相通、突出消遣娱乐功能的文学,它主要具有感性意义,而意识形态意义以及审美意义不突出。所谓严肃文学,是指那些与现实层面相通、突出教化功能的文学,它主要具有意识形态意义,而感性意义、审美意义不突出。所谓纯文学,是指那些与审美层面相通、突出超越功能的文学,它主要具有审美意义,而感性意义、意识形态意义不突出。
最后,还应该指出,解构主义是一种哲学,属于元理论,而文学理论虽然有哲学的层面,但不是元理论,而是次级理论。在哲学、元理论领域,可以否定实体论,解构一切现实事物包括文学的本质。但作为次级理论,必须认定研究对象的客观性,文学理论必须研究和回答文学的本质问题,就像伦理学要回答道德的本质、政治学要回答政治的本质一样。我们不能依据哲学解构主义,拒绝回答文学的本质问题,就像一切次级学科不能拒绝回答研究对象的本质一样。尽管对文学本质的回答具有历史的规定性,但也一定保存着超越历史的意义。这也就是文学理论将继续存在的根据。
注释:
①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第2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文学本质“四因说”
肖鹰
肖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4)
在国内近来关于“文学是什么”(文学的本质)的争议中,存在着“本质主义”观点和“反本质主义”观点的对立。但是,如果进一步考察这两种对立观点的具体阐述,我们又会发现对立的双方又都是用了一种“先验的本质”眼光去打量文学。无疑,在这种“先验的本质”眼光下,人们是不可能真正认清文学是什么的,争论也只能被置于僵局中。文学是人类进行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多面体。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认为,万物的存在都是以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为原因的。① 运用“四因说”的方法来考察和解析文学,正可以动态立体地揭示文学的本质。
一、质料因: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作品,即语言是文学的质料(媒介)。这是凡承认有“文学”的人都必然要承认的公理。但是,正是从这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开始,关于“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就开始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作品,但语言的作品并不都是文学。那么,构成文学的语言,是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文学语言呢?
从历史来看,文学语言的确是一种特殊的语言。韦勒克和沃伦曾在其《文学理论》中对文学语言和科学语言、日常语言作区别,认为文学语言有三个最重要的特征:第一,文学语言有多种歧义;第二,文学语言本身是感性的;第三,文学语言是高度提炼和严密组织的。② 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使它具有普通语言不具有的丰富表现力、象征意味和感染力。在各种文学体裁中,诗歌最典型地表现了文学语言的特性,因此,诗歌的语言是意味最丰富、最不容阐释和改写的,即中国古代诗论所谓的“诗无达诂”。
承认文学作品是由具有特殊材质的语言构成的,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基点。但是,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界限。文学语言是包涵在普通语言之中的,它不过是后者的提炼、转化和再生。从发生学的角度讲,语言本身就是文学性的,因为语言原本是感性的、象征性的,并且富有表现性的。只是在文明进化过程中,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日益朝符号化的指意功能和交流功能发展,而丧失了它的文学性——诗意。所以,海德格尔说:“语言不是诗歌,因为它是原始的诗;反之,诗歌产生在语言中,因为语言储藏着诗的原始根源。”③
目前,有一种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主张“文学终结,文学性扩张”。这种文学观念是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究其实质,是将对文学的整体性关注下降到对作品语言的文学性关注。保罗·德·曼(Paul de Man)在他的《抗拒理论》一文中指出,文学性是通过在使用语言中将修辞功能压倒语法功能和逻辑功能来实现的,它作为一个要害性的而又不安定的因素介入模式,以各种方式和面貌扰乱其内在平衡,从而也扰乱它的外在世界。④ 德里达对德·曼这个文学性的主张表示认同,他说:“德·曼没有说错,归根到底,一切文学修辞就是自我解构的。”⑤ 因此,解构主义的文学性,是关于语言修辞的非指意性、多义性和差异性的突出和强化,它拒绝文学整体性,只关注语言差异性。
二、形式因:意象
文学的形式,首先表现在文学类型(体裁)上。按传统划分,文学分为诗歌、戏剧、散文、小说四大类型。文学是什么,以及文学是否存在,都要依靠是否存在这些特定的类型来判断。不同的文学类型,有不同的结构形式,这些结构形式既保证了文学类型之间的相互差异,又保证了各种类型共同的文学属性——虚构的、非现实的、非逻辑性的世界。
文学风格是文学形式的第二层次,它是文学的文化、时代和个性差异的表现。风格并不是文学可有可无的存在,不是它的外在装饰。风格在表现文学形态的特殊性的时候,就是在展现文学的具体历史的存在,展现它的生命的真实性和个体性。因此,正如不存在抽象的文学一样,也不存在没有风格的文学。风格的形成类似于自然生命的形成和发展,虽然我们会看到文学实践中对风格的模仿和借鉴,但在精确的意义上,风格是不可学习的。在作者之间,不同风格的相互影响是存在的,但归根到底,是不会存在雷同的。
文学形式的第三个层次是作品的意象。意象是文学作品呈现出的整体的情景。文学作品并不一定要塑造具体的形象,但是必须创建一个生动可感的情景。文学意象是语言的物态化作品向非语言的想象情景转换的结果。因此,作品的意象是作品的最终形式。文学意象概念揭示文学的本质特性在于,文学不仅是想象的作品,而且最终是以想象的形式存在的。就此而言,文学意象将文学展现为一个现象学事实,即文学作品不是一个独立的自在实体,而是必须通过读者的感受和想象进行再创性来呈现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形式在其三个层次上都发生着变化。但是,相对而言,文学类型的变化更为缓慢,因为文学类型的稳定性保证着文学体制的稳定性,为文学创作和评价提供准则。文学准则的作用不同于其他体制的准则,它不是一种强制的、固定的规则,而是基于创作的自由原则具有宽泛性和灵活性。德里达认为,“文学是一个矛盾的体制”、“原则上,文学的法则趋向于拒绝或撤销法则。它因而允许人在这个‘言说一切’的经验中思考这个法则的本质。它(文学)是一个趋向于逾越这个体制的体制”⑥。看到文学体制的矛盾性和运动性,是对文学的历史性的正确揭示。然而,如果因此根本否定文学体制的相对稳定性,否定文学类型划分的相对确定性,则会走向历史性的反面——在本质主义的立场上否定文学形式,并且否定文学本身。
三、动力因:作者
作者是文学的创作者。在古代社会,文学作者一般被认为是具有神奇的创作能力的人,用柏拉图的话说,“诗人是神灵附体的人”。在近代以经典为核心的体制中,文学的作者被认为是具有特殊禀赋的人,即具有“天才”的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康德说:“天才是一个主体自然禀赋的一种典范性的原创力,它使他能够自然运用自己的知识性技能。”⑦ 这里的关键是怎样理解“自然禀赋”。黑格尔认为,天才有三个自然资源:第一,艺术创作是一种感性活动,“要用感性的材料去表现心灵性的东西”,因此,艺术家自身天生的感性素质是其创造力(天才)的重要部分;第二,民族性的特殊艺术才能,比如希腊民族擅长史诗和雕塑,意大利民族擅长歌唱,也是艺术家天生的资源;第三,艺术家对某种艺术形式的敏感和专长,也属于其天生自然的资源。黑格尔强调,天才是艺术创作的特殊资质,艺术家对于他的天生的自然因素,必须经过后天培养、训练才能达到高度的熟练,成为真正有效的“天才”。⑧
但是,作者之所以成为作者,不是因为他具有创作的“天才”,而是因为他创作了“天才的作品”。20世纪文学的作者理论就是转向通过对创作的考察来界定作者的。克罗齐是这一新作者理论的开创者。他说,“与其说诗人是天生的,不如说人天生的是诗人”。他认为,一个人是否是诗人,关键在于他是否在心中直觉到了情感表现的形式,并且因此将情感表现出来了。“诗歌的材料活动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只有表现,即形式,使诗人产生。”⑨ 因此,对于克罗齐来说,诗人不是一个完成了的自在的实体,而是一个以人为载体的进行着的活动——艺术直觉。这种非实体化的,即存在化的诗人观,对传统作者理论是一个严重的冲击,它既否定了经典理论的天才观念,又拒绝了对作者(诗人)的本质主义界定。因此,20世纪新的作者理论的趋向一方面是深入到创作心理的研究,另一方面则发展了民主的(平民的)作者观念——没有人不是诗人,反之,没有人是诗人。
在20世纪文论中,最激进的作者理论是罗兰·巴特的“作者死亡”说。他认为,经典文论一直主张作者对作品的独立创作权,这是一个关于作者的神话;相反,他主张作者并不是作品的完成者,作品的完成者是读者,读者才是作品存在的真正地方。“经典批评从来没有注意到读者;对于它,作者是文学中唯一存在的人。我们现在不再让自己受道德社会的傲慢的反诘的愚弄,而是自由地偏爱它所排斥、忽视、窒息和毁弃的一切;我们知道,要给予写作未来,就必须颠覆它的神话: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⑩ 巴特肯定读者在文学(作品)中的必然存在,是一个正确的主张,因为文学最终的存在并不是物态化的文本,而是在文本基础上建立的想象性的意象。但是,要以“作者死亡”为“读者诞生”的代价,却是矫枉过正的主张,因为一个没有作者(作者死亡)的作品,只能是一个虚无的作品。在文学的真实活动中,作者与读者必须是既对立又联系的合作者——文学的作者是由文本的作者与读者共同承担的。
四、目的因:价值
文学对于人生的价值,是多元(多层)的。简单讲,文学与其他艺术一样,对人生具有娱乐、表达、教育和审美四大功能。就具体的作用而言,文学对人的影响是因人而异的。鲁迅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11) 一部《红楼梦》尚且给人如此多变的见识, 作为整体的文学,所对于人的影响自然是难以概括的。
人为什么要写作?萨特认为,在作者的各种不同目的之后存在一个更深刻、更直接的共同目的:写作展示世界和要求自由的交流。萨特说:“因而,作者写作是为了将自己介绍给读者的自由,他吁求它以使自己的作品存在。但是,他不就此打住,他也要求他们回馈他给予的这个信任,他们确认他的创作自由,他们用对称而反向的吁请来征求它。阅读的辩证法在这里展现:我们越是感受到自己的自由,我们就越是确认他人的自由;他越是主张我们的自由,我们就越是主张他的自由。”(12)
然而,在文学活动中,还存在比自由的交流更深刻的动机。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品序》)这种诗学观与海德格尔的诗学观相通。海德格尔说,诗的根本含义(诗意)就是“存在真理的创建”:“诗在授予、奠基和开启的三重意义上是创建。”(13) 海德格尔将诗(艺术)的创建揭示为大地与世界之间的遮蔽与去蔽的持续斗争,并且认为正是这斗争构成创建了人诗意地栖居的世界——天、地、神、人共在的世界。在钟嵘和海德格尔的诗学中,揭示出了文学最深刻的动机和最深刻的价值——关于人与世界本原性的关联。海德格尔认为,这是一切艺术的诗意的本质所在。其实,这也正是文学之不可替代和取消的根据。
注释:
①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②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第12—14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③ Martin Heidegger:Poetry,Language,Thought; Harper & Row,Publishers,1971,p.74.
④ Paul de Man,The Resistance to Theory,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p.14.
⑤ Jacques Derrida,Acts of Literature,ed.Derek Attridge,New York:Routledge,1992,p.50.
⑥ Jacques Derrida,Acts of Literature,ed.Derek Attridge,New York:Routledge,1992,p.37.
⑦ Immanul Kant,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ed.& tr.by P.Guyer,et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95.
⑧ 黑格尔:《美学》,见《朱光潜全集》,第14卷,第346—34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
⑨ B.Croce,The Asethetic as the Science of Expression and of the Linguistic in General,tr.by C.Lya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16,p.27.
⑩ P.Rice & P.Waugh (ed.):Modern Literary Theory:A Reader,St.Martin's Press,1992,p.122.
(11) 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第1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12) Hazard Adams,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Harcourt Brace Jovanocich,Inc.,1992,p.988.
(13) M.Heidegger,Poetry,Language,Thought,tr.A.Hofstadter,Harper & Row,Publishers,1975,p.77.
标签:文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理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