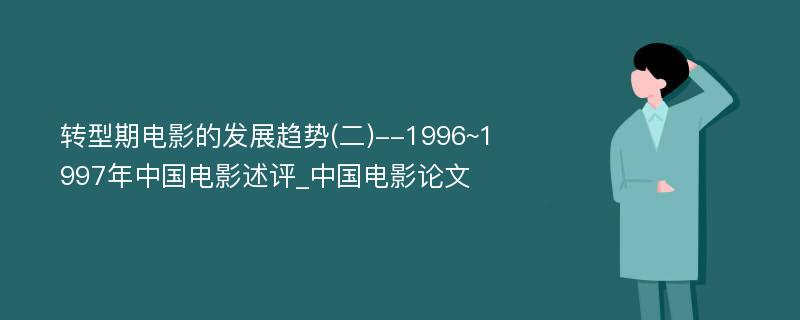
转型期电影走势(之二)——评1996—1997年中国电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之二论文,年中论文,走势论文,国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五代”的变化
相当多的早期“第五代”电影如《黄土地》、《猎场扎撒》等被看作是先锋艺术,但是从制作方式看,却是单一计划经济的产物,这与任何国家的先锋电影的制作方式都不同,在国营制片厂,选题一旦列入拍摄计划,电影制作机构就运转起来,影片即使发行量很少,艺术家也不必承担经济后果。尽管他们的不少影片对于那个体制抱着批判态度,显示出一种叛逆精神,但是应该说,他们也是那个体制的直接获益者。也许正是由于那个体制不可避免地带来官僚主义,长官意志,才需要改革。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这种拍摄条件不可能存在了。他们必须找到生存之路。张艺谋最早找到艺术探索片与商业片的交叉点,并且初步开拓了国际市场。但是当前最令各国电影业垂涎的电影市场是中国大陆,这里有文化背影和欣赏趣味基本相同的亿万观众。把注意力放到大陆市场,是“第五代”导演的必然选择。
现在时代有所不同了,让我们看一看“第五代”的作品有什么变化。
黄建新的《埋伏》与他的成名之作《黑炮事件》一脉相承,都是描写计划经济体制下官僚主义对普通人造成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影响。主人公叶民主是工厂的普通干部,他听从上级安排,到水塔上监视坏人,他忠于职守,在同事兼朋友病重的情况下,他讲义气,承担了两个人的工作。但是,在坏人被捕很长一段时间,他竟然被人遗忘了。与《黑炮事件》相似,这也是从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出发,引人深思。但是,社会背景发生变化,表达的意向也应该有所变化。《黑炮事件》中赵书信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一个群体的符号,对待他的态度是对待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的态度,而他的性格也一般被说成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性格和心态。对他的伤害所造成的影响是对整个工程的影响。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方式。而《埋伏》中的叶民主,尽管是干部,但创作者关心的不是干部队伍整体的命运,而是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
随着市场经济逐渐发展,关于个体的观念逐渐被凸现出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往往重视和关心每个阶层的代表人物,以此表示对这个阶层的关心和爱护,对于每一个个体就会因为种种原因不够重视。而在转型期,要求社会中的每一个公民都得到尊重,当然这很可能也是一种理想。
如果我们把《埋伏》放在转型期考察,就会发现主人公叶民主所处的尴尬情境,他既是一个普通人,同时也是一个英雄。在一般情况下,他是被忽略的,而只有成为英雄才会被重视。对两种体制而言,他似乎都是失意者。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人们的观念普遍受利益支配,他的未婚妻也险些被财大气粗风度翩翩的新贵抢走。他感受到双重的失落。
在他坚守岗位时最需要精神支柱,但支持不是来自上级或女友,而是来自一个热线电话。叶民主作为接受者,把一些成套的名言警句想象为对自己的精神鼓励和支持。后来他终于发现发布这些陈词滥调的居然是一位聋子。这种抽象的空话并不是针对他个人的,而是被听众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想象自己建构起来的。也许是人们太需要精神营养,才使它居然被当作排遣烦恼、坚定信念的灵丹妙药。但是,它本身的神圣感和神秘感却被消解了。人们多少还保留着计划经济时期接受他人灌输的习惯,这是作者对于盲目轻信一些宣传的社会现象的温和反讽。这种在冷静的旁观基础上几乎不动声色地批判,显示了导演日趋成熟的风格。
这部影片在很多地方并不太卖座,这说明,作者关于尊重个体的正当权利的意向还没有被广泛理解,引起共鸣。
《有话好好说》是张艺谋继《红高梁》之后与姜文的再次合作,使我们有机会把这两部影片联系起来,探讨二者的互本文关系。
《红高梁》的社会环境显然是经过精心设置的,为了张扬人物的个性,影片有意掩盖了人物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这种寓言式的提纯,只能表现一种理想状态,它表明在它产生的年代,即80年代后期,向市场经济转型并没有成为社会共识,变革的要求只能表达为抽象的理念,即:张扬生机勃勃的人性和自由舒展的生命力。它的一切表现形式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
《有话好好说》的主人公赵小帅的一些主要性格与《红高梁》的主人公“我爷爷”类似,只是张艺谋这次没有把他放在寓言式的背景中,而是放回到90年代今天的现实环境中,一些在《红高梁》中有意被隐藏的社会经济因素被突出出来,例如,在《红高梁》中从来没有出现的金钱变成最重要的角色,多次出场,而且决定了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以此表现在一个物化的社会中,人的个性必然受到挤压,不可能随心所欲。赵小帅也想张扬个性,但是显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限制。他希望娶安红,但是不能象《红高梁》时那样,只要敢抢就行。他表达爱情,不能象《红高梁》那样,引吭高歌,直抒胸臆,他需要花钱雇佣进城农民替他喊叫,笑料百出,消解了他的一片真情。现实中的安红也不象《红高梁》中的“我奶奶”那么纯情,而是庸俗而又放荡,见异思迁,选择了有钱的老板。
赵小帅需要爱异性,也希望被爱,但是不幸受阻,他深感有一种压抑感,需要通过暴力发泄,这也与《红高梁》的主角相似。但是在《红高梁》中,找秃三炮算帐的情节很简单,三言两语就摆脱了困境,而在《有话好好说》中,就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社会关系了,他处在两难境地,不愿意通过法律解决,但是使用暴力又不能象《红高梁》那么简单轻率。最终,是另一个人物张秋生的出现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在张艺谋的影片中,男性之间的关系以《菊豆》最典型,以父辈和子辈的关系象征父权制的权力结构,子辈为了争夺父辈的女人而弑父,女性背叛“父辈”而转投“子辈”,以此象征对父权制的颠覆。这种寓言模式是一种出现在单一计划经济开始发生变革时期的典型想象。但是,当市场经济在社会中影响逐渐明显的今天,这样简单的象征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观众的需要了,因为观众希望更准确更丰富地表现出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复杂感受。因此,电影中的人物必然要走出封闭的小作坊和深宅大院,进入现实社会环境。
张秋生和赵小帅不再是张艺谋习惯描述的父子关系,而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各自被烦恼困惑,因为一件偶然事件联系在一起。他们在开始时似乎要构成类似《安居》那样的互相帮助的模式,但是,情节却没有向那个方向发展,而是两人彼此交换了位置,各自充当了一次凶手和劝阻对方犯罪的牧师角色。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双方各有各的打算,却无法沟通和交流。在作者表现的社会中,暴力和金钱成为联系人际关系的纽带,而语言作为人们交流的工具却变得多余了,他们的话没有人能理解,也没有人愿意理解,消没在一片喧哗之中,只有被逼得发疯,使用暴力,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从这部影片考察,张艺谋批判的锋芒从传统转向了现实,从政治层面转向了社会,从农村转向了城市,从上层转向了下层,舍弃了依靠整体象征的寓言模式,直接描述社会现状。他对于社会走向市场经济的消极面更加关注,感到人的物化,不仅会压抑人性,甚至会把人逼迫得精神崩溃,其结果是出现难以控制的暴力,这与父权制的政治压力同样令人恐惧。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第五代”导演不仅提供了与众不同的影片样式,而且也向观众提供另外一种思维方式,让观众变换一下观察周围现实的角度。
社会的整齐划一是采取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目标,为此,电影作为宣传工具,表现的内容和主题也是确定的,要保证它是唯一正确的,不容怀疑。观众的选择余地不大。但是在向市场经济转化时期,两种经济体制并存,是这个时期最本质的特征,社会的各种奇特现象由此产生。编导对现实有不同感受,就会出现不同的描述和表现,提供不同风格的影片,进入市场,供观众选择。市场经济的一个本质特征是消费者至上,观众有选择的权利,而不是等候别人替他选择。这种选择与社会进步的方向是一致的,社会以多元而又统一为目标。
黄建新和张艺谋新作的共同之处是对社会现实持有怀疑、批判和自省精神,但是却表现了不同的个性。黄建新轻车熟路,游刃有余;张艺谋标新立异,尚欠火候。这是否标志着“第五代”今后将舍弃寓言模式,更多地直接表现社会现实,不再通过国外获奖开路,而是直接面向国内电影市场,让我们耐心等待。
构筑影像仍须努力
一些中外电影研究者认为,中国电影长于讲故事而疏于影像的塑造,其实,这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电影的影像观念是从典型西方艺术观念中发展起来的,与西方的雕塑、绘画、图片摄影等一脉相承。中国电影创作者需要有一个学习和理解的过程,观众也需要一个提高修养的过程。8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正在逐步改进,这在近年的一些优秀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在单一计划经济时期,理论界一般把影像风格赋予政治方面保守与革新的含义。保守者,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对于影像基本没有什么设计,把画面拍下来,拍清楚就基本可以了,别人怎样拍,他就怎样拍,四平八稳,不思进取。革新者把影像作为变革的突破口,以新奇影像给观众造成强烈视觉冲击,从而表达新的意义,选择的策略是,与通常的拍摄方式对着干,别人这样拍,我偏那样拍。当然,有时难免“为赋新词强说愁”,创新不被观众所接受。
在转型期,对影片最基本的要求是,它要成为在市场中能够体现自身价值的商品,根据消费者至上的原则,它应该尽量让观众满意。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个体的视觉欲望变得强烈,见多识广,欣赏水平也相应提高。无论是平庸无奇,还是孤芳自赏,都不能使观众感动和理解。这样,市场成为检验艺术水准的重要标准。创作者的创造性体现在是否能够给观众提供新颖独特而又能够使其理解令其感动的影像,而影像风格在政治倾向上是激进还是保守,其重要性大大降低了。
中国电影中一些鸿篇巨制有意识地设计整部影片的影调变化,是一大进步,《大转折》可为代表。这部影片的大部分画面笼罩在阴暗青灰湿冷的色调之中,暗示出中国革命处于一种险恶危急的氛围之中,而结局却阳光灿烂,色调明快亮丽,生机勃勃,预示前途光明,显然,色彩和影调的变化本身与革命大转折的主题完美对应,显示了编导驾驭大制作的影像的卓越艺术功力。
《林则徐》中的中国诗情画意的渲染使之成为经典之作,这无形中会给《鸦片战争》的创作者带来很大精神压力,迫使他们在影像设计方面必须推陈出新。视觉效果强烈的是两个场面的对比:中国的虎门销烟和英国的议会辩论。它们从中西艺术中吸取了精髓,构造了不同的艺术氛围,两相对照,相映成趣。
虎门销烟的场面,采用了中国山水画的构图方式,视点高远,画面开阔,向四周延伸,仿佛散点透视,令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表达了国民对销烟的喜悦之情。在晴空丽日下,销烟士兵忙忙碌碌,反差不明显,主次不分明,如同中国画的布局构思,色调明快。最巧妙的是滚滚烟雾的运用,在形式上恰似中国画中留白的技巧,不仅起到以虚当实的效果,而且预示着弥漫的烟雾中潜藏着不确定因素,烘托出危机四伏的气氛。可谓形神兼备,气韵生动。
英国议会辩论采用了典型的西洋油画构图的色调,议员们隐在浓重的阴影之中,只有两眼闪烁着光亮,画面的中心视点是放置在高光之中的中国花瓶,成为全场议员关注的中心,以此表现出英国对中国的贪婪欲望。更重要的是这种低沉的影调,一方面暗示出一种普遍的阴暗心理,因此即使是议会通过的决议,也改变不了侵略性质。另一方面也许同样预示了一种危机感,只是它是通过西方美学原则表现出来的。
电影是直观的艺术,困难在于,如何用直观的具体画面,表现一些抽象的精神。在近年电影创作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一些艺术家尽量寻找新颖独特的表现方式,通过画面造型表现人的主观心理。
《红河谷》中的野牛群狂奔而来,似乎要把英国侵略者吞噬。把处于被侵略地位的人民的仇恨和愤怒直观地表现出来,极具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美中不足的是英国人表情过于平静,没有充分表现出恐惧心理,因而削弱了艺术感染力。但是,编导毕竟用电影隐喻的方式把一种抽象的精神直观而又强烈地表现出来,这种尝试难能可贵。
《有话好好说》的手法在中国电影史上独树一帜,它为了表现人物精神的变形,而使人物影像发生变形,当观众置身于这些摇晃而又畸形的人物影像之中,就可以感受到,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和他对外在世界的感受,都出了毛病。这当然不是什么全新手法,只是张艺谋把它推到极端,几乎整部影片都在使用,而且越到高潮,使用的越频繁,表现的越强烈,在观众难以忍受的时候,正好是编导在向观众暗示,主人公张秋生的精神濒于崩溃。编导把实验电影中才会使用的一些表现方式,最大限度地运用在常规电影中,表达了独特的意义,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风格。
但是这只是在中国电影范围里讨论做出的评价。如果放到世界电影中去,不管你是否服气,这些手法基本上要被放置在模仿者的位置。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给我们带来的许多新鲜感受,也许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人早已经感受过了,中国电影人由此产生的一些创新,也许西方人早已司空见惯。在理论上说,电影手法是无限的,但是实践中,最容易发现而又最容易被观众理解接受的手法差不多被挖掘尽了,创新已经非常困难。每一种手法一经出现,获得广泛赞誉,就成为一种模式。中国电影人可以学习,使用,丰富自己的作品,满足国内观众要求,但是也许在世界范围内很难得到独创性的桂冠。
我们在《有话好好说》中可以看到王家卫、塔兰蒂诺、乃至费里尼的风格,其实,模仿他们的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他们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艺术感觉。但是这只能得其形,而不能传其神。王家卫在《重庆森林》的都市中急匆匆如历史过客幽灵一般的感觉,那种任意游荡,飘忽不定的梦幻一般的感觉,由此产生的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颓废意识,都表明了王家卫对于构筑影像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迷恋。这种全身心地投入,在《有话好好说》中难以察觉,张艺谋似乎在漫不经心地摇动着摄影机贴近角色的脸,不厌其烦地一再纪录着土匪进城一般的误打误撞,和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认死理。
那种把暴力日常化、普遍化确实有些象昆廷·塔兰蒂诺。但是《有话好好说》中设计过于工整的两人换位,实在太符合编剧规范,从而失去了昆廷·塔兰蒂诺在《低俗小说》中营造的无法控制的恶梦感,以及对流行文化反讽的幽默感。表明中国电影人在设计都市影像时,过于理性,直奔主题,缺少独特的韵味。
那些无故出现的闹哄哄的人群,或许给人传达一些费里尼《甜蜜的生活》的感觉,但是,费里尼采用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结合的叙事,使观众在主人公极度空虚以至疯狂的心灵中,总是能够感受到费里尼坦露自己的内心。而在《有话好好说》中,我们感受到的却是作者冷漠的旁观,平面化的展示,而缺乏作者的生命体验和坦露胸怀的激情。
尽管中国大陆电影人中的顶尖高手很努力,但是对于都市影像的创造仍然略逊一筹,准确把握中国人的都市感觉,创造出别具一格的中国式的都市影像,应该是今后的努力方向。
受社会影响的艺术观念
电影受社会的影响,不仅表现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主题开掘等方面,而且表现在许多形式因素方面,在社会变动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
近年中国电影在表演方面发展平稳,我们之所以看不出它有什么显著变化,也许是因为社会生活的五彩缤纷,瞬息万变,使精彩的表演暗淡无光。
中国电影表演早期直接受戏曲和文明戏影响,表演程式化,动作夸张。在单一计划经济时期,产生了一些优秀演员,但是,总体水平不高,为了让观众理解一些意念,表演偏于概念化,语调带话剧腔,表情不太细微,动作略嫌僵硬。
市场经济发展把人从家庭、单位推向社会,人的社会联系日趋复杂,参与的社会活动越广泛,承担的社会角色越多,个体在生活中的表演性就越强,因为他必须根据社会交往需要随时选择自己的态度、表情和动作。这就促使社会表演向多元化全面拓展。
社会生活的开放,使人的精神状态放松,自然也促使人们的神情放松,表情多种多样。人们更愿意也更善于把表情和动作作为表现自我的方式,而不是自我封闭,相当多的人自我表现欲望非常强烈。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无孔不入,人们参与其中的机会多起来,表演的神秘感和神圣感也就随之逐渐降低了。
总之,由于社会日常生活中人的表演性更强了,人们理解他人的表情和动作的能力也普遍提高了。这样,人们对于一般影视作品的表演的要求和基本鉴赏力也会相应提高,这就迫使演员的演技水平在整体上必须有更大的提高。
中国内地也有明星崇拜,但是其程度与香港、台湾和韩国等地相比,还不算强烈,明星崇拜的主力军是青少年,而中国大陆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对孩子管教偏严,学业比较紧张,看电影的机会不太多,更不容许他们有太多的时间追逐明星。社会对明星羡慕远远超过崇拜,因而不可能出现类似香港天王巨星式的偶像型明星。这就使一般演员,特别是电影演员不能过分依赖自己的外在条件,单纯展示像貌和个人风彩,而是要磨练演技,塑造形象换取观众的好感。
当前,电视表演正逐步类型化,而电影表演依然注重性格刻画,一些演员愿意演具有挑战性的角色,显示自己的艺术功力,这样的角色或者性格复杂,或者与自己的性格反差比较大。但是,从近年的优秀影片看,扮演这类角色时,演员也许太想演好,往往动作设计用意明显,不够松弛,略显做作,即使经验丰富的优秀演员如鲍国安、李保田也有此类情况。这与国外电影表演追求生活化的主流有相当大的差距。
在表演方面,最差的是形体语言的运用,这和我们民族习惯和文化心理或许有关,中国人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不太善于用明确的语言表达意见,说话比较含蓄,表情不够丰富,手势动作能省就省,所以人们一向比较注重察言观色,观众在看电影时,比较多的是盯着角色的脸,对动作的要求不高,这就导致演员的形体语言贫乏,缺乏特点。在近年的作品中,《黑眼睛》中陶虹扮演的盲人比较自然生动,因为根据规定情境,无法使用眼神,只好更多地借助动作。由此可知,只有观众的目光更挑剔,才能促使演技不断提高。
今后电影表演还会继续平稳发展,但可能在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的突破。
中国电影在近几年暴露的最大不足是剪辑,一言以弊之就是:乱。但问题的关键似乎不是出在剪辑本身,而是体现在电影观念方面。
最成熟的商业电影机制是好莱坞电影模式,简而言之就是通过精心设置的电影机制,把真正的创作者隐藏起来,让观众产生一种错觉,好象银幕上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让观众通过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感知,仿佛是在现场中一样。保持一种“主观认同与客观超脱之间,参与动作与观察动作之间的张力”。〔1 〕吸引观众进一步与自己喜爱的角色认同,把欲望与情感投射在他身上,让他代替自己行动,取得代偿式的满足。好莱坞电影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剪辑。
除了极少影片外,不管作者是否意识到,中国的电影方法主要是以经典好莱坞式的写实主义为基础的,但是,中国电影似乎又不同于好莱坞,区别在于,中国电影似乎偏重于让观众冷眼旁观,是看别人如何面对社会,而不是吸引观众主动投入。这也许与中国社会一种比较普遍的闲散消极的人生态度契合。
其实中国电影早期也是模仿好莱坞模式,但是社会一直处在动荡不安之中,电影业并没有建立真正严格的艺术规则。30年代左翼电影加强了思想性,但是好莱坞电影一直是左翼电影工作者艺术方面的老师,这种学习只能是各取所需。50年代后,苏联模式又全面影响中国电影,形成了一整套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电影语言,其特点是教化为主,认同为辅。“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公式化、概念化被推到极端,让人深恶痛绝,终于走向了反面。
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人对传统的商业电影规律并没有完全掌握,就开始了很多非商业电影的探索。他们比较全面了解西方电影的时候,首先比较多地学习和信奉的是非好莱坞的欧洲艺术电影。因为当时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大开眼界的时代,对于一些成规表示怀疑的时代,自己有想法强烈要求表达的时代,接受了各种电影观念却并没有来得及清理的时代,因此电影语言是新鲜而又混乱的。
当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电影人迫切需要掌握商业电影规律的时候,好莱坞通用的电影语言经过“新好莱坞”变革多年,已经非常灵活,但是它的认同机制却始终没变。但是给我们的印象是,一切规矩都不必信守了。这就使电影人相信不必完全追求经典好莱坞那种艺术效果,因此好莱坞那种严格的剪辑规范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电影人的圣经。
现在的中国电影人是见多识广的一代。由于有了录象和激光视盘,拍摄电影的神秘感消失了。一些导演比较常用的办法是被命名为“扒带子”的方式,就是照猫画虎,这极大地改变了拍摄方法,再缺乏想象力的导演也不会被任何复杂的镜头运动难倒,任何国家也无法禁止这种方式。于是,只要把这些片断组合到一起,做到大体完整,就算是可以胜任导演工作了。这样,剪辑自然难免混乱。
混乱的剪辑必然直接影响观众的投入,表面看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但是却被中国观众平静地接受下来。这违背商业电影的规律,其中应该有一些社会原因。
对于一个基本平静的社会,为了保持其观念和价值稳定不变,就需要利用电影的认同机制反复向观众强调,当观众与主要人物认同时,不知不觉就会肯定其代表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对于中国这样正处在转型期的社会,各种社会观念变化惊人,观众看电影也许不是为了找到或认定一个稳定的观念体系,而是借此了解和感受一下社会的变动,因此观众处于旁观地位,采取不主动投入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在当今这个电视遥控器比较普及的时代,面对着几十种选择,人们一般不会死守着一种影像,耐心等待自己被感动,而是随着选台,广泛接受影像信息,把各种影像混杂,已经成为观赏习惯,而这种混杂的形象流程正好与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对应,给人带来躁动不安、跃跃欲试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电影混乱的剪辑就不那么刺眼了。中国观众总是比较宽容,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看懂剪辑不规范的影片,有时甚至不太妨碍观众的喜爱,《红河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如果电影不能把观众带到梦幻之中,也就失去了自身的魅力,人们宁愿在家看电视,至少自己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挑选影像,给人一种主动权在握的感觉,而这是电影无法提供的。观众也许不会施加更大压力,但是他可以选择不看,这对走向市场的中国电影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结语
经济体制对各国电影的影响一向是比较大的,只是我们经常把它忽略罢了。特别是在单一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电影业的各方面被整合到一个系统之中,电影研究者不可能跳出这个系统反思它的对电影创作和制作的各种影响,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是在转型期,一切都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发生变动,原本浑然一体的系统露出了裂隙,新的电影体制又提供了参照系统,就给人们留下了一个考察经济体制对电影影响的良机。
社会转型的本质很难把握,因为它不是一种体制完全取代另一种的革命,而是一种缓慢平稳的改革。两种体制在本质上并非完全对立,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贡献。两种体制并存,既有计划经济因素,又有市场经济因素,最后将是什么情况,现在很难预料。人们期望的理想模式是,如何将两种体制的优越性结合起来避免它们不利的一面,这需要在实践中摸索。而在1996—1997年期间,中国电影业自身一方面需要完成转型,另一方面也要表现这种转型。不管创作者和观众是否意识到,电影从内容到形式,都受社会变革的影响,因此电影仍然可以看作是社会的铭文。本文就是在尝试捕捉这种变化,并试图推测出电影近期的基本走势。
注释:
〔1〕《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第4页,[美]托马斯·沙兹著,周传基、周欢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2 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