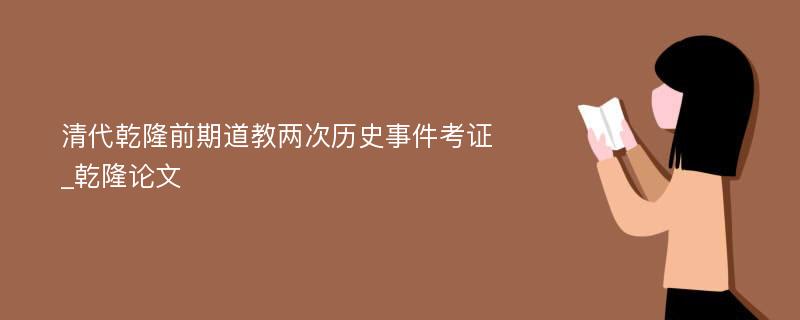
清代乾隆初年道教史事两则考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乾隆论文,初年论文,清代论文,两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教发展,与政教关系休戚相关。相对而言,有清一代对道教的扶持力度大大削弱,并接连制订贬抑与打击道教的政策,因此一般认为清代是道教发展的低潮之一。但正如学者所言,“有关道教在清代日渐衰落的历史,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因而对它被打击排斥的基本原因,也从未有过具体的答案”①,颇有加强研究的必要。清代对道教的贬抑与打击,以十八世纪中期的乾隆初年间最为明显。其中由大臣梅瑴成促成的两项举措,在贬抑正一道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清代中后期的道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这两则史事,相关研究均有所提及,但专门的讨论则迄今未见,且已有的叙述也不乏歧异之处,甚至讹误相传。现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原始档案,对此作一较为细致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乾隆初年,朝廷决定正一真人不得列入朝班行礼。此为清代贬抑道教的重大举措之一,对此,现有道教著述多定于乾隆五年。如《中国道教史》中说到:“乾隆五年(1740),第五十六代正一天师遣人至礼部投职名,欲随班祝皇寿,鸿胪卿梅瑴成上疏谓不可,帝敕礼部定议,规定嗣后正人真人不许入朝臣班行。”②这一说法,也见于其他的权威道教史著作,几成为学界共识③。然而揆之档案,却并不合于史实,颇有厘正的必要。
按上述说法源于《清史稿》“礼志”,其中记载:“(乾隆)五年,正一真人诣京祝万寿,鸿胪寺卿梅瑴成疏言:‘道流卑贱,不宜滥厕朝班。’于是停朝觐筵宴例。”④然而查乾隆四年十一月,有梅瑴成建议于明伦堂设置卧碑等事的奏折⑤;乾隆六年九月,又有梅瑴成关于查销差票以防止吏役舞弊等事的折件⑥。两折署职均为光禄寺少卿,可见乾隆五年梅瑴成所任官职,应为光禄寺少卿,而非鸿胪寺卿。这与《清史稿》所记不相吻合。又《补汉天师世家》载,张遇隆于“乾隆七年奉旨承袭入觐,召见圆明园,赐克食缎疋,宴赉视旧制有加,复赐御书教演宗传额,并朝服袍套笔墨等物”⑦。《清朝续文献通考》亦有记:“(乾隆)七年,五十六代天师张遇隆入觐,赐‘教演宗传’额。”⑧则直到乾隆七年张遇隆方获准承袭五十六代天师之职,并入觐受赐,似不可能有乾隆五年诣京随班祝寿之举。再,《清实录》对此事亦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称:“鸿胪寺卿梅瑴成奏:正一真人张遇隆恭祝万寿,据礼部文称随班行礼,应列左都御史下、侍郎前。臣思真人乃道家之流,祈禳驱邪,时有小验,仍而不革可也,假以礼貌可也。乃竟入朝班,俨然与七卿并列,殊于观瞻有碍。应请敕部定议,不必令入班行。得旨:此奏是,该部议奏。寻议:应如所请。嗣后真人承袭谢恩,臣部带领引见,并遵三年来朝之例,准其入觐,照例筵宴,宴毕还山。倘在京适值百官朝贺之期,免其列班行礼。从之。”⑨其时为乾隆七年九月,而非前述的乾隆五年,且所述内容与《清史稿》所记也略有区别。那么到底哪种记载是准确的呢,由于关系到道教史上的一段重要史事,故再作详细考察。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大力协助下,我们找到了梅瑴成当时所上相关奏折的原件,为解决这一历史疑问提供了确凿史料,其中说到:
前据正一真人张遇隆遣人至臣寺(指鸿胪寺一引者注)投递职名,欲随班恭祝万寿。臣寺未知真人应否随班,应列何品,无案可稽,行查礼部。随据礼部覆称,正一真人应列左都御史下、侍郎前。臣思真人乃道家之流,滥厕班联,不合典礼,似宜厘正,臣请为我皇上陈之。查正一真人袭自明初,当是时有张正常者,世习符箓,元时赐号天师,明太祖曰天有师乎,改授正一嗣教真人,秩视二品,俾管领道教,后遂承袭。隆庆初,内外臣工俱言张氏所为多不法,无益于世,有害于民,其世袭不合典制,宜革。遂改为上清观提点,秩五品。厥后夤缘用事太监复故号。事具《明史》,斑斑可考。迨至本朝,相沿已久,祈禳驱邪,时有小验,仍而不革可也,假以礼貌可也。而乃竟入班行,俨然与七卿并列,冠压群僚,殊于观瞻有碍。……或言张氏世袭冠带,非同常道。殊不知张氏之袭,乃假以冠服,以便约束黄冠,亦如僧人之僧録僧纲耳,虽有品级,安得与臣工伍。且张氏奉张道陵为鼻祖,言能分形炼气,白日飞升。即如其言,究何裨于世教。使张道陵而在今日,国家容而礼之,不过如法王佛子,优以赏赉,遣其还山,毋令惑众而已。亦断不使并列冠裳,以渎朝会。而况其后世之末流哉。臣蒙圣恩,承乏鸿胪,礼仪是掌。……恳求圣明敕部定议,嗣后正一真人不必令入班行,俾与太常寺乐员一同厘正,不惟朝仪整肃,且令数百年相沿之旧习,俱更定于今日,天下万世莫不仰大圣人之制度文为,实超越寻常万万也。……⑩
此折所署时间为“乾隆七年九月初四日”,奏折后面有乾隆御笔朱批:“此奏是,该部议奏。”虽寥寥数字,但明确表达了乾隆帝对此折的态度,因而也为此后的处理方案定下了基调。乾隆帝批示后不久,礼部尚书三泰等奉命议覆,并上题本请旨,档案载称:
……梅瑴成奏称……等因具奏前来。查本年七月内承袭五十六代真人张遇隆来京谢恩,臣部带领引见。复恭逢朝贺万寿圣节,据鸿胪寺咨查真人班次。臣部检查档案,康熙十九年真人张继宗承袭,曾经入觐,由臣部带领引见。其朝贺班次,无案可稽。随查前明会典,载真人秩视二品。又《江西通志》详载汉时张道陵入龙虎山修炼,历唐宋元明,代嗣其教,所纪世系封爵甚详。传至张继宗,仰荷圣祖仁皇帝赐以御书碧城匾额,后遇覃恩诰授光禄大夫。又经吏部查覆,乾隆二年六月内题请给与署理真人张昭麟一品封典在案。今张遇隆蒙皇上洪恩准袭正一嗣教大真人,宴犒赏赉不替其先世之旧,是以臣部酌议在都御史下侍郎前,咨覆在案。……臣等窃思修炼之家本系方外之教,我皇上以尧舜周孔之道治天下,百官朝会,真人自可不必列班。但奏称真人乃假以冠服,不过如僧録僧纲,虽有品级,安得与臣工伍,又援引《明史》,谓其无益于世,有害于民,不宜滥厕班联,并列冠裳,以渎朝会,观瞻有碍等语。查真人传袭几二千年,迹其先世,禳灾沴除妖邪,汉唐以来皆崇尚之,必非尽惑于异教也。殷人神道设教,周礼方相掌傩,义各有取。我朝会典籍开载真人承袭条内,定有庆贺来朝之例。盖以其炼气分形,虽属无裨于世,而驱除祈祷,实亦有济于民,似不得抑之过甚,致羽流未品不列冠裳者比。臣等伏请嗣后真人承袭谢恩,仍照例臣部带领引见,并遵三年来朝之例入觐天颜,照例筵宴,宴毕还山。倘在京适值百官朝贺之期,免其列班行礼,则朝会班联不烦厘正,而真人钦奉恩纶,益感沐皇上优渥之隆施矣。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乾隆七年十月初九日题,本月十一日奉旨:依议(11)。
于此可见梅瑴成上折提议,时在乾隆七年九月之初,而礼部议覆在十月中旬,《清史稿》将之定于乾隆五年,明显讹误。又据档案,可知《清实录》所记为礼部议覆题本的摘录,除措辞外内容没有太大出入,但将时间系于乾隆七年九月初四日亦略有误差。盖其时为梅瑴成上奏提议的时间,而礼部议覆,得到乾隆帝最终批准,并付之施行,已在乾隆七年十月以后。
再,梅瑴成所上奏折中,仅建议“敕部定议,嗣后正一真人不必令入班行”,并未提及朝觐筵宴的问题,礼部尚书的议覆也明确提出,“臣等伏请嗣后真人承袭谢恩,仍照例臣部带领引见,并遵三年来朝之例入觐天颜,照例筵宴,宴毕还山。倘在京适值百官朝贺之期,免其列班行礼,则朝会班联不烦厘正,而真人钦奉恩纶,益感沐皇上优渥之隆施矣。”可见当日关注的重点在于“滥厕班联”、“整肃朝仪”之事,《清史稿》所记“于是停朝觐筵宴例”亦有讹误,乃是将后来发生的事件前置了,随后考述,此不赘。
《清史稿》又载:“(乾隆)十七年,改正一真人为正五品,不许援例请封。”(12)《补汉天师世家》所记相同,略谓:第五十六代天师张遇隆“(乾隆)十七年以梅御史劾部议改为正五品,厥后优游山中,悉心任化,陶然以终”(13)。虽然一些学者已据文献记载,将正一真人降秩时间定于乾隆十二年,但《清史稿》“乾隆十七年”之说仍时见征引,甚至不乏影响较大的道教著述。如窪德忠先生所著《道教史》附表中,即录“1752(即乾隆十七年—引者注),张遇隆改为正五品”(14)。其他或称“乾隆十七年(1752),左都御史梅瑴成劾降正一真人为正五品秩”(15)。或称“乾隆十七年(1752),正一真人品级也由二品降为五品,而且不许援例请封”(16)。或简要记作“乾隆十七年(1752)又将其由二品降为五品”(17)。所述基本沿自《清史稿》或《补汉天师世家》。唐大潮先生则注意到有乾隆十二年与乾隆十七年两种不同的记载,称“《清朝续文献通考》和《癸已[巳]存稿》认为是在乾隆十二年,而《清史稿》和《补天师世家》则认为是在乾隆十七年”(18)。但未作考辨,仅肯定其降秩之事实。而另处又记,第五十六代天师张遇隆,“乾隆十七年(1752),在御史梅瑴成的弹劾下,天师品秩被降为正五品,并不许援例请封。”(19)前后不无牴牾。
按此事详见于《清实录》,谓:“大学士等议覆,副都御史梅瑴成奏称:正一真人,秩视二品,原属明代旧制,近复加至光禄大夫,题请袭封。伏思孔子至圣,后裔承袭公爵,颜曾思孟以下,不过博士。今张氏所袭,竟与圣裔无别。请照提点演法之类,给与品级,停其朝觐筵宴等语。查正一真人,世居江西龙虎山,至宋始有封号。元加封天师,秩视一品。明初改正一嗣教真人,秩视二品。本朝仍明之旧,而会典不载品级。盖以类于巫史方外,原不得与诸臣同列。即康熙雍正间曾荷褒封,亦用以祈求雨泽,非如前代崇尚其教,而必阶以极品也。至从前给一品封典,亦因无案可稽,但凭旧轴题给,原未可为定制。嗣后应不许援例假借,题请给封。至所奏授为提点演法之类,所见亦是。但道录司左正一系正六品,正一真人有统率道众之责,若授为提点演法,则亦系正六品。查太医院院使秩,正五品。巫医本相类,请将正一真人亦授为正五品,其原用银印即令缴部。嗣后缺出,应令该抚查其子孙应袭者,取具地方官印结,咨部袭补,照道官例注册。至朝觐筵宴,均如该副都御史所奏停止。从之。”(20)《大清会典事例》有载:“(乾隆)十二年覆准:江西张氏,世居龙虎山,真人名号,非朝官卿尹之称。存其旧名,正所以别于流品。前因无案可稽,两遇覃恩,加至光禄大夫,封及三代,邀荣逾分,理应更正。嗣后应不许援引假借,题给封典。至正一真人有统率龙虎山上清宫道众之责,视提点演法稍优。按太医院使秩正五品,医巫类本相等,应将正一真人亦授为正五品,从前所用银印缴部换给。……至于朝觐为述职大典,筵燕实惠下隆恩,未便令道流厕身其间。应请一概停止,以肃体制。”(21)亦见于《清朝文献通考》:“乾隆十二年议定,正一真人有统率龙虎山上清宫道众之责,秩视太医院院使,为正五品”(22)。可知乾隆十二年之说似有根据,而定于十七年恐为讹误。为切实起见,我们又设法查找到梅瑴成所上奏折的原件,其中说到:
乾隆七年……见礼部议覆臣奏……内称:正一真人张继宗于康熙十九年诰封光禄大夫,署理真人张昭麟又于乾隆二年题请承袭在案。臣不胜疑惧,因封典非鸿胪寺执掌,未敢渎陈。今当重修会典百度永厘之日,何敢缄默。查道教本属异端,而符箓更道家之旁门。正一真人秩视二品,原系前明敞政,仍而不改已非所宜,况又加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官阶之极品也;封及三代,锡类之旷典也。张继宗未尝居启沃赞襄之职,又无汗马开疆之劳,何由增秩而膺极品之封?若系特邀异数,必降有明旨,何以不存于档册,不见于会典耶?我国家于世袭之典,尤极慎重,……然则张继宗即果蒙特恩,诰授光禄大夫,亦必无准其世世承袭之理。……今张氏所承,远过大贤,竟几与圣裔无别,于崇德报功之意似均不符。微臣愚见,嗣后正一真人可否照提点演法之类给与品级,出自圣恩;其会典所载朝觐筵宴之处概行停止;如有差遣,礼部行文调取,赏给饮食可也。……(23)
后有乾隆御笔朱批:“此奏是,大学士会同该部议奏。”原折未署时间,末注“乾隆十二~十八年”,但笔迹不同,当为后来的档案整理人员所标,而非原来具折时间。按折中署职为“左副都御史”,经查梅瑴成于乾隆十二年四月方由宗人府府丞迁左副都御史,次年闰七月即改刑部右侍郎,十五年九月再迁左都御史(24)。上述折件既然在其左副都御史任内,则应当在乾隆十二年到十三年之间。又据清代档案处理流程,所上奏折一般记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中,如梅瑴成乾隆七年九月初三日所上奏折,“随手档”中即简要注明:“朱批梅瑴成一件:真人不宜滥厕班联。是,部议。”(25)但由于目前所存乾隆朝“随手档”存在缺佚,其中即包括乾隆十二年份,因此迄未查到梅瑴成“为羽流承袭冒滥恳请厘正载入会典事”一折的准确时间。但经过努力,我们终于在乾隆十二年十二月的《礼科史书》中,找到了大学士讷亲等所上的议覆题本抄件,其中详细记其原委:
该臣等会议得:都察院左都御史(原档如此,误,应为“左副都御史”—引者注)梅瑴成奏称,臣于乾隆七年鸿胪寺任内,见礼部议覆臣奏……等因具奏前来。臣等伏查正一真人世居江西之龙虎山,至宋始有封号,元则加封天师,授紫金光禄大夫,视正一品。明初改正一嗣教真人,中降为提点,后仍复故封,秩视二品。其时升时降,本无定资。我朝会典不载真人品级,仍明之旧尚未更改,盖以其类于古之巫史,且又系方外,原不得与诸臣工同列。即康熙二十六年蒙圣祖仁皇帝亲洒宸翰,赐号碧城,并颁大真人府太上清宫匾额。雍正九年蒙世祖(原档如此,误,当为“世宗”—引者注)宪皇帝特恩修理龙虎山上清宫,皆以累代相沿,地方名胜所在,不宜任其倾頺,且使之稍效祈祷之劳,或用以为民祈求雨泽,非如前代崇尚其教,而必阶以极品也。今该副都御史所奏加至光禄大夫,封及三代,实属逾分。虽康熙二十年至四十二年两遇覃恩,授以一品封典,崇及三代,亦由从前无案可稽,但凭旧轴题给,原不可为一定之制。查真人乃系道家名号,非朝官卿尹之称,存其旧名,正所别于流品。惟加至光禄大夫,封及三代,邀荣过分,理宜更正。嗣后应不许援例假借,恳请题给封典。至该副都御史所奏授为提点演法之类,所见亦是。但查正一真人本朝原未定有品级,惟提点娄近垣现授四品,乃奉世宗宪皇帝特恩,不可援以为例。是给与正一真人品级之处,原可毋庸置议。但今道录司左正一系正六品,正一真人有统率龙虎山上清宫道众之责,亦应给与品级。臣等酌议,若授为提点演法,则亦系六品,使之与众同列,难以统率,应较左正一品级稍优。查太医院使秩正五品,巫医类本相埒,请将正一真人亦授为正五品,永著为例。再查正一真人既定为五品,未便仍用银印,应令将所有银印送部缴销,另行换给。至正一真人承袭由来已久,不过令其奉祀宫观,亦非若文武勋阶为国家酬庸之典,爰及苗裔,以示显荣。嗣后缺出,仍由该抚查其子孙应袭者,取具地方官印结,咨部袭补,照道官例注册。至于朝觐为述职大典,筵宴实惠下隆恩,若令道流厕身其间,实于体制未协,应一概停止可也。再,此本系礼部主稿,合并声明。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题,本月十五日奉旨:依议(26)。
梅瑴成上折的具体日期,虽尚待史料方能最后确定,但据上述相关档案,似可推断形成于乾隆十二年的冬季。《实录》以原件未注时间,故系于议覆的十二月份。依时间推算,梅瑴成上折当以该年十一月到十二月初的可能性为大,往前推最早或也不会超过两到三个月。而礼部议覆施行,则明确在十二月十五日,《实录》内容亦系摘录议覆题本而来,大体准确。据此,可知《清朝续文献通考》和《癸巳存稿》作乾隆十二年,合于史实,而《补汉天师世家》和《清史稿》定于乾隆十七年,则无疑是错误的。有著作记为:“乾隆十一年(1746),左都御史梅珏成奏正一真人降为正五品秩”(27),此为仅见,或属笔误。又梅瑴成时任“左副都御史”,前引叙述或谓“梅御史”,或谓“左都御史”,均不甚准确。
再顺便指出,礼部议覆后最终批准与实施的时间,在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时届年底,若换算成公历的话,为1748年1月15日。故笼统说成“乾隆十二年(1747),左副都御史梅瑴成奏改正一真人为正五品,不许援例请封”,是可以的。但若细致到月,则必须说成“乾隆十二年十二月(1748年1月),以左副都御史梅瑴成奏请,经礼部议覆,旨准改正一真人为正五品,不许援例请封”,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清史稿》的上述错误,不仅误导国内外道教学界数十年,连历史学界亦未能注意到。最为典型的,是费多年之功、集数十位台湾学者之力而成的《清史稿校注》,颇惠于清史学界,但于此讹误亦未检出,实为遗憾(28)。上述原始档案的发掘,为考订这两件重要的道教史事提供了切实依据,据此可以纠正目前学界辗转相传的讹误。
同时,这些档案还细致记载了乾隆七年与乾隆十二年两次讨论与决策的详细内容,并回溯到此前朝廷对待正一天师的一系列举措,这对于清代道教史研究的其他方面,也不无意义。如梅瑴成折中的详细阐述,以及礼部尚书、乾隆皇帝随后处理过程中的措词与语气,无疑可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感受到当时朝廷君臣对于道教的基本认识与态度。又如清初以来有关正一道的重大史事,在这些档案中都有所反映,包括:康熙十九年真人张继宗承袭入觐;康熙二十年至四十二年两遇覃恩,“授以一品封典,崇及三代”;康熙二十六年清圣祖赐号“碧城”,并颁大真人府太上清宫匾额;奉雍正特恩,提点娄近垣被特别授予四品秩位;雍正九年清世宗命修理龙虎山上清宫;乾隆二年六月给与署理大真人张昭麟一品封典;乾隆七年七月,五十六代天师张遇隆承袭“正一嗣教大真人”,晋京谢恩时,“宴犒赏赉不替其先世之旧”,凡此等等,均不失为珍贵的档案记录。
这些内容,有的已见诸相关文献,档案的详细记录进一步提供了第一手的可靠史证。有的则更为详细,不仅有补充资料的作用,甚至可以更正某些由于史料不足而导致的失误。如乾隆七年(1742)张遇隆承袭入觐时,前引《补汉天师世家》载“召见圆明园,赐克食缎疋,宴赉视旧制有加”,即不无夸大张扬之嫌。因档案作“今张遇隆蒙皇上洪恩准袭正一嗣教大真人,宴犒赏赉不替其先世之旧”,故今人所改“召见于圆明园,有什物之赐,礼如旧制”,是较为准确的(29)。又学者往往提及废除正一真人朝觐清帝的史事,以此作为道教在清代地位下降之标志,但多数叙述均存在讹误。如傅勤家在《中国道教史》中说清代“且听廷臣之言,对于张天师,始但许称正一真人,由二品降为五品,后又不许朝观[觐],令礼部带领引见”(30)。日本著名道教研究学者窪德忠也提到:“第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入朝时,顺治帝赐其一品印,而乾隆帝将他降至正五品,继而不让天师晋谒皇帝,仅由礼部引见。”(31)这一说法,近人仍在继续沿用。如称“然至乾隆朝,天师从一品(误,应为二品)降止[至]正五品,继而又不许朝靓[觐],反令礼部带领引见。”(32)或作“如对张天师,只许称正一真人,由二品降为五品,后又不许朝觐,令礼部带领引导”等等(33)。但据档案记载,乾隆七年七月第五十六代天师张遇隆觐见谢恩时,即由“臣部(指礼部—引者注)带领引见”。又载此前“康熙十九年真人张继宗承袭,曾经入觐,由臣部带领引见”。礼部尚书三泰最后又建议“臣等伏请嗣后真人承袭谢恩,仍照例臣部带领引见,并遵三年来朝之例入觐天颜,照例筵宴,宴毕还山”(34)。可见由礼部带领引见,自清初以来一直到乾隆年间,都是正一真人朝觐皇帝的基本礼仪,所谓“礼部引见”,其实就是指朝觐皇帝。前引诸贤将“觐见”与“礼部引见”看作两个独立甚至相互替代的礼仪,是不合于史实的。也就是说,“不让天师晋谒皇帝,仅由礼部引见”的说法,乃是自相矛盾的叙述,应予厘正。
注释:
①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道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见http://fass.net.cn/fassNews/fass_readnews.asp?NewsID=1921
②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下册第836页。
③如施舟人前引文,以及李养正《道教概说》([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11月版,第209页)、唐大潮《中国道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316页)、王卡《中国道教基础知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2月第二次印刷,第109页)、卿希泰与唐大潮《道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336页)等,所述基本相同。
④《清史稿》卷一百十五,志九十,职官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2月印刷版,第十二册,第3332页。
⑤录副奏折,光禄寺少卿梅瑴成奏请设立卧碑置于明伦堂等事,乾隆四年十一月初七日。原档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3-1146-019,缩微号:082-0083。
⑥朱批奏折,光禄寺少卿梅瑴成奏为请敕下直省督抚转饬各属衙门凡有差票事竣即行查销事,乾隆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原档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4-01-01-0060-022,缩微号:04-01-01-010-0673。
⑦《补汉天师世家》,转自[日]小柳司气太:《白云观志》,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发行,昭和九年(1934年)三月版,第351—352页。
⑧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八十九,选举考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版十通本,第1册,第8494页。
⑨《高宗纯皇帝实录(三)》卷一百七十四,乾隆七年九月上,庚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1月版,《清实录》第十一册,第235页。
⑩朱批奏折,鸿胪寺卿梅瑴成奏为道流滥厕班联观瞻有碍恳请敕部定议以肃朝仪事,乾隆七年九月初四日。原档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4-01-14-0008-008,缩微号:04-01-14-001-2049。相关档案的查阅,得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邹爱莲馆长以及唐益年、吕小鲜、胡忠良、朱淑媛、刘若芳等诸位先生的帮助,谨此一并志谢。
(11)礼部尚书仍管太常寺鸿胪寺事三泰等题为遵旨议奏事,乾隆七年十月初九日。原档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全宗:内阁,文种:礼科史书,案卷号:324。
(12)《清史稿》卷一百十五,志九十,职官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2月印刷版,第十二册,第3332页。
(13)《补汉天师世家》,转自前引[日]小柳司气太:《白云观志》,第352页。
(14)(日)窪德忠著、萧坤华译:《道教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326页。
(15)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增订本),下册第836页。但该书所附《中国道教史年表》则作“1747,(乾隆)十二(年),丁卯,降正一天师为正五品,停止朝觐、筵宴等活动”,前后矛盾。见同书第986页。
(16)前引施舟人:《道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
(17)胡孚琛、吕锡琛著:《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丹道》增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351页。
(18)唐大潮编著:《中国道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309页。又卿希泰与唐大潮著《道教史》所述基本相同,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336页。
(19)唐大潮编著:《中国道教简史》,第316页。
(20)《高宗纯皇帝实录(四)》卷三0四,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上,辛未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2月版,《清实录》第十二册,第981页。
(21)托津等奉敕纂:(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九十,礼部,方伎,正一真人事例。(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91年11月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六十七辑,第667册,第7727—7729页。
(22)乾隆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卷八十八,职官考十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版十通本,第1册,第5635页。
(23)朱批奏折,左副都御史梅瑴成奏为羽流承袭冒滥恳请厘正载入会典事,无日期。原档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4-01-15-0018-002,缩微号:04-01-15-001-0907。
(24)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3月版,第二册第1210页,第一册第608、第609页,第一册第221页。又参见《高宗纯皇帝实录(四)》卷二百八十八,乾隆十二年四月上,己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2月版,《清实录》第十二册,第762页。
(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二册,第207页。
(26)大学士果毅公讷亲等题为遵旨议奏事,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原档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全宗:内阁,文种:礼科史书,案卷号:390。
(27)王卡主编:《中国道教基础知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2月第二次印刷,第109页。
(28)(台湾)国史馆校注:《清史稿校注》,[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9月版,第四册,第3306页。
(29)张继禹:《天师道史略》,[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211页。
(30)傅勤家:《中国道教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232页。
(31)(日)窪德忠著、萧坤华译:《道教史》,第262—263页。又译文“而乾隆帝将他降至正五品”易致歧义,因降为正五品时已至第五十六代天师张遇隆,而非文前所述的第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且时隔百余年,改作“而乾隆帝后来将正一真人之秩降至正五品”或较妥当。
(32)张继禹:《天师道史略》,第126页。
(33)朱越利、陈敏:《道教学》,[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08页。
(34)前引礼部尚书仍管太常寺鸿胪寺事三泰等题为遵旨议奏事,乾隆七年十月初九日。
标签:乾隆论文; 左都御史论文; 道教史论文; 中国道教史论文; 清朝论文; 清朝续文献通考论文; 历史论文; 清实录论文; 清史稿论文; 光禄大夫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宋朝论文; 唐朝论文; 北洋政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