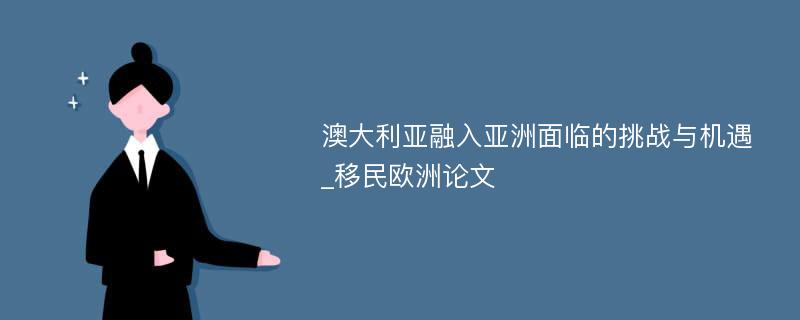
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挑战与机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大利亚论文,亚洲论文,机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澳大利亚自1901年组建联邦以来,在近一个世纪的光景里,却难以搞清楚自己归属于一个欧洲国家还是亚洲国家?从地理位置看,作为大洋洲的一个主要和有影响力的国家,它紧挨亚洲,与亚洲国家有着自然的频繁的外交和经济往来;从人种和文化背景来看,它又是地道的欧洲人移民国家。正因为如此,澳大利亚既可以是此,也可以是彼。而事实上,它既非此,亦非彼。有人把它比作童话里的蝙蝠,既非兽又非鸟。甚至有人戏称澳大利亚是个错放亚洲的欧洲国家。或把澳大利亚人称为“白色的”亚洲人。
何为“融入亚洲”?融入亚洲既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也并非只关澳大利亚一国之事。融入亚洲,不只是经济上的合作,还有政治上、文化上一定程度的认同。从地域范围来看,亚洲是一个政治上、文化上和军事上差异巨大以至于很难把它描述为一个“地区”的大洲。(注:伽耐特·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澳大利亚的外交》(Gareth Evans、Bruce Grant,Ar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inthe World of the 1990's),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 14页。)因此,澳大利亚融入亚洲是在亚太地区的融合,准确地说,是在太平洋西部地区的融合。这是由地缘政治和澳大利亚国家利益所界定的。从现实性来看,这是澳大利亚融入亚洲最实际和最本质的部分。对澳大利亚而言,融入亚洲遇到的第一道门槛就是澳大利亚狭隘的民族意识和本土观念对亚洲意识和观念的抵触。
澳大利亚狭隘的民族意识和本土观念集中体现为“白澳”意识。“白澳”意识作为一种思潮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浮出水面。最初表现为英国移民担心有色人种与之通婚会导致血统混乱,继而影响英吉利民族血统的“纯洁性”,同时又担心白种工人的就业机会会减少。“白澳”意识随着种族偏见的加深而变得系统化和理论化,它明显地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促动。一是澳大利亚作为欧洲移民的国家,它认同于欧洲民族及其文化价值观念。另一因素是对亚洲的偏见和畏惧。对亚洲偏见和畏惧是基于亚洲的落后以及庞大的人口。进而导致对亚洲移民的限制。“白澳”意识上升至统治阶级的意向和国家的意识,使“白澳政策”应运而生。“白澳政策”通过一系列的立法使“澳大利亚是白种人的澳大利亚”的口号成为教条。这种充满种族主义气息的“白澳政策”自20世纪初联邦成立时就成为澳大利亚的基本国策,直至20世纪60年代。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光景里,移居澳大利亚的主要是欧洲移民,其他非欧居民被这一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政策挡在澳国门之外。亚裔有色人种深受排斥和歧视,而受其害最深的首推澳洲土著人。
“白澳政策”是澳大利亚实行种族歧视的产物,而种族歧视是英国留给澳大利亚人的殖民遗产。
白澳意识和白澳政策给澳大利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种与殖民主义相联系的社会意识维系了澳大利亚对英国的依附性,妨碍了澳大利亚摆脱英国控制而成为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其次,它严重阻碍了澳大利亚与亚洲及其它地区的正常交往,造成了澳大利亚的自我封闭和妄自尊大。这给日后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留下了不小的历史包袱。
60年代后,推行种族歧视的国家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如南非等国,同时,欧洲来澳移民随人口出现负增长而逐渐减少。这引起一些种族主义者的恐慌。7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大家庭的合法席位,并且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亚洲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显著提高。作为亚太地区的一部分,已独立发展的澳大利亚不能不正视与其近邻的关系。澳政府这才改变了“白澳”政策,放松了对亚洲移民的限制。80—90年代,随着澳实施“融入亚洲”的政策,亚洲移民的数量才逐渐增多起来。亚洲移民占同期来澳移民总数的40%,但截至1997年12月31日,澳洲1860万人口中,亚洲人的数量不足90万,所占的份额不足5%, 如果认为“白澳政策”的废除意味着有色人种完全自由地与白人平起平坐,那就有一叶障目之嫌。“白澳政策”的废除并不意味着“白澳意识”的净灭。1993年,保琳·汉森建了一个带有极端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党——一族党,即是例证。在1996年3 月举行的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中,保琳·汉森赢得联邦议会下院的一个席位。这是种族主义沉渣泛起的表现。此后,她便利用议会和其他一些公开场合发表演讲,抨击政府的亚洲移民政策。她以毫不掩饰的种族主义的腔调警告说:“澳洲有被亚洲人淹没的危险,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宗教,并形成聚居地,他们不融入澳洲社会。”(注:转引自刘樊德《保琳·汉森今何在?—保琳·汉森及其一族党的历程》,《当代亚太》1999年第7期。)显然,保琳·汉森的话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保琳·汉森的这一连串举动不但引发了澳公众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且激起国际社会尤其是亚太地区对澳国内政的极大关注。虽在1998年10月进行的联邦大选中,保琳·汉森的“一族党”失利,但保琳·汉森现象所造成的影响却不是在短时期内能消除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加重了亚洲对澳大利亚的戒备心理,对澳大利亚融入亚洲起到了阻滞作用。
二
澳大利亚在政治上与亚洲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外交和经济方面已不再把亚洲视为一个危险的对手,而是一个利益均沾的伙伴。1972年,“像一头雄狮走上政坛”的格夫·威特拉姆(1972—1975年)给澳内政和外交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他的不因循守旧的执政风格让世人为之瞩目。这一年也因此视为澳政府最终树立了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独立形象的一年。其表现除了从越南撤军外,最主要的是:进一步独立于澳大利亚前首相罗伯特·曼兹尼称之为除英国外另一“伟大而强劲的朋友”的美国的政策,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与近邻印尼密切合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加快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独立进程等。虽然威特拉姆的外交政策在以后20多年里不断地被修改完善,但它奠定了澳大利亚未来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自二战以后,英澳经济联系如同政治关系一样,已呈稀松之态。英澳均不把对方视为依赖的伙伴。1961—1962年,英国试图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目的虽未实现,但已经为英澳关系未来的发展描绘出一个轮廓。欧共体统一市场内实行农产品补贴政策必将使澳大利亚传统的农牧产品的出口受到挤压。毫无疑问,英国将越来越多地在它的近邻当中寻找贸易伙伴。而澳大利亚也必须改变自己的方向。 1967 年澳日之间的贸易额第一次超过澳英之间的贸易额。1968—1969年, 英国要求澳配合控制伦敦的有价证券投资外流, 澳大利亚没有给予重视。1973 年英国加入欧共体后,澳大利亚也把发展同亚洲的关系尤其是经贸合作关系放到重要的位置。现实而又明智的选择使澳大利亚人“现在则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亚洲的一部分,邻国的繁荣昌盛和他们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注:约翰·根室:《澳新内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澳大利亚是个后起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7年澳大利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20540美元,排当年世界第16位。(注:《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蔡秋生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有人认为澳大利亚的富裕是因为拥有大量的原材料。澳大利亚虽是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由于受人口稀少所导致的国内市场狭小的制约,澳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和有限性表露无遗,进而威胁其国家安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出现了大动荡和大改组的局面。同时,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为回应这一逼人态势,澳大利亚承认本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在于使自身在地区间国际间贸易中更富竞争力,因此,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侧重点为确保亚洲市场对澳国商品开放。1987年外交部和贸易部的合二为一表明发展经济已成为外交政策中主要的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注:戈登·福斯主编:《当代澳大利亚社会》,赵曙明主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在政治需要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澳大利亚更加明确地将发展重点放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亚洲的东南部和东部地区。1989年2 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提议召开亚太经济合作部长会议,共商亚太经济合作发展之大计。同年11月在堪培拉召开了第一次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堪培拉会议被看作是“太平洋时代的开始”。此后,澳大利亚以亚太组织为重点,积极推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 1994年4月,澳大利亚总理基廷在访问老挝、泰国和越南时正式提出澳新(新西兰)—东盟自由贸易区,目的是保证东亚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时,澳不被排除在外。1995年,澳大利亚政府首次召开了驻东亚使节会议,讨论和研究了澳大利亚未来10年对亚太的外交战略,强调要加大对亚太的外交力度,从而使澳与东亚国家在经济上融为一体。此项战略被称为“伙伴和一体化战略”的外交政策。在该战略中,澳重点强调与东盟加强联系,对东盟推行“全面外交。”东盟是澳大利亚的近邻,又是澳通向亚洲的门户。澳大利亚认为APEC和ARF (东盟地区论坛)是澳推行亚太政策的两大支柱和两大突破口,但必须得到东盟的有效支持,否则融入亚洲只是一句空谈,也无实际意义。比如由于马来西亚的反对,澳大利亚无缘出席1993年11月在西雅图召开的第一次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目前,亚洲在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日本是澳大利亚最大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96年,澳大利亚出口产品的65%面向亚洲广大市场。这是40年前的三倍。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国已由最初12个扩大到1999年的21个。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50%,对外贸易额约占全世界的48%,成为全球实力最强大的区域经济组织。澳大利亚也从这个既开放又封闭的经合组织中取得可观的实惠。
应予强调的是,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和潜在的最大的消费市场。这种诱人的前景使得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对亚政策中占据重要位置。加强与中国在外交、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已成为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一个重要环节。澳中关系继格夫·威特拉姆政府启动以来,在弗莱瑟和霍克政府的努力下,中澳关系得以进一步深入。80年代,两国总理多次互访,加深了相互沟通和了解,使得澳中关系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典范。“文化上的交流成为80年代初期两国关系的显著特征。”(注:E·M·安德鲁斯:《澳大利亚与中国—模糊的关系》(E· M ·Andrews, Australia and China—The Ambiguorus Relationship),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页。 )并且成为经济合作顺利开展的坚实基础。中澳两国在亚太经合组织内的广泛共识以及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密切磋商。对推动亚太地区的合作与发展作出了积极性的贡献。90年代两国高层领导互访频繁。1997年霍华德总理访华。1999年江泽民主席作为国家元首第一次访澳,为21世纪中澳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两国经贸关系在良好的外交关系的推动下正稳步地向前迈进。 至1998年底,两国贸易额为50多亿美元。中国已成澳大利亚第五大贸易伙伴,第七大出口市场,是澳大利亚羊毛的最大买主。澳大利亚已成为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最大的中国对外投资国。(注:《经济日报》1999年9月8日。)
三
白澳政策的退潮以及种族主义的消退是澳大利亚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至关重要的变革。英澳特殊纽带的松动以及澳大利亚自主意识的增强,无疑为澳大利亚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一个崭新的形象,也为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对澳大利亚来说,融入亚洲,可谓机遇和挑战同时并存。从某种意义上,融入亚洲取决于澳大利亚的态度和努力,“解铃还需系铃人”。澳大利亚政府只有正视以下现实,才能避免由于回避或掩饰而带来的意外的碰撞。
首先,亚洲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生机盎然的大洲。它既是一个开放的大洲,又是一个封闭的大洲。
亚洲是一个特点鲜明的大洲。地域广泛,人口众多,社会形态各异,历史悠久,文化多元且差异巨大,宗教信仰复杂,种族多样,语言丰富。澳大利亚《墨尔本先驱日报》曾对亚洲的文化和语言作过统计:亚洲有六个甚至更多特点显著的文化传统,几十个影响稍小的重要文化以及多种多样的语言。这些特点既是亚洲久已开放的结果,又是亚洲进一步开放的基础。亚洲地区的多样性是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一大挑战,同时又使得任何一个准备融入亚洲且又作出适当努力的民族变得更容易接近。一个分散的格局留下融入的空间比一个统一的格局所留下的空间要大得多。
由于现代传媒、电讯和交通方面的急剧变化,亚洲各国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一个建立在优势互补、共存共荣基础上的开放的亚洲正在形成。边界成为开放的窗口,迎来送往不同国籍、不同语言和不同肤色的人。在亚洲境内旅行的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各国间互设公司,使得雇用劳动力成为国际性的。与工作移民相伴的是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分享着来自其它亚洲国家的食品、电视节目、电影和现代音乐,学习其它亚洲国家的语言。特别是中文和日本语在亚洲到处都已列入外语教学大纲之中。(注:戈登·福斯主编:《当代澳大利亚社会》,赵曙明主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亚洲成为世界上最富潜力和目前发展最快的市场,这一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一个现代化的、充满朝气的、具有美好未来的亚洲无论是对亚洲还是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全新的形象。(注:戈登·福斯主编:《当代澳大利亚社会》,赵曙明主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7页。)
亚洲又是封闭的。亚洲地区有着特殊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格局。亚洲国家曾经高举弘扬民族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大旗,不仅赢得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而且形成了建设国家的自信和民族凝聚力。亚洲地域分散,民族意识浓郁。亚洲的政治格局较为复杂,远不如其他大洲明朗。亚洲各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并选择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多样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他们强烈反对西方的人权标准,反对将西方伪装的价值观和民主观强加在自己头上,主张人权问题必须区别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也就是说,必须考虑到国家和地区的特点。由于历史上帝国主义在亚洲的角逐,又由于这个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多样性以及大国之间的微妙复杂关系,该地区不大可能建立类似欧安会那样的安全机制。这也是该地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处于动荡不宁局面的主要原因。这里有各国内部的民族矛盾,有各国间的贫富差距,有领土分割的压力,有邻国间纠缠不清的领土纷争,有领海主权的争议等。
为此,澳大利亚应该重新调整它的外交和国内政策,以此表明澳大利亚的“真正利益”不只是在于成为亚洲的组成部分,而且在于更好地了解亚洲。澳大利亚政府尚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必须改变公开谴责亚洲国家人权状况的方式。许多亚洲人,尤其是印尼人,不认为澳大利亚如它所宣传的那样有着良好的人权状况。在澳大利亚,言论并不自由,媒体只是政府的喉舌,“喜欢披露敏感新闻事件和写一些有关亚洲国家领导人的否定性行为文章的澳大利亚新闻记者对澳大利亚融入亚洲并无益处。 ”(注:凯耶·希利:《走向共和?— 90 年代的问题》( Kaye Healey,Towards a Republic? —Issues for the Nineties)第13卷,斯品利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其次,澳大利亚的历史、文化虽来源于欧洲,但与欧洲发展并不同步。表现在经济发展方面澳大利亚虽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但长期缺少竞争,其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滞后,在与面临产业升级和需要高附加值产品的亚洲国家合作方面,已无任何优势可言。而在这一地区,美、日凭借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在亚洲市场已显垄断本色。因此,澳大利亚必须尽快调整产品结构,发展高、精、尖技术产业,使其产品多样化,谋求更多的贸易伙伴,适应竞争日趋激烈的亚洲市场的需要,否则,澳洲在科技和经济交流方面,对一个日新月异的亚洲毫无吸引力。在军事方面,澳大利亚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地区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加强相互之间的依赖。澳大利亚虽无与他国接壤,但周边环境并不安宁。为此,霍华德政府强调了美国军事力量在亚太存在的必要性,加强了与东盟的安全对话,尤其是与近邻印尼于1995年12月签定了《澳印双边安全协定》。这些举措无可指责。但澳大利亚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充分尊重他国主权的前提下,承担与自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义务。二战后澳大利亚多次在西方联合阵线中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已在亚洲各国造成不良影响。1999年又带头组织多国部队进驻东蒂汶,不仅给澳印关系的发展蒙上一层阴影,而且引起东南亚和东亚各国的普遍忧虑。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扩充军备,配合美国的亚洲战略。这不仅打破了这一地区固有的均势,而且给澳融入亚洲设置了人为的障碍。面对一个曾遭受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且对国家主权异常敏感的亚洲,澳大利亚必须谨慎从事。
此外,克服狭隘的种族主义意识、发展多元化是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重要一环,也是澳大利亚能否真正融入亚洲的关键。多元化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各国的现代化实践业已证实:吸收更多的其他国家文化以充实和发展本民族文化是使一个国家走向富强、文明、民主的明智之路。就澳大利亚来说,多元化意味着不仅仅对于土著部落的宽容态度和对非盎格鲁——撒克逊的欧洲人的开放,更具有决定性的是把移民中日益增长的亚洲人真正融入到澳民族共同体之中。有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每年大约有106000人移居澳大利亚。1989—1990年联合王国、爱尔兰和新西兰是移民澳洲最多的国家,但同期来自越南、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中国的移民也在增长。由于人口出生地发生结构上的变化,澳大利亚人口的种族结构在未来30年内将产生显著的变化,表现为亚洲和大洋洲人所占的份额增大。(注:澳大利亚移民调查局:《1990 年澳大利亚人口发展趋势与展望》( Bereau of ImmigrationResearch,Australia's Population Trends and Prospects 1990),澳大利亚政府出版局1990年版,第12页。)为此,澳大利亚设置了专门的移民机构,负责处理移民集团的社会保障和福利问题。但人们在移民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认识方面分歧较大。支持移民并肯定移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人认为,移民补充了本国劳动力不足,有利于人口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移民刺激了对消费品服务的全面需求,有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移民使澳洲不需要付出教育培养费用,就得到了技术能动力;移民增加了税收,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开支,如学校、道路及通讯系统等。反对者认为移民的经济成本大于收益,从而使社会发展不利。理由是:移民的增加使雇主不愿培训当地的劳动力;加剧了移民与当地工人,尤其是无技术的劳动力间的竞争;大量移民在效率低、不景气产业工作,破坏了经济结构调整;移民使得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从而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这种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在这个问题上,澳大利亚政府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应该承认,移民构成了澳洲的历史与社会,也改变了澳洲的历史与社会。移民不论在澳大利亚的战后重建以及当今的现代化建设中,其作用不容置否。移民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带来了100多种语言,语言的多样化有助于澳大利亚文化的繁荣,有助于其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也密切了澳洲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1972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修改了过去的“单一社会”政策,正式推行多元化文化政策。其指导原则是,所有澳大利亚人,不论民族或宗教信仰,不论文化背景或语言传统,都享有平等的权力、义务、责任和机会。这一政策旨在使澳洲成为一个公正宽容、机会均等的社会。实践证明,澳大利亚实行的这一民族融合的政策是正确的,既符合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和长远的民族利益,也能增进澳大利亚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进一步了解。澳大利亚要想作为亚洲事务的建设性的参与者且进一步取信于亚洲国家,必须在移民和教育政策方面有所作为。(注:伽耐特·伊文斯、布鲁斯·格兰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澳大利亚的外交》(Gareth Evans、 Bruce Grant ,Arstralia's Foreign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 328页。)但也应该看到,少数有种族歧视痼疾的人仍抱着“白人优越论”的阴魂不放,这种不谐之音应引起澳大利亚政府的高度重视。
一般而论,经济的动力、开放和多样性导致了一个地区非常强烈的实用主义氛围。对社会发展和富裕的渴望差不多是每个国家前进最紧迫和最重要的力量。经济的抱负构成内政外交的首要因素。一个地区的希望,从安全的意义上看,是在下列的问题上达成共识:经济的发展比建立军事力量重要得多,地区安全的最有力保障是独立国家之间相互合作和相互交往而不是军备竞赛。澳大利亚的利益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澳大利亚应在政治上、经济上、战略上和文化上保持对亚洲的开放格局。澳大利亚应把自己视为这一地区民族国家中的一员,而不是局外人。(注:伽耐特·伊文斯、 布鲁斯·格兰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澳大利亚的外交》(Gareth Evans、Bruce Grant, Ar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 ), 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所以,从问题的实质来看,澳大利亚能否真正地融入亚洲,问题的症结在于澳大利亚人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于亚洲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与亚洲国家文化价值观的矛盾,将会影响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澳大利亚不能孤立于亚洲之外,尽管其文化、语言、社会组织以及宗教信仰都是有别于亚洲,但其外交政策在为民族行利益服务的同时,避免对抗于其他国家。”(注:亨利·马耶尔:《澳大利亚政治》(Henry Mayer,Australian Politics),E·W ·柴郡出版有限公司1966年版,第508—509页。)无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还是澳大利亚迎接未来的挑战来看,融入亚洲,是澳大利亚现实而明智的选择。如果把建立共和制看作是澳大利亚内部的政体选择,那么,融入亚洲,则是对其外部环境的认可。二者都以国家利益为轴心。融入亚洲,既不会修正构筑澳大利亚民族至关重要的价值或原则,也不会因此而失去其国家地位,相反,这种地位将更加巩固。脱欧入亚是澳大利亚民族成熟的标志。
标签:移民欧洲论文; 澳洲移民论文; 澳洲移民政策论文; 移民澳洲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澳大利亚新闻论文; 澳洲政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 移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