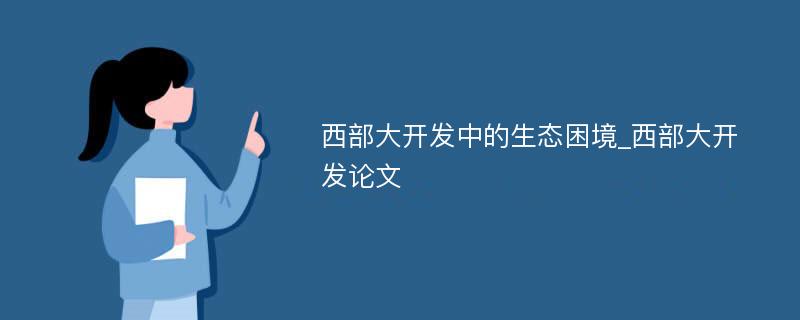
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开发论文,困境论文,生态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Q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1)02-0001-06
1999年9月江泽民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注重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要把它放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同年10月,朱镕基在青海、甘肃、宁夏视察时也强调,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只有大力改善生态环境,西部地区的丰富资源才能得到很好地开发和利用,才能改善投资环境、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则特别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力争用五到十年的时间,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有突破性进展,西部开发有一个良好的开局。西部开发要……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有计划分步骤地抓好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建设工程,改善西部地区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一、生态危机
这次被划入国家西部大开发范围的12个省市自治区的国土面积超过中东部地区面积的总和,而这里正是中国生态环境最为恶劣的地区。西部的生态非常脆弱,而西部生态堪称整个中国人的生存线。西部生态的破坏所导致的会是东部地区的生态灾难,因此这些地区实际上是东部地区的生态屏障。恶劣的生态环境成为影响和制约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远远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和东部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日渐加大。西部地区的生态恶化,威胁到了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因此当西部开发由规划变成轰轰烈烈的行动的时候,它所带给西部生态的是福音,还是另一场别的什么?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的担忧和思考。
国家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柯柄生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西部的生态环境系统十分脆弱,如不高度重视生态与环境建设,以牺牲生态环境作为代价,西部大开发变成了大开荒、大开采、大开矿,对生态环境造成大破坏和大污染,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和不可恢复的。[2]
很多人拿西部大开发与美国当年的西部开发来做比较,以此来证明其重要性和光明的前景,但他们忘了事情的另一半。19世纪30年代,美国西部由于过度垦殖,引起了一场席卷北美的黑色风暴,被刮走的是最肥沃的黑土层。类似的事情其实已经在西部发生了。本世纪50年代初,在青海柴达木盆地陆续发现了盐湖、石油、天然气等丰富的自然资源,于是在“开发柴达木”的口号下,大批人员开进了柴达木。仅仅为了解决这些人做饭、取暖的燃料,就给柴达木带来了一次劫难。据《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志》载,在开发柴达木的过程中,由于采挖植被当燃料,全州3000万亩沙生植被被破坏了2000万亩。在这种破坏之下,大面积的固定半固定沙丘又变成了流动沙丘或戈壁。60年代中期,海西州府由大柴旦迁到德令哈,德令哈很快就由一个小道班变成一座小有规模的城市,为此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附近一座长满了柏树而被称为“柏树山”的山头成了秃头,山上那些千年古树全被砍掉当柴烧了。
或许我们应当先来盘点一下西部的生态到底已经恶化到了什么程度,感受它对我们实实在在的威胁。
水危机 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水,水可以说是西部的经济命脉。由于我国的降水量深受季风的影响,夏季风由东南向西北渗透,影响力逐渐减弱,降水量也逐渐减少。秦岭—淮河线以北大部分地区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下,而西北地区则在400毫米以下。[3]降水量稀少的另一边则是惊人的蒸发量,以甘肃省为例,武威的年降水量是180毫米左右,而蒸发量则超过2000毫米;张掖的年降水量大概为130毫米,蒸发量则接近2100毫米;玉门、安西一带的降水量只有30至60毫米,而常年的风吹日晒却使蒸发量高达3000至3500毫米。近20年来,由青海注入黄河的水量减少了23.2%,而且减少的趋势还在进一步加剧。黄河源头的札陵湖、鄂陵湖之间已经出现断流,青海湖由于湖水减少、湖面萎缩,鸟岛已经变成了一个半岛。与80年代相比,长江支流白龙江流量下降了20%,黄河支流洮河下降了14%,大夏河下降了31%。[4]
水土流失 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据国务院1990年公布的遥感调查结果,全国仅水力和风力两种侵蚀形式的水土流失面积就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而西部则是最为严重的地区,目前的状况是:小片治理、大片加重,上游流失、下游淤积,灾害加重、恶性循环,水土流失面积有增无减。在青海、甘肃的甘南和临夏,宁夏等黄河上游地区,水土流失侵蚀模数为每平方公里5000达1万吨,少数严重地区达到2至3万吨,成为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宁夏西海固地区年平均流失土壤约1亿吨,相当于冲走土层深23厘米的耕地45万亩,流失有机质120万吨,损失全氮9万吨,全磷25万吨。[5]水土流失还毁坏了耕地,使平坦的地表变成沟、梁、峁,现在黄土高原的沟壑已经占到地表面积的三分之二。
森林危机 西部地区本是我国有限的森林资源的主要分布区,而森林由于其涵养水源、调节湿度的功能而被称为“绿色水库”,它还有净化空气、减缓污染、防止水土流失、遏止荒漠化等诸多功能。但这些地区的森林资源却一直在锐减之中。新疆塔里木河两岸1958年航测有胡杨林面积686万亩,现在仅剩下150万亩。宁夏南部山区原来广泛分布着森林,现在已经基本毁坏干净。[6]近代甘南洮河上游、卓尼附近各山口坡地上是茂密的树林,后来几乎被砍伐一光。[7]
草原危机 全国86%以上的草原分布在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长期以来对草原掠夺性的粗放经营破坏了草原的生态平衡,使草原生态系统严重恶化。目前,草原退化面积已经达到13亿亩,并仍以每年2000万亩的速度发展。四川阿坝自治州拥有中国5大牧场之一的川西草原,但这里的草原退化非常严重,保守的退化率估计是40%~60%,但一位草原专家估算则高达80%。据统计,仅青海每年就有上百万亩草地沦为沙漠,而因为严重退化不能再使用的草场,则是这个数字的几倍。90年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绝无仅有的“生态难民营”——内蒙阿拉善盟孪井滩综合农业开发区。这里的数万牧民都是在失去草场之后,沦落为生态难民在此聚集的。
荒漠化危机 西部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则是黄沙的侵蚀。仅西北地区沙漠化面积就达14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5.5%,大于全国耕地面积的总和,荒沙危害着西部262个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据原林业部三北防护林建设局的一次调查,三北地区的荒漠化面积呈扩大趋势,基本上是以治理1亩,荒漠化1.32亩的速度在扩张。据统计,我国70年代前沙漠化面积每年约1580平方公里,进入80年代则达到2100平方公里,90年代的最新统计则为2460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面积沦为沙地,每年的直接经济损失则为540亿元。目前我国仍有5900万亩农田、7400万亩草场、2000公里铁路受到沙漠化的直接威胁,其中90%以上都在西北地区。在新疆、青海和内蒙古阿拉善以西地区,荒漠化扩展速度高达4%。[8]据粗略统计,青海在建设以来荒漠化的土地达到4000万公顷,每年以100万亩的速度扩大。黄河源头中度退化草场有726公顷,重害草场435公顷,经济损失高达5个亿。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向四围扩张,周边的绿洲被迫向山边退缩。
二、人与自然
人类生存的基础是自然环境,环境的承载力极大地制约了人的生存可能和质量。考察生态的恶化和环境的破坏,无论是水资源危机、草原退化、森林消失、水土流失,还是日渐严峻的沙漠化,其危机之源很少“天文”(自然)的因素,更多的是“人文”(人力)的结果。大凡人迹所至,莫不使环境承受一番或大或小的灾难。人在向自然攫取资源和财富的时候,只顾眼前之利,过度放牧、过度垦殖、过度砍伐、过度捕猎,还严重污染了大气和水资源。人类对自己生存环境的破坏,带来的是自己的灾难。
西部环境的恶化,其成因甚为复杂,但不外乎“天灾人祸”,相对而言,还是“人祸”的成分为多。
(一)历史和生态债务
西部生态之恶化和脆弱,是因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生态债务十分严重。新疆自汉朝以来就是中央政府经营和开发之地。塔里木盆地北沿在汉唐时期就已经有很多屯田,如今这些遗址都已在沙化的边缘。盆地南缘和田一带凡有影响的古代文明遗址则早已被沙漠吞没。今日的黄土高原,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有4.8亿亩原始森林,覆盖率达到53%,经过自秦汉以来2000多年的烽火蹂躏和垦耕破坏,到建国前夕已不足0.3亿亩,覆盖率降到3%。历史上河西走廊曾是游牧的地方,但在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下,也相继弃牧从农。唐朝时还只是“番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9]到五代的时候,当时的回鹘、吐蕃等民族“其可汗常居楼”,“以囊驼耕而种。”[10]而明朝之时,“有近山聚族者,相率垦田、告领牛耕,与吾民杂居,并耕而食,照岁例纳粮。”[11]农垦之后,一方面由于地力下降弃耕现象十分严重,同时这些土地失去了植被保护,遇风就沙化,遇水就造成水土流失。
(二)生活的贫困与生态的贫困
居住在西部的人,尤其是农民和牧民,面临着这一个个怪圈:恶劣的环境造成了他们的贫困,而他们摆脱贫困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又进一步恶化了环境。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则认为,“贫困是生态及其他灾难的根源。”西部居民多居于高寒阴湿和干旱之地,生活长期陷于贫困。迫于生存的需要,他们只有最大限度地从环境中获取生活资料。牧场的超载即是一例,而宁南和南疆地区长期的盲目开荒,主要也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宁夏西部山区25度以下的坡地被开垦完毕,25度以上的陡坡地种庄稼的也不少,形成了无地不耕的局面。[12]西部地区滥砍滥伐、滥挖草皮也是出于能源不足这个现实的问题,而青海等地大肆捕获野生动物的行为也主要是为经济利益所驱动。
(三)马尔萨斯的忧虑:人口增长的幽灵
马尔萨斯早就忧心忡忡地告诫人们要合理控制人口的增长,以免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出现人口超载的情况。现在的西部就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样的问题。西部虽然土地广袤,但其单位土地面积人口承载力却很低,而现实这些地区的人口增殖速度过快。据统计,新疆的生育率差不多是江苏的3倍。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平均自然增长率为1.45%,而宁南山区却高达3.4%。除了本地人口的自然增殖之外,外地人口向这些地区的不断涌入也加剧了人口的剧增。自50年代至80年代,新疆人口足足增加了1.84倍,青海则增加了1.56倍。[13]干旱地区的合理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7人,塔里木盆地在80年代有514万人,每平方公里超过8人,90年代更增加到706万,如果以该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测算,到2010年将用完盆地地表径流总量。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合理人口容量为101万人,现在则超载了120万人。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西部地区的人口与1949年相比增加了265倍,人口密度大大超过了半干旱地区临界人口的密度每平方公里20人。如此看来,西部并不是我们常说的那样地广人稀,而是单位面积意义上的人满为患。
三、发展之路
西部不能不发展,环境不能不保护和改善,这个西部大开发的两难问题的解决将是整个开发工程中的关键所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考虑和注意的问题。
(一)观念的价值
西部地区生态的恶化固然与生存的迫力有关,但也与观念有很大关系。很多地方只顾眼前小利,根本置其他地区和后代不顾,这实际上一方面是认识上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道德的问题。西部地区的一些观念其实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对于生态的保护和改善是有益的。我们永远不能保证知道能够使森林不被恶性砍伐,鱼儿不被肆意捕杀。但崇拜多种植物的云南楚雄彝族决不会砍他们的神树,生活在高原的藏族也决不会动河里的鱼;贵州的侗族相信,“江山是主,人是客。”这些都得益于他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这表明现代文明所珍视的生物多样化、环境保护等价值观,与西部的传统和文化并不矛盾,反而能够得到内在的支持。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真正地尊重他们固有的观念,并把它们转化为生态保护和改善的内在支持理念。
(二)科技的投入
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保护和改善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决不能主观随意、一哄而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依靠科学技术。科学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加强宏观调控,根据西部各地区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和方案。技术则是连接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中介和桥梁,是由技术方法、工艺技术、设备、工艺流程等组成的物理、化学、生物等控制手段的总和,其功能在于使系统中的能流、物流、价值流按照一定的目的有序地进行,才能防止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收到综合治理生态环境的效益。具体而言,在干旱地区的植树种草需要先进技术的指导,单位草场的载畜力也需要科学地计算并得到执行,农业的精耕细作和加大技术含量则会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从而减少对土地的无限制垦殖。
(三)林、牧与耕种
农耕对森林和草原的破坏,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因此在不适宜农耕的地方一定不要继续开荒,而对一些已经垦殖的地方也要尽量退耕还林(草)。1999年3月开始的数次沙尘暴席卷整个北方,滚滚黄沙终于引起了人们对西部生态的广泛注意,也真切地感受到了生态恶化这个心腹大患。同年8月,国务院紧急发出《关于保护森林资源,制止毁林开荒和乱占林地的通知》,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毁林开垦行为,大力植树造林。9月,朱镕基考察长江上游5省时再次重申:从现在起,长江、黄河中上游要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植树造林,恢复生态植被,减少水土流失,防止地质灾害。而早在1985年,国家就已经颁布了《草原法》,其中第十条规定:严格保护草原植被,禁止开垦和破坏,草原使用者进行少量开垦,必须经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已经开垦造成草原沙化或严重水土流失的,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限期封闭,责令退耕还牧。
(四)人口问题
人类为了更好地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繁衍后代,就需要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就会扩大对生态环境的资源索取。一些地区已经形成了“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因此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减轻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是西部地区缓解人地矛盾,防治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不可能缺少的措施之一。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还应当注意提高人口的质量。通过教育和其他手段,使少量的人就可以生产出大量的生活产品和资料,以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再生产的需要,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人口增长的问题。
(五)政策与投入
关于生态问题,在政府与个人、计划与市场之间,需要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草原退化的原因之一就是产权不明,大家共用草场,谁也不会去考虑承载力的问题,想养多少就养多少。而一旦把使用权交给个人,他们就会考虑养多少的问题,而且还会千方百计保护和改善草场的质量。这在事实上会对草场的保护建设起到促进的作用。目前在青海,草地保护得最好的地方正是最早实行草场承包责任制的海北自治州。因此已经有人指出,多年绿化、植树事倍功半的原因之一,恰恰就是土地、草地、森林和树木的产权不明,市场手段没有发挥作用,个人和社会的积极性和责任感都调动不起来。有关部门已经在考虑出台政策,在落实它们的使用权、经营权的基础上,进一步使它们的交易、流转合法化。西部开发的一揽子政策中特别针对生态保护做了规定:“对西部地区荒山、荒地造林种草及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实行谁退耕、谁造林种草,谁经营、谁拥有土地使用权和林草所有权的政策。各种经济和个人可以依法申请使用国有荒山荒地,进行恢复林草植被等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可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减免出让金,实行土地使用权50年不变,期满后可申请续期。可以继承和有偿转让。”
西部地区地域广阔,光靠市场的“教鞭”要想达到既有经济发展,又有生态改善的目的是不够的。事实上,西部开发中,政府的任务十分艰巨,既要有政策的保证,也要有实际的投入和扶持。近年来,青海海西自治州为改变柴达木盆地的生态环境,迎接西部大开发,积极投入信贷资金1265万元,全力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大力开展治山治水、封山封沙、育林育草和植树造林活动,到1999年底,防沙治沙工作初见成效,小流域综合治理成绩明显,林业生态体系建设步伐加快,天然林草植被得到保护,对柴达木盆地的生态平衡,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产生积极的影响。
从整个国家来说,对于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项目不仅要有优惠的投资政策和税收政策予以鼓励,还应当对西部地区实施补偿政策。目前国家已经对退耕还林实行了补贴政策,一亩50元树苗钱、300斤粮食,应该说投入已经很大了,但对于一些特殊地区还只是杯水车薪而已。今年的财政预算还将安排120亿元用于天然林保护工程和生态环境建设,也包括防沙治沙,未来10年国家对此投资将达到1000亿元。从历史来看,西部以自己的贫穷支持了全国的发展,东部欠了西部的资源帐;西部当年为了东部的发展而砍伐、采矿、破坏了环境,今天的保护和改善也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处于下游的东部地区免遭旱、涝之类的灭顶之灾。目前,国家的财政补贴大量投入,用于上游退耕还林、植树造林,受益的不仅是西部,还有下游的东部地区,因此可以考虑在东部受益省份征收资源补偿税。
总之,西部开发是关系国家全局发展的大事,开发过程中的生态问题将一直是影响开发的重要因素,也是衡量开发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只要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政府与市场配合,个人与社会配合,我们就能不做破坏秀美山川的历史罪人,而重建我们美丽的家园,将美好的栖息之地留给后代。正如江泽民在西北生态环境建设的批示中所说:“历史遗留下来的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要靠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齐心协力地大抓植树造林,绿化荒漠,生态面貌会得到根本改观。经过一代又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再造秀美山川。”
[收稿日期]2001-01-05
标签:西部大开发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生态破坏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环境保护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 西部建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