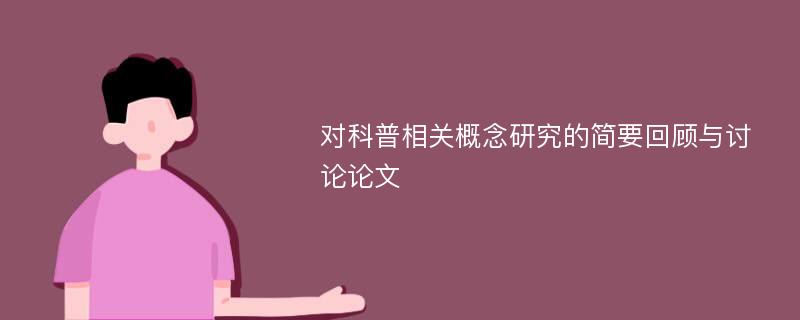
对科普相关概念研究的简要回顾与讨论
刘 兵 *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摘 要] 对近年来有关科普的相关概念(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及相关的模型和立场的一些重要研究,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和评论,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科普 公众理解科学 科学传播
就科普来说,在最基本的分类中,可以分为两类工作,一类是科普实践工作,一类是科普理论研究。多年来,国内的科普实践工作有了众多重要的经验积累。虽然与具体的科普实践相比,对于科普的理论研究还相对薄弱,虽然总体上,国内科普界还是在一定程度存在着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但近十多年来,科普理论研究也还是有了一定的发展。应该说,没有扎实的理论研究作为背景和支撑,科普的实践会变得盲目且受到诸多制约。
在这些科普理论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科普概念本身的界定,以及对于相关概念背后所承载的科学观与传播观的思考与探索。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国的科普实践是在没有更深入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的,或者说,是在对科普的一种比较朴素的理解的基础上开始的,许多相关的基本概念并不十分明确,而且是比较缺少反思的。因而,当我们要回顾我国科普的发展,回顾对科普理论研究的成果时,对于这些最基本的基础性问题的研究成果,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1 对三个基本概念及相关问题的若干重要研究
1.1 科普
虽然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讲“科普”,并使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相关的科普工作,有时也对此概念进行一些分析,但直到2000年以后,真正有历史眼光而且比较具有学理性性的考察和总结才出现。2004年初,科学史家樊洪业在《科学时报》名为“故纸拂尘录”的专栏中,发表了三篇系列的专栏文章《解读“传统科普”》《从“交通智识”到“普及”》和《科普:面向公众的科学通俗化》[1-3],对“科普”这一核心概念的来源、演变和内涵等做了清晰的考证和解说。
在这三篇文章中,樊洪业先生指出,从历史上看,“科普”作为中文的专有名词,在1949年以前并没有出现过。从渊源上讲,是自1950年起,它作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简称而出现① 1950年,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简称“全国科普”或“科普”。 。大约从1956年前后开始,“科普”作为科学普及的缩略语,逐渐从口头词语变为非规范的文字语词,并在1979年被收入《现代汉语词典》中,终于成为规范化的专有名词。从这样的考证来看,在中国规范的科普概念出现得并不是很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后来出现的概念所包括的部分所指在此概念出现之前不存在。
除了对科普这个作为规范化专有名词的出现进行了历史的追溯,樊洪业先生还指出了对共和国历史上那一段特殊时期的还原解读,这就是所谓的“传统科普”,它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科普。传统科普的特点被樊洪业先生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科普理念,是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衍生出来的;第二,科普对象,定位于工农兵;第三,科普方针,须紧密结合生产实际需要;第四,科普体制,中国集权制之下的一元化组织结构。
根据一项调查性研究的结果可知:伊朗所需要的化肥总量约为450万吨,仅占全世界化肥使用量的0.7%。这是一个非常低的占比,还不足1%。即便使用量如此之少,伊朗国内还是无法满足自身的用肥需求。在磷肥和钾肥方面,基本依赖进口。而有机肥大部分来自国内生产企业,腐殖酸和腐殖酸钾含量比较高的肥料一般需要进口。由于当地的土壤结构比较差,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非常低,所以对于有机肥料的需求量非常高。此外,伊朗还需要一些抗盐分的肥料。
正如樊洪业先生所说,如何理解或定义今日的“科普”,应该是今日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在他的文章发表之前和之后,也确实一直有人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重新定义“科普”概念并进行相关的研究。但也正像樊洪业所指出的,中国今日的科普,既是从中国昨日的科普走出来的,也是通过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普”理论与实践中吸取营养而变异的。如果离开了科普概念在中国最初产生的背景和含义,显然就无法真正深刻地理解科普概念在中国后来的变异。而且可以说,在后来有所变化的科普概念中,最原初的一些含义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作为核心内容保留了下来的。当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将“四科”(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纳入科普的范畴,是科普观念发展中另一个重要的进展。
1.2 公众理解科学
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的、与“科普”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但又对中国的科普理论和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泊来品概念,“公众理解科学(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的正式规范性提出,是源于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很快地,“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就被引入了中国。根据李大光的说法,“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进入中国大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科普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译介了一批国外著名学者关于科学素养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文章。其中,包括鲍默爵士的报告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公众舆论研究中心乔恩·米勒的 ‘1990年美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与态度’报告。同时,还译介进欧洲,尤其是英国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这些作品的译介使得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传播的新理念和研究方法有了了解,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学者的争论。其后,随着中国科普研究和实践的发展,公众理解科学的理念逐步在中国科学文化界得到认可,也导致了科普模式的逐步演化。”[4]
在前面对有关研究的极其简要(因而也略去了更多细节说明)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一个结论,即在近些年来对科普基本概念的理论研究中,用吴国盛的说法,“以北大科学传播中心为标志,实际上形成了中国科学传播的批判学派”[14]。而作为这个学派最突出而且影响最大的成果,便是前面所说的对于科普发展三阶段、三种模型和三种对应立场的划分。我们可以注意到,随着科普事业的发展和相关研究的深入,许多高校中有关专业以科普相关论题作为学位论文的数量增长很快,而在这些学位论文的文献综述中,对这种三个阶段、三种模型和三种立场的引述是非常普遍的。根据中国知网数据,《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一文的下载量高达3 000多次,被引数达189次,这也是其巨大影响的一种表征。在我们回顾近年来中国科普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影响时,显然不能忽视这样的研究成果及其影响力。
4.3 阴茎阴囊角的成形 阴茎阴囊角成形的目的是构建阴茎根部柱状外观,使其成直角外观,同时在阴茎根部腹侧的固定可以有效的防止阴茎体回缩[7]。
1.3 科学传播
但与此同时,也正因为此研究结论的巨大影响力,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还可以做一些分析和讨论。
在此前后又有诸多学者,包括来自传播学界、科普界和科技哲学与科学史界(或称“科学文化”界)的学者对科学传播概念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被称为“北大学派”的吴国盛、刘华杰和田松等人。
与之相应地,在研究者中,对于最后这种概念中蕴含的传播方式的理解,也受到后期国外公众理解科学研究和基于STS的科学传播研究发展的影响,对于传统科普中那种单向的、从专家到公众灌输式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的强调,也变成了像基于对话模型等所倡导的那种平等的、互动的双向传播方式的注重。
从散落在柳江两岸的古人类遗址,到柳江河畔确定了柳州两千多年建城史的九头山汉墓,从龙潭公园的摩崖石刻,到柳江北岸上为纪念柳宗元而建的柳侯公园。
据田松的总结,早在2000 年,刘华杰和吴国盛就先后发表文章,提出了科学传播这个概念,并指出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是科普 (或科学传播) 的三个不同阶段,并对科普进行了反思和批评,提出了一种新的更具包容力的科普理念,并将这种新的科普理念命名为科学传播,“称现代科普为‘科学传播’更合适,科学传播是比公众理解科学和传统科普更广泛的一个概念,前者包含后者”, “我们提出‘科学传播’的概念,是把它看成科学普及的一个新的形态,是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一个扩展和延续。”[10-11]
2 评论与讨论
到2000年以后,国内对于公众理解科学的深入研究陆续出现,包括对公众理解科学在西方国家的学科化、概念、目标和工作模型的变化的关注。尤其是,对于其从最初的“缺失模型”到后来像“内省模型”、“对话模型”等的研究[5-6],在后来人们对“科普”的讨论和理解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只是,在此名目下,更多的工作是伴随着对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而开展。不过,随着公众理解科学概念的引入,人们也开始注意到国外这一研究领域,或者说学科或运动的产生背景及其与中国科普在动因上的差异。正如英国科学史家皮克斯通(J. V. Pickstone)所言:“当科学在全球范围内已经与商业紧密联系时,部分公众就变得更加怀疑。从前他们担心科学因为某种内在的动力学——某种不计后果地追求控制自然的能力——而正在危及他们;今天他们担心科学家与大企业共谋——为追逐利润而搞坏世界。”[7]也正是由于20世纪在西方国家公众中存在的对科学的怀疑态度,科学家共同体担心因此导致科研经费和资源的缩减,所以开始了这场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目标是让公众更多地理解科学从而转向支持科学。虽然后来的研究对最初的目标、方法和模型设定中存在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导致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在立场和观念上的变化,但就其起源而言,显然是与中国的科普完全不同的,尽管其早期在像缺失模型中所体现出来的传播立场和传播方式,又与中国传统的科普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
其实,科学传播概念的出现是比较早的事情。从现有资料来看 , 贝尔纳是最早注意到科学传播的科学社会学家之一。在他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中 , 第十一章就专门讨论了科学传播的问题(原文是用scientific communication,中译本原来翻译为科学交流) ,其中也涉及到面向公众的科学交流的问题。国内学界中,翟杰全是比较早开始重视这一概念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发表了论文专门讨论科学传播学[8],并把考察科学知识是如何通过传播媒介向社会渗透并作用于受传对象的问题作为重要内容。后来,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他又明确地将科学普及与科学传播(有时他又用的是“科技传播”,甚至认为使用“科技传播”更好)的概念关联在一起,认为“科技传播涉及三方面的问题:科学家间的交流问题、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这三个方面组成一个科技传播系统;科学之间的交流涉及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问题,而科学普及关心的是让公众有机会理解科学所起的作用,了解对人类生活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认为不能简单将公众理解科学视为科普发展的第二阶段,“科学知识的传播如果是发生在专家与公众之间,知识流动方向必定是自上而下、专业对非专业、‘有知’对‘无知’的一种单向传播, 不可能是一种双向的交流过程。”[9]当然,这只是学者们关注科学传播初期阶段的观点,在后来,学者们的观点又有一些新的变化。在初期阶段人们对科学传播方式的这种认识,也是学术研究发展中特殊阶段的可理解的阶段性特点,在后来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于专家与公众互动式的传播的价值又有了更多的论述。
在后续的研究中,这几位学者由此出发,陆续进行了一系列更加深入系统的论述。例如,2004年,刘华杰明确提出:广义的科普经历了从传统科普到公众理解科学(PUS)再到科学传播的转变 , 它们构成了一个时间发展序列[12]。2009年,他在另一篇影响更大的题为《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的文章中,更是将这三个阶段与相对应的三种模型和三种立场对应起来: “从传统科普,到公众理解科学,再到有反思的科学传播,是广义的科普 (科学传播) 经历的三个阶段。与之对应有三种模型:中心广播模型、欠缺模型和对话模型。这三种模型也反映了三种不同的立场。”[13]而这三种立场,分别为国家(或政党)立场、科学共同体立场和公民立场。
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这三阶段发展的时间序列问题。这种发展阶段的划分初看上去,与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分期”颇有些相似,但这也正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正如刘华杰在其文章中也指出,这“三种模型并不必然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但在各国实践中它们也的确展示了时间上的演化关系”[13]。实际上,在这种划分中的三种模式,在当下中国对科普的理解和科普实践中,应该说是并存的,而且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传统科普”所占的比例还相当高,尽管代表着新理念的“科学传播”(或“有反思的科学传播”)的份额确实也在增长中。就像吴国盛所说的,“当代中国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式仍然处在剧烈的互动和融合之中”[14]。
其次,也是笔者更想讨论的,是关于代表新观念的“科学传播”的命名问题。由于学术观念的变化,用一个新的名词来命名某种新的东西,或某种与过去已有命名的东西有某种关联但又有所区别,以陌生化的方式来刻意强调其理解上的变化,这本是学术界常见的现象。例如,从传统的ST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到新的 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在名称上的变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田松也注意到:“从叙事策略上看,我们既可以使用一个新词取代旧词,也可以改造旧词,赋之以新的含义。这两种策略各有利弊,各有难易。现在看来,提出科学传播这一新的概念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此后,整个科学文化领域的思考逐渐深入,从理念上、实证上进行了更多的工作。科学传播这个概念逐渐在这个领域之内得到接受。但是,这个词在实际使用中一直是作为与传统科普不同的,与‘现代科普’相当的一个概念。”[15]
是否真的如此呢?
服务社区成员是时代赋予高校的光荣使命,是高校创新办学模式的有效途径,是高校改善办学条件和办学环境的重要前提。社区学院应把为社区成员的个人发展服务放在首位,通过社区成员个人发展服务进而为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服务。各高校应高度重视社区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支持社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使社区教育成为学校服务经济转型、服务社会发展、服务公益事业的重要窗口。
一方面,传播,其实本是一个被普遍使用而且含义甚多的名词。传播学中,各类传播(诸如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等)都可以是研究的对象。当涉及到科学传播时,本来也可以作为一般性的与科学有关的传播的所指。正如国际上著名的刊物Science Communication在其对涉及主题的描述中,就包括了研究共同体内的传播、面向公众的科学技术信息传播和科学技术传播政策[9]。因而,用这样一个原来已有诸多含义的一般化的名词来指称一个新的范式,其通过陌生化来提示新理念的功能是不够理想的。在类比中,这与在两种STS的表述中,用Studies替代原有的Society的效果就很不一样了。另一方面,随着科普的发展,原来只为学术界一部分学者倡导的“科学传播”这个名称也越来越为官方所接受,并且在越来越多的场合中,其所指的对象实际上也经常是那种“传统科普”。因而,在使用“科学传播”这一概念时,经常会是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所指,也是容易引起混淆的。
文献管理和使用能力 在文献收集过程中,文献体量较大,内容丰富复杂,学生的文献管理能力需要提高。为此,介绍和要求学生选用NoteExpress、EndNote等参考文献管理工具,借助文献管理工具具有的主题分类和随时笔记的便捷性和优势性,提高学生文献管理能力。另外,学生在写作毕业论文过程中需要经常引用文献,并随时可能对文献顺序进行调整。为此,指导学生科学使用文献管理工具,能够边写作边引用,以及运用行文中参考文献的自动排序功能,从而提高文献使用能力以及引用文献的规范性,促进写作效率的提高。
国际创伤愈合学会将慢性难愈合创面定义为:无法通过正常有序而及时的修复过程达到解剖和功能上的完整状态,以二期愈合的伤口最为常见。临床上多指各种原因形成的创面,经1个月以上治疗未能愈合,也无愈合倾向者。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超过1/3的慢性难愈合创面患者是因糖尿病造成的,已经代替创伤成为造成慢性难愈合创面的首要原因[1]。
但也正由于前述研究工作的巨大影响,要重新选择另外的概念来取代那种代表着科普新理念的“科学传播”,似乎一时也很难做到。所以,也许现在需要做的,只能是提醒人们在不同的语境下注意“科学传播”这一名称的各种不同含义了。
参考文献
[1] 樊洪业. 解读“传统科普”[N]. 科学时报,2004-01-09.
[2]樊洪业.从“交通智识”到“普及” [N]. 科学时报,2004-01-16.
[3]樊洪业.科普:面向公众的科学通俗化[N]. 科学时报,2004-01-30.
[4] 李大光.“公众理解科学”进入中国15 年回顾与思考[J],科普研究,2006(1): 24-32.
[5] 李正伟,刘兵. 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研究:约翰·杜兰特的缺失模型[J].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3(3):12-15.
[6]刘兵,李正伟. 布赖恩·温的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研究:内省模型[J]. 科学学研究,2003(6):581-585.
[7] 皮克斯通. 认识方式:一种新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史[M]. 陈朝勇,译.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187.
[8] 翟杰全. 科学传播学[J]. 科学学研究,1986(3):9-16.
[9] 翟杰全. 再论科学传播[C]//焦洪波. 科技传播与社会发展——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第七次学术年会暨第五届全国科技传播研讨会论文集. 2002:24-34.
[10] 刘华杰. 大科学时代的科普理念[N]. 光明日报,2000-05-08. 转引自:田松. 科学传播——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2):81-90.
[11]吴国盛. 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N]. 科技日报,2000-09-22. 转引自:田松. 科学传播——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2):81-90.
[12] 刘华杰. 论科普的立场与科学传播的信条[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8):76-80.
[13] 刘华杰. 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J]. 科普研究,2009(2):10-18.
[14] 吴国盛. 当代中国的科学传播[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2):1-6.
[15] 田松. 科学传播——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2):81-90.
[中图分类号] N4
[文献标识码] A
[ DOI ] 10.19293/j.cnki.1673-8357.2019.05.005
收稿日期: 2019-08-31
*通信作者: liubing@tsinghua.edu.cn。
(编辑 张英姿)
标签:科普论文; 公众理解科学论文; 科学传播论文;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论文; 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