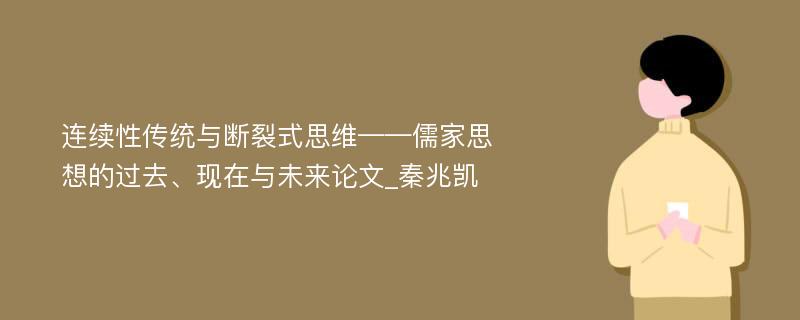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8)
摘要:传统儒家思想将人置于种种关系之中,关注人与各层关系的连续性,即个人与家庭的连续性、个人与集体的连续性、个人与天的连续性。依据这种连续性传统,儒家构建起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和以纲常为核心的国家。经过千百年的发展,这种连续性传统已贯穿于中华文化之中。近代以来,封建专制主义逐渐瓦解,儒学式微。新儒学思想家都试图以西方民主思想,内圣开新外王,以达到复兴儒学的目的。儒学的复兴必须建立在这种连续性传统之上,达到与西方“断裂式”的民主自由思想的融合。
关键词:连续性传统、断裂式思维、儒学
一、儒学的连续性传统
(一)家、国、天下关系的连续性
在政治层面,儒学把个人修养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相结合,认为“物有本末,事有始终”,构成了家、国、天下关系的连续性和递进性。
家。家族氏族结构是儒家政治秩序的基础。在中国,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来自于对家庭伦理本身的忠诚。在政治秩序的物理层面上,家是与人民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政治传播的连接点。政治生活的表现和国家对政治的运作大多是由家庭来承担。“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国与家是相通的,家庭法和国家法、生活秩序和国家秩序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使国家权力结构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国。国是家的放大,因而称之为国家。孝悌是家庭伦理的基本内容,推及到国家伦理层面便成为“君子为政之道”的根本。个人生命是有限的,家族也不能保证长久不衰,但由诸多个体组成的国家社会却能持久存在发展。将自我的生命荣辱与民族国家的兴衰相贯通,个人也能够真正获得安身立命的归所。
天下。儒家观念中的天下既不是指某一特定的国家,也不是泛指整个世界,“天下,谓天子之所主;国,谓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之家。”儒家突破了传统的天下乃天子一人之天下的观念,不仅仅是对君主个人的“忠”,更提倡“天下为公”,“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因而,士人可以摆脱对国家权势的依附关系,其根据在于士所代表的是超与国家的天下观念。“圣之任者,……自任以天下为重。”士人所追求的也不仅仅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而是对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由此,儒家将人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考察,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彰显个人价值。由此,由个人及家庭,进而建功立业,最后达到心忧天下。内在的自我修养、社会和世界的不断扩大,也决定了儒家所提倡的修身养性的延续性和递进性,即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
(二)天与人的合一性
儒家认为天道存于人的道德意识之中,且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他们崇尚以人为本,相信人的道德、智慧和力量,通过人性来展示天性,从而构成天人合一。
在先秦时期,人们常把“天”视为至上神,因而“天人合一”本身便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一方面“天”具有自我意志,能够奖惩善恶,“天命有德”、“天讨有罪”;另一方面,人必须以德配天,否则就会受到上天的责罚,招致灾祸,“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周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弗夭违,后天而奉天时。”以天意统摄人的道德,人通过自身的修养来彰显潜在的、先天的道德品行,从而把握天命。
到了西汉,董仲舒在糅合吸收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以天人感应思想来确立君王的权威,给君王以警醒,要求其修德配天。其一,人是来源于天,天是万物的始祖,万物皆由天所生。正所谓“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其二,天人感应,天能影响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遣告之;遣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警骇之,警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其三,君权神授,君主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皇帝代表天在人间行使管理万民的权力,“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天人合德”思想,从而达到天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统一。
这种“天人合一”的统一性将天与人统一起来,将王朝命运于天道理运统一起来,形成个人修养与天命的统一,因此“天人合一”也超脱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心本体与天道的统一。
(三)身与心的统一性
人作为有情有欲的个体,又有着向善的价值追求。在儒家思想中,个体的肉身性与德性之间没有根本的对立,身心的对立与互动是内在统一的,同时也是一致的。
孟子将身心之分归于大体和小体,用以区分个人欲望与德性,“体有贵贱,有大小,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大体与小体本身是身与其他感官的关系问题,孟子主张心主乎内,他的践行便是身与心的一起参与,“心虽能统耳目,而各有所司,心不能代耳司听,代目司视,犹耳目能听能视而不能思,须受制于心之思,心不能司听司视,而非心之思,则视听不能不蔽于物。”
从人的完善角度看,身心都是不可缺少的,它需要从身心两方面来努力。儒家德性传统强调欲望的约束和引导。荀子强调“制礼仪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不屈于欲。”在儒家的身心观中,虽然身心不在同一个价值观上,但他们用心支配身体,用道德理性引领感性欲望,但这并不妨碍对身心一体的理解。身心合一,道德理性对自然欲望的控制和引导,使儒家的德性必须在生活世界的具体活动中进行。
(四)个人发展的递进性
儒家伦理在最深层次上的相通性,形成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身、心、家、国、性、天等一体相通。在现实上安身立命的处事之道上,儒家思想也依据连续性传统制定了一整套层层递进的个人发展路径。
儒家信仰安身立命之道,谓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个体的自我内心出发,培养独立的道德自我和笃定的个人信念,不因功名利禄等外在条件所改变,形成个人品格的完善和升华。肖群忠教授评价“安身立命之道是儒家的退守之道,而治平之道是儒家的进取之道。”在个人发展过程中,治国平天下是最高理想,但其实现过程也必须从个人修身开始。“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儒家道德修养是从内在自我扩展放大至家庭、社会和宇宙的过程。同时,它也是一个从外部宇宙、社会和家庭中凝结和还原自我的过程。儒家的身心、内外、天人、真与应、理想与现实息息相关。儒学个体发展的路径是内在的超越和外在的超越的相结合。这种超越是“连续性的超越”,讲求内外相连、身心贯通。
二、连续性传统构建下的传统社会
在连续性传统的构建下,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规范体系,在个人层面,则是“义”;在家庭层面,则是“孝”;在国家层面,则是“忠”。通过礼法规范社会秩序,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君权至上和大一统的局面。
(一)礼法构建的社会秩序
以礼治国,注重德教,这是儒家治国方略的基本思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儒家虽然主张“尚德不尚刑”,但并不否认刑法的政治惩戒作用。“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行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虽然如此,但在政治实践中不能把刑法作为根本手段而盲目运用,走上任刑的道路,道德教化应是政治的基础和治国的根本。“王霸道杂之”和“礼法合一”的特点,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显著特征。
礼不但具有广泛的内涵,而且也是立法的根本,因此中国古代的法律具有很强的道德伦理特征。“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儒学以其政治伦理价值重建了法律,完成了儒家伦理的制度化、法制化,形成了完整的中国古代律法体系。儒家这种将政治理念法律化的行为,使朝廷官员肩负着管理和教化百姓的双重责任,进一步使儒家思想通过官吏的工作深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中国法律一直秉承家族主义、等级制度和特殊主义的概念,以及基于习俗的“非诉讼”追求,体现了儒家的社会控制思想。由此,儒家将礼通过法律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构建起礼法支撑的社会秩序。
(二)君权至上和大一统的国家观
儒家信仰“天命观”,君主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皇帝代表天在人间行使管理万民的权力。在“天人感应”体系中,天具有最高的权威,通过天之权威,来“以天论政”,为君主的权力正当性寻找依据。君权受命于天,天的权威无限,君主的权力也是无限的。以天的权威的无限性,为君主管理万民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君主居于统治的中心,掌握最高的权力,天下万民都要服从君主的管理和统治。同时,天的意志所关注的核心利益是民的利益,获得受命的关键在于以民的利益为本。“而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
在连续性传统的构建下,中国古代形成了大一统思想。孔子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维护天子的权威,维护统一的局面。荀子则称“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推崇统一,倡导一元。董仲舒则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大一统的思想,一而不二,合而不分。“王者,介于天人之间,人统一于天,必先统一于王。”君顺从于上天,民服从君主,天下统一于天。同时,又将一切统一于天具体化为“天道三纲”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由此,构建起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思想基础,政治一统,军权专制。
(三)家族制度
政权和财富通过血缘家族联系起来,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连续性传统具体到家族,成为以血缘为纽带,以孝和服从为基本准则的家族制度。
家族制度和家族伦理的构建是儒家秩序观和伦理观的起点,以家构建起国家,“其为人也孝悌,而为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在中国,专制官僚政治一直需要宗法社会组织,以宗法制度为其政治组织的补充。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儒家思想通过家族制度与所倡导的家庭伦理观念深入到农村社会,特别是宋明以后,科举制度与家庭制度相结合,促进了儒家价值观的确立。在权力垄断时代,家族权力与势力的建立必须依靠行政权威。这种权威的确立也只能依靠科举。由此,构建其家族与国家的联系。对家要孝,对国要忠,这一价值观念也成为人身安全的基本标准。
三、儒家的现代命运
近代以来,随着专制皇权的衰落解体,传统儒家挂靠的政治经济制度消失,儒家思想也受到广泛的批判。自由主义者认为儒家传统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中国传统文化显然包含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因素,其专制性与等级特权思想与民主人权思想格格不入。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应彻底摒弃传统文化。
(一)儒家不再作为合法性的依据
1911年清帝逊位,从清帝国过渡到中华民国,这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代更替,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观念,而是封建专制和等级性的政治原则被西方民主政治原则取代。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以人民主权原则取代君权至上的原则。这种政治观念的根本性变化,使人们放弃了儒学与权力制度的联系,儒家教育身份的科举制度也被彻底废除,具有儒家背景的绅士对现实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小。
同时,政府合法性依据不再是体现儒家精神的传统政治资源,新政权不再把儒学视为天道和真谛的化身,也不再把君权神其视为其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是主张西方的人民主权原则进行统治。在新的政治体制下,政府的职责是消除专制制度的毒害,决定共和和民主,实现革命目标。儒学在被解构和批判之后,统治的合法性从权威性、神秘主义转向理性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秩序的全面转型,使儒家价值观难以找到现实的支点,失去了对社会的规范性作用。
(二)礼法分离:新法律对儒家秩序观念的颠覆
儒家历来主张以礼为治国之本,礼的基本原则是通过强调人的自然等级关系,以人的等级为基础,实现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惩罚性刑法只是对伦理的补充,只有在礼所不及之处,才体现刑法的作用。西方的法律观念则是建立在个人而非家族基础上的,它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和自由。就制度设计而言,司法独立不受任何政治权力的支配,两种法律存在根本性差别。
新法律的建立瓦解了制度化儒学的惩戒机制,儒家从而彻底丧失了规范社会行为的作用。在礼法分离的过程中,固定的、定型的法律条文取代了斟情酌理的法律变例,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被现代法理学所取代。“如果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所进行的改革一般只具有‘器’或‘用’的意义的话,那么法律的改革意味着中国开始在‘道’或‘体’的根本问题上动摇了。”自此,儒家价值观不再是法律的基础,儒家秩序失去了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
(三)儒家观念性存在的批判
儒学在过去百年中受到严厉批判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被权力和理想化所扭曲。其原因在于价值原则和生活方式本身与现代生活的伦理价值背道而驰。儒学在对传统法律制度的制度支持缺失之后,其概念存在也面临着历史上最猛烈的攻击。
辛亥革命之后,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在转型过程中处于无序状态。部分旧军阀组成的新政权和文化保守主义对儒家的滥用,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保守、落后的,激进知识分子将对落后与保守势力的攻击转为对儒学思想的批判。激进知识分子并未清楚地看到儒学的内在价值,认为建立的新社会,必须与儒家彻底决裂,对儒家学说进行彻底的批判。陈独秀批判说儒家礼教“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其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李大钊也认为“宪法与孔子发生关系,为最背于其性质之事实……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法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也,非我辈生人之宪法;荒岭古墓中之宪法,非光天化日之宪法也;护持偶像权威之宪法,非保障生民利益之宪法也。”
虽然新儒家学者一直力图“内生开新外王”,在儒家传统中寻求民主政治思想,如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说、徐复观先生的“转仁成智”说等等,均主张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民主政治),认为西方自由主义需要儒家理想主义的道德基础。“中国要解开传统的死结,适应现代的新形势,就必须由民本转变为民主”。在刘述先看来,不同的现代人权、自由和合法的宪政,不深入政治和法律领域去探索和发展它,现代新儒学终将难以成为一个大气候。在与自由主义的辩论中,新儒家内部也始终不能达成一致,也始终不能复兴儒学。
四、断裂式的西方思维
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连续性思维方式,西方思维将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国家、国家与社会相互割裂,并将这种断裂式思维方式应用于政治法律的构建,形成了在国家层面上建立市民社会、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上坚持社会契约论、在法律构建上信奉个人主义,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法律传统。
(一)个人本位的法律传统
“个人本位”的哲学基础首先是正义。古希腊人把自己称为“自由人”,它保证了自由和自由,并培育了法治。“个人本位”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个人主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的斯多葛的自然法和自然平等思想。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分为普遍理性,使个人和个人都是平等的,世界上所有的公民,他们都有权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个人本位”的哲学基础也是本体论的。本体论的个人本位把社会看成是一个联盟,而不是一个共同体,也就是说,社会是许多个人的机械联盟,而不是许多个人的有机结合。联合的目的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因此,除了每个人自己的利益以外,社会没有自身独特的利益。
由此,法律是互不侵害对方权利的保证。强调个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人身权利是最高的,法律不侵犯个人权利。
(二)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与国家的真正分离和对立乃是近代历史的产物,它使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的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与互动发展,为法治的运行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导致法律至上;多元社会权利提供了分享和平衡国家权力的权利保障;公民社会利益多元化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出了理性规则秩序;以自由理性为核心的公民意识构成法治的非制度化因素。
通过推进公民社会和国家两元进程,实现权力、义务和权利的有效分配;通过促进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多元的社会权利基础和公共权力的权威性,实现了多元权力的共享、平衡和制约,促进了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的发展。为了促进法治秩序的建立,公民社会的理性规则秩序是相互回应、相互契合的。市民社会的建立和完善使得公民在国家之外能有独立生活、行使权利的领域,分割了国家的绝对性权力。
(三)个人与国家的社会契约论
不同于传统中国个人忠于国家的忠君观念,西方社会坚持个人与国家关系中的社会契约论,即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人们为了保卫自身的权利不受侵犯而组成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建立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以否认个体存在的价值为前提,而是个人意志之间的“一致”。没有人的自由,就没有社会契约,没有国家。
因而,国家不再是享有最高的权威,仅是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为目的,确立了人民主权。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仅仅是权利的让渡,且不是全部权利的转移,只是为了保护自身不受侵犯的那部分权利,人民有权建立或推翻政府。这也与中国的“君权神授”,君主受命于天的思想存在根本区别。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政府存在不是目的,而是工具。如果政府的存在不能继续为人民的自然权利服务,人民有权取消原有订立的契约。
五、连续性传统与断裂式思维的融合
在理解个人、家庭、社群和天下时,断裂式的理解和连续性的理解同等重要。断裂是个人权利和社群民主的正确基础。连续性是天下和谐与家庭和睦的基础。事实上,人的真正发展和完善既需要断裂性的思维,保护自我个性的独立发展,也需要连续性的思维,将自我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进步相联系。在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的过程中,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固然成为社会政治法律的根本,但并不能因此抛弃传统儒家思想而彻底西化。
首先,通过儒家思想,可以进行社会规范,建设共同体。这就是说,我们应该用礼乐制度来规范自我行为,对个人欲望进行调节和节制,从而消除后现代主义的分裂和无序。家庭、社群、国家,在其中的人必须受到监管,这种规范不仅需要法,还需要礼。在家庭中,礼仪要求家庭和顺,所以要求父慈子孝;具体到国家,礼要求整个国家稳定和繁荣,所以它必须是民主的,而不是专制的。礼要求尽可能减少暴力,并通过逐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确保社群与国家利益的实现。
其次,儒家思想可以通过世界上最大的社群概念为所有文明提供资源,从而全世界的和平。因为儒学最终通过递归的层次达到了天下的观念,而天下的概念是建立在普世性和特殊性的基础上的。因此,从儒学的思想资源出发,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明相遇时,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双方的平等,即基本善的普遍性。我们应该考虑文化的特殊性,求同存异,相互共存。
最后,更重要的是,儒家通过普遍性自我观和整个天下、宇宙的观念,将生态环境纳入自身范畴,从而更加关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环境,其核心是自我超越。儒家认为,个人的整体目的和道德的善是相通的,因此,我们真正的自我不是后天的个体自我,而是本质上的道德自我。这个道德自我显然要求我们不要局限于自己,而是追求自我实现。我们必须命令我们超越自己的局限,摆脱人类中心主义,为自然和生态的发展而努力。
参考文献
[1]袁长江,董仲舒集[M],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2]陈戍国,四书五经注本[M],岳麓书社出版社,2006年版。
[3]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肖群忠,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J],哲学研究,2010年第2期。
[6]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J],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02-15。
[7]尤西林,有别于“国家”的“天下”——儒学社会哲学的一个理念[J],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
[8]胡瑞军,儒家政治秩序的基本设计体系[J],孔子研究,2007年第6期。
[9]邵龙宝,儒家伦理的理论结构与思想体系剖析[J],大连大学学报,1998年10月,第19卷,第5期。
[10]孙建清、王清涛,马克思学说体系与孔子儒学体系结构的异同及其相融性分析[J],山东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11]邬定伸,从“大家族”到“家天下”——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家”、“国”、“天下”的内在逻辑演进[J],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12期。
[12]张永超,论儒家思想的现代困境及其出路探寻[J],哲学研究,2014年3月,第3期。
作者简介:秦兆凯(1992年—),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中外政治制度方向。
论文作者:秦兆凯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8年8月上
论文发表时间:2018/7/23
标签:儒家论文; 社会论文; 国家论文; 儒学论文; 连续性论文; 传统论文; 政治论文; 《知识-力量》2018年8月上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