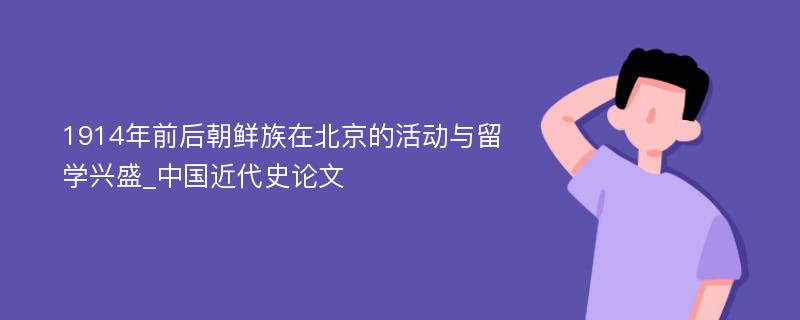
1914年前后北京韩人活动与留学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年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6)04-0028-08 在1919年韩国“三一”运动之后,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关内地区兴起,北京是中心地之一,所以关于20世纪20年代北京地区韩人社会及其民族运动,目前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在北京活动的韩人与上海稍有不同,不仅是创造派集中的地方,而且也是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比较集中的地方,相关的研究也集中在这些方面,还有人集中研究了北京高丽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这时期北京地区韩人留学生的活动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虽然也有一些研究涉及整个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或20至30年代北京地区韩人社会的情况,但是由于1919年前的资料相当缺乏,只能依靠中国和日本警察掌握的零星信息,所以对1919年以前情况的叙述都相当简略,至今我们仍难以准确把握早期韩人汇聚北京和在北京生活、活动的情况。1914年1月5日韩国独立运动领袖李承熙来到北京,4月23日才离开,期间除了3月16日至26日去过曲阜,一直住在北京。李承熙在北京逗留期间,李承熙与许多韩人有交往,在其《西游录》①有记载,为我们了解当时北京地区韩人情况提供了比较好的线索,而且也能反映早期韩国留学生到北京留学的情况。 在明清时期,除使团人员到北京一般要逗留一个月左右外,一般韩人不能在北京长期居留。1882年《清韩水陆贸易章程》签订后,韩人可以在天津口岸居留,在取得执照后也可以到北京贸易,也有无照韩人私自到北京活动。如崔元淳的父亲1894年到北京经商,1903年死在北京②。如果说最早居留北京的多是商人,则1905年大韩帝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尤其是1910年被日本吞并后,则更多的是流亡独立运动人士来到北京。李炳宪于1914年3月21日来到北京,在北京住了24天。据他的说法,当时北京有韩人不下300人。但是他们散居各处,多无室无家,朝来暮往,迁移不定,不仅没有统一的组织,而且到了北京,不是改穿洋装就是改穿汉服,虽在街头撞见也不知对方是韩人。1914年3月25日李炳宪在北京街头偶遇金起汉,两人之所以能够结识,是因为他们都是保守儒学者,坚持穿着朝鲜衣冠[1]457。事实上这时期到北京活动的朝鲜保守儒学者比较多,且多为孔教会而来。 李承熙也是为了征得孔教会对东三省韩人孔教会的承认而来北京的,随行的是次子李基仁和弟子芮大僖(国彦)。芮大僖本来是宋秉璿和宋秉珣的门人,在二宋殉国后流亡到中国东北,追随李承熙、孟辅淳从事独立运动。1914年1月5日晚上李承熙一行抵达北京后,住在前门外西河沿东升客栈。本来金爀约好在这里等他们,可是已经离开了。3月上旬金爀又返回北京,3月9日在法源寺前街大悲院见到了李承熙,向他传达了安东(丹东)、奉天(沈阳)一带韩人情况。 当晚在东升客栈迎接李承熙的是黄海道长渊人赵镛。一说赵镛又名赵克,为日本密侦,当时住在东城灯市口,经营一家韩人理发馆③。1913年1月赵克曾与李同春、李镛、朴正来等人奉延吉厅同知陶彬之命发起成立了垦民会,是否是同一人还有待考证。1914年2月朴正来也到了北京,2月24日向李承熙讲述垦民会及白纯的情况。赵镛应该与当时在北京的一些韩人有联系。开城商人梁谨泰1月16日来拜访李承熙,然后就住在了赵镛那里。像梁谨泰这样在北京经商的韩人还有不少。如金台锡1912年9月来到北京,住在前门外廊坊头条胡同。他经营一家杂货店,自己还在印铸局工作,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生活宽裕。尹永俊,又名尹永德,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从上海移居北京,住在崇文门内官帽胡同。他自1906年起经营一家餐馆,雇有30多名朝鲜妓生,主要为外国军人提供服务。虽然他在1910年加入了中国籍,但是仍与其他韩人有联系,并救济了不少流寓北京的穷困韩人。还有一些韩人在北洋军政机关任职。如朴廷迺本来也是商人,由于会中国语,流亡到北京后,在北洋政府参谋本部担任调查员,住在内城西安门内路北参谋本部内,每月也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与朴廷迺一起任参谋本部调查员的还有曾担任过郡吏的张乃亮,每月收入也有三十元④。参谋本部对北京韩人情况的掌握大概依赖于朴廷迺、张乃亮等韩人调查员,如1914年4月2日参谋本部致京师警察厅函称,“据本部调查员报称,住京韩人数达廿余,良莠不齐,行踪颇堪注意。”⑤ 尹永俊与朴廷迺有来往,但是李承熙到北京后与尹永俊等人没有来往。李承熙主动联系的是在北洋政府任职的汉城人金羽正。金羽正,本名金翼焕,也写作金益焕或金翼桓,他已经入籍中国十多年了,在通信院任主事,一说在交通部会计局任主事,当时住在西城绒线胡同板桥。李承熙一行到北京的第二天,1月6日,李基仁和芮大僖出门游览北京城,顺便拜访了金羽正。有人说金羽正也是日本高级密侦,1918年林权助曾试图通过金羽正拉拢李始荣⑥,但是在1914年当时金羽正是否已是日本密侦还有待查证。在北洋政府任职的韩人中,更有名的是赵根,他早年与驻扎朝鲜的袁世凯结有交情,1912年11月举家流亡到北京,在袁世凯的帮助下入了中国籍,担任拱卫军军需局委员,月收入一百元,住在正阳门内后细瓦厂1号。赵根虽然与金台锡有来往,但是还是有人抱怨他对韩国独立运动漠不关心,也不愿意为独立运动捐款。但是李同春到北京后,这种情况有所变化。李同春早年是译官,也与袁世凯有交情,韩日合邦前流亡到中国辽东地区,1910年曾因韩人土地问题到北京拜找过袁世凯,1913年参与组织垦民会。1915年李同春与赵根等人在北京组织新韩革命党,策划帮助高宗流亡北京,后因袁世凯死亡和国际形势变化而未能成功⑦。在袁世凯死后,许多在北洋政府中任职的韩人都不得不离职,北京地区韩人情况为之一变。 虽然李基仁和芮大僖主动拜访了金羽正,金羽正并没有去见李承熙。相反李炳宪到北京后,4月12日金羽正主动来访,谈了很久才离开[1]463。为李承熙介绍北京孔教会情况的是1月6日主动来访的尹胄荣。尹胄荣当时化名尹棠,是宣祖时期著名文臣尹斗寿的后代,曾任外部主事,白川、海州、灵光和安岳郡守等职⑧。他在北京也已经居住了多年,不仅参与孔教会的活动,与孔道会的龙泽厚也关系密切。1月14日尹胄荣拿着孔道会的请帖来请李承熙参加该会举办的拜经会,李承熙派李基仁和芮大僖前往观礼。1月17日尹胄荣来辞行,准备回朝鲜,李承熙还托他带回家信。尹胄荣后来又回到中国从事独立运动。 崔荣玖也同尹胄荣一样是旧韩末官吏出身,曾任度支部主事、书记郎等职,他当时也在北京,与孔教会有联系。1月8日,他与姜秉烈一起来见李承熙。1月20日,李承熙应龙泽厚的邀请,从东升客栈搬到宣武门外法源寺前街大悲院,2月18日崔荣玖也搬到大悲院前面的房屋居住。在崔荣玖之前,2月11日申八均(申英)和赵镛已搬到这里,住在西间,此外住在这里的还有赵元成⑨、金元、禹永禧等人⑩。 李承熙来北京前已经结识了申八均,两人曾相约到北京会面。申八均到北京后,住在东升客栈,2月2日来访,与李承熙相谈甚欢,2月11日搬来大悲院同住。当时龙泽厚租下大悲院的部分房屋,准备供孔道会活动之用,在见到李承熙后,愿意将这里作为招待所,凡朝鲜人来到北京,都可以随便住宿。龙泽厚并建议李承熙在这里开门讲学,教授门徒。当时孔社设有信古传习所,报名者四百余人(11),孔道会大概也有仿效之意,但是被李承熙婉言谢绝了。 李倬(李億)是礼曹判书李祖渊之子,曾任汉城府少尹等职,后来流亡中国,住在北京西单手帕胡同。1月16日,李倬与罗弘锡来拜访李承熙。1月20日李承熙移居大悲院后,李倬还追到这里来找李承熙谈话。2月10日,罗弘锡还带韩永福来见李承熙。韩永福是俞莘焕的门人,曾任江华郡守,还曾经作为领事书记驻天津,后来加入基督教,这时到北京传教。 李承熙对韩永福这样从儒教改信基督教的旧韩末官吏非常厌恶,感叹:“吾韩近日人情无常多如此。”2月11日,韩永福再次来拜访李承熙,拿出一份自己起草的《东省方略》,希望得到袁世凯的支持,李承熙看后觉得“良亦苦心,但藉此要华人信己而任用,则亦末矣”。但是对于信奉天主教的安重根叔父安泰敏,李承熙的态度则很不一样。当时安泰敏为学天主教而来到北京,因盘缠用尽而无法归国,向在北京的其他韩人天主教徒借贷而未果,听说李承熙来到北京,2月5日就慕名而来,两人说起安重根义举,为之怆然。安泰敏也住到了大悲院,也许是由于李承熙的介绍。也正因为如此,参谋本部调查员误以为他也是孔教中人,说“安泰敏托迹孔会,缔结不良分子”,并密通日本,行动悖戾(12)。安泰敏想在北京出售清心丸,无人问津,李承熙戏作《清心丸说》,让他以此为广告。此文大受欢迎,城中甚至有传抄者,中国人李文治看了也认为“文字高妙,大有警发人心处”。3月11日,李承熙与其他在北京的部分韩人凑了一些路费,送安泰敏回国。 李相禼本来不同意李承熙在孔教总会下设立东三省韩人孔教会的想法,在李承熙到北京前已经与他讨论过此事。李承熙到北京后,李相禼仍不放心。当时李相禼的弟弟李相益也在北京,与李复(李英)住在东城南湾子。1月18日即来见过李承熙,2月6日又到大悲院与李承熙把酒而谈。2月15日,李相益送来李相禼的亲笔信,再次强调韩人孔教会“必自立国土于世界政治之外”。李承熙再次声明这只是权宜之计,并在《读李参赞书有感》诗中说:“孔教亶宜别立土,多君抄下一南针;如今却傍邻家庑,拙法诚忏负夙心。” 李承熙在北京遇到的地位最高的旧韩末官吏出身的人物应该是1月15日来访的闵泳璇。闵泳璇是闵台镐之庶子,闵泳翊和纯明孝皇后的弟弟,1905年任忠清北道观察使、庆尚南道观察使,《乙巳条约》后因参政朴齐纯和内部大臣李址镕的弹劾被免职,不久之后又担任奉常寺提调、中枢院赞议、法部协判等职。李承熙见到闵泳璇后,两人“说及国家往事,不觉呜咽”。闵泳璇告诉李承熙,他这次到北京的目的只是游览,问及闵泳翊的情况,也说闵泳翊“今无世间想也”,让李承熙颇感失望。因此,李承熙指责说:“总社覆亡,吾人均罪,其首非大监家耶?”李承熙仍希望闵氏一族多为国家尽力,以示赎罪。 当时还有一些作为日本密侦的韩人在北京活动。如郑云复1913年冬天与日本警察渡边秘密来到北京,在北京各处设立特务机关,然后渡边回朝鲜,郑云复留了下来,住在东城。金达河是郑云复的爪牙,金孝明也与金达河一起活动,金孝明住在崇文门外,为拱卫军医官,还有住在大中府对门的赵汉根也与日本通谋(13)。但是李承熙《西游录》并没有提到这些人。不过,为日本服务的韩人密侦要到1916年以后才大量增多。1916年驻华日本公使林权助大力培养亲日韩人势力,韩人做日本密侦的就更多了。 当时来北京的韩人中,除了商人和旧韩末官吏出身者外,更多的是李承熙这样的保守儒生,他们大多是为孔教而来。在这前后,李刚台、金元、禹永禧、李丙熊等人也为孔教会而来到北京,金元和禹永禧还曾住在大悲院(14)。1914年1月到北京的全秉薰专程为孔社而来。1月27日全秉薰见到李承熙,“自述平生经历,往往悲愤下泪”。李承熙让李基仁送他去孔社,李基仁回来时带回两份孔社规则,李承熙对孔社所设博闻图书馆很感兴趣。1月30日李承熙与全秉薰一起去参观孔社图书馆,结果因社长徐琪不在而未能如愿,于是拜孔子像而还。3月7日孔社举行孔子忌日礼,全秉薰作为招待员也随班行礼[2]。全秉薰似乎也已经结识了一些中国人,2月11日晚上还将他与中国人的酬答文字交给李承熙看。全秉薰著有《献议》二册,主张在中国普及朝鲜礼教。李承熙觉得他“观其大意,多见苦心”,称其“立意颇壮”。离开北京之前,李承熙在给全秉薰的留别信中说:“若能以东之礼而反于中,必须开一制礼之席,是时当奉鄙先人所著礼要,手呈而相确之。吾友张君锡英,今于吾东礼学当屈拇,苟得共偕,赞仁兄之事矣。”(15)后来李承熙在给全秉薰的信中还问:“中华近局何如,胸里云雷稍有发施之路耶?”(16) 柳麟锡也希望中国能恢复中华之礼乐文物,1912年3月,柳麟锡有致袁世凯大总统和政府及诸省士君子书,命门人金起汉、白三圭、张基正送到北京[3]707。金起汉等人到北京后,寻找徐相默过去见过的万斛泉,得知万斛泉已经去世了,通过其门人结识了蒙藏事务局参事陈毅(士可)。陈毅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帮助把柳麟锡的信递到总统府。金起汉在北京一直呆到1914年3、4月份,就住在西河沿东升客栈。1914年3月,柳麟锡从俄国沿海州移寓中国东北,住在辽宁西丰县,又派金斗运到北京,让他与金起汉一起寻找合适的居住地。柳麟锡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受到袁世凯提倡尊孔和中国人组织孔教会等组织的鼓舞,以为中国有恢复中华礼乐制度的趋势,想做一些顺势助推之功。正是在此期间,2月12日,金起汉来拜访了李承熙。李承熙在海参崴时就认识金起汉,曾作有《赠金宗亮起汉》,诗云:“爱君忠义腑,直气干玄空。双手奉师训,万里排腥风。千言报馆字,万古惊群聋。前行愿努力,吾道在吾东。”(17)2月12日初次来访之后,2月20日又来讨论李恒老所定章甫深衣之制,2月26日又送来《华西雅言》,李承熙请龙泽厚看了看,龙泽厚“极致钦尚”。 1914年5月柳麟锡迁到兴京县暖泉子,金斗运是这时回到暖泉子的,金起汉也许是同他一起回到柳麟锡身边的。金起汉此行结识了一些中国人,所以回去后柳麟锡又让他将其1913年2月所著《宇宙问答》等书送到北京,以期对中国人有所启发,“俾尽斡旋归正之道”[3]709。金起汉在天津将《宇宙问答》印了800部,结果被警察没收了。1914年8月,柳麟锡移居宽甸县芳翠沟。这年冬天,就柳麟锡忙于写《道冒编》,而金起汉与白三圭、李贤初在暖泉山中重新刊印《宇宙问答》。1915年3月柳麟锡去世后,金起汉再次到中原,此行专门为传播《宇宙问答》。 当时金麟厚的后人金尧璿也在北京,1月17日与李鸿圭一起来见李承熙,正赶上龙泽厚来请李承熙搬到安庆观孔道会那里去住,李鸿圭担任翻译,可见他会说中国话。2月17日,赵镛薰也来拜访李承熙。赵镛薰本来是庆尚南道咸安人,后来迁到忠清北道怀仁县。1913年4月,赵镛薰与赵贞奎、赵昺泽一起流亡中国。不知赵镛薰是什么时候到北京的,当时住在杨梅竹斜街。在3月16日李承熙离开北京去曲阜后,3月21日李炳宪来到北京,住在余家胡同金华旅馆。第二天,李炳宪到太仆寺街衍圣公府孔教会打听到李承熙的住处,即赶到大悲院,见到了住在这里的崔荣玖和赵元成。他们告诉李炳宪,李承熙已于数日前去了曲阜。李炳宪看到大悲院还有空房,就找到住持,决定也搬到这里来住。但是当他3月23日带着行李来到这里时,崔荣玖和赵元成已经搬走了,于是李炳宪也决定回到西河沿三源楼住宿。崔荣玖和赵元成之所以突然离开大悲院,主要是因为常有巡警来检查,不堪其苦[1]457。 3月26日李承熙从曲阜回到北京,等他来到大悲院,见申八均、崔荣玖等人都已搬走,也不在这里住宿,直接回到德华客栈住宿。3月27日,申八均和赵镛薰来见李承熙。3月28日,李炳宪从赵镛薰那里得知李承熙已回北京,于是就一起到德华客栈去见李承熙。李承熙《西游录》中没有提到赵镛薰,只提到这一天还有全秉薰来访,而李炳宪《鲁越日记》和《中华游记》中则没有提到全秉薰。李承熙不仅与李炳宪是老相识,而且李炳宪是郭锺锡门人,为寒洲学派再传弟子,所以两人相见,“略道往景,不觉悽怆”。李承熙觉得李炳宪“颜面皆变”,因此有《李子明来见》诗云:“看君俨老苍,念我还增伤;未论当世事,吾党尽沧桑。”3月29日,李承熙也搬到李炳宪所在的三源楼住宿,与李炳宪、金爀、金起汉、赵镛薰等人时相往来。 4月3日,李承熙应云南省参议员李文治之邀,搬到西单北大街小酱坊胡同口李文治家居住,金爀、金起汉也住在附近,与李承熙是邻居,李炳宪也常来访,4月5日两人还讨论了地转说。4月12日,孔道会设讲会,李承熙、赵镛薰应邀参加,本来赵镛薰也给李炳宪送来了请帖,但是他因有别的事情没有参加。会上,李承熙临时命李基仁代为说了自己的观点,强调孔道不是虚文,惟当以实心进实学。当李炳宪赶来时,讲会已经结束了,李承熙和赵镛薰还在座,于是三人一起回到三源楼客栈[1]463。4月13日,李炳宪去曲阜的前一天还特来向李承熙辞行,李承熙托他给孔少霑、康有为和朴殷植带去书信。 除了商人、旧韩末官吏出身者和保守儒学者外,李承熙在北京也遇到一些受过新式教育的韩人青年和留学生。1月16日跟随李倬来访的罗弘锡是户曹参判罗永完的孙子,1909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这时住在前门外宾悦馆。罗弘锡虽然已经加入基督教,但是在见到李承熙之后说自己加入基督教并非出于本意,愿意跟随李承熙加入孔教。2月1日,罗弘锡也再次来见李承熙,仍表示愿意成为孔教一分子,并抄录了李承熙所起草的《东三省新附韩民事宜私议》。3月12日,陪李承熙的老相识、忠清道人金培东来访的文昌斌也是20来岁的年轻人。而让李承熙且惊且喜的是见到了在《北京日报》社任主笔的金子顺。李炳宪在国内时就已得知有韩人在《北京日报》社任职,所以4月5日就去东城镇江胡同《北京日报》社去找金子顺。当时金子顺在休假,通事告诉他金子顺住在东单牌楼附近。而根据中日两国警察掌握的情报,金子顺住在东四牌楼十二条胡同(18)。当李炳宪赶到东单牌楼,天色已晚,只好先回三源楼[1]460。4月8日金子顺来三源楼找李炳宪,4月9日又来拜访李承熙。 金子顺,又名金石我,号兰亭,本贯连山,汉城人。对于自己的经历,李炳宪记录的情况是:“幼离东土,寓日本广岛等地,经十数年,入燕者亦十有三年,与东人无关系,故不解韩语,其所习者日语汉文而已。”[1]4624月9日金子顺对李承熙说的情况是:“学生原籍朝鲜京城紫霞洞,年甫十二,离乡赴日本东京游学,二十西渡此地,迄十五载。”(19)李承熙又说金子顺为“本国京城人,十三岁入中国,今在北京新报社”。李炳宪和李承熙的记载稍有出入。中日两国警察掌握的情报是,金子顺于1900年前后来到北京,1904年日俄战争时曾充当日本宪兵分遣所密侦,在这期间结识了《北京日报》社社长朱淇,于是到《北京日报》社担任主笔,1912年加入中国国籍(20)。 当时李炳宪常到三源楼附近胡同内的阅报栏读报,其中就有《北京日报》[1]458。李承熙在北京的活动,各报也有报道。李承熙偶然读到《北京日报》的一篇社论,颇为赞赏,于是写了一封信,托李炳宪带给作者。听李炳宪回来说金子顺是《北京日报》主笔,还以为是金子顺所作。4月9日金子顺当面告诉李承熙他在休假,此文非他所作。不过,既然已经写了信,还是托金子顺转交给作者(21)。4月16日,北京各报转载李承熙上袁世凯书,误将李承熙说成朝鲜王朝宗戚,并说李承熙已在韩国国内设立孔教会,李承熙致函北京报界,加以澄清(22)。 金子顺与李炳宪见面后,“乃抽笔批谈,语颇烦冤”,与李承熙见面时也同样只能笔谈,两位韩人在北京用汉文笔谈,不能不让李承熙“有白马天涯沦落之感也”。这也说明金子顺过去很少与韩人来往,所以连母语都忘了。金子顺语涉愁怨的原因是金子顺对自己的境况很不满意,“而家无切近族戚,膝下又无一点血肉,身系汉籍,又占小星,近有身患,乍免《北京日报》主笔之任,寓京西王太监庙内云”[1]462。警察方面掌握的情报也说金子顺每月收入四十元,生活并不宽裕(23)。金子顺说他打算辞去报社的工作,另作打算。不过金子顺在与李承熙的对话中,对自己加入北京日报社的动机和今后的打算都有更崇高的解释。他说:“学生在《北京日报》充笔政者九年,本以国破家亡,身无所归,故匿迹燕市,静观世界大势。无奈大局益趋不平,窃欲改定方针,将投身他界,谋一种事业。(24) 不管金子顺加入《北京日报》社的意图如何,这时期金子顺确实充满爱国热情。他首先向李承熙请教韩国亡国的原因,其解释是:“国必自亡,然后人亡之。贼臣蠢于中,狡邻乘于外,一木而两斧矣,何足复言哉。”(25)李承熙接着强调青年对于复国的责任,而金子顺则认为要救国首先要振奋国民精神。他正是从这种逻辑出发,认为救国离不开旧学。他说:“为今之计,惟使韩人不忘自国历史,庶有望于十年百年之后。学生自幼负笈海外,不尚旧学,然自信保存国魂,非此莫可。”(26)与李承熙组织东三省韩人孔教会的意图不谋而合,但在看了李承熙《上袁世凯书》后又觉得李承熙所陈政策完全出自旧学,不一定实用。金子顺也希望用新旧两种学问教育流亡中国东北地区的韩人,建立独立运动基地,他并作有策略一篇,愿意与李承熙一起来加以实现(27)。金子顺此后确实与韩国独立运动加强了联系。 1915年3月申圭植等人在上海组织新韩革命党后,派李相禼、柳东说到北京设立总部,地址就在西单牌楼93号金子顺家(28)。 在金子顺任职《北京日报》前后,还有两位韩国人在北京报社任职。一是京畿道人卞荣晚,曾在某日报社负责庶务,日报停刊后寄食于东城灯市口的一家教会。卞荣晚1906年毕业于官立法官养成所,然后入普成专门学校学习,1908年毕业后到光州地方法院担任判事,1909年到新义州开设律师事务所,1910年韩日合邦后流亡到北京,1918年回国,专心研究汉学和英文学,解放后成为成均馆大学教授。还有一位是崔基龙,也在北京某报社任记者(29)。1915年申采浩到北京后,也曾为《北京日报》和《中华报》等报纸写稿,后因为《中华报》将其稿子删了一个“矣”字,《北京日报》编辑也在申采浩的一篇连载稿中改了两个字,申采浩一气之下不再为报社写稿(30)。 由于北京新式教育到这时仍比较落后,所以直接来北京留学的仍是少数。在1910年韩日合邦前,即有韩人以学习中国语为名流亡中国。1909年2月曹成焕就这种名义来到北京,不过到1914年李承熙到北京时,他已经去了上海。在曹成焕之前,1907年咸镜南道北青人高龙焕即到北京中央政法专门学校学习法律,1917年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1914年1月10日,高龙焕拜访了李承熙。《西游录》又提到,3月14日,“高镛焕来,详说北间儒会事,要我入其中设教会,书示其兄东焕所居(长兴洞),愿为主导,其言甚恳”。这里所说的高镛焕应该也是高龙焕,高龙焕的名字有时还写作高容焕。 而韩国留学生入北京各中学留学则更晚。1月9日来拜访李承熙的黄元方属于北京各中学招收的第一批外国学生。黄元方,庆尚南道龙南人,大约在1913年底与裴东一、徐日甫(徐曰甫)、韩云用等四人申请入北京私立山东中学学习。山东中学请示京师学务局,京师学务局又请示教育部,最终在1914年1月19日同意他们入学(31)。他们四人后来都成为韩国独立运动中的知名人物,不过当时只有黄元方去拜访了李承熙,大概因为他与李承熙关系特殊。黄元方曾是郑载圭的门人,而郑载圭虽是奇正镇的高足,在学问上接受了李震相的观点,与寒洲学派和华西学派都有交往,与郭锺锡关系甚深,与李承熙也有来往(32)。也许因为有了这层关系,所以李承熙很欣赏黄元方,觉得“其志颇倜傥”。1月20日李承熙移居法源寺大悲院,黄元方又来叙话。1914年前后,还有平安南道平壤人黄云龙到北京留学,入私立崇实中学。 这时李镛也在北京游学,住在鼓楼东大街宝钞胡同,并在申请加入中国籍(33)。1月19日李镛来见李承熙,叙别后经历,看来他也与李承熙早已相识。庆尚南道陕川人李浩然当时正在北京学习中国语,为进入中国学校作准备。李浩然之兄李载源(来活)是李承熙的门人,过继给了伯父,正在家丁父忧,1月28日李浩然来拜谒李承熙,讲述了李载源的情况,令李承熙“为念怆然”。李浩然住在东城隆福寺胡同,1914年2月3日李承熙赴国子监参观后,顺便拜访了李浩然,还正好碰到了平安北道人韩镇教。韩镇教对组织孔教会也有兴趣,2月4日来找李承熙商议在“西间岛”设立孔教会事,2月10日又来要了一份《东三省韩人孔教会趣旨书》。但是韩镇教没有成为一名孔教分子,这年6月离开北京去了上海。 在当时,即使是像徐曰甫、韩云用这样的中学留学生,也已经20多岁了。直到1922年,韩国留学生梁明在《东亚日报》介绍北京留学情况时仍说,北京各大学和中学对入学年龄没有限制,20来岁人高小或中学都可以(34)。这些早期韩国留学生也多不指望在中国学校接受系统的新式教育,而只是为了取得居留的身份。所以他们与居留北京的其他韩人往往没有本质的区别。李浩然与罗弘锡等人也有联系。2月23日,李浩然与罗弘锡、京畿道水原人尹海锡、咸镜南道元山人金声振一起去见李承熙。金声振“卒业高等学校毕业,颇有志尚”,当时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任职。李镛也认识罗弘锡,2月27日,李镛与罗弘锡、金声振、张一清一起来见李承熙。张一清是平安北道龙川人,也在北洋政府担任委员。事实上李浩然不久即放弃了在北京留学的想法,3月15日来告诉李承熙,他准备在沈阳西北购地垦荒,还约李承熙搬过去同住。3月31日再次来商议此事,李承熙让他先到沈阳与庆尚北道尚州人金达联系。在此之前,2月19日李相羲的弟弟李启东(德初)来见李承熙,也商量一起购地垦荒,设立孔教会。3月7日李德初再次来商议此事后,也先期回沈阳与金达筹备此事。4月24日李承熙回到沈阳后,即与金达、李德初、李浩然等人将此事付诸实施。 当时咸镜北道利原人朴宗根也像李浩然一样在北京为入学作准备。他住在鼓楼宝钞胡同。2月13日来见李承熙,李承熙觉得他“颇有志气,可爱”。与李浩然不同的是,朴宗根成功入学。2月24日,他告诉李承熙,已经成功进入政治学校学习,正在努力学习功课。4月19日,李承熙从侄李基炳也从安东县寄来书信说,希望到北京的学校学习,李承熙回信让他暂缓来北京,等他从北京回去后再商量。李基炳是否真的到北京留学,还不得而知。不过在1914年,还有平安北道龙川人李大伟从宣川信圣中学校毕业后到北京财政学校留学,两年后考入北京大学,专攻政治学。此外,根据参谋本部调查员报告,1914年4月在北京的卞真和郑海一也是学生身份,卞真住在东城公理会,郑海一在军需学校(35)。在1919年“三一”运动前,金尚卨和裵达武也以学生的身份居留北京。金尚卨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后来来到北京,寄居在中国人家里,一边教中国人日语,一边学习中国语。而咸镜北道人裵达武,1916年考入北京工业大学,并追随申采浩从事独立运动(36)。 虽然李炳宪估计1914年3月当时住在北京的韩人有300人,但是由于缺乏组织,韩人之间的联系并不多,新到北京的韩人很难与他人直接联系。辛珠柏教授认为,北京地区韩人直到1921年仍处于毫无势力的状态(37),大概是就北京韩人在此之前组织性不强而言的。像李承熙这样的知名儒学者、独立运动家到了北京,所能接触的韩人除少数是主动联系的外,多为慕名来访者,《西游录》中有记载的也就35人。如果再加上常被引用的参谋本部调查员掌握的22人的名单,能够确定当时在北京的韩人也就50多人,距李炳宪的估计还相差甚远,这说明还有很多当时在北京的韩人情况仍不清楚。虽然如此,从我们已经掌握的有限信息也可以推知,早期到北京的韩人,除少数商人外,多为旧韩末官吏出身者,其中有的还与袁世凯是老相识,或为投奔袁世凯而来,或是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的韩人领袖为争取北洋政府的支援而来。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情况不能不发生变化,一些在北洋政府任职的韩人离职,韩人与北洋政府的联系减少。另一个重要情况是,1914年前后来北京的保守儒学者增多,他们要么是来建议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恢复中华礼乐制度,或者希望推广朝鲜礼教,要么是联络孔教会、孔道会、孔社等孔教组织而来。但是这一时期注定是一个过渡时期。一股新兴势力也开始出现,那就是受过新式教育、具有新思想的韩人知识分子也开始汇聚北京,而且还有一些韩人青年开始到北京各级学校留学。到1915年,申采浩等人来到北京,北京韩人社会状况发生很大变化,为1919年以后北京成为中国关内地区韩人独立运动中心地之一奠定了基础。 ①李承熙:《西游录》,《韩溪遗稿》一,国史编纂委员会,1976年,第132~169页(下文有关李承熙在北京活动的叙述,除特别注明者外,主要依据这一材料,为节省篇幅,不再一一注明)。 ②外部[朝鲜]编:《外部训令附报告》二,为在北京死亡的崔元淳父亲尸体运送提供便利,1903年7月1日。 ③④孙艳红:《1910-1920年代中半北京韩人社会与民族运动的特征》,(韩)《韩国近现代史研究》第30辑,韩国近现代史学会,2004年。 ⑤《参谋部关于调查住京韩人的函》,京师警察厅训令,1914年4月4日,北京市档案馆,J181-018-03819。 ⑥(韩)朴昌和:《省斋李始荣小传》,乙酉文化社,1984年,第55页。 ⑦孙艳红:《1920年代北京地城韩人的生活像与民族教育》,(韩)《北岳史论》第10辑,北岳史学会,2003年。 ⑧《承政院日记》,高宗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甲申、高宗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丁巳、高宗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癸酉、高宗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丁酉。 ⑨也写作赵元性,参见《李炳宪全集》上,第456页。 ⑩(12)(13)《参谋部关于调查住京韩人的函·驻北京韩人调查一览表》,1914年4月2月,北京市档案馆,J181-018-03819。 (11)刘苏选编:《孔社史料(续)》,孔社本部函告信古传习所开课日期并附送呈稿及部批(1914年3月9日),《北京档案史料》1995年第1期,第9页。 (14)孙艳红:《1910-1920年代中半北京韩人社会与民族运动的特征》,(韩)《韩国近现代史研究》第30辑,韩国近现代史学会,2004年。 (15)《与全议官秉薰(甲寅)》,《韩溪遗稿》四,国史编纂委员会,1977年,第336页。 (16)《与全议官》,《韩溪遗稿》四,第336页。 (17)《韩溪遗稿》一,第125页。 (18)(20)(23)孙艳红:《1910-1920年代中半北京韩人社会与民族运动的特征》,(韩)《韩国近现代史研究》第30辑,韩国近现代史学会,2004年。 (19)(21)《韩溪遗稿》六,国史编纂委员会,1979年,第384页。 (22)《与北京报界同志会中》,《韩溪遗稿》五,第348页。 (24)(25)《韩溪遗稿》六,第384页。 (26)(27)《金子顺笔话》,《韩溪遗稿》六,第385页。 (28)(韩)崔洪奎:《丹斋申采浩》,太极出版社,1979年,第230~231页,孙科志:《1920-30年代北京地域韩人独立运动》,(韩)《历史与经济》第51辑,釜山庆南史学会,2004年。 (29)孙艳红:《1910-1920年代中半北京韩人社会与民族运动的特征》,(韩)《韩国近现代史研究》第30辑,韩国近现代史学会,2004年。 (30)丹斋申采浩先生纪念事业会编:《丹斋申采浩全集》下,萤雪出版社,1977年改订版,第500页。 (31)《私立山东中学关于可否收留朝鲜学生黄元方等四名随班上课的函》(1914年1月3日),北京市档案馆,J004-002-00079。 (32)《答郑参奉厚允载圭别纸(丁亥)》,《韩溪遗稿》一,第376页。 (33)李基元:《痛慕录》,《韩溪遗稿》九,国史编纂委员会,1982年,第520页。 (34)《在北京的中国留学案内》(全6回),《东亚日报》,1922年6月6日至13日。 (35)《参谋部关于调查住京韩人的函·驻北京韩人调查一览表》,1914年4月2月,北京市档案馆,J181-018-03819。 (36)孙艳红:《1910-1920年代中半北京韩人社会与民族运动的特征》,(韩)《韩国近现代史研究》第30辑,韩国近现代史学会,2004年。 (37)(韩)辛珠柏:《1920-30年代北京的韩人民族运动》,《韩国近现代史研究》第23辑,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