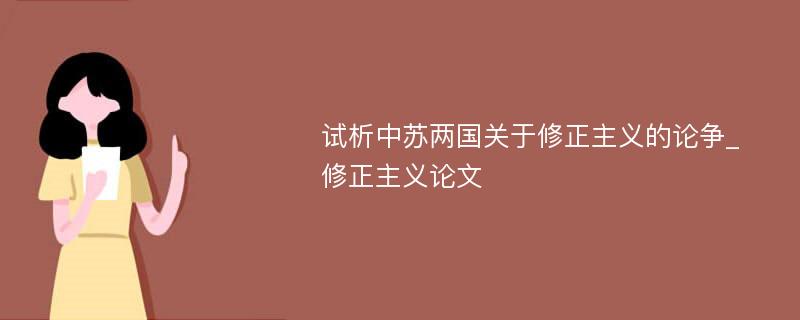
中苏两党关于修正主义问题的争论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正主义论文,两党论文,中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9)03-0032-04
从第二国际后期开始,一直到中苏论战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所谓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激烈斗争,曾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其中,中共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今天看来,中共之所以要与苏共论战,除了反对其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因素之外,就是认为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集团已经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并在苏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事实证明,赫鲁晓夫搞的不是修正主义,其探索和改革有不少积极的成分,也有一些右的东西,但更多的表现是“左”的教条主义的东西。
一、中共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
中共对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判断经历了一个过程。苏共二十大之后,随着中苏分歧的产生和不断扩大,两党关系越来越疏远,但当时中共并没有给苏共下修正主义的结论,只是有怀疑。1959年底之前,在毛泽东看来,此时的苏联仍然是朋友,“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1](P599)。但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认为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很多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已走上了“半修正主义”道路。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而能够纠正这些错误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因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1](P601)。显然,毛泽东已经开始把中苏分歧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了。
1960年是中苏两党关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在中共党内,早就有一种传统习惯,即在重大的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和发表纪念文章。1960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日,为了应对赫鲁晓夫对中共的影射攻击,从而“教育”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4月间出版的《红旗》第8期首先发表了由该杂志编辑部署名、经中共中央审定的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4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由该报编辑部署名,同样经过中共中央审定的题为《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的文章。同日,北京隆重举行了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重要报告。此后不久,人民出版社将上述3篇文章和报告汇集在一起,出版了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向国内外发行。
这三篇文章表面上是批判铁托和南共联盟的“现代修正主义”,实际上则是批判苏共在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的观点,回答了苏共对中共的批评和指责,阐明了中共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主张。文章说:“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对现代世界形势的荒谬论断出发,从他们的那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荒谬论断出发,企图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问题上,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此外,还有些人,他们并不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好心善意的人,真诚愿望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面对着某些历史的新现象,感到迷惑,有了一些不正确的想法,例如他们中有人说,美帝国主义的原子讹诈政策的失败,就是暴力的终结。在我们彻底驳斥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谬论的同时,也应当帮助这些好心善意的人改正自己的不正确的想法。”[2](P272)这里的“好心善意的人”,显然是指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文章还说:现代修正主义者提出今天世界已经进入了各国可以松一口气并平静地致力于他们国内建设任务的新时代,已经进入了议事日程上出现了新问题的时代,这些问题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而是合作、经济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他们否认暴力和战争所固有的阶级性,因而抹杀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根本区别;否认帝国主义重新发动大战的危险性,认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是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些论点也都是同马列主义根本对立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护帝国主义的统治,企图使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永远接受资本主义的奴役。”[2](P281)
随着全面论战的展开,中共开始认为与苏共的斗争是与修正主义的斗争。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中共根据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发动围攻和会后不久苏联背信弃义撤回专家的做法,认定赫鲁晓夫等人实行的是现代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而中国则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苏两党的分歧和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根本的问题是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中央认为这场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同时,中共领导人提出,由于苏共和苏联基本上是反帝、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所以问题是部分性的,尽管错误是原则性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问题,人民内部问题,它对马列主义是部分地修正,要承认赫鲁晓夫的错误是部分性质的[3](P340-345)。中共仍提出要把同赫鲁晓夫的斗争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从团结出发经过适当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4](P292)。基于这两方面的判断,中共中央制定了坚持团结但不放弃原则,敢于斗争却留有余地的斗争原则,目的是以斗争求团结,挽救濒于破裂的两党两国关系。
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二十大以来执行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已形成完整体系,赫鲁晓夫已经蜕变成为高薪阶层的代表,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代表。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指出,我们跟修正主义的分歧不是一般的分歧,而是关于世界革命的路线的分歧。刘少奇还说,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这三大问题,我们和修正主义之间有严重分歧,因为它们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5](P484-489)。毛泽东在讲话中不但断定苏共领导已完全蜕变为修正主义者,而且把他们和帝国主义者、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同等看待了[6](P37-38)。
1963年3月苏共发表公开信之后,中苏论战进入高潮阶段,中共在《九评》中认定苏共领导集团已彻底堕落为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是其中的总代表,并集中批判赫鲁晓夫。
经过对苏共发表公开信以来的形势分析,中共领导人认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不但形成了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走上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且已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已经彻底失望了,决心丢掉一切顾虑,撕破脸皮,不怕破裂,和苏共论战到底。就这样,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连续发表了9篇文章,评论苏共的公开信,中苏公开论战进入高潮。《九评》的主线是对修正主义进行彻底批判。中共领导人要求,评论文章要指名道姓,公开论战,即直接指名苏共领导,矛头对准赫鲁晓夫。9篇文章分别对中苏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问题、民族解放运动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和平过渡问题以及赫鲁晓夫如何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等9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内容之详尽前所未有,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一评》中,中共对苏共修正主义的产生、发展、形成体系作了论述。《一评》指出,苏共二十大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犯了两个重大原则错误,一是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二是提出所谓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从此,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路线从产生、形成发展到系统化。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新纲领是苏共领导修正主义路线形成完整体系的标志,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它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就是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
在《九评》中,中共对苏共修正主义形成的根源、留给我们的教训作了分析。中共把对国内阶级形势的判断应用到苏联,并作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夺权的论断。中共认为,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在苏联,在完成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已被推翻但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仍然存在着。”“在城市和乡村中,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仍然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分子还在不断地产生。”“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苏联社会上形成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主要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并成为这个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7](P449-516)。
在《九评》中,中共还系统总结了防止修正主义的历史经验。中共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提供了最重要的反面经验,使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从中吸取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教训”。《九评》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走上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一种危险性更大的资本主义复辟,向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敲起了警钟”[7](P504)。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和苏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体归纳了15条,如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着阶级斗争,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这些经验大部分是正确的,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谁战胜谁的问题要一百年到几百年才能解决的判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至今仍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警示意义。但应该看到,这些结论带有时代的特色,结论产生的依据也是不科学的,某些观点还有较大的片面性。
二、赫鲁晓夫路线不是修正主义路线
中共对赫鲁晓夫的批判是建立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夺权的基本判断之上的,中苏论战的核心是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回过头来看,尽管那个时期中共的观点有对有错,有些带有片面性,有些至今仍有积极意义,但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判断是错误的。有人根据苏联后来确实出了修正主义,并演变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断定中苏论战对修正主义的判断和批判是完全正确的[8],这就不符合历史实际了。
从历史上看,修正主义实质上是如何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如果一国共产党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是为少数人谋取私利,这样的党还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那就是真正的修正主义。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大胆地抛弃已经过时或不适合本国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和词句,就不是修正主义,而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过,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在发展中,也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这是一个认识问题,与修正主义错误是不同性质的。
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斯大林和毛泽东先后曾批判的南斯拉夫、意大利、法国、苏联等国家共产党的现代修正主义,实质上是这些兄弟党在本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或作这样的探索。铁托在被斯大林制裁的情况下,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设备,搞工人自治和部分企业私有化的试验;法共、意共提出的资本主义和平过渡论和结构改革论,等等,也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这种探索是积极的,不应该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况且1943年共产国际在解散之际,就鼓励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特点,制定革命路线和政策。毛泽东利用这个条件,才最终战胜当时在党内还有相当影响的王明教条主义势力,取得整风运动的胜利,使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最终克服毛泽东晚年错误,也是这个武器——即“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走民族化的道路”,为什么不允许别国共产党也这样做呢?
今天看来,赫鲁晓夫是搞改革的,只是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改革者。斯大林逝世不久,赫鲁晓夫就开始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试图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积累的一系列矛盾。如,在农业方面,除开垦大批荒地以外,从体制上主要是将机器拖拉机站卖给集体农庄,给农业劳动者以生产自主权。在工业方面,一是将原来由中央各部实行“条条”管理过渡到按地区实行“块块”管理;二是按此建立经济行政区;三是扩大地方在经济管理中的权力;四是发挥工人群众参加管理的积极性;五是改进对企业的计划领导制度,进行以经济手段(利润、奖金、价格、货币等)代替行政手段以刺激企业生产的试验。这些措施当时都起了积极作用。后来,赫鲁晓夫的改革逐步变形,唯意志论越来越严重,特别是“20年建成社会主义”的计划不但促使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的出台,而且赫鲁晓夫又把党组织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从而削弱了党的领导,也失去了地方和军队的支持。
后来,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中共认为其根本原因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破产了,赫鲁晓夫“妄想把历史的车轮拉回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7](P520-521),违背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是中共按照自己的理解而作出的错误判断。事实上,赫鲁晓夫下台是因为其改革既不彻底,又太轻率。他既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管理理论和产业结构,也没有完全抛弃行政命令式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既没有调动起工农群众真正的积极性,也没有充分发挥知识和科技的力量,反而把各级干部搞得人心惶惶。赫鲁晓夫迷信权力和意志,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大多未经深思熟虑,往往轻率从事。他没有建立起一套民主科学地选拔干部的制度,党政领导的主要干部仍然由自己遴选或听信别人的推荐,这一方面使真正的人才不容易得到,同时给那些投机钻营和官迷心窍的人以可乘之机,埋下了党内争权夺利的种子[9](P210-211)。从近年解密的苏联档案来看,赫鲁晓夫的下台也不是因为他搞了修正主义,而是搞个人崇拜、决策失误等等[10](P571-572)。
赫鲁晓夫有一些右的提法,如提出通过裁军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但从根本上说,赫鲁晓夫的主要表现,并非是右的修正主义,更多地显示出来的是“左”的教条主义,是脱离实际,称之为“修正主义”并不合适。中共没有看到赫鲁晓夫教条主义的实质,指责“三和”、“两全”是对外取消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对内取消了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结果把“左”倾教条主义反而当成修正主义,同赫鲁晓夫的分歧和斗争也转化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由于中共认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国外根源;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压力,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国内根源”,所以,毛泽东异常强调阶级斗争,并把党内的不同意见看作修正主义,提出了在国内防修和反修的迫切任务。在对外政策上,中共既反帝国主义,又反苏联修正主义,结果把自己搞得很孤立。中共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模糊了自己的视线,没有看到赫鲁晓夫路线的实质,是在以自己的“左”反对赫鲁晓夫的教条主义,结果使党走向了极左。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视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警惕和平演变和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看不到这种斗争和危险,是十分错误的。但是,越过真理的界限,把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甚至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对和平演变的形势做出不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夸大估计,把许多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当作“修正主义”来反对,那就是错误的和极其有害的了。这是中苏论战的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教训。
收稿日期:2008-12-20
标签:修正主义论文;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论文; 赫鲁晓夫改革论文; 中苏关系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中苏论文; 帝国主义时代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毛泽东论文; 斯大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