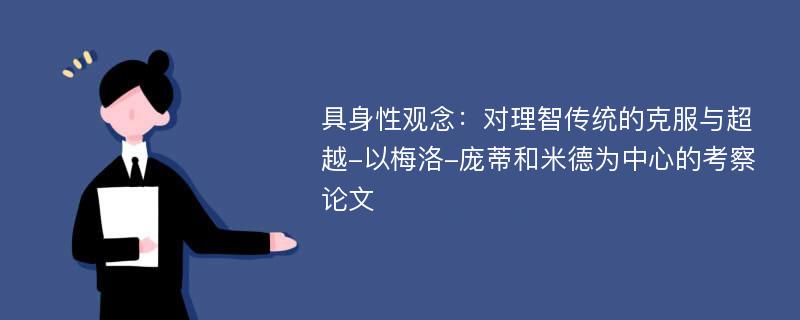
具身性观念:对理智传统的克服与超越
——以梅洛-庞蒂和米德为中心的考察
何 静
[提要] 当代认知科学中的具身性观念,挑战了以“计算-表征”为特征的经典认知观,将人类认知视为主体熟练应对具体境遇的具身能力。如果仅聚焦两种认知观在形式上的对抗,而不进行哲学史的梳理,就难以揭示具身性观念形成的思想运动轨迹及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意义。着眼于身体、心智与世界的关系,本文以梅洛-庞蒂的意向性概念以及米德的意义符号理论为中心,展现了现象学与实用主义传统中的具身性维度。两大哲学传统在具身性维度上合流,对认知科学中具身性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而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说,具身性观念颠覆了西方哲学史上根深蒂固的理智传统,并由此获得了哲学上的价值。
[关键词] 理智传统;具身性;意向性;意义理解;动力耦合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以“计算-表征”为特征的经典认知观的衰落,具身性(embodied)的认知观悄然发展起来。它主张:认知不是一种源于客观世界模型并基于抽象运算法则的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而是主体在身体-环境的动力耦合中涌现出来的具身行动能力。不过,如果仅仅聚焦于具身认知观与经典认知观在形式上的对抗,而不探究新兴的认知观与哲学传统之间的关联,就难以揭示它在西方哲学史上形成的思想运动轨迹以及哲学史的意义。
具身认知观质疑“抑身扬心”的理智传统。在此方向上,汇聚了多种哲学传统。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反笛卡尔主义”的现象学传统和实践认识论框架中的实用主义传统。这两大哲学传统中蕴含着的丰厚思想资源令具身性观念得以迸发、形成和延伸,令具身认知研究范式的内在逻辑得以展开。本文通过聚焦于梅洛-庞蒂的意向性概念以及米德的意义符号理论中的具身性维度,一方面考察具身性观念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深刻渊源;另一方面彰显它如何通过消弭身体、心智与世界之间的界限,而实现对理智传统的超越并获得其哲学史的意义。
一、理智传统与二元论:从柏拉图到笛卡尔
心智与身体和世界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哲学难题。在西方哲学史上,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非具身理智传统——认为身体与心智相分离、内在的心智与外部世界相分离;知识的本质是内在心智对外部世界的表征。柏拉图和笛卡尔正是这种非具身哲学传统的奠基人。
柏拉图认为,所有的知识都必须以明确概念的形式进行描述。那些无法被明确形式化的现象,如身体技能和情感等则不能被看作是知识。由此,他区分了理性的心智和拥有技能、情感的身体。在《斐多篇》中,柏拉图以神话故事的形式描述了灵魂至高无上的地位。[1](P.65C,66D,66E)如果灵魂羽翼丰满,那么它就能高飞并主宰整个世界;如果灵魂失去羽翼,就会下落,与凡俗的肉体结合,成为可朽的“生灵”。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灵魂依赖理性到达善良、正义、节制并获得真正的知识。而大多数无法高飞的灵魂,受到健忘和罪恶的拖累,羽翼受损而坠落地面,投身肉体。
柏拉图进一步将灵魂看作是复合的实体,理性是灵魂的本质。因此,灵魂的不朽,实际上就是理性的不朽;非理性的东西是可朽的,如,非理性的感觉。尽管在求知的过程中,感觉作为启发或诱因起到了刺激回忆的作用,但由此而获得的对事物的知觉与通过回忆获得的关于事物本身的理念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相对的、变化的,而后者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通过将知识与理念划给灵魂,将感觉划给身体,柏拉图主张灵魂先于身体而存在,且对理念早有认知。只是,身体会遮蔽理念,将灵魂引入歧途。因此要获得灵魂的升华,就必须要摆脱感觉与身体的羁绊与干扰。[1](P.75E)不难发现,柏拉图的灵魂说、认识论乃至本体论建立在灵魂与身体相分离的二元论基础上。他所建构的“灵魂-身体”二分以及灵魂统摄身体的思想,形成了心智问题探究的古典范式,是希腊哲人关于身体、心智、世界关系问题探究的起点。
布伦塔诺被认为最早提出并使用“意向性”这个概念,但是这一概念作为技术性术语被引入现象学并获得哲学上的重要性则要归功于梅洛-庞蒂。梅洛-庞蒂发展了胡塞尔意向性概念中相关性的方面,摈弃了其先验还原的方面,通过对身体及其主体地位的彰显,进而将意向性看作是身体-主体与世界建立联系并实现在世存在的特殊方式。
由于浙江省山洪灾害易发地区大多分布在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恶劣、经济社会欠发达、交通通信不便的地区,且经常在夜里发生,灾害来临时,进山的公路、通信、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也会同时被冲毁,加之部分群众防灾意识淡薄,对人员应急转移不理解,因此实施救援、恢复生产难度大,代价高。
梅洛-庞蒂越过胡塞尔对意义的意向性概念的限定,主张意向性的意义内容不在于意识的先验结构,而在于主体通过前反思的方式具身地与世界连接的方式。进一步地说,梅洛-庞蒂的意向性概念主要通过其“运动力”内涵展现出来。在《知觉现象》中,梅洛-庞蒂改造了胡塞尔“运作的意向性”(operative intentionality)的概念,并将其阐发为主体对世界前反思的默会觉知。[6](P.xxxii)这种运作的意向性表明了身体-主体运用复杂的身体运动在世界中行动的基本能力——即“运动力”,它令主体能够在没有明确意识关注的情形中指向对象。在梅洛-庞蒂看来,运动力是意向性最基本的经验和观察形式;意向性不是对对象进行置定,而是面向对象。[6](P.472)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意向性并非凌驾于运动力之上,而是内在于运动力之中并贯穿其始终。运动力是意向性的,意向对象以及意义内容的建构和存在方式并非依赖于主体的意识结构而蕴含在所做之事之中。
到了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那里,他继承并改造了以柏拉图和亚式为代表的古代灵魂哲学,力倡清楚分明地强调身心的截然二分。笛卡尔淡化了先哲关于神性灵魂的观点,而更关注人性的“心智”。[2](P.65)在笛卡尔那里,心智不再像柏拉图意义上的“灵魂”那样作为世界的本原而存在的实体,而作为个体思维的本原而存在。笛卡尔认为,内在的心智应当包含“理性”“情感”和“欲望”三个方面,理性在其中具有支配地位。个体的存在取决于理性或具有各种属性的心智,身体及其周围的世界作为物体的存在只具有从属意义。笛卡尔坚持一种抑“身”扬“心”的姿态,并且身体和心智作为两个彼此独立的实体并无实在的联系。心智是纯粹意识的,完全是心智内部的活动,因而是内在的;身体是纯粹物质的,只有外在性,身体之间各个部分的统一是因为心智的在场。这种纯粹的心智概念以及身心截然二分的思想构成了笛卡尔存在论以及与心灵实体有关的一切知识的起点。
但笛卡尔的问题在于,身体通过物质的广延性而获得了纯粹性,但心智却始终无法脱离与身体的纠缠而达到纯粹性。[3]如梅洛-庞蒂所说,在笛卡尔那里:“我的身体和心智之间存在着一种手段和目的特殊关系。身体作为心智的工具而存在。身体的新属性体现在:不可分割性和功能的统一性。由此,笛卡尔把心灵理解为‘身体的形式’。”[4](P.41)对笛卡尔而言,身体与心智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因为物质的身体无法进入心智,而理性的心智也无法真正下降到身体。
尽管笛卡尔的二元论思想没能超出柏拉图与亚式的讨论高度,但他所开创的心智哲学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主张身心二分、强调理智的传统,直接或间接地引出了两种哲学传统:现象学与实用主义,前者以克服纯粹意识为目标,后者致力于批判纯粹的理性思辨。
中国与欧盟是当今世界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大户,中欧可再生能源合作是气候减缓和气候适应的有效途径之一。基于以上分析,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二、现象学传统:意向性中的具身在世
皮尔士用符号化的方式为笛卡尔的心智观祛魅,提出根植于行动(实践)的心智符号学理论。只是作为一名符号学家,皮尔士没能够进一步追问这种符号化的过程如何可能的问题。杜威强调心智是人与环境交互过程中形成的客观意义系统。米德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皮尔士和杜威的心智观,转化了西方近代以来的心智哲学观点,将心智问题从内省的沉思模式转向实践的决定模式。特别是,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语言和心智的具身性根源并分析这一发生过程的实用主义者。正如莫里斯所说:“如果说杜威提供了范围和远见,那么米德则提供了分析的深度和科学的准确性”。[8](P.xi)
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说试图将柏拉图“灵魂-身体”二分的思想与唯物一元论进行调和。亚式基于形式-质料学说,将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他强调完整的生命是灵魂形式与身体质料的内在结合。一方面,灵魂作为自然身体的形式而存在,不同于质料也不同于形式与质料的结合,它聚合了生命现象的形式因、动力因与目的因。因此,灵魂有赖于身体,不在实体意义上与身体对立。但另一方面,理性的灵魂又能够摆脱身体的束缚而展现独特性的视角。追随柏拉图,亚氏也强调身体与灵魂的二分,并将理智灵魂放到神性的崇高的地位,将自然身体置于附属的位置。古希腊哲学对灵魂实体性和神性的强调,令认识论服从于本体论。这是古希腊哲学为现代哲学留下的重要遗产。
心理社社员总共约50个,每次聚会大概会来8成,比例算高。像我一样的大一新社员有12位,其中3位是女生。
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继承了布伦塔诺关于意向性是主体关于对象第一人称的指向性(或相关性)的基本洞见,并进一步提出了意向性的三重结构:意向行动、意义内容以及意向对象。[5](P.24)例如,“我的猫饿了”这一判断可以被解释为“我”的行动(一种判断)、判断的内容(我的猫饿了)以及“我”的意向对象(猫的饥饿)。胡塞尔进一步指出,意识活动对对象的指向表明了主体与对象之间产生了有意义的关联,即主体通过某种特定的方式来看待对象。换言之,意识活动令意向对象能够在特定的视角中(例如,作为“我的”猫)显现自身。在此意义上,对象的意义由源自意识的经验构成,而对象只是依赖于意识的“意向对象”。
由此,米德将有意义表意符号置于哲学分析的中心,主张意义的逻辑结构处于身体姿态-调整性回应-社会行动结果的环路之中:“这种存在于姿态、调整性回应以及由这种姿态唤起的社会活动的结果之间的三重或三联关系,就是意义的基础”。[8](P.80)在这种由姿态对话建构的的三联关系中,身体姿态的意义同一性得以确立。通过对有意义符号的使用,个体内化了自身在世界中的行动问题:“在你推理的时候,你正在向自己暗示那些会唤起某些回应的特征——这就是你正在做的事情”。[8](P.114)同时,个体的行动向姿态产生之前和社会行为的结果两个方向展开,分别体现了意义的客观性和逻辑性。
2018年7月,东北化工销售公司上半年经营考核指标出炉。上半年,公司累计实现产品销量306.28万吨,比预算进度多实现11.72万吨;实现营业收入186.36亿元,比预算进度多实现32.4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5053万元,比预算进度多实现10053万元;实现调运量499.28吨,比预算进度多39.28万吨;调运计划完成率100%;购销率100.31% ……
在此,关键的问题是:意向性或心智如何与身体运动天然交互、相互蕴含?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不是单纯生理性的存在,而是作为活生生的知觉和经验主体而存在。一方面,活生生的身体作为意义的基础而存在;另一方面,世界也会“质疑”身体-主体,而身体运动正是主体对来自世界的质疑作出的积极回应。他用“意向弧”的概念来定义这种环境(或世界)与身体-主体回应之间形成的动力循环机制。过去的经验被投射入当下的世界,引导主体将知觉和智力以及感知力进行统合从而产生当下的知觉体验。意向弧表明了身体-主体精细辨别环境的能力。当下的环境诱发主体相应的行为,如果主体的回应没能产生满意的结果,那么主体就会进一步完善他对环境的辨别,如此往复,直至主体与当下环境形成一种最优的协同关系。
由此,梅洛-庞蒂不仅认识到了主体与意向对象和世界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关系,而且进一步把意向性的主体从意识转变为身体。当身体通过自身的运动力和知觉能力聚集起来,朝向世界中的事物或行动的目标的时候,意向性就在身体中形成了。因此,意向性就是主体的态度或身体运动对世界中对象的具体空间指向(direction)。只有当身体的运动力具有了意向性以及当主体通过意向性与世界中的事物建立了联系的时候,身体运动才能在生成关于世界的知觉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梅洛-庞蒂力图通过运动力概念来改变对意向性的理智主义说明。在这种充分展现身体主体性的现象世界中,意向性被追溯为一种自然的、前反思的和透明的身体意向性。但是,梅洛-庞蒂对意向性的具身性说明并没有与胡塞尔意义意向性的概念产生真正的断裂。梅洛-庞蒂延续了胡塞尔,认为所有的经验从本质上说是意向性的,但他又超越了胡塞尔所坚持的认知论层面,在否认先验意识结构的同时强调了身体的主体地位。尽管事物在我们朝向它们之前就具有意义和价值,但只有当我们的身体运动朝向事物并与之发生关联的时候,它们的意义才能够被我们获得:“一个事物并非实际上在知觉中被给予,而是内在地交由我们,就它与一个世界的联系而言(这个世界的基本结构与我们相连而这个事物只是其中一个可能的具象),被我们重新建构和经历。”[6](P.341)如此一来,身体-主体活动就成了意义显现的先决条件,它以不在场的在场的方式支持着世界和事物的显现。
总之,通过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主体性原则及其理性规范的克服与超越,梅洛-庞蒂摆脱了意向性的早期现代含义并将其规定为主体进入世界和事物的方式,从而将传统的意识哲学及其理性范式带向了历史性的转换——身体主体上升到了主导性的位置。身体并不再是被纳入物质世界的物体,而是兼有知觉和运动力的整体属性。身体的运动力是最初的意向性,身体对世界回应技能的成熟并非意味着心智特征的消失,而标志着心智的发展。这意味着,我们只有将外在可观察的身体过程与相关的内省体验结合在一起才能对心智作出说明[7](P.55)。基于此,身体与心智不再是二分的,两者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统一在身体中。这是具身性的最基本含义,它开启了20世纪哲学和认知科学更新身体、心智和世界关系的理论可能性。
三、实用主义传统:意义理解的具身结构
从心智优先到身体优先,表明了具身性观念在20世纪现象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由此导致了传统意识哲学的崩塌。与此同时,20世纪英美哲学传统中的实用主义,矛头直指旁观者式的认识论,通过对知识和实践概念的阐发和提升,同样实现了对身体和世界的关切。
后期的现代哲学试图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从对立的严格逻辑中释放出来,引入主体身体的概念,以反笛卡尔的方式重新理解身体与心智以及认知主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这在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的现象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在这一现象学的思维进路中,理智传统被抛弃,心智之于身体的经典优先性,被翻转为身体之于心智的优先性。下文将通过梅洛-庞蒂对意向性概念的阐发,展示现象学中具身在世的理论视野。
笛卡尔的心智模型强调心智先于世界和语言存在。一方面,笛卡尔赋予了心智以本体论属性。在《方法谈》和《哲学原理》中,笛卡尔明确地提出了哲学的第一原则——“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在笛卡尔看来,思考(cogitare)不仅仅包含了理性活动,还包含了所有的心智活动。通过将主体性原则带入哲学,笛卡尔进一步主张任何一种心智活动都必然蕴含着主体的认知行为,即“我思考p”。主体作为一个思考物,其本质就是思考;“我存在”与“我思考p”一样必然为真。[9](P.26-28)另一方面,笛卡尔将语言看作是人类心智能力的特定类型,认为心智先于语言而存在。在笛卡尔说,任何一台先进的机器“绝不能像我们这样使用语词,或者使用其他由语言构成的讯号,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思想”[10](P.44),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机器不具备心智。因此,要解释人类的语言行为,就必须要引入心智的概念。
而姿态则是态度的示例。和态度一样,姿态是有机体的初始运动:“所有的姿态中都蕴含着行动倾向。因此,我们可以将姿态看作是行动的开端”。[11](P.123)任何态度(作为初始运动),一旦在社会行为中得到了来自其他有机体的回应,就变成了姿态:“‘姿态’这个术语表明了社会行为的开端,它们刺激了他者的回应方式”。[11](P.126)不同于达尔文和冯特,米德认为,姿态尽管是社会行为组织的方式,但作为在社会行为中作出的回应性的身体行动,从本质上说是非意向性的。只有当身体姿态经由个体间的“姿态对话”而达成行动实施的时候,身体姿态才能转化为承载了意义的、具有可沟通性表意符号。[11](P.124)
但是这种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从对立的严格逻辑种释放出来的主张,并不意味着较高级的活动能够被还原为较低级的活动,正如米德所说:“理性活动从有机体的活动中涌现出来,但两者并不等同”。[9](P.122)从根本上说,米德是一个非还原论的物理主义者。他反对将心智现象还原到在纯粹“神经生物学”过程,而主张通过对它从主体间交互中涌现出来的发生学过程的解释来描述心智现象。由此,米德用“解释转换原则”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哲学立场:尽管心智现象从本质上属于物理现象,但是我们不应该根据个体生理机能来研究它们,因为心智现象产生的层面(如,社会层面)具有自身特殊的动力学,无法从个体层面对其进行充分解释。也就是说,心智现象不能仅通过个体生理机能的层面来解释,而必须通过它所产生的社会交互层面进行解释。根据米德的这个解释转换原则,个体的心智与行为:“只能根据个体在其所在的社会团体中的行动获得理解,因为个体的行动总是处于超越个体的、关涉他者的、更大的社会行动中”。[8](P.6)因此,在米德看来,心智不是一个非具身的理性推理装置,而是从具身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中涌现出来的能力,是社会意义系统在个体中内化的产物。
那么,这种心智能力是如何在前语言的社会交互过程中产生的呢?在《心理学和语言学的关系》(1904)一文中,米德立足于实用主义传统,结合19世纪的达尔文进化论和冯特的语言手势理论,具体阐发了心智与语言形成的具身性根基。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具身性概念:态度和姿态。米德通过“态度”概念,对冯特的表意理论进行补充。首先,态度是作为行动开端的身体初始运动。从有机体的主动行为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基础来说,态度是有机体对因特定环境刺激而作出回应的身体习惯进行编码的神经通道。其次,态度是具有目标-导向的认知项。态度感知环境的承载性(affordance)并控制着行动从开始到完成的整个过程。[10](P.382)
而米德的心智主张与笛卡尔有着尖锐的分歧。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他对连续性原则和解释转换原则的阐发中。米德认为,连续性原则应具有如下两个特征:其一,较高级-较低级的连续。他否认独立意识实体的存在,强调较高级的认知能力(如,理性、意志或共情)在本质上与较低级的认知能力(如,知觉、情绪)并无不同。其二,内部-外部的连续。他否认需要通过本体论原则来对“内部”的心智和“外部”的物理世界进行描述,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内部领域。这一连续性原则构成了米德和杜威反对心智/世界、内部/外部、主体/对象传统二分的根基。
姿态对话是社会活动中,两个或多个参与者之间连续的、交互式的身体姿态交互过程。让我们想象一下两条狗对峙以准备攻击对方的情景。一条狗绕着另一条狗踱步,另一条狗则虎视眈眈地蹲伏着准备伺机发动进攻。在这一情境中,一条狗的肢体动作刺激了另一条狗的回应行动;而另一条狗的回应方式反过来又刺激了这条狗的进一步回应……两条狗之间形成了姿态和运动的刺激环路。姿态对话作为“动物彼此调整行动反应的沟通形式,预设了它们都能对对方的身体姿态表达进行诠释性的意义理解。因为唯有对于对方的身体姿态表达有正确的意义理解,双方才能作出适当的调整性反应,从而达成社会行动的付诸执行。”[12](P.66)米德认为,人类社会的沟通和交互方式并无二致。个体通过对对方身体姿态的意义理解,将他者的身体运动纳入自身运动并由此作出回应,从而形成个体间的情感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从前意识的身体姿态对话中过渡到有意识的、通过表意符号进行的语言沟通。
通过血清学检测发现,在51280份标本中,51043份标本为HBsAg阴性,25份标本为单试剂阳性,212份标本为双试剂阳性。
在2016年12月—2017年12月,我院收治100例孕妇,通过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分别划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为50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清晰地看到,米德以意义理解的具身结构为基础,解构了纯粹的理性思辨,在新的基础上重新了安置身体、心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路向既蕴含着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哲学的某些特征,同时又表现出外在主义的指向。米德总结道:“心智并不处于个体之内。心智过程从个体在环境中的复杂行为中涌现出来……如果心智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那么任何一个个体心智的场域必须延展到社会活动以及构成这种延展性的社会关系中;由此,(心智的范围)不能囿于个体有机体的肌肤之内”。[8](P.223)在他看来,人类心智是一个产生于身体与环境之间实时交互并延展至世界的“弹性场”。
在这一方向上,新实用主义者如普特南、布兰顿等,在不同程度继承了米德积极的外在主义心智观并推向了新的高度。与现象学的思路不同,实用主义更多地站在社会学和与语言学的立场上,对反笛卡尔主义主题加以发挥,共同为20世纪具身性观念的形成和具身认知研究范式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对83例胃癌患者的性别,肿瘤的位置、直径、Borrmann分型、分化程度、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和远处转移,以及新辅助化疗和 CTC阳性等指标,进行COX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胃癌患者术后生存的独立影响因素为肿瘤分化程度、新辅助化疗和 CTC阳性这3项指标(P值分别为0.035、0.011和<0.001,表2和表3)。
四、具身认知:嵌入在世界中的身体性心智
正如我们所见,在具身认知研究范式问世之前,反笛卡尔传统的具身性维度作为一种哲学运动,在现象学和实用主义的哲学传统中已经持续了百余年。这种对具身性维度的探索最初在现象学中作为范式出现,而后在实用主义传统中,根据分析哲学的思路对它进行诠释,并最终导致了现象学和实用主义在具身性观念上的合流。
与此同时,随着以“计算-表征”为特征的第一代认知科学的衰落,研究者们一方面注重哲学史上的思辨成果的总结和推进,另一方面敏感于认知科学经验研究的最新进展,促进了具身认知理论框架的形成。因此,具身认知的理论框架出自哲学和经验科学的交汇。它关注身体和行动在心智实现过程中深层的积极作用,主张通过涌现、离散、自组织和动力系统等新的概念工具来理解身体以及自然环境中的事物激发身体的方式[13](P.126)
其次,农产品流通环节不畅。目前东营市农产品市场数量明显不足,现有农产品市场设施不健全,信息设备缺乏,市场信息发布方式简单,服务不到位[6]。
如此一来,认知过程并不是通过对世界进行内部表征性映射而获得意义的,而是根据它们在主体应对具体环境而产生的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生成关于自身和世界的意义。因此,与第一代认知科学聚焦内部机制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不同,具身认知强调认知主体及其身体行动与具体情境之间的耦合过程。
右手指头因握笔用力而出现痉挛现象,我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摸索了半天安全带。她看我慢吞吞的样子,急性子地扭转腰身在我座位右侧扯出安全带,麻利地替我扣上。她的发梢不经意地在我脸上绕来拂去,撩得我心里头痒痒的,竟然有些心猿意马。捷达驶出津城进入澧州境内,丁香花将音响调得很低,率先打破沉寂和我聊起天来,无意间倾吐着她最近的烦心事,让我感觉戴望舒在《雨巷》里想遇而没能遇上的、像丁香似的姑娘就在眼前,只是不在雨中的小巷……
具身认知有着深刻的哲学意蕴和方法论意义,在它对西方哲学史上理智传统的反思和超越中,我们再次瞥见了身体与心智、理智与行动以及哲学与科学在断裂与碰撞中日臻趋于新的统一的曙光。当然,我们也需要警惕对认知具身性的简单化理解。将身体及其行动置于认知的核心位置,并非意味着要将身体的作用普遍化或者由此得出一劳永逸的结果,而是要在注重身体、心智和世界不可分离的同时,为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心智提供一种积极而开放的思路。
参考文献:
[1][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杨大春.理解笛卡尔心灵哲学的三个维度[J].哲学研究,2016(2).
[3]杨大春.从身体现象学到泛身体哲学[J].社会科学战线,2010(7).
[4]Merleau-Ponty,M.,Nature :Course Notes from the College de France [M].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3.
[5][德]胡塞尔.逻辑研究[M].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Merleau-Ponty,M.,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M].trans.by A.L.Donald,Routledge,2012.
[7]费多益.意志自由的心灵根基[J].中国社会科学.2015(12).
[8]Mead,G.H.,Mind ,Self and Society [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
[9]Johnson,M.,The Meaning of the Body :Aesthetic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
[10]Mead,G.H.,1904,The Relation of Psychology to Philosophy[J].Psychological Bulletin 1: 375-391.
[11]Mead,G.H.,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Meaning,in Selected Writing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
[12]林远泽.姿态、符号与角色互动——论米德社会心理学的沟通行动理论重构[J].哲学分析,2017(1).
[13]费多益.心身难题的概念羁绊[J].哲学研究,2016(10).
中图分类号: B016.9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9)09—0072—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具身哲学视域中的社会认知研究”(15CZX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何静,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心智哲学、社会认知。上海 200241
收稿日期 2019-04-30
责任编辑 尹邦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