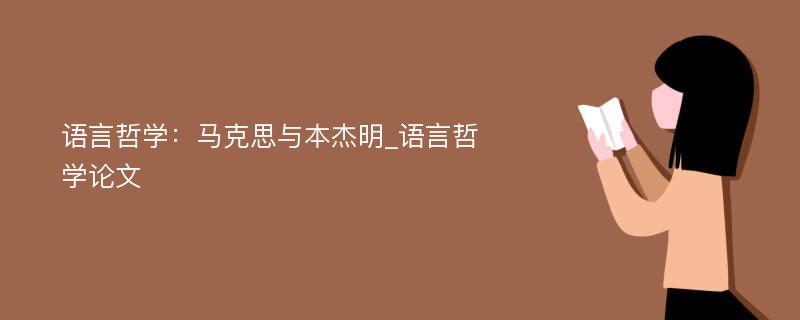
语言哲学:马克思与本雅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与本论文,哲学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马克思语言哲学的系统的梳理和探讨较为少见。但无疑这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文试图对马克思的语言哲学思想进行归纳与概括,并与本雅明较为丰富和明晰的语言哲学进行比较,以试图在马克思语言哲学的挖掘和建构方面有所推进。语言哲学这个概念在本文中更多指对语言的一种哲学思考和探讨。这与现当代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哲学有联系,但也有区别。马克思与本雅明的语言哲学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较为一致,具有可比性。 一 马克思的总体性语言哲学 马克思的语言哲学思想丰富而深邃,这里从发展线索、总体性特征、语言与意识形态及物与名的关系几方面作出概括。 其一,马克思的语言哲学思想,散见在他各个时期的著述中。他有几个阶段的研究非常重要。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之前,除了曾经在《莱茵报》时期为言论和思想自由进行辩护,马克思主要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阐述了本体论层面的语言观,揭示了物、思、行、言、交往相互融贯的总体关系。从总体性的语言哲学出发,马克思批判割裂语言与社会现实生活,反对疏离直接语言和普通语言的语言异化,马克思在1844年《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指出:“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所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我们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我们不懂得人的语言了,而且它已经无效了;它被一方看成并理解为请求,哀诉,从而被看成屈辱,所以使用它时就带有羞耻和被唾弃的感情:它被另一方理解为不知羞耻或神经错乱,从而遭到驳斥。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人类尊严的侮辱。相反,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还批判了把语言完全等同于现实的唯心主义哲学,指出唯心主义的抽象哲学语言脱离了普通语言,歪曲了现实。他反对唯心主义哲学在把思想看成独立的存在,把作为思想直接实现的语言看成是独立的。“对于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我们已经指出,思想和观念成为独立力量是个人之间私人关系和联系独立化的结果。我们已经指出,思想家和哲学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也就是使这些思想系统化,乃是分工的结果。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和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②。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之后,除了比照语言、符号来研究价值、货币,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之外——例如,比照语言的共性和差别性,阐述一般概念和个别的具体现实的差别之间的关系③——马克思更多地批判交换价值生产体系和拜物教割裂语言、符号与现实的关系,反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平等主义把语言和符号加以形式化。尽管马克思也提到资产阶级语言,但是他并没有把语言完全划归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阶级语言和专门化的语言实质上不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关系,这表现在普通的日常语言之中并且对日常语言进行了改造。因此马克思也从实践哲学的总体本体观出发,分析和批判语言的社会历史变化。马克思还在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仔细研究了语言史,分析语言变化和遗存的背后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 其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本体论层面阐述了他的语言哲学观,他认为语言是物质、意识、行动的统一体,即总体,从而创立了他的实践唯物主义语言哲学基本原则。他指出:“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④语言是思维本身的要素,是内在于思维本身之中的一部分,思维中那些可以被表现的部分就是语言;同时,语言作为感性的自然界,也是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观念化的物质。“语言,它的物质的现实存在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它在观念上充当物质。”⑤“语言,是我们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⑥语言既是物,又是意识,是物与意识的统一总体。“感性的自然界”这个概念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感知的自然界或纯粹无人的物的世界,我们需要认真解读这个概念,因为它标志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和思想创新。马克思所说的“感性的自然界”既是自然界,又是人的感觉。这个感性的世界,应该从主体的实践方面去理解。⑦在他看来,人的感性活动也属于自然,但这个感性活动是属人的能动实践;因为,人能以任何自然物为对象,能按任何尺度生产,人的感性是全面的,作为人的感性活动的人类自由劳动是可以有人的思想设计的,而且人能在劳动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后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在生产物质生活必需品的必然王国中,也存在着人的自由的可能性。由马克思各个时期的相关表述可知,“语言是感性自然界”这个命题,正是对物质与意识、物质与思维、自由与必然之间矛盾的解决。由此,(1)语言不仅与思维不可分割,而且语言本身就是思维的一部分,语言是思维中可以表现为客观存在的那部分思维;(2)语言是自然界中的“自然界的社会实现”部分;(3)语言是观念化的物质,又是人的能动感性活动——实践。正是在语言中,存在着物、意识、行动的总体上的统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语言哲学原则。他指出:“人还具有‘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与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⑧相较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英文版中关于物质、语言和意识这一段的翻译,更细致地把德文版中的“形式”一词的内在意蕴翻译出来,“从一开始,精神就受到物质负担诅咒的折磨,在这里物质以空气振动层、声音的形式,即语言的形式使精神得到表现。”⑨这里,作为精神表现的物质形式,例如声音,既是语言的表现形式,更是“意识—语言—感性自然物”这个总体的物质存在方式和表达形式。语言是思维中可以表现的部分和感性自然界,语言通过物质的某种存在方式表现出来,同时也使得思维被外在化了。语言与意识的外化是由于交往的需要,并不是意味着语言、意识先于它们的外化形式,也不意味着语言、意识与交往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外在的关系;恰恰相反,人的意识和语言本身是由于交往而被构造的,没有交往也就没有人的意识和语言。人的语言是“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存在”的、在交往中表现出来的意识,意识和语言也在交往中被构成,因而语言由于交往的需要才产生,意味着语言具有社会性质和伦理性质。意识是交往的意识,人的语言是交往的语言,意识、语言、交往三者从根源上来说,就是相互联系的。在明确了人的语言作为感性自然物—意识这个总体的一部分之后,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交谈的媒介物是指语言的外在物的存在形式。“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所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我们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⑩完整的语言,在内容方面是思维中的生命表现的要素,也是交往中所构造的“交往化的意识”,同时,语言也是能动的感性自然界即实践。 人类语言的交往性质就是语言的社会性,“观念的社会性同观念并存在语言中”(11)。人的语言与社会现实生活不能分离,它是社会现实生活的表现;语言并不是独立于现实生活的,语言是“人们的社会的产物”。(12)“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13);“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们的”(1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分析了现代语言形成的具体条件,强调语言随着交往的扩大而发展。“语言在这里被看作是类的产物……其实,在任何一种发达的现代语言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言语之所以提高为民族语言,部分是由于现成的材料所构成的语言的历史发展,如拉丁语和日耳曼语;部分是由于民族的融合和混合,如英语;部分是由于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不言而喻,在将来,个人完全会把类的这种产物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5)在《资本论》第一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人的发展、共同生活和交往导致了语言的创新,“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形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6)。 总体性的语言观,不能被理解为物、思想、语言之间是等同或者完全可以相互替代、互换的,因为马克思认为语言只是思想的要素和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都是在本体层面探讨的。这种语言本体论思想的基础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马克思所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既不同于旧的唯物主义,也不同于唯心主义,而认为自然物与精神是不可分割的。在感性自然中存在着自由,人的感性活动本身就是能动的,即在作为必然自然世界的人的感性和感性活动之中,就存在着能动实践的自由。人本身及其实践也是自然与自由的共存,这就是人的历史的起点和作为实践基础的初步的总体,所以马克思认为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物”。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革命意义上,语言是物、意识、实践、交往的总体。语言的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个人性与社会性是交织在一起的,不是二元对立的;语言是实践活动,是现实的意识,即在现实中实现着的交往意识。 其三,马克思还分析了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按他的理解,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贬义性的,即它是扭曲的现实世界的思想反映和表现。从马克思的总体本体论语言观出发来看,语言不可完全还原为意识形态,语言不能仅仅被视为意识形态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工具。马克思所认为的精神生产在语言中实现,并不意味着语言就完全属于意识形态。尽管他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7),但是,阶级并不是人类历史一开始就有的。对于资本主义时代来说,只有在资产阶级逐渐获得统治地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的买卖关系才更多地反映在语言中,并且形成了一种阶级化的语言。“资产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根据自己的语言证明重商主义的和个人的或者甚至全人类的关系是等同的,因为这种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因此像在现实中一样,在语言中买卖关系也成了所有其它关系的基础。……所有这些字眼既意味着商业关系,也意味着作为个人自身的特性和相互关系。在其他的现代语言中,情况也完全一样。”(18)恩格斯也很早就指出:“金钱使资产阶级所处的那种可耻的奴役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它的痕迹。……小商人的气质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概念来表现。”(19) 在分析商品的价值和货币形式时,马克思首先揭示了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之中,作为个人劳动社会实现的交换价值,本质上是不同商品之间的量或比例的关系,而构成交换基础的价值,则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相互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的,因而是可通约的。”(20)交换从交往中抽象出来成为纯粹的数量比例关系并发展成为交换价值生产体系,这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才能实现的。马克思认为,在现代社会之中,劳动的社会规定及其实现的生产者的关系即社会关系,变成了物之间的关系,人的关系采取了虚幻的物与物的关系。拜物教意识形态不只是精神的而且是物质的。在商品交换中劳动产品本身成了“象形文字”(21),隐含着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制度、货币制度在量化形式上对个人的社会强制。“个人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者才能存在。”(22)个人必须生产交换价值或货币,他的活动和产品才能实现社会性,而交换价值是否定和消灭所有个性和特性的一般的东西(23)。 其四,马克思还分析了物与名的关系。在阐述商品、货币、铸币和纸币符号化的根源和历史过程时,他指出了这些符号化背后的社会实质。在交换扩大和交换价值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商品的交换价值经历了从相对价值形式发展到一般等价形式,再到一般等价物即货币这种特殊的商品。“尽管商品体五花八门,商品价值都变为同名的量,即金量。”(24)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即人们劳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变成了物之间的关系。(25)他在分析原始交换的内在过程时,也指出了这种交换的数字计量本质(26):商品被二重化,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和商品陷入对立之中。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在如下意义上才是符号:商品只是耗费在商品上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货币作为可以与所有商品交换的特殊商品,本身并不能被视为一种任意性质的单纯符号,只是货币的某些职能,即纯粹的计量职能可以用单纯的符号来替代。(27)货币某些职能的符号化,是从货币计量标准命名开始的,一定重量的贵金属等量切分,在习俗和官方规定的基础上获得了它们的命名,“法定的教名”(28);并且变得与物的本性毫无关系,抽象成了纯粹的形式。“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对他还是一点不了解。同样,在镑、塔勒、法郎、杜卡特等货币名称上,价值关系的任何痕迹都消失了。由于货币名称既表示商品价值,同时又表示某一金属重量即货币标准的等分,对这些神秘记号的秘密含义的了解就更加混乱了。另一方面,价值和商品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物体不同,必然发展为这种没有概念的物的而又纯粹是社会的形式。价格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因此,商品同称为它的价格的那个货币量等价,不过是同义反复。”(29)马克思还分析了金的名称和实体、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在流通中的分离过程:铸币成了法定金属含量的象征,铸币的金子成了金本身的假象。“货币的铸币名称离开了货币的实体,而存在于实体之外,存在于没有价值的纸片上。”(30)货币本身并非是单纯的符号,只是它的某些职能比如计量职能可以符号化。交换价值就是这样发展的,当纸币成为金或货币符号时,只有货币的象征就够了。最终纸币成了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31)“这个金量则由纸象征地可感觉地体现出来。纸币只有代表金量,才称为价值符号。……金可以用它本身的没有任何价值的符号来代替……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32)。 总之,马克思反对物与名称的分裂,特别是反对名称脱离和掩盖与其交织在一起的社会生活现实。马克思对交换价值体系、货币符号化的批判,运用了他的语言哲学思想,这一批判是对语词和符号彻底形式化、脱离其与物的关系的批判。商品成为符号,商品交换价值变成同名的量,货币计量标准被冠以法定的命名,使得名称掩盖了价值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内涵,物的名称完全外在于物的本性。“商品就其本身来说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限制的。它们的共同语言是价格”(33)。 马克思的语言哲学思想在很多方面与当代本雅明的思想有不少可资比较的地方。 二 本雅明:多样化语言与可沟通性 本雅明的语言哲学思想形成于1916年的《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在《德国悲苦剧的起源》中被用于文学理论,(34)并且成为他后来历史哲学思想的基础。在他的另外一些著述中也论及了语言哲学问题,例如《未来哲学纲要》(1918)、《语言与逻辑》(1921)、《译者的任务》(1921)、《简历》(1925)、《反思洪堡》(1925)。由于马克思的语言哲学思想主要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而这两部著作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发现的,本雅明在1916年还不可能知道马克思的相关具体论述,因而本雅明的思考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思想传统中具有很高的独创性。 一定角度看,马克思的语言哲学思想与洪堡的语言哲学有密切的联系,比如重视语言与思想的统一,语言是活动,而本雅明的语言观也深受德国语言哲学思想传统的影响,例如他强调洪堡看到了词是语言的最重要成分。当然,他在分析洪堡的语言思想时,借助神话学研究中的“语言魔力”,批评洪堡把语言限制在黑格尔的客观精神之内,没能看透语言的诗性方面。本雅明还深受哈曼的影响,在哈曼的著作中清晰可见本雅明语言哲学思想的来源。与康德、赫尔德、歌德同时代的哈曼,激烈地批判康德的哲学及其启蒙思想,他认为康德的形而上学经验概念仅仅局限于数学,“把我们经验知识的所有词语标志和言语记号都变成理想状态的图形符号和典范模式”(35)。哈曼还主张经验、思想与物构成共通体(36),反对康德的纯粹形式,认为康德割裂了经验和材料、经验和知觉。歌德在自传中这样谈到哈曼反对理性抽象和直观:“因为语言要说明一些情况,就必须分离,必须分散成各个部分。人们在谈话时,有时会片面一些。没有任何消息的传播,知识的传授不是分散进行的。哈曼任何时候都非常反对这种分离,正如他在统一中感受、猜想、思考,同样也如此说……他要把握各种因素;自然与精神暗地里相碰时的最深刻最隐秘的直观。”(37)哈曼在批判赫尔德关于语言起源于知性的思想时,反对启蒙时代的孔狄亚克(人的语言起源于需要、动作语言)、卢梭(人的语言起源于情感)、赫尔德的语言起源论割裂人的语言与自然语言,强调哲学的语言只是人类头脑中思想的言说。他认为人的语言源于自然的启示,人的语言、自然物的语言、上帝的语言之间有可沟通性,“自然的每一种现象都是一句话,是一个标志、象征和一种新的、秘密的、不能言说的信仰凭据,但是更内在的上帝全能与全智的合一、宣告及联结。所有的,所有的人类一开始听到的东西,用眼睛看到的东西、察看到的东西,用手触到的东西,都是一种活着的话语;因为上帝就是话语。由于这种在口中,在心中的话语,语言的起源是如此的自然,如此亲切,如此轻松,就像孩子的游戏”(38)。 现象学也影响了本雅明的语言哲学思想。胡塞尔提出回到事物本身,力图克服“是”与“应是”之间的差别,更广泛地整合经验,提供超越启蒙的、包容各个领域的哲学理论概念。(39)本雅明试图改造哲学,解放启蒙所排斥的精神分析学、宗教信仰的经验。他参照现象学和浪漫主义,重新整合经验,尤其是把机械的经验、艺术经验、历史经验与宗教经验在新的知识概念下整合起来。他的新知识概念不是康德意义上的,而是全新的,因为作为知识对象的经验基础已经被拓宽了。 正是在哈曼的影响下,本雅明形成了思、言、行、物、神可沟通的语言哲学思想,批判由孔狄亚克、赫尔德和洪堡等人孤立地抬高的人的语言,反对索绪尔开创的现代形式主义语言观。他比哈曼更进一步指出:人的判断语言是建立在主观意志上的善恶语言,即命题语言和间接的语言,与总体上可沟通的、神的命名语言、物的语言、人的命名语言相背离,是“堕落的语言”。在现代语言观中,命名语言、名称语言不再是整体性和永恒的真理,语言和符号具有时间性和连续性,名称和符号成为任意的、人为约定和设定的,仅仅是工具和标记,词、物、思想之间的联系被割断,而人的语言整体被主观地理解为可以把握住一切,因而从日常语言改造可以制造出更一般的哲学概念语言,使得人的语言彻底成为透明的、工具性的,能够绝对把握住世界的概念本质,或者设计出完全独立的数学语言、计算语言、形式语言、符号语言、人工语言、逻辑语言,克服词语多义性,从而让准确而合逻辑的思想得到交流,净化古老的人类经验。(40) 本雅明对语言演变和分裂的研究,早于福柯系谱学、伽达默尔解释学对语言演变史的研究和现代语言学的批判;在本雅明之后,福柯、伽达默尔也主张语言与更完整经验的直接联系,重视词语,批评形式化命题语言的独立性和符号自主论。 在广义语言概念的本体论层面上,本雅明通过如下几个重要概念和命题,阐述了他对物、语言、思想、行动之间可沟通的“整体(an undivided whole)”关系。 (1)人的语言。人类精神生活的任何表达都可以理解为语言,语言内在于所有人类思想的表达,词语交流是人类语言的一种特殊情况。 (2)物的语言。任何自然物都以某种方式参与语言,事物本身就是语言,正如哈曼所说:“每个自然现象都是语词。”(41)物的语言表现和交流其精神内容、传达思想。没有与语言无关的事物。 (3)表达、表现即语言。语言即思想,但不是所有思想都是语言。语言即事物,即事物的思想存在;语言是思想实体中能传达的那些思想实体(语言即思想,但语言是思想的一部分)。所以语言传达思想,也就是语言传达和表现语言自身,也可以说,语言传达语言本身。思想是“有等级的”,并不是所有思想都能交流和表现。语言在事物中并没有完全传达,因为,无论是物的语言还是人的语言都是有局限性的,是有限的语言。 (4)人的命名语言。人的真正语言是命名语言,就是为事物命名。人通过名称、词语与事物联系起来,人通过命名实现物、整体、精神之间的可沟通性和交流性。本雅明理解的命名语言即真正的名称和词语,本身包含着没有被抽象化的、广泛的、直接经验和事物的本质,或者说,词语就是事物和精神,词与物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两者相似基础上的(如福柯所理解的建立在类推和相似性基础上的符号和透明符号)。(42)命名语言在柏拉图的《克拉底鲁》中就曾经被讨论过,其中提到名称就是事物,正确的名称是事物的性质,与它们所表示的事物是相同的,名称属于物的存在,而不是人为约定的。语词与其表达的词义或物有本质的必然联系,而不是约定的。维柯曾说,词对于希腊人来说指的是实物,在古希腊语中“名称”与“性质”意义相同,“字母”指印象和形状的范本,“词源”这个词的本意就是“真话”。福柯和伽达默尔都提到这种观点是基于词与物的相似性,而卡西尔在解释原始的语词时说,名与实之间有内在联系,名称是对象的实质,符号形式不是模仿之物,而是实在的器官,语词具有魔力。但是本雅明的命名语言概念主要不是来自柏拉图的对话录,而是源于宗教。 (5)上帝之言、纯粹的语言和翻译。本雅明借用《圣经》创世论神话对“整体”、“创造”和“交流”进行了阐释,把上帝创造性的语言称为神的命名语言。在这种语言中,言、物、思、行、创造、神的知识完全是相同的。本雅明认为神性词语是无限的,即无条件和绝对的,因而是“纯粹的”。维柯也曾经说,拉丁人也把言词看成与确实、确定同义的。神的智慧即语词;神的言(词)是绝对真实和完美的,词、真理、生成与创造是互相转化的。上帝让人为动物命名,动物接受人的命名欢快地跑开,不过是表明人参与了神圣无限的创造性词语,神、人、物之间可以互相沟通,人的词语传达了整体的共性。本雅明认为,神话把词语误认为事物的本质,实际上,事物本身并没有词语,事物是神的词语和自然无声的词语。人的判断语言、善恶语言、道德语言,即从伊甸园堕落开始的主观化语言,放弃了名称,就动摇了语言的基础,破坏了词语的纯粹性,因而也就分离了整体的交流性,陷入抽象性和间接性;人的判断语言形成之后,人乱用名称,导致自然不可传达,陷入悲恸之中,人的语言也因此变得平淡无奇并且失去表达力。本雅明不过是借助了神圣语言的神话来讨论语言哲学问题,因为他在讨论了上帝之言和人的语言堕落之后,仍然讨论翻译的本质问题,即多样化的人的语言的交流性问题。他认为,翻译的功能不过是让多样化的、不完善的、有限的、多元的人类语言在流动中互补、协调和聚合,以便重新获得圆满的纯粹语言,“语言间一切超历史的亲缘性都包括这一点:在作为整体的每一种语言中,所指的事物都是同一个。然而,这同一个事物却不是单独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而只能借助语言间相互补充的总体意念(intention):纯语言。外语中的所有个体因素——词语,句子,联想——是互相排斥的,但这些语言的意念却是互补的。”(43)这个纯粹语言不过是总体意念,也就是说,本雅明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交流和创造。这种整体可沟通的思想也体现在他对费希特的批评和对浪漫主义代表人物施莱格尔的赞同之中:反思不能达到概念的总体,而能追求美和无限。 (6)概念、词、真理、图像和文字。本雅明主张整体以及物、思、言的可沟通性,认为真理是世界的完美状态,同时真理也是多样性的,不同真理之间存在着和谐(如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它们共同构成了星座,发挥一种系统化的功能。在他看来,每个词语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完整的真理,而且这个完整的真理就是柏拉图用“理念”所谈论的神圣语词,真理即神圣语词和名称。“理念是语言的东西,观念是词语本质中的符号(象征)成分。在语词已经变得残破的经验知觉中,除了他们多少有些被隐藏之外,符号的方面,显而易见的东西,它们还具有世俗的含义。哲学家的任务是通过表现来恢复语词的符号这一首要特征,与外部指向的交流相反,在符号中理念达到自我意识。因为哲学家不能以启示的调子说话,这只能通过在记忆中回忆知觉的原初形式。”(44)每个神圣语词都是一个整体,神圣语词或名称包含着完整的真理。本雅明在1921年的《语言与逻辑》中就引用过赫尔曼·君特(Hermann Güntert)的相同说法:“柏拉图的理念基本上是神化的词语和词语的概念。”(45)无疑他接受君特的这个说法。本雅明把词语比喻为每块闪着光彩的马赛克,他并没有止步于柏拉图。他进一步指出,真正的哲学之父是逐出伊甸园之前说着神圣命名语言(词)的亚当,即使柏拉图哲学的理念,也被看成受到了原初词语的启示,而人的哲学概念是用来进行认识而非表达的,只是认知的、间接的和占有性的,认知的对象还不等于真理。真理和理念是世界的完美状态。这种整体论和多元论合一的语言哲学也延伸到对文字的理解,他认为话语与图像、语言和文字在语言中能够统一起来,因为创造即显示、即图像,图像也是给出真理,与神圣命名和神圣词语是不可分割的。他赞同约翰·威廉·李特的观点:“话语和文字就其起源而言是合一的……整个创始的语言都是语言,而且名副其实地从话语中创造出来……但是这样的话语……都是与字母不可分割的。……文字不是臣仆,在阅读的时候它不会像残渣一样脱落。”(46)本雅明的语言哲学既是批判性的又是历史的,在他看来,主观语言和知识遗忘了原初的真理词语和名称,导致人类语言和名称失去了与整体的联系,人类语言和经验被破碎化了。他认为对于堕落的语言和经验,仍然可以辩证地看,因为每个碎片中包含着与整体联系的可能性,有待被救赎——即回复到命名语言之中。这样的思想逐渐发展并体现在他的历史哲学之中。 (7)法律暴力、神话暴力、神圣暴力和历史时间意识。在本雅明的思想中,神的暴力不过是纯粹的整体性的救赎,是绝对交流性的恢复,而并不受单纯自然必然性和偶然的主观性的控制。按马克思的理解,资本主义及其之前的历史不过是自然史,人受制于盲目的自然必然性控制。在本雅明这里,法律是阶级斗争时代的产物,阶级斗争的存在不过是人类处于自然史阶段才有的,所以法律与神话一样,根本上受制于盲目性和自然命运(自然必然性)。对于神圣暴力这个概念来说,并非如齐泽克所说的“愤怒的直接反应”(本雅明认为直接暴力与法律暴力是同一的),而是作为“纯粹手段”,正如“纯粹语言”一样,其存在是为了恢复整体的可沟通性,消灭阶级、法律和国家,从而根除政治暴力。本雅明甚至认为,教育是独立于法律之外的神圣暴力,神圣暴力是救赎灵魂的。本雅明关于整体、直接的可沟通性、法律即神话的思想,受到德里达的批评。即使本雅明所言的弥赛亚革命是消除暴力的暴力,并且会抵抗革命胜利后产生的新的压迫,德里达还是认为,本雅明的全部思想中缺乏间接性和中介性,尤其是法律的正义是不能放弃的。哈贝马斯则辩护说,本雅明是从可沟通性出发提出“纯粹手段”的政治的,这个手段始终与没有暴力的整体可沟通性相联系,从而使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区分开来。(47)本雅明的可沟通性的整体概念也存在于他的历史时间概念阐释之中,他反对的是同质、空洞、连续进步的历史观,而他所说的弥赛亚历史意识,主张过去包含着对未来的希望,过去面临着被遗忘的危险,失败者的过去会被胜利者用连续进步的历史观变成碎片堆积的废墟,因此过去是要被救赎的;未来也不是连续进步历史观的未来,而是每个瞬间都可能打断线性进步历史观,消除进步论的未来。未来是结束“现在”,开启不同的历史,而不是海德格尔的“到时”;未来在过去,但是可能被故意遗忘,过去的未来需要救赎,而救赎来自永恒随时介入连续的现在并且结束现在。在他看来,创造新的历史如同在语言多样性基础上建立“世界语”,不是把历史碎片变成废墟,而是恢复可沟通性,创造新的历史。 本雅明的语言哲学思想较早地(主要在1916年著作中表达出来)批判了形式主义的二元语言观,借助神学语言学传统,把语言的本性看成创造、行动和显现。特别是,本雅明与海德格尔不同,他不是把存在(Being)或事件(event)看成线索和遮蔽着显现、涌现,而是看成哲学无法彻底捕捉到的非时间性真理和独立于现象的完整纯洁的“美的理念”,它涉及现象的整一和总体,他聚集现象而不是从现象中进行抽象,它决定现实而不是意图实现自己于现实之中。最重要的是,本雅明强调碎片中的理想应该拯救,而不是完全超越一般的日常生活,从非本真存在中摆脱出来,或者摆脱主观理性的“格式塔”预设,而是强调完整总体的绝对优先性和完整性的救赎。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的探讨回避了修辞学和符号学,而本雅明通过克洛伊策和格雷斯的符号研究,已经注意到符号、时间、空间和意义之间的关系。 三 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本体论 马克思与本雅明从各自的角度独立提出了他们的总体性语言哲学思想,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本体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从哲学革命出发,在批判思辨哲学和旧唯物主义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实践唯物主义语言哲学总体性原则;本雅明则是借助神学语言学提出了他的整体性语言哲学,他的“纯粹语言”概念,并不是神学性质的,而是指语言的可沟通性和世界的统一性。他们都主张言、思、物、行的总体性,共同强调语言的唯物主义性质,认为物与人在实践中相互统一,人的语言是意识和思维中可表达的部分。从总体性原则出发,他们的语言哲学都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批判性,对语言的彻底形式化和空洞化(语言的堕落)都采取了批判态度,认为现代社会的计算合理化和语言抽象化把经验狭隘化了,其结果是导致真实的社会关系被掩盖和历史的废墟化;他们都主张名称与物的关系不可分割,名称蕴含着更广泛的经验。 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开创了现代哲学一样,本雅明的思想也延续了现代哲学革命的思想。与胡塞尔、伽达默尔一样,他们批评科学与道德、是与应是的分裂,力图超越二元论,回到原初经验的形成过程,发现更广泛的经验基础;并且从前逻辑经验出发,分析概念和意义的构成,重建个别与一般的联系,以克服科学在片面经验基础上所做的形式化和对意义的忘却,而语词恰恰为现象学和解释学克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准备了这种批评的视域。卡西尔也曾追溯了逻辑的形成过程,认为原初的人类语言与人局限于自身的内在世界有关,语言是神话性质的,物物不分,物我不分,语词被主观想象为与物是同一的、有魔力的,逻辑力量只是潜伏在神话语言中。这种状况必然随着人的发展而产生分化,超越仅仅依靠模模糊糊感觉想象的阶段,摆脱感性、具体、有限的状态,升华、凝聚和强化经验,上升到一般概念,从原初语言中产生逻辑语言。与卡西尔不同之处在于,本雅明不是要论证逻辑的分化及其必要性,而是要打破学科界限,拓展知识的经验基础。 马克思和本雅明反对的只是语言被彻底形式化和形式化语言的完全自主性,而不是泛泛地反对语言的形式化。语言意义的形成,一方面不能完全摆脱符号的物质性,把语言完全透明化和工具化;另一方面不能脱离广泛的经验基础。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原则。语言的生命力离不开物质性、交往和创造性实践,这在德里达运用修辞学反对形而上学、批判语言被彻底形式化和透明化中得到了体现。正如当代认知语言学走出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转而强调概念的形成离不开经验域一样,哈贝马斯也强调形式语言学无视经验分析和交往语用学。 注释: ①⑥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6页;第36页;第36页。 ②(15)(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525页;500页;第255页。 ③(11)(13)(16)(22)(23)(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6页;第112页;第482页;第487页;第203页;第107页;第91页。 ④(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308页;第30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第420页。 ⑦参见朱光潜:《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译文的商榷》,《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⑧(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81页;第72页。 ⑨转引自英格·陶伯特编:《MEGA:陶伯特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李乾坤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80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9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565~566页。 (20)(21)(24)(25)(27)(28)(29)(31)(3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09页;第91页;第115页;第92、94页;第108页;第118页;第119页;第145、148页;第148~149页。 (30)(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508页;第547页。 (34)(39)(45)Benjamin Collection,Vol.1,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423,pp.100~110,p.273. (35)(36)(38)刘新利选编:《纪念苏格拉底》,华夏出版社,2009,第210页;第203页;第178页。 (37)杨武能、刘硕良主编:《歌德文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第65页。 (40)(42)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83、500页;第49页。 (41)James C.O'Flaherty,Johann Georg Hamann,Twayne Publishers,1979,p.128. (43)陈永国、马海良主编:《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83页。 (44)Walter Benjami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trnas.by John Osborne,Verso,1998,p.36. (46)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李双志、苏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264~266页。 (47)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第256、257页。标签:语言哲学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交换价值论文; 物质与意识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本雅明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思维品质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商品货币论文; 资本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