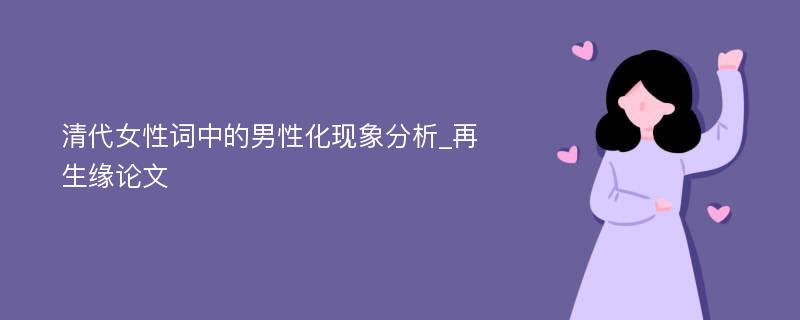
清代女性弹词中女扮男装现象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弹词论文,女扮男装论文,清代论文,现象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4)03-0021-08
有清一代,女性一直是弹词创作的主力军。乾隆以后,更出现了女性写作弹词的热潮,涌现出了陈端生、邱心如、侯芝、程惠英、孙德英等杰出的弹词女作家。在现存五百多种清代弹词中,文人的案头之作约有五十余部,其中出自女性之手的就有四十多部,占文人弹词的百分之八十多(这其中不包括无法确认作家性别之作)。弹词女作家及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其中女扮男装似乎又是一个标志性情节。女作家们通过这些“魅力无限”的文学形象,寄托了她们对女性的性别身份及社会角色的复杂情绪。当然,作为一种写作题材,这一文学现象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深远的文学创作传统,而且也是具体时空范围内的社会文化、文学思潮、审美风尚等因素的综合产物。
一、女性弹词中的女扮男装现象及其文化内涵
在小说、戏曲中,女扮男装的情节往往出现在生活常态被打破,无奈之际,女主人公只好改装为男,闯入另一个性别世界,故事也就因此有了转机,这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情节演绎的程式。清代弹词女作家们也承袭了这样一个构思模式,但她们的作品更注重表现主人公改装后的生活,特别是因性别脚色的反串而产生的各种尴尬与矛盾。在阅读时我们发现,形形色色的男装倩影中大都重叠着女作家们的身影,较强的“自传”色彩使我们在分析时不得不时时联系作者的身世。作品中女扮男装的出路,归纳起来,大体可以有如下三种:
1.终身不复女装:以《金鱼缘》中的反叛者钱淑蓉为典型。
“夫妇为五伦之始”。在伦理社会中,婚姻是最鲜明的显示社会性别角色的一组关系。封建婚姻完全把女子定义在一个卑微、恭顺的奴隶位置上,在家庭中,“夫者天也,一生须守一敬字”[1](三集卷二,p.14)。这使得许多未婚女子对未来的婚姻生活视若畏途,甚至立誓终身不嫁。如《金鱼缘》的作者孙德英,自幼“天资明敏,迥与人异……清净潇洒,颇有林下之风。”这样一位清丽女子,却有“不愿适字之意……每为论及婚嫁,……惟怏怏不乐”。尊长“不得已,允遂其志”[2](钮如媛《金鱼缘·序》)。孙德英的人生经历,影响到了她笔下人物的归宿。在《金鱼缘》中,女扮男装的主人公钱淑容化名竺云屏,中状元,为太子师,终身不复女装。她不愿恢复本身的原因,足可以代表作者的心声:
(云屏云)世间最苦无如女,诸事依人难自专。命好者,夫倡妇随情好合,生男育女乐欣然。也无非,操劳白首因人累,再不能,一刻心闲与意闲。命薄者,凤寡鸾孤悲只影,只落得,花荫月夕珠泪涟。……悟彻尘缘皆若此,儿因此,了无情爱系心牵。[2](第十九回)
除了表达对婚姻角色的绝望外,作者还有个“大旨”,就是“欲伸世上闺娃志”:
古来闺阁裙钗辈,也多有,磊落襟怀胜过男。干一番,惊天动地奇人事,做一个,出类超群巾帼郎。[2](第一回)
钱淑容,才华冠世、志愿孤高;秦梦娥,英雄绝顶、才智兼全……若辈尽属女中巾帼,并非七尺须眉,谚云:有智妇人赛过男子,信非诬也……。[2](第二十回)
为了证明“有智妇人赛过男子”,作者偏偏要塑造一个“假丈夫”,不仅在智慧、才能上胜过书中所有的男子,而且为官做宰,娶妻生子(领养),也如男子一样养老送终、支撑门户。钱淑蓉的归宿,透露了作者对女性现实处境与未来命运的看法。在作者看来,女人要避免个人悲剧,最现实的途径就是逃避婚姻角色;而女人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则必须承担起男人的社会角色与责任。
2.“开门雌伏不能堪”——孟丽君群像。
孟丽君是陈端生所著《再生缘》中的主人公。为了“避世全贞”而易装出逃,离家前,曾留下“愿教螺髻换乌纱”的豪言壮语。后来果然连中三元,位及人臣。她的绝世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最高的认可,从此不愿恢复女装。当父母逼她复装嫁人时,她表白道:
丽君虽则是裙钗,现在而今立赤阶。浩荡深恩重万代,惟我爵位列三台。何须必要归夫婿,就是这,正室王妃岂我怀?况有那,宰臣官俸嵬嵬在,自身可养自身来。[3](第四十四回)
在她看来,婚姻的实质就是女子依附男子,寻一个终身着落。自己既然功成名就、经济独立,就不需再多此一举了。况且随着眼界日益开阔,阅历逐渐丰富,她对封建纲常加于妇女的那一套也颇有些悟出内里实质,不再似未改装前那样虔诚遵奉了。她不但在金殿扯了未婚夫的奏章、反唇相讥父亲惧内,而且还将欲挟圣旨逼她现身的尊长、夫婿派了一个亵渎师尊、戏弄大臣的罪名。她的行为已经表明了“她是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挟爵位功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从父母,挟师道而不认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挟孝弟力行而犯上作乱。”[4]
陈端生出身杭州望族,祖陈兆伦、父陈玉敦都是朝廷命官,母亲汪氏亦出身书香门第。端生的绝世才华与书中的孟丽君差可比肩,未出阁时即完成了《再生缘》的前十六卷,一时间“浙江一省遍相传”。作者对此也颇自豪,称“反胜那沦落文章不值钱”[3](十七卷卷首)。出阁后,丈夫因科举作弊被充军,而自己空有满腹才华却无处施展,她切身感受到了现实对女子才能的压抑。因此,在处理更装的情节时,她没有象别的作家那样让主人公摄于皇权、夫权的淫威而束手就范,而是负隅顽抗到底,坚持“开门雌伏不能堪”,最后竟“口吐鲜血一命危”[3](第六十五回、第六十六回)!
陈端生由于愁病交加,《再生缘》未竟而卒,孟丽君也就“生死未卜”、“不知所终”。后续者大多不得要领(如侯芝的《金闺杰》、梁德绳的《再生缘》后三回),大大歪曲了作者本意和人物性格(详后)。而在众多的仿作之中,也只有汪藕裳的《子虚记》接续了陈端生的未竟之志,主人公赵湘仙在泄露真身后的表现俨然醉酒吐血的孟丽君。小说中,赵湘仙在行藏暴露后,坚持不脱男装,三天后,郁郁而亡。临死前与未婚夫解除了婚约,彻底否定了自己的性别角色。
在《再生缘》中,作者还借元帝之口提出“成了亲来改了妆,依旧要,天天办事进朝房”[3](第六十一回)的要求,对“女主内”的现存秩序提出了彻底颠覆的愿望。李桂玉接过了陈端生这个大胆设想,其《榴花梦》中女主角桂恒魁就是这样一位集“英主、哲后、名将、贤臣”于一身的“女中英杰,绝代枭雄”,作者在序言中论其有四大“无以加”:
一、正国家凌替之秋,草野分崩之际,彼独弃脂粉于妆台,拾衣冠于廊庙,献策金门,才魁多士,立功沙漠,武冠一军。金台授印,力图匡复之功;虎帐运筹,果遂勤王之愿,金瓯重奠,社稷复安,是古之名将,无以加也。
二、治水筑城,省刑薄敛,搜贤才于山野,退邪佞于朝堂,是古之英主,无以加也。
三、治国兼可齐家,相夫并能教子。拦车进谏,罢歌舞于通宵,避位上章,化恩波之普庆,使《螽斯》成诵,《荇菜》重歌,是,古之哲后,无以加也。
四、能匡君救母,开天王感格之心,剪佞安良,动黎庶生平之乐。是古之贤臣,无以加也。[5](《自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般的易装女子复装后,就雌伏不出了。而桂恒魁复装时,事业才刚刚开始。复装后更直接的参与国家机要政事,甚至创建自己的王国,成为女性弹词中唯一一位复装后继续发挥才干的闺阁精英。这一点,是极大限度地实现了陈端生的设想(但对“女主内”的形式还是保留着,没有做到“天天办事进朝房”,而是在后宫把持朝政),但形象内涵却没有因此而升华。特别是桂恒魁最后以逃禅的方式解脱的结局,实在不能不令人有怅然之感,从而也对孟丽君等人负隅顽抗的现实性和女子从政的现实意义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3.循规蹈矩的贤内助——姜德华模式。
既不满于现实秩序对女子才能的压抑,又对传统的思想桎梏不能自拔,挣扎于叛逆与卫道之间,并最终皈依礼教的典型是《笔生花》里的女主角姜德华。女主角这种首鼠两端的矛盾态度与作家的身世、遭遇直接有关。作者邱心如从小受的家教是“父谈《内则》书和典……母督闺工俭与勤”[6](第八回),在思想上是自觉维护女性的社会角色的。她看不惯《再生缘》中有违纲常的描写,要对其进行翻意、更调,使书中人物成为纲常典范。她评论《再生缘》兼阐释自己的创作动机云:
新刻《再生缘》一部……评遍弹词推冠首,只嫌立意负微愆。刘燕玉,终身私定三从失,怎加封,节孝夫人褒美焉?《女则》云:一行有亏诸行败,何况这,无媒而嫁岂称贤?郦保和,才容节操皆完备,政事文章各擅兼。但摘其疵何不孝,竟将那,劬劳天性一时捐。阅当金殿辞朝际,辱父欺君太觉偏。[6](第一回)
因此在小说中刻意安排了女主角改装后恪守女诫的“出格”行为,不仅处处表现出淑女的教养与矜持,就连表哥无意中碰了她的胳膊,也羞愤交加地要砍掉!复装后,不但周旋于娘家、婆家的事事非非,让老老少少都满意;而且为了讨好丈夫,竟然不惜再一次男装代夫骗娶!
在清代女性弹词中,对易装女子的出路,认同姜德华模式的作品最多,较早的有《玉钏缘》、《安邦志》三部曲、《昼锦堂记》等。此外梁德绳和侯芝在续写(改写)《再生缘》时,也不约而同地为孟丽君选择了姜德华式的结局。梁所续的《再生缘》,婚后的孟丽君成了个“循规蹈矩毫无错,宽宏大量大贤人”[3](第七十九回);而侯芝在她所改编的《金闺杰》里,则让孟丽君伏阶请罪,自认改装之荒唐,从此甘心雌伏。在《榴花梦》、《凤双飞》、《四云亭》等作品中,姜德华的影子也不同程度地叠映在那些假儿郎的身上。
二、叙事传统与社会审美思潮对女扮男装的影响
1.女扮男装的文学叙事传统。
易装,表面看来只是个着装问题,实则关系到社会的既定秩序与政治、文化的意识积淀,体现着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在古代中国,最讲究的是男女有别,不仅有“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7](p.29)的社会分工,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男女“不同巾栉”、“男女不通衣裳”(注:《礼记·曲礼》云:“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等着装方面的严格限制与规定。女扮男装或者男扮女装都被看作是有悖礼法的行为,如果再着了异性的服装闯入其生活圈子,则要触犯社会既定规则,为舆论、法律所不容。尽管如此,易装者还是代不乏人,见诸史册的也不少。如《南史》载南齐“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粗知围棋,解文义,遍游公卿,仕至扬州议曹从事。事发,明帝驱令还东。逞始作妇人服而去,叹曰:‘如此之伎,还为老妪,岂不惜哉!”[8](卷四五,p.1143)《十国春秋·前蜀》载临邛女子黄崇嘏,“居恒为男子装,游历两川”,以诗才“称乡贡进士”[9](卷四五,p.657)。这两则史料虽是历史记载,但有着浓厚的文学意味。我们不妨将之作为史传散文来读,当然亦可视之为记实小说。总之,具有了一定的文学虚构成分在内。
由历史而文学,易装行为始终是一个有“异端”色彩的题材,在史传文学中,常以奇人逸事来处理,而在文学传统中,则被以佳话形式流传。如黄崇嘏的故事就在后来的文学叙事中不断出现,金院本《春桃记》、明代徐渭的《女状元辞凰得凤》、清代才女张令仪的《乾坤图》,写的都是这个故事。而有些易装题材已经不能辨识其历史真实性,我们姑且将之看作是民间叙事。其中最有文化含量、文学意味的莫过于木兰从军的故事。(注:虽然文人笔记中常有对木兰籍贯考证之记载,如焦竑《焦氏笔乘》卷三“我朝两木兰”条载“木兰,朱氏女子,湖北黄州黄陂县北七十里,即隋之木兰县,有木兰将军冢、忠烈庙。”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亦有类似记载。但木兰故事于史无征,这里姑且将之看作民间叙事。)从汉乐府《木兰诗》“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成功作一回男儿的窃窃自喜到常香玉理直气壮地唱出“谁说女子不如男”,这中间,木兰故事已经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文学叙事,由诗歌而小说、戏曲,以致于渐成气候,至清代女性弹词作家手中,俨然作为一个渊源深厚的写作传统来继承了,其中的易装女子居然都是“木兰”派。当然,梁祝故事也是一个女扮男装的文学典范。一曲“十八相送”催生出了多少女扮男装追求自由爱情的才子佳人!但有趣的是,在清代弹词女作家们的笔下,易装闺娃们很少有步英台后尘,利用男装身份自由恋爱的。相反,她们千方百计逃避的,就是这“整日逼生和逼死”[3](六十六回)的婚姻大事!
2.文人“女性化心态”的历史积淀与文学创作思潮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的《离骚》开创了文人学士妾妇自拟的寄托传统。文人们往往将自己在仕途上的不顺利比拟为女子在婚姻中的被冷落,将怀才不遇的落寞比拟为美人迟暮的哀怨。他们的作品哀感顽艳,呈现出十足的阴柔美。这个传统在《古诗十九首》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其中的怨妇诗大多出自失意的男性文人笔下。随着唐宋科举制度的发展,落第文人队伍的不断扩大,这种女性化心态在文学上的表现愈加突出,唐诗、宋词中由男性文人写的怨妇诗、词更是不胜枚举。明清鼎革之际,文人们对那些不能力挽狂澜、救国家于危亡的男性表现了极度的鄙夷,羞于为伍的自卑感让他们转而颂扬、羡慕女性的忠贞、节烈。这个时期小说、笔记、戏曲中女胜于男的题材、事迹比比皆是。如吴伟业的《临春阁》,就是借着描写冼夫人的忠贞报国来慨叹当时的时局:“到今日呵,这样的男儿一个也不见了,倒靠着木兰征战,苦了粉将军乔镇绿珠川。”[10](《吴梅村全集》下册,p.1366)而刘廷献的《广阳杂记》中就直接以对比的形式写了大敌当前,男不如女的尴尬:黄鼎降清后,“其妻独不降,拥众数万,盘踞山中,与官兵抗,屡为其败”[11](p.14)。明末女将秦良玉应诏北上勤王,行则男装,止则女装,崇祯皇帝在召见她时曾赋诗云:“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12](p.147)从表面上看是对秦良玉的至高嘉奖,实则是对“养文臣帷幄无谋,豢武将疆场不猛”(《桃花扇·哭主》现实的彻底失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遗民情绪逐渐退出了文学叙事,但经过这一历史阶段的推波助澜,女性情结在清代士人的审美视野里更加突出了。在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里,这种“女性情结”即转化为对才女佳人的追寻。书中才子们所青睐的女性总是有着浓郁书卷气的“文人化”了的佳人,能诗会画、知书达理成为男性择偶的重要标准。如《定情人》中双星要求妻子应有“咏雪的才情,吟风的韵度”[13](第一回,p.4),而《女开科传》中的余丽卿则宣称“要作我的浑家,殊非是今世上没有的才,没有的色,方可牵丝结缡”[14](第一回,p.5)。佳人文人化的极致就是佳人的名士风度,《平山冷艳》里的才女冷绛雪、山黛简直就是着了女装的士人,其谈吐、举止浓重的头巾气、书卷气恰是作者对士人品格的自许与高扬。把对名士风度的最高追求寄托在这种理想叙事上的典范是《红楼梦》。金陵十二钗大多才情横溢,其中好男装的史湘云最具名士风范,其任情率性、旷达自然的娇憨之态令作者禁不住击掌而叹:“是真名士自风流”。可以说,这个时期小说里易妆佳人普遍的具有士人的内蕴与禀赋,她们集美貌、智慧、品德、学问于一身,实际是男性文人对自身形象的期许与翻版。才女们既具土人的品格,当然也有士人的追求。在中国,功名一直是读书人的一块心病,自然也是这些诞生于才子笔下的才女们的渴望所在。所以,几乎每一个易妆女子的首选奋斗目标都是金殿夺魁。在弹词小说中,女作家们被这一思潮潜移默化,很自觉地把塑造士人化的女子作为自己的创作追求,“愿教螺髻换乌纱”成为易装佳人实现自身价值的标志性目标。
3.社会审美意识对女扮男装题材审美倾向的影响。
人们对于女性化美男子的偏爱由来已久,先秦时的楚人就对女性化的美男子非常欣赏,《荀子·非相》云:
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比肩并起。[15](p.48)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风习甚至形成了一种贵族化的审美风尚。《世说新语·容止》一章,品评了一大批士族中的美男子。像“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荣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去。”卫玠有“璧人”之称,“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16]。到了齐梁时代,对姿容的讲究已经成为上层社会的时尚。《颜氏家训·勉学》:“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17](p.328)飘逸的魏晋风度最终随着南朝的消亡一起没落了,但这种审美习气的心理积淀却留存了下来,在与它几乎同时并存的男风爱好中继续起着主导作用。
男风现象由来已久,自先秦直至明清,一直绵延不绝,明清时期更是盛行一时。其共同的审美习惯就是欣赏男人的女人气。对“貌美如好女”的伶旦、娈童,文人狎客总是情不自禁的顾盼留情,“心窃爱之”。如《燕兰小谱》中赞姚兰官“纤腰仄步,细歌寒肩,望之绝似柔媚女郎”[18](p.36)。又如《品花宝鉴》描写小旦杜琴言:
子玉觉得鼻中一阵清香,非兰非麝,……一个已似海棠花,娇艳无比,眉目天然,一个真是天上神仙,人间绝色,以玉为骨,以月为魂,以花为情,以珠光宝气为精神。[19](第一回)
梁绍壬曾对时风做了这样的概括:“软红十丈春风酣,不重美女重美男。宛转歌喉袅金缕,美男妆成如美女。”[20](p.322)
对美男的评价,以白皙的皮肤和乌黑的眼睛为首要标志[21],“面如凝脂,眼如点漆”,便是“神仙中人”(注:《世说新语·容止》王羲之赞杜弘治云:“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社会积淀已久的审美风尚直接影响并反映到了文学写作中,在明末清初的小说、戏曲中,这样的“神仙”频频现身,而且往往大受欢迎,最具有典范意义的就是《红楼梦》中那个“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的贾宝玉,清代弹词中的男主角也是这种审美风气的产物。《再生缘》中的男主角皇甫少华“面映梨花含夜雨,眉分柳叶带烟绡。秋水冷冷生眼媚,春风淡淡上容娇。”孟丽君的母亲一眼便相中了:“若此英雄婚爱女,真称一位美东床。”而对“端严品格非凡像”[3](第一回)的另一位候选人刘魁璧则不太感兴趣,认为皇甫少华较其容貌“胜三分”。
在这种女性化审美标准的影响下,着了男装的佳人们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位美男:孟丽君男装后俨然“一位风流俊俏郎”[3](第十回),姜德华一旦青衫在身,更是“何郎赋粉言休及”、“荀令薰香步莫追”[6](第七回)。她们“混迹”于男性圈子,往往运气极佳。上至皇帝、下至同僚百官,无不爱其貌,敬其才,甚至奸臣也撇去成见,欲与之联为婚姻。像男装后的姜德华,被奸臣楚元方一眼看中,定为东床,从而为她在政治上的平步青云打下了基础。这样的情节在女性弹词中司空见惯,人们在阅读时总是将之归结为女性创作的弊端,认为是女作家们的白日梦。孰不知,文艺作品作为审美对象,一方面是一定时代、社会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时代社会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对应物,一切的想象和夸饰都是立足于现实的文化审美心态之上的。女扮男装的情节模式,更多的是弹词女作家们对时代、社会精神内核的反映。
三、才女文化对女扮男装题材写作的影响
1.才女文化与女弹词写作热潮。
明末清初以来社会上兴起了女子读书热,一些家长从有益“阃教”的角度鼓励女子读书,把这看成一种必备的“事夫之道”。认为女子“于妇职余闲,浏览坟索,讽习篇章,也因以多识故典,大启性灵,则于治家相夫课子,皆非无助”[22](卷二)。另外,清初明确禁止官员狎妓,文人穿行狭邪、与妓女诗酒唱和的风气逐渐衰退。一些士大夫便把休闲娱乐转向了家庭,外而召集幕友清谈,内而与妻妾酬和,以此为赏心乐事。一时间,人人效尤,蔚然成风。在这股风气的影响下,闺房里“一编横放两人看”[23](卷六,p.309)成为琴瑟和谐的理想图画。有女之家为了女儿“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牡丹亭·训女》),年在龆龀便让她们“依兄就读”(侯芝《金闺杰·序》)。这样的读书氛围造就了大量的闺秀诗人,如著名的随园女弟子、璧城女弟子。她们或在家庭、乡里之间结社、唱和,或将诗词结集互相交流,诗社活动一时成为文坛盛事,如清初康熙年间浙江仁和顾之琼、林以宁婆媳先后组织的蕉园诗社。
在推崇才女文化的大氛围中,女子读书、写作便成为一时时尚,认为“女人识字,便有一种儒风”[24](p.337)。出现了许多自幼嗜书若痴的女才子,无锡女诗人杨蕴辉,“于诗书文字,尤宵研炬膏,晨依朗旭,勤劬问学,无异男子也”[25](卷二二,p.15952)。孙德英“凡经史诸子,以及异书杂传,无不博览记诵”[2](钮如媛《金鱼缘·序》)。邱心如“喜读父书翻古史,更从母教嗜闲篇”[6](第一回);陈端生则“姊妹连床听夜雨,椿萱分韵课诗篇”[3](十七卷卷首)。日常的文墨熏陶使她们不约而同地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她们不但写诗,(注:清代弹词女作家大多有自己的诗集,如陈瑞生的《绘影阁》、郑澹若的《绿饮楼集》、周颖芳的《砚香阁集》、程惠英的《北窗吟稿》等。)而且进行弹词创作。出现了陈端生、邱心如、郑澹若、周颖芳、程惠英等一大批弹词女作家。弹词的韵文体形式使这些“有文才的妇女们便得到了一个发泄她们的诗才和牢骚不平的机会了。她们也动手写作自己所要写的弹词,她们把自己的心怀、把自己的困苦、把自己的理想,都寄托在弹词里了”[26](p.353)。几乎每一部弹词都是思无窒碍、洋洋洒洒的长篇巨著。
2.才女士人化与女扮男装主题的写作。
在才女文化的氛围中,产生了许多博通经史的女才子,她们的聪明才智往往受到“精神长者”——父亲的类似“身有八男,不易一女”(注:此乃清代才女王端淑父语。王“意气荦荦,尤长史学。”见陈维菘《妇人集》。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明末清初桐城方梦仪,“敏而好学,九岁能文”,父亲“抚爱笃甚,常目之而叹曰,有此子为快,惜是女。”见《纫兰阁诗集·序》。)的欣赏与赞誉。在这种男性文化的鼓励、熏陶下,不自觉地养成了功名事业心,“以身列巾帼为恨”者大有人在。但身困闺阁的现实成了实现这种雄心抱负的最大障碍,无奈之际,她们只得将满腔的热情转诸于“纸上谈兵”。用作品中女扮男装的人物来做自己的画图小影,稍解其埋没闺阁的冲天之怨,清代才女王筠即是这样一个典型。筠字松坪,为乾隆进士王元常女,“幼嗜书,以身列巾帼为恨”[27](p.245)。曾作《繁华梦》传奇以自传。作者在《繁华梦传奇·序》中抒发了自己生为女子的遗憾:“闺阁沉埋十数年……木兰崇嘏事无缘。玉堂金马生无分,好把心事付梦诠。”乾嘉时期女词人吴藻也曾经写作杂剧《乔影》,并因此而将自己的小照绘为文士装束,以寓速变男儿之意。
在许多闺阁女子“恨生不为男”的同时,以“闺阁而有林下风者”也不少,出现了士人化才女。如清初的女诗人黄媛介因家被蹂躏,只得在江浙一带过流亡生活。期间,以“卖诗画自活,稍给便不肯作”[1](卷二,p.250)。黄与当时文人名士、闺阁名媛多有交往,王世祯、吴梅村、柳如是、祁彪佳次女祁德琼等男女诗人皆为其诗友。而安徽当涂才女吴岩子“其诗多玉树铜驼之感”,“吐词温文,出入经史,相对如士大夫”(魏禧《青山集·序》)(注:《青山集》已佚,后有梁溪邹斯漪刻《吴岩子诗》。此处参考马福清著《文坛佳秀——妇女作家群》,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5~57页。)。在这种才女士人化的风气中,我们的弹词女作家也深受影响,如郑澹若“补天有愿”(《梦影缘》序言),其女周颖芳“平生爱慕古名臣”(李枢《精忠传·序》)、陈梅君“夙负唐窦后‘恨生不为男子’之志”(林肖蜦《文藻遗芬集·跋》)、李桂玉“于唐史大有感慨”(陈俦松《榴花梦·序》)……,一些女作家不但“读万卷书”,而且还“行万里路”,与士子文人一样有着广泛的游历经验。《四云亭》作者彭靓娟“幼侍蜀东,长游燕北”“从郎万里,戍鼓惊霜”(《四云亭·自序》);李桂玉“生于西垅,长适南湘”(《榴花梦·陈序》),最后落脚于福建;陈端生“恃父宦游游且壮”(《再生缘》十七卷卷首),广历北京、云南、山东等地。走出闺阁,领略大江南北的无限风光,这些胸藏万卷书的女才子本身已经有了十足的“士人”气质。她们的胸襟抱负大都寄托在弹词创作上,弹词作品中那些“出语吐辞,英华蕴藉”(《凤双飞·序》)的风流才女之所以能“扬眉吐气装男子,举止全然非女流”(《再生缘》第十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本身的士人气质。才女作家们用她们的如花妙笔表达了共同愿望:拒绝自己的性别角色,走出闺阁,成为男人。
由男性文人抒发怨艾、逃避现实发端形成的对阴柔之美的写作传统、审美思潮,到了清代,被女作家继承过来,成了她们反抗传统、反对现存秩序的最佳表达方式,并且出人意料地颠倒了乾坤,竟然真的塑造出了领袖群雄的假男儿。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戏剧情节”,而这个情节只有在女性手中才会产生令人震撼的完美。从这个角度上说,文学也是有性别的。
收稿日期:2004-0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