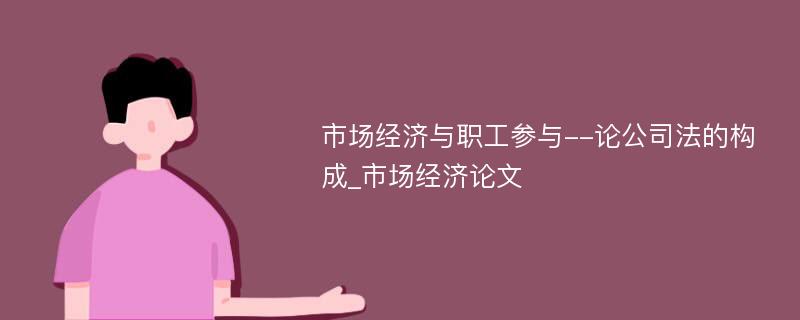
市场经济与职工参与——试论公司法学的构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学论文,市场经济论文,试论论文,职工论文,公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奥岛孝康 白国栋译)
一 问题的所在--市场参与成本的观念
目前日本在经济国际化的旋涡中,应该说正处在迎接战后最严峻的考验的时期。不用说这就是,1989年开始的日美结构性问题协议及其事后经验,进而在1993年开始的日美一揽子协议中,美国政府又接连不断地提出了改善经济关系的要求。尤其,在日美结构性问题协议中,美国对日本市场的闭锁性的指责,以及在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中开放市场的要求,已为众所周知。当然,日美两国间不仅在各种各样问题上具有不同的认识,而且在美国方面的指责中也不乏失误之处。但是无须赘言,就大局来看,在美国方面的指责中,也有不少是日本难以否认的可以称之为多年积弊的问题,现在日本政府也正以禁止垄断法的修改及其运用的强化为中心苦求对策[(1)]。
尤其,经济国际化的问题,不仅仅是日本一个国家的问题,欧洲共同体的市场一体化(1992年)以至单一市场的形成等等,可以说这已是如今全世界的潮流。不得不指出,各国若要抗拒这种经济国际化的动向,去设计各国自己应有的经济模式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各国无论主观态度如何,都不得不致力于市场参入条件的改善。既然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则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换而言之,为了加入到市场经济中去,支付一定的入场费(参与成本)也是当然的了。
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因此作为参入市场的代价而被要求一定的负担,正所谓“有利所得,必有成本”。这就是说,既然参入市场则不能允许“乘车不买票”,可以说这也正是日美结构性问题协议中美国方面主张的基调。
在探讨伴随着经济的国际化的发展,需要对各国法律进行调整这一课题时,市场参与的成本问题成为一条有效线索[(2)]。本文试图以此为线索,并以职工参与为题作一探讨[(3)]。
二 市场经济与职工参与--作为社会费用的职工参与
企业的社会费用之所以引起人们注意,起因于企业的社会责任的社会化问题,具体地说,是在围绕着公害企业的防止公害费用的负担的讨论中出现的[(4)]。所谓市场经济,意味着自由企业体制,也可以说是以竞争为动力的经济体制,这里当然是以有秩序的市场行为为前提。进而言之,为实现有秩序的市场行为,参与市场的各个企业的“恰当的经营”则成为其前提[(5)]。在此之上,作为市场参与的资格,要求企业为了确保其恰当的经营,而建立自律的监督体制。
但是,众所周知,欧洲共同体为了调整各成员国之间的公司法,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特别是欧洲共同体在1975年关于各成员国职工参与的详细的调查报告书公布以来[(6)],虽然就职工的经营参与在公司法领域进行了调整,但至今尚未得出最终的结论[(7)]。不言而喻,这是因为各成员国的参与环境各不相同。例如,因为有象德国那样富有劳资双方共同决定经验的国家,也有象撒切尔为首相时的英国那样对所谓参与负担持否定态度的国家并存之故,所以这样的调整就无法不遇到困难了。但是无论怎样困难,既然以单一市场为目标,那么对这种调整的回避则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对于承担参与成本的国家来说,难免产生所谓“资本逃避”的现象。同纳税大国产生的便宜船籍国(巴拿马)一样,根据职工参与方式的不同的选择,亦难免产生便宜总公司所在地的问题,也就是说,十分可能会产生总公司从参与负担大的国家(比如说德国)转移到参与负担小的国家(比如说英国)的这种严重的事态。因此,承担着共同决定法重负的德国,对该问题的调整的强硬主张,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但是,尽管如此,在欧洲共同体诸国中,虽然参与的方式和程度不同,可以说职工参与现在已正成为社会体制的一部分。欧洲共同体作为单一市场的完成度越高,为了进入其域内的市场,对于域外诸国的公司来说参与成本就越不可避免。与此相反,职工参与尚未成为社会体制的国家,比如美国又如何呢?在日美结构性问题协议中,美国强烈要求日本导入“公司外董事制度”,从某种意味来说,可以认为是要求负担参与成本[(8)]。其结果,日本在平成5年(1993年)的商法修改中,新增了“公司外监事制度”条款,作为对其要求的对应。
可见,市场参与需要支付其相应的代价,这可以认为是一种社会的费用。因此,可以说在美国它是作为股份上市资格的公司外董事制度,在欧洲共同体则是职工的经营参与。
三 从理念论看职工参与公司机关的构成和参与的诸形态
职工的经营参与绝不单单是公司机关构成上的技法。它是欧洲大陆传统思想孕育出的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对欧洲共同体来说,更是如此[(9)]。
在此背景下,在股份公司如何建立自律的监督制度的问题上,德国法规定的指挥和监督的分离即二元制机关的构成虽然在理论上被评价为最佳的制度,但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之所以没有对其表示好感,其最大理由就在于监事会的劳资同数决定制(即所谓共同决定制)[(10)]。当然,职工参与的形态并不只限于德国法型的共同决定方式。至于应该采用何种参与方式,毕竟是属于各国立法政策的问题。但是,如若采用二元制的机关体制,则更容易导入共同决定这种参与方式,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在指挥与监督未分离的所谓一元制机关构成(美国法模式)的体制下,职工参与可以采用哪一种方式呢?还有,指挥与监督作为并列机关而构成的日本,又如何呢[(11)]?
职工对公司机关的参与形态,如果以欧洲共同体绿皮书为主要依据作一分类,则可以得出下面四种方式。即(一)所有参与(职工持股制度即股东大会的参与),(二)经营参与之一(一元制机关体制下的董事会的参与)、(三)经营参与之二(二元制机关体制下的监事会参与)、(四)信息参与(劳资协议机关参与)(此外,虽然不是机关的参与方式,还有利益参与的方式,即法国特有的参与方式)[(12)]。但是,就法理而言,既然公司的共同所有者虽然仅仅在观念上非股东莫属,那么,对所有参与的方式的探讨,如只限于职工持股制度尚无疑义(在这个意义上,该参与方式甚至在美国也得以普及),但若涉及到经营参与,则不无疑问。这是因为,职工不管是作为董事还是监事,都不会成为代表股东利益的存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够参与董事会或监事会)。那么,劳资协议机关参与又如何呢?劳资协议制是职工对经营方针、经营计划以及班组组织在信息上的参与制度,现在,不仅在日本,在世界各国都广泛得以普及,甚至已成为社会体制的一部分。
由此来看,现在在世界各国业已社会制度化,并且在法理上也几乎无可质疑的所有参与(职工持股制度)和信息参与(劳资协议机关参与)的参与方式,即便在公司立法上也值得给与充分的考虑。如果是这样,那么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将劳资协议机关作为公司的第四个机关的思路,不仅在立法政策上并非不可能,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也是极富有说服力的。而且,所有参与和信息参与并不与现在的公司机关的构成直接联系,因此在职工参与的实现上,也可以视之为抵抗较小的参与方式[(13)]。
四 从方法论看职工参与--参与的任意性和立法政策
日本公司支配的现状,在理论上无论基于何种观点,称之为管理职工的支配(薪金阶层经营者的支配)并无大过。现实既然如此,那么,以现实为依据,对职工参与在立法论上的出发点作一番探讨也是十分必要的。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如何论述股份公司经营的理念,完成无视职工存在的公司运营都是不可能成立的。的确,尽管如今股东大会的存在已如形骸,但在立法上尚不能找出可以取而代之的机关。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不能否定与职工基本上仍处于对立的地位,但是,完全无视职工存在的公司运营也是不可能成立的。岂止如此,如今在日本,如何确保由薪金阶层组成的高级管理人--董事的有效监督的问题,已成为立法的一大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至今仍应严格遵循Sinzheimer的所谓劳动从属论吗?的确,一方面在美国可以看到以团体交涉为中心的劳资“武装和平”(劳资对立)思想的俨然存在,但另一方面,在欧洲(特别是欧洲共同体国家)以劳资协议为中心的“非武装和平”(劳资协调)思想也根深蒂固地存在。因此,应该说通过经营参与使职工从“企业的对立者”转向“企业的协作者”,这在法思想上也具有充分的根据。与把劳资对立绝对化的美国式的对抗的民主主义论相反,这也就是把这种对立相对化的欧洲型的参与的民主主义论[(14)]。
问题在于“参与”的概念及其法思想。无须赘言,参与是民主主义的基础概念,但从传统公司法的构成来看,则不能不说它是异质的观念。因此,如果在公司法上强制参与,则会产生很大的疑问。这是因为,“参与”观念的存在,本来就是基于以“自发性、自主性、任意性”为要素的“自由”的观念,而它与“强制”明显地处于对立地位[(15)]。
如此看来,职工参与制度说到底应当始终贯彻“任意性的原则”。在日本,公司的支配在理论上虽属于股东,但在现实上却属于薪金阶层经营者,这种现状正好表明职工的经营参与已成为现实。那么,在日本,在公司法领域,是不是说职工参与已不成为问题了呢?职工参与只要坚持任意性的原则,在公司法的领域问题当然较少[(16)],但是,至于信息参与是否也必须贯彻任意性原则,则仍有待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应当把以信息参与为目的的劳资协议制度作为第四个公司机关(在日本为第五个机关)纳入公司制度的问题,在日本亦不能完全否定它迟早会作为立法一大课题而出现的可能性[(17)]。参与应当选择任意制还是义务制,虽然终究属于立法政策上的问题,但却不能完全依靠理论决定,这一点,已由欧洲共同体国家的立法实践所证明。
五 从具体事例看职工参与--日本职工持股制度的问题点
如上所述,在日本最为普及的职工参与形态当属所有参与(职工持股制)和信息参与(劳资协议制),前者属于公司法的范畴,后者则属于劳动法的范畴。下面,以前者为中心,以职工参与的具体制度为线索,就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作若干探讨。
首先,对日本职工持股制的实际情况作一简单介绍。截止到平成4年(1992年),在全部上市公司的2123家中有2011家公司(占94.7%);在非上市公司中,以资本金在1亿日元以上,职工人数在100人以上的4415家公司为调查对象,其中得到回答的991家公司中有273家公司(占27.4%)已实施了该制度[(18)]。其目的是(1)职工财产的积蓄,(2)经营参与意识的提高,(3)稳定股东的形成等[(19)]。
其次,作为法律上存在的问题,不仅该制度本身缺乏法律规定,并且由于涉及到商法、民法、租税法、劳动法、证券交易法等领域,尚存在许多难点。就商法而言,无须赘言,一般存在股份取得上的问题(自己股份取得、对第三者的新股发行、资金的支付等)和取得股份的管理上的问题(表决权的行使,股份转让的限制等)[(20)]。其中大部分问题虽属技术性问题,但与制度的目的相关也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职工财产的积蓄的目的和持股转让限制契约以及股份赎买契约的关系,另一个是稳定股东形成的目的和禁止利益给与的规定的关系。
第一,采用职工持股制度的非上市公司,通常通过章程或契约,对股份转让加以限制,特别是封闭性较强的家族公司,其中多签订股份赎买契约。如果从该制度参与意识的提高和稳定股东的形成等目的来考察,那么,好不容易采取资金援助等措施,籍以扩大的职工持股制度,如果职工持股一旦可以自由转让,那么制度的目的又何在呢?反之,从职工财产的积蓄这一目的来考察,若通过契约加上限制转让条款或赎买条款,其上述制度的目的则难以达成。如此看来,上述问题可作如下概括:即实际上它是,职工持股的转让限制和以职工退职时强制售出为内容的契约是否有效的问题。具体地说,也就是限制股份转让的契约是否适用商法第204条第1款的规定,职工持股的赎买契约是否违反商法第210条的规定的问题。那么,上述问题应如何考虑呢?如果说职工持股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职工财产的积蓄,并且对股东收回投资给予保障乃是股份公司法的一大基本原则的话,那么上述契约原则上都应解释为无效[(21)]。这类问题虽属于非上市封闭公司所特有的问题,但若要使职工财产的蓄积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得以实现,那么也就必须贯彻以保障股东收回投资为最大命题的这一现行公司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采用职工持股制度的公司,不论公开公司还是非公开(封闭)公司,通常给予取得股份的职工诸如奖励金等资金或提供其他方便。尤其是上市公司,如果没有公司提供的资金及其他便利,该制度则无从成立。但是,熊谷组持股会事件(福井地方裁判所昭和60年(1985年)3月29日《金融商事判例》720号40页)提出了该奖励金的支付是否触犯了商法第294条之二(禁止利益给与)所规定的“无偿的利益供与”的规定的问题。该事件的经过是,原告股东认为,股份公司熊谷组对持股会的奖励金的支付属于利益供与,因而提出追究代表董事对公司责任的要求。的确,如果从职工持股制度的目的之一就在于稳定股东的形成(公司和持股会会员的共同体意识的提高)这一角度来考察,若要证明该奖励金并非作为商法第294条之二的第1款所规定的“有关权利的行使”而支付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福井地方裁判所首先承认了该奖励金的支付是为了有关股东权利行使的推定的成立,之后,以公司支付该奖励金的目的是为了职工的福利等为由,推翻了所谓为了股东权利行使而支付的推定,因而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对判决结论虽然没有产生不同意见,但对判决中有关推翻商法第294条之二第2款的推定的理由,尚有疑问。但是,上市公司的职工持股制度的利益就在于奖励金的支付。因此,将其作为利益给与而必须予以禁止的这一问题的提起,在某种意义上正刺中了立法者的要害。总之,若要完全消除解释论上的疑义虽然还有许多困难,但从职工持股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谋求职工财产的积蓄这一积极意义来看,熊谷组持股会事件具有深远意义。
在探讨上述问题时,职工持股制这种参与方式在美国的普及和积累的经验再一次告诉我们,职工参与的任意制这种运营方式对该制度的健康发展具有多么大的作用。
六 职工参与的展望--职工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现代的股份公司同30年代前的所谓近代股份公司相比,有着惊人的变化。以最具代表性的股东大会为例来说,它正从“决策的场所”到“信息公开的场所”进行实质性的转变。随之,公司的信息公开方面,对于利害关系者的公开的范围也在逐渐地扩大。而且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信息公开是控制大公司有效的手段,可以说如今对职工的信息公开和对出资者的信息公开应区别对待的主张正在丧失其理论根据。岂止如此,如果对围绕着现代股份公司多元的利益调整的必要性加以考虑的话,那么建立对经营的多角的有效监督体制则属当务之急。在这个意义上,姑且不论对经营的参与,就信息参与而言,对职工和出资者区别对待的实质上的根据正在急速地消失。
那么,是不是应该使劳资协议机关成为法定的公司机关,并且对股份公司实行强制性的职工信息参与呢?作为结论,我是很难赞成的。既然职工参与的思想是立足于参与的民主主义的,那么信息参与机关的设置与否到底应该归于章程的自治。这一点,与作为所有参与的职工持股制度相同。虽然不能否定职工实质上有正在成为公司的成员的倾向,但因此并不能就认为劳动者是公司的构成人员。但是,如果从保护职工的观点出发而强制公司实行信息参与的话,那么它应该等待劳动法上的措施。
日美结构性问题协议的教训,使我们明确地认识到市场参与必须要负担相应的成本。中国现在正在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转变,如果谋求对世界市场的参与的话,也不得不承担参与成本。本文以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职工参与为题,暗示了为了实现市场经济的参与,中国将要负出相当大的成本(牺牲)。
下注
[(1)]围绕着日美结构性问题协议这一系列问题,暂可参照奥岛“日美结构性问题协议和公司立法的课题”《法律时报》第63卷第9号第2页(1991年),及“日美结构性问题协议和禁止垄断政策的动向”《法律时报》第65卷第8号第2页(1993年)。另外,还可参照松下满雄“日美一揽子协议”《书斋之窗》第432号第24页(1994年)。
[(2)]关于市场参与成本问题,笔者就与监查役制度之间的关连有所论述(请参照奥岛“监查制度和公司立法的国际化”《法律时报》第65卷第7号第57页(1993年)。
[(3)]本稿是1993年10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的“日中民商法和市场经济法律秩序”讨论会(于新大都饭店)上的发言稿经若干修改加注而成的。
[(4)]比如可参照K、W、卡普(原泰三译):《私企业与社会费用--现代资本主义中的公害问题》昭和34年(1959年)。
[(5)]关于这一点,暂可参照奥岛“从日本企业的构造、行动看公司法和禁止垄断法的交错”《经济法学会年报》第12号第47页(1991年)。
[(6)]关于green paper,暂可参照森本滋:《EC公司法的形成及展开》165页昭和59年(1974年)
[(7)]对于这个问题,有关欧洲共同体的现状,请参照奥岛“EC公司法的形成及展望”《日本EC学会年报》第11号第136页(1991年)。
[(8)]参见奥岛前注[(2)]。
[(9)]请参照奥岛:《现代公司法的支配与参与》第172页(1976年)。
[(10)]请参照注[(7)]第147页。
[(11)]关于二元制、一元制、并列制的公司机关构成,请参照奥岛注[(2)]第58~59页。
[(12)]请参照奥岛“企业与职工”,竹内·龙田编《现代企业法讲座·2》第249页(1984年)。
[(13)]以上讨论,请参照奥岛“职工的经营参与”,《法学教室》第132页(1991年)。
[(14)]奥岛注[(12)]第249页。
[(15)]请参照大野实雄“职工持股制度的任意性”《商法研究》第3卷第87页(1963年),奥岛“法国职工持股制度的现状”,《判例时代》第499号第80页(1983年)。
[(16)]为了促进职工持股制度,尚存在承认缓和自己股份取得限制的必要性等技术问题,参照平成6年(1994年)2月2日法制审议会商法分会决定“商法及有限公司法的一部分修改法案要纲草案”《商事法务》第1345号第7页(1949年)。
[(17)]当然,信息参与虽有程度之差,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方向已得以确立,在这个意义上,把信息参与作为法律制度给以追认,似有缺乏实际意义之嫌。但笔者认为,考虑到欧洲共同体的动向,在日本亦不能断然否定未来采用--把信息参与机关作为公司机关的设置当做职工参与的突破口--这样的立法政策的可能性。
[(19)]日本证券经济研究所“职工持股制度的实态调查--昭和60年(1985年)的实情”《证券资料》第49号第7页(昭和61年--1986年)
[(20)]有关对职工持股制度的法律问题进行比较清晰的整理了的资料,请参照新谷胜《职工持股制度--运营和法律问题》(平成2年--1990年)和牛丸舆志夫“职工持股制度的法律上的诸问题”《商事法务》第1102号第2页(1987年)。
[(21)]暂可参照市川兼三“职工持股制度和股份在公司内的保留契约”,《香川法学》第12卷第3号第1页(平成4年--1992年)和牛丸舆志夫“职工持股制度的股份转让限制和证券交易法58条〔4〕”《商事法务》第1215号第113页(199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