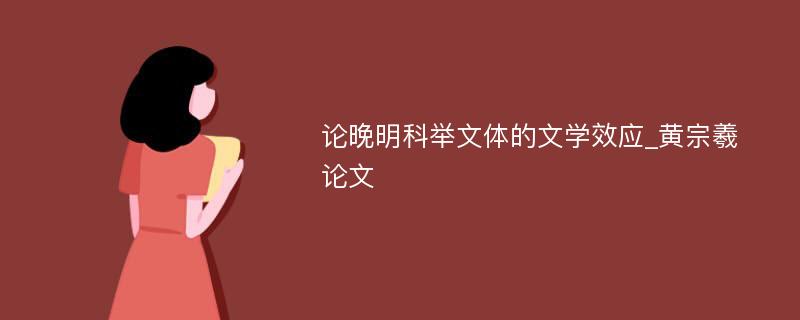
论明末科举文风的文学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风论文,明末论文,科举论文,效应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7)05-0145-06
明代末年,以研讨八股文为主要文学活动,兼及诗文创作的文社大量兴起,到崇祯二年(1629)形成以复社为核心的全国性社团联盟,社团文人成为明末文坛的主要文人群体,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啻为特殊的文学景象。作为备科举考试的社团文人,在社团内接受科举考试训练和八股文创作的学习,其文学素养多从严密的八股文训练中所得,科举思维对社团文人的文学创作影响极为深刻。没有经过科举八股文训练的文人在诗文创作上往往会“格格不达”,清初王士禛言:“予尝见一布衣有诗名者,其诗多有格格不达,以问汪钝翁(汪琬)编修,云:‘此君坐未尝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无与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终不分明。”[1] 300可以这样说,明末社团文人创作多受科举思维影响,使明末文坛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色。
一、儒者古文:以六经为根本的古文创作
明万历中叶以后,科举八股文日趋走向模拟的境地,文坛文风日趋腐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科举士子为学不能根柢经术。作为明末文坛盟主的复社联盟领袖,张溥提出“尊经复古”思想以救文坛文风腐朽之弊,“返经”成为开创新的文坛风气的重要方式。钱谦益也说:“今诚欲回挽风气,甄别流品,孤撑独树,定千秋不朽之业,则惟有反经而已矣。”[2]答徐巨源书
社团倡导“返经”思想救文坛科举之弊,主要源于六经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所谓“六经”,主要指儒家学说的六种经典著作,包括《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部儒家经典著作各自为用,又合为整体,内容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谓古人不可动摇的“大百科全书”,同时也是古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和最高标准[3]2-3。朱元璋定科举,以“四书”“五经”为士子为学对象,其目的在于传承儒家“道统思想”,实现儒家“德治”的社会功能,培养具有治国理政能力的合格官吏。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明建立科举制度,以八股文取士的良苦用心。
因而,明初科举方兴,士子读书本于经术,其古文创作亦能以“经术”为根柢。如成化年间著名的时文大家王鏊“以制义名一代”,《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古文亦湛深,经术典雅道洁,有唐宋遗风。……其泽于古者已深,故时文工而古文亦工也。”[4]《震泽集》提要明万历中叶以后,随着明末文社的大量兴起,文社成为改变文坛自万历以来逐渐形成的腐朽文风的重要力量。文社诸子大多主张时文、古文创作皆须本之“经术”,以此来达到厘正文体目的。如代表明末文坛主流的江西豫章社领袖艾南英与江南复社联盟虽然在宗法对象上存在较大分歧,而且艾南英始终不肯加入到复社联盟中来,但在倡导返经救时文之弊思想上,豫章社与复社却出奇地一致,二社皆把“六经”作为古文创作根柢的不二法则。豫章社领袖艾南英说:“今夫古文辞之为道,其原本经术,与举子业无以异也。”[5]李元云近艺序复社领袖张溥亦言:“概时文之盛兴,虑圣教之将绝,则各取所习之经,列其大义,聚前者之说,求其是以训乎俗。”[6]诗经应社序文虽有“古”“今”之分,而各自本于“经术”的创作基础和思维理路是相通的。正如清初学者俞长城所言;“理学透则文章自工,非有二事。”[7]题邹谦之稿也就是说,士子通过研习经术,能透彻理解经书所蕴含的圣人之道,文章也就自然而至,自然而工。这个道理艾南英非常明白,他说:“文以明道为主,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5]陈大士合并稿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章本质在于阐发圣人之道,而不仅仅是模拟古文技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受祺才把艾南英“以孔孟经学为根基的古文”称为“儒者古文”,把“以孔孟经学为根基的学问”称为“儒者古文之学”。由于艾南英“起而大声疾呼”,“天下瞿然知有儒者古文之学”[5]总论。艾南英成为明末启、祯之际文坛“儒者古文”代表,在当时文坛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人是这样评价他的:“三十年来,古文一道半归豫章,豫章之文,必以千子(指艾南英)为领袖。”[5]总论
社团文人对经书义理的深刻研究往往使其古文创作气脉贯通,思想深刻而显博大精深,表现出儒者古文的显要特征。如果胸无经术,仅以形式上的“新”“异”为文,反坠时文蹊径。明末竟陵派诗人钟惺古文就有此种毛病,黄宗羲就批评他:“其文好为清转,以纠结见长,而无经术本领,求新求异,反坠时文蹊径。”[8]卷37可见,古文析理是否本之六经、析理是否深刻、文章是否博大精深,几乎成为判断古文创作是否“空疏”的标准。由于明末文社诸子提倡读书尊经,创作古文以“经术”为根柢,这就使得社团文人古文创作在阐发事理时往往从六经中寻找依据,以六经所蕴含的义理来分析事理。如张溥古文中有很多为他人八股文选集写的序,这些序言大多从六经的视角言理,如《房稿〈遵业〉序》,房稿《遵业》之选是复社成员周立勋所选时文集,张溥认为周立勋选文有两个特点:其一,人伦道德皆蕴经中,选家须通经,方能辨时文真伪;其二,被选者须“径明行修”、“懋义不倦”、“读经尽伦”之人,“文之可录者皆出其中”。总之,张溥古文总是围绕六经以及六经所蕴含的儒家人伦道德阐发事理,可谓在古文中“行《六经》、《语》、《孟》之理”,以此来实现他所提倡的“质访实用,不务虚文”[6]后场名山业序的古文风格。
在古文中“行《六经》、《语》、《孟》之理”的古文创作当然可以使古文“质访实用”,但有时也会出现赘“经语”入古文的弊端,即为了表达思想的需要,随意对经书语句进行解释,以符合文中表达主题的需要。张溥古文创作就出现了此种弊端,因此遭到其他社团的批评,批评最为激烈的是豫章社领袖艾南英,他说:
今必赘经语以就题,复强吾意以就经语,又况夫尊经而不能通其解,业一经而误用其四。若是而号于人曰尊经,吾恐先圣有知,必以为秽而吐之矣。呜呼,今日制举之弊已至于此,一人倡之,人人和之,遂至臭腐而不可读,而吾以为此皆空疏不学之过也[5]戊辰房删定序。
应该说艾南英对张溥的批评言词是比较激烈的,并扣以“空疏不学”之名,这在当时文坛可是一个不小的“罪名”。谢国桢对张溥古文也持怀疑态度,他说:
自从李东阳、王弇州前七子后七子等人主张复古,弄成似子非子,非汉非魏晋,一般似通不通的文章出来,真有改革的必要。所以艾千子主张由欧、曾以取法成、弘,把文章弄得清清楚楚的,不要用支离的文句和琐碎的典故,他的主张本来是很不错的。但张天如他却主张祖述六经来矫正时弊。他这个主张,我们倒很怀疑。所谓尊经复古者,是不是学圣人的品行,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要效法六经的字句,拿他这种主张,与王李七子“文必汉魏,诗必六朝”比较,却是同样不识时代性,同一样的失败。所以我们一翻开《七录斋集》里面的标题,像《房稿霜蠶》、《房稿香却敌》、《房稿文始经》,这种模仿《六经谶纬》,似通不通的文字,比王李七子还要可笑[9]131。
谢国桢也同样指出张溥古文中“赘经语”的毛病。更主要的是,张溥在应社(为复社前身)内分治五经的十一人中专治《易经》,这就容易使其古文创作“无意识”的“夹杂”某种带有神秘“谶纬”色彩。总的来说,从当时古文创作的实际来看,此种弊端,张、艾二人文中皆有,但艾南英称张溥古文“空疏不学”实在是有些片面;相比张溥之作,艾南英古文更显空疏之弊。二人以“空疏”相击,不过为明代文人之间的义气之争和门户之争的结果罢了。
以经学为根柢的古文创作在清代初年表现得更为强烈。明清易代之后,很多由明入清的社团文人一变而为明遗民。在那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很多社团遗民加入了反清复明的洪流之中。抗清失败后,他们转而沉潜于学术研究,反思明亡原因,在思想上与清政权作斗争。他们把明亡的一个原因归结于明代学人的空谈心性和科举八股文的空疏误国。因而,他们反过来更加提倡学者为学务必以经学为根基,提倡以经学为基础的“经世致用”之学,形成清初“为文不言心性,而讲经世致用”[10]339为主要特征的“学人之文”,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他们的古文创作特别强调根植于经史之学和当世之务,“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10]358,强调“文需有益于天下”[11]卷19。这些“学人之文”思想性比较深刻,明末形成的“赘经语入古文”的弊端也逐渐克服,使得清初古文一归于正。
二、时文古:八股文创作对古文法的借鉴
八股文重法,复社联盟领袖张溥倡导不遗余力。如张溥在给程楚石《程墨选》所写的序言中就特别强调士子作八股文如匠人制器,既要“操斤准节”,又要符合“长短尺寸”之数,以“法”规矩之[6]程楚石《程墨选》序。
社团领袖所倡导的“重法”科举文风,经过社团文人的广泛宣传,在明末文坛形成一种重法风气,对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很大影响,不仅古文创作思维受时文严密体制的影响,而且时文创作也多借鉴古文法;甚至当时士子为训练八股文作法,在平常的书信来往中也自觉不自觉地采用时文法。如陈际泰少贫学无师授,“凡写家信与寻常客子书,皆用八股法”[13]陈氏三世传略,以此作为他提高八股文创作水平的训练方式。在古文法与时文法的相互借鉴上达到非常熟练的境界,由此在明末文坛形成“时文古、古文时”的风格特色[14]《蠌桐后集》序。这也是当时社团形成的“重法”科举文风对文坛影响比较突出的一个特征。
所谓“时文古”,指时文创作借鉴古文创作技法,使时文呈现出古文的某些特征。从渊源上来讲,八股文与古文最为接近,以古文法入八股文也在情理之中,同时也是提高八股文创作品位的一种方法。自南宋王安石定以经义取士之后,便出现了专门评点古文作法的专门论著,如吕祖谦的《古文关键》、魏天应编选的《论学绳尺》,以及南宋末年谢枋得的《文章轨范》,等等。这些专门评点古文作法的专门论著,成为此后时文创作可资借鉴的“得力助手”。明初以科举八股文取士,“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15]凡例。其后,不管是七子派还是唐宋派、公安派,都把“以古文为时文”作为创作高品位八股文的最高追求,以古文法入时文也是创作“真时文”的不二法则。明代万历中叶以后,士子日益把八股文作为仕进荣身的“敲门砖”,以“程墨”、“坊稿”为学,八股文越来越脱离了它的高品位追求而日趋腐朽。艾南英指出,当时士子作八股文的病症在于“为制艺者不知古文为何物”[5]与友人论文书,“制举业之道与古文常相表里,故学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为时文”[5]金正希稿序。因而,明代末年,文社便提出了“以经史古文抚养程文”的主张。提出这一主张的是与张溥号称“娄东二张”的复社联盟另一领袖张采,他在《论文纪事》中说:“予谓时文之为害,使人一生无文章,经史古文,正以抚养程文。”[16]豫章社陈际泰也持相同的观点[13]同人年谱社序,并以能“以古文入时文”而自居[13]复刘孝若,他的时文创作明显地表现出古文创作的某些特色,以至于汪函朗读陈际泰的时文却不知为时文,而以为是古文。陈际泰是这样陈述这件事的:
陈子在浮梁舟中晤汪函朗,朗为伯玉(汪道昆)大司马从子,素不习时义而善古文辞,得予制举业,大嗟赏。予刻怪卿不习是,何以独赏是?然以别友文使之读,则已不解为何语矣。世之习举子业者以陈子之文不可句,而汪所不解者乃在彼不在此,彼非以时文读陈子之书,以古文读陈子之书也[13]罗贞卿诗集序。
再如黄宗羲所作时文,据伍崇曜《重刻南雷文定跋》记载,黄宗羲“年尚少,阁学文文素见先生行卷,曰:‘是当以大著作名世也’,都御使方孩未亦曰:‘是真古文种子也’”[17],黄宗羲所作行卷呈现古文风格和气态,明末著名学者文震孟竟赞赏其“以大著作名世”。为何文震孟对黄宗羲的评价如此之高呢?原因就在于黄宗羲“以濂、洛之绪,统会于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济,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者所未有也”[17]。黄氏为学既能根柢经学,又能融合各家,其时文创作并不模拟古文之法,而在时文中行古文神气,阐圣贤之意,黄宗羲借古文入时文在技法上达至“化境”。
文社选家一般通过对前人时文的具体评点,指出时文中如何行古文之法,以便士子模仿学习。如艾南英评点归有光所作八股文《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看他每股接头转折处,纯是古文行局,一种空漾浑雅,繁委周匝,无一不古,真国朝第一时文手乎,亦深于古文者方知之。”[18]367指出在八股文中的每一股转折处如何行古文法。周介生评茅坤八股文《质胜文则野》:“雅而洁,鹿门为文得《史》、《汉》、欧曾之遗法。”[7]题茅鹿门稿指出茅坤八股文中行以古文风格之法。艾南英评王鏊八股文《许子必种》:“此题散叙差易,而截作四段整齐,又于问答处一字不漏,此非守溪先生不能。昔人模仿史迁叙事,但能见之古文词耳;今见之时文此开辟来文章一变局也。”[7]题王守溪稿指出时文叙事题材如何借鉴史传叙事之法,等等。这样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文社选家通过对时文的具体评点,在明末文坛形成一股“以古文法入时文”的风尚[5]三与周介生论文书。
晚明文坛对前后七子模拟复古文风批评非常激烈,如公安三袁就提倡“独抒性灵”的自由创新文风,试图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七子派”给文坛带来的沉闷模拟复古文弊。艾南英也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文风深恶痛绝,批评前后七子“相率取马迁、班固之言摘其句字”,相袭为“腐剿”之弊[5]重刻罗文素公集序。古文创作如果从字句技法上师法古人,往往会被人讥为“模拟”。为了避免重蹈“模拟”之途,艾南英提出古文“贵传古人之神”的说法[5]与沈昆铜书应该说,古文中能传古人之神,为古文师法前人的最高境界。但是,古文中传古人之神就已显困难,何况时文在体制上又多所限制,以古人之神入时文就更显困难。艾南英就曾抱怨说:“况于制举艺限以题旨,拘以排股,而欲于其中行以史汉之神,可谓难矣。”[5]与沈昆铜书无深厚的经史之学,在八股文中行“古文之神”的确很难,以致一些学无根柢之人往往喜欢在八股文的形式技巧上作文章,“句必精俪,字必纤役”,误以“东汉末年至于梁隋陋习”为古[5]与沈昆铜书;黄宗羲也以“以古文法入时文”为“剿袭之字句,饰时文之音节”[8]七怪,讥讽时文由于以古文法“装点门面”而误入“模拟”之途。因而,时文是否借鉴古文法也不可一概而论。
三、古文时:古文创作对时文法的借鉴
所谓“古文时”,指古文创作借鉴时文创作技法,使古文呈现出时文的某些特征。借鉴古文之法以滋养程文,被当时人所普遍认可接受,并作为改变时文之弊,提高八股文创作品位的重要方式,文社为此提倡不遗余力。但时文法能否给古文提供有益借鉴,在当时文坛争议还是比较大的。毕竟,明代中叶以后,文坛对八股文的批评越来越多,八股文不仅导致士子不知为学,而且禁锢了士子的思想创造,再加以士子为时文过多追求形式技巧,其弊端越发明显。因而,以时文法入古文,势必会造成古文创作如时文一样陷入泥潭。人们对此颇多指责,黄宗羲言:
当王、李充塞之日,非荆川、道思与震川起而治之,则古文之道几绝。……今日时文之士,王于先入,改头换面而为古文,竞为模仿之学,而震川一派,遂为黄茅白苇矣。古文之道,不又绝哉[8]郑禹梅刻稿序。
从明末当时的古文创作实际来看,古文创作的确不如正、嘉之际,复社张溥对此也曾发过牢骚。黄宗羲是这样记载的:
往丙子、丁丑间,一时文集行世者十余部。娄东张天如曰:“此数十余人者,皆今之巨子也,吾读正、嘉时不以文名者之文集,其浑厚悠长,反若过之。岂世运之升降欤”?[8]李果堂文钞序
丙子、丁丑间,指崇祯九年、十年间,当时以古文盛者,大致以陈子龙等人为领袖的几社文人和以张溥、张采、吴应箕为领袖的复社文人。张溥所言十人没有详细点名,大概即指几、复二社文人。张溥作为众社团领袖,与正、嘉之际文人古文创作相比,他也自叹不如。张溥虽然怀疑导致明末文学不如正、嘉文学的原因与世运日坏有关,但还没有具体指出世运坏在哪里。黄宗羲则对此有缜密思考:
“科举盛而学术衰。……今之为时文者,无不望其速成,其肯枉费时日于载籍乎?故以时文为墙壁,骤而学步古文,胸中茫无所主,势必以偷窃为工夫,浮词为堂奥,盖时文之力不足以及之也。”为说者谓百年以来,人士精神尽注于时文而古文亡[8]李果堂文钞序。
可见,启、祯间古文不振的真正原因正是在于“八股文”。为时文者不能本之经术,学无根柢,骤为古文必然空洞,语多浮词;且所为古文多由时文“改头换面”而来,即古文家受八股文体制的影响,往往有意无意以“时文法”入古文,导致古文在结构形态上类似时文,“古文与时文之畛,无复可分”[13]同人年谱社序,“古文与时文之界不分,而文必遂至软熟”[19]9,“以时文入古文”其弊甚大。谢国桢就批评张溥:“在模仿古文当中,夹杂些八股的文调,倒还不如艾千子的文章清通可喜。”[9]131即使是古文大家,完全不受“时文法”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时文法入古文”既然弊端甚大,是否就表明古文一定不能借鉴时文法?未必然。黄宗羲批评以时文法入古文导致文弊,是建立在士子不本经术,八股文日益走向模拟之路而发。如果士子学为八股文能勤治径史,博览群书,古文也受其概沾,黄宗羲说:
昔之为时文者,莫不假道于《左》、《史》、《语》、《策》、《性理》、《通鉴》,既已搬涉运剂于比偶之间,其余力所沾溉,虽不足以希作者,而出言尚有根柢,其古文固时文之余也[8]李果堂文钞序。
时文、古文同为“载道”工具,在治学路径上皆本于经史,艾南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称古文与时文并无实质性区别[5]李元云近艺序,时文与古文在“技法”上具有相通之处,艾南英说:
其首尾开阂、抑扬浅深、发止敛散之局,与举子业无以异也。为古文辞,不得杂取《世说》、《谐谭》以自累,与为举子业而不得沿时趋习语方言俚谚,以自远于尔雅深厚之意无以异也。盖有为诗古文辞而不能为举子业者矣,若夫精于举子业者未有不由于诗古文辞也[5]李元云近艺序。
可见,古文与时文在文章结构和语言运用上是相通的。八股文自身基本融汇了中国古代一切文章作法,为八股文者经过严密的八股文技法训练,学为古文也就比较容易了;而古文创作则无严密体制的限制,在内容和形式上可以“自由”发挥,因而,古文能作好但时文则不一定会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待社团文人的古文创作,其古文中“夹杂”八股文法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文社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士子的科举应考能力,学习和训练八股文作法是文社的主要文学活动。综合黄宗羲与艾南英所言,我们可以看出,古文创作必然要受时文法影响,但要创作出优秀的古文,必须以经史为基础,以时文法入古文。
从当时文社成员的古文创作来看,八股文法对古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八股文“破承起讲”、“起承转合”结构法使古文与八股文的结构形式有些类似,社团文人在创作古文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一种比较固定的八股文逻辑思维模式,有时也在古文行文中无意识“借用”八股文的股股相对法。举复社领袖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为例,全文主要分为五部分,与八股文比较,第一部分点明题意,总说五人为何而死,确立“为义而死”中心,相当于八股文的破题部分;第二部分承上题五人为“义”而死,葬五人于魏阉废祠之址,并立碑以志其义,相当于八股文的承题部分;第三部分把五人与富贵子弟、慷慨得志之徒死而湮没相比,烘托出五人为义而死,死得伟大,原因何在?开始起讲,相当于八股文的起讲部分;第四、五、六、七部分为正文部分,详细记叙五人在周顺昌被逮之日与阉党余孽的英勇斗争和舍生取义的英勇事迹,以周顺昌被逮之日“起”,五人就义“承”,表彰五人“义”转,五人流芳百世“合”,惟这四部分不与八股文“股股相对”格式同,却与四大比“起承转合”逻辑结构合;第八部分为文章收结部分,作为结束语交代了收敛五人尸首者姓名,相当于八股文的收结部分。由此看来,张溥古文创作受八股文格式体制的影响,在形式结构上与八股文有相似之处,用曹学佺评当时文坛古文创作特色“古文之近于时文”[20]古文自序,来评价张溥的古文特色亦十分恰当。这种古文作法在逻辑上层层深入,结构上婉转曲折,气脉贯通,言简意赅,虽由时文法入,却无时文法之程式,可谓活用时文之法入古文。对张溥的古文创作我们还是应该加以肯定的。由于张溥为当时的社团领袖,在当时文坛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所创造的古文作法为广大社团文人所效仿,成为当时古文创作的一种较为固定的格式。
文社的文学活动大多集中在八股文的评选和训练,由于时文和古文的姻亲关系,社团文人也把古文作为日常课业内容。因而,文社所倡科举文风对社团文人的古文创作影响最大,而科举文风对诗歌的影响则并不明显。这固然因诗歌与时文在形式上很难找出较为明显的相似之处,同时又因二者在创作逻辑思维上的截然不同。这是否就意味着当时的诗歌创作不受科举文风的影响呢?也未必然。袁宏道说:“夫诗与举子业,异调同机者也。”[21]郝公琰诗叙诗歌与科举还是有共同之处的。中国古代诗歌以“儒家诗教”为正宗,内容上载“圣人之道”,风格上追求“雅正”,在这一点上正与科举八股文同。因而,要振起一代诗歌,必须如八股文一样根植于圣人经典。
由于当时社团文人能够勤治六经,其诗歌创作过多注重义理的阐发,往往带有浓厚的儒家说教色彩,语多“兴寄”,用典多从“六经”中来,风格上“端庄雅正”、“质木切实”,被钱谦益称为“儒者之诗”。这主要表现在复社、几社文人的诗歌创作中,如钱谦益评复社顾麟士的诗歌:“顾麟士有宋诸儒之学,沉研钻极,已深知六经之指归,而毛、郑之诗,专门名家,故其所得者为尤粹。其为诗蒐罗杼轴,耽思旁讯,选义考辞,各有来自。虽其托寄多端,激昂俛仰,而被服雍雅,终不诡于经术。目之曰儒者之诗,迨无愧焉。”[2]顾麟士诗集序由于复社、几社又诗宗“前后七子”,故二社文人的诗歌创作又不免带有模拟痕迹,诗歌抒情本质反而湮没。
总的来说,文社科举文风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反面的。由于文社日常活动在于评选八股文,探讨八股文技法,社团文人把时间过多放在科举考试上,而对诗歌创作则无暇顾及,这就使得当时很多文社领袖无诗集流传,如著名的复社领袖张溥、豫章社领袖艾南英等人皆如此。吴梅村不无惋惜地说:“嗟乎!自举世相率为制举义,而诗道湮灭无闻。”[22]663文社很多成员对科举文风于文学的影响多持批评态度。
标签:黄宗羲论文; 儒家论文; 八股文论文; 古文论文; 张溥论文; 国学论文;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科举制度论文; 经世致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