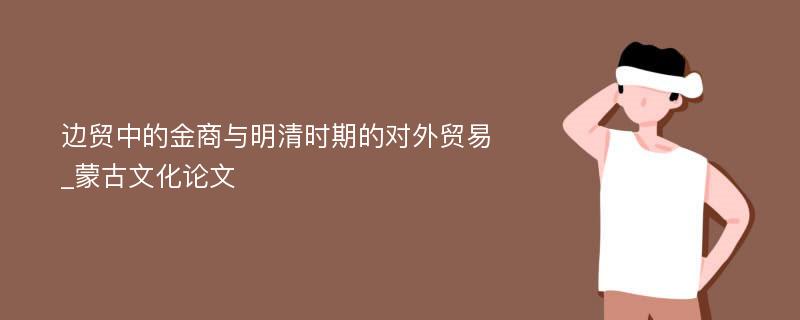
明清时代边地贸易与对外贸易中的晋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地论文,明清论文,对外贸易论文,晋商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晋商崛起于明而鼎盛于清。明人谢肇淛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注:《五杂俎》卷四。)可见,晋商在当时已是一支与徽商共执中国商界牛耳之劲旅。有清一代,晋商势力臻于顶峰。晋商足迹遍布中国大陆,并远涉蒙古、俄罗斯、朝鲜、日本和新加坡,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晋商活跃时间之长、活动范围之广、积累财富之多、影响之大,实属罕见。关于晋商的研究,本世纪以来一直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晋商和明清对外贸易问题提出一孔之见。
一、晋商与明代蒙汉边地贸易
中国封建统治者历来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的活动受到明显的限制,对外贸易在封建经济中居于微不足道的地位。明代对外贸易以政府统制型的朝贡贸易为主,私人民间贸易长期受到严格控制。明代中叶之后,随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和商业资本的活跃,商人的贸易活动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不同阶层居民的生活。因此国家对商人的限制逐渐放松,社会上重儒轻商、重农抑商的观念开始有所淡化。隆庆(1567—1571)年间的开放海禁和封贡通市是明代社会由封闭走向相对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晋商就是在这样一种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中走上对蒙贸易舞台的。
南倭北虏一直是明王朝的心腹之患。为了防备蒙古封建主的南侵,明廷不断加固和修缮长城,并设置了九个边镇,到明中叶建立了以长城为主体的九边防御体系,将九镇防地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一防御体系有效地遏制了蒙古封建主的侵扰,使中国北方边境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安定局面,并促进了蒙古南部地区的开发和汉蒙之间的友好往来。同时,庞大的九镇军需供应大大刺激了内地和蒙古边地贸易的发展。九边防御体系为晋商开展边地贸易创造了活动空间。在明代的九个边镇中,位于山西北部的大同、宣府和山西三镇是九边防御体系的中心地带。大、宣、山三镇规模最大、驻军最多,耗费军饷最巨。明初政府为了给各边镇筹集军饷实行开中制,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招商代销制度,它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契机。明中叶在纳银开中法的执行过程中,晋商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政策优惠,凭借地理上和交通的优势,通过贩运盐、米、布、草料等物品,捷足先登,首先占领了边镇军需市场,然后开始涉足于长城沿线的蒙汉私市贸易和马市贸易。
所谓蒙汉私市贸易是指明中叶在长城沿线地区广泛开展的以交换布帛、粮食、牲畜和畜产品为主的走私贸易。在私市上一件价值七八两的估衣,可换马一匹,卖至稍远处可得银十余两。嘉靖三十年(1551年)后,私市贸易不仅在山西、大同、宣府三镇地区十分活跃,而且在其他各镇也存在着类似情况。据统计,仅大同墩哨军每月同牧民的交易额约可达三千两银。嘉靖年间官府对出入军兵严加搜检,隆庆四年(1570年)王崇古任宣大总督后,墩哨军的走私贸易完全合法化(注:王崇古:《禁通虏酌边哨以惩夙玩疏》。),晋商成为私市贸易的主要参加者。长城沿线私市贸易的发展,使蒙古地区的畜产品进入了江南市场。嘉靖中叶,大同、山西等边地出现了以晋商为主的专门贩运马鬃、马尾的集团。隆庆四年,大同阳和军兵马西川与榆次人李孟阳、偏关人李义等十数人结伙出塞“与虏私易马尾”。事败露后,马西川率八千骑兵,先攻打边军主力驻地老营堡(在偏关),趁边军无暇它顾之机,使李孟阳“携马尾驰扬州。”(注:《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中》。)这不仅说明晋商从事的蒙汉私市贸易规模大、涉及范围广,而且居然将塞北蒙古同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江南扬州直接联系起来。
蒙汉政治关系的改善对北方边地贸易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隆庆五年(1571年)明王朝与蒙古俺答汗所达成的“封贡通市”和议,基本结束了蒙古和明王朝之间的战争状态。这一事件不仅成为明中后期北方边境走向安定的契机,也是秦汉以来中国北方边境由以战争对抗为主导走向以和平交往为主导的重要转折点。封贡通市后恢复的马市为晋商扩大边地贸易提供了新的机遇。
马市是在明官方控制下蒙汉人民在指定地点进行的一种贸易,通常每年开一、二次,每次3—15天。隆庆五年,明廷在宣府、大同、 偏关和宁夏开设四处马市,以后又在宣府迤西开设固定市场20余处。马市分为官市和民市,永乐至嘉靖年间,马市多属于官市。官市是明朝的官方贸易,它以购马为主,也兼收畜产品。每年九边各镇官方购买的数量及马价银两,都有一定的限额。购马银两除兵部拨发外,其余由各镇支出。万历初年各镇购马价银有限,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后,随着马市贸易的迅速扩大,宣府、大同、山西三镇马价银增至41.03万两白银。 (注:《明神宗实录》卷五○○。)自隆庆封贡至明末60余年间,在蒙古马市成交的马匹约有300万匹左右,价值3000万两白银之多。 (注:葛贤慧、张正明:《明清山西商人研究》,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官市结束后,才允许牧民与商人、百姓和士兵等互相贸易,是谓民市。后来又出现了月市和小市。民市的设立是马市的一个重要发展,它为山西商人的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马市贸易中,蒙古牧民以出售杂畜、畜产为主,汉民除违禁物外,如棉布、绸缎、纱、烟草等日用品都可上市出售。各镇还“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注:《明史·王崇古传》。)明代中后期,张家口逐渐由军事重镇演变为商贾云集的边贸城市。晋商是马市上最活跃的人物,商品运销多由他们承担。马市的销物以布、绸缎、纱、烟草为主。明代大运河是江南商品销往北方的重要通道,因此北方濒临运河的商埠,如山东临清、河北香河和北京通县遂成为晋商转运南北商品的集散地。山西北部的杀虎口是“云中第一要冲地,自献琛以来,汉夷贸迁,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注:《明实录》万历四十五年六月。)出杀虎口西行,可通宁夏、新疆,往北则可进入蒙古腹地。明代后期每年内地与蒙古贸易“利不下数十万”。(注:魏源:《圣武记》卷一二,《武事会记》。)“自是边疆休息,东起延水,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注:《张太岳集》卷四七。)晋商在马市中的贸易活动使汉蒙民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经济上使中国南北方逐渐联成一个整体。
晋商还积极从事对满洲地区的贸易。据史料记载,“汉民至(黑龙)江省贸易,以山西最早。”(注:余宗亮:《龙江述略》。)明人葛守礼说,“辽东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更过半”。山西介休范氏是清代对蒙、满贸易的卓越开拓者。范氏家族早在明初就从事对蒙边贸,历经七代到范永斗时已成为大富豪。据《万全县志》称,范永斗等八大名商“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范永斗在长期经营对满蒙边贸的过程中,与努尔哈赤等满族后金集团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深受信任。清王朝建立后,范永斗承充内务府皇商第一代,他在其子范三拔襄助下,成为皇商中最受宠遇的一家。(注:汪由敦:《太仆寺卿范府君毓馪墓表》,载《碑传集》卷四二。)
二、由“旅蒙商”起家的清代晋商
清王朝统一内外蒙古后,长城不再是蒙汉往来的屏障,马市随之失去了存在价值,应运而生的“旅蒙商”成为边境交易的纽带。明末旅蒙商曾是为后金统治者服务的随军贸易商,为清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1637年皇太极为了加强对内蒙地区的直接控制,命满洲贵族率100多名汉人商贾,带着货物到归化城(呼和浩特)进行贸易。 康熙中叶,山西商人尾随康熙帝从事随军贸易,在征讨准噶尔部的叛乱中建立了功勋。清人纳兰常安说:“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以其沿边居处,素习土著故也。其筑城驻兵处,则建室集货。行营进剿,时也尾随前进。”(注:纳兰常安:《行国风土记》。)他们深入蒙古草原为清军购买粮秣,运送辎重,甚得将士赞赏。此后以晋商为主体的行商便开始在蒙古和西北地区流动经商,人们称之为“旅蒙商”。
清初政府对汉人赴蒙满地区经商多有限制,但对旅蒙商十分优惠,给予种种特权。如允许旅蒙商到新疆、蒙古的张家口、归化城、多伦诺尔和西宁等沿边城镇进行蒙汉贸易,还可在蒙古伐木出售。康熙后期政府还规定,凡赴内外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地区贸易的旅蒙商人,须经由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归化城将军、多伦诺尔同知衙门批准,颁发准入蒙古的“部票”(亦称龙票)后,可去指定的蒙旗进行贸易。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随着清政府对蒙古地区封禁政策的松弛,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归化城和西宁等长城沿边的几个通道口,成为旅蒙商出入蒙地经商的重要孔道。他们循着古代中原通往蒙古的驿站,逐渐由近及远。从事蒙古贸易的人以山西人为主,其余大多是河北、陕西等地商人。晋商一般是从晋北的杀虎口开始“走西口”,或从张家口开始“走东口”。有的则深入到漠北的喀尔喀、科布多乃至唐努乌梁海,以及西北边疆的古城、伊犁、塔尔巴哈巴等厄鲁特蒙古地区。晋商的活动使沉寂多年的草原丝绸之路重新焕发出了青春。晋商不辞劳苦,几乎跑遍了漠南、漠北和西北蒙古高原的各个角落。他们带着内地所生产的粮食、烟茶、布匹、器皿和生产工具,“以车载杂货,周游蒙境”,换取蒙地的牲畜、皮毛等畜产品以及珍贵的野兽裘皮、金砂、玉石、茸角、麝香和羚角等,然后将这些收购品输入内地出售。随着时间的推移,旅蒙商贩所设的具有固定性质的销售网点不断扩大,于是“行商易为坐贾”,一些旅蒙商在当地建立了永久性商店。据统计,到19世纪60年代,活跃在漠北喀尔喀地区的旅蒙商人就已达20余万,定居的大小商号约500余家。他们在库伦、恰克图、 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地建设了许多宽敞的店铺、货栈和住宅,形成了边地贸易的“买卖城”(注:《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442页。)。
由旅蒙商而发家的晋商不胜枚举。太谷“大盛魁”是清代北方边境的最大边贸商行,其创始人原是该县的三个贫苦农民。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他们跟随康熙帝征剿噶尔丹的部队进入外蒙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充当肩挑小贩,供应军需用品。当平叛结束后,清军营地移驻大青山南,他们也随军转移,在山西杀虎口开设商号供应军需,专营对蒙和对俄贸易。(注:孔祥毅:《清代北方最大的通事行——大盛魁》,《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另一家为祁县乔氏“复盛公”的商号,发迹于包头。乾隆初年复盛公为供应驻军粮秣,在包头(原属土默特旗)开设草料铺,经营豆腐制品、日用杂货,供应当地蒙汉居民生活用品。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成为包头地区首屈一指的钱庄和当铺。(注:刘静山:《山西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介休范氏更是发家于旅蒙商的典型。第三代皇商范毓馪兄弟三人从事随军贸易凡40 年(1697—1737年)。“康熙辛丑壬寅(1721至1722年)间,西征准噶尔, 道远,粮运石费一百二十金,多不能继,公私苦之。毓馪与弟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克期必至,且省国费以亿万计。将帅上其功,赐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弟职布政司参政。”(注:嘉庆《介休县志》卷九,《人物》。)范氏家族在西征平叛中,为保证清军后勤供应立下了重大功勋,受到清廷的奖赏,从此奠定了发家的基础。
准噶尔部叛乱平定后,晋商利用蒙古地区的安定局面以及同内地经济联系的加强,积极开展对蒙贸易,并获得更大利益。外蒙首府库伦是清代晋商会聚的中心。“康熙年间在此经商的山西商人有12家”。(注:《内蒙地志》。)清代后期在库伦的西库东营两区,晋商就有1634人之多,主要经营大宗批发。(注:陈录:《蒙事随笔》。)晋商大盛魁、天义德、元盛德是清代后期对蒙贸易的三大商号。介休商人侯氏蔚字号绸缎行,康熙年间到内蒙以贩卖苏杭绸缎为主,获得巨额利润。道光初年侯氏蔚字号改为票号,专门经营金融汇兑业务。(注:冀孔瑞:《介休侯百万和蔚字号》,《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清代晋商为发展蒙汉边地贸易建立了丰功伟绩。
三、晋商与中俄恰克图贸易
清代中叶,晋商在称雄国内市场和垄断满蒙边贸的同时,大力开拓海外市场,积极参与中俄恰克图贸易和中日长崎贸易,是清代晋商走向世界的壮举。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定之后,中俄关系进入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和平往来时期。《尼布楚条约》规定,“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这就打开了中俄贸易的大门。尼布楚条约后,为了让俄蒙商人来市,清廷在齐齐哈尔城北设立互市地。当时晋商已活跃于黑龙江边贸中。据史料记载,“汉民来(黑龙)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市肆有逾百年者,本金钜而利益厚。”(注:《龙沙纪略》。)可见晋商是中俄贸易的先驱。1727年(雍正五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和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图市约》签定后,恰克图便成为中俄贸易中心,双边交易额迅速增长。双方规定恰克图贸易采用易货贸易方式,禁止使用货币。计价以畅销货为单位,1800年之前用中国棉布,此后改为茶叶。1736年(乾隆元年)清廷规定中俄贸易仅限于恰克图一口,中国商人到关外贸易,必须领取“部票”。从内地赴恰克图贸易的商人大多为山西人。据何秋涛《朔方备乘》记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毯片等物。初立时,商民俗尚俭朴,故多获利。”但山西人的足迹不仅限于恰克图,新疆、满蒙各地的贸易也几乎全由他们垄断。
晋商运销俄国的大宗商品有茶叶、棉花棉布、丝绸、烟叶及家具日用品等,其中尤以茶叶出口为主。19世纪40年代茶叶出口已占首位,到1851年茶叶已占全部出口93%;从俄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毛皮、毛呢哔叽、金属和牲口等。中国对来自俄国的进口货实行免税,因此许多晋商出境赴俄采购,然后运销国内。专门经营恰克图贸易的是山西驼帮,其经销商品以茶叶为大宗,故又称山西“茶帮”。清代山西茶商每年要深入四川 两湖、浙赣、福建等著名产茶省份办茶。其最盛时有100 多家专营商号,并分为“榆次帮”、“太谷帮”和“祁县帮”等。据清人衷斡记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注:衷斡:《崇市杂咏》。)西北重镇兰州城的茶商分为东西两柜,东柜茶商皆山陕之人。而在恰克图,出口茶叶完全由50余家山西茶商所垄断。
中俄恰克图通商后,张家口成为晋商从事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枢纽。出口贸易要先在张家口完税,然后运往库伦,经办事大臣检验部票,发放护照,方可运到恰克图出口。清代中叶,仅张家口专营茶叶贸易的晋商茶庄就有大升玉、大泉玉等十几家。这些茶庄资本雄厚,都是直接从南方茶场采茶进货。每年运往库伦、 科布多和恰克图等地的砖茶多达40万箱(每箱27块,每块2市斤),折合3240万斤茶叶。每年经张家口输往漠北各地销售的绸缎、布匹、茶、烟、糖等生活用品,计银约2083.1万两。由外蒙各盟输入张家口转销中原地区的各种毛皮等畜产品、 野兽裘皮、贵重药材等,约折银1767.5万余两。(注:宣统《商务官报》第7册,1909年刊。)
恰克图贸易给中俄双方都带来好处。道光十七至十九年(1837 —1839年)间仅在恰克图一地,中国对俄茶叶出口每年平均达800余万俄磅,价值800万卢布,约合白银320万两之多;而同期俄国每年由恰克图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仅600~700万卢布,中国由此获得大量以白银支付的贸易盈余。(注:葛贤慧、张正明:《明清山西商人研究》,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页。)1821—1859 年间恰克图俄对华贸易额占俄国全部对外贸易的40%~60%,而中国出口商品的16%和进口的19%都是要经过恰克图贸易的。另外,恰克图贸易为俄方带来巨额的关税收入。1760年俄国从恰克图所收入的关税占全国收入的24%,1775年上升到38.5%。(注:孔祥毅、张正明:《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 《山西日报》1991年11月18日。)
太谷大盛魁是清代晋商从事蒙俄贸易的最大商行,它在乾隆以后的极盛时期,“有职工六七千人,骆驼商队有骆驼16000头到20000头。业务重心在内外蒙古,活动地区包括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以及内蒙古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塔尔巴哈台和俄国西伯利亚和莫斯科等地。内地则以北京、山西、山东、河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为主要活动舞台。其资本周转额仅在外蒙古即达1000万两白银以上。”(注:孔祥毅:《清代北方最大的通事行——大盛魁》,《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大盛魁专门经营茶叶、丝绸、烟叶、布匹的出口,长期保持对俄蒙贸易的垄断地位。清代另一家专门经营俄蒙贸易的著名商号是太谷曹氏家族,它所开设的彩霞蔚、锦泰亨等商号主要经营丝织品贸易。曹氏家族将中国丝绸“运往库伦、恰克图、伊尔库次克、莫斯科等地销售, 每年可运销12000匹,价值白银36万余两。当时做此生意的商号有一二十家,而锦泰亨是其中财力最雄厚的一家。回头货则将俄国的金沙、呢绒、哈喇、毛毯等物,行销内地。(注:聂昌麟:《太谷曹家商业资本兴衰记》,《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清末民初,旅俄商人之多,山西当推首位。1920年阎锡山接见因十月革命而被迫由俄返晋的山西商人代表时,汾阳代表说当时在俄的山西商人有1万人。 (注:孔祥毅、张正明:《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 《山西日报》1991 年11月18日。)
晋商在多年进行远距离的长途贩运贸易中,逐渐开拓和形成一些商业路线。在众多对外贸易商路中,以出长城,北越蒙古,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腹地的商路最为著名,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草原丝茶之路。试以中国福建武夷茶的运输来看,其运输路线是:从福建崇安县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县河口镇装船,顺信水下鄱阳湖,出九江口进入长江;然后溯江而上抵武昌,转汉水至樊城(襄樊)上岸;由河南入泽州(晋城),经潞安(长治)抵平遥、祁县、太谷、大同等地,再北上张家口,贯穿戈壁沙漠,到库伦、恰克图;再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除恰克图贸易外,还逐渐深入到俄国的克拉斯诺亚斯克、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彼得堡等地经商,乃至设立商业分号,成为显赫一时的国际贸易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先后胁迫清政府与之签定《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中俄陆路通商章程》。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沙俄攫取了许多商业特权。1860年俄商在蒙古获得边境通商权,1911年又获得免税贸易权。1862年和1866年沙俄先后在天津获得享受低于列强1/3税率的优惠及海关免征茶叶关税的特权。而晋商却仍需向清政府交纳沉重的厘金税收,在贸易成本上处于劣势地位。八国联军入侵时,俄商趁火打劫,公然拒付购茶欠款,使“大泉玉”、“大升玉”、“大珍玉”等16家晋商损失62万两白银。(注:《清外务部档》卷二二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俄的晋商仓皇出逃,损失白银数百万两。仅“大德玉与连号大美玉、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在莫斯科累赔140 余万两”,(注:卫聚贤:《山西票号史》,说文社1944年版。)事实上中俄恰克图贸易已难以为继。其次,本世纪初西伯利亚铁路、中东铁路以及京张、京绥铁路的通车,使俄国将对华贸易的重心由蒙古转移到东北。中南地区如汉口对俄输出茶砖,向来依靠经由张家口到恰克图的陆上运输。而有了中东铁路后,茶叶出口改为先由内地至天津,然后经大连到俄国。俄商利用中国国内通商口岸的通商特权,直接深入中国内地进行直接贸易。这种状况使晋商在对俄蒙贸易中的中介作用丧失殆尽,并导致张家口、库伦和恰克图等传统边贸中心日趋没落。再次,十月革命的爆发和外蒙宣告独立,沉重打击了一大批多年来经营对俄蒙贸易的山西商号。他们在国外的资产被没收,经营人员被驱逐,不得不宣布破产,从此中俄恰克图贸易便一蹶不振。
四、晋商与中日长崎贸易
山西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历史上中国首次出使日本的使节是山西闻喜人裴世清。(注:《日本书纪》;又见《大日本史》卷一○,《推古天皇纪》。)隋大业三年(607年), 裴世清奉炀帝之命率12人的使节团出访日本,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盛事。明清之前,山西和日本的交流主要集中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唐宋期间参诣佛教圣地五台山的日本高僧络绎不绝,唐代有灵仙大师、圆仁,以及慧运、圆觉、惠运、惠萼、圆修和宗睿;宋代有奝然、成寻,以及成算、祚一、嘉因、寂昭、赖缘等。至于交城玄中寺则因北魏山西人昙鸾和唐代山西人道绰创立净土宗而出名,后来成为日本净土宗人士来华参诣的圣地。
晋商与日本的经济交流始于长崎贸易。长崎贸易是锁国日本仅限于长崎一地的对中国和荷兰的国际贸易,其中尤以中国商船赴日的唐船贸易为主流。唐通事在长崎贸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不仅是翻译官,而且是幕府的商务官和外交官,并负责管理华侨社会事务。江户时代第一任唐通事是山西上党人冯六。(注:[日]《长崎实录大成》卷一○,第361页。)1604年冯六被幕府任命为唐通事, 隶属于长崎奉行(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与中国无外交关系,中国政府也不允许日本船只来华贸易,因此长崎便成为中日国际交流的窗口。冯六出任唐通事时,长崎贸易尚属于初创时期,他为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做了不少贡献,至今他的墓地仍在长崎。
中日长崎贸易又称唐船贸易,广义上的长崎贸易贯穿于整个江户时代。锁国后的长崎贸易可分为三个时期:明末清初为前期(1637至1684年),前期因日本和清政府都实行锁国政策,中日贸易以郑氏集团的走私贸易为主。从康熙开放海禁到日本颁布正德新例为中期(1684至1715年),中期以中国船只大量涌向日本为特征,洋铜进口商以民商(又称额商)为主。后期(1715至1861年)为信牌贸易时期。后期以日方加强贸易管制,减少金银铜出口,铜价暴涨为特征,洋铜进口以官商额商并办为主。介休范氏参加了后期长崎贸易。
从清初到乾隆年间,范氏不仅是最大的满蒙边贸商,也是全国最大的铜商和盐商。清初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铸造铜币成为清廷的当务之急,但国产铜斤严重不足。于是清廷沿袭明制,准许东南沿海省份商人自备船只赴日购买。清初长崎贸易主要以丝铜交易为主,利润十分丰厚。“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易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注:《东倭考》(作者佚名)。)这种状况使内务府所辖皇商不胜妒羡,居于张家口的皇商——介休范氏遂主动申请承办赴日进口洋铜业务。因范氏家族在中国商业贸易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清廷同意其办铜要求,于是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长崎贸易活动。
范氏对日贸易始于1738年,结束于1783年,是清代中叶经营对日贸易时间最长的皇商。其主要经营者开始是范毓馪, 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先后是第四代皇商范清洪、清柱、清济等人。 乾隆三年(1738年)范毓馪“奉命采办洋铜运京局,以抵分限应输之数。……铜产东南外长崎诸岛。……府君(范毓馪)立命人驾巨舟赴洋采办”(注:汪由敦:《太仆寺卿范府君毓馪墓表》,载《碑传集》卷四二。),范氏商船在长崎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以前,按照德川幕府规定,清朝赴日洋船商(官商和民商)船只数共有15只,其中范氏为3只。乾隆三十一年至四十八年间, 中国每年赴日洋船总数不变,而范氏拥有的洋船数经常在六七只之间。每年每船约运10万斤铜,总共运60万斤以上,范氏一家的洋铜进口量占中国洋铜进口总额的一半左右。范氏的洋铜贸易具有内外贸易相结合的特点,洋铜进口后要立即运往指定的省会去出售。乾隆九年(1744年)范毓馪“有承办运米、运盐及销售参票未完各项银114万余两,应令其办铜完补。 每年办洋铜130万斤。解运直隶保定府30万斤、陕西西安府30万斤、 江苏苏州府30万斤、江西南昌府25万斤、湖北武昌府25万斤。于本年置货出洋,自乾隆十年始,按数陆续交纳。”(注:《清朝文献通考》,第五○○页。)在办铜贸易中,范氏享有许多民商难以享受到的特权。乾隆九年规定“其铜办回经过各关,免其纳税。”(注:《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六《钱币考》。)政府对于赴日所带的出口货物也给予各种照顾,特准配给一些日本短缺的畅销商品,如生丝、绸缎、药材、糖等,洋铜商可以不受“丝斤出洋之禁”(注:《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七《钱币考》。)。范氏既能在出口货源上得到保证,又能取得贩铜权利,这是除铜商外任何人所不敢企望的事情,足见清廷对范氏的重视。但是,由于中日丝铜价格的大幅变动以及皇商经济本身的局限性,乾隆三十年后范氏的洋铜贸易和河东、长芦盐场的经营连年亏损。乾隆四十七年介休范氏家产被抄,其所从事的长崎贸易宣告结束。
五、山西票号与中国近代对外贸易
票号是近代中国独特的金融组织,票号的出现促进了商业经营资本与金融资本密切结合,将传统的中国商业资本运动推向了最高峰。票号作为工商业者从事埠际货币汇兑的专业信用机构,不仅促进了国内商品的流通,而且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也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19世纪60年代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已经超过广州,19世纪末上海外贸总额已占全国外贸总额的44.2%。(注: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69页。)上海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也是最大的外贸和金融中心。对外贸易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组织。在当时上海的金融界,外国银行、山西票号和上海钱庄呈鼎足之势。上海中外银行虽多,但在国内分布和通汇方面,仍“赖有票号为之周转”(注:潘承锷:《中国之金融》上册,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版,第53页。)。长期以来票号存款大于放款,其存款行主要集中在北京和票号总号所在地——平遥、祁县、太谷,人们称之为“北存南放”。上海成为金融中心后,上海也成为票号的存款行,“北存南放”变为“南存南放”。票号借贷资本的大进大出,极大地支持了上海的对外贸易。有人估计,日升昌等22家票号1910年汇兑总额为82404.4万两,这个数字与同年中国进出口总额84300多万两基本相等。 (注: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87年5月版。 )可见,票号汇兑在商业贸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票号与钱庄的关系来看,在上海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在金融调度上主要是使用钱庄庄票,但上海钱庄的资金并不雄厚。19世纪70年代以来,上海钱庄之所以能够在对外贸易活动中提供数十倍于资本的信用贷款,乃是因为它取得了外国在华银行和中国票号的信用支持。从资金运动的角度分析,钱庄并不是票号信贷资金的归宿;票号贷放给钱庄的资金必然要流到经营国内外贸易的商人手中。就是说,票号的生息资本通过钱庄以经营资本形式活跃于国内市场。如东印度公司要在上海购买100担生丝,委托广州某洋商代办;该洋商付款给当地钱庄, 让他们将款交给上海该洋商的代理人,以便就近购买丝。广州钱庄因在上海没有分号,乃托当地的山西票号,请其将款汇往上海。广州的山西票号随即开出汇票,上海的山西票号得讯后,嘱托上海钱庄将现款交付广东洋商所指定的在沪代理人,以便购丝寄回广州。事实上,票号并无现金转运,因为当东印度公司在上海付款购丝的同时,也许正在九江出售毛呢。山西票号在广州、上海、九江三地均有分号,通过票号结算,可使进出口业务更加有效、便捷。若两宗款项相等,即可两方相抵;若款项不等,可俟下回做生意时再结算。(注:陈其通:《山西票庄考略》,大东图书公司1936年,第159页。)可见, 票号的金融业务是与近代对外贸易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进出口商人在外贸活动中必须依靠票号和钱庄的共同支持。清末山西票号在全国各个通商口岸都设有分号,形成一个巨大的金融网络。票号的信贷活动及其与钱庄的配合加速了口岸和内地城镇商品流转的速度,既扩大了国内市场,也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山西票号不仅在中国商业金融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标签:蒙古文化论文; 晋商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山西经济论文; 明清论文; 清朝论文; 对外贸易政策论文; 历史论文; 明朝论文; 中俄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