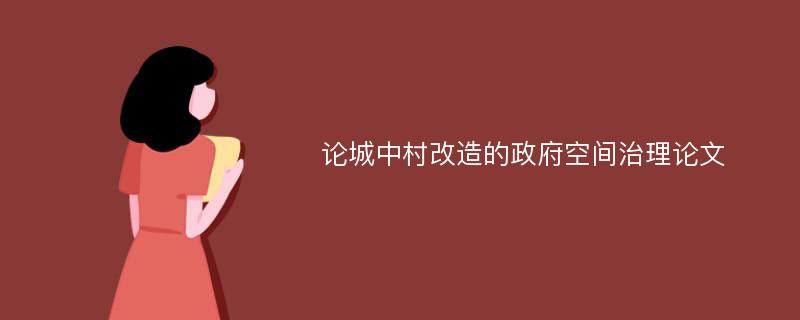
论城中村改造的政府空间治理
◎吴莉娅 (苏州大学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 在“棚改”中,扶贫的国家叙事与城市叙事介入个人和集体空间,“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模式诱致城中村改造呈现改造主体外部化、改造目标公共化、改造知识去地方化、改造结果士绅化等空间生产困境,大多数城中村常住人口居住处境改善程度有限。基于可持续人居目标,批判和导正空间异化的现实逻辑,政府应将空间正义作为价值导向,以房屋使用价值回归为焦点,通过包容性和整体性空间治理,促进城中村改造主体的多元合作共治、过程的包容开放、成果和收益的普惠共享,实现对弱势利益相关者的特别关注,构建空间再生产图景,实现既有企业家城市治理逻辑的突破与空间治理绩效的提升。
关键词: 可持续人居;城中村改造;空间生产;政府空间治理;包容性治理;整体性治理
城市“空间是一种在全世界都被使用的政治工具”“它是某种权力(比如,一个政府)的工具,是某个统治阶级的工具……空间的表现始终服务于某种战略。它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既是思想的也是欲望的,也就是被规划的”[1]。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变革引发人类聚落剧变,进而诱致了政府空间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导向。
在泌乳素测定上,采用ADC CLIA400全自动微粒子化学发光仪,对泌乳素进行测定。在试剂盒方面均采用该公司配套的试剂盒;在定标液方面均采用配套定标液。同时检测患者血脂。在治疗前、后对以上指标重复测定,并实施对比。
一、可持续人居:政府空间治理的理论逻辑
“对空间的思考是社会科学现代性框架的产物”[2]。“空间并不是平均化的毫无差别的容器,空间是被人们按照权力意志建构起来的,不同的权力关系将产生不同的空间关系”[3]。政府作为城市空间生产主体,其空间政策制定与执行既是贫民窟和棚户区产生的诱因之一,又致力于消解这种空间非正义。以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引,人类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政府空间治理的重要议程。
(一)异化了的城市化:城市空间生产中的政府失灵
城市规划是政府主导空间生产、应对城市危机、构建空间治理的政治逻辑的重要凭借,建设无贫民窟无污染的田园城市群疏解大城市人口,与以技术性手段全面改造城市物质环境、提高城市容纳能力的空间构想,深刻影响20世纪中叶以来政府空间治理的政治逻辑与行政行为,既诱致“标准化”街区替代历史形成的个性空间的“创造性破坏”的城市叙事,又指引规模宏大的新城新区空间生产的国家叙事和城市叙事,亦衍生出空间异化与空间剥夺困境。
政府与市场的增长联盟推动欧美城市建设重点由市区向郊区转向。基础设施落后破败及公共服务不足的空间实践,萧条、滞胀、低就业率的经济空间与高犯罪率、大规模冲突、骚乱的社会空间交织的空间表征,缺乏生气与希望的棕地、灰区、贫民窟的空间想象,所有这些既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逻辑主导的内城空间生产的产物,又预示资本循环过程中内城空间再生产的可能。
1.以整体性治理概念重新界定政府的主体地位与作用,有机整合城中村改造中空间再生产涉及的政府组织层级关系,加强各政府组织层级间的协同与合作。城中村改造涉及城乡住房与建设、社会保障、国土(自然)资源、城市规划与设计、市政、园林绿化、公安、消防、农业农村等多部门。以大部制改革深入推进为基础和支撑,在城中村改造中,各级政府之间、各政府部门之间可以“借助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立足于整体主义思维方式,通过网络治理结构培育和落实协调、整合以及信任机制,充分发挥多元化、异质化的公共管理主体的专有资源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强大合力,从而更快、更好、成本更低地为公众提供满足其需要的无缝隙的公共产品和服务”[31],着力推动政府职能向城中村改造更新规划、居民权益保障、社会秩序维护、依法行政与监督检查等方面转变。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低成本城市化战略与城乡二元体制等使中国城市中形成了较大面积的棚户区,也诱致了城中村这一特殊棚户区类型。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是城市空间生产的唯一主体,意识形态冲突直接而强力诱致了城市的内生发展,形成“异化了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薄弱的国民经济基础、乏力的政府财政、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等直接导致城中村的出现。城中村常常被国有土地包围,集体土地性质及基于此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匮乏、规划缺失、监管缺位,使城中村成为城市异化空间。“异化了的城市化”倾向限制了这一时期城中村的数量和规模,社会力量是这种被城市包围的“传统”村庄的空间生产的最重要且近乎唯一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仍然是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重要主体,弥补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历史欠账与工作、游憩、居住、交通空间不足成为重要任务,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以开发区、新城建设为主的“被动城市化”发展模式。这一阶段,“蛙跳”式的城市开发遍地开花,导致城中村的数量与规模迅速增长,在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导致的巨大的住房市场需求,政府与滞后的房地产市场的有限住房供应之间,形成巨大的住房(租房)缺口,灰色市场、非正规经济、社会力量主导下的空间生产导致城中村“异化空间”进一步异化,形成容积率上升、土地开发强度加大、公共绿地与公共空间严重压缩等的空间实践(体验),事故与冲突频发、制假售假温床、落后与愚昧等的空间表征(感知),以及升值潜力巨大、拆迁成本高昂的高度内生型、传统市场与社会力量发达的超级“异化”空间的表达的空间(想象)。城市“异化空间”的进一步异化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政府失灵。
(二)适当住房与可持续人类住区:政府空间治理的理论逻辑
基于全球范围内城市贫困与住房问题,1976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一大会)首次提出“人居环境”概念;1977年,《马丘比丘宪章》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城市和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强调了公众参与的极端重要性,“鼓励建筑使用者创造性地参与设计和施工”[4]25-26。1978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详细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强调“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兼顾”;1992年,《全球21世纪议程》把人类住区的发展目标归纳为“改善人类住区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质量,以及所有人(特别是乡村的贫民)的生活和居住环境”;1994年,《中国 21世纪议程》指出“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未来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大会)审议了“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和“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两大主题;1998年,《北京宣言》提出建筑学的循环体系和根植于地方文化的城市与建筑发展观[4]26-28。2002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设立举办第一次世界城市论坛,其后每两年召开一次,至2014年已经召开了七届,分别以“可持续的城市化”“城市——文化十字路口,包容与综合”“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由理念到行动”“和谐的城市化”“城市权利——促进城市平等”“城市未来”“在发展中实现城市公平:生活型城市”为主题,通过了一系列行动方案,促进可持续人居的探索与实践不断深入。2016年,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发展大会(人居三大会)以“探索可持续的城市化和我们现有城市的未来”为主题,审议通过《新城市议程》,该议程强调通过创新与协同“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5]。2018年,第九届世界城市论坛以“2030年的城市,人人共享的城市:实施《新城市议程》”为主题,确立行动领域,致力于可持续人居全球愿景的实现。
与“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14]的新型聚落的空间理想不同,在现实中,城中村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把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拼贴在一起,它们既彼此融合,又互相排斥,形成各具特色的多元混合式高熵值空间。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资本积累不但因社会差异和异质性而茁壮,更积极生产了社会差异和异质性”[15],推动中国城市由“空间中的事务的生产”向“空间本身的生产”[16]173-174转移,也导致城中村充满了根植于二元经济时期、成长于“企业家城市”阶段的“从国家、金融资本和土地利益的结盟中创造出来的”“新空间关系”[17],而零星的地方自发的城中村改造探索以及全国范围的自上而下强制在没有改变这种“国家、金融资本和土地利益的结盟”[16]173-174的情况下,导致以人本关怀为基础的空间异化。
二、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政府空间治理的现实逻辑
棚户区改造的自上而下制度强制打断了城中村空间生产的自发性、草根性、内卷化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扰动地方政府对城中村空间生产的权力干预的方式和程度。“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改造模式的确立导致国家叙事与城市叙事介入个人和集体空间,生成了整齐划一、标准而抹杀历史痕迹的改造后居住景观,改造后的城中村空间作为新的空间文本,又进一步表征着当下的国家式扶贫与棚户区改造文化、企业家城市治理逻辑,亦引发了城市中国“驱离”[7]的思考。
总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如何完善和发展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也是当前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工作。基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视角来探究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状况,为解决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提供重要的解决路径,在构建和完善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改造主体外部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26],城中村改造必须摒弃“经济的飞速发展依赖于迅速的消耗,依赖于不断替代的新产品,并因此而拒绝使产品长寿,因为获益的欲望只有在不断的替代中得到暂时的满足。事物是为了消耗而被生产出来的,它们越快地被消耗尽,它们就越轻易地被替代”[27]这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产品—资本”关联逻辑在空间生产领域的渗透。这种“产品—资本”关联逻辑贯穿于资本的三次循环当中,即不仅包括日常用品、耐用消费品、奢侈品,还包括生产性建成环境和消费性建成环境,以及科研教育休闲产品。破除这一“产品—资本”关联逻辑与物质空间决定论、理性主义、机械主义、“一张白纸作图”的耦合,回归到可持续人居这一空间生产的理论逻辑,以房屋(住房、工商业用房)使用价值这一核心价值回归为焦点,重构城中村改造中空间再生产图景。
超高的人口密度、人口规模、容积率使城中村被各级政府持续关注,城市社会经济转型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历史任务使城中村改造成为重点民生项目。在珠海、杭州、深圳、广州等城中村改造先行地区,政府都是最主要主体,甚至是唯一排他性主体,城中村改造的区域选择、区域性质(重点村、一般村)、改造方式、拆迁补偿方式等基本上完全由政府决定。
“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生产剩余价值”[8]4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使城中村土地资源配置问题及潜在的巨大地租价值为市场所关注,市场(资本)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途径进入城中村的空间演替或改造当中,积极而活跃。如在深圳,“万科、金地、碧桂园等房地产公司在城中村里获得大量民居,改造后推出价格更高的长租公寓”,许多房地产公司在“城中村改建中投入不少资源”[9]。
1.政府通过摸排与调查,在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指导下,确定城中村改造区域范围,根据地理位置、规模、重要性等确定城中村为重点区域或一般区域,根据地理位置、大小、形态等确定改造后的用地性质和容积率,并确定相应的改造方案、投融资方案、拆迁补偿方案、居民过渡安置方案等,充分表明城中村改造的整体性和社会治理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城中村及周边人口积累形成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经历的社群[10]极其脆弱,在城中村改造中的话语权有限或缺乏。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鼓励的“建筑使用者创造性地参与设计与施工”[4]26在城中村改造中被无视或忽略,城中村大量居留的、远超户籍人口的非户籍常住人口在城中村改造中没有参与权,甚至没有发言权。村集体作为土地的原所有权人、原住民作为土地使用权人,参与程度视代表人物精英化程度(人大代表等的人数)而定,总体来说,其话语权亦相对有限。
(二)改造目标公共化
城中村改造不仅意味着居住设施和环境的改善,还意味着不完全城市化的“异质空间”的祛除。从土地权属、社会治理和居民社会身份变化视角来看,改造后,土地权属由集体所有改变为国家所有,撤村(委会)建居(委会),村民变市民,村办企业改为股份公司,村民变股东等。于是,城中村改造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再是为了谋求更多居住空间或租房空间的单纯的个体行为,而是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社会经济转型的公共行为。从定点、规划到实施的过程表明,尽管具体改造模式多样,大拆大建、小拆小建、综合整治等不一而足,但整体而统一的改造被赋予特别的关注和强调。
规划师和建筑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在不同环节作为权力或资本的代言人,在有限的调适余地里,基于规划理念或理想为城中村的社群或历史特色空间发声。
同时,数字化进程也帮助公司优化内部流程,比如业务流程文本的挖掘就是最直接的方式。高效的内部流程也是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所必需的。即使在数字化的世界中,电力产品不会发生属性上的改变。改变的只是分销渠道和客户需求。客户正在从单纯的需求方,向市场的参与者转变,能够切身影响市场的活动。客户的需求,变得更加个性化和多变化。在销售方面,数字渠道平台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推广效果。公司可以通过更多的形式与客户的绑定在一起:线上,移动互联,呼叫中心和现场销售等等。同时,这种绑定在数字化背景下,也为公司提供了深入分析的底层基础。
2.城中村改造规划、设计方案由政府发包,中标规划设计单位依据规划要求、地块用地性质、容积率、市场前景等对整拆整建、综合整治等的城中村进行整体的规划、设计,一些小拆小建的城中村也要依据整体的规划设计方案进行小规模小范围的拆建及形象整治,形成整齐而统一的建筑风格和城市景观。
3.城中村改造进度受到整体观念影响,改造进度并非仅仅对单个城中村改造的具体工程进度的阶段性描述,既是对权力与资本共同作用下的城市“草根”“异质”空间进行整体性重构的抽象描述,也是政府拨款、多渠道融资、用地指标安排等的考核依据和计划依据,还是对城中村改造进度进行管理的重要指征。
因而,城中村改造的综合部署、具体安排、实施管理,均表现出外部力量对作为公共事务的城中村改造的整体性地特别关注。在这样的语境下,城中村改造作为政治性鲜明的社会治理的整体性的强调更加显著,远超具体城中村案例的改造(整治)或村民个体对家园的改造,具体城中村的改造或村民个体改造只有在构成整体的情况下,其空间生产的政治性、社会性意义才能明确。
通过L9(34)正交试验得到卷曲形茶最佳做形工艺:揉捻压力为揉捻机加压力度的1/5,次数2次,时间5 min。在此条件下干茶外形条索尚紧、较弯曲、较绿、有毫、匀整;清香高长,汤色黄绿明亮,滋味醇正,叶底黄绿明亮、鲜活,完整,感观审评综合得分94.06分。碎茶率为0.57%。
(三)改造知识去地方化
城中村改造中空间生产的主导知识表现出明确的现代主义、去历史化、去地方化特征。地形地质测勘、基础资料收集、村庄规划、社区与道路设计、建筑样式与屋顶屋面设计、户型设计、建筑施工、工程监理等均以外部知识形式进入改造过程并起主导作用,这些外部性“普适”“标准化”“科学”知识抽离城中村独特的地理、历史、生活情境,强势介入城中村这一“二元”自发演化社区,并与地方性知识碰撞,直接表现为外部知识对地方性知识的冲击、压制与替代。
1.标准化科学知识主导、大量地方化知识被否定。“规划引领”是城中村改造的基本原则,而这一原则又以“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11]为第一要务,规划设计单位按照《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等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提供改造方案,而政府部门审核监督的依据亦是相关法规和技术标准,这种“标准化”“科学”规划设计方案的实现实质上意味着与城中村自发形成的超高建筑密度、高容积率、低绿地率、超高土地混合利用、“多合一”空间、街道客厅等空间特征的割裂,城中村在现代化、城市化冲击下形成的房屋建造习惯、方式,经济、社会空间融合共生的社区营造模式等成为被否定、被舍弃的知识。
2.部分地方化知识被切割、移植、符号化与被忽略。专业素养使规划师、设计师、建筑师等在“标准化”“科学”知识运用中或多或少地始终关注着地方历史文化保护,而这种保护因巨大的市场价值亦被房地产商重视。在具体改造过程中,尽管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并未被完全否定,但被切割、移植、符号化为受社会公众认可或关注的建筑营造符号。如“青砖黛瓦马头墙”成为江南地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符号和象征之一,并通过“情怀”“营销”被广泛应用与接受。部分地方突出的文化元素被提炼出来作为标志或Logo 大量复制运用,而真正的浩繁庞杂、地方化色彩浓厚的传统建筑技艺与表现形式、工匠的个人经验与方式、传统建筑材料被忽略。
(四)改造结果士绅化
政府、市场、技术精英对城中村“草根”自发演化的多元混合式高熵值空间的“教科书式”批判要求给“工作、生活和文化分类和秩序化”,整体上否定了原住民与外来人口以“工作—场所—人”紧密联系为基础、对具体问题的应激性个性化应对的地方化知识诱致的多样化、冲突而又互相包容的复杂复合空间,取而代之以标准、科学、现代化的城市空间,从社会结构视角来看,则表现出士绅化倾向。一是城中村改造后,中高收入居民占比大幅提高,在一般情况下,改造完成后回迁人员占比相对较低;二是城中村改造后,原有高度异质性的“多合一”空间转变为功能分区明确的空间、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限由模糊且共容转变为清晰且分明;三是城中村改造后,街区特征和文化品位发生变化,中产阶级精致生活、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新潮文化取代了传统文化、草根文化、大众文化,仅部分传统文化、草根文化、大众文化元素可能会作为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表征而在形式上被保留下来。
城中村改造切实提高了原有街区的居住空间质量,但大多数原城中村低收入居民享受到的改造成果未能使其得到充分满足,他们迁往更边缘的棚户区或正在形成的棚户区,甚至迁往其他城市,他们的经济处境与生活环境未发生本质上的改变。这在事实上造成了“主体居住空间的分异与隔离”[12],包括“物质空间的隔离、社会空间的隔离和文化——心理空间的隔离”[13],这也是当前被热议的城市中国“驱离”的主要诱因。
三、空间正义:政府空间治理的价值导向
“住者有其屋”“享受平等的发展机会”以及良好“生活和居住环境”是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基于此,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引,政府与市场的增长联盟期望通过空间再生产消弭内城、贫民窟/棚户区的“异化”空间和“差序”空间,世界范围内的内城更新、贫民窟和棚户区改造开展起来。空间作为现代国家对个人的管理和控制手段[6]的属性导致这种更新与改造既与政治紧密联系,又是资本逻辑运作的必然要求。以可持续人居、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为目标和导向,以深圳等地城中村改造探索性实践为先导,中国政府推出改造城镇危旧住房、改善困难家庭住房条件的民生工程,这一战略决策奠定了全国范围内的城中村改造的政策基石。
马克思认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8],而空间“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看起来其纯粹形式好似完全客观的……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19],这意味着,一切公民都应当具有平等的空间权利。“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20]1。空间正义作为城中村空间再生产的价值导向,既是对可持续人居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响应,也是对空间剥夺和异化的现实逻辑的批判和导正。
案例基于生产实践,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思维的活跃性,增强学习理论知识的渴望性,并对案例中的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通过对案例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和触类旁通,学生要反复思考、分析和探究,从理论的高度审视案例,以便真正掌握理论和实践知识,能够把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起来,解决实际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培养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
空间正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分配正义。“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这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20]292;其二,权利正义,城市权利“是一种高级的权利形式,包括实现自由的权利、在社会化过程中实现个体化的权利、享有居住环境的权利、生活和居住的权利;同时也包括参与权和占有权(侧重于对使用价值的占有而非财产权)”[16]173-174,城市居住者们“不被排斥于城市中心和城市运行之外”[21],并“远远超出我们所说的获得城市资源的个人的或群体的权利……按照我们的期望改变和改造城市”[22];其三,社会正义,即“领地再分配式正义”“社会资源以正义的方式实现公正的地理分配,不仅关注分配的结果,而且强调公正地理分配的过程”[23],“社会空间的分配不但要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而且额外的资源应该用来帮助那些由于自然和社会环境导致特殊财政困难的区域”[24]。
空间正义,“正义/非正义(是正义和非正义一词的结合)的空间性影响社会和社会生活,就像生活过程构成正义/非正义的空间性或者特殊的地理学一样”,空间正义是“正义的空间性”,既不是指“正义仅仅取决于其空间性,也不是说空间正义应被视为社会正义很多方面或者要素之一”,而是“所有社会事物(也包括正义)同时且内在具有空间性,就像任何空间事物,至少在人类世界中,同时且内在地具有社会性一样”“空间性地看正义”“寻求的是提升民主政治和社会积极行动主义的更为进步、更可参与的形式,为动员和维护社会的内在联合,草根的区域联合,以及正义指向的社会运动提供新的理念”[25]。
作为异化空间的城中村既是政府职能缺位与市场失灵的产物,又因此进入政府与市场的视野,“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改造模式意味着城中村改造由外部力量主导。
四、包容性治理:政府空间治理的行动路径
“空间是社会性的”[8]48。在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包容性治理来应对城中村改造中的空间异化和剥夺,“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让“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28]。包容性治理,一是指包括穷人、妇女、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土著民及其他弱势群体等在内的所有人都能够实质性地参与治理过程,并影响与自身相关的决策;二是指治理制度和政策对弱势群体而言是可行、负责和回应性的,治理制度与政策能够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并为不同群体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机会,如公正、健康和教育[29]。包容性治理强调主体的多元合作共治、过程的包容开放、成果和收益的普惠共享、对弱势利益相关者的特别关注[30]。
(一)推动多元主体共治
以空间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进行空间再生产,推动多元主体共治,消除城中村改造主体的外部性,尤其是正视城中村居民的城市权利和差异权利,即政府向城中村居民充分授权,使他们能够真正有效地参与到城中村改造当中。
生活中,学习中,到处布满荆棘,常常听到很多人在感叹生活或学习中的苦闷。大自然尚且阴晴变化,何况是人呢?所以,当你被失败和挫折的阴影笼罩时,不妨点亮心烛。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政府在就业与住房供给上存在职能失位、缺位,日益增长与规模扩大的贫民窟、棚户区等成为大多数乡村移民的生产与生活空间。
应对场景:I)研究人员对其研究领域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的需求,以帮助其更好的开展研究工作;II)研究人员、高校教师、学生发表论文的需求(含写论文、投稿等);III)科研机构购买多家服务商的数据,需要整合数据统一服务的需求或者国内外服务商合作互补数据(数据接口)
2.以“建筑使用者”概念重新界定城中村改造公众参与主体,在“租售同权”原则得到法律认可的前提下,赋予常住外来人口(租户)城中村改造的参与权。“城市权利不包括从上而下分布的权利,是一种积极地共同参与城市政治生活的方式……因此,城市权利不仅是参与权,更重要的是授予权”[32]。城中村居民人数众多、构成复杂,经济处境、社会身份和政治倾向多样,阶层与层界多元化,并与村集体与原住民、开发商之间形成了以土地或房屋租赁为基础的松散而脆弱的利益联盟。城中村常住居民尤其关注房屋的使用价值这一本源价值,只有对这一团体充分赋权,才能消除资本逻辑对城中村空间再生产可能施加的负外部性影响,实现“房子是用来住的”“居者有其屋”的发展目标。
3.审慎对待城中村改造中的市场主体,既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要积极防范资本逻辑的负外部性,防止城中村改造公共化目标的资本化偏移。肯定资本的力量,允许参与改造的房地产企业的合理利润,但限制其对城中村“在土地上进行建设、聚居而获得的增值”以及改造后因“地租缺口”和垄断地租产生的超额利润的攫取,对房地产企业有限理性可能带来的泡沫风险进行有效预测与监管。
(二)促进程序公正
以空间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进行空间再生产,促进城中村改造过程的包容性、开放性,消除改造知识的去地方化、消除基于改造公共性目标的改造过程的整体性、统一性。程序公正“本质上不是一种过程价值,它主要体现于程序的运作过程中,是评价程序本身正义与否的价值标准”[20]234。
每台设备需要配备3人及1台运输切缝用水三轮车,每天切缝80m,折合成本5.75元/m。通过对比分析节省总成本38.88万元,速度快2.5倍。
1.明确城中村改造中空间再生产过程的标准和规范,通过对城市更新、棚户区改造的法律法规、政策、技术标准、实施细则等的完善,填补现行土地政策和规划体制在城市再开发方面的空白,形成覆盖法规层面、政策层面、技术标准层面、操作层面的更新改造制度体系,构建包容性的规划、建设、管理机制,以有效地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有效地保障各类主体的参与权,明确各类主体在更新改造全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权力与权利,并明确违法违规后的惩处内容与方式。
2.突出城中村改造中地方化知识的运用,既充分尊重规划师、设计师、建筑师、开发商在其专业领域的专业素养与现代化知识,又充分尊重地方发展历史,在接受现代文化冲击、外来文化融入的同时,切实保留与传承地方特色历史文化元素,保留其原真性,以此作为核心要素凝聚起社区的特性与标识性,形成场所感,激发居民的归属感与荣誉感,使他们自愿自觉地加入到城中村社区的更新改造与后续地方创生活动之中。
材料在质地和色彩中都存在不同的差异性,要想将这些材料综合运用起来,就必须通过对建筑物整体设计的了解,通过协调处理,并加以合理利用,从而形成和谐统一的建筑外观装饰效果。
3.拓展城中村改造中公众参与内容和形式,增加城中村改造相关政务公开的内容,充分保障城中村居民在改造过程中的知情权、决策参与权和救济请求权。突破当前城中村改造公众参与停留在通知、新闻发布、规划公示及展示等形式主义“走程序”困境,将公众参与贯穿于城中村改造的决策、规划、建设、治理的全过程。通过“倡导式规划”,“为广泛的社会团体服务”,并“用规划来支持最需要支持的人”,实现“平等和反贫困”[33],促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同与共同决策,协调分配多元化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利益。从“市民参与阶梯理论”[34]的“无参与”层次或“象征性的参与”层次逐渐上升到“市民权利”层次,充分行使主体的权利,尤其是决策的权利,实现分配正义、权利正义、社会正义、空间正义。
通过对横店影视职业学院进行普遍调查发现,足球选项课整体开课情况处于良好状态,学校利用不同形式开展足球课程,有力地推动了足球运动在本校的开展。某些活动的组织和开展不是很充分,是由于学校对足球课的设置重视程度还不够,认为足球运动身体对抗激烈,动作幅度大,难以控制,学生在短时间内较难训练和掌握,比较容易出现运动伤害和事故,所以对足球相关活动持观望的态度。
(三)实现成果共享
以空间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进行空间再生产,实现发展结果的包容性,改变以资本逻辑与技术官僚主义为支撑的“大拆大建”改造模式,消除改造结果的士绅化倾向,促进改造成果的多样化和改造成果与利益的共享。
1.促进城中村改造中空间再生产成果的多样化与差异化。针对城中村的位置、规模、建筑生命周期阶段和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管理等特征,构建城中村改造分类体系,在以相关技术法规和部门规章为基础的“标准化”空间再生产基础上,因地制宜地确定多样化、差异化的空间再生产方案,促进多元混合式高熵值空间向多元混合式低熵值空间转变。以回归房屋使用价值为核心和目标,确立以“微改造”为主导的城中村改造更新模式,吸收借鉴深圳、广州等城市的经验教训,把重建、改建与综合整治结合起来,对于能够通过改建、综合整治达到一般城市建筑质量标准的集中连片房屋,尽量不拆除,通过基础设施配套、环境卫生和社会治安整治来提高其宜居宜业程度;对于确需整体拆除重建的区域,在重视物质空间规划设计的基础上,更要注重社会规划、文化规划、生态规划,提高治理水平。
疏旷高远、曲折无穷的空间意识是王维山水诗的主要构图,此外,王维的诗中亦有如“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所表现的一个由光与影构成的明暗映衬的如西洋印象画般的空间意识。
2.实现城中村改造中空间再生产成果和收益的共享。“空间和时间实践在社会事务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们始终都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35]。土地作为空间的自然承载物和基础,空间正义不可避免地与土地制度与地租联系起来,正如马克思指出,“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当作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私人意志的领域”[36]695,“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地租的量(从而土地的价值)作为社会总体的结果而增长起来”[36]718,在土地私有制下,“土地所有者只是坐享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中一个这样无须他参与而不断增大的份额。这就是他所处地位的特征”[36]719,即地租“由于支配一种可以和他的资本分离、可以垄断并且数量有限的自然力而产生”[36]728。这一论断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当前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某些激烈冲突爆发的根源,以及最广大“建筑使用者”被排斥在改造主体之外的原因。城中村土地价值与房屋价值的增值,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地产品的价值,从而土地的价值……随着非农业的商品生产者人数和非农业的商品生产量的扩大,按相同的程度增加”[36]719。正视城中村土地增值的源泉,将其源于“在土地上进行建设、聚居而获得的增值”“地租缺口”和垄断地租的收益在其直接利益相关者与非直接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尤其关注真正的建筑使用者这一被无视或忽视的群体,打破城市政府与村集体凭借土地所有权人身份、原住民凭借村集体成员及土地使用权人、房屋所有权人身份、开发商凭借土地使用权人身份排他性垄断城中村改造带来的以地租收益为主体的一切收益的格局,也即突破当前所有权利益相关者主导城中村改造格局,关注空间依赖性利益相关者与社会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与作用。并以“微改造”为主导模式进行城中村改造空间再生产,为最广大的建筑使用者(租客)提供可支付的、“适当的住房”,促进改造成果的共享。
参考文献:
[1]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第 2 版.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4.
[2]赵衡宇,等.乡一城移民聚居空间实践及其文化调适[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103-108.
[3]ELDEN S.Mapping the Present: Heidegger, Foucault and the Project of a Spatial History[M].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 2001: 6.
[4]戴慎志.城市规划与管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5]毛其智.“人居三”与《新城市议程》[J].人类居住,2016,(4):55-64.
[6]FOUCAULT M.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M].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1979: 25-87.
[7]萨森.大驱离:揭露廿一世纪全球经济的残酷真相[M].台北:商周出版社,2015:3.
[8]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C]//.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王志弘,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9]不拆了,深圳城中村由“拆”变“治”[EB/OL].(2019-04-01)[2019-04-06].https://mp.weixin.qq.com/s/G_yh8Yn_Z8Tm1c_ykwm7hw.
[10]CAMPBELL C & WHITTY G.Urban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Section Editors’Introduction [M].In PINK W T & NOBLIT G W(Eds)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Urban Education.Dordrecht:Springer,2007:929-942.
[11]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规划编制办法[EB/OL].(2005-12-31)[2019-04-06].http://www.mohurd.gov.cn/fgjs/jsbgz/200611/t20061101_15 9085.html.
[12]王志刚.社会主义空间正义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67.
[13]王红阳.空间正义:我国城市空间生产的基本价值取向[J].青海社会科学,2017,(4):92-97.
[14]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倪文彦,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66.
[15]大卫·哈维.资本的空间[M].王志弘,等,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181.
[16]LEFEBVRE H.Writings on Cities [M].MA:Blackwell,1996.
[17]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M].黄文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3.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4.
[19]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C]//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王志弘,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62.
[20]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1]LEFEBVRE H.The Urban Revolution [M].Minneapolis,MN: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150.
[22]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M].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4.
[23]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3.
[24]李佳依,翁士洪.城市治理中的空间正义:一个研究综述[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3):14-22,46,126.
[25]苏贾.寻求空间正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5-6.
[2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2017-10-28(001).
[27]张兴成.现代性、技术统治与生态政治[J].书屋,2003,(10):4-12.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3.
[29]UNDP.Towards Inclusive Governance: Promo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Asia-Pacific[M].Bangkok, TH:United Nations Pubns, 2007: 9.
[30]李春成.包容性治理:善治的一个重要向度[J].领导科学,2011,(19):4-5.
[31]胡象明,唐波勇.整体性治理:公共管理的新范式[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11-15.
[32]彼得·马库赛,等.寻找正义之城[M].贾荣香,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96.
[33]于泓.Davidoff 的倡导性城市规划理论[J].国外城市规划,2000,(1):30-32.
[34]ARNSTEIN S R.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1969, 35(4):216-224.
[35]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周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99.
[36]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中图分类号: D693.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0X(2019)06-0108-07
收稿日期: 2019-05-29
作者简介: 吴莉娅(1978—),女,河南固始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城市化研究。
(责任编辑:温美荣)
标签:可持续人居论文; 城中村改造论文; 空间生产论文; 政府空间治理论文; 包容性治理论文; 整体性治理论文; 苏州大学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论文;
